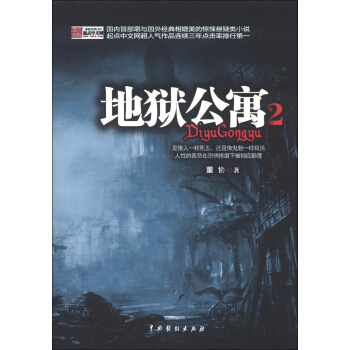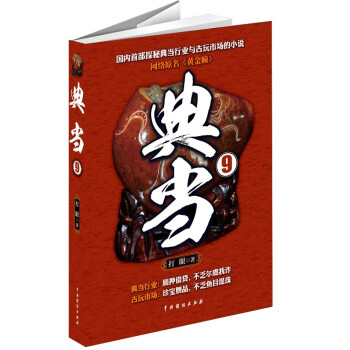![福克纳经典:喧哗与骚动 [The Sound and the Fury]](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99322/5567c536N3d1ca49c.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喧哗与骚动》是威廉·福克纳著名的作品,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它以四个人物的不同视角将一个故事讲了四遍,如同一部交响乐的四个乐章,构筑了一个立体主义的美国南方社会,其创作手法之大胆丰富,足以为一部“创作艺术教科书”,是现当代文坛罕见的大手笔。《喧哗与骚动》被福克纳认作自己“*伟大的作品”,它也是公认的福克纳小说中*精美的一部。
内容简介
《喧哗与骚动》书名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句台词:“生活就像傻子讲的故事,满是聒噪和狂怒(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小说主题也在被这句台词说中。小说分为四部分,分别由四个人讲述同一个故事。有智障弟弟班杰明完全时空错乱的心理活动;有昆汀在自杀前的种种臆想;有杰森有私利无亲情的所作所为;有黑人女仆眼中的烦扰家事。这些人以及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的另外的人,如凯蒂、父亲母亲、毛莱舅舅,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在同时发出声音,急于诉说自己的欲望、困惑、愠怒和绝望。这些声音就如同现代派交响乐中的那种乐句,如低吟和嘶吼,倾诉着人在凝滞的时间中的窒息和苦熬,此起彼伏地充满整部小说的每一页,但没有一句是和谐和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精彩书评
★福克纳以其杰出的艺术描写我们所有人的窒息,描写一个因年老而垂死的世界。——让-保罗·萨特
★你对福克纳的五体投地,其实是来源于他一个个文本对你的压迫,你甚至感觉他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没有一个作家能企及他的丰富、开阔、庞杂与统领万物。
——苏童
★再没有一个作家像威廉·福克纳这样将心和灵魂倾注于创作的世界。
——尤多拉·韦尔蒂
目录
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
1928年4月6日
1928年4月8日
附录
译后记:绕不过的福克纳
精彩书摘
1910年6月2日窗框的阴影出现在窗帘上的时候,约莫七八点钟,我又回到了时间里,又在听表了。表是爷爷的,父亲把它给我的时候说我把它给你了,你要把它当成所有希望和欲望的坟墓。你要通过它,认识到所有人类体验的reductoabsurdum——这认识让人痛苦但不可或缺。它不符合他和他父亲的需要,也未必满足你的需要。我把它给你,不是要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不时地忘掉它,不至于把力气全用在企图征服时间上。他说,人类和时间战斗从未胜过。这些战斗甚至从未发生。战场只不过昭示了人类自己的愚蠢和绝望,而所谓的胜利,不过是哲人和傻子的幻觉。
它靠着衣领盒子,我躺着,听着。是在聆听。我想不会有人刻意去听钟表的声音。也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长时间无视这个声音,可是一秒的滴答,就足以把你未曾听过的那些时间从脑海里全都调集出来。这时间排成队列,绵延不绝,渐渐消逝。如父亲说的那样,在那漫长而孤寂的光辉里,你或许能看到耶稣在行走,还有那好心的圣弗朗西斯,虽然他从来没有妹妹,口中却说着死神小妹。
隔着墙壁,我能听到什里夫的床的弹簧在响,还有他的拖鞋拖过地板的哧哧声。我起身走到梳妆台前,手从上面掠过,摸到表,将它翻过来,表面朝下,又回去睡了。但是,窗框的阴影还在,我现在几乎能据此判断时间,能精确到分钟,所以我得转过去背对着它,当它投射在身上,痒痒的,我感觉自己像过去的动物一样在后脑长了眼睛。你养成的无聊习惯往往让你后悔。父亲这样说。说基督不是钉死的:是被小小齿轮那么一分钟一分钟的滴答慢慢给累死的。耶稣没有妹妹。
当我知道自己看不见,我就开始琢磨到什么时间了。父亲说,老是考虑一个杜撰的表盘上指针的位置,是心理功能的一种病态。一种排泄,父亲说,就像出汗。我嘴里说着好吧。还琢磨。不停地琢磨。
若是阴天,我会看着窗户,思考他说的无聊习惯具体所指。想着这天气如果持续下去,对于新伦敦那儿的人来说倒是不错。难道不是吗?这是新娘结婚的好月份,声音响彻在她从镜子里直接跑出来,从那一堆香气里出来。玫瑰。玫瑰。杰森?里士满?康普森先生和夫人宣布女儿结婚。玫瑰。不像山茱萸和马利筋这般贞洁无瑕。我说我犯了乱伦,父亲,我说。玫瑰。狡猾而安详。如果你上了一年哈佛,但没看过划船比赛,那学校就该退钱。让杰森去吧。让杰森去哈佛待一年。
什里夫站在门口,在装自己的硬领,他的眼镜亮晶晶的,如有玫瑰色,就好像他脸上的光泽洗到了上面一样。“你今天上午又要逃礼拜吗?”
“有这么晚吗?”
他看了看手表。“再过两分钟就要敲钟了。”
“我不知道这么晚了。”他仍然看着手表,嘴动了起来。“我得赶紧了。我不能再逃。院长上周告诉我——”他把表放回口袋里。接着我就不说话了。
“你最好提上裤子赶紧跑。”他说。他走了出去。
我起身忙碌,隔着墙听到他的声音。他走进客厅,走向门口。
“你准备好了没?”
“还没有。你快走吧。我能赶过去的。”
他走了出去。门关上了。他沿着走廊走了过去。接着,我又听到表的声音。我停下来,到窗前把帘子拉开,看着大家跑向礼拜堂,同样的人对付着同样甩动的大衣袖子,同样的书和摆动的领子奔涌而过,如同潮水中的碎渣,还有斯波德。把什里夫说成我丈夫。得,别理他,什里夫说,他是不是傻到去追这些肮脏的小荡妇,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在南方,是处男的会感到羞耻。男孩。男人。他们都撒谎。因为对女孩来说,贞洁不贞洁关系没那么大,父亲说。他说贞洁这说法是男人发明的,而不是女人。父亲说,它就好比死亡:只是一种舍此即彼的状态,可是信不信它并不重要,他说。他说这一切的悲哀也正是这个:不仅仅是贞洁问题。我说,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她不贞。他说这也可悲;没什么东西重要到值得去改变。什里夫说,他是不是傻到去追这些肮脏的小荡妇,我说你有妹妹吗?有没有?有没有?
斯波德在他们中间,就像一只乌龟,行走在撒满枯树叶的街上,他的领子翻到了耳朵上,依然还那么不慌不忙地走着。他来自南卡罗莱纳,四年级。他们俱乐部老吹嘘,说他从来不跑着去小礼拜堂,从来不准时到,但是也从来没落下一次,另外也从来没把衬衫、袜子穿戴齐整了去小礼拜堂上课。大约到十点钟,他会走进汤普森咖啡馆,要上两杯咖啡,坐下来,趁等咖啡晾凉的时间,从口袋里拿出袜子,脱了鞋,把袜子穿上。到中午,你会看到他和其他人一样,衬衫穿好了,领子也装上了。别人都跑着打旁边经过,可是他从不会加快脚步。过了一会儿,四方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
一只麻雀斜向穿过阳光,落到窗台上,歪着脑袋看我。它的眼睛又圆又亮。它先用一只眼睛看我,然后嗖地一转头!另一只眼睛在看我了。它的喉咙抽动着,速度比任何脉搏都要快。整点报时的钟响了。麻雀不再转头了,直直地一只眼睛看我,直到那钟的尾音消失,仿佛也一直在聆听。接着,它展翅从窗台上飞走了。
最后一次敲钟的尾音过了好一会儿才消失。它长久地留在空中,与其说让人听,不如说是在让人感觉。像那绵长将熄的光辉之中,耶稣和圣弗朗西斯谈论他妹妹时响过且仍然不绝于耳的所有钟声一样。因为,如果只是下地狱,如果这便是一了百了,那该有多好。结束了。如果一切自我了断。那儿只有她和我,没有其他人。如果我们能做点可怕的事来,让他们都吓得逃离地狱,只剩下我们俩。我犯了乱伦我说父亲那是我不是道尔顿?埃姆斯。当他把枪放道尔顿?埃姆斯。道尔顿?埃姆斯。他把枪放在我手里,我没有动手。我就是为着这个原因没去动手。他会下地狱,她会,我也会。道尔顿?埃姆斯。道尔顿?埃姆斯。道尔顿?埃姆斯。如果我们能做出点可怕的事来父亲说这也很可悲人做不出那么可怕的事情他们根本做不出可怕的事情他们甚至今天看来可怕的事第二天就想不起来了然后我说,你可以逃避一切啊他说,啊是吗。我会向下看,看着我那喃喃自语的尸骨看着那深深的河水,河水像风一样,如同风做的屋顶,很久以后,他们甚至无法分辨哪里是尸骨,哪里是孤寂的未受污损的河沙。直到有一天,主说起来吧只有铁熨斗能浮起来。这时重要的不是你意识到什么都帮不了你——宗教,骄傲,任何东西——而是你意识到自己不需要任何帮助。道尔顿?埃姆斯。道尔顿?埃姆斯。道尔顿?埃姆斯。如果我是他的母亲,躺着摊开手脚抬起身子笑着,搂着他的父亲,我的手半挡着,眼睛看着,看着他在获得生命之前就已经死去。突然间,她站在门口了。
我走到梳妆台前,拿起那只反扣着的表。我将表的玻璃罩子在梳妆台一角磕碎手接住那玻璃渣放到烟灰缸里将指针扭掉放入烟灰缸。表接着滴滴答答。我把表正过来看,空白的表盘,后面的小轮子不知已经发生的变故仍在滴答作响。耶稣在加利利水面行走,华盛顿不说谎。父亲从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带回一只表坠送给杰森:小小的观剧望远镜,你眯上一只眼睛往里看,能看见一座摩天大楼,一座蜘蛛织网一样辐射开的摩天轮,还有针头大小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表盘上有处红污点。看见它时我的拇指开始疼痛。我把表放下来,到了什里夫的房间,拿了些碘酒,涂在伤口上。我用毛巾把剩下的玻璃渣从梳妆台边上扫掉了。
我拿出两套内衣、袜子、衬衫、硬领和领带,放进箱子里。我把我的一切都放进去了,除了我的一件新外套一件旧外套,两双鞋子,两顶帽子,还有我的书。我把书拿进起居室堆在桌子上,我从家里带来的还有父亲说,过去人们是看一个人的藏书判断他是不是绅士,而今是看没归还的书来判断我把箱子锁上,写上地址。一刻钟的钟声响了起来。我停下来听,直到余音消散。
我洗了澡刮了胡子。水让我的手指又痛了,所以我又涂了些碘酒。我穿上新外套,戴上表将另外一只箱子装好把一些零碎物件我的剃须刀还有牙刷等放入手提包,将箱子钥匙卷进一张纸里放入信封,写上父亲地址,写了两张条子,然后封入信封。
阴影还没有完全离开门口的台阶。我在门口停住,看着阴影移动。它以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移动,缓慢地退回门里,把屋子里的阴影赶了回去。可是我听见的时候,她已经在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镜子里她已经在奔跑了。跑得很快裙后摆都飘了起来缠到她的手臂上她像一片云跑出了镜子,她的面纱旋动着发出长长的闪光她的鞋跟声音清脆步子快捷她用另外一只手将裙子按在肩膀上,跑出了镜子那玫瑰玫瑰的气息那在伊甸园上方发出的声音。然后,她穿过门廊我听不到她鞋跟的声音了,接着在月光下就像一片云,面纱飘动的影子从草地上掠过,进入那吼声里。她跑着,裙子飘到身后,手抓着婚纱,跑向那吼声中,T。P。在露水里沙士汽水好哎班吉在箱子下头嚷嚷。父亲一起一伏的胸前挂着个V形银胸甲。
什里夫说:“嗯,你还没……这究竟是去参加婚礼还是葬礼?”
“我没去成。”我说。
“你这一通梳洗打扮,去得成才怪。怎么回事?你以为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偶尔穿一回新买的正装,不会有警察来抓我吧。”我说。“我在想着广场上那些学生。他们会认为你去了哈佛。你是不是傲得课也懒得去上了?”
“我先吃点东西吧。”台阶上的阴影消失了。我走进阳光里,又找到了我的影子。我沿着台阶走下去,影子紧随身后。半小时过去了。接着,钟声停了,余音慢慢消散。
执事也不在邮局里。我把两个信封贴上邮票,一封寄给父亲,什里夫的那封信我放在衣裳口袋里,然后我想起上次是在哪里看到执事了。那一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他穿着G。A。R。军装,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如果你多等一会,无论是在哪个角落,你总会看到他出现在某个游行队伍里。前一次是在哥伦布或加里波第或其他什么人的诞辰纪念日。他在“清道夫”组,戴着烟囱帽,拿着一面两英寸的意大利国旗,在扫帚铲子之间抽着雪茄。不过,最后一次,一定是穿G。A。R。军装的那次,因为什里夫说:
“瞧瞧。看你爷爷把这老黑鬼给收拾的。”
“是的,”我说,“现在他天天去参加各种游行都成。要不是我祖父,他得像白人一样去干活。”
我哪儿都没见他。但我连个能召之即来的靠干活吃饭的黑人都没见过,更不要说吃国家闲饭的黑人了。一辆汽车开过来。我进城去了帕克餐馆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了时钟打点。但是我想需要用起码一个小时才能忘记时间。人类开始进入机械式时间推算的过程比历史都要长。
吃完早饭我买了一支雪茄。那女孩说,五毛钱一支的雪茄最好,所以我买了一支,点着,走到街上。我站在那里,抽了几口,然后拿在手里,向着角落走去。我穿过一家珠宝钟表店的橱窗,不过及时把目光挪开了。在拐角处,两个擦皮鞋的缠住了我,一边一个,声音刺耳,沙哑,像是乌鸦。我把雪茄给了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我给了一枚五分钱硬币。他们这才不再缠我了。拿雪茄的那个想把雪茄卖给同伴,换他那五分钱。
有个时钟,在阳光下高高挂着,我在想怎么回事,为什么心里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身体却还要骗我们去不自觉地做。我能感觉到后颈上肌肉的动作,接着又听到了口袋里表的滴答,过了一会儿,所有声音我都避而不听,只留下口袋里的表,滴滴答答。我在街上转过身,走到橱窗前。店里那人在窗后的桌子前忙活着。有些谢顶了。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那是一个嵌进他面孔的金属管。我走了进去。
整个地方到处都是滴答声,就如同九月草地里的蟋蟀,我能听到他头顶上一口大钟的声音。他抬起头,眼睛大而模糊,简直要从镜片后冲出来。我把自己的表拿出来递给他。
“我把表弄坏了。”他把表拿在手里翻看。“的确。肯定是踩到了。”“是的,先生。我把它从梳妆台碰了下来,黑灯瞎火地又踩了一脚。不过它还在走。”他把后盖撬开,眯着眼睛看。“好像没事。不过,我得查查才能说得准。我下午看看吧。”“那我迟点再回来拿。”我说,“能不能请问一下,这橱窗里哪只表走得准?”
他把我的表放在掌心抬头用那模糊的要鼓出来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一个家伙打过赌,”我说,“另外,我早上忘了戴眼镜。”“嗯,好吧。”他说。他放下表,从凳子上略起身,目光越过柜台看过去。然后,他又抬头看看墙上。“是二十一。”
“不要告诉我,”我说,“拜托了,先生。就请说说有没有一个是准的。”
他又看了看我。他坐回凳子上,把放大镜推到额头上。他的眼睛周围留下了一个红圈,镜子一拿开,一张脸显得赤裸裸的。“今天是什么庆祝活动?”他问,“划船比赛下周才有,不是吗?”
“不是的,先生。我这只是一次私人的庆祝活动。是过个生日。有哪只表比较准么?”“没有,不过那是因为没有对好。如果你想买一只的话——”
“我不买,先生。我不需要手表。我们客厅里有钟。我要表的话,把这只修好就行了。”
我伸出手。
“最好还是现在丢下来。”
“我回头再拿过来。”他把表给我。我把它放进口袋里。在别的表的滴答声中,我这表的声音终于听不见了。“非常感谢你。但愿没占你太多时间。”
“没事。你准备好了拿来就行。你那庆祝活动最好推迟一下,等我们赢了船赛再说。”
“好的,先生。我看这样最好。”
我走了出去,把那些滴答声关在门后。我回头看了看橱窗。他在柜台后看着我。橱窗有十二三只表,十二三种不同的时刻,每只都带着同样的坚决和互相矛盾的确信,就和我这只连指针都没有的表一样。互相矛盾。我能听到我的表在走,在口袋里滴答,哪怕没人能看见,哪怕看了也是白看。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就用这表的时间吧。父亲说,钟表杀死时间。他说,只要那小小的齿轮在转动,让时间滴滴答答流逝,那么时间就是死的,只有在钟表停转的时候,时间才会活过来。指针伸展着,略略上翘,如同迎风侧飞的海鸥。心中装满旧日的苦水,如同新月装满雨水一样,黑鬼们说的。珠宝钟表店老板又忙了起来,弓腰站在台子前,金属管嵌在脸上。他梳着中分头,发缝线一直伸向秃斑,那里如同十二月排干了的沼泽。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如果非要用一个比喻,我会说这本书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发生在南方庄园里的心理实验。那些人物,他们被困在各自的时间循环和无法言说的痛苦之中,每一次尝试挣脱,似乎都只会让他们陷得更深。我特别留意了那些关于“逝去”和“记忆”的描写,它们不是清晰的闪回,而是更像是幽灵般的存在,渗透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那种挥之不去的颓败感和无可挽回的失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你读到的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而是他们如何感知和处理这些事情。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私密性。我们像是闯入者,窥视着他们灵魂深处最脆弱、最不堪的一面。这种对人物内心深处近乎残酷的解剖,让人既感到不适,又无法自拔地想要继续阅读下去,去见证这种精神上的慢性腐蚀。
评分天哪,这本书简直是文字的迷宫,初读时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团浓稠的、带着南方潮湿气息的迷雾里。那些句子,那些视角,它们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更像是在你耳边低语、在你脑海中闪回的碎片。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勉强抓住一点故事的轮廓,但即便如此,那种抓不住、影影绰绰的感觉却成为了阅读过程中最深刻的体验。它不是那种能让你一口气读完,然后合上书本,拍拍手说“啊,明白了”的作品。相反,它要求你放慢速度,甚至需要反复咀嚼那些看似不连贯的段落。你会发现,作者似乎故意打乱了时间的逻辑,让你在不同的心智状态和生命阶段之间跳跃。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真的感到一种强烈的眩晕,仿佛自己的意识也被拉扯进了角色们混乱的内心世界。这绝对不是一部轻松愉快的读物,它像一块粗粝的石头,需要你用耐心和专注去打磨,才能从中发现那些深藏不露的光泽。那种阅读的“难度”,反而成了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想知道这表象之下的真实结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处理,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反叛。我很少读到一部作品,能如此彻底地打破时间的一致性,却又能奇妙地在读者心中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内在的时间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页你会跳到前一年,还是仅仅跳到前一个小时的心灵活动中。这要求读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叙事线索来导航。它更像是一首复杂的交响乐,不同的声部——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时间点——不断地交织、碰撞,最终汇集成一种令人震撼的整体效果。当最后那个清晰了一些的片段出现时,那种感觉不是“解谜成功”,而更像是在暴风雨后,云层短暂地分开,让你瞥见了片刻宁静的真容。这不依赖于外部事件的推动,完全是精神世界的内部涌动所驱动的叙事,非常罕见。
评分我得说,这本书的语言密度高得惊人,简直可以用“颗粒感”来形容。每一个词语似乎都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含义的重量。我试着在咖啡馆里读,结果发现周围的喧嚣完全被书中的那种内在的、更为剧烈的“骚动”所取代。它不是通过情节的跌宕起伏来制造紧张感,而是通过句法结构和意识流的运用,直接冲击读者的认知边界。有几次,我不得不停下来,深吸一口气,重新组织我接收到的信息。这感觉就像是试图理解一幅立体派的画作,你看到的是各个角度的重叠,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固定的形象。这种写作手法,虽然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也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它强迫你放弃传统的线性思维,去拥抱一种更原始、更混沌的情感和记忆的表达方式。读完一个章节,我常常需要花几分钟时间“恢复正常”,才能确保自己没有把书中的情绪残留到现实生活中去。
评分坦白讲,这本书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经历”的。它带来的阅读感受是如此沉重、如此复杂,以至于我需要找其他更轻快的作品来“中和”一下。但即便如此,书中的某些意象和场景,却像烙印一样留在了我的脑海中,时不时地会跳出来,提醒我曾经经历过那样的阅读深度。它探讨的那些关于家族衰落、男性责任的缺失以及身份认同的挣扎,都是如此深刻和永恒的主题,只是它们被包裹在一种极度实验性的外壳之下。这本书无疑挑战了文学的既有范式,它不迎合任何人,只忠实于它自己构建的、扭曲而又真实的内心世界。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了全新的认识,它证明了叙事远不止于情节的排列组合,它更是一种对人类意识复杂性的终极探索。
评分多看书 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 让心灵饱满 让灵魂丰富。
评分不错,货真价实,值得信赖!
评分很好的一本书
评分发货迅速,包装专业,开卷有益。
评分书质量很好,慢慢阅读
评分还没仔细看,朋友推荐的书籍,一次购入很多书,打算从此静心读书,修身养性
评分大赞,物流很快!很喜欢!信任京东,很愉快的购物体验!
评分福克纳的经典,必读的书目。
评分送给爱米丽一朵玫瑰花死活没货啊,京东你叫我怎么办?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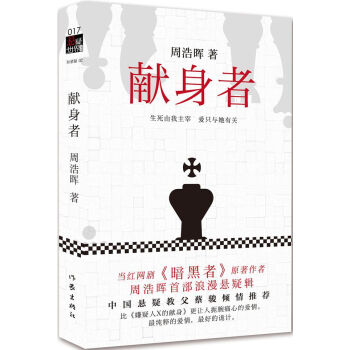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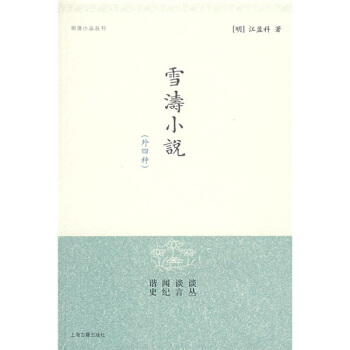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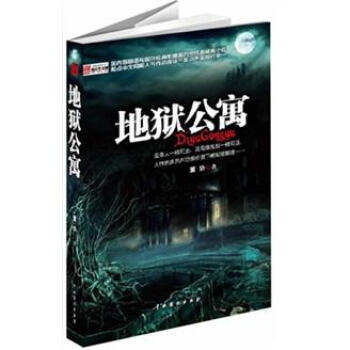



![华生手稿:罪恶的艺术 [Art in the Bloo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8299/58117e6cN026dc721.jpg)


![脸上的门,口中的灯 [The Doors Of His Face,The Lamps of His Mouth and Other Stor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396566/5a659c1eN7f84e6d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