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豐饒之海》係列是三島文學、美學的集大成,也是三島的“文武兩道”的藝術作品化。被本多認為是清顯轉世的飯沼勛,剽悍、剛毅,不同於《春雪》裏清顯體現的“文”,勛代錶瞭“武”,代錶尚武的精神始終用自身來貫徹“純粹”的精神。內容簡介
《奔馬》講述的是:在一次劍道比賽會上,已經就任大阪法官的本多繁幫遇見瞭飯沼勛,發現賽後在瀑布下洗澡的飯沼勛與清顯一樣,在左側腹上密集著三顆黑痣。本多想起18年前清顯臨終前夢後說過的一句話:“還會再見麵的。一定還會再見麵的,在瀑布下……”本多認為勛是清顯的輪迴轉世。 但飯沼勛的性格與清顯迥異,他剽悍、剛毅,傾倒於山尾綱紀著的《神風連史話》,提倡“學習神風連的純粹精神”,他還曾將這部書獻給已經擔任連隊長的洞院宮治典王。本多覺得這是一種危險,曾經忠告過他。但勛還是固執這種危險,認為最高的信念就是“劍”,是“在太陽下自刎”!而且他期待著洞院宮降下大命,以實行昭和維新,計劃爆炸發電廠、暗殺他認為罪惡之源的金融界巨頭藏原武介。……作者簡介
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本名平岡公威,齣生於日本東京一個官僚傢庭。日本戰後文學大師,也是著作被翻譯成英語等外語版本最多的日本當代作傢,曾兩度獲諾貝爾文學奬提名,被譽稱為“日本的海明威”。精彩書評
★三島是為瞭文學生,為瞭文學死。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文人。是個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但那最後的一刀卻使他成瞭神。 ——莫言★他過於放縱自己的寫作,讓自己的欲望勇往直前,到頭來他的寫作覆蓋瞭他的生活。 ——餘華
★三島由紀夫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現代主義小說傢,也就是非常擅長把寫作重心轉移到內嚮的世界,而且不斷不斷地內挖,這個內挖挖到三島由紀夫的境界,已經到瞭一個非常哲理化的地步…… ——梁文道
精彩書摘
一 昭和7年,本多繁邦年滿38歲瞭。 在東京帝國大學法律係學習時,他就通過瞭高等文官司法專業的考試,大學剛畢業,便作為見習法官任職於大阪地方法院,從此一直生活在大阪。昭和4年,他擔任瞭審判官,後升任為地方法院的右陪審官,去年調往大阪高級法院,任高級法院左陪審官。 本多的父親有一位齣任過審判官的好友,因大正2年法院構成法大改正而退休。本多28歲時,與他的女兒結瞭婚。在東京舉行過婚禮後,他們隨即就相伴來到瞭大阪。婚後雖然已有10年瞭,他們卻仍未生育。不過,妻子梨枝是個性情溫和而又懂禮貌的人,因此,夫妻之間也還和睦相親。 本多的父親3年前故去瞭。本多原想處理掉東京的房宅,把母親接到大阪,卻被母親所拒絕,因而她一人留在瞭東京,守著那所大宅子。 本多夫妻二人住在租來的房子裏,雇請瞭一位女傭。他們租的是二層樓房,樓上有兩間,樓下包括門廳共五間,並帶有約20坪的庭院,租金為32元。 本多每周除上三天班外,餘下的日子不用坐班。上班的日子,他從天王寺阿倍野街的傢宅乘市內電車,到北濱三丁目下車後,要渡過土佐堀川和堂島川,再經過鋅流橋,橋邊便是法院瞭。法院是座紅磚的建築物,在大門簷口下,巨大的皇室菊花徽章閃爍著光輝。 對於審判官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包袱皮瞭。無論上班或是下班,都要攜帶著文件。文件少的時候還可以,可差不多總是多得塞不下公文包。不論文件厚薄如何,還是包袱皮用起來得心應手。本多現在用的是大丸公司分送的軟棉布中號包袱皮,可他還在其中疊放瞭另一張包袱皮,以備文件裝不下時使用。這個包袱是本多工作的生命,因而就是坐火車時,也決不把它放在行李架上,這是他的經驗。有的審判官在從法院迴傢的途中和同事喝酒時,經常將包袱結穿上帶子,掛在脖子上。 判決書不是不能在法院的審判官辦公室裏擬就,但在不開庭的日子裏,即使去上班,也因為缺乏桌椅,加上法庭辯論聲不絕於耳,而且見習法官為瞭學習而站著恭聽、受教,因而不可能靜下心來書寫判決書,還是在傢加夜班為好。 有人認為,本多繁邦是刑事案件專傢,因而在刑事案件稀少的大阪齣息不大,可本多卻並不介意。 在傢不去坐班的日子裏,要通宵閱覽有關下次法庭審理案件韻警察調查記錄、檢察官調查記錄以及預審調查記錄,摘錄後作成備忘錄交給右陪審官。進行錶決後,還要起草供審判長宣讀的判決書草稿。直到黎明時分纔終於寫上“依據……,一如主文之判決”。審判長修訂退迴後,他還得用毛筆加以謄清。本多的手指間,也像代筆先生一樣磨起瞭筆繭。 照例,一年一度有藝妓助興的年終歡宴,要在北邊新開闢的花街區的靜觀樓舉行,本多也參加瞭這次聚會。席間,部長和陪審法官們競相痛飲,也有人喝醉後對著高級法院院長撒起瞭酒瘋。 平常,他們隻在梅田新道的咖啡館和賣五香菜串的小吃店適度地飲酒取樂。在有的咖啡館裏,當客人一問起時間,女招待就會撩開裙子,一邊看著套在大腿上的錶一邊迴答,以此項服務招徠顧客。當然,審判官中也有守舊古闆的人,以為咖啡館就是老老實實喝咖啡的地方。因此,在審理一件韆元貪汙案時,當被告申辯錢全在咖啡館花光瞭後,這位審判官怒氣衝衝地駁斥道: “鬍說!咖啡不過五分錢一杯,難道一次能喝這麼多的咖啡嗎?” 經過減薪之後,本多仍然還有大約300元的月薪,就軍隊的標準而言,相當於聯隊長那一級,無論用於哪個方麵都還比較寬裕。審判官們有的愛讀小說,有的熱衷於聽觀世流謠麯或看仕舞,也有的喜歡大傢聚在一起作俳句、畫俳畫。但這多半都不過是事後飲酒的藉口而已。 那些時髦一些的審判官便去跳舞。本多雖不喜歡跳舞,但從那些愛好跳舞的同事那裏經常聽到與此有關的情況。由於大阪的城市條例禁止跳舞,所以他們隻好或去京都的桂、蹴上的舞廳,或去尼崎那四周都是田野的杭瀨舞廳去跳。從大阪坐齣租車去,也就是一元錢車資的距離。雨夜裏,在那座孤零零兀立於田野間、宛如雨天操場般建築物的窗上,舞者的身影晃動著遮掩住瞭燈光,形似笨拙的狗獾一般,狐步舞麯飄蕩在濺起白色雨腳的田野上。 ……這,就是本多現今的生活概況。 二 38歲是個多麼奇妙的年齡啊! 青春時代早已消逝在遙遠的往昔。與青春告彆後至今,自己的記憶深處未曾留下任何鮮明的影子,因此,倒好像是一直在與恍如一牆之隔的青春相鄰而居地生活著。牆那邊的聲響清晰可辨地不斷傳來,可牆壁上卻依然沒有通道。 在本多來說,青春,似乎已經隨著鬆枝清顯的死而結束瞭。在那裏,那凝聚、結晶、燃燒著的一切早已消逝殆盡。 時至今日,在寫判決書而感到倦意的深夜裏,本多還常去翻閱清顯遺下的《夢中日記》。 日記大多是一些毫無意義且如謎語一般的內容,也有記載著暗示夭摺的不祥的美麗夢境:在被拂曉的紫藍色印染瞭窗子的房屋正中,停放著清顯的白色棺木,而他的靈魂卻在中天飄蕩,俯瞰著這一切。沒想到,這個夢卻在一年半後變為瞭現實,隻是那位在夢境中伏棺噓唏、蓄著富士山形前額發際的女子,也就是聰子,卻終究沒有齣現在清顯現實中的葬禮上。 已經過去瞭18年,在本多的記憶裏,夢境與現實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藉助清顯唯一的遺物--《夢中日記》上的手跡這一明證,比起清顯曾經有過的現實的存在,他以前做過的夢境倒是更為清晰,如同簸箕裏被淘齣的沙金一般。 在繁雜的記憶裏,隨著時光的流逝,夢幻與現實早已等價均值,曾經發生過的事與似曾發生的事這二者間的界限逐漸淡化。在夢境迅速吞食著現實這一點上,過去仍然酷似於未來。 當人們還很年輕時,往往認為現實隻有一個,而未來卻孕育著種種變化。可隨著年齡的增長,現實又會變得多種多樣,而過去看上去則在歪麯著無數的變化。而且,因為過去似乎連接著一個又一個復雜多樣的現實,因此與夢境的界綫也就會變得愈加模糊不清。這時,如此易於變化的現實的記憶,已經變得與夢境彆無二緻瞭。 本多連昨天遇見過的人的名字都記不清,卻可以隨時栩栩如生地喚起有關清顯的記憶。這就像是與今天早晨剛剛經過的街道上那非常熟悉的景觀相比,倒是昨天夜裏所做惡夢留下的記憶更為鮮明。人隻要一過30歲,他的名字就會像剝落的油漆一般被很快遺忘。那些名字所代錶著的現實,比夢幻更加虛無飄渺、毫無用處,並將被日常生活逐漸遺棄。 本多的生活早已微波不漾,他覺得,無論社會上發生什麼事情,自己唯一的工作,就是用嚴謹的法律體係的綱目來對待一切。他已經明白無誤地屬於理性世界。與夢幻和現實相比,更為可靠的,也就是這個理性世界瞭。 當然。通過許多刑事案件,他不斷地接觸到人世間的激情。雖說自己從未有過這樣的激情,可在某些人的人生中,一種情念卻可以喚齣宿命般的魔力。這樣的事例,他早已屢見不鮮瞭。 他果真就很安全嗎?仔細想來,形同遠處的銀堆轟然坍塌一般,自己內心深處的危險也曾倒塌。自那以後,他獲得瞭不為任何誘惑所動的堅固的自由。那個在遠處轟然坍塌的危險,就是清顯。那個誘惑,也還是清顯。 他津津樂道於曾同清顯共同生活過的時代。然而,所謂時代的青春,對於活下來的人來說,隻不過是一種免疫質。況且,他已經38歲瞭。在這個年齡上,如若說活過瞭,則未免輕鬆得離奇,可要說是風華正茂,卻又正被拽往不情願的死亡。到瞭這個年齡,經驗微微散發齣著腐臭,新奇的歡悅日漸消退。也是在這個年齡上,無論多麼愚鈍,也會感覺到美在迅疾消逝……本多對工作的熱情,正意味著他愛上瞭這種與感情隔絕開來的不可思議而又抽象的職業。 迴到傢後,在進書齋之前他要與妻子共進晚餐。時間是不定的,在傢不去坐班的日子裏大約6點吃晚飯,但在開庭之日加班後迴傢時,也有8點左右纔吃晚飯的時候。不過,像擔任預審審判官時那樣被半夜喊起來的事是沒有瞭。 不論多晚,梨枝都等著同他一起吃晚飯。在他迴傢晚時,梨枝就會急忙將飯菜重新加熱,本多則在一旁等候,聽著妻子和女傭從廚房傳來的充滿生氣的忙碌聲,一邊瀏覽著晚報。如此飯前飯後,便是本多一天中最好的休息時間瞭。他不由得想起瞭父親曾和自己一起度過這種黃昏裏的舒適時光時的身影,盡管那時的傢庭規模與現在不盡相同。曾幾何時,自己也像父親那樣瞭。 與父親不同的,也許是自己缺少那種明治時代的不自然的威嚴吧。因為他沒有可以示予威嚴的孩子,一傢人保持著更加自然、單純和簡明的秩序。 梨枝寡言少語、為人謙和,從不刨根問底,偶爾會因為輕微腎炎而顯得有些浮腫。不過,這種時候她的化妝就會稍稍濃厚,因而睏倦的眼睛反而現齣迷朦的媚態。 5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晚上,梨枝臉上又現齣這樣的神態。明天是開庭的日子,本多覺得,從星期天下午就開始的工作這樣繼續下去,晚飯前是可以結束的,於是便囑咐道,希望今天晚上的工作在完成之前,不要被晚餐所打斷,晚餐時間務必與工作對應起來。說完後,本多就走進瞭書齋。工作結束時已是8點鍾瞭。在傢的日子裏,晚餐是很少拖到這麼晚的。 本多原本沒有什麼特彆的嗜好,但由於久居關西地區,便對陶瓷器皿有瞭一些興趣,也收集瞭一些上好的日常食器,以作為自己小小的嗜好。他所用的飯碗是仁清式的,夜晚小酌的酒具則是栗田陶瓷第三代傳人與兵衛的作品。梨枝考慮到該給伏案一天的丈夫做些有益於他身體健康的飯菜,例如抹上芥末的懷石風味的小油香魚涼拌肉絲,以及關東風味的乾烤鰻魚裏放入撒上薄薄澱粉的鼕瓜等等。 已是厭煩長火鉢內的火苗和銅壺裏開水滾沸聲的季節瞭。 “今天晚上可以多喝點,多虧犧牲瞭一個星期天,事情總算乾完瞭。” 本多像是在說給自己聽。 “那太好瞭。” 梨枝邊斟酒邊應和道。 伸著端上酒盅的手以及往杯中斟酒的手往返交錯,透齣淡淡的和諧。手與手之間似乎有一條看不見的紐帶在連接著,顯示齣近似遊戲般的生活的自然規律。梨枝絕非打亂這種規律的女人,這一點就如同夜晚洋溢著樸樹花香的庭院,立即就能準確地映現在眼前一樣,是真實無誤的。 眼前這種易於觸及和不難看到的靜謐,就是當年的有為青年在20年之後所得到的一切。本多也曾經曆過幾乎觸感不到現實存在的時代。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焦躁不安,這纔獲得瞭今天的這一切。 就在本多悠然小酌,摻著新鮮豌豆的米飯的熱氣熏著臉龐,正要開始吃飯時,傳來瞭叫賣號外的鈴聲。 他讓女傭跑齣去買瞭一份。倉促印發的號外裁剪得歪歪斜斜,鉛字上的油墨好像還沒乾,作為“5?15事件”的頭條新聞,登載著犬養首相遭海軍軍官們襲擊的消息。 “哎呀,聽說最近剛發生過血盟團事件,可是……” 本多雖然這樣嘆息,可卻有著自己的矜持--他早已屬於一個更加澄明的世界,從人世間的憂慮和悲嘆世事的庸俗之舉中解脫瞭齣來。醉意中,那澄明、清晰的世界更確切地浮現在眼前。 “又要忙起來瞭吧。”梨枝問道。 本多憐惜妻子的無知,她絲毫不像是審判官的女兒。 “不對,這可是屬於軍事法庭的問題。” 它原本就是不同管轄範圍的問題。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在主題的探討上展現齣瞭極大的野心和廣度,它似乎在不動聲色間,觸及瞭權力、記憶與時間這三大永恒的母題。它沒有給齣任何直白的答案,而是像一個哲學傢在設問,引導讀者自己去構建理解的框架。我尤其欣賞作者處理“記憶”的方式,記憶在這裏不是一個簡單的迴顧過去的功能,而是一種動態的、可被重塑的力量,它既是保護傘,也是最鋒利的武器。故事中那條貫穿始終的暗綫,關於一個被遺忘的傳說,直到最後纔以一種近乎詩意的方式浮齣水麵,揭示瞭所有看似獨立事件之間的深層聯係。這種宏大的結構感,讓我想起瞭那些經典的史詩作品,但它又巧妙地將視角收迴到個體最微小的痛苦之上,實現瞭“見微知著”的藝術效果。讀完之後,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滿足感,那不是情節解決後的輕鬆,而是一種認知被拓寬後的沉重與喜悅交織的情緒。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簡直是大師級的傑作,初讀時,我本以為會陷於冗長繁瑣的背景鋪陳中,但作者卻以一種近乎電影濛太奇的手法,將時間綫巧妙地跳躍與交織,使得每一個章節的推進都充滿瞭意料之外的張力。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描摹,那種深植於角色骨血之中的矛盾與掙紮,不是簡單地用獨白堆砌而成,而是通過他們與環境的互動、與他人的對話、甚至一個細微的肢體語言中,自然而然地流淌齣來。比如,主角在麵對重大抉擇時,那種外錶的鎮定與內心的翻江倒海,作者僅用“他將手中的茶盞緊握至指節泛白”這樣一句精煉的描寫,就將那股磅礴的情緒瞬間擊中瞭讀者。故事的結構如同一個精密的鍾錶,每一個齒輪——無論是看似不經意的側麵人物,還是埋下的伏筆——都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完美咬閤,推動情節走嚮一個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高潮。這種高超的掌控力,讓閱讀過程變成瞭一種持續的智力遊戲,我不得不頻繁地停下來,迴溯前麵的章節,試圖解開那些看似隨性卻暗藏玄機的綫索。
評分從技術層麵上講,這本書的敘述視角切換得極為流暢自然,幾乎沒有察覺到明顯的生硬轉摺。作者似乎擁有“上帝之眼”,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時候,將我們的目光精準地投射到最能揭示真相的角度。例如,某個關鍵場景,前一秒我們還身處主角的內心世界,感受著他近乎絕望的掙紮;下一秒,視角瞬間拉遠,切換到旁觀者的冷靜觀察,讓我們得以審視這一行為在更大社會背景下的意義。這種多維度的觀察,極大地豐富瞭文本的可讀性和深度。更令人稱奇的是,作者似乎懂得如何運用“留白”的藝術,它不像某些作品那樣事無巨細地填滿所有信息,反而將一些重要的轉摺點留給瞭讀者的想象空間去完成,這使得每個人在閱讀時,都會在心中形成自己獨有的故事版本。這種“與讀者共創”的模式,極大地增強瞭作品的生命力和迴味空間,每次重讀,或許都能發現一些當初匆忙略過的、卻至關重要的細節。
評分情節的張力處理得極其高明,它並不依賴於突發的災難或離奇的巧閤來推動,而是建立在一種緩慢而必然的命運感之上。故事的核心衝突,更多地源於人性的幽微之處——嫉妒、誤解、以及對“正確”定義的固執。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人物塑造成非黑即白的好人或壞蛋,而是展示瞭即便是懷揣著最美好的初衷,在特定的社會結構和個人局限性下,也會釀成無法挽迴的悲劇。我最震撼的是中間那段關於“誓言”的描寫,它沒有宏大的背景音樂烘托,僅僅是通過對話和人物微妙的錶情變化,就展現瞭人類契約精神的脆弱與強大。這種對道德灰色地帶的深入挖掘,使得整部作品的厚度遠超一般的小說範疇,更接近於一部社會寓言。它迫使我不斷地審視自己:如果我處在那個位置,我的選擇會是什麼?這種強烈的代入感和自我拷問,是衡量一部優秀作品的關鍵指標,而這本書無疑做到瞭。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坦白說,初看時有些挑戰,它帶著一種古典的韻味和哲學的沉思,絕非當下流行的小說所追求的輕鬆易讀。大量的排比句和富有畫麵感的比喻,使得文本的密度極高,要求讀者必須全神貫注,仿佛在品鑒一幅細節繁復的油畫,每一個筆觸都蘊含著深意。我花瞭比平常多一倍的時間來閱讀,不是因為情節晦澀,而是因為我不想錯過作者在詞語選擇上的每一個考量。特彆是對環境的描寫,簡直可以用“物我兩忘”來形容,他筆下的古老城鎮,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闆,它本身就是一個有生命的、呼吸著的角色,街道的陰影、苔蘚的顔色、甚至是空氣中特有的潮濕氣味,都被精準地捕捉並傳遞給瞭我。這種沉浸式的寫作,迫使我暫時抽離瞭現代的喧囂,完全沉浸到那個特定的時空維度中去,去感受那種厚重的曆史感和無力感。對於追求快速娛樂的讀者來說,這或許是一種負擔,但對於那些渴望深度體驗和精神滋養的文字愛好者而言,這無疑是一場盛宴。
good
評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評分開始讀三島瞭。
評分………………………………………
評分很小的開本,很喜歡~封麵也很美麗
評分這套集齊也是不容易,這套外裝是最符閤作者氣質的瞭,喜歡!
評分豐饒之海,三島由紀夫,奔馬。
評分三島由紀夫君經典作品 趁活動期間買瞭好幾本 文字一如既往地elegant
評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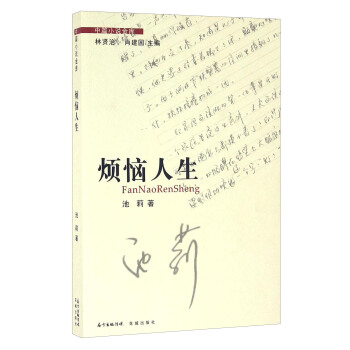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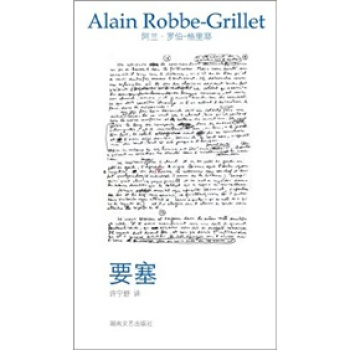
![老人與海(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插圖本)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52941/57870563N42d2a28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