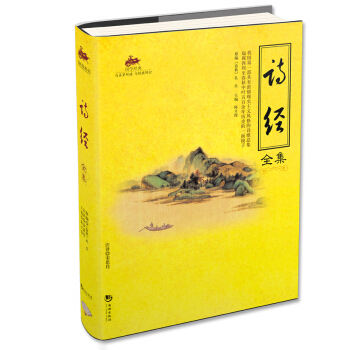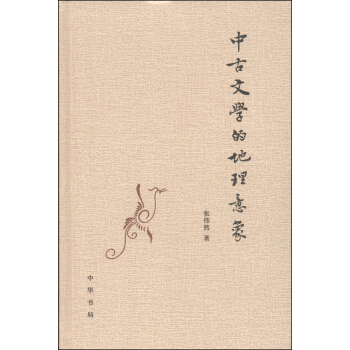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不过相对而言,《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现在略陈《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的学术构想。
一、“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
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汉》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
限于时间和精力,《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同时,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内容分四部分,围绕的是“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一般情形,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例如,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特指”与“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指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西汉水”,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汉,因之可称“江汉”。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而全然不顾“江汉”、“吴”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三、“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
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其中视角比较独特,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相关研究都很少;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特别是关于“潇湘”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潇湘八景,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毕竟非其研究主旨;而关于“潇湘”语汇的探讨,则必然要对“潇湘”意象进行分析。
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从文学角度探讨“潇湘”意象,虽然也不能不考量“潇湘”作为地理实体,但目标还是其中的“意”,如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①。而《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关键是考察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
在中古文学中,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
四、“‘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
毋庸赘言,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颠覆、转化的过程。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更受制于文化取向、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环境产生刺激,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
中古以前,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诗》三百虽然以“关关雎鸠”开篇,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而且,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诗中有“鸟言”,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因而,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山水诗。中唐以后,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酝酿到北宋,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
目录
前言一、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思维传统
二、从文化水平、文化面貌到地理感知
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学术构想
第一章 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
一、关于感觉文化区
二、华夷之界:唐代中华文化的空间范围
三、山川之异(上):北方各区
四、山川之异(下):南方各区
五、唐人对于文化地域的感知
第二章 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
一、杜诗中的“江汉
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
三、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的再讨论
四、《柳毅传》中的“洞庭
第三章 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
一、“巫山神女”的生成环境
二、“潇湘”的意象及其流变
三、“竹林寺”与“桃花源
第四章 “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
一、关于禽言诗的一段学术公案
二、古人笔下的鸟禽言语
三、“鸟言”与其特定的生态
四、“禽言”兴起的时空过程
五、禽言诗的生态背景
六、环境刺激与文化感应
七、从地理交流到生态发现
结论
一、地理经验与本土问题
二、学科间的互济
地图
图1-1 唐代文化区域意象图
图1-2 唐代十道图
图2-1 杜甫在南方主要活动空间
图2-2 《上安州裴长史书》空间逻辑示意图
图2-3 柳毅传书空间示意图
图3-1 湘江水系图
图4-1 十五国风图
图4-2 汉代方言分布图
图4-3 五藏山经地域范围图
图4-4 历代禽言诗作者籍贯分布图
图4-5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图
列表
表4-1 鸟禽言语的意义分别
表4-2 历代禽言诗作者籍贯分布
表4-3 历代禽言诗篇数
表Ⅳ1 《诗经》鸟类表
表Ⅳ2 《山经》自呼名之动物分布
表Ⅳ3 自宋至清禽言诗及其作者一览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最能表现这种距离感的,是《诗经》中对于鸟类行为能力的描写。“骇彼飞隼,其飞戾天”(《小雅·采芑》),“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小雅·四月》),“将翱将翔,弋凫与雁”(《郑风·女曰鸡鸣》),大量的这种近乎程式化的遣词,令人印象深刻。显然,这些鸟类的活动空间非常辽阔,人类对它们可望而不可及。“鸿飞遵渚”,“鸿飞遵陆”(《豳风·九罭》),“鸿雁于飞,集于中泽”(《小雅·鸿雁》),这是鸿雁(雁形目鸭科)。作为候鸟,它们总喜欢在水边活动。“翩彼飞鹗,集于泮林”(《鲁颂·泮水》),“墓门有梅,有鹗萃止”(《陈风·墓门》),这是鹗(鹗形目鸱鹗科)。后者的活动相对较靠近人居,但作为猛禽,它们与人类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比较疏远。
就生态特性来讲,在《诗经》出现的所有鸟类中,家燕(雀形目燕科)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它“喜欢栖息于人居环境,筑巢于檐下或庭廊,与人相处安然”①。在后世的诗作中,很容易发现“旧时王谢堂前燕”(刘禹锡句)、“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句)之类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句;然而在《诗经》里,燕子的这一特点却完全看不见。“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所谓“玄鸟”指的是燕子,诗中全未言及其行为特点。《邶风·燕燕》中有三章咏及燕子的行为:“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从这些诗句中,仔细回味也不难捉摸到一些感情的成分,但这种感情主要是一种离情别绪:“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为何要把这种情绪跟“燕燕于飞”联系在一起?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对“燕燕”是否就住在诗人或“之子”的屋里,更是不得而知。
更令人吃惊的是,《诗经》中描写鸟类的栖息地,几乎无一与人类的生活空间有交集。尽管有写到在屋顶栖止的,如“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小雅·正月》);有写到穿堂入户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但这些乌、雀的窝巢何在,不明。大量的鸟类都是栖止于树林、灌木丛。如“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周南·葛覃》);“欤彼晨风,郁彼北林”(《秦风·晨风》);再如:“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肃肃鸨翼,集于苞棘”,“肃肃鸨行,集于苞桑”(《唐风·鸨羽》)。要不然就是感觉距村落更远的处所,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或“有鹜在梁,有鹤在林”(《小雅·白华》)。当然,鸟巢也都看不到。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诗人们对于鸟类的生活其实并不关心,只不过它们从天而降,不请自来,不时对人类活动构成影响,因而不能不对它们有所警惕。换言之,当时诗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自身的生活,对鸟类的观察也只是为这一终极目标服务。唯其如此,《诗经》中对鸟类与人类相友善的一面几乎视而不见。在种类上,更关注那些行为能力强悍,有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某种危害的猛禽;而对于常作依人状的各种小鸟,也更多地是把它们当作食物链上的竞争者。如《卫风·氓》中有句云:“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小雅·黄鸟》中更是反复吟唱:“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样一种生态关系中,要让诗人在作品中将鸟类描写得与人类和谐共处,如同“仓庚喈喈,采蘩祁祁”(《小雅·出车》)所展现的那样,无疑是一件有悖其基本生活感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诗人对于鸟类的声音很不容易产生审美的情致。《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实在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深度远超我的初始预期。它不仅仅是对文学地理意象的梳理,更是一次对中世纪知识分子心智世界的深刻探访。作者对不同文化语境下地理名词的词源考证和象征意义的衍变分析,展现了令人赞叹的跨学科能力。书中对“理想城市”与“现实聚落”之间张力的剖析尤为深刻,它揭示了文学作品中对完美秩序的追求,与中世纪城市生活纷繁复杂的现实之间的永恒矛盾。行文之中,偶尔出现的拉丁文引文和古法语片段,非但没有造成阅读障碍,反而为整体的学术氛围增添了一份醇厚的历史质感。对于希望深入理解中世纪文化心态的读者而言,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既有广度又有锐度的参考指南。
评分这部作品深入探讨了中世纪文学中空间观念的演变,尤其是那些描绘地理环境、自然风光以及人与土地关系的文本。它并非简单地罗列作品,而是通过精妙的文本解读,揭示了作者们如何利用具体的地理元素——无论是蜿蜒的河流、巍峨的山脉,还是广袤的森林——来构建叙事结构,塑造人物命运,并传递深层的文化与宗教寓意。例如,书中对朝圣之路的分析尤为精彩,它不仅仅是一条物理路径的再现,更被视为精神救赎的象征性旅程。作者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将文学想象与历史地理背景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中世纪欧洲的“世界图景”是如何在诗歌、史诗和传奇中被建构、被诠释的。我对其中关于“失落之地”和“理想化家园”的论述印象深刻,这部分内容细腻地展现了中世纪知识分子对于现实边界的超越与渴望,文字的张力十足,引人深思。
评分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文本细节的捕捉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本书的行文节奏张弛有度,语言风格兼具学者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它不像某些学术专著那样枯燥乏味,反而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对于那些熟悉中世纪文本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角度,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完全理解的经典段落。书中对“异域”描写的辨析尤其值得称赞,作者细致地梳理了从中东到北欧不同地理单元在中世纪想象中是如何被混杂、挪用和改造的,揭示了当时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与想象力的丰富性。整体来看,此书的论证链条清晰有力,结构安排富有逻辑美感,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原来如此”的顿悟感,实属难得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之独特,令人耳目一新,它成功地避开了传统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对主题或人物的聚焦,转而将“地图”和“景观”本身提升到了核心分析地位。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地域文本时的那种审慎和克制,没有过度解读,而是扎根于文本提供的有限信息,进行合理的推论。比如,书中对比了早期修道院文献中对“荒野”的描绘与晚期骑士文学中对“森林迷宫”的处理,清晰地勾勒出社会变迁对自然空间象征意义的影响。这种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使得原本较为抽象的文学地理学变得触手可及,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世纪世界观的理解。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或许需要一些耐心去消化其中的术语和背景知识,但一旦进入状态,便会发现其中的宝藏。
评分这本书的学术品位极高,但其叙述方式却保持了一种近乎散文般的流畅与优雅。它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话的姿态,仿佛作者正携手读者一同穿越那些中世纪的羊皮纸卷,亲身丈量字里行间的山川河流。其中对“边界”概念的探讨,对我触动最大。作者巧妙地指出,在那个时代,“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地理界线,而是一个不断被书写、被争夺、被想象的动态场域。无论是城邦之间的壕沟,还是传说中世界的边缘,都反映了中世纪欧洲人在面对未知时内心的不安与秩序的渴望。这种对“不确定性”文学表达的挖掘,极大地提升了全书的深度和厚度,让人在合卷之后,依然能在脑海中回荡起那些由文字构建起来的、充满神秘感的地理景象。
评分六、环境刺激与文化感应
评分一家之言。
评分2.地方水利建设的开端
评分一家之言。
评分表4—3历代禽言诗篇数
评分四、《柳毅传》中的“洞庭”
评分好书,值得拥有。。。。
评分图4—3五藏山经地域范围图
评分包装很好,很有深度的一本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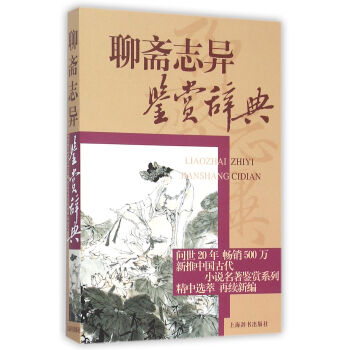

![辫子姐姐故事星球系列(套装共6册) [10-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92812/56a97b8bN9171f850.jpg)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 孤独之旅:曹文轩专集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98135/56385e48N26481184.jpg)

![独臂男孩 曹文轩小说馆 [7-11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30217/56711ce8N3dc48832.jpg)
![你一定没听过的神秘动物故事·科幻系列:炫酷的神话动物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58999/569e0b3fNfa29dd4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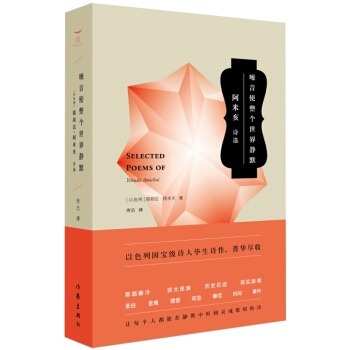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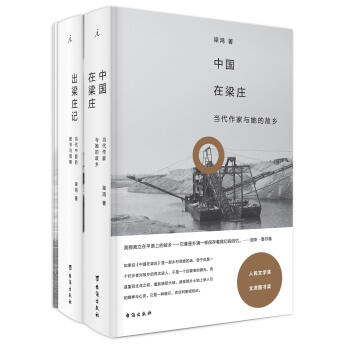






![冰心三部曲: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小橘灯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97041866/5abdca67N17eeb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