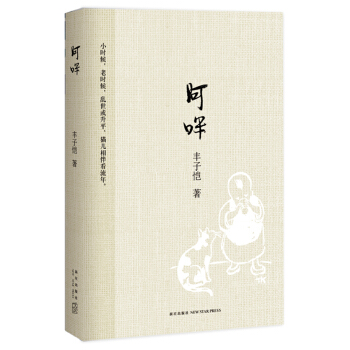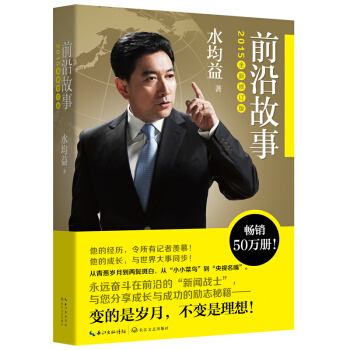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众人褒评,梁文道、白岩松、杨照、陈平原、杜维明……启发几代华文世界,“在岛屿写作”,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诗人杨牧文学自传的发轫之作,以散文笔路回顾早期文学,自剖文学诗意之缘起与信念——“经常有人问我:花莲和我的创作、成长,及对文学信仰、大自然的看法有无关系?久而久之,我就想藉由较正式的形式——文学,将此表达出来。”
发轫之作《奇来前书》、收官之作《奇来后书》创作时间横跨二十年,用书写“重新活过那生命的时光”;不同于一般回忆怀旧,更是文学性创作——早期三自传《山风海雨》、《方向归零》、《昔我往矣》,探索大自然与记忆之于诗,合为一部《奇来前书》;《奇来后书》接续《前书》之结构,从十八岁之后写起,告别青少年岁月的山林与海洋,追探成年后的学院时光。
从杨牧的文字,感受中文的另一种可能——《奇来前书》关于故乡与成长,关于大自然与文学信仰,山林乡野,日月海洋,声籁色彩,皆由杨牧铸成优美典雅的无韵诗行。
内容简介
杨牧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十年之内持续地书写三本以少年时光为叙事反思之聚焦的《奇来前书》,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那一远阶段的结束。之后,杨牧自觉地开始了一件新的写作,前后易六寒暑才完成,即《奇来后书》。《奇来后书》在时序上衔接《奇来前书》之结构,同样隐含文学自传的况味,却是从杨牧十八岁之后写起,告别青少年岁月、故乡花莲的山林与海洋,以成年后的学院时光为追探主题──东海、爱荷华、柏克莱、华盛顿、东华等大学……置身多样的人情和知识环境之间,感受学术、伦理,与宗教等及身的信仰和怀疑。笔法翻复、文类跨界之际,依然紧扣“诗”主题,对诗的执著始终不变,于风雨声势中追求爱与美之恒久。
封面绘图(杨牧胞弟作)奇莱山,台湾中央山脉中段的山峦,在杨牧故乡花莲境内,台湾十峻之一。台湾版《奇莱后书》来到大陆,杨牧易名《奇来后书》。
作者简介
杨牧,本名王靖献,早期笔名叶珊,1940年生于台湾花莲,著名诗人、作家。1964年自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保罗?安格尔及其妻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诗创作班,获艺术硕士学位,在爱荷华的前后期同学有余光中、白先勇、王文兴等日后引领台湾文坛的作家。
杨牧自十六岁开始写作,超过半世纪的创作生涯,累积出无数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并曾分别于北美、台湾、香港等地任教,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身兼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与学者多重身身份,作品译为英、韩、德、法、日、瑞典、荷兰等文,获吴三连文艺奖、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其中,马悦然翻译《绿骑:杨牧诗选》[Den grone riddaren]中文、瑞典文对照版,荣获2011年瑞典皇家图书馆书籍艺术大奖),影响后进无数。
代表作有《柏克莱精神》、《搜索者》、《奇来前书》、《奇来后书》等。作品曾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兰文。译著有《叶慈诗选》、《英诗汉译集》等。
“但知每一片波浪都从花莲开始”,文学大师系列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重新诠释、纪录六位台湾文坛重量级文学家(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以及杨牧的生命与创作历程),其中杨牧电影,即《朝向一首诗的完成》(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精彩书评
杨牧《衣饰与追求》一文,把《离骚》和斯宾塞《仙后》相比,是比较中西文学论文中最有见地的一篇。
——夏志清
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位把诗歌当做生命的诗人,一位学养非常深厚的诗人,他的诗的敏感度特别值得大家的赞赏,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民族的气息非常浓烈。他可以说帮助台湾建构了一所大学,他在这所大学里服务了很长时间,就是现在台湾的国立东华大学。
——杜维明
我对杨牧诗歌的理解受惠于我的一位朋友,他对杨牧崇拜得五体投地,总说杨牧是现代汉语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且不允许我加之一。我在台湾的朋友说过一段话特别令我受感动,他说杨牧先生的诗的写作,让我们知道尊重知识,知道写诗有一种精神系统在里面,而不是一触即发的行为。
——陈平原
陈芳明一行诗,一段文字,一则论述,一首译诗,都可视为生命里有机的内在连结。每种文体,每种技艺,形成诗人灵魂的巨大象征。杨牧孜孜不倦致力一个诗学的创造,进可干涉社会,退可发抒情感;两者合而观之,一位重要诗人的绮丽美好与果敢气度,俨然俯临台湾这海岛。
————
杨牧是一位革新者,一位巨匠。以其对世界文学、文化和历史的深度介入,他的诗作有着其他现代的汉语诗人,或甚至现代汉诗史上无与伦比的多样性和深度。……读者能随他而思索,深入诗中,深入到他的性灵和情愫之中,并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及其对人类的究竟意味。
——奚密
台湾著名诗人杨牧的诗集,它让我们感受到中文的另一种可能。生活不只是眼前,还有诗与远方,所以读读诗,活得有点诗意。
——白岩松
(2009年3月26日,梁文道在北京大学演讲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即席朗读台湾杨牧的一首诗《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写在一封缜密工整的信上,从/外县市一小镇寄出,署了/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梁文道
目录
设定一个起点
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青烟浮翠
一山重构
雨在西班牙
复合式开启
神 父
翅膀的去向
左 营
谁谓尔无羊
加尔各答黑洞的文字档
抽象疏离 上
抽象疏离 下
爱荷华
翻译的事
蜘蛛蠹鱼和我
鼬之天涯
破缺的金三角
中 途
奇来后书跋
精彩书摘
翻译的事
六十年代中因为偶然的机缘认识了林以亮,应该就是在爱荷华第一年结束的暑假。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三十年间维持着极好,温馨的友谊,虽然只见过少数几次面。我们写了许多信,绕着读书,创作,和翻译之类几样事情谈论着,商量着,偶尔月旦或存或殁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但他又时常提到自己怎样就生病住院,甚至开刀服药而终于无碍痊愈了,适可而止,笔锋一转又回到读书,创作,和翻译。
我记得他最初是接受聂华苓的推荐,邀我参与翻译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译者有林以亮,张爱玲,于梨华,和我。翻译篇数最多的是张爱玲,计有关于小说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编者的序文一篇,其次于梨华和林以亮各一篇,我两篇。张爱玲译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纳是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文笔精锐,剑及履及。记得首页翻开就有一则关系著作者相对于小说主题的论述,被她这样毫无保留地转化呈现了出来:小说家“不应当预先知道他的题材的意义。他必须等待故事开展,逐渐发现他的主题。如果这本书写完以后,主题极清晰地出现,那么作者大概是隐匿了一些证据,写出来的是一套教训或是宣传品”。林以亮指定我译的两篇,一篇关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另一篇则为拿撒奈·韦斯特(Nathanael West, 1903—1940);前者原文执笔人也是俄康纳。那暑假我住在柏克莱,每天规规矩矩坐在楼上窗前,设法把严谨的学术论文译成中文,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什么参考书。林以亮为早年燕京大学西语系出身,内战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从事西书的翻译和电影编剧,到我们通信的阶段,已经是朋辈中有名的“翻译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谓朋辈,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对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龄的友好,如姚克,张爱玲,乔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为衣食忙,他说,致未能专心文学,接下去就感慨地讲了些觉得“苍凉”的话。那当然也是长久以前的事,远在我能完全领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后数十年,他曾经屡次提到些时不我与,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话,都使我矍然心惊,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来他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好,长期带病养生,遂有许多恐惧不安,因此更倾向在信中多谈他写作和编译的计划。在我这方面,林以亮对翻译一事的热衷竟有意无意为我点出了一条值得试探的路,一片学术与创作的新领域,充满了信念,远景。
回想起来,在为林以亮译福克纳和韦斯特两文之前,我可以说从未曾真正尝试过翻译。有则在大学时代私密的练习,而我记得的却是一件颇具野心的计划,和济慈最纯净,透亮,而不减丝毫繁美的神话与诗有关。就是在东海毕业前一年吧,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动手开始翻译起济慈的长诗《恩迪密昂》。这首诗原文分四卷,全长超过四千行,以英雄双行体为基调,在严谨中赋予浪漫叙事的气息,所以也颇具有一种无韵体的声色,在英诗中亦属源远流长:
美的事务是永恒的欢愉:
其可爱日增,不消逝于
虚幻无影;反而就长久为我们
维持一座静谧的凉亭,为睡梦
……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确定至少翻了一千余行才停,手稿还在箧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关口戛然中断,原因不难想象,只是当时已惘然。最后那几行约莫如此:
当微风奏出一支甜蜜的圣歌
去取悦德俄菲的时候,就有雪白轻快的
节奏溶进无声的静寂。他的两脚急促
依然在这轻翼的引路人下飞跑……
济慈二十二岁动笔写此诗,不及一年脱稿,出版时书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恳切希望读者谅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错误”,果然,济慈为了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诗之传奇”,很快就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我自己也挑了这样一首艰深而不祥的长诗来译,在那青涩的年代。中断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开始四句亦复如此:
美的事务是永恒的欢愉,
它的可爱日增,永不消逝;
恒久为我们保有一个
无声宁静的园亭,又像那……
那一年暑假顺利译毕福韦二文,回到爱荷华,冬天开始选译卡缪的札记,取其文学与哲学以及一些关于社会文化的思维,逐日就英译本转译,自以为兴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荣,死亡,爱情。比起我内在那些沉重又真实的东西,这些名词有什么意义?“而那是什么?”“这泪水浩荡的重量,”他说:“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体会的死亡的滋味。”
例外:德国人发明了自鸣钟。这种东西是时间之流的可怕象征物。那宏亮的鸣声在西欧无数大城小镇日以继夜地响着,而且那也许最有力地表现道:“以历史意识面对世界乃是有利于创造的。”
同时,就在那冰雪严封的冬天,我开始以一种责无旁贷的态度埋头翻译西班牙诗人罗尔卡的吉普赛谣曲。所以说翻译的事,真正有个开端的话,痕迹确实在林以亮派给我的那暑期工里,后来才紧跟着做了少许一些零星的事,但还是有限。当时林以亮并不是把我分内的材料指定就罢。我交稿后,他显然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提出疑点,以讨论的口气建议我是否修改,怎样修改等等翻译者经常遭遇的问题。他的耐性和细心常使我觉得很感动,写信的时候我就维持着最严谨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如此,称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办《译丛》半年刊于香港中文大学,那几年我专致于二十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不久就针对周作人和希腊文学的关系在深入阅读着相关的书。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腊和现代汉文学的题目这样连结起来,非常高兴。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书,打开一看,才知道是他特别为我从朋友处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邮寄来的《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译希腊文学的珍本,竟原书渡海,还附一信云:“书我既已借来,可暂时存兄处,不必影印,俟论文写竟后再寄还不迟。”不久写竟的论文就发表在《译丛》。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时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张爱玲,和蔡思果我前后都见过。但我知道和他年纪相当在海外的友好,至少还有陈世骧和夏志清,没提到是因为后两位都在大学教文学,研究文学,不在他感慨须分心“为稻粱谋”的范围之内。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颇觉苍凉,似乎夸张,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确,最保守的两个字。林以亮生前谈到二十世纪的新诗人,必举吴兴华,认为是那一辈中翘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证吴的生卒年代是1921—1966,属“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识分子之列。吴死后,林以亮将他的遗作四处发表,一部分就寄夏济安,登在早期台北的《文学杂志》上;《文学杂志》也刊过一篇《论里尔克的诗》,作者署名邝文德,及若干直接译自德文的里尔克诗选,都是他提供的,而邝文德正是他为吴兴华取的另一笔名。早在抗战时期吴就已经以本名为中德学会译过一册《里尔克诗选》。又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林以亮夫人名邝文美。
张爱玲于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莱任职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为研究员。研究中心也是大学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别单元称为“当代语言计划”,主持人一直是陈世骧,早期独当一面的研究员即夏济安。我初到柏克莱那年暑假,陈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份整理夏遗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间老研究室里东翻西翻,其实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过目了许多新中国稀奇古怪的宣传口号和批判语汇之类,一直到秋天开学,就不做了。中心后来正式聘庄信正为计划研究员,越二年庄辞职去洛杉矶就南加大教职,陈先生不声不响请来了一位女士继任这件工作,就是张爱玲。我第一次见到张爱玲的时候,其实从来还不曾读过她的小说,但我读过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大半,其中辟有专章研究她,何况我们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下,合译了一本《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
所以就赶快去找她的小说来看。现在想想,那时张爱玲大概也才四十多岁,但几乎所有她到今天还有人读的小说都已经写好了。张穿着很朴素,总是那样安静端庄地坐在那里,不和人家抢话讲,只专心听着,点头,好像没有太多表情,虽然偶尔脸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张爱玲记得我为那本美国书翻译的福克纳和韦斯特,很惊讶我原来还是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生。有人问她关于《倾城之恋》的事,她支吾不愿意谈;又问七巧,也同样无心深入的样子。那之前,我们来自台湾的同学都读过一本不知道怎么从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于是不怀好意地想试探这个题目,但她把头转到一边,面无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济安一路下来的延续,但那一两年“文革”方炽,我们关心中国现状的人课后常到中心的图书馆看报;我去时通常是下午暮霭迟迟的时候,屡次遇见张爱玲刚进中心大门,互相礼貌地招呼,随即看她安静地穿过长廊,走进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惯例,研究员一年须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论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陈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她的论文怎样。据说那一天晚上陈先生的追思会中,张爱玲其实也是在座的,但我没有注意到;又据说会未终了,她就起身在檐下独立,逡巡,而终于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这样一种暗淡,逐渐微弱的光影里,我们的六十年代就几乎无声息地隐入势必的记忆,忽然的和累积的,未竟的音讯,情节,故事,无法重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偶然浮现,提醒我们蓄意编织的梦,破碎的梦,消灭虚无的梦,归根究柢终于是真实的,曾经都将在此后局促的岁月里,转化那具象的真实为更高层次的神情体验,在文字的驱遣,复沓,重叠,和离析等等这些大动作里,这些艺术结构的诉求里,找到我们的思维借以诠释的端倪,发现生死归宿何其渺茫: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爱和恨的时代,风云和烟雨的时代,残忍,同情,我们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禅修,抗议和出卖,无数影像犹栩栩在记忆里有机地滋生,欲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向,红杉巨木的针叶在窗外摇摆,窥探,古典文本在灯下,猕猴桃在冰箱里,香烟在床头,家国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复的水瓶,金牛,和处女座,稀薄的音讯里未竟的音讯,失踪,监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伤,何其庄严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节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发觉这其中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异国情调,广大深沉的港湾,更远更远异样的水平线,和我从窗口俯视的住民,安静的和熙攘嘈切的人车,使我精神为之摇动。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见面时,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现出一种对我特别接纳的神色,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通了许多信,在一般的文学修养范围内几乎无事不谈。同时我也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至少对某些人说来,甚至是不可亲近的。他问我的写作和研究计划,家庭情况等等,又突然问我练过字没有,于是就谈碑帖源流异同,非常深入,许多都是我不见得理解的。后来回到台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来的一包书法碑帖,原来他是觉得我的钢笔字显然欠缺了什么规矩之类,必须加以约束,就为我进城去挑选了这些书法范本,要我定下心来拿毛笔勤练习之。我很感动,但练字实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随意在书堆里拿出一本《道因法师碑》跟着写起来,一匝月即止,未再写过。
我听说林以亮和早期香港的电影事业很有关系,曾担任过几个大公司的制片和编剧,而他和张爱玲的交情大半际会于此。六十年代张曾为电懋写剧本,其风格即受林以亮早出的喜剧《南北和》的影响,而且她笔下的粤语对白一向须由林以亮修改才定稿。然而相识那么多年,我并不曾看过他在信里谈及电影这个题目。但我也记得当初他为我译韦斯特一文改稿时,进进出出特别精细准确的是关于韦斯特在好莱坞编剧之始末。他八十年代好像都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校长特别助理;我可以想象他依然故我,爱才不吝施舍,绝无保留,甚至到了护短的程度,但又不愿意含糊以敷衍平庸,也就是说,原来那一份知识之傲气总是不少的,所以我在香港遇见的人当中,对他不以为然或谈起来就咬牙切齿的,似乎比对他倾心致敬的人更多。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香港参与科技大学创校,那时林以亮已自中大退休,平时在家看书养病,或提供咨询资料给《译丛》编辑同人。秋凉时,经过多次要求,他终于答应让我前去拜访。记得他家在一个叫“嘉多理山嘉多理道”的陂陀多树的社区,甚为幽静。林以亮坐在起居客厅的大椅子上,侃侃而谈,或起立走到书架前取物示我,精神相当不错。告辞出来,回头扬手作别的时候,才感到他那清癯的病容,以及更明显触动我内心的,他多么舍不得我们这样匆匆来去,依依的表情,在南国晚起的秋风里。
林以亮去世时,我已离开香港若干年,而在这之前,因为健康和际遇的关系,他的信也写得少了,来往香港的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情况。等到证实他已溘然长逝,大概就是一九九七年暑假之后了。林以亮身体一向不是最好,长期都在就医服药,甚至屡经外科手术,坚忍养护,还做了许多有功于文化的事。对个人而言,他期许激励于我的正是文学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授受之间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遗余力,以及我偶尔奋起从事的翻译工作,其实正是他给予我的启发,所以说翻译是我的“香港因缘”的开始。虽然,我还是不免遗憾,当初选译叶慈诗得以成书出版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开始的时候我还住在清水湾,竟未能就近让他看到一些稿本;至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想必是他最感兴味的题材,无论就他的家学或人生体验而言都是,但也来不及了。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奇来后书》这本书,它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慢热”的美。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它的节奏有点慢,情节发展也不算特别抓人眼球,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被它所吸引。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沉静的力量。他擅长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描绘,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在他的笔下却充满了深意。我尤其喜欢书中对自然景色的描写,那种宁静、悠远的意境,仿佛能洗涤人的心灵,让人暂时忘却尘世的烦恼。人物的塑造也很有意思,他们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英雄,而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有着自己的缺点和烦恼,但正是这种真实,让他们显得更加可爱和可敬。这本书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但它却能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你在平静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力量。它像一杯陈年的老酒,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醇厚和甘甜。
评分读《奇来后书》真的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旅程。一开始我完全是被这个书名吸引住了,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奇感,仿佛藏着什么惊天秘密。拿到书后,它的封面设计也很有质感,散发着一种复古又神秘的气息,让人迫不及待想翻开。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作者的文笔极其细腻,每一个场景的描绘都栩栩如生,仿佛我亲身置身其中,感受着空气的温度、光影的变化,甚至能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淡淡的香气。人物的塑造也十分立体,他们不再是简单的纸片人,而是有着复杂的情感、矛盾的内心和各自的成长轨迹。我尤其喜欢主角在面对困境时的挣扎与坚持,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故事的推进节奏张弛有度,有令人屏息的紧张时刻,也有让人回味无穷的温情片段,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恰到好处。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探讨,也引起了我深刻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
评分怎么说呢,《奇来后书》这本书,它好像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我之前从来没读过类似风格的作品,它不像我平时看的那些快餐小说,也没有那么强的娱乐性,但就是有一种魔力,让你一旦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个人化,充满了诗意和哲思,有时候读起来会觉得有点费力,需要停下来仔细琢磨,但正是这种“费力”,才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共鸣。书中对情感的描绘非常克制,但越是克制,反而越能感受到其中汹涌的暗流。人物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极其隐忍和复杂,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交流并非依靠言语,而是通过眼神、肢体语言,甚至是沉默来传递。这让我在阅读的时候,需要调动更多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去体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些关于孤独和寻找意义的段落,它们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普遍焦虑,让我觉得作者仿佛是我的知己,理解我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这本书更像是一场心灵的对话,它不强迫你接受什么,只是静静地呈现,然后留给你无限的思考空间。
评分《奇来后书》带给我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我很少写书评,但这次真的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作者在叙事上的惊人天赋,他能够将多个看似无关的线索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宏大而精巧的叙事网。每一个伏笔都埋得极其巧妙,在不经意间就给你带来巨大的惊喜,让你忍不住惊叹“原来是这样!”。我喜欢作者在细节上的把控,无论是人物对话的微小之处,还是场景切换的衔接,都显得那么浑然天成,毫无斧凿痕迹。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智力探险,每一次的猜测和推理都充满了乐趣,而最终的真相揭露,更是让你拍案叫绝。我尤其佩服作者对人性的洞察,他毫不避讳地展现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剖析得淋漓尽致。那些内心的挣扎、纠结、痛苦与抉择,都真实得令人心疼。这本书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精彩,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深刻寓意,它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的书。
评分我真的要为《奇来后书》这本书点赞!它完全颠覆了我对某类题材的刻板印象。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但作者却用了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展开。他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让故事在不同的时间线和视角之间跳跃,起初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跟不上,但当你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就会发现这种叙事方式带来的独特魅力。它让整个故事更加立体和丰富,也增加了悬念感,让你总是在期待下一个惊喜。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人物情感变化的细腻描绘,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人物内心最细微的波动,将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纠葛刻画得入木三分。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或者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都能牵动起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且,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情感,它还涉及了许多历史、文化和社会层面的议题,而且探讨得非常深入,让我受益匪浅。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视野被打开了,对很多事情都有了新的认识。
评分好书,买来与《奇萊前书》凑一对
评分好的,。knot扣扣咯哦哦OK啦咯哦哦
评分还没开始看呢,很喜欢杨牧的诗。
评分好棒的书,条理清晰基础扎实。送货快。
评分这个商品不错,快递也很快!赞一个!
评分《奇来后书》在时序上衔接《奇来前书》之结构,同样隐含文学自传的况味
评分这本书不仅是一份珍贵的记录,也是一次见证。从手艺人质朴的语言中,对工作的认真、对手艺的自豪、和倾注一生的匠人精神触动人心。同时,他们对传承的忧虑和失落,让人揪心,也更体现了这本书作为“记录”的珍贵价值,它让我们得以见证京都手工艺辉煌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评分还可以吧,没详细看呢,物流快
评分前后都买了 前后都喜欢 前后感觉不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世界儿童文学精选:吹牛大王历险记(拼音美绘本)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0627/55827ed2Nb4f0d61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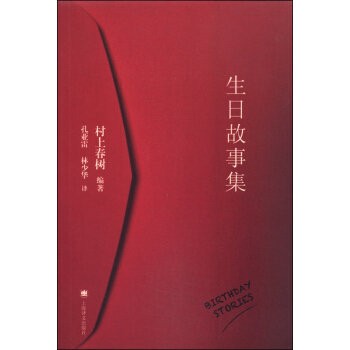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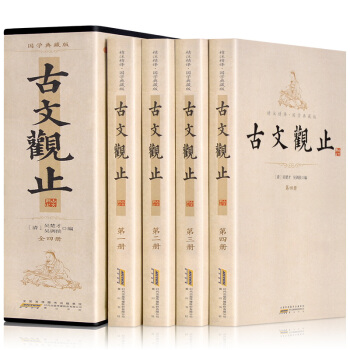


![畅销十年的原创经典·杨鹏装在口袋里的爸爸:追击章鱼王子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22298/54ca0be8N3e35f4be.jpg)

![最励志校园小说第三辑:赞美改变你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290/rBEbRlNp3VIIAAAAABLyrl7Gpw4AAAFEQE7-l8AEvLG081.jpg)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西游记(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964/rBEbRlNrVxwIAAAAAAs0hSIMd18AAAWngBe6pUACzSd312.jpg)
![繁星春水 冰心奖大奖书系(套装共10册)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17976/53f40cd5Ne9d3053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