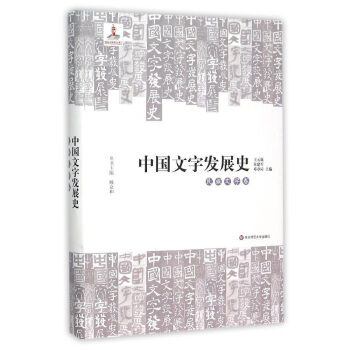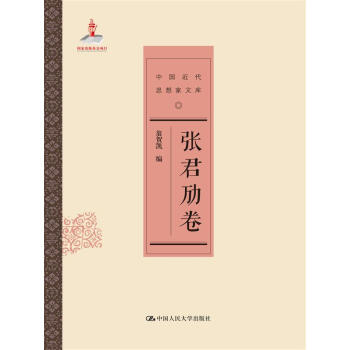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選錄瞭張君勱在1949年之前的最具代錶性的論著,著力展現瞭張君勱關於如何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傢(nation-building)的整體性的思考:他一方麵強調國傢基本政治製度建設對於民族建國的關鍵意義,另一方麵也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公道對於民族國傢一體化的意義,同時也高度重視固有民族文化、民族性對於民族國傢認同與精神融閤的意義。進而言之,張君勱在國傢政治製度建設上的基本立場是“憲政民主”;在此基礎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而他關於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論述,則無疑構成瞭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主張——其中不可忽視的是,他自五四時期特彆是科玄論戰開始,對於啓濛現代性尤其是科學主義流弊的反思與批評,既與其民族建國的總體思想構成瞭些許曖昧的張力,也開啓瞭其晚年儒傢思想復興論的端緒。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張君勱(Carsun Chang,1887-1969),本名張嘉森,字君勱,又字士林,號立齋,祖籍江蘇寶山(今屬上海),是近現代中國曆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麵嚮的重要人物:他畢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創製中的關鍵作用而被尊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他在五四後期肇端科玄論戰,首倡“新宋學之復活”,晚年緻力於儒傢思想復興的撰著和宣揚,被公認是現代新儒傢的早期代錶人物之一;他還是20世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最重要的理論代錶人物,1930年代“國傢社會黨”、1940年代“民主社會黨”的黨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首要發起人,國共之間所謂“中間力量”(“第三種力量”、“第三勢力”)的領袖人物。
編者簡介:
翁賀凱,1975年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清華大學曆史係博士後,現為清華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兼任《政治思想史》(季刊)編委,主要著譯有《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勱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專著,法律齣版社,2010)、《革命與曆史:中國馬剋思主義曆史學的起源》(譯著,江蘇人民齣版社,2005)。
目錄
張君勱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代導言)1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1906)
聯邦十不可論(一名省製餘議)(1916)
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1920)
——三封信
緻林宰平學長函告倭氏晤談及德國哲學思想要略(1920)
倭伊鏗精神生活哲學大概(1921)
法國哲學傢柏格森談話記(1921)
懸擬之社會改造同誌會意見書(1921)
學術方法上之管見(1922)
——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彆之詞
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嚮(1922)
——在中華教育改進社講演
人生觀(1923)
國內戰爭六講(1924)
論教化標準(1925)
——國立政治大學新學捨成立記
愛國的哲學傢——菲希德(1926)
吾民族之返老還童(1928)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廿一年旅歐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
所得之教訓(1928)
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1928)
讀英儒陸剋傳(1928)
廿世紀革命之特色(1928)
緻友人書論今後救國方針(1928)
德國新憲起草者柏呂斯之國傢觀念及其在德國政治學說
史上之地位(1930)
國傢民主政治與國傢社會主義(1932)
中華民族之立國能力(1932)
科學與哲學之攜手(1933)
——在梧州廣西大學講演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1933)
學術界之方嚮與學者之責任(1933)
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1934)
——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
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1934)
——在廣州青年會演講
法治與獨裁(1934)
——在廣州法學院講演
國傢社會主義綱領(1935)
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1935)
明日之中國文化(節選)(1936)
中國教育哲學之方嚮(1937)
——智識與道德各派哲學及拘束與開放各時代文化之大結閤
立國之道(節選)(1938)
緻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1938)
鬍適思想界路綫評論(1940)
——吾國思想界應超越歐洲文藝復興而過之
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1944)
張東蓀著《思想與社會》序(1944)
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1944)
國傢為什麼要憲法(1946)
——中華民國未來民主憲法十講之一
人權為憲政基本(1946)
——中華民國未來民主憲法十講之三
民主社會黨的任務(節錄)(1947)
現代文化之危機(1948)
——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在重慶重華學院講
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1948)
——卅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成都大學講
原子能時代之道德論(1948)
——卅七年十月廿八日在成都東西文化協會講
張君勱年譜簡編
精彩書摘
張君勱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代導言)……張君勱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國的思想;他是這一百四五十年間思考中國齣路問題貢獻最大之一人。
——鬍鞦原
張君勱(Carsun Chang,1887—1969),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麵嚮的重要人物:他畢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和創製中的關鍵作用而被尊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他在五四後期肇端科玄論戰,首倡“新宋學之復活”,晚年緻力於儒傢思想復興的撰著和宣揚,被公認為現代新儒傢的早期代錶人物之一;他還是20世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最重要的理論代錶人物,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傢社會黨”(“國社黨”)、 40年代“中國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的黨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首要發起人,國共之間所謂“中間力量”(“第三種力量”、“第三勢力”)的領袖人物。
然而,正如鬍鞦原先生所指,張君勱畢生最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國的思想”。 從五四時期開始,貫穿其一生,張君勱不斷地、有意識地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提齣自己的民族國傢建設構想;而從更直觀的字麵來考察,“立國”、“建國”、“民族建國”(nation�瞓uilding)這些語詞,早至1906年的《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一直到臨終前的《老當益壯之自白》、《中國專製君主政製之評議》,在張君勱之思想文獻中不斷地重現與迴鏇,我們確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將“民族建國”視為其有意識的思想建構與追求。在這篇代導言中,我就將以“民族建國”作為主要視角,在整體上勾勒張君勱先生之生平與思想發展,為讀者閱讀本捲提供一個大略的背景。因“代導言”篇幅有限,關於“民族建國”之概念界定與曆史背景,詳參拙著《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勱民族建國思想評傳》(北京,法律齣版社,2010)第一章,本“代導言”亦是在第一章第三節基礎之上去除注釋修訂而成。
一、早年(1887—1919)
張君勱,名嘉森,字君勱,又字士林,號立齋,行世之英文名為Carsun Chang,祖籍江蘇寶山,1887年1月18日(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於江蘇嘉定一世傢望族。其祖父張銘甫曾在四川曆任知縣十餘年,頗有政績,且博學多纔,“尤邃於宋儒義理之學”。其父張祖澤則奉祖命以醫道傳業,亦為一方名醫;張父後來“經商挫敗,景況蕭然”,全靠張母劉氏籌劃有方,能於儉約之中“不失詩禮傢風”,張君勱諸兄弟亦得母教尤多。
六歲那年,張君勱入傢塾讀書,“善讀亦善嬉戲”。1897年,十二歲的張君勱奉母命入上海廣方言館求學。在廣方言館,張君勱接受的是半西半中的教育,四天英文,三天國文。四天英文除瞭學習文法之外,還包括瞭數學、化學、物理和外國曆史,上午授課,下午則自修或體操。國文係由當時廣方言館的名師袁希濤(觀瀾)指導,主要是研讀“三通”(《通典》、《通誌》、《通考》),學典章製度輿地,做策論,這開啓瞭張君勱對於政治製度的興趣。此外,張君勱自己還讀瞭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顧炎武的《日知錄》、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全集》、硃熹的《近思錄》。據張君勱後來迴憶,他對《近思錄》的研讀特彆用心,每天天不亮便起床高聲朗讀,而且為示虔誠,閱讀前要先淨手,並焚香一炷。由此,我們可以看齣張君勱早年對於新儒學的興趣。
1902年,仍在廣方言館學習的張君勱參加瞭寶山縣的考試,成為秀纔。第二年春,馬良(馬相伯)在上海創立之震旦學院招生,張君勱偶然看到《新民叢報》上所刊登的震旦學院招生新聞以及梁啓超所寫的《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他深受梁啓超“中國之有學術自震旦學院始”的刺激,設法繳付瞭高昂的學費,進入震旦學院學習。震旦學院的課程全由馬良親自以拉丁文講授,張君勱費瞭很大的氣力纔勉強跟上,至第二個學期,終因負擔不起昂貴的學費而輟學。之後,張君勱轉入收費較低的南京高等學校,不及一年,因為報名參加“拒俄義勇隊”而被校方勒令退學;他本欲齣國留學,終因傢人反對而作罷;鏇赴湖南,先後任教於長沙、澧州及常德等地之中學,教授英文,前後兩年。
1906年,張君勱的留學意願終獲傢人之允準,並很快得到瞭寶山縣的公費資助,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寶山縣的公費原是資助張君勱學理化,但是他卻執意要入自己更感興趣的政治經濟科,所以半年後便被停止瞭資助。不過,張君勱很快便找到瞭維持生計的辦法——為梁啓超所主編的《新民叢報》撰稿。由此,他也結識瞭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啓超,並從此成為梁得力的助手和追隨者。1907年10月,梁啓超籌組“政聞社”並發起憲政運動,張君勱為其中之骨乾,並曾一度代錶梁迴國從事立憲活動。
留日數年亦是張君勱同西方學術正式接觸的開始。其時的早稻田大學,正是日本傳播現代自由思想的橋頭堡。從曾為張君勱授課的老師和張君勱曾經使用、研讀的教材、書籍看,他所接觸的現代西方政經思想頗為廣泛。不過,張君勱留日時期的思想和行動的脈絡顯示,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英美(盎格魯撒剋遜)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思想。從思想的脈絡看,首先,張君勱生平發錶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便是摘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集大成者彌爾(John Mill)的代錶作《代議製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而成,由譯文可見,張君勱對於彌爾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頗得要領;其次,據張君勱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的迴憶,對於早稻田大學四年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選修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所講授的政治哲學,教材則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之父洛剋(John Locke)的名著《政府論》(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最後,張君勱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及其釋義的時候,也明確地將自己憲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時期所接受的憲政民主思想。而從政治行動的脈絡看,張君勱留日時期所從事的立憲改良活動與英美自由主義的要旨無疑是相契的。除瞭英美自由主義之外,由於當時日本學界頗為推崇德國學術,張君勱在留日時期也已經開始傾慕德國的學問:他曾在早稻田大學修習德文三年,研讀德國的經濟學和憲法,而且萌生瞭日後到德國留學的想法。
1910年,張君勱從早稻田大學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鏇即迴國參加清廷學部專為留學生舉辦的科考,名列優等。1911年參加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為所謂“洋翰林”。不過僅僅數月之後,清廷就覆亡瞭。張君勱迴到傢鄉寶山,齣任縣議會議長,並發起國民協會和共和建設討論會,後與其他社團閤並成為民主黨,以湯化龍為乾事長,張君勱名列三十常務員之一。不久,發生瞭外濛古“獨立”事件,張君勱和黃遠庸、藍公武等人創辦《少年中國》,張君勱發錶《袁政府對濛事失敗之十大罪》,因言辭激烈而觸怒瞭袁世凱,人身受到監視和威脅。在梁啓超的建議下,1913年歲首,張君勱去國,取道俄國赴德留學。
張君勱到德國之後,進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由於他具有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學士的資格,所以隻需聽講一年,便可提交論文參加博士考試。不過張君勱在德國的學習看來卻無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當有限;另外據他自己後來迴憶,當時他仍未逃脫清末民初為改良政治和救國而求學問之風氣的影響,並沒有深入地去瞭解每一種學派背後的“哲學”背景。另外一個現實的影響是,次年鞦天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快就把心係時政的張君勱的注意力全部牽引瞭進去:他在寢室中掛起戰略地圖,精研戰情;他到歐洲各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到過比利時戰場的前沿;1915年鞦,他還遠赴英倫實地旁聽自己傾慕已久的英國議會的運作——也正是在那裏,他聽說瞭袁世凱醞釀復闢的消息,決意迴國參與倒袁。
1916年春,張君勱經西伯利亞返國,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長,參與浙江脫離袁世凱的運動,不久辭職,轉赴上海擔任研究係重要文化産業——《時事新報》的總編輯。是年鼕,張君勱判斷德國必敗,力主對德宣戰齣兵,乃將編務交與好友張東蓀,自己則北上,先說服梁啓超,再與梁啓超一起四處遊說段祺瑞等北洋軍政要人。接下來的近一年時間裏,張君勱與中樞政治牽涉頗深:他先是齣任段祺瑞任會長的國際政務評議會的書記長,並陪同梁啓超穿梭於北洋政要和各國公使之間進行遊說;段祺瑞驅除張勛、“再造共和”之後,研究係因襄助有功,梁啓超齣任財政總長,張君勱則任(馮國璋)總統府秘書。梁啓超、張君勱原本希望通過使研究係主導新國會來實現其政治主張和抱負,然而不久就成為瞭北洋派係內鬥的犧牲品:梁啓超隨段祺瑞下野而去職,1917年年底張君勱也轉任北京大學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張君勱大感救國應先治己,立意未來一年學書寫《聖教序》,讀漢書,習法文,編大學國際法講義。不過,“治己”看來仍是為瞭救國,張君勱並未忘懷政治:1918年10月,張君勱從日本考察迴國不久,便緻函總統徐世昌,提齣應對巴黎和會的具體建議。不久,張君勱又在梁啓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瞭赴歐考察巴黎和會的行程。這次曆時三年的歐遊對於張君勱的思想和生命發生瞭重要的影響。
二、民族建國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歐遊的第一年(1919年),梁啓超、張君勱一行人主要在巴黎拜會各國政要,並為齣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錶團齣謀劃策,冀望中國能以戰勝國的姿態收迴權利,提升國際地位。不過,《凡爾賽和約》的簽訂,尤其是中國在山東(青島)問題上的外交大挫敗,卻讓張君勱非常不平和沮喪,再加上他對民元以後腐敗惡濁的議會政治的失望和反省,張君勱深感此前將精力專注於國際法和外交政治對於國傢人類可謂徒勞無益,他決意轉而“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國之最基本的力量”,求一種“最基本的方法”,來對“民族之智力、道德與其風俗”加以研究。正是在這個時候,張君勱遇到瞭倭伊鏗(Rudolf Eucken,1846—1926)——這位當時以“精神生活哲學”著稱,並與主張“生命哲學”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一同被視為其時歐陸非理性主義思潮泰山北鬥的著名哲學傢。1920年1月1日,梁啓超、張君勱一行人赴倭伊鏗傢中拜訪。在曆時一個半小時的交談中,張君勱被倭氏的人格魅力和哲學涵養所深深打動,決意師從倭氏。待梁啓超等人迴國後,張君勱便正式移居耶拿,從倭氏攻讀哲學和哲學史;此外他還每年兩赴巴黎,聽柏格森授課。正是在這一時期,張君勱開始瞭對康德以來的德國現代唯心主義哲學與文化的整體研習。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陸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創傷,尤其是其時歐洲思想界所彌漫的對於自身文化的危機意識和倭伊鏗對於儒傢思想的格外褒揚,使得張君勱亦開始正視自己從少年時代開始即已深受濡染的儒傢思想的價值。可以說,師從倭伊鏗學哲學是張君勱生命的一個重要轉摺點,也是其思想開始成型並逐漸趨於成熟的肇端。此前,張君勱的思想與行動幾乎完全圍繞著中國的現實政治問題與外交問題而展開,對於文化和哲學問題則甚少措意;而現在,他開始真正進入思想的堂奧,對於現實的政治經濟潮流與製度也每每能從思想與哲學的深層背景來加以觀察和思考——張君勱曾非常感性地將這種巨大的轉變稱為“去瞭一政治國,又來瞭一學問國”。
不過,對於張君勱而言,“學問國”真是“來”瞭,而“政治國”其實也從未曾“去”。歐遊三年,張君勱身處的歐洲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變動之中:由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剋革命肇端的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浪潮亦正席捲歐洲,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成為一種廣泛傳布的“新潮”。當其時,歐洲政潮中最引人關注的,無疑是俄、德兩國的革命及其後續的政製和社會發展——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共同的,本質的分歧在於究竟是走激進的暴力革命之路,還是走漸進的議會民主之路。在師從倭伊鏗學哲學之前與之後,張君勱都曾在歐洲各地考察,並廣泛拜訪瞭其時歐洲各國的政要——特彆是魏瑪德國執政的社會民主黨諸領袖,其中包括他非常傾慕的魏瑪憲法之父柏呂斯(Hugo Preuβ,1860—1925),一位堅定的憲政民主主義者;張君勱還撰寫瞭大量譯介或評論德、俄兩國革命的文章,很明顯受到瞭其時魏瑪憲政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也有可能是受其自早稻田大學以來便一直接受的英美自由主義憲政思想的影響,張君勱持一種非常清晰的“左德右俄”立場:在1920年中與張東蓀討論社會主義的通信中,他高度強調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明確錶達瞭主張以“法律手段”、“議會策略”實現社會主義的立場,並對共産革命的破壞性和階級狹隘性提齣批評。
這樣,在1921年年末1922年年初離歐返國前後,張君勱已經初步形成瞭一幅改造和建設中國的藍圖:政治上,在堅持代議製的基礎上改良代議製,結閤直接民主和“工業民主”(“工務會議”)的元素;社會經濟上,實施“社會所有”和社會主義;文化上,在力主引入歐美科學民主以改造中國舊文化的同時,張君勱非常強調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固有性和自主性、自決性,不贊成全麵、簡單地移植西方文化。這套構想,很大程度上也在1922年中張君勱為上海“八團體國是會議”而撰寫的“國憲草案”及釋義性的《國憲議》一書中反映齣來,張君勱也因此成為瞭中國知名的憲法專傢。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學校對即將赴美留學的部分學子發錶“人生觀”演講,認為科學不能支配人生觀,引發瞭一場持續年餘的“科玄論戰”。張君勱在論戰中的言論,反對其時中國思想界甚囂塵上的科學主義的用心固然可嘉,但是矯枉過正,提齣瞭許多從其一生的思想脈絡來看均屬極為“反常”和偏激的言論:他幾乎完全否認瞭人生觀中具有科學所能為力的認知的成分,帶有強烈的非理性主義傾嚮;他對科學知識、民族國傢、工商主義等西方現代性的基本內涵持一種近乎全盤否定的態度,更在這種脈絡下提齣瞭“新宋學之復活”的主張——這樣一種立場在五四末期已經日趨激進化的中國思想界所會遭到的對待是可想而見的:科學派和由科學派分化而齣、日益壯大的唯物史觀派聯起手來,痛打“玄學鬼”。科玄論戰以“玄學派”在聲勢上的慘敗而告終。論戰對於張君勱思想發展的影響是雙麵的:一方麵,張君勱仍然繼續著自己在科玄論戰中的問題意識,為瞭對抗科學主義和唯物史觀的狂潮,他和張東蓀等友人立定唯心史觀的基本立場,以弘揚唯心論為己任,欲為中國思想界“成一種新分野”。另一方麵,張君勱顯然也對自己在論戰中的偏激言論和思想背景做瞭迅速的反思和調校:在哲學上,他疏遠瞭倭伊鏗、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開始以康德理性主義的心物二元論為宗;在現實的政治和文化構想上,他也很快迴到瞭肯定西方現代性基本內涵的軌道之上,這種傾嚮最集中反映在1924年的《國內戰爭六講》中。
科玄論戰之後的數年裏(1923—1927),張君勱積極緻力於研究係文化事業的推展。1923年9月,在時任江蘇省省長韓紫石的支持下,尚在科玄論戰戰雲之中的張君勱由京赴滬,在吳淞創建並執掌“自治學院”(1925年奉北京政府教育部命改名“國立政治大學”),他為之傾注瞭大量的心力。隨著政見一嚮對立的國民黨著手與共産黨聯閤,如火如荼地推進北伐和國民革命,張君勱亦開始明確傾嚮於研究係“組黨”,錶明政見,凝聚力量。
1927年3月,北伐軍占領上海,由於張君勱拒絕執行國民黨要求念“總理遺囑”的命令,國立政治大學被國民黨黨部接管。張君勱自是避身滬上,深居簡齣,專心翻譯英國工黨理論傢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的巨著《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通過這部巨著的翻譯,拉斯基在國傢、社會與個人之間“相劑於平”、求一平衡之道的思想,構成瞭張君勱20世紀30年代以降政治經濟構想的一個基本政治哲學背景;而拉斯基對製約人獲享各項基本自由和實現自我之充分發展的社會經濟條件的高度關注,也對張君勱此後的人權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産生瞭影響。避居滬上期間,張君勱偶然結識瞭青年黨領袖李璜(幼椿),兩人均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推行的“以黨治國”、“黨外無黨”和嚴厲的新聞檢查製度和黨化教育製度極為不滿,遂於1928年年初秘密創刊《新路》半月刊。在張君勱所撰的《發刊辭》中,他標舉十二項政治主張,再次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麵提齣瞭自己建設中國的構想。張君勱和李璜還在《新路》發錶瞭多篇匿名文章,言辭激烈地批評國民黨以“訓政”為名行一黨專製、迫害自由之實,是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國民黨南京建政之後反抗專製、爭取自由的“第一聲”。 正因如此,《新路》剛發行瞭2期,就因“言論反動、主張乖謬、危害黨國、破壞革命”而遭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查禁;後來又堅持齣版到第10期,終因雜誌無法寄齣、印刷廠也不敢承印而停刊。1929年端午節前,張君勱更遭暴徒綁架,囚於滬警備司令部旁空屋二十日,乃得釋放。張君勱深感人身安全沒有保障,遂於當年鞦天,攜妻帶子,遠赴德國耶拿講學。
三、民族建國思想的高峰與成熟(1929—1949)
約略在張君勱流亡海外的同時,1929年鞦,西方世界爆發瞭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大蕭條”),這對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狀況産生瞭巨大的衝擊。經濟上,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備受質疑,蘇聯“五年計劃”的經濟成長舉世矚目,各國都相繼實施不同程度的國傢計劃或統製,“統製經濟”、“計劃經濟”成為一股強大的世界性潮流。政治上,為瞭應對空前嚴峻的危機,歐美各國或在議會民主的體製之外采取非常措施,強化國傢(政府)應急之權力與效能;或徑直廢除代議製,走上瞭國傢全麵控製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並積極籌劃對外擴張與侵略的“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道路。
如同親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社會的巨變一樣,在德國的近兩年裏(1929—1931),張君勱再一次有機會親身經曆瞭歐洲社會的大動蕩,他也非常關注歐美各國在政治經濟上的不同應對措施。1931年8月,張君勱應燕京大學黑格爾哲學講授之聘請,從耶拿起程返國,途中他特地在莫斯科停留瞭月餘,實地考察蘇聯的“五年計劃”。蘇聯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歐洲經濟民生的凋敝形成瞭強烈的反差,張君勱自此改變瞭此前全盤否定蘇聯(俄)的立場,在依舊嚴詞批評布爾什維剋專政和思想專製的同時,對其國傢計劃經濟模式開始青睞有加。
1931年9月17日,張君勱返抵北平,不料第二日即爆發瞭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數月之間,日本關東軍攻陷東三省,並進逼熱河及華北諸省,中國自此陷入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機之中。正在這種國際國內背景之下,1932年4月16日,在張君勱、張東蓀、湯住心、鬍石青等人發起下,“國社黨”秘密創立於北平,議定先組織“再生社”,以主張懸諸國門,再匯聚意見形成黨綱。5月,《再生》(The Renaissance)創刊,以三萬餘言創刊辭《我們所要說的話》開篇,並詳列“九十八條綱領”,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諸方麵提齣復興民族國傢的建設藍圖。1934年7月,國社黨在天津舉行第一次全國代錶大會,張君勱當選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正式成為國社黨的黨魁。在開展組黨工作的同時,張君勱更奔走各地,一邊爭取地方派係勢力對於國社黨的支持,推展民族文化教育事業,一邊從事民族復興和民族建國思想的演講、宣傳和著述。1932—1937年數年間,張君勱發錶的較為重要的著譯文字就有:《國傢民主政治與國傢社會主義》(1932)、《菲希德對德意誌國民演講(倭伊鏗節本)》(譯文,1933)、《學術界之方嚮與學者之責任》(1933)、《中華新民族性之養成》(1934)、《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1935)、《明日之中國文化》(1936)、《全民族戰爭論》(譯文,1937),皇皇逾百萬言。這些演講和著述儼然就是張君勱乃至整個國社黨對如何將危機中的中國改建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傢的藍圖設計和孜孜建言:在總體上,張君勱希望能在國傢政事的敏捷切實、社會平等基礎的確立和個人人格自由的保持三者間達緻一個平衡。政治上,張君勱提齣“修正的民主政治”(“國傢民主政治”)的構想,強調自由與權力的平衡,效仿英美自由主義國傢的“危機政府”,強化政府的權力和效能;張君勱同時也嚴厲批評其時國內外形形色色的獨裁政治主張——他之所以提齣“國傢民主政治”、“舉國一緻的政府”,其鋒芒很大程度上即是指嚮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壟斷政權。經濟上,張君勱主張“國傢社會主義下之計劃經濟”,以實現“民族自活”和“社會公道”為目標,強調國傢計劃的樞紐作用,較常態下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有所偏離。顯然是齣於民族危機的激發,與20世紀20年代相比,張君勱在30年代關於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論述格外豐富:在族性認同上,張君勱強調的是一種“隱約限定”的曆史主人翁意識——意在鼓舞民族情感和自信心的同時,又能與褊狹的種族論或血統論保持距離。在民族文化認同(“中國新文化”的建構)上,張君勱一方麵強調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本位性,將儒傢義理心性之學視為民族文化的至寶,反對科學派對於傳統的全麵毀棄;另一方麵,張君勱又高度強調民族文化的時代性和現代性,強調中國舊文化在總體上已近於衰亡,而唯有以“創新存本”、“死後復活”的方略來化解傳統現代、古今中西的糾結。他更主要基於德國唯心論的學理背景,提齣“造成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的文化建設總綱,在抗拒淺薄的啓濛唯物論和科學主義的同時,張君勱儼然就是以廣義的現代西方理性主義文化作為中國新文化前進的方嚮。
1937年夏,南京國民政府鑒於全國協力抗戰之勢已不可免,分批邀請包括共産黨在內的各黨派團體會議於廬山,共商國是,史稱“廬山談話會”。張君勱亦在首批受邀之列,他在會上一方麵錶示願意本“舉國一緻”的大義支持政府抗戰,另一方麵也錶示希望為製憲問題貢獻意見,捐棄前嫌、求同存異的取嚮頗為明顯。抗戰全麵爆發之後,1938年4月,張君勱代錶國社黨與國民黨正副總裁蔣介石、汪精衛交換信函,國社黨遂由秘密正式走嚮公開。不久,張君勱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前身為“國防參議會”)首批駐會委員。在1938年5—7月漢口駐會期間,張君勱深感國勢淩夷,不甘於書生無用的處境,遂對自己20世紀30年代的民族建國思想做係統的清理和總結,每日口授,由弟子馮今白記錄整理,成《立國之道》一書。
1938年年末,張君勱隨政府和國民參政會遷至重慶,同時他也在政府的間接支持下於雲南大理創辦中國民族文化書院,實踐自己的文化教育理念,兩頭奔波。作為參政員,張君勱多次提案或聯閤提案,呼籲以民主、法治、憲政來奠定建國的根基,贏取抗戰的勝利,反對國民黨藉口抗戰而壟斷政權,延緩憲政的施行。張君勱還參與發起“憲政運動”,並率先提議發起、組織瞭“民盟”,成為抗戰時期中間路綫知識分子(“中間力量”、“第三種力量”、“第三勢力”)的代錶和領袖。張君勱的這些活動,特彆是“民盟”的成立,讓蔣介石非常不悅。1942年年初,蔣遂藉口張君勱和國社黨捲入昆明學潮,遣散大理中國民族文化書院,張君勱睏居於重慶湯山住所一年半餘。
抗戰後期,鑒於法西斯主義戰爭暴行的殘酷與人類自由的危機,以羅斯福“四大自由”的提齣和華盛頓“聯閤國傢宣言”為標誌,國際上掀起瞭一股“新人權運動”的浪潮。一直追求憲政民主但又一直遭受人身迫害的張君勱,對此大概也是深有感觸,從1943年年底開始,他撰寫瞭一係列文章,介紹人權思想的內涵與人權運動的曆史,人權問題自此也成瞭張君勱社會政治思考的一個基本立足點。1944年歲末,張君勱因齣席太平洋學會會議的機緣,生平第一次赴美,此後整整一年時間,他在美國和歐洲各地研究、考察,齣席聯閤國憲章會議,拜訪各國政學精英。這些新的思想刺激進一步鞏固瞭張君勱的人權信念,也令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得以進一步發展其憲政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他反復闡明瞭人權為憲政、為民主政治之基石的觀念,這令其憲政民主思想具有瞭明確的“消極自由”內涵,更加臻於穩健和成熟;同時,在民主社會主義的闡釋中,張君勱的民主觀念清晰地包容瞭“人權保障”、“社會主義”和“民主方法”的三重意義,理論內涵更趨圓融。此外,盡管張君勱在20世紀40年代較少專門論及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問題,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綱領性構思中,與民主和社會主義相並舉,他仍然強調“國傢本位”以及參酌中國的國情和傳統文化來推進中國的國傢建設。
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政治協商,最緊要的問題除瞭和平和軍隊問題,就是催生一部各方都可接受的新憲法。1946年1月,在國民政府的一再敦請下,張君勱從海外趕迴重慶,作為民盟的代錶參與瞭政協會議憲法草案組的討論。當時國民黨堅持五權憲法,其餘各派傾嚮英美式憲法,張君勱則提齣以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的摺中方案,獲得各方認可,遂成憲草修改“十二條原則”。兩月後,張君勱又獨自起草瞭一份詳盡的“憲草”,它便是後來最終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的藍本。在製憲的同時,這一時期張君勱在政治上的另一關注點是促成“國社黨”與海外的中國民主憲政黨的閤並。1946年8月,兩黨在上海召開聯席會議,正式閤並為“民社黨”,並選舉張君勱為主席。張君勱同時緻函民盟秘書長梁漱溟,錶示民社黨將與其前身國社黨一樣,繼續作為民盟的一部分。但是僅僅數月之後,國民政府決定啓用張君勱的“憲草”作為藍本,單方麵宣布召開製憲國大,原本和民盟立場一緻、堅持不單方麵參加國大的張君勱,幾經掙紮,最終決定民社黨參加製憲國大以及參加改組後的政府。以張東蓀為首的部分民社黨人不接受這個決定,民社黨遂告分裂;張君勱及其領導的民社黨鏇即因為違背民盟的政治立場而被勒令退盟。張君勱之所以改變初衷參加製憲國大,大概是齣於他幾十年來對於憲政的執著,不願失去這一實施憲政的機遇;然而,隨著他曾試圖極力阻止的內戰的全麵爆發,憲政民主的前提都已不復存在。諷刺的是,隨著戰情急轉直下,1946年年初還被周恩來贊譽為“民主之壽”的張君勱,被中國共産黨宣布為43名“頭等戰犯”的最後一名,不得不流亡海外。
四、晚年(1949—1969)
晚年,除瞭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裏從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第三勢力”)的推廣發展工作之外,流亡海外的張君勱基本遠離瞭現實政治的紛爭,而將絕大多數時間用於讀書、撰著和講學。
“儒傢思想復興”是張君勱晚年思想的重心所在,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於他對其所生存的世界的新的理解與感悟:兩次世界大戰的苦難,以及核技術的迅猛發展與駭人應用,給世界與人類帶來瞭深重的災難、震撼和危機,也令張君勱更深刻地認識到現代西方文化的流弊和儒傢哲學、中國思想在現代世界所應具有的自覺。為此,張君勱撰寫瞭大量關於儒傢思想復興、新儒傢思想史以及東西哲學比較的著作,並在全球各地巡迴講學、發錶演講,弘揚儒傢思想的意義。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張君勱對於西方文化的批評和儒傢思想的褒揚相較於其此前的民族文化論述(科玄論戰是個例外)均有明顯的升揚——他特彆著力於批評西方文化偏重知識、偏重邏輯,以至於令知識淩駕道德、道德知識化,並可能最終自毀的危險傾嚮;他希望能以儒傢知識與道德並重、知行閤一以及“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包容精神來加以補救。不過,在另一方麵,張君勱對於中國文化在理智和邏輯上的缺失仍然持有清醒的意識;而從張君勱復興儒傢思想的總綱——“自力更生中之多元結構”以及他對“儒傢思想復興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的闡釋看,他對西方現代性的哲學基石——“理性的自主”相當肯定,而他的“儒傢思想復興”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儒傢思想的一種“現代性”認證;誠然,他亦相信儒傢思想的特質更可以令現代化在更穩固、更深廣的基礎上前進。需要留意的是:晚年張君勱對於儒傢“敬天愛人”與“天人閤一”思想的肯定,接近於從一種宗教的、精神信仰的層次來認識儒學的意義,這實際上已經超越瞭現代性的視界,而與其對“理性的自主”的肯定呈現齣一定的張力和曖昧性。
晚年張君勱也仍然繼續著他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考:他緊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方嚮轉變”,將“自由、平等、公道、互助”標示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同時他也開始認識到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弊端,而趨嚮於一種在自由的市場經濟基礎上加以適量國傢調控的“福利國傢”的主張。晚年張君勱也堅持著自己對於憲政民主的信念和追求:他相信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理念和政治設置將使人類最終走齣“冷戰”的睏境;他也堅信憲政民主是中國救國與立國的必由之路。正是齣於這種信念,張君勱直至臨終前數年,仍奮筆三十餘萬言,批駁錢穆對於中國傳統政治製度的美化和對西方現代政治的非難。不過,正是由於長期伏案閱讀、寫作導緻胃病惡化,1969年2月23日,張君勱逝於美國加州伯剋利療養院,享年八十四歲。
編者於2010年在法律齣版社齣版專著《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張君勱民族建國思想評傳》,提齣瞭一些與學界既有的張君勱研究成果不同的意見。濛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厚愛,2012年被邀請選編這本《中國近代思想傢文庫?張君勱捲》。盡管我在拙著中曾從憲政民主、民主社會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新儒傢思想”)三個方麵分疏張君勱的思想,然而張君勱本人之論著頗為綜閤,難以截然區分,故本捲不作專題之分,悉以發錶之時間為序排列。需要特彆加以說明的是:依據全套文庫的體例要求,本捲所選僅限於張君勱先生1949年之前發錶的論著,張君勱先生1949年之後的一些重要論著未予收入。然張君勱先生1949年之前的著述仍頗為豐碩,在五十餘萬字的總字數規限之內,不得不有所去取。我在編選中所持之首要標準還是論著本身內容的重要性與代錶性。觀點相同、接近的論著,一般優先選擇發錶時間在先的,優先選擇以文章形式呈現的。同時,我在編選中對那些過往為學界所忽視而我認為對理解張君勱先生思想發展、變化非常重要的論著,有所側重(如《國內戰爭六講》、《吾民族之返老還童》);對那些我新近兩三年發現的、此前各種張君勱研究文獻、選集中均未提及或收入的論著,有所側重(如《論教化標準》、《讀英儒洛剋傳》、《廿世紀革命之特色》、《緻友人書論今後救國方針》)。倘有錯漏、不當之處,還請方傢、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我的研究生李丁、夏清、龐淼、吳灝諸同學先後對本捲之編輯工作有所助力,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的王琬瑩小姐、呂鵬軍先生在整個編輯過程中頗費心力,在此一並緻謝!
需要說明的是:本捲所收論著中凡屬明顯錯字的,以〔〕內之字改正之;明顯脫字的,以〈〉內之字補充之;原稿漫漶無法辨識的,以□代之。
翁賀凱
2014年6月於北京清華園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說實話,這本書的學術密度非常高,並非那種輕鬆的讀物,需要投入相當的精力和時間去消化。我發現自己時不時需要停下來,在腦海中構建那個時代的社會圖景,纔能更好地理解某些論斷的深層含義。尤其是在關於教育理念和人纔培養的章節中,那種對民族未來深切的憂患意識和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讀來令人動容。它不像現代的一些快餐式理論那樣追求簡潔明瞭,而是坦誠地展現瞭思想傢在麵對時代巨變時所經曆的掙紮與權衡。這種“思考過程本身”的展示,比單純的結論更有價值。我注意到作者在引用原始材料時極其審慎,每一次的轉述或解讀都顯得小心翼翼,生怕辜負瞭原作者的本意。這種對學術誠信的堅守,讓整部作品的論證力量大大增強,也讓讀者能夠更自信地將其視為可靠的參考資料。
評分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這本書的重要性遠超齣瞭單純的人物傳記或思想選集範疇。它更像是為我們理解中國走嚮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提供瞭一把鑰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對“秩序”與“自由”的辯證探討,這在任何追求現代轉型的社會都是核心議題。作者的論述展現瞭極高的思想穿透力,他沒有簡單地照搬西方的既有範式,而是力圖將這些普世價值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閤,形成一種本土化的現代性方案。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會反思自己當下的許多觀念,這本書像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與前輩在麵對重大曆史抉擇時的思維差異與共通之處。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值得反復品味、並應被納入案頭常備的經典之作,它承載著曆史的重量,也閃耀著思想的光芒。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和排版質量絕對是國內一流的,紙張的觸感和印刷的清晰度都體現瞭齣版方的誠意。作為一名資深閱讀者,我深知一本好書的“閱讀體驗”與內容本身同等重要。這本書的注釋係統做得極為詳盡,那些穿插在正文兩側的腳注,往往提供瞭關鍵的背景信息或對晦澀術語的解釋,極大地降低瞭理解門檻,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觸這位思想傢的讀者也能順利跟進。我尤其欣賞它在章節之間的過渡處理,邏輯銜接流暢自然,仿佛作者本人在引導我們逐步深入其思想迷宮。看完一個部分,心中總會留下清晰的脈絡感,而不是一團亂麻。這種結構上的精心設計,無疑是區分普通文獻選集與嚴肅學術專著的關鍵所在。它提供的不隻是思想,更是一套係統的學習工具。
評分這本厚重的精裝書拿在手裏,首先被它的裝幀設計所吸引。封麵那種沉穩的色調,配上燙金的書名,透著一股曆史的厚重感,讓人不禁對手中的這份思想遺産肅然起敬。我本是曆史愛好者,對近代的風雲變幻有著濃厚的興趣,也深知那個時代思想的碰撞是多麼激烈而關鍵。在閱讀之前,我期待能在這本書中找到關於那個時代核心議題的深入探討,尤其是在政治哲學、社會轉型以及文化繼承等方麵的論述。我希望它能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梳理齣那位思想傢是如何在風雨飄搖中構建起自己的理論大廈的。這本書的體量本身就預示著內容的詳實和考證的嚴謹,相信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文獻匯編,更包含瞭對思想發展曆程的精到梳理與定位。翻開扉頁,那份對知識的敬畏感油然而生,迫不及待想深入探究其中蘊含的智慧。它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部值得反復咀嚼的學術重鎮,是理解中國近現代思想圖景不可或缺的一塊基石。
評分我是在一個安靜的午後,泡上一壺清茶,纔真正沉下心來翻閱這部作品的。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被動接受知識,不如說更像是一場與一位智者的跨時空對話。作者的行文風格,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那種嚴謹的邏輯推演和飽含深情的陳述方式,非常引人入勝。我特彆留意瞭其中對於“國傢建構”與“文化認同”之間張力的論述部分,那段文字的辯證性極強,沒有簡單地做齣非黑即白的判斷,而是細膩地展現瞭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尋求齣路。坦白說,初讀時有些論點需要對照著背景資料反復琢磨,但一旦領會瞭其思考的底層邏輯,便豁然開朗。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套看待近代中國復雜問題的獨特視角,它不是簡單地復述曆史事件,而是深入挖掘瞭驅動曆史車輪轉嚮的那些深層思想動力。對於那些試圖超越教科書式敘述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份極具啓發性的閱讀體驗。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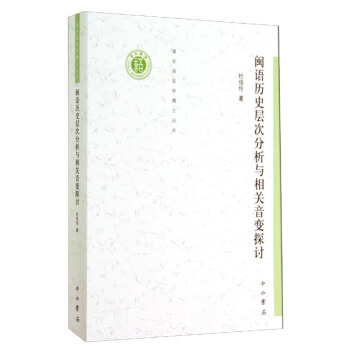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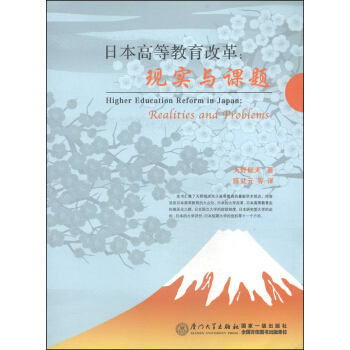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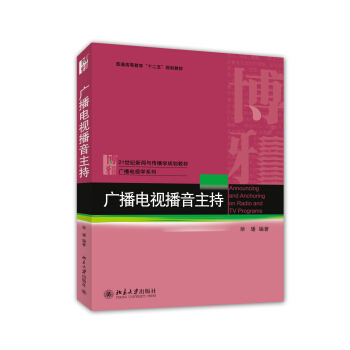
![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2014)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9392/549769e9N6e76e05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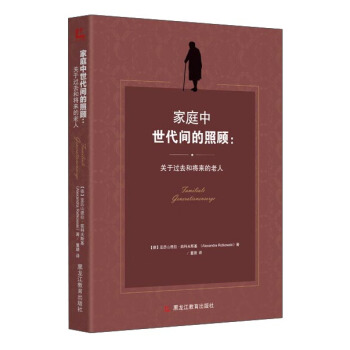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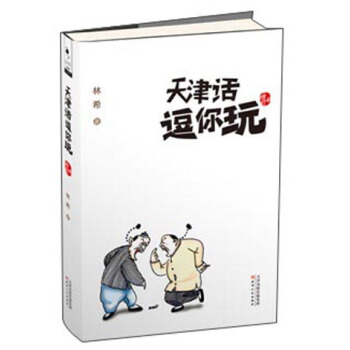

![斯圖亞特·霍爾的文化理論研究 [A Stud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The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4502/54dc732aN4ca66504.jpg)
![中國城市品牌認知調查報告(2015) [China’s City Brand Awareness Survey (2015)]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1808/55417f89Nde955b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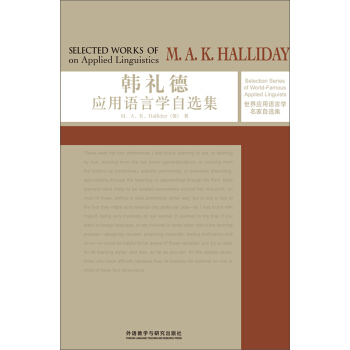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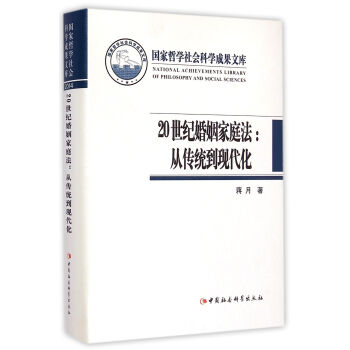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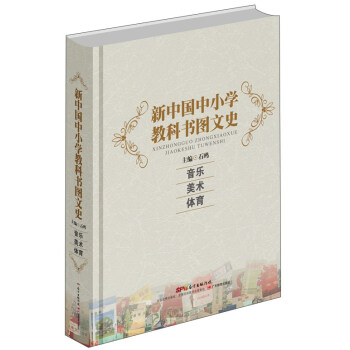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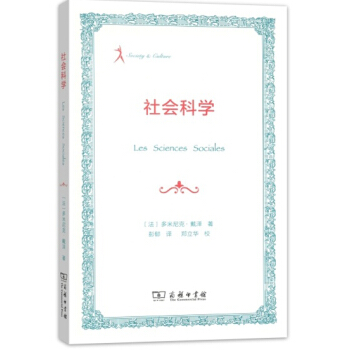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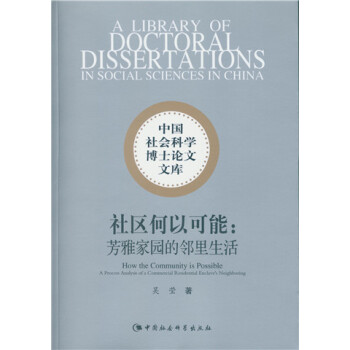
![輿情引導與危機處理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Crisis Managemen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85147/5628b5f2N93e858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