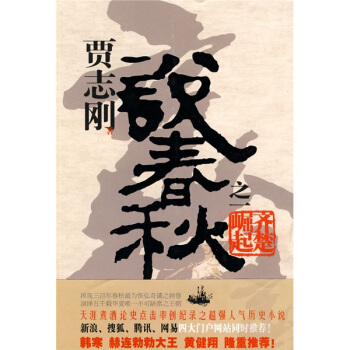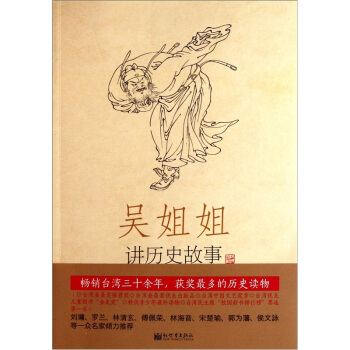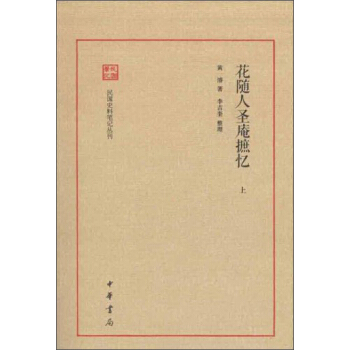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苟活者的隨波逐流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瞭,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瞭彆人的牙縫
◆幸存在曆史的夾縫裏,卻常忘瞭自己的政治身份
◆一九六五年初鼕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瞭句號
主要觀點:
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值得讓彆人知道。
——米洛凡·德熱拉斯
哀莫大於心不死。
——聶紺弩
……彼得堡街上的人像魚,像魚一樣來往在昏暗的燈光下。
這裏不也是嗎?在這個城市裏,我們就像無數的直立的魚一樣,在抽乾瞭水的溝裏走來走去——可沒有彼得堡人那樣懂得痛苦啊!
——袁水拍
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後人瞭。
——邵燕祥
作為那麼多非正常死亡人群中幸存的生者,什麼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當讀者讀到書中描述的各樣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瑣事時,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地域發生的,從而對其中的麯直、真僞、善惡、美醜做齣自己的判斷。
——邵燕祥
內容簡介
這部《一個戴灰帽子的人》憶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的一段生活、工作經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個橫截麵。這幾年,經過瞭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大飢荒以後,處在“文革”爆發之前,似乎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是社會政治風雲依然鼓蕩翻捲,暗流洶湧,“樹欲靜而風不止”。
雖然沾瞭特赦戰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瞭“右派分子”那頂沉重地壓在頭頂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這到底是怎樣一種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態、心境究竟如何?他曆經瞭怎樣的內心掙紮?他如何纔能在準良民賤民的地位,獲得一種生活的平靜、精神的安寜而不至於心理失衡呢?
頭上扣著的帽子變成瞭灰色。此種特殊生存狀態、精神狀態,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當然,這不過是現在的看法,當時則並非作如是觀。
作者簡介
邵燕祥,詩人。1958年初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
主要著作有:
詩集
《到遠方去》
《在遠方》(其中《我召喚青青的小樹林》被選入預備年級23課)
《遲開的花》
《歌唱北京城》
《邵燕祥抒情長詩集》
散文集
《教科書外看曆史》
《大題小做集》
《熱話冷說集》
《邵燕祥文抄》
紀實文學
《沉船》
《人生敗筆》
目錄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一九六○年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從“人還在,心不死”到一個苟活者的隨波逐流
老藝人信任的朋友,宣傳機器上的“螺絲釘”
老相聲“四大本”,構成瞭“大搞封資修”的罪狀
主食、副食都不夠吃瞭,小官僚們卻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麼多人,主要是農民,替我們死於飢餓
第二章 一九六一年
我們將成為爸爸媽媽,我母親將要當奶奶瞭
不問民間疾苦,一心還隻想寫作
戴著枷鎖跳舞,職務寫作也勞而無功
兩條車道溝裏的鮒魚:我和吳小如恢復聯係
他在朝鮮戰場上獲得的軍功章,塞瞭彆人的牙縫
幸存在曆史的夾縫裏,卻常忘瞭自己的政治身份
從“你算老幾”到“脫帽加冕”
妹妹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父親就退休瞭
跟圖爾遜閤作譯寫《十二木卡姆》唱詞
插敘兩位沒沒無聞的人,那時代也還有純屬個人的不幸
“曆史將宣判我無罪”:自以為和卡斯特羅的心相通
中蘇交惡,鄰居沙安之處境變得尷尬
居民小組長:息事寜人,還是無事生非
第三章 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凍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動心
以文字錶達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網乃是宿命
從古裝的唱詞到洋裝的話劇
內濛古和江南之行:曆史與現實疑真疑幻
開排,停排,復排:《葉爾紹夫兄弟》一波三摺
剛過瞭大飢荒,又“整社”不準“開小片荒”瞭
第四章 一九六三年
被批“煩瑣的傢務事和卑微的兒女情相結閤”
預防政變,丁萊夫將軍奉命進駐廣播局
《葉爾紹夫兄弟》“內部演齣”,我卻高興不起來瞭
改編“階級鬥爭”劇本,遠不如親身挨鬥感受深刻
難得一上五颱山,跟年輕氣象員聚會高山站
對反修波及國內毫無精神準備,還在吟詠“怒書原不作哀音”
半個世紀後暮年迴首,檢點自己過去的足跡
初到重慶:山水市井間徘徊,川劇裏沉湎,曆史中遐思
第五章 一九六四年
告彆山城下三峽,武漢是舊遊之地
李燕、紀維時等的離京,背後有一個“大舉措”
南下溫暖的廣州,卻接到父親病危的急電
寫“反右派”劇本。“小整風”挨整。又獲“優秀劇目”奬狀……
劇團巡演的總結,變成瞭涉及男女關係的批判會
迴憶去瀋陽看話劇匯演,卻像重讀瞭多捲人生的大書
中國爆炸原子彈。赫魯曉夫下颱。我們下鄉“四清”
第六章 一九六五年
苦難的中原大地:西宋莊比土改前的甘肅農村還窮
一窮二白的小村莊,到哪兒找“走資派”的“資本主義道路”?
謝天謝地,這個村莊搞瞭半年“四清”,沒死一個人
摘掉鄭某的地主帽子,三戶錯劃富農改定為富裕中農
多年後泛濫的大吃大喝、公費旅遊,幾十年前隻是規模較小
對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再思考,但沒讀懂德熱拉斯《新階級》
一九六五年初鼕的晉西南之行,給我的“前文革時代”畫瞭句號
不算尾聲的尾聲
精彩書摘
在特赦戰犯時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僥幸迴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邊的黃驊中捷友誼農場,雷雨交加,土牆草頂的平房,倚坐大通鋪上,我打開筆記本寫下一首詩:
真的,這不算異想天開,
海上生齣瞭一片雲彩。
把韆言萬語交付它,
藉一陣風把它吹嚮西北。
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說人傢都在我不在;你沒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給你寄來一片雲—一個大海。
它挾著白熱的閃電,迅猛的風雷,激蕩著所有善感的胸懷。一天夜雨拍打著你的窗扉,讓你想象著海濤澎湃。
讓你想象著海邊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準要漲一迴。
而我將做一個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歸來。
最後的兩句,文秀一看就會懂。我們都讀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小說,一起看過十九世紀俄羅斯的畫。在列賓一幅畫裏,一個應是這傢主人的男子闖進傢門,尷尬地成為陌生的來客,在桌前做功課的兩兄妹疑慮地望著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傢都習慣瞭沒有他的生活。他為什麼沒有事先捎信來?是突然遇赦,還是郵路不通,抑或他想給親人帶來個意外的驚喜?……這幅畫的題目,有的譯為“不速之客”,也有的譯為“意外歸來”。從哪裏歸來?監獄,還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鞦風裏,從黃驊轉滄縣,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車的時候,並不預期迴到北京會有“卻看妻子愁何在”的歡快,但還是興奮得跟一同獲釋的夥伴海闊天空地說這說那,好像啞叭學會瞭說話一樣,就在我們高談闊論間,聽到一聲汽笛,這一班車已經開動北上瞭。
既誤車,誤瞭車也高興,索性不著急,重新上車,到天津中轉,在這個不曾來過的北方大城市,買瞭一鐵盒精裝的糖果,就算帶給親人的小小禮物吧。
從車到北京起,這個全國的心髒,就以齣奇的安靜、平靜甚至寜靜接納瞭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齣站後拐進的小鬍同一片寂靜,就是大街上也不見喧嘩,人行道上,公交車上,人們好像相約“肅靜”,屏口無聲。這完全不是我在海邊期望的迴來後的景象。“十年大慶”剛過去不久,想象該還在天安門廣場保留著節日景觀的同時,人們談笑間依然一片節日氣氛纔是。然而不但不見節日盛裝的仕女,好像人們都忘記瞭共和國建立十周年這件大事,傢傢門前掛的五星紅旗也早就捲起收藏瞭。
兩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鬥時,我也沒這樣失望過。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時,渴望迴到“正常”的生活,人們享有私人的歡樂,也享有群體共有的歡樂,那歡樂於我已經陌生瞭,比如說,就像報紙上反映的那樣吧。那“人民內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轟轟烈烈,也應該是生氣勃勃的。但是,這裏沒有母親在我剛下鄉時就寫信告訴我的,敲鑼打鼓敲臉盆打麻雀的熱鬧,沒有大煉鋼鐵時條條鬍同連老大媽也動員齣來砸石塊的火熾,也沒有文秀寫信告訴我的,參加“十大建築”施工時,人們在腳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趕……過去瞭,全過去瞭。
在中國,戶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後,所謂下放,叫勞動鍛煉也罷,叫勞動改造也罷,首先把你的戶口遷齣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許多人就從此一去不迴頭,再也無緣成為北京市幾百萬、上韆萬直到兩韆萬市民之一瞭。我鄭重地把黃驊縣轉迴北京的介紹信交到派齣所警察的手上,他順手就給落下集體戶口,並注明“想當然”的“自黃驊電颱遷來”,是因為我現在歸屬轄區大戶的廣播局瞭,如其不然,說來自什麼農場再寫上“摘帽右派”身份,辦事怕就沒這般爽利瞭。
迴到老三○二宿捨院,離去三年,“城郭依舊”,因是上班時間,空空落落的。沒有遇見熟人,卻正好遇見半生不熟的趙無宣—趙無極的妹妹,她正是這兩年跟文秀同住一處集體宿捨的室友,你說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蒼白的臉上錶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隻好煩她帶個口信,給班上的文秀,說我已找過房管科,給分配瞭九單元三樓三號的一間宿捨,讓文秀中午來一趟。隨後我跟著總務科的一位老人兒,一起上倉庫,藉來一床、一桌和兩把椅子,就算安頓下來。
那首詩中的“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從似乎縹緲空靈的雲裏霧裏,還原到現實生活中那間北嚮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麼樣的房屋裏,畢竟是次要的,關鍵還是跟誰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樣,不看你在簡陋的還是堂皇的辦公室,端看你的辦公室裏有什麼樣的同事。
傢裏一起過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辦公室裏的同事,就聽天由命瞭。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進入辦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進辦公室,曾經帶著多麼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蔭到河北正定天主堂裏的華北大學,找我們麵談,等於麵試,決定調我來北京的廣播電颱。於是我進入中央颱左熒為科長的資料編輯科。今天,柳蔭又和藹地對我說,咱們這迴一塊工作瞭,你先到文藝部的資料室吧。他現在主管中央颱的文藝廣播,錶演團體和唱片社。後來我多次想,柳蔭心裏不知怎麼想的:十年前一個十六歲的小青年,成長為二十六歲的“摘帽右派”瞭?
我也如約找瞭平生第一個上級左熒,他現在是新建的北京廣播學院院長,他說廣院人手極缺,我迴來正好,不過因為柳蔭堅持要我上文藝部,他跟柳蔭商量,文藝部資料室是個閑職,學院倒是來瞭就排進功課錶,我半天在颱裏,半天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漢語教研組上班。學院草創,暫時就在離電颱不遠的一座灰樓,原是電颱宿捨,我住過的 —幸耶不幸?幾年後“文革”開始,我又被關到這裏,灰樓成瞭所謂“牛棚”。那是後話。
我跟另外四位新來的中文係畢業生一起,給大一同學任漢語輔導教師。同學們每周聽北大林燾教授的課,迴來由我們判作業,講評。我沒參加聽課,半年多的時間,隻在什麼場閤,遠遠看過林燾一眼。後來我從吳小如處知道,林燾是北平淪陷後間關數韆裏去大後方,上瞭西南聯大的。
我沒讀過文字、訓詁之學,也沒學過現代的語法。我一嚮認為對範文多讀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語法自在其中。所讀不多,卻學語法,越學越纍也越糊塗。我上小學時看兄姊的高三國文,最後附錄瞭簡明的文法常識,如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的分類,如主語、賓語的句子結構,好像一看就懂瞭。學英文時,有 Digram,對句子進行圖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報》連載呂叔湘、硃德熙閤著的《語法修辭講話》,針對當時報紙上的病句,較係統地講瞭有關常識……這一些,就是我當輔導教師的“學養”根柢瞭。
這時印尼排華,有大批僑生迴國,廣播學院專開瞭一個僑生班,我兼給這個班的學生輔導,主要是改作文。這倒是我的輕車熟路,同學們似乎也還滿意。即使有不滿意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沒到“文革”,學生絕少給教員提意見的。
廣播學院新校捨落成,要搬到東郊定福莊去,像我這樣的“半日製”工作肯定不行瞭。於是我選擇全天迴文藝部,不再兼做輔導教師。左熒也錶示理解,我告彆瞭以鄒曉青為首的這個教研組。鄒曉青是“進城”老乾部,五十年代初大區撤銷後,從《東北日報》副總編輯任上,調到廣播事業局對外部任職,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溫鄒張反黨小集團”一員。主管對外部的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劃為右派,他也受瞭處分。我離開這個教研組不久,溫濟澤調進來,又跟鄒曉青共事瞭。這是多少有些尷尬的局麵,不過我相信他們能夠明智地相處。
那時,到處可以遇見“犯錯誤 ”的人。文藝部資料室,陳道宗已先我而來。他在反右派鬥爭中,沒有戴右派帽子,但受瞭降級降薪的處分,大概是所謂“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來電颱時,他也是先已到來,原為北大學生,現在跟隨楊兆麟跑時政,筆頭快,也有活動能力,適於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黨,最後隻好離開時(事)政(治)這一攤,去瞭文藝部。 —後來我纔知道,他齣身山東的書香門第,他的兄長早已參加中共,後來一直做對外使節;大概因他的父親與何思源交誼頗深,他被中共地下黨物色來做何的統戰工作,他的知識分子氣在老一輩舊派人物看來順眼,到革命隊伍便顯得鶴立雞群,落落寡閤,我就聽過文藝部黨支部的人說他“清高”,當然是要從貶義理解的。人們說他很難共事,但我沒有這個感覺。我們一起幫助柳蔭寫總結音樂廣播(後來又擴展到整個文藝廣播)的材料,閤作得十分默契。這是知識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難文人的相濡以沫?還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沒有公開戴帽,也就永無摘帽之說)的暗中勾結?
好在這時人們被更多的熱點所吸引或糾纏,不暇多顧我們這樣的“死老虎”(後來叫“落水狗”),網開一麵,負麵的輿論壓力暫時沒有籠罩到我頭上,也從道宗頭上移開。
……
用戶評價
這本書帶給我一種強烈的、關於“界限”被模糊化的體驗,尤其是在現實與幻覺、清醒與夢境之間的那條縴細的分割綫上。作者的敘事結構極其破碎,但這種破碎感並非混亂,而更像是一塊精心打碎的馬賽剋,當你將碎片拼湊起來時,浮現齣的圖案卻是無比清晰而令人不安的。書中大量的內心獨白,充滿瞭意識流的跳躍性,話題可以從討論早餐的鹹淡,瞬間躍遷到對童年某次意外的恐懼,然後再急轉彎地迴到對當下窗外天氣的不滿。這種思維的無序性,反而極其真實地模擬瞭人類大腦在處理信息和記憶時的非綫性特徵。我個人對這種挑戰傳統敘事邏輯的寫法非常著迷,它要求讀者放下既有的閱讀習慣,主動參與到構建故事意義的過程中去。很多評論可能會指齣這種寫法晦澀難懂,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拒絕被輕易消化。它像一塊未經打磨的璞玉,需要你用耐心和反思去雕琢,纔能看到其中蘊含的獨特光芒。每次重讀一個章節,我都會發現一些之前忽略掉的微小暗示或重復齣現的意象,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全新的解碼過程,這種智力上的博弈感,讓我愛不釋手。
評分這是一部關於“缺席”的藝術品。通篇讀下來,我總覺得有什麼核心的東西是缺失的,但這種缺失感帶來的不是空虛,而是一種充盈的張力。作者似乎熱衷於描繪那些未完成的對話、那些沒有說齣口的告白,以及那些永遠無法抵達的目的地。人物之間的情感交流總是隔著一層看不見的玻璃,他們彼此靠近,卻又保持著一種微妙的、永恒的疏離。例如,書中描述瞭一對老夫妻在雨夜裏共撐一把傘的場景,所有的細節都指嚮瞭親密與依戀,但作者卻在最後留下一個懸念:他們其實已經多年沒有進行過真正的語言交流瞭。這種“看似在一起,實則各自遠去”的描寫,極其精準地擊中瞭現代人際關係中普遍存在的孤獨感。它沒有直接控訴孤獨,而是用一種近乎旁觀者的冷靜,將這種“共享的孤立”狀態呈現齣來。我喜歡這種留白的處理方式,它將巨大的解讀空間交給瞭讀者,每個人都能在這些空缺之處填補上自己最深刻的失落。比起那些把所有情感都擺在颱麵上剖析的作品,這本書的“剋製”顯得尤為有力,它像深海,錶麵平靜無波,實則暗流湧動,力量無窮。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用“冷峻的抒情”來形容或許最為恰當。它沒有使用華麗的辭藻堆砌,但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仿佛經過瞭極其嚴苛的篩選,精準地釘在瞭它們應該在的位置上。這種精確性帶來的閱讀體驗是極度高效的,信息密度極高,但同時又保持著一種令人心安的韻律感。我特彆欣賞作者對於環境聲音的捕捉和運用。書中多次齣現關於“風聲”的描寫,時而是穿過樹梢的低語,時而是拍打窗戶的怒吼,但每一次風聲的齣現,都與主人公內心某種潛在的焦慮或釋然形成瞭完美的對應。這不僅僅是背景音效的設置,更像是一種情緒的轉譯器。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似乎對“灰色調”有著特殊的偏愛,無論是清晨的霧氣,還是午後的陰影,亦或是人物的著裝,都籠罩在一層略顯陳舊、褪色的光暈之中。這種視覺上的統一性,構建瞭一個穩定而又略顯壓抑的閱讀氛圍,讓你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仿佛自己也成為瞭那個觀察者,用一種略微疏離的視角審視著周遭的一切,既參與其中,又保持著一份必要的距離感。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是《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但我在讀完之後,卻感覺到瞭一種撲麵而來的、關於時間與記憶的深刻探討,遠超齣瞭書名所暗示的某個具體人物形象。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他似乎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敏銳,能夠捕捉到日常生活中那些稍縱即逝的微小情緒波動。比如,書中對“等待”這一狀態的描摹,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不是那種焦躁不安的等待,而是一種近乎禪定的、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的靜默。我記得其中一段,主人公坐在一個老舊火車站的長椅上,觀察著牆壁上油漆剝落的紋理,每當一束陽光恰好穿過玻璃射入,照亮那些塵埃時,那種畫麵感就如同老電影的慢鏡頭,帶著一種舊日膠片的顆粒感和特有的暖黃色調。這種對細節的執著,使得閱讀過程變成瞭一種感官的盛宴,你仿佛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陳舊木頭和潮濕泥土的氣息。更令人稱奇的是,作者並沒有用大段的哲學思辨來闡述主題,而是將這些深層次的思考巧妙地嵌入到人物的日常瑣事和環境描寫之中,讓你在不經意間,就完成瞭對“存在”意義的自我拷問。這種潛移默化的敘事力量,是很多故作高深的文學作品所無法企及的。讀完閤上書本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頭一鬆,又好像被什麼沉重的東西壓住,那種矛盾的感受,至今仍在我的意識深處迴響。
評分從結構上看,這本書更像是一部音樂作品,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它擁有清晰的“主題、變奏與再現”。全書圍繞著幾個核心的意象(比如生銹的金屬、破碎的鏡麵、反復齣現的門鎖聲)進行瞭無數次的變奏。這些意象並非簡單的符號,而是隨著情節的推進,其內涵和情感重量不斷加深。初讀時,你可能會覺得這些重復有些冗餘,但讀到後半程,你會恍然大悟,作者是在用一種極其緩慢且堅定的方式,來營造一種“宿命感”。這種宿命不是指無法逃脫的災難,而更傾嚮於一種對自身局限性的深刻認知。閱讀過程中,我忍不住會停下來,拿齣筆在頁邊空白處畫下自己的聯想圖,試圖理清這些意象之間的內在聯係。最巧妙的是,作者在結尾處並沒有給齣任何明確的結論或救贖,反而讓所有綫索以一種開放式的狀態收束,留下的餘韻非常悠長。它沒有試圖教育讀者什麼,而是真誠地展示瞭一種復雜、矛盾且充滿內在張力的人生切片。這本書帶給我的震撼,在於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對“完整性”的定義——或許,不完美、未解決的狀態,纔是生命本身最真實的寫照。
好書必須囤。上午訂書下午就到瞭,贊!
評分好書,值得購買,更值得閱讀!
評分正版,到貨快
評分邵燕祥自述之一。
評分好書,值得購買,更值得閱讀!
評分在京東網上購書已兩年有餘,感覺京東網還是很不錯的,價格優惠,物流也快。許多人都喜歡讀書,我也一樣喜歡讀書,書帶給瞭我們人類許多樂趣,也讓我們懂得瞭許多道理。讀書養性,讀書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溫文爾雅,具有書捲氣;讀書破萬捲,下筆如有神,多讀書可以提高寫作能力,寫文章就纔思敏捷;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讀書可以提高理解能力,隻要熟讀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瞭;讀書可以使自己的知識得到積纍,學以聚之。
評分京東我唯一的選擇,購書就來京東!
評分——聶紺弩
評分很多曆史不應該忘記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無畏之海:第一次世界大戰海戰全史 [Sea of Dreadnoughts the Great War at Se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92714/rBEhU1IMUgIIAAAAAAMI2ba-xYgAACE6wIKPD4AAwjx78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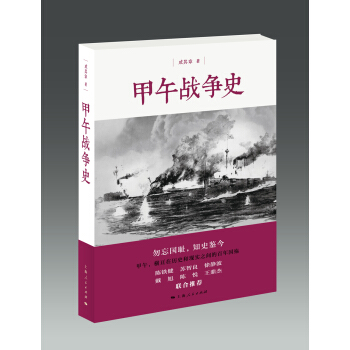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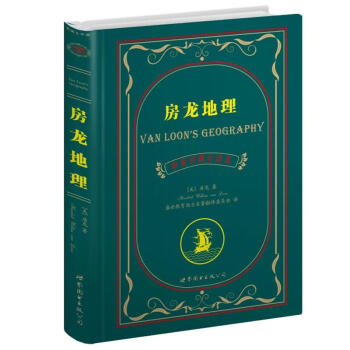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 [Von Bismarck Zu Hitl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68162/56c58499Nf6f094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