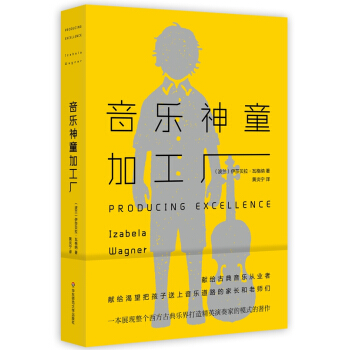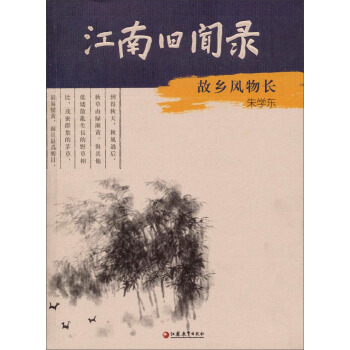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是作者朱学东通过笔触,寻找自己童年的记忆,对年少时曾经走过的路、发生的事,所见所闻的记录和随感。内容极具江南乡土气息和人文特色。文笔清秀,易于阅读。《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主要写作者对故乡风物的回忆,从中反映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页插图
目录
水花生浴锅旧事
我爱荷花郎
失落的油菜花
消失的做坯
柳笛声残
失落的竹枪
拎着板凳上学的日子
抢抛梁
牛背上的童年
偷甘蔗
麦堆里的秘密
钓鱼的大头针时代
门板上的童年
消失的乌鹊麦
搪蛳螺
造桥记
草塘里的童年
打田鼠
远去的帆影
看夜更
我爱红嘴绿鹦哥
消失的糠虾
造楼房
拍麦
种化肥
捉虾记
纳鞋底
风车
扁连枷
水缸里的记忆
洋灯故事
扑火的飞蛾
没有洗发液的岁月
消失的野泳
学游泳
沟渠里游水
秧田里的记忆
竹园惊梦
知了声声
竹廊记忆
脚炉忆旧
晒太阳
换糖佬
父亲的脚盆
笃镰刀游戏
放野火
点年财
捉蜻蜒
请灰姑娘
故乡的杆棵
故乡的蛇
棉茧头草
拖网时代
做秧田
拔秧记忆
有关莳秧的记忆
追车少年
捡麦穗
没有儿童节的童年
记忆中的癞蛤蟆
拔茅针
摘刺苔
乌绒树
精彩书摘
水花生前不久太太在江南,拍了张植物照片发我,问我何物。
我一看照片,一个激灵。水花生!水花生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太深了。
自我有记忆起,水花生便与我们的生活牢牢纠缠在了一起。
时至今日,故乡水域,仍饱受水花生之害。
在我的记忆中,长在河里的水花生,首先是一种饲料,俗称猪草,可以喂猪喂羊。
我很小的时候,便跟着祖父去打猪草,打水花生。
打水花生的工具,通常也是耙河蚌的钉耙,把手是一根特别长的竹竿,头上是一个小钉耙。
把手要长,是因为站在岸上要伸到河里才能钩拉住水花生。
打水花生要讲诀窍。水花生生长时交叉连接,层层叠叠,可不易打了。
通常,会从一大块水花生的边缘开始,钉耙下去,钩住一部分,使劲拉扽,拉一拉,扽一扽,以使局部与整块撕裂,拖到岸边,然后摁在水里荡一荡,洗掉水花生根部的水锈污物,撩起,放在苗篮里,沥干水。
来来回回,直到苗篮放不下了,便挑着苗篮满载而归。
因为水花生交织群生,一拉一于屯之间,有时难免会把钉耙拉脱落水。若是纠缠在水花生间,那倒简单,下水游过去捡起来即可。最怕沉到河底,得潜水去摸,水花生层层密密,不透气,若潜在水花生下,危险很大。但钉耙值钱,必得想办法弄回来。即便摸不回来,也要用另一把钉耙到水底像耙河蚌似的,把钉耙给耙回来。
水花生打回家后,一般用铡刀切成段,可以生着喂猪,也可以煮熟喂猪。
喂猪时,无论生熟,都加些麦屑搅拌,猪更喜欢。
不过,水花生要是喂羊,需要沥干水,否则羊吃了会闹肚子。
兔子则一般不喜欢吃水花生。水花生湿,兔子吃了易闹肚子。
冬天的时候,也会打上许多水花生,晒干了堆放着,等天冷了,没青草了,喂羊,或者垫羊圈。
等我们年岁渐长,已经能够扛起长竿钉耙的时候,打水花生的任务,便落到了我们头上。虽然最初挑不动苗篮,是兄弟用竹竿扁担扛着一筐水花生回家的。
打水花生的任务,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上高中后,家里人希望我好好读书考大学,这打水花生的活,重新落到了祖父身上,有时父亲也会帮着打。
除了打猪草,水花生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还有其他记忆。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夏日午后,故乡的河流碧波荡漾,蓝天倒映,河里总有一块面积不算太大的水花生,嫩绿的枝叶白色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
嬉水的顽童,通常有两个重要的游戏,与水花生相关。
一是练习在水花生上行走,看谁“轻功好”,走得远。
因为水花生的生长习性,河面上水花生的茎叶下,根须相互攀缘,交织成厚厚的一层,相互牵制,重物在其上,也不易下沉。
一脚深一脚浅,小心翼翼地走在水花生上,水从水花生丛渗出,先是脚底见水了,接着水没过了脚面,越往前走,水花生被压得下沉得越厉害。
终于,脚下的水花生被撑裂开了,人落水了,周围是顽童们的一阵阵欢呼。
二是潜水,看谁水性好,能够潜泳过一摊水花生。
通常,大人都会警告小孩,不准在水花生下潜泳,怕水性不好,半途要透气,却被水花生压住,透不得气而憋死。小时候听说,周边就有小孩这样淹死的。
不过,这样的警告通常会成为顽童的耳边风,一旦下水,什么警告都没用了。
我小时候也经常和同伴们一起练习钻水花生,若是半途憋不住了,便用头使劲顶水花生,同时用手扒拉,弄开一些缝隙,吸口气,以便继续,虽然紧张,倒也没有被憋着过。年轻时的肺活量,大抵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其实,还有一种水里游戏也与水花生关联。
故乡河里盛产鲢鱼。夏天嬉水的顽童使劲在河里折腾,常常弄得鲢鱼乱跳,有不幸的鲢鱼,跳出水面后落在了水花生上,只能算自己倒霉。一帮小子们一看鲢鱼在水花生上挣扎,便奋力游过去,爬上水花生,落在上面的鲢鱼,也就手到擒来,被迫成了人家晚饭的美味。
不过,水花生的根须比较脏,沾染了常常让人皮肤发痒,总要好好洗洗才行。
除了劳作和美妙的记忆外,水花生还有可怕的记忆。
水花生是外来物种,原产南美,故乡大规模养殖,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养殖的目的就是作为猪饲料。
没想到,这水花生非常霸道,故乡的水土气温又特别适合它,一种下去,便得势不饶人,不知疲倦地向外扩张,蔓延不可收拾。
……
前言/序言
故乡在江南,在童年的记忆里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赫尔德(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北上求学,在陌生的京城拜望客居此地多年的乡邻旧戚时,突然发现,我的那些在北京读书工作了一辈子的前辈乡贤们,一个个操着极为奇怪的普通话,简直就是故乡方言的翻版,只不过声调高低起伏,显示出了努力靠拢北方腔调的残存。
须知,我故乡方言,几乎找不到与如今流行的普通话的一丝影子,当年我在北京讲方言,还经常被笑话为“跟日本话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长辈,绝大多数人年轻时说普通话并不是这样。年岁越长,乡音越重,到最后几乎全部回归了儿时的音调,无论是文字学者,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普通职员、达官贵人,我所接触认识的前辈乡贤,无一例外。
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有此魔力?我向乡邻旧戚请教,他们只知道本就是这样;我向语言学者请教,他们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我也没有在文献中发现这样的研究……直到有一天,我在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里,发现了这变化背后的隐秘逻辑和魔力所在:“捷克人民的歌声这般甜蜜又深沉;被它感动的心灵,欣喜得想要哭泣。
当一个儿童在土豆地里咿语;穿过长夜守望者的梦,它的清唱来临。
纵使你远远离开,到世上最寂寞的所在,往后的岁月,它执着的声音,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里尔克,民歌)里尔克的谣曲,让我心旌摇荡。
不是别的,是出生时依托的那块土地的造化神秀,是跟着亲人学舌的咿语乡音,深种于心,溶进了血液躯体,一开始就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外部环境,会让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去学习接受并习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咿语,此时也会悄然躲进某个角落,让位于生活工作的现实。
但是,当工作生活的世俗压力一旦消退,那早已深种于心、暂时避让的记忆,就会悄然溢出,慢慢滋长,“往后的岁月,它执着的声音,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纵使你远在海角天涯。
岂止是萦回在心里,它最终将成为我们的主宰,让我们在愉快而悲伤的回忆和诉说中,渐渐老去。
故乡的水土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人们出生的时候,便规定了他们的未来。
人们在那里住过,便会受其影响。住越久,它便将每一个人缠住越久。
这才是故乡。
我的故乡在江南,曾是季札领地,今属江苏常州武进。
故乡沃野千里,蔚蓝的天底下,遍地绿意,河渠纵横,水波晶莹。村庄掩映杂树竹园中,鸡鸣狗叫之声,此起彼伏。热闹中透着大地的沉静。
故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就连凶悍的台风到此,也变得温驯了。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是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
羡慕什么?春天地上随便挖口塘,春水漫过,经过酷夏,待到秋冬时,小儿捞鱼虾忙,这便是故乡旧时风物,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我们的祖辈父辈,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出生在武进的一个叫西朱西的小村庄,在常州南,离市区有二十几公里。我十八岁离开故乡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只有十四户人家,如今各家开枝散叶,各造大房,隐隐然已成一个大村子了。
西朱西坐北朝南,村子虽小,却不脱江南乡村的格局风情,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西朱西坐落在两条河间,东有永安河,西有永胜河。父亲曾给我手绘过故乡地势图,告诉我,故乡之地,河道交错,地势虽高却平,状如龟板,俗称乌龟地,讨口彩取其谐音,祖传富贵地,既富且贵之地。
村口有条小河,码头离我家不过十来米。村子向南五百米内,过去有三条东西向的河流,东入永安河,西连永胜河。水势平缓,水波清莹。老风水说,出门一里三横河,水清则灵,好地方。这四条河都是我们小时候钓鱼嬉水玩耍的好地方,曾耗费了我多少光阴!确实是好地方。武进前黄北边的朱氏宗祠,即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按家谱,也算是朱熹苗裔。我们宗祠也不辱先祖盛名,村里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读书人,尤以教师为多。
“土改”时,宗祠被分,我曾祖是江阴南漂而来扛长工最后入赘落户本族的,算是村里最穷的,所以分得宗祠两间,另外的给了村里当仓库。1985年我拿到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们邻村一位同宗同学的母亲,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生先生的弟媳,羡慕地跟我祖母说,你们家风水好啊,有祖宗庇佑啊。
因是宗祠所在,西朱西祖产颇丰。虽然土改分给了其他村不少,但村里人均土地在江南依然不低。而且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故乡粮食产量还是颇高的。
但是,缴了公粮之后,留给自己的口粮有限,像我家当年,只有父母是壮劳力,老人孩子多,以长辈们的勤劳,也还常常不够吃,直到分田之后,才解决问题。
我小时发育不良,与缺少营养有关。以至于我上高三时,父母担心我将来考大学,即便考分够了,也怕身体赢弱,‘不能被录取,绞尽脑汁寻找偏方给我炖童子鸡之类的食物,试图弥补早年营养不良之缺憾。
还只能在地上爬的时候,长辈们下地,我们通常被带到田间地头,在地上自己折腾,就像泥娃。稍长,父母长辈便已无暇顾及。于是,小小年纪,我们或在蓝天白云下割草戏耍,或穿梭于猪圈羊栏灶台柴房间,或忙碌于自留地上,或帮着大人割稻插秧打场……少年不识愁和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天地为伴,与自然为伴,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度过了自己自由放任的童年时代。这些快乐,常常让我们忘却物质生活的匮乏的痛苦,“没记性”。
因为生活所迫,在我学会“狗爬”之后,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每年夏天,我腰里系着一个蛇皮袋,跟着父亲和堂叔,摸甲鱼贴补家用。彼时我光着脚,追逐着父叔的足迹,逢河过河,遇田过田,东走西奔,丈量着故乡的水土,熟悉了故乡周边四邻八村的几乎每一条河,每一块高埂。
后来跟父母兄弟聊及过去,自然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我问父亲,也问自己:这么富饶而美好的地方,像你们这么勤劳,我们还从小当童工,要有多大的本事,才能把这样的地方治理到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水平?父亲默然无语。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1921年1月,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里,这样写下了对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的纠结。
相比先生所看到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么多年之后,我的故乡呈现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色:旧时故园成了“新城里人”的商品房和工业区。
崭新宽阔的马路,鳞次栉比的高楼,齐整漂亮的厂房,密布开发中的工地,以及来往喧闹的车流,操着各种方言底色普通话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繁华热烈,生机勃勃。
我的故乡是进步的,崭新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不过,这进步崭新的故乡,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了。它正以游子无法理解的速度,继续更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迅速压过了对古老传统的尊崇,除了游子和老人,越来越多故乡的年轻人欢迎这种变化的到来。
当然新是有代价的。当年蓝天碧水白帆南通宜兴北通湖塘常州的永安河永胜河,前者成了臭水沟,臭水日日夜夜呜咽流淌,几经治理而不清。而永胜河,当我驱车经过曾经的港桥古镇所在时,只能看到一座新桥上写着永胜河桥四个字,边上是一条几乎一步就能跨过的长满杂草的沟——当年这两条河,可是故乡与外界交通的主要水道啊。
当我站在旧石桥上,指着污臭呜咽远去的河流,得费劲向我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解释,我小时候就在这桥上,在河边的杨树上,往这河里跳跃游泳,清澈的河水渴了就可以喝,这绝不是谎言——我的孩子自小学游泳,却从未在她父亲游过泳的河下过水;我得让孩子相信,我小时候房前这地里夏天遍地蛙鸣,萤火虫漫天飞舞,春天挖口塘,秋冬满塘小鱼虾,也不是神话——在故乡的夏夜,我的孩子从未见过萤火虫……如今的故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日新月异,目力所及处,必有塔吊工地,路和建筑干篇一律,越来越找不出故乡的影子,除了河边村头那些杂树。
格式化——我的朋友用了一个电脑用户熟悉的概念,总结了故乡乃至整个中国的进步与崭新。
格式化意味着清零,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另一面则是与传统的割袍断义。
那些被迫洗脚上楼的父辈们,行将告别张弛有度、年岁有盼以及守望相助、彼此熟悉的生活,逐渐像城里人一样,习惯紧张无度且冷漠无助。他们将再也找不到熟悉的工作,找不到熟悉的生活。他们最终将成为断线的风筝,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就像一棵棵被斫断了根的树……但是,变化是一定要来的。
“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鲁迅先生沉郁的笔调,或许就是提前对现代化城市化代价的一种无奈的指示。
我每年都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兄弟。
每次回家,尤其最近这些年,我都会独自一人,漫步在四邻八村间的村路和竹园杂树边,驻足凝思,熟悉的场景正在一个个消失,故乡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故乡风物曾经历数百年而不变,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的父亲,直到我的少年时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故乡的风物,变化有限。
历史上,与传统的决裂,历战乱、新文化运动而“破四旧”、“文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尚能藕断丝连。但在推土机下,传统瞬间幻化成一堆堆瓦砾和零碎的记忆。
历史和精神的断裂,发生得如此迅捷,如此彻底,甚至挽歌都来不及唱。
人们抛弃了自己的祖居祖坟,也就埋葬了自己的故乡。
不是没有人在乎。
“尽管我对个人自由的长期辩护,但我从来没有被诱惑到像有些人那样,以这种个人自由为名而否定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语言……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然纽带的拒绝诚然崇高却误入歧途。”以赛亚·伯林告诫我。其实,在精神上,我从来没有离开故乡,在北京,我被同乡戏称“前黄沙文主义者”。
两年前的春节,我偶尔拍了一张家里的老式浴锅照片(至今的冬天,我仍喜欢泡这大铁锅),发在了微博上,我的同乡好友王亦农君提醒我,能不能写篇关于浴锅洗澡风俗的文章?亦农君一言,提醒了我。尽管此前我也零零碎碎地写了些关于故乡风物的回忆,但也就是从此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记忆中的故乡旧闻记录下来,而且,一旦动笔,思绪便如潮水般奔涌而出,没有腹稿,没有雕琢打磨,信马由缰,写了便贴在新浪我的博客里。
我没有想到,这些散记最终引得了那些与我有相似生活经历的朋友同学和故乡许多人的共鸣。他们给我点题,鼓励并支持我坚持写下去。
“失去故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所”。于是,我就像法兰克福的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在异乡的城市,灯红酒绿的喧闹后,努力通过笔触,寻找自己童年的记忆和回家的路。所有怀想,都在梦里江南,都在那些永不逝去的旧闻笑谈中……萨义德说,只有经历过两种文化的人才能理解流亡者。对于正在失去故乡的人来说,其实就像流亡者一样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感触最深。
我的生于斯葬于斯的祖辈们,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变化,于他们,这一切太平淡了。
我的父辈们,他们经历了这种变化,而且仍将忍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欢乐、不适,甚至煎熬,但他们当年受教育的水平,他们为讨生活而努力的忙乱,常常不能让他们有时间有能力记录曾经的生活。
到我们的下一代,故乡已经是新的了,他们自然没有那些美好而痛苦的记忆。
因此,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记录渐行渐远的江南故乡旧时生活的担子,自然要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
于是,便有了这部《江南旧闻录》,尽管那些陈年往事永远絮叨不完。
这不止是对故乡远去时代的记录,更是为我自己,为我的父母兄弟,为我的孩子所写的书:没有这块土地,便没有我。
无论它发生什么改变,它终将是我的牵挂。
感谢我的女儿朱佩玮,你是我一切努力的动力。
感谢我的太太谷丽影,没有你的支持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感谢我的父母兄弟,没有你们,便没有一切。
感谢我的同学老乡潘建岳、马志良、邹忠伟、丁学兵、盛志峰、眭怀福、陈秋良、蒋国锋、徐卫东、王岷颜、羌砾国、周志兴、诸雄潮、陈文伟、姚青松、康晓东、陈新华、王其涵、郭小明、管建新、周志兴、诸雄潮诸君,你们的督促、点题和表扬,让我下笔如神。
感谢王亦农君,不吝墨宝,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感谢我多年的朋友诸暨郭建欢君,为本书配图及提出建议。
感谢正知书院我的院士朋友们对我写作的激励。
感谢我的老友新朋江建文、顾芳、孙泽新、苏萍、路锦、沈向阳、张培忠、孙泽阳、张骏诸君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武进区委宣传部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感谢新浪网新浪博客,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刊布在我在新浪的实名博客上,感谢新浪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的支持。
感谢《北京青年报》和《中国经济报告》,感谢“腾讯大家”的编辑们,你们的支持,让我故乡的故事得到了更多的传扬。
感谢腾讯《大家》及各位编辑对我写作的鼓励。
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我的老友新朋朱永贞、张平、孙兴春、孔融诸君对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2013年11月19日于旭日嘉园
用户评价
拿到《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扉页上那淡淡的水墨画,就足以让人心生向往。作者的文字,如同涓涓细流,缓缓地流入读者的心田,涤荡着心灵的尘埃。他笔下的江南,不是那种被商业化过度包装的旅游景点,而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故乡。我看到了那些古老的戏台,听到了那咿呀作响的锣鼓声,感受到了老人们在戏台前津津有味地观看的情景。我看到了那些布满青苔的石板路,感受到了雨后泥土的芬芳,看到了行人打着油纸伞,在雨中匆匆而过。我看到了那些传统的节日庆典,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看到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孩子们嬉笑打闹。作者对这些风物的描绘,充满了人文关怀,他不仅仅是在记录,更是在传承。他用他的文字,让那些即将消失的传统,那些被遗忘的习俗,重新焕发了生机。我尤其欣赏他对于“时间”的解读。他并没有回避时间的流逝,而是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拥抱时间,去理解时间。那些老去的房屋,老去的人,老去的记忆,在作者的笔下,都变成了珍贵的宝藏。这本书,就像是一部江南的史书,一部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关于记忆的史书。它让我看到了故乡的过去,也让我对故乡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它提醒着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要忘记那些曾经滋养我们的根,不要忘记那些让我们感到温暖的情感。这本书,是一次心灵的回归,一次对故乡深情的告白。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触动,在于它所展现的那种“慢”的生活节奏。在如今这个追求效率和速度的时代,作者用他的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悠闲与宁静的大门。他描绘的江南,是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有安详与从容。我看到了老人们坐在家门口,摇着扇子,谈论着家长里短,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我看到了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无忧无虑,充满了童趣。我看到了工匠们一丝不苟地打磨着手中的器物,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专注和耐心。这些场景,构成了江南独特的慢生活图景。作者的文字,就像是一位耐心的说书人,娓娓道来,不急不缓。他不会刻意去渲染什么,而是用最朴实的语言,去展现最真实的生活。他描绘的每一个风物,都仿佛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散发着温润的光泽。我尤其喜欢他对于“等待”的描绘。等待春天到来,等待收成的季节,等待亲人的归来,等待一份宁静。这种等待,不是焦虑和不安,而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对生活充满期待的态度。这本书,让我反思了现代生活的意义。我们是否在追逐速度的过程中,丢失了生活的本质?我们是否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忽略了内心的宁静?《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就像是一剂良药,能够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初心。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关于“慢”的艺术品鉴,一次关于“心”的温柔回响。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像是一本陈年的老相册,每一页都承载着一段珍贵的回忆。作者用一种极其克制却又饱含深情的方式,描绘了故乡那些渐渐远去的风物。我尤其欣赏他对于“声音”的捕捉。江南的声音,不仅仅是水流的潺潺,鸟儿的啾鸣,更有市井的喧闹,孩童的嬉笑,以及那些熟悉的乡音。他会描绘集市上小贩的吆喝声,那一声声带着乡土气息的叫卖,是那么的生动而鲜活。他会描绘夜深人静时,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那声音中带着安详和宁静。他甚至会描绘老人们在聊天时,那带着吴侬软语的腔调,那是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旋律。这些声音,如同一个个音符,串联起故乡的岁月,勾勒出故乡的轮廓。作者的文字,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能够将读者带入到一个久远而美好的时空。我常常在阅读的时候,不自觉地放慢速度,细细品味每一个字句,仿佛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打扰了那份宁静。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更是让我感动。比如,描写一位老奶奶用手搓洗衣服时,那布满皱纹的手,那略显粗糙的指甲,以及那衣服上淡淡的肥皂香,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岁月的痕迹。这些细节,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动人。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江南的风物,更是关于那些在故乡默默付出,默默奉献的人们。它让我看到了故乡的人情味,看到了故乡的温情。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一次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就像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每一个字都闪烁着智慧和温情。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的严谨,和对故乡深沉的爱,为我们挖掘和呈现了江南那些鲜为人知却又无比珍贵的风物。我特别赞赏书中对于“民俗”的细致描绘。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庆典,那些代代相传的习俗,都在作者笔下活了起来。比如,他会描绘端午节赛龙舟的盛况,不仅仅是比赛的激烈,更是那种全民参与的喜悦,那种对传统的尊重。他会描绘中秋节赏月的雅致,不仅仅是月光的美丽,更是那种家庭团聚的温馨。他甚至会描绘一些小小的习俗,比如逢年过节给长辈送去亲手制作的糕点,又比如在迁新居时,邀请邻里乡亲前来热闹一番。这些细节,虽然平凡,却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生命力。作者的文字,有一种穿透力,能够直达人心。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故作的煽情,只有真挚的情感和朴实的表达。读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淳朴善良的江南人民,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关怀,对邻里的友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风物志,更是一本关于“人”的书,一本关于“情”的书。它让我看到了故乡的温度,看到了故乡的灵魂。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关于“根”的寻根之旅,一次关于“爱”的深刻体验。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绝对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仿佛拥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将那些普通甚至有些陈旧的江南风物,描绘得生动而迷人。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吃”的描写,那些地道的江南美食,从食材的选择,到烹饪的过程,再到品尝的感受,都写得淋漓尽致,让人垂涎欲滴。比如,那一道道精美的时令点心,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对节气和时令的尊重;那一口口醇厚的米酒,不仅仅是饮品,更是承载了乡邻情谊和节日喜庆的象征。作者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描绘,他更深入到这些风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这道菜会在这时候出现,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承载了怎样的民俗。这种深度挖掘,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风物志,更是一本关于江南文化的百科全书。读着读着,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听到了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闻到了食物的香气。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某个夏日的午后,我坐在廊下,品尝着一口清凉的甜品,感受着微风拂过脸颊的惬意。作者的文字,充满了画面感和场景感,让人仿佛置身于其中,与书中的人物一同感受,一同经历。这本书,让我对江南的认识,从肤浅的“水乡”印象,上升到了更深层次的文化理解。它让我看到了江南独特的魅力,看到了江南人民的生活智慧,看到了江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关于江南的深度对话,一次关于故乡的情感连接。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无论我身在何处,当我翻开这本书,就会被一股浓浓的乡愁所包裹。作者的文字,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我与故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描绘的江南风物,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真实存在过的,或者依然存在着的生活印记。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于“四季”的描写。江南的四季,各有各的美,也各有各的韵味。春天的桃花灼灼,夏天的荷风送爽,秋天的稻浪滚滚,冬天的梅香暗送。作者将这些季节的变换,描绘得如诗如画,让人心驰神往。他不仅仅描绘了自然的景色,更描绘了人在不同季节里的生活状态。比如,春天的忙碌耕作,夏天的纳凉闲谈,秋天的丰收喜悦,冬天的围炉夜话。这些场景,构成了江南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作者的文字,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它能够驱散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带来一份宁静和祥和。读这本书,我仿佛能够听到故乡的声音,看到故乡的笑脸,感受到故乡的温暖。它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珍惜与家人的时光,珍惜与故乡的联系,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一份关于故乡的爱的馈赠。它让我的心,永远都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 读后感: 这份沉甸甸的《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刚拿到手里,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书页泛黄的质感,仿佛承载了时光的温度,触手可及。我本身就生长在江南水乡,对于书名中的“江南”二字,天然就带着一种深厚的感情。翻开第一页,一股淡淡的墨香伴随着文字扑面而来,瞬间将我拉回了遥远的童年记忆。书中对于故乡风物的描绘,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细腻的观察。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古老的石桥、潺潺的流水、以及四季更迭中那些细微的变幻,都在作者的笔下鲜活起来。我尤其喜欢他对于一些老物件的描写,比如一把用了几十年的竹椅,一张刻着花鸟的木桌,甚至是缝补衣裳时使用的针线笸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在作者的笔下却被赋予了生命,它们不仅仅是物品,更是承载了家族的历史,记录了岁月的痕迹,见证了人情的冷暖。读着读着,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奶奶坐在摇椅上,慢悠悠地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仿佛看到了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炊烟袅袅,香气四溢;仿佛看到了孩提时代的自己在巷子里追逐嬉戏,欢声笑语回荡在古老的屋檐下。作者的文字非常有画面感,他用词考究,意境深远,读来朗朗上口,却又耐人寻味。有时候,我会停下来,闭上眼睛,细细品味文字中的每一个细节,仿佛自己就置身于那片熟悉的土地,感受着那里的空气,聆听着那里的声音。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江南的风物,更是关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与时间慢慢对话的生活态度。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故乡,也让我对“故乡”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乡,从来都不是地理上的一个点,而是心灵深处的一种归属,一种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割舍的情感。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作者以其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了江南故乡那些充满诗意的风物。我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并非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的故乡人。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感情,无论是那古老的廊桥,还是那蜿蜒的河道,亦或是那遍布村庄的古树,在他笔下都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我尤其喜欢他对于“光影”的描绘。江南的光影,是那么的柔和而富有变化。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洒在青石板路上,泛着朦胧的光泽;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充满了生机;傍晚的夕阳余晖,将整个村庄染成一片金黄,美轮美奂。作者善于捕捉这些稍纵即逝的光影,并用文字将它们凝固下来,让读者能够感受到那份独特的美丽。书中的一些比喻和象征,更是妙不可言。他将故乡的山水比作温柔的母亲,将故乡的孩童比作活泼的精灵,将故乡的老人比作智慧的长者。这些比喻,不仅仅是文字的修饰,更是作者对故乡深厚情感的表达。读这本书,我仿佛走在江南的乡间小路上,感受着微风拂面,听着鸟儿歌唱,看着孩童嬉戏。我仿佛能够闻到泥土的芬芳,闻到花草的清香,闻到炊烟的味道。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家”的意义,让我更加珍惜与故乡的羁绊。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关于故乡的灵魂洗礼,一次关于生命的热爱宣言。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我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情去阅读,因为它触及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作者以一种温润如玉的笔触,描绘了江南那些渐渐淡去的旧日时光,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风物。我惊叹于他捕捉细节的能力,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微小之处,在他笔下却熠熠生辉。比如,他对江南老宅院落里那些精美的雕花木窗的描绘,不仅仅是窗的形态,更是窗外映照进来的光影,透过窗户看到的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以及窗前发生过的种种故事。他没有刻意去渲染悲伤或者怀旧,而是用一种平静而深情的叙述,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那种逝去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我尤其欣赏书中对时节变化的描绘,清明时节细雨蒙蒙,雨滴打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圈圈涟漪;仲夏夜,蛙声一片,萤火虫点点,照亮了寂静的乡村;秋日里,稻谷金黄,阵阵稻香随风飘散;冬日里,瑞雪初降,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纯净的白色。这些描写,不仅仅是简单的景物描写,更是一种时间的印记,一种生命轮回的写照。作者的文字像是一幅幅水墨画,淡雅而富有层次感,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读这本书,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孩子们在田埂上奔跑,老人们在门前闲谈的年代。那是一种缓慢而充实的生活,一种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生活。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像是一杯醇厚的老酒,越品越有味,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情。它让我重新思考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我们在追求物质繁荣的同时,是否正在失去一些更宝贵的东西。这本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故乡的样子,也照出了我自己的心。
评分《江南旧闻录:故乡风物长》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关于江南的书,不如说是一本关于“根”的书。作者用他细腻的笔触,将江南这片土地上那些古老而淳朴的风物,那些被时光冲刷却依旧闪耀的记忆,一点一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作为一个远离故乡多年的人,阅读这本书时,内心涌动的情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那些书中所描绘的场景,比如摇着橹船穿过窄窄的河巷,听着船夫悠扬的歌声;又比如春节时家家户户贴春联,空气中弥漫着年糕的香甜;再比如夏夜里,大家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前,摇着扇子,谈天说地的场景,都深深地触动了我。作者对细节的捕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不仅仅描写了建筑的宏伟,更描写了砖瓦上的青苔,石板路上的水渍,以及挂在墙上的老照片。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江南。我尤其喜欢他对于“人”的描写,那些朴实的农民,勤劳的渔民,慈祥的长辈,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共同构成了江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书中的人物,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温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勤劳善良,都让这本书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这本书,不仅仅唤醒了我对故乡的思念,更让我对“根”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那片承载着我们童年记忆的故乡,永远是我们心中最深的眷恋。这本书,就是一本献给所有“故乡在远方”的人的温暖慰藉。
评分晒太阳
评分——赫尔德(德)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北上求学,在陌生的京城拜望客居此地多年的乡邻旧戚时,突然发现,我的那些在北京读书工作了一辈子的前辈乡贤们,一个个操着极为奇怪的普通话,简直就是故乡方言的翻版,只不过声调高低起伏,显示出了努力靠拢北方腔调的残存。
评分水缸里的记忆
评分竹廊记忆
评分造楼房
评分洋灯故事
评分摘刺苔故乡在江南,在童年的记忆里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
评分故乡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就连凶悍的台风到此,也变得温驯了。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是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
评分捡麦穗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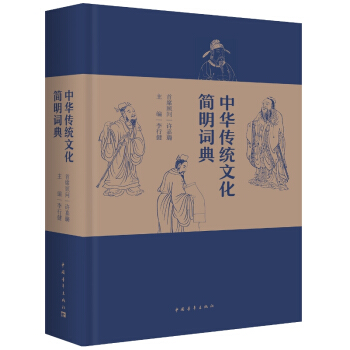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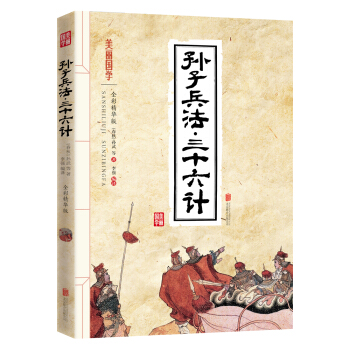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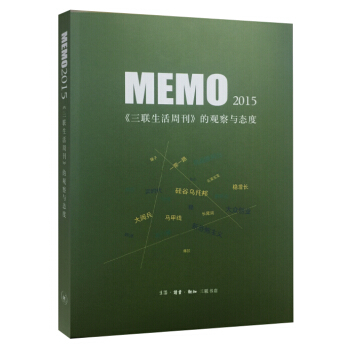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 [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13694/573bec63N511cc12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