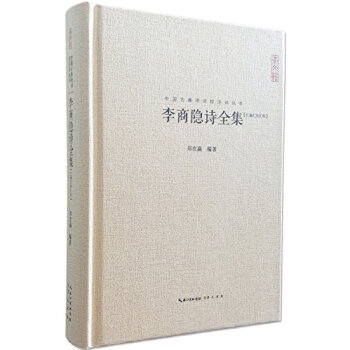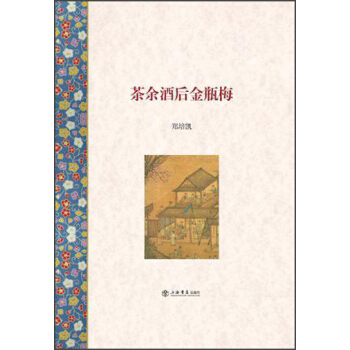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洪晃自传全新升级版!须说明一下,《我的非正常生活(增补版)》是由两本书构成:《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我的私家相册》。其中,《我的非正常生活》全部由文字构成,黑白的印制(包括封面也设计成了最简洁的黑白色),其中新增补文章占20%以上;而,《我的私家相册》全部由图片构成,此画册从正文到封面全部四色印刷。书中包含上百张照片,其中大量照片属首次公开。
《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分“当出版人”、“我的隐私”、“圈子”三个部分。
洪晃“名门痞女”,她“离经叛道”、非传统的生活道路既传奇又独特。《我的非正常生活》除了作者自己书写的文字外,还用大量篇幅收集了她周围人所揭发的关于她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从多个角度讲述了真实的洪晃故事。作者通过工作上的“下属”“同事”、家庭中的父母亲人和生活中的哥们儿姐们儿笔下的她,以及她笔下的这些人来“写”自己经历过的那些“非正常”的人和事。这种写法着实独特,但真实生动。她笔下的名人以及别人笔下的她辉映成趣,栩栩如生。
参与撰写洪晃的有著名出版人、《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朱伟;有著名作家及音乐艺术家刘索拉;著名作家罗点点;自由撰稿人廖文;她的母亲,著名外交家、作家章含之;时尚刊物出版人晓雪;“文化分子”伊伟等等。使得这个出身名门、满嘴粗话、性格率真、知人善用、勇于改错的性情中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通篇洋溢着洪晃独特的个人魅力。
作者简介
洪晃,十二岁留学美国,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久负盛名的七大女校之一Vassar学院。二十五岁,已经是德国金属公司驻华首席代表,年薪七万美金,成天忙于合同、谈判,有钱但生活刻板、乏味。
三十五岁,辞去高薪的首代职位,一头扎进文化创意产业,改行办杂志,发掘本土创意人才,至今乐在其中。
2000年初担任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hina Interactive Media Group)首席执行官,旗下除了《iLOOK世界都市》,还有《TIME OUT名牌世界·乐》、《SEVENTEEN青春一族》。
近几年投资BNC薄荷糯米葱中国设计师原创店,帮助中国设计师销售他们自己的作品。
《纽约时报》称洪晃为中国的奥普拉·温弗里,美国《时代》杂志将她选入2011年度最具影响力时代百大人物。
精彩书评
洪晃出身名门不假,而她的"离经叛道",非传统的生活道路也是确确实实的。——章含之
洪晃做《iLook世界都市》,一本时尚杂志要倡导的是规则,而她恰恰是规则的破坏者;她要的是革命性的观念,而时尚界的各种人等却都在大众时尚潮流之中。
——朱伟
洪晃和晓平的关系暴露出她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这个经历多次感情风波,仍充满孩子气的"女强人"追求的是一种朴素、诚实和热情、完全放松而有童心的爱情关系。
——刘索拉
在认识洪晃之前,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会骂人的女孩肯定是"不好"的女孩,会骂人的女人肯定是男人不喜欢的女人。但是洪晃的"骂人"彻底颠覆了我受的教育。
——晓雪
目录
新版前言旧版前言
Ⅰ 当出版人
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
朱伟:洪式审美趣味
我不时尚行吗?
朱伟:洪晃与“时尚的包袱”
晓雪
我的四个小祖宗
伊伟:洪晃的艺术激情
我说伊伟
王勇:与洪晃死磕到底
我说王勇
戴政:大女人洪晃
我说戴政
曹鹰:给晃的三封信
我说曹鹰
朱伟:革命与大众潮流
当出版人
老典:《洪晃出刊》
改版iLook
Ⅱ 我的隐私
童年时我身边都是摩登上海女郎
相貌与出身
朱伟:不平凡的历史烙印
纽约空降红小兵
上一代交给我的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朱伟:非典型“童年缺失”
我妈妈的惊喜
章含之:与妞妞“求同存异”
我爸爸的魅力
我爸爸的逻辑
史家胡同51号
爸爸的来信
四合院里的“文革”
冬天的享受
我的隐私
男人分两截
爱孩子的男人
解剖男人
朱伟:晃——永远的反抗者与叛逆者
晓雪:穿丁字皮鞋的晃
刘索拉:左看晃像个嬉皮,右看还像个嬉皮
回到私人空间
幸福的责任
Ⅲ 圈子
我的理想生活
科学幻想
陈娘子
所以人都说我坏
话说女强人
时尚包袱
老情人
小女人的福气
当代寓言
特殊人才使用说明
矮望图死逼克English
廖文
廖文:网状思维的晃
母狗制作:Bitch Production
我眼里的姜文(一)
我眼里的姜文(二)
我眼里的姜文(三)
献身还是卖身
姑奶奶逛公社(一)
姑奶奶逛公社(二)
男人管理好N个女人的方式方法
嘉宾油条
预防艾滋病的方法(二)
上流社会,下流车
《无穷动》的后遗症(一)
《无穷动》的后遗症(二)
以公司为床
近距离接触奸商
时尚与环保
芬兰见
写在后面
精彩书摘
1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脸上做出非常严肃认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圆,小嘴巴噘起,薄薄的嘴唇紧闭,身体不时摇摆以便显示我在从各个角度观察面前的选择,像专业人士一样。这是1998年11月,我头一次为《iLook世界都市》挑选封面。
康明手里有两张封面:左手举着的是金黄色调,一个纯洁的女孩肩上扛着麦穗,白色的衣服几乎是围在身上的,有点像古罗马的装束,女孩的脸是个侧面,有一个像蒙娜丽莎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头上有一个用柳树枝编的花环。右手的决然不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孩,双眼警惕地凝视前方,一种紧张的神态,身上黑色的衣服没有任何细节,两只胳膊半张,也是一种神经质的姿势。
“你觉得哪个好?”我问利丰雅高分色部的头儿,潘先生。
“这个吗,要看你喽。”小潘是那种可以去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的商人,说话滴水不漏。
“你觉得哪个更好?”我追问道。
“这个金黄的嘛,和你原来《iLook世界都市》的风格比较近似;那个黑白的嘛,比较有个性。”在他的脑子里话已经很清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两张都不能当封面,金黄的这个还凑合,和你杂志勉强有点关系,那黑白的纯属于瞎胡闹,想都别想。”可那个时候我还是属于热血沸腾的阶段,不具备听明白这种话中话的能力,我当时的理解是,这个看过无数封面的香港人觉得我两个封面都不错。
“你说呢?”我问康明。
康明是我们的美编,他是一个小个子,说话有一丝非常好听的四川音。他还会眯眯笑,而他笑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拒绝他的。这时候他笑眯眯地说:“你说了算喽,我都喜欢。”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主编真牛,能让一张破照片挂满全国成千上万个街头。
我刚接手《iLook世界都市》的时候,我们整个后期几乎都是在印刷厂做的。现在想想,利丰真是很照顾我们。我们每次都是大队人马杀到蛇口,有美编、责编、主编,美编还经常是两个两个地派去。到了就去利丰的分色车间,霸占两台上好的苹果机,把还没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这时候美编身后还坐着一个责编或主编什么的,没完没了地下修改指令,“这个再往上点”“那个再往左点”“把这个模特的腿再修细点”……
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哪张照片当封面。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们当时坐在利丰为客户准备的小会议室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玻璃墙,外面是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利丰办公室,而现在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个看守的保安,哼着粤语流行歌曲在外面走来走去。我其实也应该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兴奋让我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明天封面必须要出来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他走了之后我又把封面放到会议室的书架上,那上面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国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丰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显眼一些?”我问康明。他打了个哈欠,“嗯”了一声。
“那就是它吧,”我说,“咱们就得有点个性。”
刊终于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封面。一个模糊的、神经质的女孩儿,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现在280克铜版纸、过UV、加膜的封面上。我骄傲地把刊物交给我的伙伴。
“啊,”他惊讶地看着封面,“谁选的封面?”
“我。”
“嚯。”他想了想又说,“显然,《iLook世界都市》马上要起来了。”
“真的?!”听了这话我高兴得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
“肯定。”他笑着,坚定不移地说,“因为我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封面,《iLook世界都市》已经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
2
从国外回来的人刚开始都有点优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一截。一般来说,这种优越感在两年内会被撞得支离破碎,如果你还能保持你的自信,还能坚持下来,那你就说不定能混出来了,真的能出人头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为有三条感觉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轻松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做内容策划是没有问题的。二来我在纽约上的中学,每学期去三次当代艺术博物馆,听一次大都会的歌剧,我上的大学是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任美国总统夫人的母校,还出过两个女文豪,在这种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里?就更不用说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了。最后,我有十几年的商业经验,知道什么是现金流,而国内哪个编辑又能够如此精通商务?看样子办刊真是非我莫属了。
而实际上我的办刊能力是王府井街头任何书报摊贩能一语道穿的。我到现在都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点觉悟,办刊交的学费远远超过了留洋的学费。
我的大学,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个工业小镇上。这个学校和她的环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全镇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经失业、痛恨另类和移民的“红脖子”,而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马修·瓦瑟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啤酒商,发财以后于1861年建立了这个女校。原来应该是培养夫人完成学校,英文叫FinishingSchool,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女孩再涂上一层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学84届的毕业生,而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和其创始时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远了。
瓦瑟的改变在二战以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瓦瑟大学出了一个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写了一本书叫《THEGROUP》(《群体》),里面描写了四个瓦瑟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之后在社会里混荡的故事。当然,书里最尖锐的是麦卡锡冷酷地形容这四个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没有得逞的性活动。由于这本书的轰动效应,瓦瑟大学女生从此得到了比较“开化”的名声。学校的看家学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艺术史、英文是全美国都叫得响的。
1981年我入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玛丽·麦卡锡是谁,也不知道这艺术史到底教什么东西,我去瓦瑟大学是因为学校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是9月的一个下午扛着铺盖卷入校的。由于是转校生,没有来得及选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个拐角里的小屋子。后来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楼,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楼,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恋死党才会选择住女生宿舍楼。
这里和我原来上的州立学校简直天壤之别。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浓厚的东欧口音。每个楼里有一个共用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小三角钢琴。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而我原来的学校,宿舍大堂里面只有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和满墙的涂鸦之作。在瓦瑟大学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3
我总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两者中让我选一个,我想自信更实惠一点。家庭、相貌、文凭都可以予以优越感,但是这和本人没有什么关系,瓦瑟大学给我的优越感来自于她的三角钢琴、红地毯和黄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来自于瓦瑟大学给我的教育。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去看书去了。他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根本无法做笔记,如果这堂课时间再长一点,他在黑板上的涂鸦就和杰克逊·波拉克的画有一拼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Whatif”(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教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噢!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液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液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漂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来,”梁教授说,“你来看看我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梁教授说这很不容易,因为柏林的很多资料已经在二战中消失了。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教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会背书的学生都是傻×。
我的自信来自于这顿饭之后我再也没当过傻×。
4
“为什么?”我问。
“做啥,做啥,呒没啥,哦不欢喜。”老于头看也不看我,一边摆弄着他摊头的报纸,一边很不耐烦地打发我。
他的摊位在上海美美百货的拐角,所有高档生活刊物都要朝拜这个摊点,因为就他这里卖得好。我不知道我怎么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把他得罪了,这个倔老头把《iLook世界都市》先是拒之门外,后来是把《iLook世界都市》和过期的刊物放在一起,严重影响了销售。
“是不是我们刊物不好看,我挺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拍马屁的语气自己听了都肉麻。
“我才勿要看侬个杂志。”他干脆坐下来,屁股对着我。
“老于啊,我们老板给你带了点见面礼。”我的发行总监黄晓洁一边帮我打圆场,一边示意我把我们刚买的一条中华烟递过去。
“是是是,”我赶紧接过来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老于头把烟一把拿过去,瞪着眼睛跟我喊:“格做啥?!!格做啥?!!我要吃侬个香烟咯?!”然后随手把烟扔到淮海路中间。
晓洁和我都吓坏了,我已经有点气急败坏地想动手揍这个不讲理的老头子,还是晓洁使劲给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别这样,老于,我们是来和你谈工作的。”晓洁劝他。
“格么伊讲事体,做啥拿香烟来啦?!”老于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没什么,于先生,你不要误会,我们头次来,总是客气一下,没别的意思。”我缓了口气,决定再试一把。“烟就算了。我妈妈刚刚写了一本书,我让她签了字,给你带来了。”也许,他买我妈的账。
老于头把书接过来,翻了一下,扔到一边。“我给侬讲,呒没用咯,我有事体,我跑了噢。”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一个小弄堂里面。
我和晓洁傻呵呵地愣在那里,摊位上的小报童捂着嘴笑话我们的无能。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抢救淮海路中间已经被车轧扁了的那条中华烟。
我跟我妈妈要她书的时候她问我:“这个于先生是谁啊?”
“是上海的一个摊贩,我得求他好好帮我卖《iLook世界都市》。”
“我为什么要给他书呢?”我妈还是不解地问,“这有用吗?”
“有用,有用,你不懂。”
事过两三年之后,东航出版社的叶荣臻跟我妈说:“听说你女儿曾经在上海被一个摊贩轰出去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我妈问他。
“这个老于头大家都认识,他到处和别人讲,章含之的女儿拿着她妈妈签名的书来求他,也被他骂跑了。”
我妈妈随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只好承认。
“那我的书就给扔那儿啦?”
“嗯。”我一直没敢告诉我妈,怕她生气。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没用吧?”她哈哈大笑,“你就丢脸吧。”
……
前言/序言
新版前言洪晃/文
我不怀旧,风花雪月真的不是我。
《我的非正常生活》重版,逼着自己重新把书看一遍,挺恐怖的。十年来,文字没长进,反而少了几分认真。
写这本书是个偶然,当时贝塔斯曼约别人写书,我是被捆绑进来作陪衬的。稿子拖了很久,最后听着Leonard Cohen当时的新专辑《Ten New Song》,每天晚上两点起来写字,自传体的东西本应该多少有点风花雪月,而那时候我住在798, 夜深人静,正伤感的时候,附近的发电厂的蒸气管道“砰”的一声响,好像一个巨人在你窗前放了个屁。好不容易挤出来的几滴风花雪月,也被崩得支离破碎了。
可是重版书的前言只能怀旧,十年来,最大的改变是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写给妈妈和爸爸的。我记忆中没有太多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场景,模糊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被允许跟爸爸妈妈一起睡,挤在两个大人中间,开心的感觉至今还在。现在想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么一晚,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敢去碰那些风花雪月的记忆,万一神马都是浮云怎么办?1992年,我突然想请父母一起吃饭,很自私的目的,就是想在记忆中非常清晰地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和印象,那时候我和法国男朋友住在建外外交公寓,我们决定在他的公寓里面给我父母做顿饭吃,结果爸爸妈妈都找了个借口没有来赴约。
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妈妈先写了自传,里面提到了爸爸,也就三句话吧。但是爸爸很不开心,主要是他身边的人都认为妈妈实际上是在攻击他。之后我出了书,再之后,爸爸也出了书,这本书就冲着妈妈去了,有点像今天微博上的愤青,一定要彻底抹黑自己四十年前就离婚的前妻。其实我爸爸并不是这么小心眼儿的人,他去世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很犹豫是否要出这本书,是否要这么写。我记得小时候爸爸曾经跟我说,别出风头,结果就是你的痛苦都是别人茶前饭后的笑话。可能,我们这一家人都太爱出风头,最后还是应验了爸爸的话。
我知道我没有爸爸妈妈的文笔,所以既不能风花雪月,也不能愤世嫉俗。只能用大白话的方式,两千字、两千字地写点对生活的体会、对时政的评论、对时尚的吐槽、对朋友的赞赏。
书中有一篇写了三个喜欢孩子的男人,其中一位就是我闺女她爹。我俩已经一起15年了。虽然开头有点闹,但是基本上,这十年一直很滋润地过着小日子。只是一转眼,人胖了、头发白了、孩子大了。
《我的非正常生活》重版,我要再次感谢帮我完成写作的人。
首当其冲要谢谢朱伟,像三联毕业的其他编辑一样,我能写字,能编辑,能作杂志,要感谢他。我是他的徒弟。而回头再看他的文字,发现他真的非常了解我。我和朱伟现在见面不多,但是每年春节前,他、索拉、点点姐姐和我都会一起吃顿饭。
索拉一直是好朋友,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艺术家天分的人,我总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她和她的作品,她真的是天才。我曾经企图写小说,也整了4万来字,就这时候,刘索拉发表了她的小说《迷恋·咒》,我一晚上看完,天亮了就决定放弃写小说。真的没那金刚钻。
伊伟后来去做电视了,我们还有些合作和来往,也不是很频繁。戴政和王勇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了,而晓雪和我却从朋友走到同事走到冤家了,充分说明,时尚绝对不是给你带来毛绒般温暖的行当。
我泪流满面地看了三遍妈妈在书里写的文字,我想抱抱她,告诉她我爱她。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她爱我更多。我想她。
索拉曾经教我,写不出来字的时候,可以用歌词滥竽充数。我写东西的时候必须有音乐,写这个前言,几次提笔又放下。终于选了一首我最喜欢的怀旧的歌曲伴随着我完成了这个前言。第一版的结束是Leonard Cohen的歌词,所以,就把这首怀旧歌词也滥竽充数在这个重版的前言里面吧。
这首歌是Joan Baez写的,歌名为《钻石与锈》(Diamonds and Rust)。据说她曾经和鲍布·迪伦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这是她写给他的。
用户评价
这本书,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抱着一种“看看现在年轻人都怎么折腾”的心态去翻的,毕竟书名就透着一股子“不走寻常路”的劲儿。结果呢?嗯,我发现我低估了作者的脑洞,也低估了生活本身能有多少种“非正常”的可能性。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在坐过山车,时而让我心跳加速,时而又让我陷入沉思。它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讲道理的书,也不是那种纯粹的鸡汤文,而是把生活中的各种戏剧性、荒诞感、甚至是一些我们难以启齿的瞬间,毫不留情地呈现在你眼前。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绘人物的时候,那种细致入微的笔触,仿佛每一个角色都是从你身边走过的某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纠结挣扎,都那么真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但转念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曾有过相似的冲动和选择?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对“正常”的固有认知,让我们开始审视自己,也审视这个世界。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抛出了无数个问题,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寻找答案,去碰撞出新的火花。我承认,有些情节确实让我感到意外,甚至有些震惊,但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敢于触碰那些被我们忽略或压抑的角落。
评分拿到《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本轻小说或者什么青春校园题材的读物,毕竟“非正常生活”这几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不着边际的奇遇。然而,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玩的远不止于此。这本书更像是一场关于个体如何在社会洪流中找寻自我,如何在看似规律的日常中发现裂缝的探索。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背景,也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聚焦于主人公在各种“非正常”事件中的内心挣扎与成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关于“选择”的部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选择描绘成非黑即白,而是展现了选择背后的复杂性、无奈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每一次看似微小的“非正常”决定,都可能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主人公就是在这种不断试错和反思中,一点点摸索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种写法,让我觉得特别有代入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又何尝不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选择堆砌而成?有时我们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有时又会在事后回味曾经的犹豫不决。这本书,用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调,揭示了“非正常”背后的人性深处的纠结与真实。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名字一开始吸引了我,我心想,能把“非正常生活”写得有趣,并且还“升级”了,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读完之后,我只能说,我的期待被远远超越了。它不是那种一看开头就能猜到结局的故事,也不是那种生硬的说教。相反,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可能都不愿承认的另一面。书中很多情节,乍一看都充满了荒诞感,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但细细品味,却又能从中找到一丝丝现实的影子。作者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场景,却让书中的人物在其中做出种种“非正常”的反应。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捕捉,那些细微的、难以言说的情感波动,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你会跟着主角一起迷茫,一起挣扎,一起在看似混乱的局面中寻找出路。这本书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它更像是提供了一个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视为“正常”的规律,思考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和价值。读这本书,与其说是看故事,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对话。
评分不得不说,《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这本书,它真的刷新了我对“生活”这个词的理解。我原本以为“非正常”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件堆砌,但读完后我才发现,它所探讨的,是更深层次的、关于个体与社会、规则与自由、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作者在叙事上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它不像很多书那样,一上来就告诉你主角是谁,要做什么,而是徐徐展开,一点点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甚至有些“拧巴”的人物形象。你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定义他们,他们身上既有我们熟悉的喜怒哀乐,又有我们难以理解的冲动和选择。我特别喜欢书中对细节的刻画,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能传递出人物复杂的情绪和内心活动。而且,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很有意思,时而犀利,时而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总能恰到好处地触动读者的心弦。它没有试图去说教,而是用一种平视的姿态,让你去观察,去思考,去感受。每次合上书,我都会忍不住想,生活到底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或许,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实。
评分《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这本书,就像一本意外闯入我生活中的奇幻地图,让我原本熟悉的日常,瞬间充满了未知和色彩。我并非那种追求惊险刺激的读者,但这本书的“非正常”,却恰恰以一种非常巧妙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剥开了生活的表层,触及了那些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暗流。作者的叙事风格很独特,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力量,能精准地勾勒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和困惑。我特别欣赏书中对“选择”的描绘,它并非将选择简化为对与错,而是展现了每一个选择背后所蕴含的复杂考量、偶然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涟漪效应。读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书中的人物为何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而我自己在面临类似困境时,又会如何应对。这种强烈的代入感,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旅程。它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正常”的定义,也让我意识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恰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这本书,更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去拥抱那些“非正常”,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评分洪晃自传全新升级版!须说明一下,《我的非正常生活(增补版)》是由两本书构成:《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我的私家相册》。
评分一般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评分京东买书,正版,也很方便,省得东奔西跑。
评分洪晃自传全新升级版!须说明一下,《我的非正常生活(增补版)》是由两本书构成:《我的非正常生活》(升级版)+《我的私家相册》。
评分好。。。。。。。。。。。。。
评分7、是金子总会花光的。是镜子总会反光的。
评分书很好,是正版,打折买很划算
评分收到了,一如既往的快
评分8、不要为旧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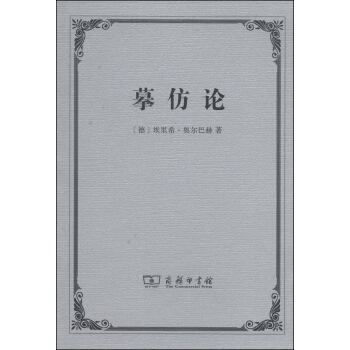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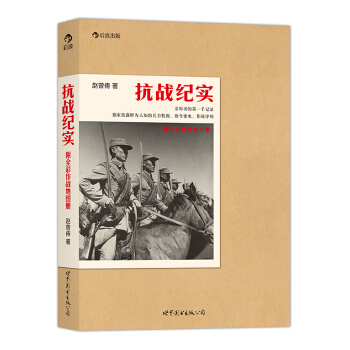
![世界儿童文学精选:木偶奇遇记(拼音美绘本)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0829/55826b87N152f168f.jpg)
![安徒生童话全集彩色典藏版+格林童话全集彩色插图版(套装全7册)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6983/56de7152N08e5ed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