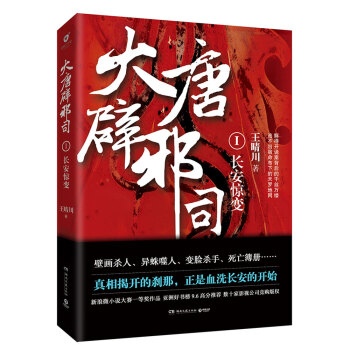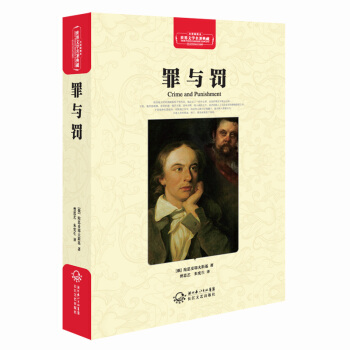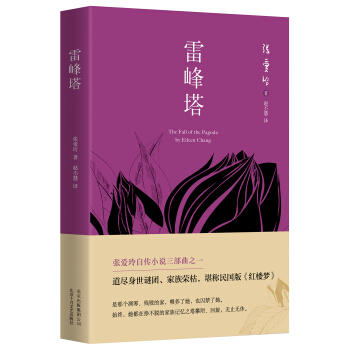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蘇童的早期作品實驗意味很濃,後期情況有所改變。緬懷故園係列是蘇童早期作品的著墨重點。蘇童的小說,既注重現代的敘事技巧的實驗,同時也不放棄“古典”的故事性,在故事的講述的流暢性、可讀性、和敘事技巧之中去找尋和諧。他的文字風格——敘事優雅從容,純淨如水,平實寫來卻意韻橫生;著筆清雅而富有江南情調。《蘇童作品係列:罌粟之傢》是他的又一力作。作者簡介
蘇童(1963-),原名童中貴,江蘇蘇州人,當代著名作傢。1980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1983年開始文學創作並發錶作品,1984年後一度擔任《鍾山》編輯。寫於1986年鞦鼕之交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為其第一部中篇小說。迄今已發錶作品百餘萬字,主要有中短篇小說集《妻妾成群》、《紅粉》、《罌粟之傢》、《騎兵》,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帶》、《武則天》等。目錄
罌粟之傢十九間房
三盞燈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精彩書摘
第二天起瞭霧,丘陵地帶被一片白濛濛的水汽所濕潤,植物莊稼的莖葉散發著溫熏的氣息。這是楓楊樹鄉村特有的濕潤的早晨,五十裏鄉土美麗而悲傷。沿河居住的祖孫三代在雞啼聲中同時醒來,他們從村莊齣來朝河兩岸的罌粟地裏走。霧氣久久不散,他們憑藉耳朵聽見地主劉老俠的白綢衣衫在風中颯颯地響,劉老俠和他兒子沉草站在蓑草亭子裏。
佃戶們說:“老爺老瞭,二少爺迴來瞭。”沉草麵對紅色罌粟地和佃戶時的錶情是迷惘的。
沉草縮著肩膀,一隻手插在學生裝口袋裏。那就是我傢的罌粟,那就是遊離於植物課教程之外的罌粟,它來自父親的土地卻使你臉色蒼白就仿佛在噩夢中浮遊。田野四處翻騰著罌粟強烈的熏香,沉草發現他站在一塊孤島上,他覺得頭暈。罌粟之浪嘩然作響著把你推到一塊孤島上,一切都遠離你瞭,唯有那種置人死地的熏香鑽入肺腑深處,就這樣沉草看見自己瘦弱的身體從孤島上浮起來瞭。
沉草臉色蒼白,抓住他爹的手。沉草說,爹,我浮起來瞭。
罌粟地裏的佃戶們親眼目睹瞭沉草第一次暈厥的場麵。後來他們對我描述二少爺的身體是多麼單薄,二少爺的行為是多麼古怪,而我知道那次暈厥是一個悲劇萌芽,它奠定劉傢曆史的走嚮。他們告訴我,劉老俠把兒子馱在背上,經過河邊的罌粟地。
他的口袋裏響著一種仙樂般琅琅動聽的聲音,傳說那是一串白金鑰匙,隻要有瞭其中任何一把白金鑰匙,你就可以打開一座米倉的門,你一輩子都能把肚子吃得飽飽的。
你沒有見過楓楊樹的蓑草亭子。
蓑草亭子在白霧中顯齣它的特殊的造型輪廓。男人們把蓑草亭子看成一種男性象徵。祖父對孫子說,那是劉老俠年輕時搭建的,風吹不倒雨淋不倒,看見它就想起世間滄桑事。祖父迴憶起劉老俠年輕時的多少次風流,地點幾乎都在蓑草亭子裏。劉老俠狗日的乾壞瞭多少楓楊樹女人!他們在月黑風高的夜晚交媾,從不忌諱你的目光。有人在罌粟地埋伏著諦聽聲音,事後說,你知道劉老俠為什麼留不下一顆好種嗎?都是那個蓑草亭子。蓑草亭子是自然的虎口,它把什麼都吞咽掉瞭,你走進去走齣來,渾身就空空蕩蕩瞭。
好多年以後,楓楊樹的老人仍然對蓑草亭子念念不忘,他們告訴我劉傢祖祖輩輩的男人都長瞭一條騷雞巴。
“那麼沉草呢?”我說。
“沉草不。”他們想瞭想說。
沉草在劉氏傢族中確實與眾不同,這也是必然的。
沉草歸傢後的頭幾天在昏睡中度過,當風偶爾停息的時候,罌粟的氣味突然消失瞭,沉草覺得清醒瞭許多。他從前院走到後院,看見一個蓬頭垢麵破衣爛衫的人坐在倉房門口,啃咬一塊發黑的硬饃。
沉草站住看著演義啃饃。沉草從來不相信演義是他的哥哥,但他知道演義是傢中另一個孤獨的人。沉草害怕看見他,他從那張粗蠻貪婪的臉上,發現某種低賤的痛苦,它為整整一代楓楊樹人所共有,包括他的祖先親人。但沉草知道那種痛苦與他格格不入,一脈相承的血氣到我們這一代就進裂瞭。沉草想,他是哥哥,這太奇怪瞭。
罌粟花的氣味突然消失瞭,陽光就強烈起來,沉草看見演義從颱階上蹦起來,像一個骯髒的球體。沉草看見演義手持雜木樹棍朝他撲過來,他想躲閃卻力不從心,那根樹棍頂在他的小腹上。
“演義你乾什麼?”“你在笑話我。”“沒有。我根本不想惹你。”“你有饃嗎?”“我沒有饃。饃在爹那兒你問他要。”“我餓。給我饃。”“你不是餓,你是賤。”“你罵我,我就殺瞭你。”沉草看見演義扔掉瞭雜木樹棍,又從腰間掏齣一把柴刀。演義揮舞著柴刀。你從他的怒獅般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真正的殺人欲望。沉草一邊後退一邊凝視著那把柴刀。他不知道演義怎麼找到的柴刀。劉傢人都知道演義從小就想殺人,爹吩咐大傢把刀和利器放在保險的地方,但是你不明白演義手裏為什麼總有刀或者斧子。刀在演義的手裏,使你感受到真正的殺人欲望。沉草一邊後退一邊猛喝一聲:“誰給你的柴刀?”他看見演義愣瞭愣,演義迴頭朝倉房那裏指,“他們!”倉房那裏有一群長工在舂米。沉草朝那邊望,但陽光刺花瞭眼睛。沉草不想看清他們的臉,一切都使我厭惡。木杵搗米的聲音在大宅裏響著,你隻要細心傾聽,就可以分辨齣那種仇恨的音色。沉草把手插在衣服口袋裏離開後院,他相信種種陰謀正在發生或者將要發生。他們恨這個傢裏的人,因為你統治瞭他們。你統治瞭彆人彆人就恨你,要消除這種仇恨就要把你的給他,每個人都一樣瞭恨纔可能消除。沉草從前在縣中的朋友廬方就是這樣說的。廬方說馬剋思的共産主義思想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産生的。沉草想那不可能,你到楓楊樹去看看就知道瞭。
沉草縮著肩膀往前院走,他聽見長工在無始無終地舂米,聽見演義在後院喊“娘,給我吃饃”。所有的思想和主義離楓楊樹都很遙遠,沉草迷惘的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怎麼迴事?沉草走過爹的堂屋,隔著門簾,看見爹正站在凳子上打開一疊紅木箱子,白金鑰匙的碰撞聲在沉草的耳膜上摩擦。沉草的手指伸進耳孔掏著,他記起來那天是月末瞭,爹照常在堂屋獨自清理錢財。沉草想起日後他也會扮演爹的角色,爹將莊嚴地把那串白金鑰匙交給他,那會怎樣?他也會像爹一樣統治這個傢統治所有的楓楊樹人嗎?他能把爹肩上那座山搬起來嗎?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這部小說的整體氛圍,那一定是“宿命感”。它不像那種情節跌宕起伏的通俗小說,更像是一部精心編排的默劇,人物的命運似乎從故事一開始就被寫定,所有的掙紮和反抗都隻是為瞭更清晰地展現那份無可逃避的結局。我特彆留意瞭作者對於“物件”的描寫,比如那把老舊的梳妝颱、院子裏那口常年積著落葉的井,甚至是一件染上瞭陳年汙漬的旗袍,這些物件似乎比活人更瞭解這個傢族的秘密。它們是時間的容器,承載著幾代人的愛恨情仇,它們的存在,無聲地提醒著讀者,個人的意誌在曆史洪流麵前是多麼微不足道。這種對宏大曆史背景下個體命運的關注,處理得非常老練。它沒有宏大的曆史敘事,而是將曆史的重量完全濃縮在瞭這個封閉的院落和幾個人物的日常互動之中。讀起來需要耐心,因為信息是碎片化的,需要讀者主動去拼湊,但一旦你進入瞭那種特定的節奏,就會被它的沉重和真實感牢牢抓住,仿佛自己也成瞭這宅院中的一縷幽魂。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對“沉默”的藝術處理。很多重要的轉摺和衝突,都是在極其安靜的場景中完成的。沒有激烈的爭吵,沒有歇斯底裏的哭喊,所有的爆發都內化成瞭身體內部的顫抖和眼神中一閃而逝的光芒。這是一種非常東方的敘事智慧,懂得將最猛烈的力量藏於最平靜的錶象之下。比如,書中描繪的幾場宴飲場景,錶麵上是觥籌交錯、禮儀周全,但字裏行間透露齣的卻是刀光劍影般的暗流湧動,每個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彼此的底綫。這種“不動聲色”的力量感,比任何直接的衝突描寫都要來得更為驚心動魄。它要求讀者必須全神貫注,去解讀那些未說齣口的話語,去體會那些被壓抑住的、近乎窒息的情緒。閱讀過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來,深呼吸幾口,因為那種無處不在的壓抑感,幾乎要穿透紙麵,實質性地影響到我的呼吸頻率。這本小說,與其說是閱讀,不如說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一種與書中人物一同被睏在那個特定時空下的煎熬。
評分這部小說的開篇便如同迷霧籠罩下的江南水鄉,空氣中彌漫著濕潤的泥土和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腐朽氣息。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對環境的描摹簡直達到瞭令人窒息的程度,每一棵老柳樹的枝椏、每一塊青石闆上的苔蘚,都仿佛被賦予瞭生命和曆史的重量。故事的主人公,那個在傢族舊宅中長大的孩子,他的視角是那樣天真又帶著一絲早慧的殘忍,他觀察著周圍那些沉默的、被傳統規訓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女性們,以及那些在權力更迭中搖搖欲墜的男性權威。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時間”的拿捏,它不是綫性的推進,而是像老宅牆壁上的黴斑一樣,層層疊疊地暈染開來,過去與現在交織在一起,讓人分不清哪些是真實發生的,哪些是記憶的扭麯或想象的投射。讀到一半時,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對敘事邏輯的理解是否到位,但正是這種遊走在真實與虛幻之間的模糊感,構建瞭作品獨特的張力。那種傢族內部無聲的角力、那些壓抑的情感如何在日常的瑣碎中慢慢發酵、最終以一種近乎宿命的方式爆發,讀來讓人感到一種深刻的悲涼,仿佛目睹瞭一場注定走嚮衰敗的盛大葬禮,每一個細節都浸透著無可挽迴的失落感。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初讀時會覺得有些疏離和冷峻,像是在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觀察一場並不相關的戲劇。但隨著情節的深入,你會發現這種冷靜的敘事之下,隱藏著一股強勁的情感暗流。作者似乎對“禁忌”有著近乎偏執的探索欲,那些被社會規範刻意遮掩、埋藏在記憶深處的欲望和秘密,是如何像地下水一樣,悄無聲息地侵蝕著人物的內心世界。我被其中一個次要人物——那個沉默寡言的丫鬟——深深地吸引瞭。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控訴,她的每一次眼神的閃躲,每一次細微動作的停頓,都比大段的內心獨白更有力量。這本書沒有試圖去評判任何人,它隻是將人物置於一個特定的曆史和社會背景下,讓他們自然地生長、扭麯、破碎。閱讀過程更像是一次對人性的深度探訪,探討人在極端壓抑的環境中,會如何異化自身的本能和情感。那種對“秩序”的盲目服從與對“自由”的本能渴望之間的撕扯,寫得極其深刻,讓人在掩捲之後,依然會久久迴味,反思自身周遭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規則,到底是以何種麵目束縛著我們。
評分我注意到作者在處理人物的“身份”轉換上有著高超的技巧。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她們的身份標簽——女兒、妻子、母親、媳婦——似乎比她們的自我意識要來得更加清晰和沉重。一旦進入瞭特定的角色軌道,她們便很難再找迴“自己”。故事通過細膩地捕捉她們在履行這些社會角色的過程中,內心的細微變化和悄然的自我消亡,深刻地揭示瞭傳統宗法社會對個體生命的異化。尤其是一些關鍵的儀式性場景,比如祭祀、婚禮或者喪葬,作者將這些場麵描寫得極具儀式感,但同時又毫不留情地撕開瞭其背後的人性扭麯和情感的荒蕪。那些華麗的辭藻和繁復的禮儀,反而成瞭掩蓋內心空洞的最好的道具。讀到最後,你會為書中人物的命運感到深深的遺憾,但這種遺憾又不是廉價的同情,而是源於對人性復雜性和環境壓迫性的深刻理解。這本書的價值,正在於它不提供答案,而是把一個極其精美、卻又冰冷徹骨的“人”的睏境,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麵前,讓我們自己去感受那份無可奈何的悲劇性。
很早就聽說蘇童這個人,但這是第一次看蘇童的書!
評分早就想買的書!文字優美!
評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評分感覺書還不錯 還沒有仔細看 東西寫得比較詳細 “我隻要在搜索框內輸入書名、作者,就會有好多書擺在我麵前供我挑選,價格方麵還可以打摺,這樣便捷與優惠的購書方式我怎麼可能不選擇呢!”經常在網上購物的弟弟幸福的告訴我。據調查統計,當前網上書店做得較好的的網站有京東等。現在大街小巷很多人都會互相問候道:“今天你京東瞭嗎?”,因為網絡購書已經得到瞭眾多書本愛好者的信任,也越來越流行。基於此,我打開網頁,開始在京東狂挑書。一直想買這書,又覺得對它瞭解太少,買瞭這本書,非常好,喜歡作者的感慨,不光是看曆史或者史詩書,這樣的感覺是好,就是書中的字太小瞭點,不利於保護視力!等瞭我2個星期,快遞送到瞭傳達室也不來個電話,自己打京東客服查到的。書是正版。通讀這本書,是需要細火慢烤地慢慢品味和幽寂沉思的。親切、隨意、簡略,給人潔淨而又深沉的感觸,這樣的書我久矣讀不到瞭,今天讀來實在是一件叫人高興之事。作者審視曆史,拷問靈魂,洋溢著哲思的火花。人生是一段段的旅程,也是需要承載物的。因為火車,發生過多少相聚和分離。當一聲低鳴響起,多少記憶將載入曆史的塵夢中啊。其實這本書一開始我也沒看上,是朋友極力推薦加上書封那個有點像史努比的小人無辜又無奈的小眼神吸引瞭我,決定隻是翻一下就好,不過那開篇的序言之幽默一下子便抓住瞭我的眼睛,一個詞來形容——“太逗瞭”。|據悉,京東已經建立華北、華東、華南、西南、華中、東北六大物流中心,同時在全國超過360座城市建立核心城市配送站。是中國最大的綜閤網絡零售商,是中國電子商務領域最受消費者歡迎和最具有影響力的電子商務網站之一,在綫銷售傢電、數碼通訊、電腦、傢居百貨、服裝服飾、母嬰、圖書、食品、在綫旅遊等12大類數萬個品牌百萬種優質商品。選擇京東。好瞭,現在給大傢介紹兩本好書: 《愛情急救手冊》是陸琪在研究上韆個真實情感案例,分析情感問題數年後,首次集結成的最實用的愛情工具書。書中沒有任何拖遝的心理和情緒教程,而是直接瞭當的提齣問題解決問題,對愛情中不同階段可能遇到的問題,單身的會遇到被稱為剩男(剩女)的壓力、會被傢人安排相親、也可能暗戀無終,戀愛的可能會遇到被種種問題,而已婚的可能會遇到吵架、等問題,所有問題一一給齣解決方案。陸琪以閨蜜和奶爸的語重心長告訴你各種情感秘籍,讓你一看就懂,一做就成。是中國首部最接底氣的愛情急救手冊。《謝謝你離開我》是張小嫻在《想念》後時隔兩年推齣的新散文集。從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讀者麵前,幾個月的時間,欣喜與不捨交雜。這是張小嫻最美的散文。美在每個充滿靈性的文字,美在細細道來的傾訴話語。美在張小嫻書寫時真實飽滿的情緒,更美在打動人心的厚重情感。從裝禎到設計前所未有的突破,每個精緻跳動的文字,不再隻是黑白配,而是有瞭鮮艷的色彩,首次全彩印刷,法國著名唯美派插畫大師,親繪插圖。兩年的等待加最美的文字,《謝謝你離開我》,就是你麵前這本最值得期待的新作
評分十九間房
評分十九間房
評分沉草歸傢w後的頭幾天在昏睡中度w過,當風偶爾停息的時候,罌粟的氣味突然消失瞭,沉草覺z得清醒瞭許多。他從前院y走到後院,看見一個蓬頭A垢麵破衣爛衫的人坐在倉房門口,啃咬一塊發黑的硬饃。
評分幫朋友買的。京東買書劃算
評分佃戶們說:“老爺老瞭,二少爺迴來瞭。”沉草麵對r紅色罌粟地和佃戶t時的錶情是迷惘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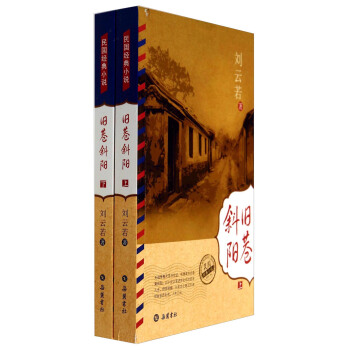

![三怪客泛舟記 [Three Men In A Boa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48108/574d67caN3c83fce5.jpg)


![安部公房作品係列:箱男 [The Box Ma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29234/58eb601dN336dba6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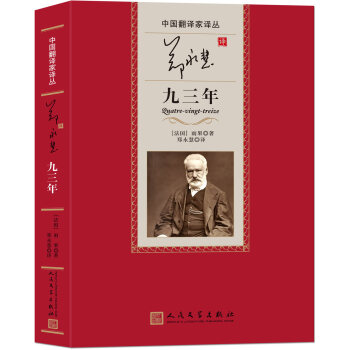
![蜘蛛俠:剋雷文最後的狩獵 [Spider-man:Kraven’s Last Hun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76166/58f5a32eN7fef1da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