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译文纪实)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23239/rBEQWVF0-aEIAAAAAAsrKziQ2-oAAEsEQC9BjQACytD126.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我们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爱上了那里的一个人
我们怀念一座城,是因为怀念着这里的一群人
一条胡同的因缘,一座城市的生死,一种历史的记忆!
彼得·海斯勒、伊安·约翰逊、冯骥才联合推荐!
内容简介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一百多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
作者简介
迈克尔·麦尔 Michael 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亭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再会,老北京》是他的第一本书。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处。两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
——彼得·海斯勒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愤怒地毁掉自己的文化。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快乐地毁掉自己的文化。
——冯骥才
令人难忘地,麦尔记录了一座城的死去。尽管看起来有些极端,但这绝不仅仅是北京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我们美国正在经历的问题。
——《纽约时报书评》
有回忆,有历史,有旅行,也有对身体力行的呼吁,这本优美的处女作,表达了作者对老北京的恋慕,也是对一种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的挽歌……对于北京而言,麦尔的这部力作就如同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于纽约。
——《出版人周刊》
目录
第一章 走过大前门
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
第三章 Mocky与我
第四章 “告别危房”
第五章 寒冬降临
第六章 拆之简史一: 燕都旧迹
第七章 《北京晚报》
第八章 幸福城中好时光
第九章 把感觉留住
第十章 春天
第十一章 拆之简史二: 皇城兴衰
第十二章 “去贫化”的贫民窟
第十三章 抢救老街
第十四章 夏日大回收
第十五章 过去时与将来时
第十六章 拆之简史三: 民国首都的现代化之路
第十七章 朱老师: 树的记忆
第十八章 “他有病了你不给他治,是你的责任”
第十九章 老寡妇的故事
第二十章 拆之简史四:“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工业浪潮
第二十一章 回音壁
后记 新北京,新奥运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译后记 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
精彩书摘
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
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和平队”(Peace Corps) 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本来,我是希望能被派往拉丁美洲的,因为当时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工作日的上午,我在一所中学给九年级的孩子们当老师,接着则步履匆匆地走过麦迪逊 生产奥斯卡?梅尔烟熏火腿 的工厂,四十二个六年级孩子正等着和我共渡下午的一段上课时光。
这些实习教职都是没有收入的,所以下课之后,我又兼职做起了特殊的接线员,充当需要打电话的听力障碍人士与电话接听人之间的桥梁。工作的时候,我戴一副耳机,面前摆着一台显示器,把电话接听人的话打成文字,同时把电话那头听力障碍人士的文字回答读给接听人。这场交流中没有标点符号,“qq”代表一个问号,“ga”代表“请讲”(go ahead),代表对方可以回话了。常会出现类似下面的句子:“萨拉你好,(语气愉快),今天能和我共进晚餐吗qq ga。”接线员们不过是一条条电话线,不能和通话双方发生直接的对话。我只是重复对方的句子,然后说“请讲”。这份偷窥狂们一定会梦寐以求的工作于我却是个无可奈何的累赘,我得一边上班,一边看我给学生们布置下去阅读的小说,要比他们的进度提前一章,一边还得不时停下来,将一个女人打出的字大声读给电话那头的男人听,有些内容让人很是尴尬,比如,“宝贝儿我丈夫走了我现在就想要你——请讲。”
一个春日的早晨,九年级学生们去参加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集会,而我则直挺挺地躺在教室里冰凉的地板上。我的右眼失明了。“压力大而已,”校医院的护士下了简单的结论,并且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我抬眼看看那沉重得仿佛快要掉下来的天花板,发现其中一块嵌板上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大字:“麦尔老师是个大笨蛋!”大厅的那头,响起一阵及时雨般的电话铃声。
和平队给了三个去向让我选择:中国、蒙古和海参崴(Vladivostok) 。我不会说中文。我用不惯筷子。但中国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曾经走进学校里的一家旅行社,问去那里的机票多少钱一张。对方给出个“天文数字”,瞟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去挖点儿金子吧你。
和平队在电话里告诉我,毕业三周以后就可以出发了。当天晚上会把各种表格快递给我。结果联邦快递不给送货上门,我辗转去机场才拿到那封邮件。打开硕大的信封,我仔仔细细地翻看每一份文件:《志愿者任务表》、各种体检合格证明、眼镜订购套装、《隐私法声明》以及签证申请,一切都真实可触,我真的要去中国了。去吧(go ahead),眼前的邮件仿佛在说,这两个字从未在我心里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去吧,去吧,去吧。
那是1995年,中国当局对和平队的戒心很重,认为其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这由十五个老师组成的队伍换了个新名字,“中美友好志愿者”。我的个人信息也被进行了一些“润色”。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读起来音同“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子的凄凉画面。在接受和平队培训期间,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在看见我名字之后低声轻笑,给了我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我用这个名字向中国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总会一阵窃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
和平队来到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内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当地一个专爱揭露丑闻的作家在一本名为《天府之国魔与道》 的著作中,对内江的毒品交易有过描述。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两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英语教师。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外一座悬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满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窗外刺耳的猪叫。没有手机电话,更无网可上,要和家里联系了,就用学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纸,写封家书,放进信封,用鱼胶粘上邮票,再寄出去。校园窄窄的主路总是泥泞不堪,旁边有一家餐馆,地面是泥巴铺的,我就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最忙的时候,我一周上八小时的课,向那些二十出头,仿佛拥有无尽活力和智慧的学生们传授知识。日常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每月领八百块钱工资的我能生活得不错,这里除了当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从来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什么压力和必要。手表从我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以及学校的开学放假,就足以说明时间的变换了。
1997年,我作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务期已满,就来到北京,继续教英语。在“乡下”呆了整整两年之后,北京于我,简直就是个国际大都市。当时,这座城市也和其它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汪汪相连的湖水,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一条胡同的宽度一般和两边四合院院墙的高度一致。四川有着起伏的丘陵,其间间插着农田和开阔地,天空中总是飘着阴云,一年到头难见阳光。而北京则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这里的气候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明尼苏达。我还在这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见钟情。
世间的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然而,从小的经历也让我对城市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母亲童年时居住的底特律,曾经繁荣辉煌,现在则成为一座工业“废城”,贫富阶层分群而居。我父亲的故乡洛杉矶,一条条高速公路无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园,并且肆无忌惮地四处延伸。在我土生土长的明尼阿波利斯,人们竟然不得不在室内观看职业棒球大赛。我在那里的家位于城外一条偏僻得好似与世隔绝的泥路上,一排排榆树和桦树伸展着枝条立在两边。后院的栅栏只为美观而设,一片片玉米地绵延好几公顷。今天,那条路被铺上了砖,树木被修剪和砍伐,只为绿化某些公司的停车场而设。玉米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别墅。一个教书匠微薄的薪水,是绝对买不起的。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甚至速度更快。每过几年我都会回到和平队生涯开始的内江,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充满怀疑地说,“你确定在这里住过?你指的方向都让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渡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桥;河岸的峭壁也通了一条条公路;职业技术学校也升级成了一所大学。我下了车,站在一片雾霾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响起,“梅教授?”原来是那时的邮递员。他领着我,沿着铺饰崭新的人行道,来到我过去住的那座外墙铺有白瓷砖的楼房。那是十年前盖的楼了,状况仍然不错。但已经被指定为需要拆除的房子,即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宾馆。过去的那个校园,那个我曾经渡过生命中两年快乐时光的校园,早已经消失了。
不过,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变化时,也意识到这整体上是一件好事。我不是个刻意怀旧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新校园有现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气,锻炼运动的场地也宽了许多,校园中的道路也铺了沥青,更加美观和安全。学校申请到一些请外教的资金,不再单纯依靠志愿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奥的响亮口号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美化和翻新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条条的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逐渐地消失着。可能你不久前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经是家常便饭。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这儿了,”没有人能给出别的答案。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新北京”一点儿也不陌生。这座城里的第一家星巴克于1998年开张。九年后,城区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馆,将近两百家麦当劳和规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数十家必胜客,还有一家猫头鹰餐厅 。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宽,上面行驶的私家车也以一天约一千辆的速度增长。一家北京报纸惊呼《自行车王国一去不返!》。在曾经荒凉的郊区,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而高尔夫球场(11座)和滑雪度假村(12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书。学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发展的郊区。这片区域处处是奢华贵气,独门独院的别墅,因此被大家称为“别墅之乡”。我从市内乘车去上班的时候,总会经过一段布满购物中心的地带,还能看见一家达美乐披萨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豪华的大门上写着诸如“丽高王府”、“王朝花园”、“优胜美地”等富贵洋气的名字。我总是睡意朦胧地靠着校车窗户望出去,周围的学生们则在争论谁家的乡下保姆更蠢笨,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进我耳朵里。经过“美林香槟小镇”的建筑工地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工地外的大广告牌上有几个丰满高大,面带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槟正在开怀畅饮。旁边有一行英文:“同来喝香槟圣饮,一切烦恼远离你。”我觉得牌子上那几个人真是面目可憎。在“别墅之乡”,一切的确看起来很遥远,特别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烦。正值“非典”肆虐,市民们几乎中止了所有的户外活动,只有建筑工地还照常开工。在从学校返回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时,校车会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大的电子计时牌,正为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做着以“秒”为单位的倒计时。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变成了165,369,211。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再会,老北京》的书名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感,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而括号里的英文副标题《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更是让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我一直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气质和灵魂,而老北京的那种韵味,是独一无二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一种非常细腻、富有画面感的方式,为我展现那些正在或已经消失的老北京的街景、建筑,以及最重要的,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我希望作者能够捕捉到那些细微之处,比如胡同里孩子们的游戏,老街坊们的家长里短,以及那些传承了许多年的老手艺。这些细节,往往比宏大的历史事件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让人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温度。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对过去的温柔回望,是一次与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的告别。我希望它能够让我沉浸其中,仿佛亲身经历那个年代,去感受那份浓厚的京味儿,去体会那种“再会”所带来的复杂情感——既有对过去的留恋,也有对当下和未来的审视。
评分我一直对那种能够勾勒出时代轮廓的叙事方式情有独钟,尤其是那些关于城市变迁和人文记忆的作品。从这本书的书名《再会,老北京》以及括号里的英文副标题《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我 immediately 感受到了故事的基调。它并非是那种宏大的历史宏观叙事,更像是一种近距离的观察,一种带着个人情感的注视。我猜想,作者一定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体验和感受那个时期的北京,用敏锐的笔触捕捉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是清晨街边早点摊的热气腾腾,也许是胡同里孩童的嬉笑打闹,又或者是老人们坐在门口闲谈的温情时刻。这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往往才是构成一个时代最生动、最真实的肌理。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走进那些古老的胡同,穿梭在青砖灰瓦之间,去感受那份独属于老北京的宁静与淳朴。我也很好奇,在“老北京”逐渐隐去的过程中,那些曾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是如何流转的,他们又是如何面对时代的洪流,又是如何与自己心中的“老北京”告别的。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一次与过去的温柔拥抱。
评分拿到这本《再会,老北京》,我最先被它的标题所吸引,那种带着告别意味的名字,总能勾起人心底最柔软的怀旧情绪。而括号里的英文副标题《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则更加直观地指出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属于“老北京”的最后时光。这让我充满了期待,我希望这本书能以一种极其生动和写实的方式,将那些被岁月冲刷的细节重新呈现出来。我想象中,它会描绘出老北京独特的街景,那些弯弯曲曲的胡同,那些古老的四合院,那些在晨曦中冒着热气的早点铺,以及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更重要的是,我期待它能够捕捉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哲学。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地理和历史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情感的书,一本关于记忆的书。我希望能从中找到一种与过去连接的桥梁,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温度,以及那份“再会”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既有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评分这本书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普遍的情感共鸣点:对过去美好的追忆和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当我们谈论“老北京”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不是一个具体的年份,而是一种抽象的、充满温情和人情味的生活状态。我相信《再会,老北京》这本书,正是试图抓住这种感觉,用文字来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我期待它能够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节奏,那种不急不缓,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或许会有关于四合院的描写,关于各种传统手艺的传承,关于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我尤其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刻画,在那个相对淳朴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更近,情感也更加真挚。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扇打开的窗户,让我能够窥见那个曾经鲜活而又充满魅力的世界。我希望能从中感受到那种“再会”的意味,不仅仅是对一个地方的告别,更是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某段时光的告别。这本书,定然承载着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深深眷恋,也承载着无数读者的共同回忆。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人,那种泛黄的纸张质感,加上略显沧桑却又充满故事感的插画,仿佛已经穿越了时空,将我带回那个时代的北京。我一直对老北京有着一种莫名的情怀,或许是因为那些经典的京剧、京味儿十足的胡同生活,又或者是那些承载着历史痕迹的老建筑。所以,当我在书店看到《再会,老北京》时,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翻开它。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一种细腻、真实的方式,展现那些即将消失的旧日时光。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关于建筑、街道的记录,更能触及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点滴,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坚守与变迁。当我拿到这本书时,那种沉甸甸的纸张和油墨的香气,仿佛就是老北京的味道,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期待。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那些稍纵即逝的画面,又是如何用文字唤醒那些沉睡在记忆中的影像。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充满温度的老照片,它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离别,也预示着新生的可能。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感受到那种“再会”的仪式感,既有对过往的眷恋,也有对未来的憧憬。
评分很好的一本书,值得一看,京东买书也很优惠
评分618活动入手的,价格很合适,只希望以后经常做活动,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啊!
评分我只想说,老板你实在是太好了。 你的高尚情操太让人感动了。本人对此卖家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永不变心。交易成功后,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静。自古英雄出少年,卖家年纪轻轻,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今,沧海桑田5000年,神州平地一声雷,飞沙走石,大雾迷天,朦胧中,只见顶天立地一**立于天地间,花见花开,人见人爱,这人英雄手持双斧,二目如电,一斧下去,混沌初开,二斧下去,女娲造人,三斧下去,小生倾倒。**,实乃国之幸也,民之福,人之初也,怎不叫人喜极而泣 .......看着交易成功,我竟产生出一种**——啊,这么好的卖家,如果将来我再也遇不到了,那我该怎么办?直到我毫不犹豫地把卖家的店收藏了,我内心的那种激动才逐渐平静下来。可是我立刻想到,这么好的卖家,倘若别人看不到,那么不是浪费心血吗?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牺牲小我,奉献大我。我要以此评价奉献给世人赏阅,我要给好评……
评分多年前就看过,我也想去重庆拜访一下书中所说的“江城”。
评分这个书是陈书简装版,印制的也就一般般吧,买了三本平均一本20。说是优惠了很多,实际算算也不便宜。唉商家的噱头都是这样!
评分高龄、无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
评分不向前走,不知路远;不努力学习,不明白真理.
评分译文纪实丛书是学习非虚构写作的好材料。
评分“一块零五。”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血疫(译文纪实) [THE HOT ZON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77378/56d94518Nf263c8b6.jpg)
![大灭绝时代(译文纪实) [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0316/553750f8N1aa4d2e0.jpg)
![正义的代价(译文纪实) [The price of justice: a true story of greed and corrup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41155/57b693e7N43a28d31.jpg)
![末日巨塔(译文纪实)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o Road to 9/11]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6242/5aaa25b0Ne3909fd0.jpg)
![奇石(译文纪实) [Strange Ston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3602/rBEQYFNHjVcIAAAAAAR1umt-1pUAAEPMgEbvpQABHXS037.jpg)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荐书联盟推荐】 [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37470/55af0dbfN1c45b88d.jpg)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Complications: A Surgeon's Notes on an Imperfect 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5054/56023fe7N02c36a91.jpg)

![医生的精进:从仁心仁术到追求卓越 [Better: A Surgeon's Notes on Performa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5061/56023491N98dc8ee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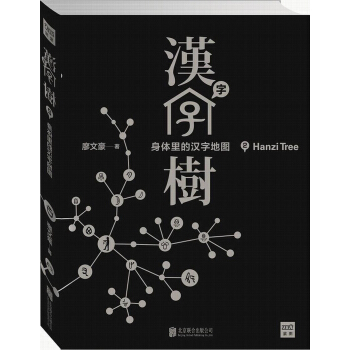



![DK人类的思想百科丛书:科学百科 [THE SCIENCE BOOK]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2602/554c68b3Ne06d37c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