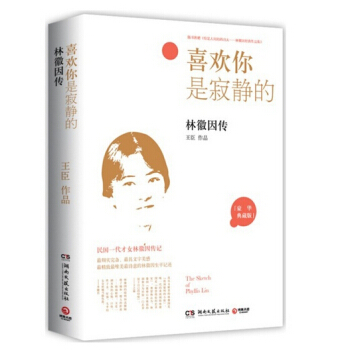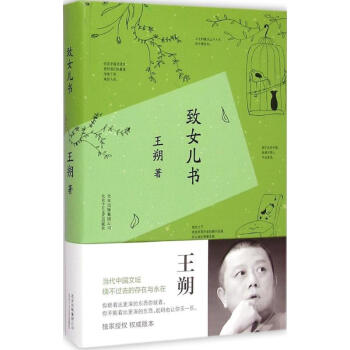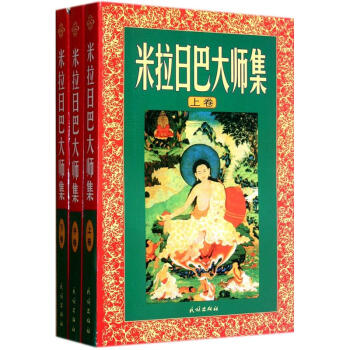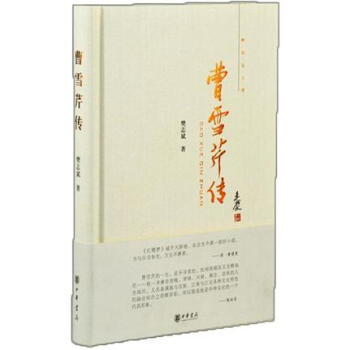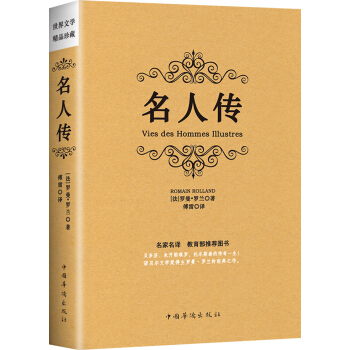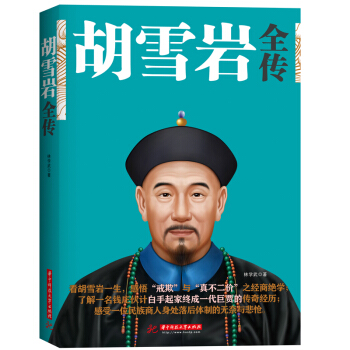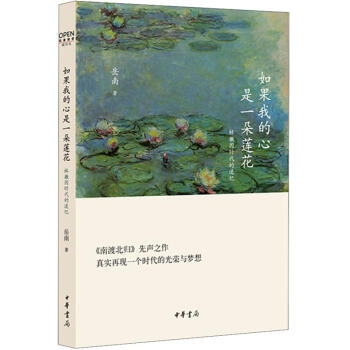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们身边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金岳霖、陶孟和……被迫拖家带口,从北京、南京等地流亡长沙、昆明,最后辗转到达四川李庄。坎坷动荡中,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致力于文化的传承。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史》就是在李庄完成的。抗战胜利,他们虽得以重返内地,但接下来的时代巨变,却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从此天涯永隔!《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通过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图片,对于这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进行了再现。同时,还以当代独特的视角,对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的情感纠葛,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是非恩怨,傅斯年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之间的学派纷争,等等,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与事件,再度以鲜活的形象与映像,凸现于世人眼前。
作者简介
岳南,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理事,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始,着力对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思想脉络、道德精神与学术成就进行调查研究,有系列作品问世;同时撰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部。他的作品屡获好评:《风雪定陵》(合著)入选1996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十大好书,《陈寅恪与傅斯年》入选2008年《光明日报》十大好书,《从蔡元培到胡适》获评第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推荐图书,《南渡北归》入选《亚洲周刊》2011年十大中文好书等。目录
第一章 乱世惊梦五台山的神奇之旅
凄风苦雨别北平
李济的梁家缘
第二章 往事何堪哀
清华四大导师
开田野考古先河的李济
风声灯影里的梁家父子
八方风雨会羊城
梁思永踏上殷墟
第三章 流亡西南
长沙的救亡合唱
千里奔徙到昆明
跑警报的日子
死神过往中的短暂沉寂
第四章 雾中的印痕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
梅贻琦来到梁家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
第五章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
徐志摩之死
第六章 往事俱没烟尘中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
第七章 回首长安远
鸿雁在云鱼在水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
遂把他乡当故乡
第八章 落花风雨更伤春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
血性男儿柔情女
第九章 岁月如歌
川康古迹考察团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一代名媛沈性仁
梁家的烤鸭
傅斯年与陶孟和之争
第十章 胜利前后
京都、奈良的恩人
狂欢的节日
颁布还都令血色黄昏
第十一章 离愁正引千丝乱
归骨于田横之岛
群星陨落
梁思永之死
飞去的蝴蝶
最后的大师
精彩书摘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徐志摩乘风西去,世间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留学美国时的金岳霖生长于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所学专业由经济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他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于欧洲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此点非彼“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已经受欧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当西化的金岳霖,重返清华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自清朝同治年间老金的家乡出了一个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地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和“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斗争哲学”,似乎没有引起金岳霖的兴趣,他的血脉中流淌的是浪漫、天真、风流、率性、淳朴的因子,他作为三湘大地的一个异数,抛弃了湖南人叫得最起劲的“斗争哲学”,而渐渐转向“形式逻辑”的研究。超然物外,视名利金钱如粪土,则是金岳霖的典型特性,他的身上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有不可摆脱的杂质。老金曾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对金岳霖这位多年的同事和旧友,曾做过如此的评价:“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冯氏的比喻未见得完全妥帖,但在老金身上看到人们想象中嵇康的影子当是不差的。
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轶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青睐,其中有一风流俊美的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神神道道地追随老金来到北平,并同居了一段时期。自与林徽因相识后,这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打发到美国娘家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据好事者研究考证,跟金岳霖同来中国的是中文名字叫丽琳(莉莲)的美国女人。此女与老金何时相识相恋记载不详,外界所知的是,该女子与老金同于1924年赴法国游历,后又去意大利转了一圈,于1925年11月来中国同居。在当时看来,丽琳属于妇女界的另类,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又极感兴趣,表示以同居的方式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的生活与爱情真谛,于是便和老金在北平悄然蛰住下来。对于这段生活,当时北平学界许多人都知此事并识其人。徐志摩与丽琳同样相识,他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给陆小曼写的信中对此事有所披露:“老金他们已迁入(凌)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至于这位来自美国的丽琳,因何事、何时离开了老金回归家乡,并黄鹤一去不复返,在已发现的文字中少有记载,而当时的学界中人又为爱护老金的面子计,对此事大多讳莫如深,后人也就无从知晓了。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老金与梁、林夫妇相识并成为朋友,思维与处事方式颇为另类的他一高兴,干脆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择林而居”了(金岳霖语)。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是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同住在一处的,只是按老金的说法:“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这段话是老金晚年的回忆,并自称“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中的座上常客。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自然地非寻常人可比。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而林对老金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甚至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这段情缘,许多年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关于金岳霖为林徽因而终身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从口传与残存的文字看,这三人间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生未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继续孤独的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只存温热的灰烬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自己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推理:“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老金闲来无事,平时迷恋养鸡、养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奇事。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晚年在回忆录《赵家杂忆》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按:杨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莉莲·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
就在杨步伟“助产”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据当代作家黄集伟说:“某日,伏天,数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闲坐。一进门,便见金先生愁容满面,拱手称难:‘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啦!’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细问,但念及‘金老头儿’独身一人,不便诸多,便做英雄状慷慨允诺。俄顷,厨师为来宾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英雄言辞尚余音缭绕,无奈,只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于不顾将碗碗热奶一饮而尽。谁知几位不几日再次光顾,重又承蒙此等礼遇,且金先生口气坚定,有如军令。事隔旬日,好事者向金先生问及此事,方知原来金先生冬日喜饮奶,故订奶较多;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饮奶’一举。也许金先生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减尽由主人之便的通例。当友人指点迷津甫毕,金先生照例回赠四个字的赞许:‘你真聪明!’”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使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雇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面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实际负责人吴宓是老金的好友。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之句(吴与自己的发妻陈心一生下三个女儿后离婚,转而追求一代才女毛彦文,但终生未果)。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夫妇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受业于金岳霖,后成为知名作家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另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整个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国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断,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张岳霖了。
金岳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基本上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属于名重一时的欧美“海归”派。虽然各自的专业不同,但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老金的专业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老金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1922年28岁的时候,曾经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海归”派一样,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也和其他教授一样,有自己的一贯看法和一套为人处世的道德哲学。
为此,金氏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海光,1949年赴台湾在台大任教多年)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后来在思想与学术上的发扬光大。尤其到台湾之后,殷氏成为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并成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殷海光去世后,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记录殷氏临终前话语的《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一书,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的交往及其对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的逻辑研究会。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哥德尔(K。Goedel)工作的重要,老金说“要买一本看看”,他的一个叫沈有鼎的学生当场对金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老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当时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认为“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后来,老金在西南联大的一位叫王浩的高徒,在美国读到这个故事后,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所言是也。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学生,金岳霖精神的血脉得以延续,薪火代代相传。而他来李庄的故事,因其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地位,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坐标,成为整个中国抗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长期存活、绵延于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记忆里,成为一道亮丽、永恒的风景,镌刻在滚滚东逝的扬子江头。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捧读这本书,书名本身就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徐徐展开。“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这是一句多么温柔的自我审视,饱含着对纯粹与宁静的向往,隐约透露出一种不染尘埃的灵魂特质。而“林徽因时代的追忆”,则将这份内心的诗意安放在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背景中。我开始想象,作者是否会以林徽因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去描绘她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与价值?抑或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体味那个时代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他们对家国命运的忧思,对艺术的执着,对情感的真挚?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呈现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忽略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的瞬间。或许,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林徽因,更是关于那个时代无数个“我”,她们的心,或许都曾是那朵在时代风雨中静静绽放的莲花,在艰难中保持着内心的坚守与优雅。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份对那个时代女性力量的深刻理解,一份对人性在动荡中坚韧不拔的赞美。
评分初读这本书名,便被一种难以言喻的诗意所吸引。“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多么温婉而坚韧的比喻,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似乎暗示着一种超脱尘俗、内敛而又自持的精神境界。而“林徽因时代的追忆”,则将这朵莲花安放在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坐标上,一个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一个诞生了无数才情横溢的灵魂的时代。我忍不住想象,在这本书中,作者是否会以林徽因的心境为引,带领读者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去感受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与忧伤,去品味那些文人雅士间细腻的情感纠葛,去聆听他们对艺术、对人生、对家国的深刻思考。我期待着,在这文字的海洋中,能够遇见一位如莲般静美的林徽因,看到她如何在乱世中依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留下她独特的印记。这本书,或许不仅仅是对林徽因个人的缅怀,更是对那个时代精神气质的一次深度挖掘,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让思绪随着笔尖,在那个古老而又新生的时代里,尽情地徜徉,去发现那些被时光掩埋却依然闪耀的智慧与情感,去感受那份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评分翻开这本书,仿佛推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窗,微风携着历史的尘埃扑面而来,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书名本身就极具画面感,莲花,自古以来便是高洁与宁静的象征,而“我的心”则将这份意境拉近,赋予了情感的温度。紧随其后的“林徽因时代的追忆”更是点明了主题,瞬间勾起了我对那个风华绝代的女性的好奇与向往。我开始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的坚韧,她们的才华,她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闪光。是通过林徽因的视角,去窥探那个时代的女性群像,还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将那个时代的种种悲欢离合娓娓道来?我期待着书中能够有细腻的人物刻画,能够还原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风貌和文化氛围,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也许,书中会有关于爱情的缠绵,有关于理想的碰撞,有关于家国的忧思,这些都会让这本书更加丰满和动人。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对那个时代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是历史的事件,更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悲喜无常,都值得被细细品味。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像一首婉约的古诗,又像一声悠长的叹息,勾勒出一种宁静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这是一种多么纯粹的自我期许,一种超脱世俗的渴望,仿佛在喧嚣的世界里寻觅一处属于心灵的净土。而“林徽因时代的追忆”,则将这份内心的宁静与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紧密相连,这其中定然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张力。我猜测,这本书或许会以林徽因的生命轨迹为主线,但并非简单的生平叙述,而是通过她对艺术、对人生、对情感的独特理解,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影。或许,书中会深入探讨林徽因在动荡年代中的情感选择,她与梁思成、与徐志摩、与金岳霖之间那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感情,作者会如何解读?是着重于她内心的挣扎与取舍,还是从更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去分析?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够超越对明星人物的猎奇,去挖掘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担当,去呈现他们如何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里,在传统的束缚与现代的呼唤之间,寻觅自己的价值与归宿。
评分古人说“书剑报国”,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学识和工作服务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奉献我们所生长的国家。作为一名语言文字工作者,手中的笔便是利剑,便是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热忱的关怀。
评分媒介和技术的剧烈变革,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发生裂变,从传播到互播的过程也厘清了整个媒介发展的脉络。本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应该正确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并且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正如作者所言:“从媒体到新媒体,没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实际上,相对于新的传播工具的兴起,我们也大可不必用焦虑的心态来看待传统媒介的日渐式微,而如何找寻一种突围机遇,恰恰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传统媒体应对时代发展所不可忽视的问题关键。
评分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徐志摩乘风西去,世间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留学美国时的金岳霖生长于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所学专业由经济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他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于欧洲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此点非彼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已经受欧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当西化的金岳霖,重返清华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自清朝同治年间老金的家乡出了一个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地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和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斗争哲学,似乎没有引起金岳霖的兴趣
评分很好的书,值得大家买来一睹
评分:..岳南1.岳南
评分虽然说没有京东自家的物流送,也不至于直接用出版社的那个蛇皮纸包吧!里边也不加个塑料袋,弄得书都脏了,书角也皱了,当年贝塔斯曼用的是盒子装、当当网也包了至少两层塑料袋,还有本书本来的封皮都给弄破了内页还有水渍
评分《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通过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图片,对于这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进行了再现。同时,还以当代独特的视角,对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的情感纠葛,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是非恩怨,傅斯年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之间的学派纷争,等等,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与事件,再度以鲜活的形象与映像,凸现于世人眼前。
评分:..岳南1.岳南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得一读,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们身边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金岳霖、陶孟和被迫拖家带口,从北京、南京等地流亡长沙、昆明,最后辗转到达四川李庄。坎坷动荡中,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致力于文化的传承。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史就是在李庄完成的。抗战胜利,他们虽得以重返内地,但接下来的时代巨变,却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从此天涯永隔!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通过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图片,对于这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进行了再现。同时,还以当代独特的视角,对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的情感纠葛,林徽因与冰心之间的是非恩怨,傅斯年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之间的学派纷争,等等,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与事件,再度以鲜活的形象与映像,凸现于世人眼前。,内容也很丰富。,一本书多读几次,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徐志摩乘风西去,世间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留学美国时的金岳霖生长于三湘大地的老金,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所学专业由经济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他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于欧洲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此点非彼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已经受欧美文化的熏陶,生活已相当西化的金岳霖,重返清华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自清朝同治年间老金的家乡出了一个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地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和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斗争哲学,似乎没有引起金岳霖的兴趣,他的血脉中流淌的是浪漫、天真、风流、率性、淳朴的因子,他作为三湘大地的一个异数,抛弃了湖南人叫得最起劲的斗争哲学,而渐渐转向形式逻辑的研究。超然物外,视名利金钱如粪土,则是金岳霖的典型特性,他的身上没有像
评分不错的一本书,值得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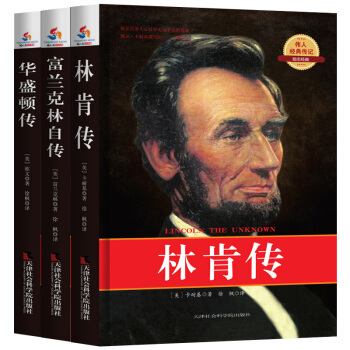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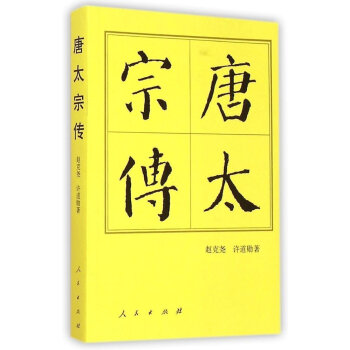
![皇马圣经 [Biblia Del Real Madri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39181/57c959ecNdc9212b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