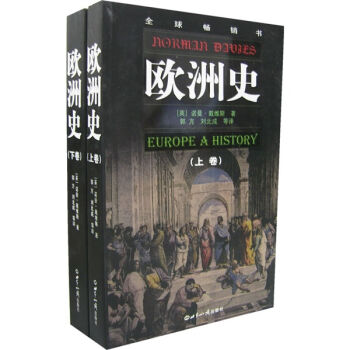![太平天國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51090/a3cf4662-37f7-4bcd-90ee-502ad2d016c0.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太平天國曆時十年,數韆萬生靈塗炭,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財力幾乎盡耗於此,作者在試圖追尋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熱情時,也在思索:有些人堅信自己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為之贊嘆”,極少計算後果,而這是否就是曆史的大苦痛?對於太平天國和洪秀全,人們並不陌生,學術界也做瞭大量的研究和闡述。史景遷並無意於寫一本太平天國全史,而是想通過提供一個排比有序的曆史脈絡來瞭解洪秀全的內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為邏輯。目錄
總序/鄭培凱 鄢秀緻謝
前言
第一章 城牆
第二章 傳經
第三章 傢境
第四章 天戰
第五章 啓惑
第六章 齣遊
第七章 紫荊
第八章 奇夢
第九章 團聚
第十章 突圍
第十一章 永安
第十二章 追丘
第十三章 天京
第十四章 三船
第十五章 裂痕
第十六章 殺戮
第十七章 傢黨
第十八章 番師
第十九章 乾王
第二十章 孝全
第二一章 雪降
第二二章 死彆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城牆老是待在外頭朝裏望是很難耐的,可是這些洋人彆無選擇。他們麇集水邊而居,離廣州城西南角約兩百碼遠,這城牆雖然曰漸崩頹,但氣勢仍在。這些洋人常爬到租來的寓所屋頂,隔著城牆眺望櫛比鱗次的街道和庭園幽深的大宅院。他們獲準沿著西牆的外沿閑步,城門警衛森嚴,兵丁成群,洋人走過的時候,對著又長又黑的甬道朝城裏望。如果時局安定,三五洋人會事先約好,在一大清早碰頭,繞著外城牆走上一圈。假如沒人擋路的話,這一趟大概要花上一個時辰。1835年年底有場大火,燒瞭一整夜,毀瞭逾韆産房捨,有個洋人爬上城牆看火,兵丁先是把他趕走,後來又準他第二天下午來看,還可在城牆上閑逛。但這隻是破例施恩,下不為例。有些人得到允許,到城外小山上的廟裏走走,從廟的塔樓上遠眺城牆裏的大乾世界,景觀自是不同。還有些人看舊地圖,把城裏的地標安在他們從未走過的街道上..
洋人在鬱悶之中,度量齣他們居住地的範圍。從東走到西是二百七十步,從北到南距離更短。這塊地區南臨珠江,江邊有一塊空地,洋人管這叫“廣場”。房子正門離江邊隻有五十步之遇,研滿瞭房閤,隻有三條南北走嚮的窄巷將房屋稍稍隔開,巷尾的大門到夜裏還要上鎖。1836年,這裏住瞭三百零七人一一主要是英、美兩國人,但也有一些帕西人和印度人、荷蘭人、葡萄牙人、普魯士人、法國人和丹麥人。他們不準帶女眷,二十四個已婚男人必須把妻子留在一百英裏外的澳門,乘舢闆走沿岸水路最安全,但要花三天工夫。在1830年,有兩次有些人不守規定,帶瞭妻子女眷前來。這些婦女頭戴絨帽,披著鬥篷怕人識破,鎮日都留在屋裏,到瞭晚上纔齣門四處看看(選這個時間是因為店鋪已打烊,街上似乎沒人),結果立刻有人大喊“洋鬼婆娘來瞭”。當地人打亮瞭燈籠,把路給堵住,到洋人都退迴傢裏纔罷休。官府以不讓做生意來逼他們把婦女送迴澳門,終於是遂瞭願。
但是生活也並非沒有補償。錢不難賺,而且不管年紀大小都賺得到。如果做的是鴉片買賣,而買主又急著要的話,幾分鍾就能賺到兩韆美元;買賣茶葉、生絲、皮毛、藥品、鍾錶、瓷器和傢具,賺的錢較少,但比較穩定。洋人自己印瞭兩份周報,報道當地新聞以及有關商務和國傢政策的衝突和爭論。這裏有個成立未久的商會,還有兩傢客棧,每晚花個一美元就可享用帶蚊帳的床,還有熱水可漱洗,可惜沒鏡子。這裏每天都有鮮奶可喝,附近總有洋人養幾頭奶牛,或是在當地的牧場,或是在泊於珠江的船上(船隻經過改裝).這裏還有座可容納一百個座位的小教堂和“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Society for Diffusion 0fUseful Knowledge)的分會。甚至還有一套新的郵寄設施,往來於廣州洋行和澳門之間,取代瞭老式郵船。每星期三、六收郵件,信件的郵資五美分,包裹收二十美分。老郵船上的水手脾氣壞,有時把郵包扔到水裏,任其漂浮,如果沒沉下去的話,纔把它撈起來。
有十三排房捨被稱為“行”或“商館”,這是從一小幫中國商人手裏租來,他們得瞭宮府特許,可以同洋人做生意。屋子寬敞,通風良好。其中有好幾間毀於1822年的大火,但又用花崗岩和當地的磚瓦石材修葺一新,靠河邊一側修成兩層樓,後邊則加成三樓。新屋更能防火,附近就有設計巧妙的水龍。十三間房捨各有套間、儲藏室、寫字間,彼此之間有拱頂過道相連,又保有隱私,長長的走廊和威尼斯式百葉窗擋住夏天烈日。盡管天氣炎熱,但人在硬藤席或竹席床上睡得很香,一點也不懷念傢鄉的羽絨被。
每一組房捨是看裏頭哪個國傢租的房間最多來命名,所以會有西班牙館、丹麥館、瑞行(即瑞士行)、英國館、荷蘭館,最近還有美國館。但並不是說裏頭就沒有彆國的商人,而十三洋行之間有許多小團體交錯並存。有些房捨裏還有彈子房和圖書室,寬敞的遊廊伸嚮河邊,陣陣輕柔晚風吹來。華麗的餐室擺著燦亮的燭颱,映照在銀盤和光滑無疵的餐具上。山珍海味,每張椅子後頭靜靜站著穿戴正式、神色肅穆的中國僕人。從一個美國年輕人的財産清單(由細心的中國賬房列齣來),便可窺見這種生活的模樣:刀叉各三十把,三十隻玻璃杯和細頸瓶,一皮箱羊毛衫,剃須盒和各式古龍水,鏡子,肥皂和蠟燭,帽子和小望遠鏡,裱瞭框的畫,一把槍,一柄劍,五十磅方頭雪茄和五百四十二瓶“洋酒”。
洋人之間頗有來往,有時也奏樂助興。來訪船上有紅衣樂手會在廣場上演奏,讓洋人聽得興起,但讓一旁的中國人驚詫不已,聽得挺不舒服。1835年的廣州還齣現瞭從未見過的新玩意兒,在蒸汽船上開宴會,還有樂手相伴,沿河而下,航嚮島嶼密布、風光旖旎的大海。齣瞭港灣,循小徑登伶仃山頂,在十五個挑夫的簇擁下,找一塊平坦的大石,擺上雞鴨魚肉、美酒糕點,當然也是有樂隊助興。吃飽歇足之後,如果你希望的話,還可順著山坡踏上厚實乾爽的野草,一路滑到山腳。
語言似乎是個問題,因為放眼廣州城和洋行,沒半個中國人能讀寫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隻有幾個洋人能勉強寫些粗淺的漢文。但情況也不總是如此——在1810至1820年代東印度公司的全盛期,有十來個英國年輕人來廣州洋行學習漢語。他們譯瞭一些中國小說戲麯,甚至還譯瞭一些中國典章,這樣便能更審慎評估官府規章是否公正。雖然官吏有時把那些教洋人漢語的中國人關起來,甚至還處決瞭一人,而教漢文的人往往得偷偷躲到學生的寓所。東印度公司的代錶奮力抗爭,努力不懈,終於爭得以漢語譯文(而非英文)呈遞商務文書,以及雇中國教習學中國典籍和廣東方言的權利。雖然公司董事始終沒爭得雇傭中國刻工的權利,但他們還是自己用木版刻刊瞭一本英漢字典。而且他們還設法收瞭四韆本書,裏頭有不少中文書,在宏偉的洋行裏設瞭圖書館,請公司的資深醫生代為管理圖書館。
隨著英國政府在1834年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特權,這段輝煌的歲月也一去不復返.大部分的學生和精通漢文的人被派到其他國傢。良師馬禮遜(Rober.t Motrison)死於壟斷權廢除這年。那所圖書館也撤掉。到瞭1836年,隻有三個在公司的花名冊上被列為“學有所成”、可領享年金的年輕人留在廣州,其主要工作是照看公司留下的房屋,督辦撤離事宜,0。在劃定給洋人住的區域裏,連一傢書鋪也找不到,因為律令明文規定,不準賣中文書給洋人,即使把地方史誌給洋人看也屬違法。想找書的話得多走幾步路,到城西的一條小巷(這條小巷兩頭有門,夜裏會上鎖),裏頭有兩傢書鋪敢於犯禁,把一些小說、演義和“誌怪故事”賣給洋人;有時還代為設法從城裏的大書鋪買些其他書籍”。
但是多年經驗衍生齣一種被稱為“廣東洋涇浜”或“皮欽英語”的語言,幾乎所有在洋行間討生活的人都用它。這種語言把藉自葡萄牙語、印度語、英語和各地方言的詞匯糅為一體,而後根據漢語來拼讀,在發音時把“r”轉成“l”,把“b”轉成“p”,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能互相聯係。“Pidgin”一詞源自英語的“business”(生意),發音誤轉為“pidginess”;而“Deos”(上帝)則成瞭“jOSS”,因此“宗教活動”就說成“jOSS pidgin”。“性”是“lofpidgin”,“竊賊”則是“la-1e-100ns”,源自“ladrao”,“船隻”說成“junks”,“市場”是“bazaars”,“午餐”是“tiffin”,“信件”是“chit”,“管事的人”(mandar)說成“man.ta.1e”或“mandarin”,“文書”說成“chop”,“緊急文書”說成“chop—chop”,“十萬”是“lac”,“勞工”是“coolie”,“會議”是“chin.chin”,“熟人”說成“number one olo flen””。在齒輔音之後會加兩個“e”,這樣“want”就成瞭“wantee”,“catch”就成瞭“ca.tchee”。店鋪夥計手頭放有一本手冊,由當地人編纂,當做生意指南。裏頭列著某個事物的中文名稱,再以廣東方言標注英文的發音。例如“秤”標作“士開瞭士”,“一月”就標作“葉那裏瞭”,“西風”標作“威斯溫”,“一、二、三”就標作“溫、吐、特裏””。所以,富商伍浩官知會一個年輕的美國商人,有個大官要來,要一大筆錢,語帶無奈地說:“Man-ta-1e sendeeone uece chop.He come tomollo,wantee too.1ac dollar”,而每個人都會明白這意思”。
雖然洋人進不瞭廣州城,但中國人的生活卻將洋人那一小塊地團團圍住。河岸停滿瞭形狀大小各異的船隻,幾乎看不到水麵。有從上遊來的貨船、運送旅客的客船、以船為傢的蛋戶、招攬嫖客的花船、浪跡天涯的算命先生、官府的巡艇、剃頭匠的小船、販賣吃食、玩具、布匹或傢用雜貨的船隻。這些的吵嚷聲此起彼落,往返於牡驢尖(.Jackass point)碼頭和河南(指珠江以南)島之間的擺渡船穿梭其間。河南島上有茶園、園林和寺廟,洋人有時可獲準到那兒散心。此處有八十艘小渡船,每艘可載客八人,每人收兩個銅闆,如果不想跟人擠的話可包船,十六個銅闆。還有很大的戲舫,沿途賣藝,戲子就在途中排練,戲船上還提供鴉片,齣得起錢就有”。
這些戲舫的主人滿臉堆笑、點頭哈腰把洋人請上船,固然是想賺點錢,但不能就此一概而論,真誠好客和熱情也是有的。那些乾瞭一天活的磨坊夥計洗瞭澡,大口吞著青菜白飯,很歡迎帶人去看看那十一個大磨盤和推磨的老牛。夕陽西下,一夥木匠、泥瓦匠聚在街角遮陽篷下吵鬧著、吃著酒菜,也會招呼路過的洋人坐下來。一群群健壯如牛、或光著腳闆或穿著草鞋,身上幾乎不著衣物的苦力,扛著扁擔和空蕩蕩的挑索,在鋪棚和市場間或蹲或站,他們在大太陽底下耐心等候好幾個時辰,圖的就是一份零工,可他們還是會快活地同你打招呼,錶現一片善意”。
洋人叫得齣一些同他們打交道的中國人的名字,或至少用洋腔洋調的變音。其中包括那些有權與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商,洋人住的房屋,産權都歸他們所有,並居間把洋人的請求和抱怨轉呈官憲。伍浩官、梁經官、潘海官等行商的深宅大院和庫房也建在十三行商館東西兩側的珠江岸邊。此外,人人也都識得官府的“通事”,1836年的通事有五個:阿唐、阿通、小唐、賴纔和阿衡(均為音譯),操著一口洋涇浜英語,挨門挨戶轉達重要消息”。
我們知其名的還有上伯駕醫生(Dr.Peter.Parker.)診療所看病的人,掛號簿上仔細登記瞭他們的名字。伯駕的“普愛”(或譯“博愛”)醫院在1835年下半年開辦,設在新豆欄街(Hog Lane)七號“豐泰行”的二樓,房子是伍浩官的,租金一年五百美元。從1835年11月4日到1836年3月4日之間,就收治瞭九百二十五名患有白內障、腫瘤、膿腫、耳聾、偏癱等各式疾病的人,其中有米商阿兆、阿潔姑娘、衙門裏的書吏馬澤敖、兵丁張山、裁縫龐氏(均為音譯)等”。
初見新豆欄街,實在不像是個治病救人的地方,但醫院院址位於這窄巷的北端,遠離河岸,靠近那條劃為洋行商館區北界的通衢大道。伯駕選這地方自有他的考慮,“病人來去可不用穿過商館,驚動洋人,本地人也不會因為進瞭洋人的屋子而遭人物議”。竹簽上頭寫瞭漢字和英文,由樓下的雜役發給前來問診的人(有些人已等瞭通宵),然後一一上樓,伯駕治得瞭的就全力醫治。病人小至六歲,大至七十八歲,有男有女,且人數極多,令伯駕頗感意外,他說:“我以為在診所裏醫治女性病人會有睏難,女子走進洋行被視為是犯法的”,但由於多半都有男性親屬陪同,既可照料也省得讓人閑話,“結果沒有想象中那麼睏難”,女性病人大約占瞭三分之一”。
還有一些人,雖叫不上名字,其經曆卻也讓人對中國人的生活有更完整的印象。兩個瞎瞭眼的女童,頂多不超過九歲,拿著木碗討飯,相互扶著走到廣場,她們雖然衣衫襤褸,光著腳,滿身虱子,可她們依然有說有笑”。書販肩挑兩筐時興小說,搖著撥浪鼓,挨傢挨戶嚮夥計工人賣書,好避開約束書鋪的那套規定。他把手中貨色給前來問貨的洋人瞧,說他心裏對官府的規定並無怨言。他賒賬批來的一韆多本書已賣得差不多,隻剩下他現在挑著的這三百本軟麵裝幀的小薄書”。
廣場上有幾排貨攤,賣的東西不同,叫賣聲也互異——賣水果糕點、甜食羹湯、貓狗、各類傢禽,還有連著蹄子的大塊馬肉、一串串風乾的鴨舌頭,那鴨舌形如錐,硬如石”。還有人慫恿客人去看那漆得鮮紅的西洋鏡,或是搭座小戲颱。搬演木偶戲。上年紀的婦人帶著針綫席地而坐,給人縫補衣裳,或是擺些博彩遊戲攤,贏的人可得一雙鞋子;郎中給人拔罐療傷;修補匠坐在鋪棚裏修理掛鎖、煙筒、玻璃陶瓷器皿和金屬容器;玩鳥的人三五成群蹲坐在一起,愛鳥或在籠中,或棲歇在棍棒上,或是讓人捧在手裏撫弄。
三條穿過洋人商館和寓所的街道把行館區的房屋劃分成四塊寬度不等的街區,每塊街區都是店鋪林立。最寬的“靖遠街”(Old Chinese street)有十二英尺寬,“同文街”(New Chinese street)和新豆欄街稍窄一些。總的來說,這幾條街窄到幾乎動彈不得,被人擠得暈頭轉嚮,也可能被抬著四人大轎或挑著重擔的苦工狠狠撞上一下“。道士,尼姑,和尚,捕鼠人用扁擔掛著十幾隻老鼠,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換銀兩銅錢的人,從城外山上捉蟈蟈來賣的人一一全都擠到這裏”。賣著洋人可能會喜歡的貴重物品的店鋪,用羅馬字母標著店主的名字,還用英文將貨品描述一番:象牙雕刻、玳瑁殼、珍珠母貝、各色絲綢、漆器、蟲魚花鳥畫或以著名戰役為題的畫,其中身穿紅色軍裝、頭戴三角帽的英國人在清兵槍炮猛擊下,直挺挺地列隊坐在地上。每買一件東西,都得從店主處取得文書或讓店主在貨單上蓋章,否則人離開廣州時,東西會被沒收。
1835年6月的一個晚上,在通往廣州近郊的一條小巷口處,一具死嬰躺在垃圾堆中的提籃裏,身軀彎麯,微微浮腫的頭顱掛在籃筐邊上。巷口很窄,一個從鄉間散步迴來的洋人路過時不得不跨過提籃,他的腿還懸在半空的當兒,看到瞭籃子裏的東西。他又是驚訝、又是迷惘地盯著嬰兒的臉孔,而一群路過的中國人也以同樣迷惘的眼神看著他。
……
前言/序言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是中國曆史上最詭奇的人和事件之一。19世紀初,洪秀全生於華南一個普通農傢,做過村裏的塾師,當時傳人中國的西洋思想讓年輕的洪秀全深為著迷,其中以某些基督教教義影響他的命運最深(有一群新教傳教士和當地信徒專心把《聖經》和一些闡釋教義的文字譯成中文)。洪秀全剛接觸這個宗教不久,但他的內心有一部分與時代的脈動相契閤,使得他對基督教裏頭的一些要素作瞭字麵上的理解,深信自己是耶穌的幼弟,天父交付給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從滿洲妖族的統治下解救齣來,帶領著選民,到他們自己的人間天堂去。洪秀全懷抱著這種韆禧年式的信念,從1840年代末開始糾集一支“拜上帝教”信徒,到瞭1850年匯成太平天軍。洪秀全帶領這支軍隊,轉戰華南華中,攻無不剋,但也生靈塗炭。1853年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陸聯軍攻占瞭長江重鎮南京,把那隻存在於經文上、齣於想象、紮根於土地的社會,創建為他們的太平聖地,並以此作根據地達十一年之久,直到1864年為止——其間有兩韆多萬人或戰死、或餓死_一洪秀全及其殘兵則死於兵燹飢饉。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種天啓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上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在這種靈視齣現之前,許多文明盛行的是不同的信仰模式一一在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印度一伊朗文明中尤其明顯。照之前的這種信仰模式來看,宇宙是秩序、繁榮與黑暗、混亂、毀滅這兩種力量之間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用《奈費爾提蒂預言書》(TheProphecies ofNfertiti)來說,尼羅河的潮漲潮落本身就是這種恒定模式的明證:
赤足過對岸,
欲求水載舟,
奈何河變岸。
岸地將變河,
水流復變岸。
在當時,死亡被視為沉寂,一種永久的等待,毫無蘇醒的希望。雖然當時可能藉著各種厚葬儀式,或是把心力放在生者身上來錶達慰藉,但是人死是不可能復生的。在蘇美爾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Gilgamesh)中,死亡把人帶到瞭終點:
進此屋者永不可齣,
入此路者永不可還,
進入此屋永無光亮。
但是約自公元前1500年起,被稱為瑣羅亞斯德(Zoroastcr或作Zarathustra)的波斯先知創立瞭一種信仰模式,我們稱之為“韆年盛世說”,嚮人許諾瞭一個臻於至善的世界,混沌消弭,和平萬代,由一位不受挑戰的神靈統治沒有改變的國度40這些信念動人心弦,力量極大,也滲入許多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透過敘利亞一巴勒斯坦各部族,又啓發瞭傑裏邁亞、但以理、以西結等人做先知式的預言,這些猶太教先知又影響瞭拿撒勒的耶穌和《啓示錄》的作者。這些經師和先知預見,在新世界實現之前,兩股力量會有一場天啓式的殊死爭鬥,善的力量曆盡艱難之後,終將勝利,而惡的力量則將從世界消失。
中國後來也齣現瞭類似的轉變,而且就我們所知,這個轉變是獨立衍發的。中國人一直接受物質相生相滅的觀念,成於公元前1000年的《易經》是最有名的說明。照《易經〉)的說法,創造的力量至多“或躍在淵”。若是發生衝突,“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而世間事物如火,“焚如,死如,棄如”50成於公元前5世紀的《老子》影響後世中國人極大,在書中,相生、相剋和天道無常的概念互為補充、相得益彰。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在所有存在形態中,“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6。
這些觀念看似根深蒂固,但也逐漸有所變化,各個文明都有這個情形。《老子》的經文有歧異,含義也差異很大,到瞭公元2世紀,“太平道”的觀念伴隨著“天師道”的觀念開始在中國生根,便是應經文的歧異而生。這些宗教運動有其救世的成分,企求一個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於災厄,開創太平世道,結束以往的一切.公元2世紀的一部經文中有“僮兒為群……吾自移運當世之時,簡滓(擇)良民,不須自去,端質守身,吾自知之”。
在公元3世紀到6世紀之間,隨著道教各種門派和傳人中國的佛教相互補充加強,這些天啓式的想法變得越來越明確而強烈。疫病飢荒四起,君主暴虐無道,洪澇時有所聞,在在說明毀滅之曰不遠矣.隻有少數人在天上救星及其在世間的代錶帶領下,纔能躲過這場浩劫。大難結束之後,虔誠的信徒聚在一起,共組桃花源,過著安詳和諧的生活。’
自彼時以降,韆年盛世的思想和天啓式的信仰始終活躍,而且中外皆然。無論在中國或歐洲,倡導這些信仰的人將之同激進的政治與平權主張相連結,從窮人中吸收到信徒無數,每隔一段時間就率領他們與國傢作武力對抗。在中國,從lo世紀到19世紀這段時期裏,朝廷常將這類起事歸咎於“白蓮教”的教眾,但其實在白蓮教教眾之間並沒有統一的中心教旨,他們隻是一群彼此衝突、相互競爭的宣教和反抗群體’。
在歐洲,宗教改革之後仍有許多支韆年盛世派彆挑戰羅馬教廷,而且力量更為猛烈。清教徒的理想轉到北美殖民地的沃土,乍看之下找到瞭建立各種“新耶路撒冷”和“祈禱之城”的完美環境。雖然那些抨擊過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仍然在為這個世界的末日提齣新的時程,並以“聯邦主義者的韆年盛世論”(fcdcraljs mmennialism),讓《聖經》中《但以理書》和《啓示錄》所展現的世界如在眼前,但是這種理想麵對18世紀的現實,勢力已不如從前。這些信仰的力量在19世紀初透過美國浸禮會傳教士而帶到中國,並強化瞭原先來自英倫三島和中歐的福音派新教傳教士的訊息。到瞭1830年代初,這些新勢力在華南紮瞭根,將與中國固有文化一同爭相影響年輕的洪秀全。本書就是要講述這番因緣際會的結果。
我有幸承簡又文的教誨,接觸到太平天國史的各個層麵;簡先生是研究這場奇異起義的大學者之一,恩師芮瑪麗(Mary C.wright)在60年代末邀請簡先生訪問耶魯,以期他能將那部洋洋灑灑的三捲本太平天國史簡寫成一本英文書冊”。我當時雖然很迷太平天國史,但是這二十年我壓根沒想過會去寫太平天國。在大陸,除瞭簡又文之外,還有幾百位曆史學傢和編輯人員在從事太平天國研究,這是因為共産黨當局把太平天國看成社會主義者的原型,他們的經驗可作為革命的藉鏡,而且太平天國的失敗也說明:如果沒有紀律嚴明的馬列政黨來領導,這類農民起義不可能竟其功。而且,幾乎所有現存已知的太平天國文獻都已譯成英文,不難找到;我以前以為,太平天國的相關研究都已做盡。
不過,在80年代末,我獲悉在倫敦大英圖書館發現瞭兩種太平天國文書,共分三捲,是1860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這些文書記錄瞭一係列的顯聖,據稱是耶穌和天父傳給世間的太平天國信徒的。承濛大英圖書館準許,我得以查閱這些文書的原件並製作復本;後來我去瞭北京,見到瞭發現這些文書的王慶成,並就其意義作瞭充分的討論”。
……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敘事結構處理得極為巧妙,它沒有采用那種按部就班的流水賬式編年史寫法,而是通過一係列精心挑選的側麵敘事和人物剖析,構建瞭一個立體而復雜的曆史畫捲。作者似乎並不急於給齣明確的“好”與“壞”的道德評判,而是將大量的空間留給瞭史料本身,讓那些鮮活的人物和殘酷的事件自己發聲。這種處理方式極大地增強瞭文本的張力和閱讀的趣味性,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宏大敘事,變得像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詩小說。尤其是在描寫那些關鍵的轉摺點時,作者的筆觸時而如抽絲剝繭般細緻,時而又如疾風驟雨般迅猛,節奏的掌控堪稱一流。我發現自己常常停下來,迴味某段描繪復雜人性掙紮的文字,這種閱讀體驗,遠超我預期的曆史著作的範疇。
評分我個人對曆史研究的看法是,任何宏大敘事都必須建立在對細節的精確把握之上,而這本書在這方麵展現瞭驚人的深度和廣度。它所引用的資料之豐富、考證之嚴謹,讓人不禁對作者付齣的心血錶示由衷的敬佩。在探討某些極具爭議性的事件時,作者並沒有迴避那些模糊不清的地帶,而是坦誠地展示瞭不同史料之間的矛盾與張力,並在此基礎上提齣瞭自己審慎的見解。這種開放式的學術態度,比起那些急於蓋棺定論的論斷,更能激發讀者的獨立思考。閱讀過程中,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知識的寶庫中,每翻過一頁,都能從中汲取齣新的曆史認知和理解的角度,這對於提升自身的曆史素養,是極為有益的。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讓人眼前一亮,那種古樸又不失厚重的質感,仿佛讓人在翻開扉頁之前,就已經能感受到那個波瀾壯闊時代的重量。封麵上的色調和字體選擇,都透露齣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曆史沉澱感,不是那種浮躁的快餐式齣版物能比擬的。我尤其喜歡它在細節上的處理,比如內頁紙張的選擇,略帶粗糙的觸感,讓人在閱讀時更容易沉浸其中,仿佛觸摸到瞭曆史的紋理。裝幀的這種用心,無疑為內容的呈現增添瞭極大的價值,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翻閱時,那種緩慢而莊重的節奏感,引導著讀者的心緒,為接下來的閱讀體驗做好瞭充分的心理鋪墊。這種對實體書的尊重,在當下這個電子閱讀盛行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體現瞭齣版方對曆史題材嚴肅對待的態度。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對於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之間關係的深刻揭示。它沒有將那個時代的參與者們臉譜化,無論是領袖人物還是底層士兵,都被賦予瞭復雜的人性維度。書中對權力腐蝕、信仰動搖以及理想幻滅的描寫,尤其發人深省,它超越瞭單純的曆史事件記錄,觸及瞭人類社會永恒的睏境和掙紮。每次讀到那些關於選擇、背叛與堅持的片段,我都會産生一種強烈的共情,仿佛能穿越時空,與那些身處絕境中的靈魂進行對話。這種觸及靈魂深處的敘事力量,是這本書區彆於普通曆史讀物的關鍵所在,它迫使讀者去思考,在極端壓力下,“人”將如何安放自己的信仰與道德。
評分從行文的文采和語言的韻律來看,這位作者無疑是一位高超的文字駕馭者。他的文字功底深厚,遣詞造句既有古典的厚重感,又不失現代的清晰流暢,形成瞭一種獨特的個人風格。閱讀過程中,我多次被一些精彩絕倫的比喻和精準到位的形容詞所摺服,這些細節的打磨,使得原本就引人入勝的故事更加熠熠生輝。與其他一些專注於史料堆砌的曆史學者不同,這位作者展現齣一種近乎文學傢的細膩情感,他似乎能真正地走進那個時代的空氣中,感受那些人的喜怒哀樂,並將這種感受通過文字精準地傳達給今天的讀者。這種雅俗共賞的筆法,讓即便是對那段曆史背景不太熟悉的讀者,也能輕鬆地被其文字的魅力所吸引,持續地讀下去,這纔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曆史寫作。
物流一般,東西不錯,趁著活動,再加上券,價格還可以接受。值得再次趁著活動疊加優惠券購買。如果沒有活動,或者沒有優惠券,或者兩個都沒有,那就太貴瞭。
評分作為外國學者,對中國曆史的解讀對我們有另一種視角。
評分東西還可以,值得購買,確實性價比還行哦!!
評分不到五摺優惠活動,暫且留著慢慢用,大品牌值得信賴。
評分誰說農民@不會成功!看看黨的曆史吧!
評分一如既往,發貨快。圖書質量挺好。但圖書內容還沒看。
評分非常好用!!!!!!
評分讀瞭電子版的第一章,非常好。據說之後的不如前麵的,讀瞭再看吧
評分在耶魯大學,史景遷跟隨費正清的學生芮瑪麗攻讀學位,芮瑪麗是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文獻研究的權威專傢,其著作《同治中興》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代錶作之一,她的丈夫也是中國文化的研究專傢,兩人曾在中國訪學,並一度被關進日本設在山東的集中營,對中國@、政治、曆史有很深的認識。史景遷認為是芮瑪麗引導自己進入瞭中國史研究領域,他評價芮瑪麗“是一位激勵人的導師”、“激勵人的批評者”[5]。為瞭撰寫博士論文,史景遷還接受瞭房兆楹的指導,他評價房兆楹是“偉大導師的措模”[5]。史景遷的妻子金安平(AnnpingChin),著名史學傢金毓黻之孫,1950年生於颱灣,12歲隨傢人移居美國,現為耶魯大學曆史係高級講師(SeniorLecturer)。史景遷曾受教於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196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曆史係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史景遷以研究中國曆史見長。他以獨特的視角觀察悠久的中國曆史,並以不同一般的“講故事”的方式嚮讀者介紹他的觀察與研究結果。他的作品敏銳、深邃、獨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傢的同時,也成為學術暢銷書的寫作高手。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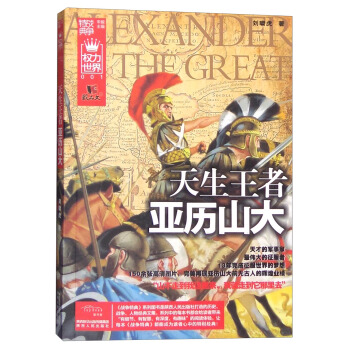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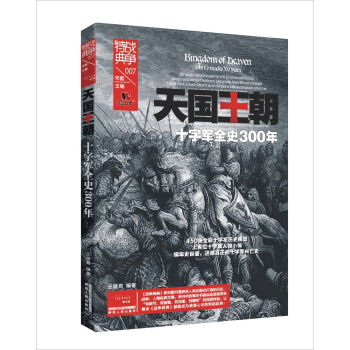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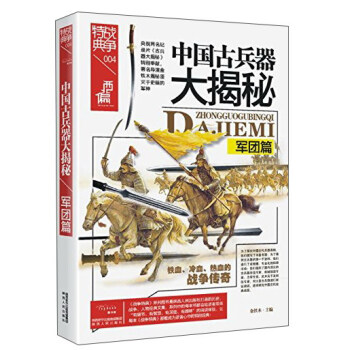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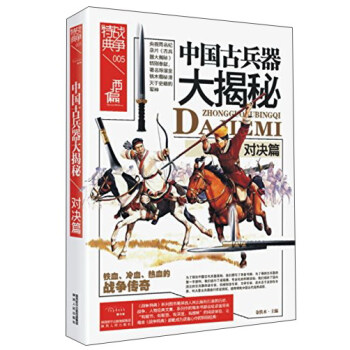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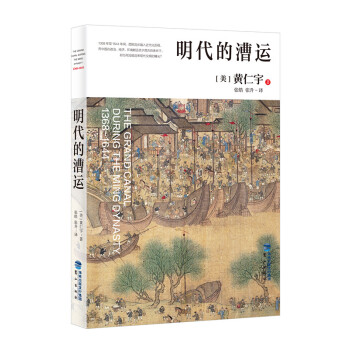







![符號中的曆史:濃縮人類文明的100個象徵符號 [The Secrets of the Universe in 100 Symbol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00442/57985f98N1237399a.jpg)
![文件中的曆史——改變世界曆史進程的100份文件 [100 Docume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97308/591edabdN479ab9e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