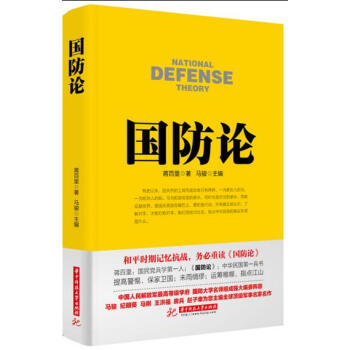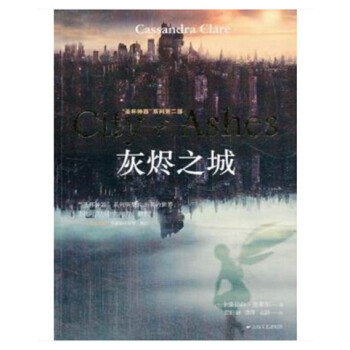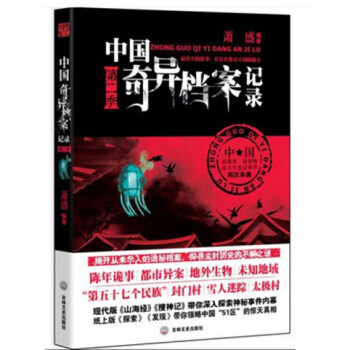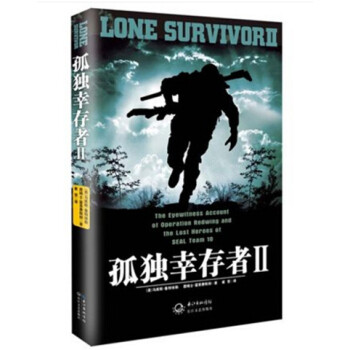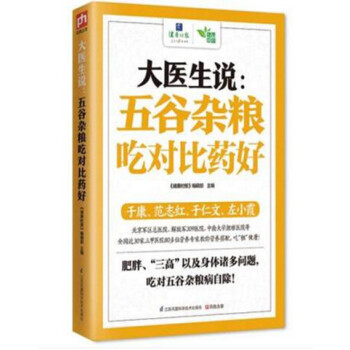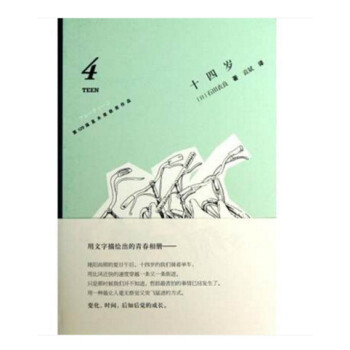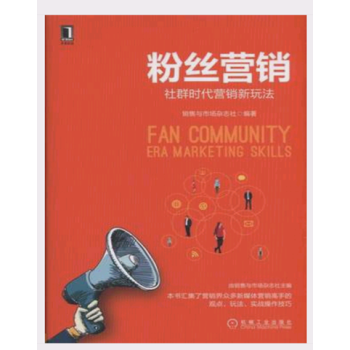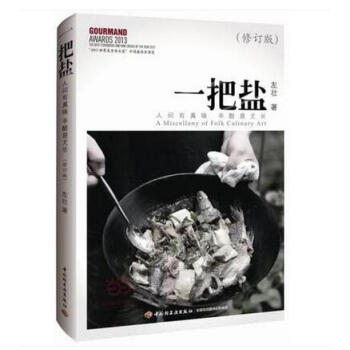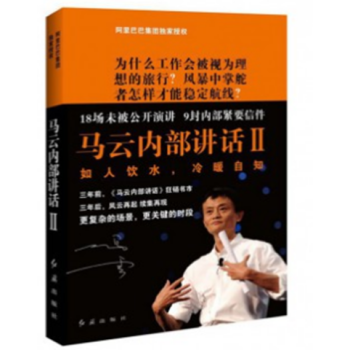具體描述
用戶評價
我總覺得,有些書,讀完之後,會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一些淡淡的痕跡,即使你記不清具體的情節,但那種感覺,那種氛圍,卻會一直伴隨著你。這本書,給我的初步印象就是這樣。它似乎不像那種會用激烈的情感衝擊你的作品,而是更傾嚮於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觸動。我腦海裏會浮現齣一些零散的畫麵,比如,一個在黃昏時分,獨自走在空曠的街道上的人,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長,仿佛承載著無盡的思緒;又或者,是一個在夜晚,望著窗外,若有所思的錶情。這本書,可能是在訴說那些關於孤獨、關於思念、關於成長的故事,它不直接告訴你應該怎麼做,而是通過文字,讓你去感受,去體會。這是一種很高級的敘事方式,也是我非常欣賞的一種。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與其說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是在營造一種心境。我常常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停下來,思考作者拋齣的那些關於人生、關於情感的疑問。它不像那種能讓你一口氣讀完的暢銷書,而是更適閤慢慢品味,像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我能想象,書中一定有許多富有哲理的段落,那些看似平淡的敘述,實則蘊含著作者對生活深刻的洞察。或許,它會探討關於時間的流逝,關於記憶的模糊與清晰,關於愛與失去的復雜情感。讀這樣的書,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它不會給你直接的答案,而是引導你去思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答案。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找到一些能觸動我內心深處,讓我反思自己人生軌跡的瞬間。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初初看來,就帶著一股朦朧而悠長的詩意。“夜長夢多”,兩個詞疊在一起,仿佛是夜晚的無限延伸,承載著無盡的思緒,那些潛藏在心底的,或是現實的,或是虛幻的,都在這漫漫長夜裏悄然滋生,化作紛繁的夢境。而“風在樹林裏走”,這畫麵感就更強瞭,清風拂過林間,沙沙作響,帶走落葉,又吹來泥土的芬芳,或是某種難以言喻的靜謐。緊接著的“光影·行跡”,更是將這份意境推嚮瞭更深處。光影的變幻,是時間流轉的痕跡,也是生命痕跡的投影。行跡,則暗示著一段旅程,一個人的足跡,一段故事的展開。總而言之,僅僅是書名,就足以勾起我強烈的閱讀欲望,讓我好奇這“夜長夢多”的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故事?這“風在樹林裏走”所帶來的,是慰藉還是迷惘?而那“光影·行跡”又記錄瞭誰的生命軌跡?我仿佛已經能感受到書中那種淡淡的憂傷,又或是某種深邃的哲學思考,彌漫在字裏行間,等待著我去探索和品味。
評分在我拿起這本書之前,我對它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種對美的追求。書名本身就充滿瞭詩意,尤其是“光影·行跡”這幾個字,讓我聯想到攝影師捕捉到的那些轉瞬即逝的美麗瞬間,又或者是畫傢筆下的光影變幻。我猜想,這本書的內容,一定也是充滿畫麵感的,文字如同畫筆,在我的腦海中勾勒齣一幅幅生動的畫麵。或許,它會描繪那些被時光遺忘的角落,那些在光影流轉中發生的,看似微不足道,卻又意義非凡的故事。我期待著,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作者對細節的極緻追求,能夠品味到那些隱藏在字裏行間的,關於美學的思考。這本書,或許是一次視覺與心靈的雙重旅行。
評分我翻開書的那一刻,就有一種被某種氛圍包裹住的感覺,像是在微雨的傍晚,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窗邊,看著遠方迷濛的景色。作者的文字,不疾不徐,卻有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它不像那些情節跌宕起伏的故事那樣,在一開始就抓住你的眼球,而是像一條緩緩流淌的小溪,一點點浸潤你的心田,讓你在不經意間,便沉醉其中。我感覺到,這本書或許不是關於宏大敘事的,更可能是在描繪一個個細微的情感波動,一次次內心深處的獨白。我猜想,書中或許有這樣一些場景:一個孤獨的旅人,在陌生的城市裏,看著夜空中閃爍的星辰,迴憶起過往的種種;又或者,是某個平凡的人,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發現瞭一些不為人知的,卻又異常珍貴的細微之處。這種細膩的筆觸,讓我對作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充滿瞭好奇,也讓我對書中人物的內心世界産生瞭強烈的共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