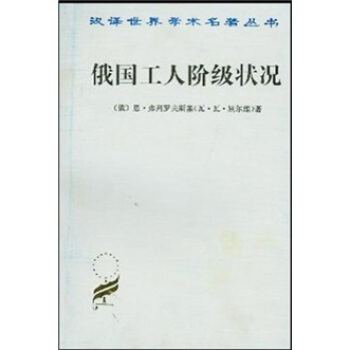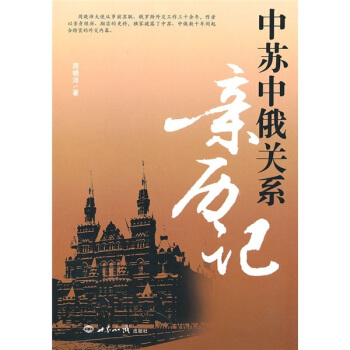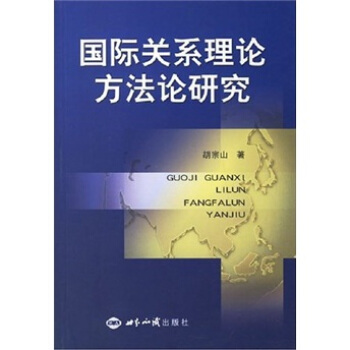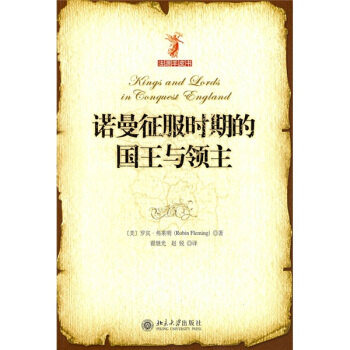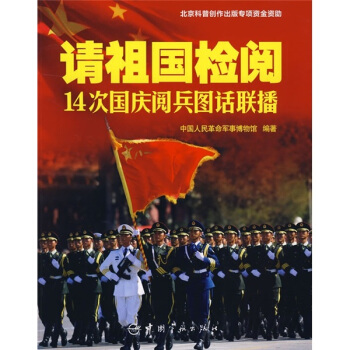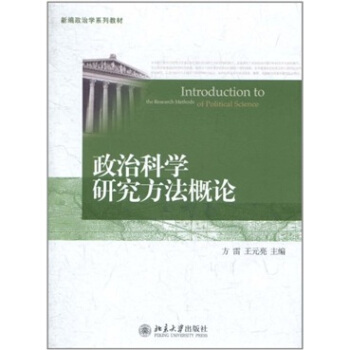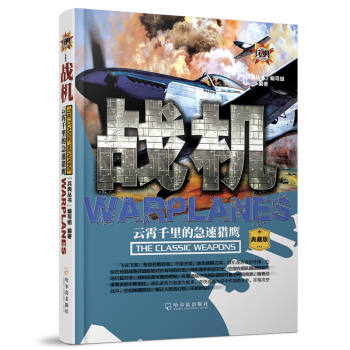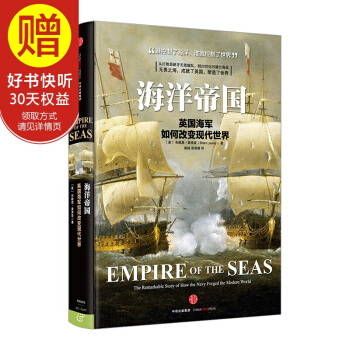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从英国海军400年奋斗历程,讲述大英帝国的崛起,及其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一部了解海权与文明兴衰的入门读物。
第1篇“橡木之心”,讲述16至18世纪皇家海军的发展,帝国的财富、权力和荣誉将诞生于海洋;
第2篇“黄金海洋”,讲述18至19世纪大英帝国的崛起,这一时期的英国证明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第3篇“风起浪涌”,讲述19世纪海上贸易和海上霸权,英国手持两柄三叉戟,缔造了19世纪的帝国传奇;
第4篇“海洋巨变”,讲述20世纪至一战,英帝国海上霸权的衰落,及其引发的全球文明危机。
2、以史为鉴,反思海洋文明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秩序。
英国是海洋文明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近代世界的形成,都被深深地打上海洋文明的烙印。而传统中国一直固守封闭性的农耕文明,长期游离并且落后于以海洋文明主导的现代世界。
如何弥补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差距?是以海洋文明的方式重构现代社会?还是寻求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统一?身处当下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这些问题。
3、《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BBC热播同名纪录片。
《海洋帝国》荣登《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同名纪录片在英国播出时,上至首相,下至民众反响极为热烈。该纪录片由BBC历史类栏目的著名主持人丹·斯诺主持,它和本书一起,共同呈现了一段充满豪情壮志的400年帝国兴衰史,慷慨激昂地再现了大英帝国曾经创造的无与伦比的辉煌。
内容简介
1588年,英国皇家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一胜利成就了一段传奇,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帝国的财富、权力和荣耀将诞生于海洋,皇家海军将推动英国从欧陆边缘走向现代世界的中心。
《海洋帝国》以英国海军400年发展历史为主线,讲述大英帝国的崛起,及其如何影响现代文明的兴衰。全书分为4篇,“橡木之心”、“黄金海洋”、“风起浪涌”、“海洋巨变”,一一展示英国从控制海上交通生命线,到建立全球性海洋帝国,zui终带来全球文明危机的历程。读者可以从书中探寻以下历史:
皇家海军如何从一支从事海上劫掠的乌合之众,发展为维持“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的世界警察?
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怎样打败欧洲几乎所有的海上强国,缔造称霸世界的海上传奇?
海盗德雷克、首相小威廉·皮特、海军大臣费舍尔和丘吉尔……他们所进行的海军改革对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产生了哪些影响?
英国变成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些与皇家海军有哪些内在联系?
英德为何进行海军军备竞赛,英国海上霸权又是如何从鼎盛走向衰落的?
作者简介
[英]布赖恩·莱弗里(Brian Lavery),享誉盛名的海洋历史学家,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名誉馆长。
布赖恩·莱弗里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他不到30岁开始写作,至今著有30多部海洋史著作。他曾担任英国广播电台历史悠久的“时代瞭望”节目(BBC:Timewatch),以及热播纪录片“海洋帝国”系列(BBC:Empire of the Seas)的学术顾问。
布赖恩·莱弗里的代表作有《征服海洋》《航行:5000年海洋探险史》《海洋帝国》,其中《海洋帝国》为BBC热播同名纪录片的配套作品,荣登《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榜前列。
精彩书评
《海洋帝国》初版以来持续占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榜前列,在海军界与大众之间引起很大轰动,到目前为止,这部作品的优秀程度无人能及。
——彼得·霍尔(Captain Peter Hore)
英国海军防御研究中心主席
慷慨激昂,富有深度且亮点频出……本书描述的是一段充满豪情壮志、令人神往的400年帝国兴衰史。
——《星期日快报》
本书引人入胜……如果一位执掌国防、财政大权的政府官员打算读本好书以消磨周末时光,那么此书便是上选。因为从书中他才能知晓:在那旷日持久的战争、冲突中,是皇家海军的辉煌为英国赢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不列颠”。
——《西部早间新闻报》
《海洋帝国》为我们呈现了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第yi次世界大战期间皇家海军的概况。然而,一些极为有趣的史实更好地为人们再现了海军的风采。15世纪战船上的海员们都做些什么?18世纪的高桅帆船上,船员们又能获得何种供给呢?只有诸如此类的详尽细节才能让我们重新认识海军前辈,敬意方生……精彩绝伦。
——《家族史月刊》
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读起来酣畅淋漓,读罢令人掩卷沉思,作者布赖恩·莱弗里是英国著名的海洋历史学家之一,他深厚的研究功底使得本书在写作上扎实、可信。
——BBC “历史”栏目
目录
关于作者
前 言
第1 篇 橡木之
第1 章 战胜无敌舰队
第2 章 漂向内战
第3 章 荷兰战争
第4 章 改良和革命
第2 篇 黄金海洋
第5 章 欧洲战争
第6 章 稳定与停滞
第7 章 拓宽地平线
第8 章 由败转胜
第3 篇 风起浪涌
第9 章 丢失美利坚
第10 章 危机和兵变
第11 章 纳尔逊及新战术
第12 章 海上强国的胜利与局限
第4 篇 海洋剧变
第13 章 长期和平的影响
第14 章 蒸汽、钢铁和炮火
第15 章 战争之路
第16 章 战争的考验
致 谢
注 释
精彩书摘
第1篇 橡木之心
第1章 战胜无敌舰队
世界上大部分武装部队都能寻根溯源到确切的起始年月。英国陆军,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就以有着“第yi脚”(First of Foot)之称的皇家苏格兰团的成立年份——1627年为自己的纪年起始点。皇家空军也有自己的生日:1918年4月1日,空军甚至还有一个父亲——皇家空军司令特伦查特勋爵(Lord Trenchard)。然而,皇家海军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成立日期,因为自国王阿尔弗雷德(King Alfred)于公元900年左右建造战船抵御维京人起的几个世纪中,海军经历了诞生、多次衰落,然后多次重生。300年后,国内外都不受欢迎的约翰王(King John)建造了一支拥有超过50艘战船的海军,由此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海军基地得以发展成形。为了支撑自己冒进的外交方针,亨利五世(Henry V)也营造了舰队,其中就有著名的1418年“神赐”号(Grace Dieu),“神赐”号以1 400吨的排水量位居当时大船之首。1530年新教改革后,亨利八世(Henry Ⅷ)需要舰队抵御天主教近邻们对自己海岸的侵扰。他的堂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James Ⅳ)建造了“伟大的迈克”号(Great Michael),号称“(建造用了)法夫(Fife)地区除了福克兰森林外所有的木材,(以及)所有从挪威运来的木材”。为此,亨利八世也建造了巨大的“神赐亨利”号(Henri Grace à Dieu),势以应对。“神赐亨利”号装载有122门大炮(多数是轻型的),配备了340名士兵,301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49名炮手。到1546年时,亨利已经拥有共计58艘船,其中分为运输船、三桅划桨炮舰,以及小得多的船载艇和划桨驳船。
亨利的船队并没有因为他的过世而解散,这支船队在他的新教儿子爱德华(Edward)和天主教女儿玛丽(Mary)统治期间,虽然规模不再,却得以保存。这种继承延续在历史上是juewujinyou的。玛丽在与法国的对抗中输掉了加来(Calais),所以当伊丽莎白(Elizabeth)在1558年登上王位之时,英吉利海峡第yi次成了英格兰的天然疆域。而她的海军,也在人民的欢呼中,击败了外来的天主教入侵——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zui初,伊丽莎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君主,她于国内外都推行和解政策。但是逐渐地,女王不断陷入与西班牙的小规模战争中,这多起因于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兄弟。他们zui初只是与西班牙进行奴隶贸易,但是1568年,他们的船只在墨西哥的圣胡安德乌卢阿(San Juan de Ulúa)被袭。震怒之余,他们以私人名义与西班牙展开商战,而1577年,他们更是在女王的资助下掠夺了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财物。
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 1596)
德雷克出生于德文郡的塔维斯托克(Tavistock),其父以剪羊毛为生,不时兼职传教,曾在逃亡中落脚肯特郡(Kent),而德雷克就是在梅德韦河(Medway)上学会了驾船。回到德文郡后,德雷克加入了表哥霍金斯的船队,后者对他影响极大。不久后,他们开始从事奴隶贸易,将非洲黑奴贩卖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几次试水后,收益颇丰。然而,这种贸易是违反西班牙当局规定的。1567年,他们的奴隶贸易陷入困境。在回国途中,暂歇于墨西哥的圣胡安德乌卢阿,准备修补船只。一艘西班牙宝藏船也停入港口。几日后,西班牙人突袭了德雷克和霍金斯的船队。兄弟两人损失巨大,勉强得以保命逃脱。破损的船只载着超载的船员一路颠簸到家,惨不忍睹。自此往后,德雷克就胸怀复仇的怒火。据传说,德雷克对西班牙的敌视源于宗教,他本身可并不是什么虔诚信徒,但这完全无碍后世的宣传家追封他为新教英雄。
回国后,德雷克娶妻成家,却并未在新家久留。几次成功劫掠了西班牙货船和据点后,他开始计划1577年的大行动。这次出击可能得到了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支持,并得到了女王本人的资助。他准备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Cape Horn),去劫掠那些西班牙位于太平洋地区富饶但疏于守卫的据点。航行中,大副托马斯·道蒂(Thomas Doughty)因煽动兵变被处以极刑。由于之前损失了大半船只,德雷克只剩下“鹈鹕”号(Pelican)一艘航船。在成功穿过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进入太平洋地区后,他将此船更名为“金鹿”号(Golden Hind)。虽然当时他的船员只剩30人,但是他还是抢劫了不少地方,甚至袭击了满装货物的“理念夫人”号(Nuestra Se�媜ra de la Concepción),而不是其他记录中所说的“卡卡弗戈”号(Cacafuego)。德雷克在加利福尼亚,可能是如今旧金山所在地登陆,又取道太平洋回国,并在归途中,还不忘寻找马尼拉开来的货船。
远航耗时近3年,1580年9月,德雷克终于回到祖国,成为第yi位完成环球航行的英格兰人。起初,女王还因为外交原因对德雷克稍显疏离,但是一如所有的投资人,女王对于此次航海带回来的巨额财富还是表现出了欣喜。德雷克出身卑微,现在却能升官加爵,成为议会一员,甚至买下一座曾经的修道院,当作私宅。很快,德雷克又投入他的海洋事业,举起大旗对抗西班牙,期间成败各半。1585年到1586年间他组织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袭击,攻击了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卡塔赫纳
(Cartagena)以及佛罗里达,并将弗吉尼亚罗阿诺克(Roanoke)地区殖民未成的同胞解救回国。到1587年,战火已燃(德雷克的活动是部分因素),德雷克还洗劫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港口,当时,这些港口都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德雷克攻击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Cadiz),这片海域险要却易攻,劫掠过后,德雷克带着172 000达克特金币荣归,留下25艘西班牙船只沉入海底。在离开葡萄牙港口时,德雷克截获了满载财宝的“圣费利佩”号(San Felipe),并从其船员口中得知西班牙正在准备报复。回国途中,他被提升为英格兰舰队副司令,官阶仅次于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Lord Howard of Effingham),若不是出身寒微,又身处注重门第的时代,总指挥的位置非德雷克莫属。
通过海峡上游时,德雷克命令自己的一支小分队与霍华德(Howard)、霍金斯和马丁·费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一起迎击无敌战队。战斗中,德雷克罔顾命令,截获“罗萨里奥”号(Rosario),并将其带回托贝(Torbay)。在格拉弗林海战(battle of Gravelines)中,德雷克在优势情况下毫不恋战,仅一小时左右就匆匆回撤,显然是为了保护所俘之宝。
战胜无敌舰队之后,德雷克又组织前往葡萄牙的远征,可能由于疏于计划,他既没能煽动起群众反抗西班牙的热情,也没能占领里斯本,或是俘获从亚述尔群岛来的西班牙货船。至此往后,德雷克就在国内休养。直到1595年,他与霍金斯又重组船队,目标是掠夺西印度群岛,如有可能,更想占领巴拿马。霍金斯11月不幸去世,在掠夺了巴拿马之后不久,德雷克也因病去世。他被装在铅制的棺材中,沉入海底。坊间仍有传说[尤其是他的家乡伯克兰修道院(Buckland Abbey)]:“如若英格兰蒙难,只要德雷克的战鼓再次擂响,他定当回归救国。”
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德雷克充满矛盾。他具有典型的航海者的英勇和激进,却在领导力和与下属的关系上饱受争议。他从未彻底放弃过海盗事业,因而在为海军决策时难免心不在焉。他与霍金斯一起为英格兰开启了非洲黑奴贸易的先河。虽然出身卑微,(可能正因为如此,)
但他颇爱在服饰和消遣上掷重金以示不凡。他对于圈中比他富裕或地位高的人出手阔绰,以昂贵礼品慷慨赠予,却很少给自己的船员以同样的待遇。他是一个新教英雄,但他自己的信仰却并不坚贞热忱。
第2篇 黄金海洋
第5章 欧洲战争
法王路易十四不能容忍詹姆斯被篡位一事,计划重新将这一牵线木偶扶上王位,由此英法两国于1689年7月正式开战。此时,不列颠内部的分裂尚未弥合;政府和海军的高层中支持詹姆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齿威廉的篡位行径,意欲帮助詹姆斯复位。与荷兰一样,法兰西也是一个海军大国,同时还是大陆上距离英国zui近的国家,但是英荷战争与英法战争尚不可相提并论。法国对海洋贸易的仰赖程度较荷兰要低得多,英国不可能仅凭海军就将其
打败。相较于荷兰和英国,法国的独裁政府更为高效,国内又少有矛盾斗争。法国能够征召的军队,在规模和效率上都让英国望尘莫及。因此,要想打败法国,英国必须要在大陆上寻找可靠的同盟军。
就单论海战,英国也难以触动法国核心。对战荷兰时,英国只需端坐于其出海口,掐断荷兰与世界联系的咽喉,便可稳操胜券。但是法国的港口遍及大西洋和地中海漫长的海岸线,封锁起来格外费时耗力。与荷兰一样,法国也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帝国,因而切断其大陆和海外领地之间的联系是英国必然的选择。另外,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海岸线相对孤立,英国若想牵制法国海军,还需在此花心思,建基地。
1689年的问题有点儿棘手,因为法国此时的海军规模已经与英荷相当,关键是法国还培养了一名伟大的海务大臣。与佩皮斯一样,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睟aptiste Colbert)的身家背景也不显赫。与佩皮斯不一样的是,柯尔贝尔全然是个工作狂,丝毫不会被周遭俗世所扰,金钱和消遣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柯尔贝尔近乎从零开始营建法国海军。他在荷兰订购、建造船只;在法国本土的造船师出师之前,一直引进国外优秀的造船师(其中包括佩皮斯的好朋友安东尼·迪恩)。他颁布了《航海章约》(Inscription Maritime),至少从公文上看,他建立了比英国公平、有效得多的征兵制度。他还创建了zui低从军校学生[或海军卫兵组织(Gardes de la Marine)]起的完整而规范的海军级别。虽然柯尔贝尔于1683年去世,但是他给法国留下的是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丰富的对英、对荷作战经验。到1689年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军有93艘战舰,而英军要算上佩皮斯新建的30艘,方能勉强与之抗衡;荷兰的战斗力更是只及其一半。
虽然双方的主战场在佛兰德(Flanders),但由于詹姆斯从爱尔兰登陆,寻求天主教徒的支持,因而早期很多小战役都在爱尔兰进行。5月1日,法国军队护卫一支舰队驶出爱尔兰西南部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时,与赫伯特上将(Admiral Herbert)率领的一小支英军狭路相逢。短暂交火中,双方都未尽全力,因而损失也都不大。1690年,当另一支法国舰队行至英吉利海峡,计划封锁泰晤士河,以防英荷两军会师时,英国予以坚决的反击。法国大败,英荷舰队占领海峡。虽然法国舰队在数量上要有优势,但是女王仍命令托灵顿伯爵(Earl of Torrington)迎战,认为“避战之损失将远超投身此役”。两军于1690年6月30日在比奇角相遇——法军舰队拥有战列舰73艘,而英荷联军只有56艘。荷兰小分队充当先遣,全力以赴,而英国的两支分舰队负责留守待命。此次战斗中,荷军只损失1艘船,之后的战斗中也只损失3艘,但是托灵顿决定将舰队撤离到泰晤士河口的贡弗李特。英国weiyi受损的船只是配备70座火炮的“安妮”号,这艘战舰是佩皮斯制造的30艘之一,其船长为约翰·泰瑞尔(John Tyrrell)。托灵顿曾下令让它撤离险境,但是战后第二天,船长报告说:
……伤亡上百人。主桅、后桅、斜桁均破裂粉碎,前桅更是被炮弹击飞。劲风巨浪中,船身连中6炮。我爬上中桅,试图以其充当应急前桅,但是方帆太小,不能匹配。风吹东偏北22.5°及东北方向,法军顺风起势。而我方船只就被老天爷遗弃在敌军的猛击之下。1
到7月3日时,天气越发糟糕,涨潮时“安妮”号在黑斯廷斯搁浅。泰瑞尔写道:“我中枪倒地,被潮水冲上了岸,退潮时,人们可以围着船走动。如果法军炮船不曾乘胜追击至此,我定会全力保其周全。”愿虽如此,泰瑞尔还是没能逃过法军的袭击。5号,法军在拉伊(Rye)海岸造成了不小的恐慌,据当地商人塞缪尔·吉克(Samuel Jeake)回忆:“……他们来此就是为了焚毁、劫掠这个镇子……”2泰瑞尔船长下令焚毁“安妮”号,直到今天,潮落之时,“安妮”号的残骸仍然依稀可见。
托灵顿战败的消息与威廉三世在都柏林附近的博因(Boyne)战胜詹姆斯党人的消息同时传到伦敦,城中一片恐慌。与之前交战的荷兰不同,法国有足够的陆军可以入侵英伦,并且此时,法军已然控制了海峡。万幸的是,法军意不在此。托灵顿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时称,他确保“船队完整”事出有因,因为只要英国海军实力尚存,法军就不敢轻易犯境。这显然违背了女王全海岸作战的方针,女王的计划也是海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多少年来的所思所想。但事实证明,托灵顿才是正确的,法军的攻击确实只是虚张声势。
英荷两国于次年大兴船建,而法国碍于资源紧缺,只建造了区区几艘战船。时至1691年末1692年初,两军都做好了再度开战的准备。英国建造了驳船,训练了炮手,准备从圣马洛(St�睲alo)或是布雷斯特登岸。与此同时,法王路易和前英王詹姆斯也在科唐坦半岛
(Cotentin peninsula)的拉霍格(La Hogue)召集了军队,准备进攻托贝,此处正是当年威廉的登陆点。英荷联合舰队的战船数达近百艘,1692年5月19日,英荷舰队在巴夫勒尔(Barfleur)不远处遇见规模尚不及自己一半的法军。在天气多变的英吉利海峡,两军短兵相接,佩皮斯所建的90门火炮规格的“奥索雷”号(Ossory)也在舰队之列,船上军官记下了当时的战况:
5月19日下午2点,我们占尽天时,迎击敌军。荷军本欲张帆鼓风,风向却略有偏差,只得作罢;我军红队与蓝队少将包围了他们。我方操作熟稔,重填炮弹,沉着应对。大约3点的时候,风向突变朝东,大雾弥漫中我军难以辨清敌军的位置,无从开火。4点左右,迷雾渐散,敌军此时在我军北面。7点时,法军中将所在之船被我炮舰击中,船毁人亡。3艘三等船着火,2艘三层战舰被击沉。当夜幕降临时,风向转为东北向,敌军处于上风,到9点时,已昏暗不见敌踪。3
法军退至拉霍格,联军于23日又率战船火炮围而攻之。很快,战场变为水陆双向——法国骑兵在浅水滩攻击战船,联军在船上以钩竿回应。前英王詹姆斯就随军驻营在不远处,看到此情不免感叹:“唉,唯有我英勇的大英战士能如此奋战。”法国此役共损失大船十数艘,放弃了入侵英伦的计划,伦敦为此欢呼雀跃。
由于法军的主力舰队损失惨重,再想营建新的船只匹敌英荷已属奢望,就连重拾海军强国的雄风,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法军改变海战策略,采用游击战术消耗英荷。全副武装的私人战舰和私掠船在圣马洛和敦刻尔克的港口徘徊,他们都手握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以防其船员在被捕后被以海盗之名处死。他们希望通过劫掠和出售英、荷的商船发笔横财,其中不少也确实能够得偿所愿。1692年一年,仅圣马洛一处的59艘私掠船就劫掠200艘英荷船只。英国海军不得不建立护航和巡游体系来保护商人利益,但是可用的资源分散而稀少,颇为议会中的商人集团诟病。
1693年,贸易保护与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增长产生矛盾。与土耳其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等了近两年时间才盼来自己的护航队,帮助他们穿越那些危险的法国海域。5月,乔治·鲁克(George Rooke)受命率领小分队护送400艘商船出航。英国舰队只护送了整个航程的一小部分,就掉转船头回去保护祖国海岸,留给鲁克的只有21艘战船作为防备。他们不知道的是法国已经提前得知英国船队的计划,从布雷斯特和土伦(Toulon)调集船只90艘,埋伏于葡萄牙南岸的拉各斯海湾(Lagos Bay)。当埋伏的法船突然袭击时,鲁克需要当机立断:
我估约敌军此次出动了整支舰队,商船若想全身而退已属奢望。我原打算竭尽所能保全他们,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转念间,想到中将的言论可能陷我于不义,若不能生还辩解,我就只等骂名传世。
我没有时间左思右虑,如果应战,我们zui多只能撑上一个多小时;敌军的先遣战舰就足以让我军瘫痪,而对方那些后备的船只只需在此时上前,协助补刀,我军必死无疑。而那些先遣部队就能突破防线,直击商船,为所欲为。因此,我确信,倘若当时我们硬做抵抗,当晚整支船队就会一败涂地。4
鲁克撤退了,抛下92位商人被俘,其损失堪比当年的伦敦大火。法军售卖战利品,获得300万里弗的不义之财,抵销了自己近一年的海军开支。而在英国国内,破产者不计其数,议会也吵得乌烟瘴气。
比奇角战役的失败已经让政府感到恐慌。1691年,议会在1677年佩皮斯法案的基础之上,再次通过法案,决议增建海军船只。只可惜此时的英国再也找不出佩皮斯那样的人才,能够贯彻法案的执行,而国王威廉也深陷战争泥淖,腾不出手修改法案。人们已经意识到,与法军相比,英军的战列舰吨位太小;但是议会到此时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劣势。1677年他们曾批准建造20艘配备70门火炮的战舰,而如今也只是将船的规格提高到80门火炮、双层甲板而已。这次船建的结果并不理想。1694年,“苏塞克斯”号(Sussex)在直布罗陀海峡沉没。此后,未完成的船被加建了一层,而已建成的船只也在不久后重建。事与愿违,这些改建只让船况更糟,由于重心过高,造成船身不稳,而且船身过高还容易招风。
法案中欲建造的另一种船型是装载50门火炮的小型船。当时英国海上的主要威胁是私掠船而非战舰,这一船型尤显得应时。从理论上说,50门火炮的数量将达到列队的规模,但这种船型灵活且价格低廉,能够大规模生产,投入海上巡逻和商队护卫使用。可实践结果却并不能让人满意。许久之后,议会终于吸取教训,将船只的设计和建造交还给专家。
战争耗资巨靡,其中大部分被威廉用于佛兰德的战场。为了应对军队在佛兰德的开支,也为了筹集海战军费,1694年,英国成立了英格兰银行。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他于日后带领苏格兰民众,试图在巴拿马的达连湾(Darien)建立殖民地,却未能成功。银行的第yi位行长名叫约翰·霍布伦(John Houblon),是个伦敦商人,也是位金融家,近来升任海军大臣,其所在的委员会负责的正是海军的粮食储备。银行的建立引进了国债这一新概念,政府通过签发债券募集战款,这就避免了时时为了军费与议会口角。在zui初的投资人中,有一位就是塞缪尔·吉克,他曾目睹法军入侵拉伊的暴行,在银行中一次性存入500英镑巨资。与吉克一起购买债券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国王、王后(投资1万英镑),下至砖瓦匠和佣工。
尽管不断有战船损耗,海军规模仍然在战争中得到了扩大,战舰的数量从109艘增长到了176艘。为了支持海军的建设,所有工业的规模都相应扩大了。这些产业除了造船本身,还包括木材供应、铸铁制作、火炮浇铸以及食物补给。一艘标准的战舰需要5吨铁钉。安布罗斯·克罗利(Ambrose Crowley)在泰恩赛德(Tyneside)设厂,以原始的批量生产模式专事生产铁钉。
食物同样重要。1701年,政府下达一系列命令,规定每位海员每天需要“1磅健康、干净的罐装食物,以及用马鞍毯裹好的烘焙到位、储放良好的全麦饼干”。每周要有两天能够吃到“2磅牛肉,所用牛肉均来自精心饲养的牛,并需要在英国本土被屠宰和腌制”,还有两天要能吃到“1磅培根或英国腌猪肉,猪也必须是精心饲养的,且体重不低于0.75英担的;以及以温切斯特的计量衡为标准的1品脱的豌豆”。除却这4天,海员们在剩下的3天中应该能吃到“一份8小块的北海鳕鱼,鱼长24英寸”以及“2盎司黄油和4盎司萨福克奶酪(或是2/3盎司的柴郡奶酪)”。海外服役的标准会稍做改变,例如以甜面包取代饼干,米饭取代鱼,橄榄油取代黄油或奶酪。海员每天都能喝上1加仑的啤酒,如果没有啤酒,就以半品脱的白兰地取而代之。5
没人能如此藐视死亡,在自己的坟墓之上吃喝拉撒;无人能如此无惧风暴,只因醉酒后头昏脑涨。无数次死里逃生,已让他的心如其布满老茧的手掌一样坚硬麻木。他不再噩梦连连,虽然仍逃不开沉没和死亡,但这些威胁已不足以扰乱心绪。
别人委顿时,他却格外坚强;恶劣的气候下,你见他头戴毡帽身披大衣,恍惚间仿若莫斯科归来的沙皇;虽然,他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但在气派的外套下,他无坚不摧,一如穿上盔甲的公猪。6
1697年,法国终于同意签订合约,承认威廉三世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自此往后,1688到1697年间的英法战争就鲜有艺术家或作家问津。少数那几部事关海战的回忆录,主角也枯燥乏味,所用之船形体笨拙,既无法媲美查理二世时期的奢华,也不及后世的轻便敏捷。
而史学家甚至都无法统一口径,为此战命名——“威廉王之战”、“九年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王位继承战”,莫衷一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为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定下了反法的基调,也创造了海战策略中两个著名的短语——“fleet in being”(现存舰队)以及“guerre de course”(种族战争)——虽然这两个短语主要都是英格兰的敌人在用。
克里斯托弗·雷恩建造的格林尼治海军医院(Naval Hospital at Greenwich),却让这场战争成为英国海洋大业中zui值得铭记的时刻。事情起因于1692年,玛丽女王关心离船海员的安置问题,遂在格林尼治划出大片土地用于安置老兵,国王查理之前在此建过要塞。女王任命克里斯托弗·雷恩为这些老兵建造一所医院(或者现代意义的招待所、疗养院)。医院的修建耗时半个多世纪,1694年女王去世时,也未能见得医院全貌。但建成之后的医院被称为“我们拥有的zui庄严雄伟的建筑群”7。其壮丽的绘画厅并不常对那些领抚恤金的老兵开放,却因詹姆斯·桑希尔爵士(Sir James Thornhill)那幅庆祝胜利的画作而声名远播。绘画位于大厅中央,图中国王威廉击败路易十四,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对于17世纪90年代来说,提出这个胜利的预言还为时太早。大厅直到1726年才得以完成,此时,这幅画作所言之物确已凿凿。这绘画厅让人忆及西斯廷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展示了不列颠对海洋霸权的憧憬和向往。
……
用户评价
说实话,我选择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新思文库”这四个字,让我觉得它一定蕴含着新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而“海洋帝国”则勾勒出了一个广阔而充满想象的空间。我一直觉得,对于历史的解读,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视角,才能不断地突破固有的认知。这本书的出现,让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它不仅仅是陈述事实,更可能是在解读事实背后的逻辑,挖掘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以及那些影响深远的动因。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一些前所未有的见解,能够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尤其是那些与海洋息息相关的文明。我更希望它能引发我的思考,让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阅读历史,而是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思考历史的未来,以及我们作为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这种带有启发性和思考性的书籍,才是我一直所追求的。
评分这套书真的太有分量了,光是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它的厚重感,书页的纸张也很有质感,摸起来滑滑的,印刷清晰,色彩也很鲜艳,一看就是用心制作的。封面设计更是让我眼前一亮,那种复古又大气的感觉,特别符合我心中对“帝国”二字的想象。书里的文字排版也很舒适,不是那种密密麻麻压抑的字体,留白也恰到好处,读起来一点都不会觉得累。而且,我特别喜欢它那种能唤起人无限遐想的封面插画,每一页都像一幅精心绘制的油画,让我忍不住想沉浸在那个宏大的故事里。我一直对历史和地理类书籍情有独钟,尤其喜欢那些能够打开我眼界,让我了解不同文明和时代变迁的读物。这本书的装帧和设计,无疑为阅读体验增添了极大的美感,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艺术品,摆在书架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去探索那些未知的世界,去感受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
评分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让我沉浸其中的历史读物,一本能够带领我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震撼。这本书的出现,仿佛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我喜欢它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力量,仿佛能够勾勒出壮阔的画面。我喜欢它对细节的把控,从战争的场面到宫廷的生活,从宏大的战略到个体的情感,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更让我着迷的是,它不仅仅是关于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更是关于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我喜欢那些能够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的作品,它们让我觉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生命。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仿佛能够听到战鼓擂响,闻到硝烟弥漫,感受到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是很多书都无法给予的。
评分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时代,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解读。这本书的出版,让我看到了“中信出版社”在历史类图书出版上的用心和品味。“海洋帝国”这个主题本身就足够宏大,它能够串联起地理、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让我们不仅仅看到那些辉煌的战役和伟大的航海家,更能了解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文化习俗,甚至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我更看重它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或者独到的见解,能够刷新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一本好的历史书,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表面,而应该深入到骨髓,去剖析那些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满足我对深度阅读的需求,能够让我收获更多的知识和启发,并且能够激发我进一步探索相关领域的兴趣。
评分我刚拿到这套书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翻看了目录,光是目录的名字就足以让人心潮澎湃。“海洋帝国”,这四个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和力量。我之前读过不少关于海洋文明的书,但总觉得缺少一些什么,要么过于学术化,要么过于碎片化。而这套书似乎给我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它不像那种枯燥的历史文献,也不是那种猎奇的海盗故事,而是一种宏观的、系统性的叙述,将一个伟大文明的兴衰、崛起与衰落娓娓道来。我尤其好奇它会如何描绘那个时代的海上贸易、军事力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书中的图文并茂的设计,让我对知识的理解更加直观,不再是单纯的文字堆砌。我喜欢这种能够将历史知识与视觉享受完美结合的出版物,它让学习的过程变得轻松而有趣。我期待着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海洋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那些曾经在浩瀚海洋上叱咤风云的帝国,它们是如何创造历史,又是如何被历史所塑造。
评分好书推荐给大家
评分质量很好的书本,快递很给力,准备开始翻阅!
评分中信精品图书,装帧大气精美,值得一读
评分好书推荐给大家
评分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评分内容不错,是我要看的书,印刷精美,就是左下书脊碰了角了。
评分书不错 装曾可以 但是翻译水平一般
评分书不错 装曾可以 但是翻译水平一般
评分书很好是打折买的很便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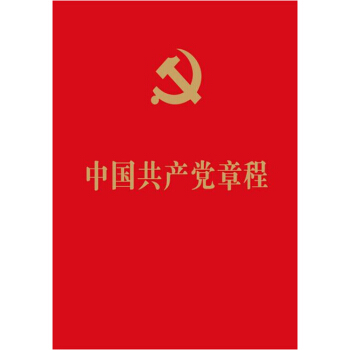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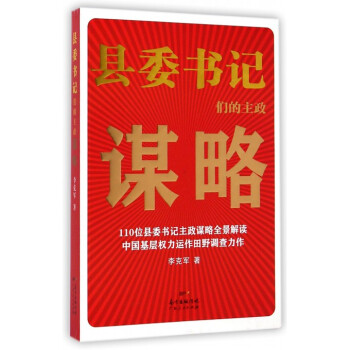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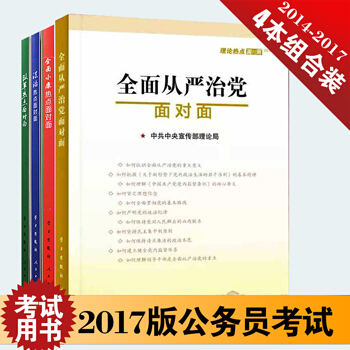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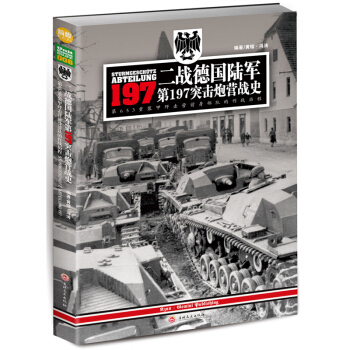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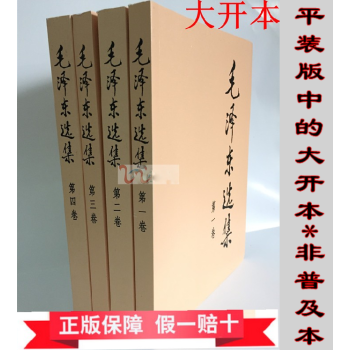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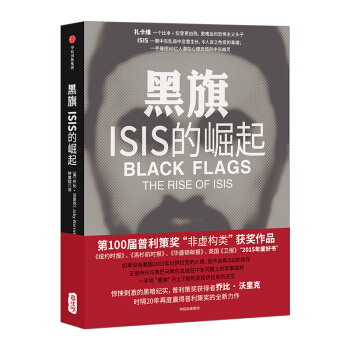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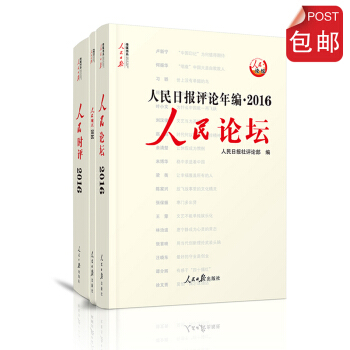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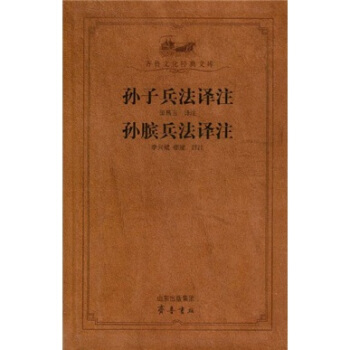
![风险的社会视野(上) [The?Social?Contours?of?Risk]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274561/59e803c6N4b2c3a4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