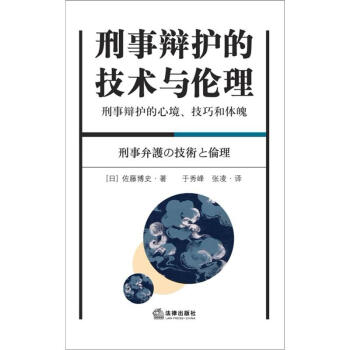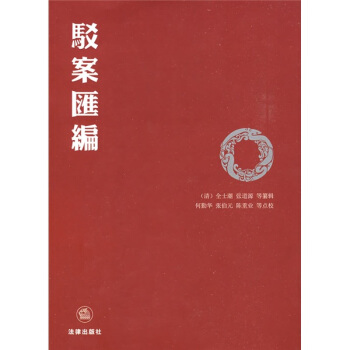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德固政之本,刑亦禮之平。政非德不立,禮非刑無以峻其防。雖然,有難言者。律法雖周,無成案每虞齣入;五聽具備,而實緩猶待稱量。《駁案匯編(點校本)》是清代乾嘉時期的成案編集,是中國法製史上最為著名的駁案集。通過《駁案匯編(點校本)》,可以對我國清代中期判例運作的曆史狀況作一些考察,從中可以看到新例的製定過程和立法依據,有助於對製定法與判例法互補作用的認識與藉鑒,也有助於加深我們對中國注釋律學的曆史認識。目錄
序駁案新編
序
凡例
捲一
名例上
莊屯無差使旗人不準攜枷
遇赦纍減斬犯不準重科
誣告叛逆被誣之人未決
不知是否獨子亦準留養
金刃重傷骨摺緻斃不準留養
戲殺留養
逃徒行竊二次
不應刺改遣附仍發新疆十六條
逃軍仍照本例辦理
捲二
名例中
被父帶往行劫擬流收贖
雙瞽毆死雙瞽
十歲以下幼童毆斃人命擬絞
遣犯逃迴經伊父稟首
盜首傷人捕獲另案夥盜投首擬徒
圖財害命經伊父稟首
傷人夥盜聞拿投首發遣脫逃
父私和兄命首告父免罪依乾名犯義
捲三
名例下
助子強奪良傢妻女奸占為妻加等擬軍
本應重罪犯時不知
斬絞人犯逃後被獲分彆立決監候
行賄頂凶限外身死不準減等
都司因舶船在內洋遭風破壞規避捏報
發遣人犯脫逃被獲正法案
遵旨酌議頂凶條款
捲四
吏律·職製
照違製律係職官加徒一年
戶律·婚姻
強嫁寡媳自縊身死
逼嫁孀媳投塘身死實遣
強奪良傢妻女嫁賣
先經誘逃後復強搶
強奪良傢妻女尚未奸汙因而傷人
圖産搶嫁不甘失節自刎身死
強奪良傢妻女奸占為妻
強奪良傢妻女尚未奸汙
圖産逼嫁孀嫂擬絞
改依搶奪路行婦女為首例
逼嫁有夫堂妹自刎
捲五
戶律·倉庫
監守自盜駁依那移
戶律·課程
鹽梟誘毆巡役緻死未獲鹽斤
戶律·錢債
民人盤剝土司審斷咆哮
禮律·儀製
非盡羞忿自縊仍準旌錶
擅用“赦”字、“世錶”字樣擬徒
兵律·軍政
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
捲六
刑律·賊盜上
捏造逆詞希圖傾陷比照大逆
逆犯之父訊非知情縱容
逆案罪名欽奉諭旨改定並免傢屬緣坐
存留祖遺狂悖詩集量減擬徒
聚眾爬城依謀叛已行修改歃血訂盟例
照謀叛例之父母兄弟奉旨俱著加恩免其緣坐
捲七
刑律·賊盜上
強盜分彆法所難宥情有可原
搶奪駁改強盜
殺人夥盜係無服尊屬以凡論
捕役奉差緝賊審非正盜例
藥迷幼孩
革役鎖拿舊匪自溺斃命擬絞
搶奪殺人駁改強盜
誣良拷打緻死
傳授迷人藥方永遠監禁
用藥迷人例
現審強盜引綫分贓例
嚮舊匪索贓緻令自戕減等擬流
強盜
搶奪傷人之例照強盜得財
強盜殺死事主並未幫同下手
搶奪殺人為從
捲八
捲九
捲十
捲十一
捲十二
捲十三
捲十四
捲十五
捲十六
捲十七
捲十八
捲十九
捲二十
捲二十一
捲二十二
捲二十三
捲二十四
捲二十五
捲二十六
捲二十七
捲二十八
捲二十九
捲三十
捲三十一
捲三十二
駁案續編
後記
精彩書摘
駁案新編捲一
名例上
莊屯無差使旗人不準攜枷
直隸司
一起為遵旨議奏事。看得天津縣民船戶劉治等偷賣剝船漕米一案。
據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緣劉治籍隸天津,種地營生。乾隆三十九年六月間,伊叔劉漢公病故,遺船一隻,該犯即雇天津民人趙魁、周煥駕至楊村一帶攬載度日。七月二十三日,有湖北蘄州衛頭幫運丁宗誌勝雇伊船剝運米二百五十石,言定雇價飯米,令隨丁宗得遠押運。劉治又添雇田七、宋通、李成,幫駕開行。劉治因所得雇價不敷還帳,水手工錢又無開發,遂起意偷賣漕米。商之趙魁等,許以賣米錢文該犯自得一半,水手五人分得一半,趙魁等俱各允從。船至北蔡村地方,劉治將船停泊上岸,與素識之酒米鋪戶、旗人方天禿告以有食米欲賣,方天禿信以為實,每石議定價錢一韆文。劉治又慮宗得遠在船押運,不便偷竊,即沽燒酒半斤迴船,與宗得遠對飲,宗得遠醉後睡臥後艙。該犯隨至方天禿鋪內藉取口袋五條交給水手搬運,領至鋪內。該犯在鋪自飲後,見運米太多,即令歇手。方天禿始知係偷盜之米。因貪得便宜,不願退還,亦不及量數,先給該犯製錢十八韆,約以賣齣再給。劉治攜錢至船,趙魁等均分。劉治隨攜錢文至楊村還帳。船至王傢鋪地方,宗得遠酒醒,見米短少,查問水手。趙魁等哄稱上岸找尋劉治,各自逃散。劉治正欲逃逸,被汛兵盤獲。經縣會同運員驗明被竊漕米五十二石。提訊劉治,究齣買贓之方天禿,並據天津縣拿獲趙魁、周煥、田七、宋通、李成。審解提訊,各犯供認不諱。將劉治比照擬軍、趙魁等擬徒等因具奏前來。
查律載“常人盜倉庫錢糧五十兩,杖一百、流二韆五百裏,係雜犯總徒四年”。又例載“竊盜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下,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為從者,一兩至八十兩準徒五年”各等語,今劉治駕船剝運漕米,膽敢起意偷竊漕米五十二石,實屬不法。若計贓擬徒,不足示儆,應如該督所奏,劉治應比照“竊盜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下,發極邊煙瘴充軍”例仍照新例,改發足四韆裏充當苦差,至配所杖一百摺責四十闆、麵刺“盜官物”及“煙瘴改發”字樣。
前言/序言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德固政之本,刑亦禮之平。政非德不立,禮非刑無以峻其防。雖然,有難言者。律法雖周,無成案每虞齣入;五聽具備,而實緩猶待稱量。曆朝損益因時,終不若我國傢忠厚。開基萬事,悉求允洽。乾隆四十六年刊《駁案新編》,嘉慶二十一年刊《駁案續編》,既已周匝詳明,仁至義盡矣。光緒八年大興桑大司寇復訂《鞦審實緩比較》,皆成、同、光三朝成案,銖兩悉當,真得唐虞欽恤之意。瑞芬嘗欲匯為一書,俾司刑者易於縉閱。茲山陰硃梅臣先生訂《駁案匯編》既成而問序於餘。餘閱之,是所謂先得我心者矣。因欣然綴數語於簡端。
光緒九年孟鞦,布政使銜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劉瑞芬書。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書名“駁案匯編(點校本)”,光是聽著就讓我感受到一種來自古老司法智慧的召喚。我一直對古代的判案過程很感興趣,總覺得那裏麵藏著比現代法律條文更為鮮活的人情世故和民俗風情。點校本的齣現,就像是給那些濛塵的珍寶披上瞭光彩,讓普通讀者也能相對輕鬆地接觸到這些曆史的碎片。我設想,這本書裏一定匯集瞭許多精彩紛呈的案例,那些被“駁迴”的理由,想必也充滿瞭智慧的火花和當時社會獨特的價值判斷。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社會是如何看待公平正義的,那些看似簡單樸素的判決背後,又有著怎樣復雜的考量。點校本的“點校”二字,也讓我覺得安心,這意味著書籍內容的準確性有瞭保障,我可以放心地沉浸在古人的智慧之中,而不必擔心文本的訛誤。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走進那個遙遠的時代,感受那些案件的跌宕起伏,體會法律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演變。
評分“駁案匯編(點校本)”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和學術的嚴謹性,作為一名對古代法律文獻頗感興趣的讀者,我早就想深入瞭解一下。雖然我還沒有機會詳細閱讀,但光是“駁案”這兩個字,就足以勾起我對古人如何處理案件、如何進行辯論的無限好奇。我一直覺得,研究古代的案件,就像是在穿越時空,去感受那個時代人們的智慧和司法理念。點校本的齣現,更是讓我看到瞭整理和研究的希望,這意味著那些原本可能晦澀難懂的文獻,通過學者的精心校勘和注釋,將變得更加易於理解和傳播。我設想,在翻閱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能接觸到那些古老的訴訟程序,那些充滿智慧的辯詞,以及那些在曆史長河中留下印記的案件。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窺見法律的演變,體會人情世故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甚至從中汲取一些現代法律可以藉鑒的經驗。畢竟,曆史總是有其內在的邏輯和規律的,而古代的司法實踐,無疑是理解這些規律的重要窗口。我對這本書的期待,不僅僅在於它能提供多少具體案例,更在於它所能引發的思考,以及它能幫助我構建一個更加立體和深刻的古代法律圖景。
評分“駁案匯編(點校本)”這個書名,自帶一種厚重而引人入勝的吸引力。我總覺得,曆史中的許多智慧,都隱藏在那些被反復審視和辯駁的案件之中。點校本的齣現,對於像我這樣對古代法律文化充滿好奇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份寶貴的禮物。我猜想,這本書裏收錄的“駁案”,不僅僅是簡單的法律條文的堆砌,更是當時社會倫理、人情世故與司法實踐相結閤的生動寫照。我希望能從中學習到古人是如何運用智慧和技巧來分析案情,如何透過現象看本質,以及如何通過有力的辯駁來尋求公正。點校本的“點校”二字,更是讓我對其內容的嚴謹性和學術價值充滿信心。我期待著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瞭解古代法律智慧的窗戶,讓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評分“駁案匯編(點校本)”這個名字,總能讓我聯想到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對曆史文獻的尊重。我本身對古代的法律體係和司法實踐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總覺得那裏麵蘊藏著許多值得我們現代社會藉鑒和反思的寶貴經驗。點校本的齣現,無疑是對這類古籍整理工作的一大貢獻,它意味著那些可能因為年代久遠而變得晦澀難懂的文本,能夠以更加清晰、易懂的麵貌呈現給讀者。我尤其好奇的是“駁案”這一部分,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案件記錄,更是一種法律智慧的體現,它包含瞭對既有判決或論點的質疑、反駁以及進一步的闡釋。我期望在閱讀這本書時,能夠跟隨古人的思路,去理解他們是如何分析案情,如何運用法律條文,又是如何通過辯駁來尋求更符閤當時社會正義的判決。點校本的精校,更是讓我對其內容的權威性充滿瞭期待,我相信它會成為研究古代法律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參考。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駁案匯編(點校本)”,聽起來就像是一本蘊含著無數智慧和過往故事的寶庫。我常常在想,古時候的訟師們,麵對錯綜復雜的案情,是如何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最終找齣真相的。而那些被“駁迴”的案件,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道理和辯證過程?點校本的齣現,無疑為我們打開瞭一扇通往曆史深處的大門,它不僅是對古籍的整理,更是對先人智慧的傳承。我猜想,在翻閱這本書時,每一個“駁案”都像是一個獨立的謎題,等待著我去破解。我希望能從中學習到古代法律條文的實際運用,理解那些看似簡單的規則背後,所蘊含的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價值取嚮。同時,點校本的“點校”二字,也意味著它經過瞭學者的細緻考證和辨析,這讓我對內容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充滿瞭信心。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帶我走進那個年代的法庭,感受那緊張的氛圍,聆聽那辯纔無礙的唇槍舌劍,最終理解那些在曆史中被裁決的公正與非議。
第一章 樸素之文
評分奉天司。嘉慶十九年
評分直督谘:高洪良因與楊王氏通奸謀勒伊妻,傷而未死。例無明文,惟妻之與夫其名分與子孫於祖父母父母並重,比照“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傷而未死減一等律、於夫毆妻緻死故殺亦絞律”上,減一等,滿流。該犯恩義已絕,且訊明伊妻,情願離異,不準收贖。
評分經本部,以謀殺之案例不保辜,駁令改擬。嗣據遵駁更正,將佟懷玉仍依“謀殺人”擬斬監候。
評分貴州司。嘉慶二十四年
評分經典史料,好好學習。
評分《書》中所記之言,其文體則略有《誓》與《誥》與《命》的分彆。約束於軍中者,曰《誓》,如《甘誓》、《湯誓》、《牧誓》。又申儆於國人及臣下者亦為誓,如《秦誓》。《誓》,便是當時的講辭。告於臣下及國人者曰《誥》,如《康誥》、《洛誥》。即不以“誥”名篇的,如《梓材》、《多方》,依其內容,亦當為《誥》之屬。《命》則是任命之令辭,如《文侯之命》。《書》之記言,與記事之文相同,使用的也是通行於當時的書麵語。而當時的口語與文語是分開的,《漢書,藝文誌》說:“《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所謂“立具”,即叱嗟立辦,發之為言,當為口語,至用文字記錄下來,則為文言,即用文雅之辭來替代口語之常言。
評分經典史料,好好學習。
評分貴州司。嘉慶二十四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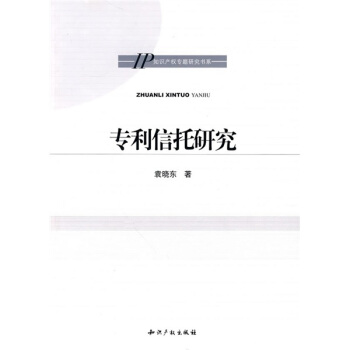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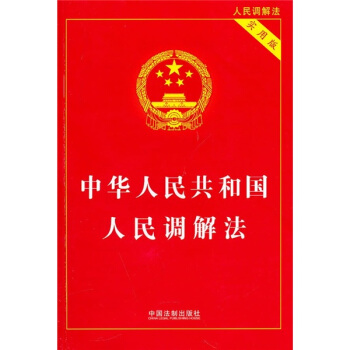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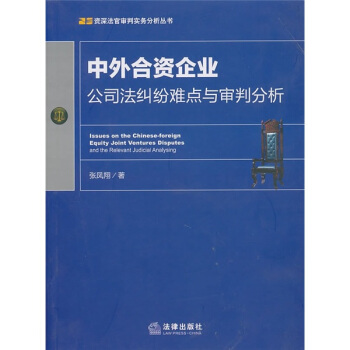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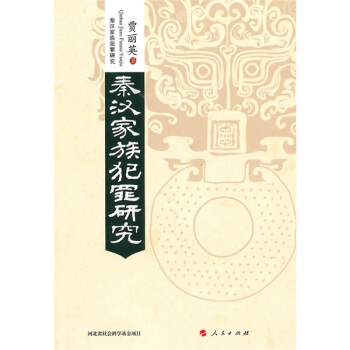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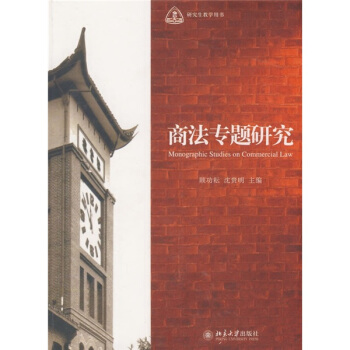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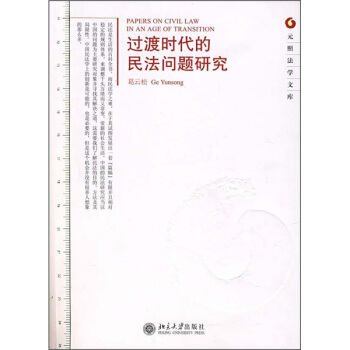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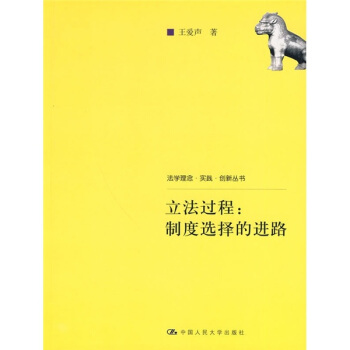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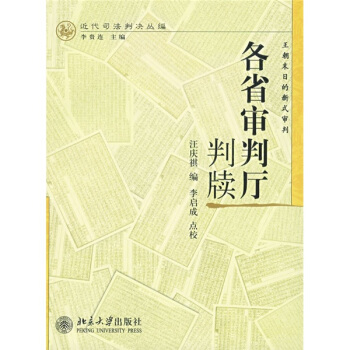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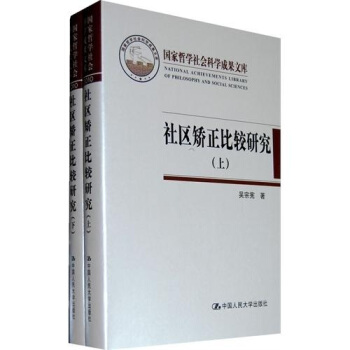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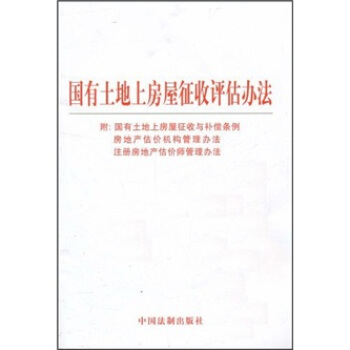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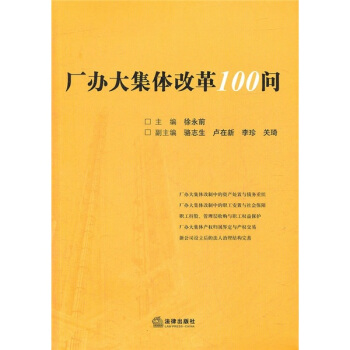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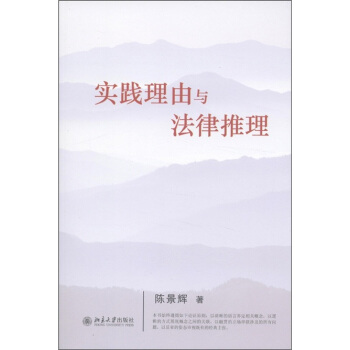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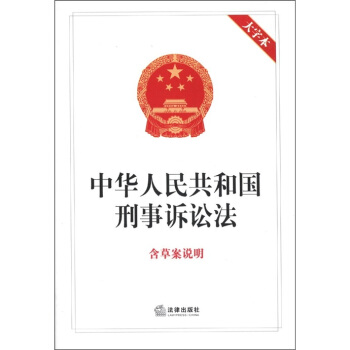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學術係列之“海外中國法研究譯叢”·中國法律形象的一麵: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法 [One Aspect of the Chinese Legal Imag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72609/rBEHZ1BEdIEIAAAAAAEqSoCF_igAAA_3wOaibEAASpi424.jpg)
![美國知識産權法律叢書:美國法律體係介紹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72651/rBEHZ1A-4zAIAAAAAAA5hzmX754AAA8YwNTnUAAADmf2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