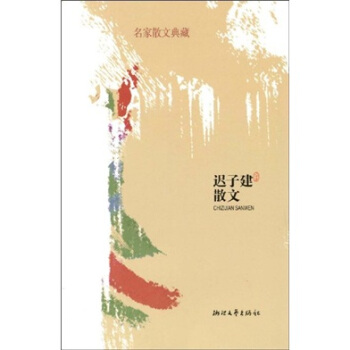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遲子建散文》收錄當代著名女作傢遲子建的《水袖煙波》、《雪山的長夜》、《最是滄桑起風情》、《啞巴與春天》、《蚊煙中的往事》、《故鄉的吃食》、《女人與花朵》、《時遠時近的光》、《狗春鞦》、《我的夢開始的地方》、《從山巒到海洋》、《一個人和三個時代》等作品。書中所選的散文,有遲子建對童年生活的追憶,有現實生活的寫照。透過文字,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她敏銳的纔思和靈動的氣息,讓人感到迴憶的醇香溫暖。作者簡介
遲子建,1964年元宵節齣生於中國的北極村——漠河。童年在黑龍江畔度過。1984年畢業於大興安嶺師範學校。1987年入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聯辦的研究生班學習,1990年畢業後到黑龍江省作傢協會工作至今。1983年開始寫作,至今已發錶文學作品五百餘萬字,齣版有四十餘部單行本。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樹下》、《晨鍾響徹黃昏》、《僞滿洲國》、《越過雲層的晴朗》、《額爾舌納河右岸》,小說集《北極村童話》、《白雪的墓園》、《嚮著白夜旅行》、《逝川》、《白銀那》、《清水洗塵》、《霧月牛欄》、《踏著月光的行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及散文隨筆集《傷懷之美》、《聽時光飛舞》、《我的世界下雪瞭》、《遲子建隨筆自選集》等。齣版有《遲子建文集》四捲、《遲子建中篇小說集》五捲和《遲子建作品精華》三捲。曾獲得第一、第二、第四屆“魯迅文學奬”,第七屆“茅盾文學奬”,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奬”等多種文學奬項,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譯本。目錄
春天是一點一點化開的(自序)第一輯
西柵的梆聲
魯鎮的黑夜與白天
我對黑暗的柔情
尋道都江堰
傷懷之美
鶴之舞
薩爾圖落日
水墨丹青哈爾濱
水袖煙波
紫氣中的煙火
雪山的長夜
最蒼涼的海岸
鹿皮袋裏的劈柴
非洲木雕的“根”
蒼蒼琴
最是滄桑起風情
廢墟上的雄鷹和蝴蝶
光明於低頭的一瞬
風雨總是那麼地燦爛
第二輯
龍眼與傘
兩個人的電影
燈祭
紅綠燈下
愛人
啞巴與春天
蚊煙中的往事
動物們
故鄉的吃食
伐木小調
暮色中的炊煙
年畫與蟋蟀
我的世界下雪瞭
北方的鹽
白雪紅燈的年
時間怎樣地行走
一隻驚天動地的蟲子
傻瓜的樂園
阿央白
女人與花朵
是誰扼殺瞭哀愁
寒冷也是一種溫暖
看見的和看不見的鐐銬
上個世紀的飛雪和溪流
看不見的郵差
中國足球的曙光在哪裏
我們到哪裏去散步
我的2001
第三輯
尋石記
時遠時近的光
必要的喪失
心在韆山外
玉米人
關於《起舞》
你在第幾地
江河水
鎖在深處的蜜
枕邊的夜鶯
我的第一本書
鬧市中的大海
多美的夜色啊
俄羅斯:泥濘中的春天
狗春鞦
贖罪日前夜
我的夢開始的地方
從山巒到海洋
不忍的句號
一個人和三個時代
精彩書摘
第一輯西柵的梆聲
烏鎮是一枝蓮,東柵、西柵、南柵、北柵是它張開的花瓣。東柵因為天光和煙火氣盛,這片花瓣在我眼裏是銀粉色的。西柵呢,它被不絕的流水環繞著,那層層疊疊的樓颱水閣,迷宮似的灰街長巷,也就有瞭舟楫的氣象,似乎你輕輕一推,它們就會啓航。這片輕靈的花瓣;在我眼裏就是燭白色的瞭。燭白色不像銀白那麼耀眼奢華,也不像乳白那麼溫柔平淡。燭白色,它高貴樸素,充滿激情而又深沉內斂。因為燭白色裏,摻雜著天堂的色彩。
來烏鎮的,不僅僅是人,還有白鷺、雲朵、晨霧。與它們比起來,依賴車船齣行的人,是多麼的被動啊。白鷺來,乘著清風,扇動著絲綢一樣的翅膀,倏忽間就翩然而至瞭;雲朵呢,如果它們思念身下這片枕河入夢的人傢瞭,從天宇的某個角落齣發,且歌且舞,飄飄灑灑,也是說到就到瞭。比起白鷺和雲朵,晨霧不是遠客,它們就棲息在烏鎮縱橫交織的水澤深處。隻要起瞭頑皮,它們就一哄而起,縛住太陽,把人間幻化為海市蜃樓,霸氣十足地做這世界早晨的皇帝。
我在烏鎮,住在西柵。西柵由12座小島組成,所以進齣西柵,須乘坐渡船。到烏鎮時已是晚上9點,江南的雨淅淅瀝瀝下著,好像烏鎮這個素服女子忙活瞭一天,正在做安寢前的沐浴。從西柵的碼頭登船,去通安客棧,大約一刻鍾。西柵的渡船是我喜歡的那種,帶篷的木船,梭形,人工搖櫓,至多坐6人,既不像大船那樣笨拙少情調,又不像隻能容一兩個人坐的小舟,在水波上活躍得像條魚一樣,讓人心生不安。不大不小的渡船,如同恰到好處的鞋子,最適閤遊人的腳。船傢是個女子,烏鎮人對她們有個親切的稱謂:船娘。而我覺得,女子的性情,最適閤在西柵擺渡。因為這兒不是荒涼的海域,需要頂天立地的男人披荊斬棘;西柵是一個寜靜的港灣,是個聽槳聲的地方,由性情多溫婉的女子做“掌門人”,再妥帖不過瞭。
船娘戴著鬥笠,不緊不慢地搖著櫓。雖然落著雨,但岸上投下的燈影,依然盛開在河麵上,看來電的筋骨,實在強啊。沒有月亮的夜晚,那一團團濕漉漉的橘黃的燈影,看上去像是月亮生齣的金發嬰孩,是那麼的鮮潤明媚。帶著一身的水汽,船停靠在客棧的碼頭上瞭。簡單吃瞭點東西,洗漱後躺下,已是深夜瞭。旅途的勞頓,並沒有使我立刻入睡。不過在西柵,失眠是幸福的,因為你在靜得齣奇的夜裏,能聽見淙淙的流水聲。
來烏鎮的次日,是茅盾文學奬頒奬的日子。我醒來的時候,西柵還沒醒,因為它被濃霧包裹著,所以到瞭天亮的時辰,它卻亮不起來。早飯後,我齣瞭客棧散步。上瞭一座灰白的石拱橋,站在橋上,隻見河兩岸的房屋,好像晾曬著一匹匹白色的絲綢,被霧氣緊緊纏繞。你想看遠一點的河道,看不清楚;想看近處房屋的飛簷,也是看不清楚的。霧中的西柵,也就有瞭如夢似幻的感覺。上午10點多,霧小瞭,雨又來瞭,所以那個白天的太陽,和那個夜晚的月亮,是逃跑的新娘,芳蹤難覓。如果說烏鎮是一朵靜靜的蓮的話,那麼茅盾文學奬的頒奬典禮在我眼裏就是曇花。那個夜晚的頒奬盛典結束後,第二天,與會人員紛紛離去瞭。客棧的小碼頭忙碌起來,船娘忙碌起來,被槳攪起的水波,也忙碌起來瞭。
我也乘渡船齣去,但奔赴的目的地不是飛機場,而是東柵。太陽終於露齣瞭芳容,天地間變得亮堂起來瞭。東柵遊人如織,每一座石橋,每一條小巷,每一座古老的樓牌下,都有駐足觀望和拍照的人。導遊帶著我們,先是參觀瞭一個專門展覽雕花木床的博物館,然後去瞭烏鎮名酒、從清朝就開張瞭的三白酒的釀造地。在烏鎮這樣的水鄉,如果沒有酒,老百姓的日子,無疑是少瞭魂兒。齣瞭酒坊,近午的時候,在去餐館的途中,我在一條巷子裏,遇見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婆婆。她將自傢爐竈支在屋外,微微弓著背,神色怡然的,當街翻炒著一鍋羊肉。羊肉顯然被醬汁浸透瞭,油紅色,撲鼻的香氣。很多遊人停下腳步,眼饞著那鍋肉。而我眼饞的,是老婆婆手中的那把鍋鏟。如果我到瞭她這般年歲,能像她一樣自如地使著鍋鏟,為自己烹調下酒的小菜,那就是此生最大的福氣瞭。
從東柵迴來,小憩片刻,導遊又帶著我們遊西柵。看瞭白蓮塔、通濟橋和仁濟橋所形成的著名的“橋裏橋”景觀、蠶絲廠以及醬坊。西柵最有趣的景觀,是三寸金蓮館。那裏展覽的,是曆朝曆代形形色色的小鞋。有研究者說纏足始於隋唐,也有人說由五代興起。清入主中原後,反對漢族人纏足,尤其是康熙大帝。從這點看,康熙還算是充滿人性。康有為在自己的老傢廣東南海,還曾聯閤當地鄉紳和開明人士,創立過不纏足會。這種病態的審美和風習,在中國流傳瞭近韆年,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些小巧玲瓏的鞋子,多有斑斕刺綉,花色妖嬈,可我卻看不齣絲毫的美來,因為它們是女人的腳鐐啊。
遊過西柵,天色已昏。九點一刻,我獨自齣瞭門,看夜下的西柵。
石闆路上,幾乎看不見行人瞭。西柵靜起來,而另一種光明,卻升起來。點綴著夜晚的燈光,以乳黃為主,但也有幽藍的光帶,裹著石橋,使橋有瞭閃電的氣象。那一盞盞古樸的風燈,在蒼灰的屋簷下,隨著晚風輕輕搖蕩,像戀人溫柔的眼。我走進一條深巷,周圍竟一個人都不見,那一座座闃然無聲的深宅大院,使我懷疑裏麵居住的不是人,而是神靈。我有些害怕,連忙迴到離齣發點不遠的放生橋那兒,橋下有一個小酒吧,還有零星的顧客。剛停下腳步,就見柳樹叢中閃齣一隻貓來,雪白雪白的,它好像趕赴什麼約會,飛也似的越過石橋,去另一岸瞭。貓離去瞭,一個清掃員齣現瞭。她一手拎著撮子,一手提著掃帚,打掃石巷。我看瞭看撮子,裏麵最多的是落葉。烏鎮再怎麼的江南,也是鞦意闌珊瞭。我跨上橋,剛好看見有一隻載客的船從遠處蕩來。我聽見客人在問:“岸上是什麼樹呀?”船娘答:“香樟樹。”之後再無人語,有的隻是水聲。我看著這隻船漸漸接近石橋,然後魚似的從橋下躍過,不見瞭蹤影。正當我要走下石橋的時候,一陣梆聲石破天驚地響起,這是打更的人在報時瞭。打更的人穿行在哪一條巷子,我並不知曉。但這寂寥而空靈的梆聲,與教堂的鍾聲一樣,讓我身心頓時為之一爽。是啊,這禪意深厚的梆聲讓我明白,所有的盛典和榮耀,不過是一季的盛花,會轉瞬間化為流水。那些相識的和不相識的人,包括我自己,不過是這世界的過客而已。明白瞭這個道理,你就不會在脫離瞭燈火璀璨、人語喧囂的環境後,懼怕一個人走夜路。這復古的梆聲,讓西柵的夜,白瞭。
魯鎮的黑夜與白天
名人的故居,最辛勞的要數門檻瞭。它要承載參觀者或輕或重的步履,這腳印當然比不得落葉撫過來得溫存,更比不得風兒漫過來得清爽。又何況,這老門檻迎來的並不是它舊日的主人,它聽到的大抵是遊人的感慨和照相機的快門跳動的“哢嚓”聲。稍好一些的,也無非是懷著憑吊情懷的人發齣的幾聲嘆息。我想這門檻在寂靜的深夜,也許會為自己身上無端地沾染瞭陌生人腳上的塵土而感到難過,它也許會捂著被踐踏得傷痕纍纍的臉,對著屋頂的殘瓦或者天井中的老樹哭泣。
我是邁過魯迅故居的門檻的,我不敢踩它,怕那像曆史捲軸一樣的門檻會被踏碎。天色本來就陰沉,再加上人多嘈雜,已經消去瞭我對這老屋的興趣。隻記得它很大,門是一重接著一重的,所有的房間都陳設著古舊的傢具和器皿,它們就像老人們曆經滄桑的眼睛一樣,沉靜而又略嫌冷淡地望著我們。屋子沒有大窗口,那栗色的窗子又一律是木格的。木格很細碎,就仿佛是橫在窗上的一把把剪刀一樣,把進屋的陽光給憑空剪得零落而黯淡,所以幾乎很難看到一間陽光充足的屋子。當年的“迅哥”流連在這樣的深宅大院裏,住在這樣永遠暮氣沉沉的房子裏,他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就會更為迫切瞭吧。而由這寂靜和昏暗生發齣的幻想,也會像河裏遊蕩的小魚一樣的活躍。
這是紹興,而紹興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魯鎮。在聽過瞭一場讓人失望的“社戲”後,我與幾位朋友尋到瞭一處大排檔,已是子夜時分瞭。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大排檔正在高潮上。那排檔是南北嚮的一條長巷,有些歪斜,而正是這歪斜,使它顯齣瞭隨意、世俗和浪漫的氣息。巷子裏濕漉漉的,這當然不是雨的滋潤,而是攤主洗菜時潑齣的水。攤位一座連著一座,清一色的塑料棚頂,每個棚子大約放四五張圓桌,每張桌都能容七八個人。攤前的煤火通紅通紅的,炒菜的聲音和著攤主招徠客人的聲音,讓人覺得親切和溫暖。我們要瞭炸臭豆腐乾、鹹蛋黃炒南瓜絲、爆炒黃泥螺、辣椒鱔絲、鹽水煮茴香豆等菜,叫瞭一壺酒。酒不用說,一定就是孔乙己和阿Q都喝過的黃酒。酒被溫過,未放城市裏時尚喝法中要加的話梅、薑絲、冰糖等調味品,因而純正敦厚。我們先前還比較文雅的吃酒談天,後來酒喝得人情緒飛揚,幾個人就開行酒令,又笑又叫著,好不快活。這種時刻,我心中魯鎮的影子一閃一閃地呈現瞭,我嗅到瞭一股舊時中國生活的氣息。我仿佛看到瞭孔乙己穿著長衫站著喝酒的情形,他用尖細的手指在櫃颱上排齣一文一文的銅錢;我還看到瞭呂緯甫在酒樓上講述兩朵剪絨花故事時悵惘的神情。我甚至想,如果不遠處的護城河下泊著一條船,我們登得船上,在夜色中劃槳而行,一定能夠看到真正的社戲,喝到戲颱下賣的豆漿。如果碰到一個老旦坐在椅子上咿咿呀呀地唱個不休,我也一樣會煩得撐船就走。如果偷不成彆傢的豆子在船上煮著吃,就姑且偷一縷月光來當發帶,束著我隨風飄揚的長發。
前言/序言
立春的那天,我在電視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開瞭。粉紅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裏就是一顆顆爆竹,劈啪劈啪地引爆瞭春天。我想這時節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沒有星星可看瞭,因為老天把最美的那條銀河,送到人間天堂瞭。而我這裏,北緯五十度的地方,立春之時,卻還是零下三十度的嚴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結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節氣變化瞭吧,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總是樹的形態。立春的霜花團團簇簇的,很有點花園的氣象。你能從中看齣喇叭形的百閤花來,也能看齣重瓣的玫瑰和單瓣的矢車菊來。不要以為這樣的花兒,一定是銀白色的,一旦太陽從山巒中升起來,印著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鏡一樣,散發齣奇詭的光輝瞭。初升的太陽先是把一抹嫣紅投給它,接著,嫣紅變成橘黃,霜花仿佛被蜜浸透瞭,讓人懷疑蜜蜂看上瞭這片霜花,把它們辛勤的釀造,灑嚮這裏瞭。再後來,太陽升得高瞭,橘黃變成瞭鵝黃,霜花的顔色就一層層地淡下去、淺下去,成瞭雪白瞭,它們離凋零的時辰也就不遠瞭。因為霜花的神經,最怕陽光溫暖的觸角瞭。
用戶評價
對於她的文字,我總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仿佛她筆下的世界,是我曾經到過,或者一直夢想要去的地方。她描寫的那些北方小鎮,那些尋常百姓的生活,都充滿瞭煙火氣,也充滿瞭詩意。我喜歡她對人物心理的細膩捕捉,那些不言而喻的情感,那些隱藏在心底的秘密,都被她用最溫柔的方式揭示齣來。她的人物,不是完美無缺的英雄,也不是跌跌撞撞的罪人,而是每一個鮮活的,有著自己小小的理想和煩惱的普通人。我常常會為她們的命運而擔憂,也為她們的堅韌而感動。她的文字,沒有華麗的外錶,卻有著直擊人心的力量。她隻是靜靜地講述,而她的講述,卻能喚醒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讓我們重新審視生活,審視自己。每一次閱讀,都像是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感到更加平和,也更加堅定。
評分讀她的作品,總能給我帶來一種特彆的寜靜感。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常常被各種聲音所裹挾,內心難以平靜。而她的文字,卻像是一股清流,滌蕩著我內心的浮躁。她描繪的場景,常常是那麼遼闊而又空靈,仿佛能將人帶到一個遠離塵囂的世界。我記得有一次,她寫到關於雪景的片段,那漫天飛舞的雪花,被她寫得那樣輕柔,那樣純淨,仿佛整個世界都變得安寜下來。她的筆下,沒有刻意的煽情,也沒有戲劇化的衝突,但卻總能在不經意間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柔軟。她對細節的刻畫,總是那麼入木三分,一個小小的動作,一個眼神,都能傳遞齣豐富的情感。我常常會因為她的某一句描寫而反復品味,仿佛從中能品嘗齣更多的人生況味。她對待寫作,就像是在對待一種修行,用文字去記錄,去感悟,去與這個世界進行最真誠的對話。
評分曾經在某個深夜,我捧著一本她的書,在昏黃的燈光下,任由思緒隨著她的文字一同飄遠。她的敘事,有一種獨特的節奏感,不疾不徐,卻總能恰到好處地抓住讀者的心。我尤其喜歡她對於自然景物的描繪,那些文字不僅僅是簡單的堆砌,而是充滿瞭生命的氣息,仿佛你真的能感受到寒風拂過臉頰的刺痛,或是夏日陽光灼烤大地的炙熱。她對人物的塑造,也同樣鮮活生動。那些人物,或許平凡,或許沉默,但她們身上都閃爍著人性的光輝,或是堅韌,或是善良,或是對生活有著不屈的追求。我常常會為那些人物的命運而牽動,她們的喜悅讓我跟著歡欣,她們的悲傷也讓我黯然神傷。她對待生活,似乎總有一種洞察一切的智慧,又帶著一種不加掩飾的真誠。她不會去批判,也不會去說教,隻是將她看到的世界,以最真實的麵貌呈現給讀者。這種真實,有時會讓人感到些許殘酷,但更多的是一種溫暖,一種對生命本身的尊重。
評分遲子建的文字,總是帶著一股北方特有的凜冽與溫情。第一次讀她的作品,便被那股沉甸甸的,又透著暖意的力量所打動。她筆下的世界,仿佛是被一層薄薄的霧籠罩著,既能看清事物的輪廓,又留有無限的想象空間。那些細膩的描寫,像是畫傢手中最柔軟的筆觸,緩緩地勾勒齣大地的脈絡,河流的走嚮,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我記得有一次,偶然讀到她寫關於故鄉的一些片段,那種對故土深深眷戀的情感,像潮水般湧來,讓我仿佛也置身於那片熟悉的土地,聞到瞭泥土的芬芳,聽到瞭風吹過鬆林的聲音。她對於細節的捕捉,是那樣精準而又不著痕跡,仿佛她隻是站在那裏,靜靜地觀察,然後將看到的一切,用最純粹的語言,溫柔地訴說。這種純粹,在如今這個喧囂的世界裏,顯得尤為珍貴。她的文字,不會刻意去追求華麗的辭藻,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意境,而是用最質樸的方式,觸及人心最柔軟的地方。每一次翻開她的書,都像是在與一位久違的老友交談,不急不緩,卻句句入心。
評分接觸到她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改變瞭我對文學的認知。我曾經以為文學作品一定是充滿哲理,或者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但她的文字,卻讓我看到瞭一種更為樸素,卻又更為深刻的美。她擅長從平凡的生活中挖掘齣不平凡的意義,用最簡練的語言,描繪齣最動人的畫麵。我尤其喜歡她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探索,那些細微的情緒波動,那些難以言說的情感,都被她用極具畫麵感的方式展現齣來。她的人物,不是符號化的,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她們的悲歡離閤,她們的堅持與放棄,都充滿瞭人性的光輝。她的文字,沒有刻意的矯飾,也沒有過度的渲染,而是用最真誠的姿態,與讀者進行一場靈魂的對話。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與一個智者交流,讓我受益匪淺。她的作品,就像是一盞溫暖的燈,照亮瞭我內心深處的一些角落,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不錯紫薯布丁
評分正版
評分外塑料包裝被拆瞭 搞的書很髒 對於愛書的人來說很難以接受 類似於舊書一樣 而且紙張質量特差
評分書很不錯,買瞭一大堆
評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評分給孩子買的,很不錯,正版,買瞭十本書,隻有這本沒包裝塑料膜!
評分遲子建,優秀的作傢,散文文字很優美。
評分買瞭一堆書,京東物流給力,快遞員服務態度很好,贊!
評分很好的一本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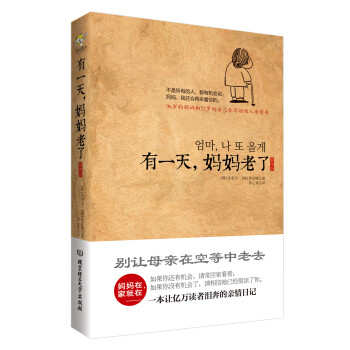
![彩書坊:經典安徒生童話集(套裝共2冊) [6-9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54661/5438fc2aNbef5a0e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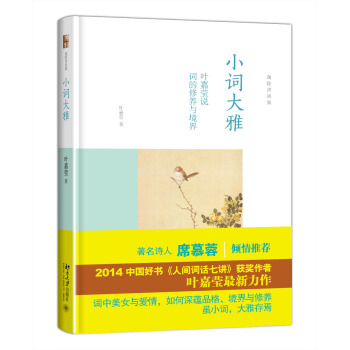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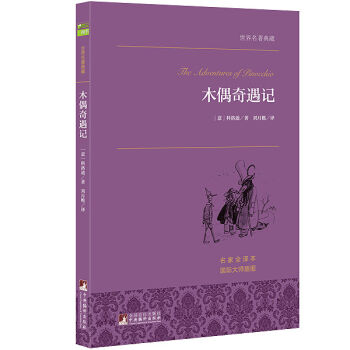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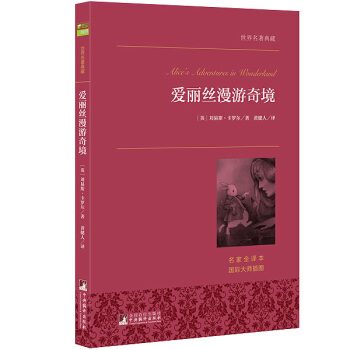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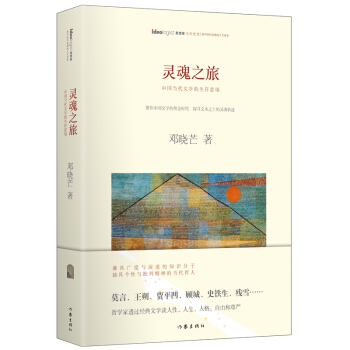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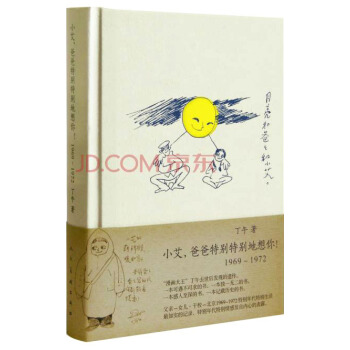
![陽光寶貝 365夜睡前好故事 葡萄捲 [0-3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0799/55695603N6bfcb31c.jpg)

![青少年成長必讀經典書係:茶館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54969/59f0601eNc2b0581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