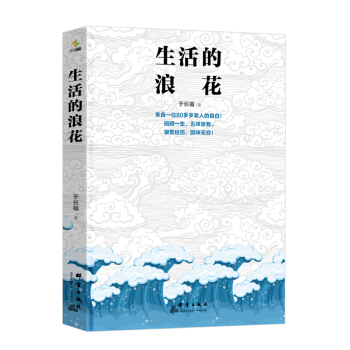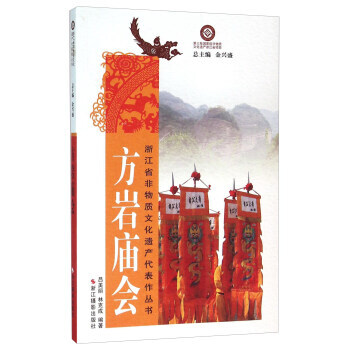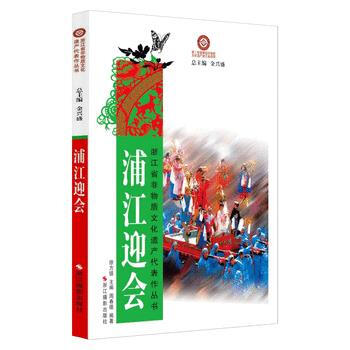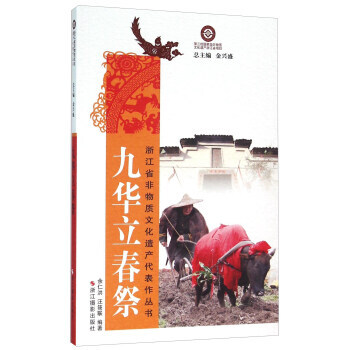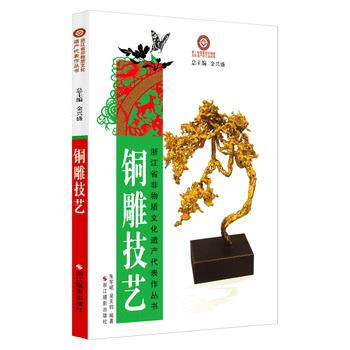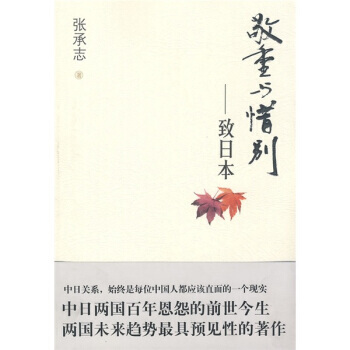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书名: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定价:29.80元
售价:20.3元,便宜9.5元,折扣68
作者:张承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01-01
ISBN:9787505725126
字数:
页码:28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40kg
编辑推荐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是中日关系,始终是每位中国人都应该直面的一个现实、中日两国百年恩怨的前世今生、两国未来趋势具预见性的著作。
张承志数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
内容提要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是作家张承志总结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虽然没有面面俱到,但若干章节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尽管时而披沥胸臆,但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不同于往昔的名人旅日谭,也不同于当今的学者论文集,虽是一册散文,但力求处处考据。此书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把中国同时作为剖析和批判的对象,大声疾呼着历史的大义、国家的和平,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
目录
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
第二章 三笠公园
第三章 长崎笔记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
第五章 四十七士
第六章 解说·信康
第七章 文学的“惜别”
第八章 亚细亚的“主义”
第九章 束尾:红叶做纸
跋
作者介绍
张承志,1948年秋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下乡,放牧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以来,多次获得全国短篇、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1983年、1991年两次长期居留日本,任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1993年任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助教授。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八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谁是胜者》、《聋子的耳朵》、《鲜花的废墟》等。其中在日本出版的有:《モンゴル大草原遊牧誌》、《黒駿馬》、《紅衛兵の時代》、《殉教な中国イスラーム》、《回教から見た中国》、《北方の河》、《鞍と筆》。
文摘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u,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ahus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己!……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霍洛特(horo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序言
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
第二章 三笠公园
第三章 长崎笔记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
第五章 四十七士
第六章 解说·信康
第七章 文学的“惜别”
第八章 亚细亚的“主义”
第九章 束尾:红叶做纸
跋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感受,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宝藏室,里面陈列着无数珍贵的文物,每一件都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作者的笔触,如同考古学家的细心挖掘,小心翼翼地拂去岁月的尘埃,展露出事物的真实面貌。我在这里读到的,不是简单的历史陈述,而是一种情感的重现,一种心境的还原。那种“敬重”,是一种超越简单好恶的评价,是对一种复杂存在,甚至是曾经的对手,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理解与尊重,这种尊重,源于对历史进程的认知,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洞察。而“惜别”,则饱含着一种对失去的珍视,对曾经美好的,即使已经远去的,也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价值的悲悯情怀。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告别,而是在告别中,依然能够保留住那些有价值的、值得被记住的东西。书中没有激昂的陈词滥调,没有廉价的煽情,只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深刻,一种娓娓道来的力量,让我沉浸其中,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感悟。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带着一种沉静而深邃的色彩,一种淡淡的忧伤,但又不失尊严。当我翻开它时,我立刻被作者那细腻入微的笔触所吸引,仿佛作者并非在叙述,而是在轻声诉说,将那些遥远而又触动心弦的过往,一点点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文字中流淌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对过往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叹息。那种“敬重”二字,似乎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体、某个时期,更是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致敬。而“惜别”,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即将逝去的,无论好坏,都曾存在过的痕迹的珍视与告别?书中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没有大张旗鼓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内敛的、深沉的思考。我仿佛看到一位饱经风霜的旅人,在旅途的终点回首来时路,眼中既有对过往的眷恋,也有对前路的平静。这种叙事方式,让我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每一个词句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去感受作者内心的波澜。我期待着,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一些关于理解、关于共情、关于放下与前行的答案,即使这些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也已足够引人入胜。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但又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震撼,而是一种如鲠在喉、欲语还休的沉重。作者的视角是如此独特,他仿佛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俯瞰着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偏袒,没有憎恨,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观察。我能感受到他试图去理解那些“日本”所代表的,不单单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某种精神层面的存在。字里行间充斥着对过往的审视,那种“敬重”并非盲目的崇拜,而是对其中某种值得铭记的价值的肯定,也许是某种坚韧,也许是某种匠心,也许是某种在逆境中依然存在的风骨。而“惜别”,则更像是一种对必然的接受,对历史洪流中不可避免的失去的释然。这种告别,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带着一丝不舍,一种对曾经拥有的、曾经塑造了我们一部分的存在的温情回望。这本书的语言,时而如同一首婉转的诗,时而又如同一篇深沉的哲学散文,让我不断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游走。它没有给我明确的答案,却激发了我更多的问题,关于记忆,关于历史的重量,关于如何与过去达成和解。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力,它不像那些直白的叙述,而是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每一笔都充满了意境。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在月光下,对着远方的山峦,轻声诉说着他对过往的思索。“敬重”二字,在我看来,是对一种强大力量的承认,即使这种力量曾经是挑战,是对手,但在作者的笔下,却能看到其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闪光点,这是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宏观视角。而“惜别”,则是一种对时间和变化的感慨,是对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却又不可避免地要消逝的,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与惋惜。这种告别,不带怨恨,不带愤怒,只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的理解。作者的叙事,时而如同涓涓细流,时而又如惊涛拍岸,变化莫测,却又始终扣人心弦。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一种与过去对话的方式,一种理解与被理解的桥梁,它让我重新审视了一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概念。
评分翻开这本书,就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遥远时空的大门,作者以一种诗意的语言,带我进入了一个充满复杂情感的世界。我感受到的,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一种对人类情感深处的回响。他所表达的“敬重”,是一种对某种难以言喻的特质的欣赏,也许是某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许是某种独特的审美,这些特质,即使在对抗中,也依然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值得被看见和铭记。而“惜别”,则是一种对时光流逝的无声叹息,对那些曾经鲜活的存在,即使是短暂的,也带着一种深沉的眷恋。这种告别,没有哀嚎,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对过往的珍视。作者的笔触,时而如同一位老朋友,娓娓道来,时而又如同一位哲人,引人深思。它没有给我标准化的答案,却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一个让我能够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人类情感的独特视角,这种体验,是如此的深刻而又令人难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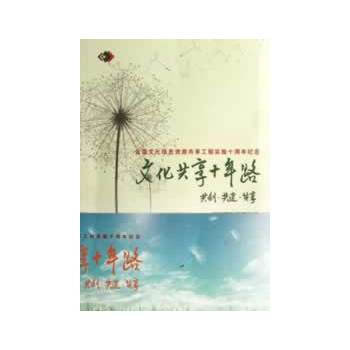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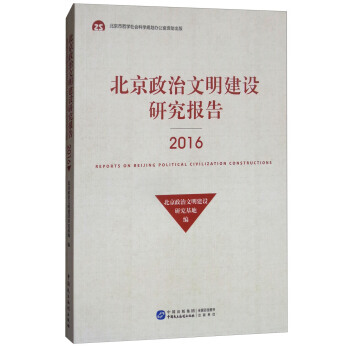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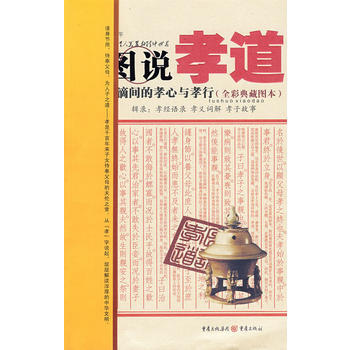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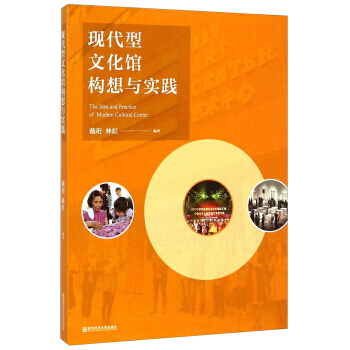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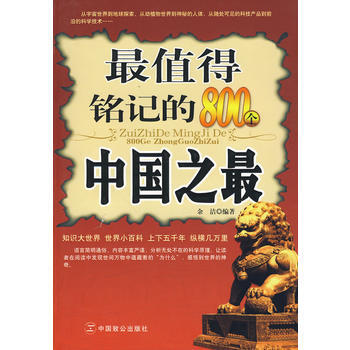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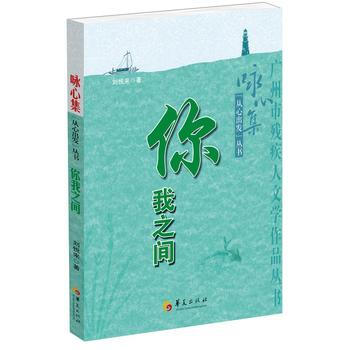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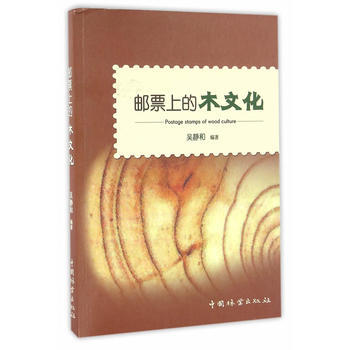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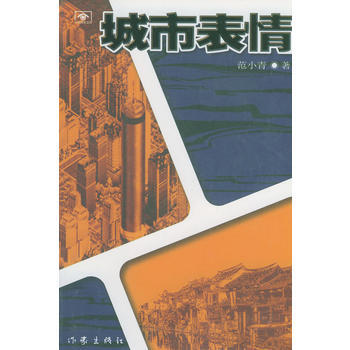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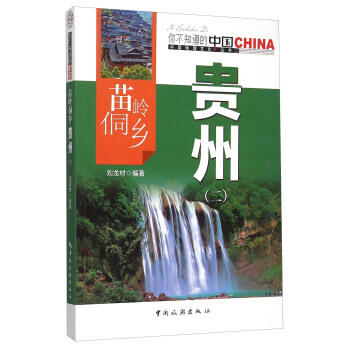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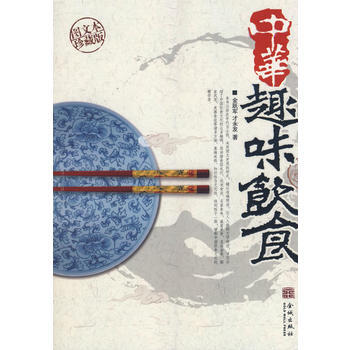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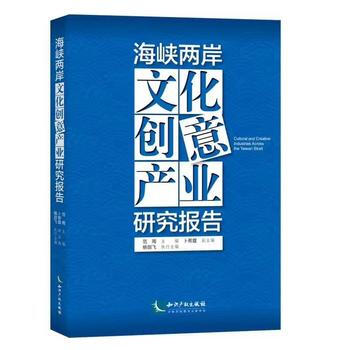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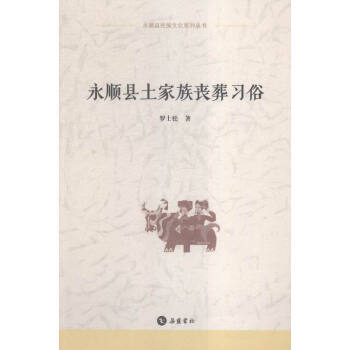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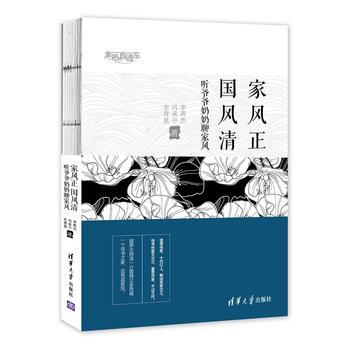
![造物记:人与树的故事(《泰晤士报》2015年度佳图书) [英] 罗伯特佩恩(Rob Pe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29692888606/5b32d904N54ad9b0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