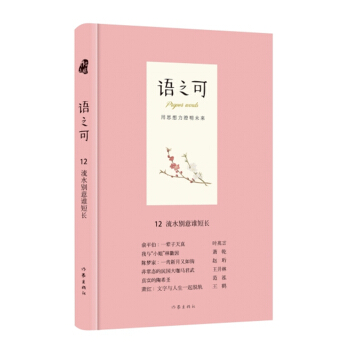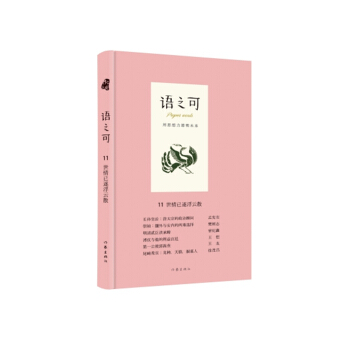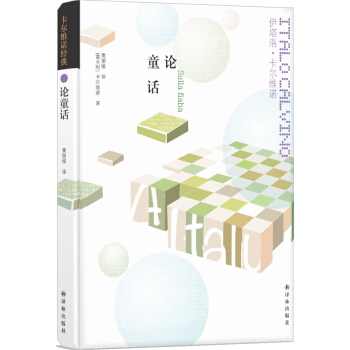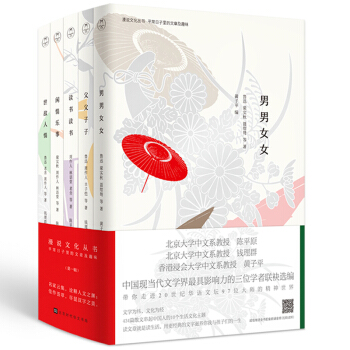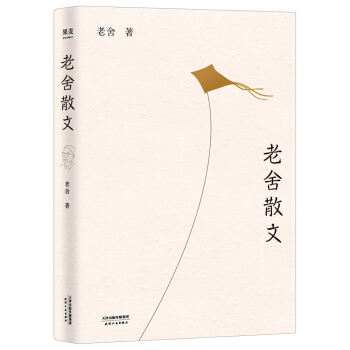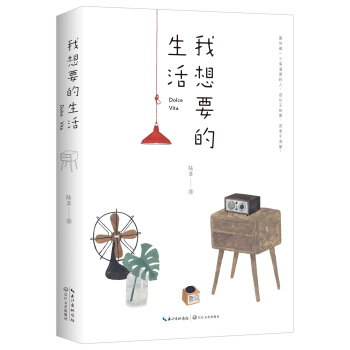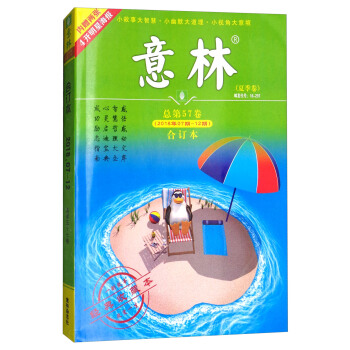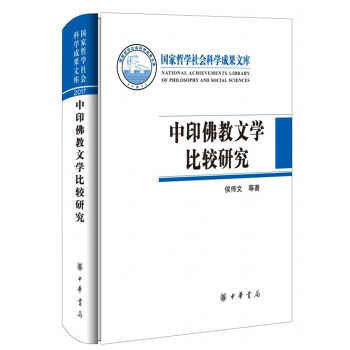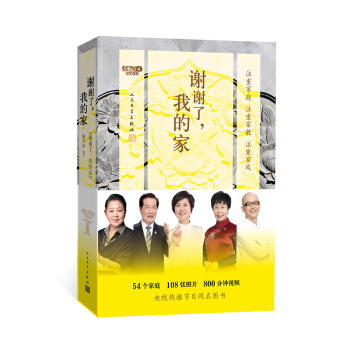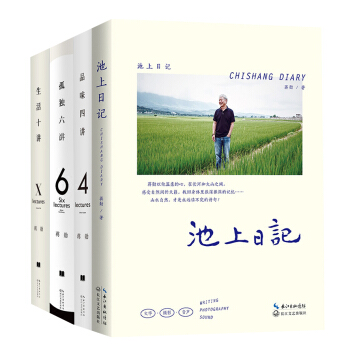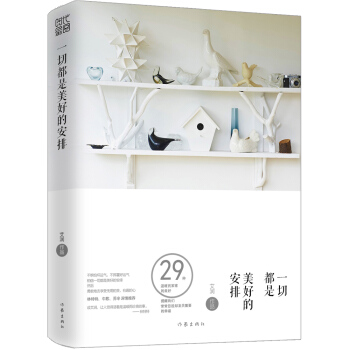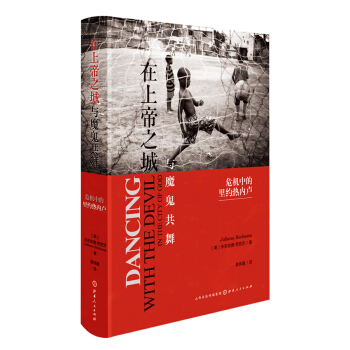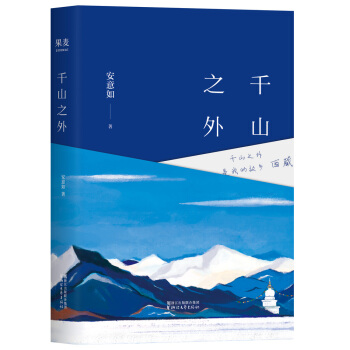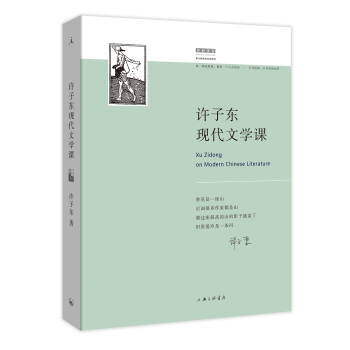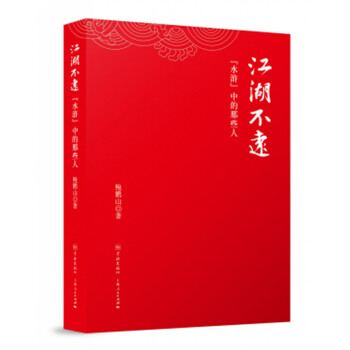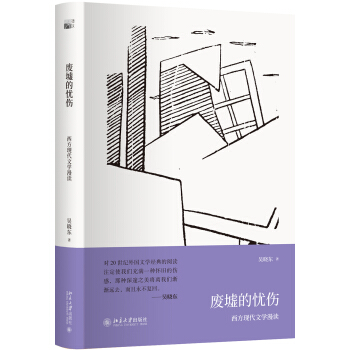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当下著名文学批评家吴晓东老师评西方现代文学经典,带领普通读者阅读经典、解读经典。
晓东老师倡导阅读经典,他认为在初涉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阅读一部真正的经典,会对你的一生都产生重大影响。
了解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世界,认识20世纪人类的心灵境况,读20世纪的现代经典是可行之途径。
本书囊括了诸多读者耳熟能详和喜爱的外国文学文本进行鉴赏和细读,帮助读者领略这些图书的深邃和精妙所在。
内容简介
了解20世纪人类的生存世界,认识20世纪人类的心灵境况,读20世纪的现代经典是可行之途径。《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作者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一些20世纪具代表性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和评论,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尝试探究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触摸作家深邃的心灵世界,进而透视20世纪复杂的社会历史图景。本书文字优雅、可读性强,可作普及类读物。作者简介
吴晓东,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1994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担任共同研究者,1999—2000年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讲学,2003—2005年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2016年被聘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入选北京新世纪社会科学“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年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等。
目录
目 录“阅读的德性”(代序)III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1
记忆的神话 15
意识流小说的集大成 26
情境化的小说 35
“没有人传达过的经验” 47
一个关于自我欺瞒的人性故事 54
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旅 67
对人的处境的探索 90
荒诞世界中的反抗哲学 99
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博尔赫斯 106
现代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 117
新小说派:呈现“物”的本身 124
对不存在事物的想象力 139
20世纪最后的传奇 146
《日瓦戈医生》与俄罗斯精神传统 159
始于希腊的东方精神之旅 166
魔幻与现实 169
“绞架下的幽默” 180
对存在的勘探 196
昆德拉的小说学:作为“存在编码”的关键词 218
科勒律治之花 224
废墟的忧伤 232
疾病的文学意义 239
孤独的人才能发现风景 250
风景观的浪漫主义传统 256
司各特的目光 262
关于中国的异托邦想象 266
“记忆的暗杀者” 271
帝国的历史魅影 277
什么是“黑暗的启示” 288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 296
与文学经典对话 315
附录一 我们曾被外国文学经典哺育 324
附录二 个人的、时代的与人类的 337
精彩书摘
卡夫卡:20 世纪的预言家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奥登
时代的先知
在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
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奠基者。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卡夫卡的创作就引起了西方文坛的关注,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成为 20 世纪的作家所能创作出的最振聋发聩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持续的“卡夫卡热”。美国女作家欧茨称“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 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卡夫卡也 被视为 20 世纪现代主义的第一人,欧美各种权威书评杂志在评选
20 世纪现代主义大师时,卡夫卡都无一例外地排在第一位。英国大诗人奥登曾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1
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 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可以说是最 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的 作家,也是最早传达出 20 世纪人类精神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是 20 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卡夫卡的创作个性和文学世界可以在他成长过程中找到背景。从小到大的压抑的环境造就了他内敛、封闭、羞怯甚至懦弱的性 格。内心敏感,容易受到伤害,对外部世界总是持有一种戒心。他在去世前的一两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地洞》,小说的奇特的叙 事者“我”是个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地洞的小动物,但这个小动物却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充满了隐忧、警惕和恐惧,“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这个地洞的处境在某种意义 上说也是现代人的处境的象征性写照,意味着生存在世界中,每 个人都可能在劫难逃,它的寓意是深刻的。而从卡夫卡的传记生 平的角度看,这个小动物的地洞中的生活也可以看成是作者的一 种自我确认的形式,借此,卡夫卡也揭示了一种作家生存的特有 的方式,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的生活,回到一种经验的生活和 想象的生活。卡夫卡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 在地窖一样的处境中沉思冥想的内心写作方式。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 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 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 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
2 废墟的忧伤
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这是一种与喧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生活构成了巨大反差的内在生活,衡量它的尺度不是生活经历的广度,而是内在体验和思索的深度。
卡夫卡正是以自己的深刻体验和思索,洞察着 20 世纪人类所
正在塑造的文明,对 20 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
的预见力。写于 1914 年的小说《在流放地》描述了一名军官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参与制造了一部其构造复杂精妙的处决人的机器, 并得意洋洋地向一位旅游探险家展示他的行刑工具。一个勤务兵 仅仅因为冒犯了上司,就要被他投入这部机器受死,死前要经受 整整十二小时的酷刑。但是在勤务兵身上的表演并不成功,于是 读者读到了 20 世纪现代小说中最具有反讽意味的一幕:那个制造了这部机器的行刑军官最后竟自己躺在处决机器上,轧死了自己。 机器的发明者最终与杀人机器浑然一体,成为机器的殉葬品,从 而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它是关 于使人异化与机械化的现代统治的一个寓言。
卡夫卡的另一篇代表作《变形记》写的是职业为一名旅行推销 员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3
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
格里高尔·萨姆沙最初的反应尚不是对自己变成甲虫这一残 酷现实感到惊恐—仿佛变成大甲虫是个自然不过的事—而是担心老板会炒他的鱿鱼。当然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失掉了工作,并 成为一家人的累赘,父亲甚至把一个苹果砸进他的背部的壳中, 并一直深陷在里面。最终,连起初同情他的妹妹也不堪忍受他作 为甲虫的存在。小说的结局是格里高尔在家人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中死去。
《变形记》写的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社会现实是一个使人异化的存在,格里高尔为了生存而整日奔波,却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归宿感。社会甚至家庭、人伦都使他感到陌生,最终使他成为异己的存在物,被社会与家庭抛弃。这就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可能面临的生存处境的变形化的写照。卡夫卡以一个小说家的卓越而超凡的想象力为人类的境况作出了一种寓言式的呈示。现代人面临的正是自我的丧失和变异,即使在自己最亲近的亲人中间也找不到同情、理解和关爱,人与他的处境已经格格不入,人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同时却对自己这种异化无能为力。而这一切,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变形记》因此也状写了人的某种可能性。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就是卡夫卡对人的可能的一种悬想。在现实中人当然是不会变成甲虫的,但是,变成大甲虫却是人的存在的某种终极可能性的象征。它是我们人人都有可能面对的最终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写的是人的生
4 废墟的忧伤
存现状。因而,当格里高尔本人和他的家人发现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的时候,都丝毫没有怀疑这一变形在逻辑上的荒诞,而是都把它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卡夫卡的写法也完全遵循了写实的原则,仿佛他写的就是他在生活中所亲眼目睹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读者也完全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的写真而接受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宿命。
卡夫卡的小说都有一种预言性。譬如德国作家黑塞就说:“我相信卡夫卡永远属于这样的灵魂:它们创造性地表达了对巨大变 革的预感,即使充满了痛苦。”而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 吉斯则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表达了对世界的梦魇体验,对这些作品,
“人们无法作直截了当的阐释。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是平淡的,累赘的,但气氛总是那么像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作家而已”,“而随着我们父老一辈所熟悉的社会的解体,那些使人人感到孤独的庞大的综合城市代之而起以后,卡夫卡描写人的本质的那种孤立的主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是一个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的先知。
对可能性世界的拟想
文学史家们一般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一种表现主义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技巧,他是表现主义在小说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表现主义”的概念最初是运用在绘画评论中。1901 年,法国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5
画家朱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在巴黎“独立沙龙”展出了八幅作 品,被称为“表现主义”绘画。1911 年 4 月在德国柏林第二十二届画展的前言中,表现主义一词又再度出现,用来描述一群法国年青画家(其中包括毕加索)的绘画特色。而在文学批评界,表现主 义一词则在 1911 年 7 月正式出现在德国,并在此后的几年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表现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流派,它在绘画、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中均有不同的表现,“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即不满社会现状,要求改革,要求‘革 命’。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要求进而表现事 物的内在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描绘而揭 示人的灵魂;要求不再停留在对暂时现象和偶然现象的记叙而展 示其永恒的品质。”因而,表现主义的出现,为作家们进一步提供 了一条通向内心的文学道路。作家们越来越关注对人性和心理世 界的发掘,关注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揭示。而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 则强调主观想象,强调对世界的虚拟和变形的夸张与抽象,强调 幻象在文学想象力中的作用。正如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埃德施米特所指出:“存在是一种巨大的幻象……需要对艺术世界进行确确实实的再塑造。这就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图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整个用武之地就在幻象之中。他并不看,他观察; 他不描写,他经历;他不再现,他塑造;他不拾取,他去探寻。于 是不再有工厂、房舍、疾病、妓女、呻吟和饥饿这一连串的事实, 有的只是它们的幻象。”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也濡染了表现主义的艺术特征。这突出地表现在卡夫卡同样是个营造幻象的艺术大师。卡夫卡的文学世界
6 废墟的忧伤
中就充满了这种再造现实的幻象。《变形记》中人变成大甲虫的虚 拟现实,《地洞》所描绘的洞穴的生存世界,《骑桶者》结尾所写的 一个人骑着空空的煤桶“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的情景…… 描绘的都是这种幻象世界。正如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所说:“他是一个梦幻者,他起草完成的作品都带着梦的性质,它们模仿 梦—生活奇妙的影子戏—的不合逻辑、惴惴不安的愚蠢,叫 人好笑。”但是笑过之余,你会惊叹卡夫卡的幻象的世界看似不合 逻辑,但却并非虚妄,它恰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更本真的图景, 是人的境遇的更深刻反映。
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猎人格拉胡斯》中,写了这样一段死后 再生的猎人格拉胡斯与一位市长的对话:
“难道天国没有您的份儿么?”市长皱着眉头问道。
“我,”猎人回答,“我总是处于通向天国的阶梯上。我在那无限漫长的露天台阶上徘徊,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在右,时而在左,一直处于运动之中。我由一个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您别笑!”
“我没有笑,”市长辩解说。
“这就好,”猎人说,“我一直在运动着。每当我使出最大的劲来眼看快爬到顶点,天国的大门已向我闪闪发光时,我又在我那破旧的船上苏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旧在世上某一条荒凉的河流上,发现自己那一次死去压根儿是一个可笑的错误。”
徘徊在通向天国的阶梯上的格拉胡斯可以看成是卡夫卡本人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7
的化身,卡夫卡也正是一个出入于现实世界和幻象世界之间的小 说家,他的小说中真实与幻象纠缠交错在一起,是无法分割的统 一世界。单纯从现实的角度或单纯从幻象的角度来评价卡夫卡, 都没有捕捉住卡夫卡的精髓。他所擅长的是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手 法写神秘的幻象。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就认为卡 夫卡的作品有相反相成的两个世界:一是对“梦幻世界‘自然主义式’的再现(通过精致入微的画面使之可信),二是大胆地向神秘主义的转换”。卡夫卡的本领在于他的小说图像在总体上呈现的是 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一个想象的梦幻的世界,一个在现实中并不 存在的荒诞的世界,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世界;然而,他的 细节描写又是极其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有着非常精细入 微的描写,小说场景的处理也是极其生活化。比如他的《在流放 地》,关于杀人的行刑机器以及行刑的军官最后对自己执行死刑的 构思都具有荒诞色彩,但是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卡夫卡又充分 表现出细节描写的逼真性,尤其对行刑机器以及行刑过程的描摹, 更是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而另一方面,这种细节描写与传统现 实主义的描写又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 现实主义小说中,细节的存在是为了更形象逼真地再现社会生活, 烘托人物形象,凸现典型环境;而在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中, 真实细腻的细节最终是为了反衬整体生存处境的荒诞和神秘。而 最终卡夫卡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陌生的世界最 终隐喻了现代人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陌生感,隐喻了现代人流放 在自己的家园中的宿命。
卡夫卡特别擅长的是对一个可能性的世界的拟想。《在流放地》中行刑的军官最后对自己执行死刑就是一种悬想性的境况,是未
8 废墟的忧伤
必发生却可能发生的情境。这个情境与变成甲虫的艺术想象一样, 都是通过对一种可能发生的现象的拟想来传达的。卡夫卡小说的 表现主义的想象力也正表现在处理拟想性的可能世界的能力,并 往往借助于荒诞、变形、陌生化、抽象化等艺术手段来实现。譬 如其中变形的手段就是通过打破生活的固有形态,对现实生活中 的事物加以夸张与扭曲的方式来凸现生活以及人的存在本质的一 种艺术手法。它既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家常用的技巧,同时在卡 夫卡那里,又是“变形”化地对现代人的意识和存在的深层本质的 超前反映。就像卡夫卡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一次,卡夫卡和雅赫 诺参观一个法国画家的画展,当雅赫诺说到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 扭曲者的时候,卡夫卡说:
我不这么认为。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 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 走在前面。
对于卡夫卡和他的时代的关系而言,他正是这样一个走在前面的,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的艺术的先知。
作为预言书的《城堡》
《城堡》虽成书于 20 世纪初叶,但它是属于整个 20 世纪的书。
今天看来,它也分明属于 21 世纪。它是人类阅读史上少有的历久弥新的一部书。每次重新翻开它,都会感到有令人无法捉摸的新的意蕴扑面而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预言书是毫不为过的。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9
发表于 1926 年的《城堡》写成于 1922 年,是卡夫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K,小说开头写 K 在一个遍地积雪的深夜来到一个城堡外的村庄,准备进入这座城堡。K 自称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受城堡的聘请来丈量土地。但是城堡并不承认聘请过土地测量员,因此 K 无权在村庄居住,更不能进入城堡。于是 K 为进入城堡而开始了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
K 首先去找村长,村长告诉他聘请 K 是城堡的一次失误的结果。多年前城堡的 A 部门有过一个议案,要为它所管辖的这座村庄请一个土地测量员,议案发给了村长,村长写了封答复信,称并不 需要土地测量员,但是这封信并没有送回 A 部门,而是阴错阳差地送到了 B 部门。同时也不排除这封信在中途哪个环节上丢失或者压在一大堆文件底下的可能性。结果就是 K 被招聘来到了城堡, 而城堡则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于是 K 成为了城堡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城堡当局一直拒绝他的任何要求,连城堡管辖的村庄、村民 以及村庄中的小学校、客栈都与 K 为敌,结果是 K 最终也没能进入城堡。小说没有写完,据卡夫卡的生前好友,《城堡》一书的编者马克斯·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附注中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 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 行斗争,斗争至筋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 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 K 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 但是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
这是一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相径庭的作品,以往用来分析传统小说的角度—譬如故事性、戏剧冲突、人物性格、典型环境、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等等—在这里都显得
10 废墟的忧伤
失去了效用。这是一部从整体上看像一个迷宫的小说,卡夫卡营 造的是一个具有荒诞色彩的情境。理解这部小说的焦点在于,为 什么 K 千方百计地试图进入城堡?城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它有着什么样的象征性内涵?小说的主题又是什么?在卡夫卡的 研究史上,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最终的明确答案的,《城堡》的魅力 也恰恰在此。而这一切都因为小说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荒诞的处境。正像一位苏联学者扎东斯基所说:“正是渗透在卡夫卡的每一行作品里的这种荒诞色彩—这种预先就排除了弄懂书中事件的任何潜在可能的荒诞色彩,才是卡夫卡把生活非现实化的基本手段。一切的一切—物件啦,谈话啦,房屋啦,人啦,思想啦,—全都像沙子一样,会从手指缝里漏掉,而最后剩下来的就只是对 于不可索解的、荒诞无稽的生活的恐惧情绪。”
“城堡”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小说一开头就引入了对“城堡”的描写:
K 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 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光亮也看不见。K 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 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卡夫卡对城堡的描写策略是想把它塑造成既真实存在又虚无 缥缈的意象,一个迷宫般的存在。因此,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一 种近乎梦幻般的氛围。这种氛围提示了小说的总体基调,此后, 梦魇般的经历就一直伴随着 K。尤其当 K 第二天想进入城堡的时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11
候,卡夫卡更是呈现了一个鬼打墙般的存在:城堡看上去近在眼前,但是却没有路通向它,“他走的这条村子的大街根本通不到城堡的山冈,它只是向着城堡的山冈,接着仿佛经过匠心设计似的, 便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 步没有靠近它”。这是一段具有隐喻和象征色彩的文字,提示着城 堡的无法企及,从而也无法被人们认知。卡夫卡正是想把城堡塑 造成一个难以名状的存在物,它的内涵因而是不明确的,甚至是 抽象的,就像一位卡夫卡研究者所说的那样:
卡夫卡的世界却是由象征符号组成的,那是一些启发性的象征,然而它们无法带我们找到结论,就像一把十分精致的钥匙,却没有一把锁可供他们来开启。卡夫卡作品的最基本的性质也就在于此,任何想得到结论或解开谜底的企图必将归于徒然。
“城堡”是一个有多重象征意义的主题级的意象,同时也使小说成为一个解释的迷宫。
《城堡》问世以来,关于它的多种多样的解释可以写成几本厚 厚的书。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视野出发,得出 的是不同的结论:从神学立场出发,有研究者认为“城堡”是神和 神的恩典的象征,K 所追求的是最高的和绝对的拯救,也有研究者认为卡夫卡用城堡来比喻“神”,而 K 的种种行径都是对既成秩序的反抗,想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持心理学观点的研究者认为, 城堡客观上并不存在,它是 K 的自我意识的外在折射,是 K 内在真实的外在反映;存在主义的角度则认为,城堡是荒诞世界的一
12 废墟的忧伤
种形式,是现代人的危机,K 被任意摆布而不能自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从而代表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社会学的观点则认 为城堡中官僚主义严重,效率极低,城堡里的官员既无能又腐败, 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代表着崩溃前夕的奥匈帝国的官僚主义作风, 同时又是作者对法西斯统治的预感,表现了现代集权统治的症状;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则认为,K 的恐惧来自个人与物化了的外在世界之间的矛盾,小说将个人的恐惧感普遍化,将个人的困境作为 历史和人类的普遍的困境;而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K 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是深层的不可知的秘密,他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 实证主义研究者则详细考证作者生平,以此说明作品产生的背景, 指出《城堡》中的人物、事件同卡夫卡身处的时代社会、家庭、交往、工作、旅游、疾病、婚事、个性等等有密切的关系[1]。
这证明《城堡》是一部可以有多重解释的作品,这种多重的解释,是由于“城堡”意象的朦胧和神秘所带来的。有论者指出:“卡夫卡的作品的本质在于问题的提出而不在于答案的获得,因此, 对于卡夫卡的作品就得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这些作品能解释吗?” 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城堡》是没有最终的主题和答案的,或 者也可以说,对于它的解释是无止境的,这使小说有着复义性的 特征,有一种未完成性。未完成性也是卡夫卡小说的特征。他的 三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都没有结尾,在表面上看,似乎是 因为卡夫卡缺乏完整的构思,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小说没有写完, 就可以看成是卡夫卡一种自觉的追求。从而未完成性在卡夫卡那
[1] 参见谢莹莹《Kafkaesque —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国外文学》,1996 年,第
1 期,第 44 页。
卡夫卡:20世纪的预言家 13
里成为一种文学模式,昭示了小说的开放性。有研究者说:未完成性是“卡夫卡能够以佯谬的方式借以完善地表达他对现代人之迷惘和危机的认识的唯一形式。”
这种复义性以及未完成性的特征,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城堡》的复杂解释史启示着我们,对于阅读一篇有着丰富而不确定含义的现代主义小说,读者也应该调整自己的阅读心理和态度,从而把对确定性结论的热衷调整为对小说的复杂而不确定的寓意的无穷追索。
前言/序言
“阅读的德性”(代序)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里漫游,看到塞尚画的一幅读报的父亲的肖像画,忽然意识到在短短一个夏日午后所浏览的从 13 世
纪到 20 世纪初叶各个年代的绘画中,大约有几十幅都表现了阅读
场景,似乎可以组成一个关于“阅读”的主题系列。而 19 世纪的
绘画在其中占了相当比例,于是想到不止一个史家把 19 世纪看成是西方人阅读的黄金时代。一大家子人在饭后围着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听有文化的长者或正在上学的少年读一本小说来打发长夜,是漫长的 19 世纪常见的场景。
这种 19 世纪式的温馨的阅读情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怀想。
因此读到张辉的《如是我读》(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10 月版),产生的近乎一种怀旧般的亲切感。该书的腰封形容《如是我读》是“一组关于书与人的赋格曲”,“关乎读,关乎书,关乎人”,“如是我闻,如是我读,如是我想”。而该书在自序中直接触及的就是“阅读的德性”的话题:“如何阅读是知识问题,但更是读书人的德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张辉的这部随笔集看成是一本关于“阅读的德 性”的书,也是在序言中,张辉倡言“读书风气的更易,乃至士风
“阅读的德性”(代序) III
的良性回归,应该从认真读书始”。
而张旭东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中,则从“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的角度,呼吁“经典阅读”,认为“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与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 换的需求”。书中收录的《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一文中 指出:
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 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 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 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而能够触及这种 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 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通过阅读这些伟大心灵的记录, 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 感和价值定位,才能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做出有效的 应对。
张旭东强调通过经典“与过去伟大心灵”“直接对话”。而这种“对话性”也决定了经典构成了我们与“过去伟大心灵”进行“晤谈”的日常性和恒常性,决定了一部真正够分量的文史哲经典不是随便翻阅一过就能奏效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在
《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关于什么是经典的十四条定义中,第一条就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IV 梦中的彩笔
我由此对“阅读”的话题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相继读了洪子诚的《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 2015 年 2 月版),特里·伊格
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版),托马
斯·福斯特的《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南海出版公司 2015 年 4 月版),
《埃科谈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年 1 月版),詹姆斯·伍德
的《小说机杼》(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埃兹拉·庞德的《阅读 ABC》,约翰·凯里的《阅读的至乐—20 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安妮·弗朗索瓦的《闲话读书》等,这些书虽然不尽讨论阅读,但都或多或少对 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乐趣,以及“读什么”、“怎样读”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思考。
如果说“经典”阅读,因之关涉的是“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和家园”(张旭东语)的大问题,而显得有些“高大上”,那么耶鲁学 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所讨论的“阅读”,也许会让普通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和力,在本书“前言”中,布鲁姆说:“如何善于读书,没有单一的途径,不过,为什么应当 读书,却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布鲁姆看来是人的 “孤独”:
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一,因为, 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最具治疗作用的。我转向阅读,是作为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 事业。
很多人都是在孤独的人生境遇中开始养成阅读习惯的。而“阅
“阅读的德性”(代序) V
读”在布鲁姆这里,则有助于消除生命本体性的孤独感,这对于日渐原子化的孤独的“后现代个人”而言,是具有疗治意义的善意提 醒。而庞德的见解也同样属于“治愈系”的,他在《阅读 ABC》中这样看待“文学”的作用:
文学作为一种自发的值得珍视的力量,它的功能恰恰是 激励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它舒解心灵的压力,并给它给养, 我的意思确切地说就是激情的养分。
这种“激情的养分”如果说对人类具有普泛的有效性,那么, 一个专业读者的“阅读”,则更多关涉到人类审视自我、主体、历史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洪子诚先生的《阅读经验》,提供的就 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心灵在半个多世纪的阅读岁月中留下的时光 印迹。批评家李云雷认为洪子诚“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 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 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的
‘经验’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经验’在这里就不仅是‘自我’ 与历史发生具体联系的方式,也是‘自我’据以反观‘历史’与切 入当下的基点。”《阅读经验》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
“自我”省思的氛围,一种雕刻时光般的对岁月的思考所留下的缓慢刻痕。
真正的阅读,似乎也因为这种与岁月和历史的缓慢的对话, 而越来越成为一项技术活。就像手工艺人的劳作,必须精雕细刻, 慢工出细活。因此,张辉在《如是我读》中的《慢板爱好者》一文中
VI 梦中的彩笔
重述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中的一个故事:一帮抬尸 工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却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不走了。雇主过来催促,工人回答说:“走得太快了,灵魂是要跟不上的。”张辉说,此后,每记起这个故事,就想起尼采在《曙光》一书的前言中,面对“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对“缓慢”和
“不慌不忙”的强调,以及对“慢板”的爱好:
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慢板的爱好者。…… 因为语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 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 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 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这种艺术 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 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 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
如果说在尼采那里,“慢”构成的是“正确地阅读”的标准,那么,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告诉普通读者:看似深奥的文 学分析也“可以是快乐的”。这堪称是一种快乐的阅读哲学。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也称自己选择图书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埃科在《埃科谈文学》中也对文本持类似的理解:
我说的文本并不是实用性质的文本(比方法律条文、科学公式、会议记录或列车时刻表),而是存在意义自我满足、为人类的愉悦而创作出来的文本。大家阅读这些文本的目的在
“阅读的德性”(代序) VII
于享受,在于启迪灵性,在于扩充知识,但也或许只求消磨时间。
也许,“快乐”最终构成了“阅读”的最低但也同时是最高的标准。
用户评价
这本《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真的像一本时光胶囊,沉甸甸地握在手里,翻开扉页,仿佛就跌进了一个由文字织就的迷宫。我一直对西方现代文学的那些“碎片化”叙事、“内心独白”的洪流以及“解构”传统的故事模式感到着迷,却又常常被其晦涩的语言和跳跃的逻辑搞得晕头转向。这本书的标题就自带一种宿命感,让我预感到它将带领我穿梭于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学“废墟”之间。我期待着它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为我梳理出那些错综复杂的文学脉络,点亮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邃意涵。比如,普鲁斯特的“失落的时光”,是如何通过无数个细节的堆砌,构建起一个庞大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卡夫卡的荒诞,又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对个体存在困境的深刻隐喻?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如何用简洁的语言,在字面之下暗流涌动着巨大的情感张力?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也希望它能让我对这些文学巨匠的创作手法和哲学思考有更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在那些看似支离破碎的现代主义叙事中,是否依然能寻找到人性的共通之处,是否在“废墟”的残垣断壁中,仍然有值得我们珍视和回味的“忧伤”之美。
评分《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共鸣。我一直觉得,西方现代文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反思,对人类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挖掘。然而,有时候,面对那些复杂的叙事结构和晦涩的语言,我也会感到一丝无所适从。这本书的“漫读”二字,让我看到了一个轻松的切入点,仿佛它能把我从那些繁复的理论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文学作品本身所带来的冲击。我期待着,它能为我打开一扇了解莫里森、昆德拉、或者加缪这些作家作品的窗户。我想知道,他们笔下的“废墟”,究竟象征着怎样的社会现实或是精神困境?而“忧伤”,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主题?这本书是否能让我理解,为何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存在感会如此脆弱,为何我们会对失去的、未曾拥有的事物产生如此深切的怀念?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引领,我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关怀,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与作者、与作品灵魂对话的奇妙体验,并从中获得一些对生活和人生的启示。
评分这本《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听起来就充满了哲学意味和艺术气息。我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一些零散的印象中,比如某个作家的名字,或者某个作品的片段。但我总觉得,那个时代的作品,蕴含着一种与我们当下息息相关的精神特质,一种对人生、对世界更深层次的追问。这本书的“漫读”二字,让我觉得它不会是一本教条式的教材,而更像是一次随性的、充满发现的文学漫步。我期待着它能带领我走进那些文学作品的“废墟”之中,去发掘那些被时间尘封的宝藏。我希望从中能了解到,像叶芝、斯特林堡、或者里尔克这样的诗人,他们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用诗歌捕捉住灵魂的细微触动。我也想知道,那些小说家们,如柯南·多伊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在解开一个个谜案的同时,是否也在揭示着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隐秘?“忧伤”这个词,让我感觉这本书的解读会带着一种感同身受的温度,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分析,而是会触及作品背后的人文关怀。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现代文学所传达的关于存在、关于失落、关于希望的永恒主题。
评分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这本书名时,脑海里闪过的是无数破碎的意象:古老的庄园、被遗忘的书页、风中摇曳的残花,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弥漫在空气中的哀愁。我对西方现代文学一直抱持着一种既敬畏又好奇的态度,总觉得那些作家们仿佛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能将日常琐碎升华为深刻的哲学命题,将个人的迷惘描绘成时代的缩影。这本书的出现,正是我内心深处对这份好奇心的一次回应。我希望它能像一个温和的引路人,带领我走进那些曾经让我望而却步的文学殿堂,却不会让我感到压力倍增。我期待着能从中了解像乔伊斯、伍尔夫、狄兰·托马斯这样的大师,他们是如何在语言的疆域里进行大胆的实验,又是如何捕捉住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我尤其好奇,在他们的笔下,那些“废墟”究竟是物质的荒凉,还是精神的枯竭?而所谓的“忧伤”,又是否是一种对逝去美好的眷恋,抑或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感?我更想知道,通过这些“漫读”,我是否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阅读方式,能够理解那些看似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并从中获得某种启发和慰藉,就像在废墟中发现一朵顽强盛开的花朵一样,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生机。
评分《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这本书,光是听名字就让人联想到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我想象着,它就像一位老朋友,娓娓道来那些西方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充满个性和深邃思想的作品。我一直对那个时代涌现出的种种文学思潮和艺术变革感到好奇,但又常常被各种理论和术语弄得眼花缭乱。这本书的“漫读”二字,恰恰给了我一种轻松的信号,暗示着它不会是枯燥乏味的学术论述,而更像是一次充满趣味和感悟的文学之旅。我期待着能在书中看到对那些现代主义巨匠的生动解读,比如福克纳笔下南方小镇的家族史,是如何在层层叠叠的时间线中展现人性的复杂;贝克特笔下的荒诞剧,又是如何用极简的对话和场景,直击存在的虚无。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我理清这些大师们作品中的逻辑线索,理解他们所探讨的关于个体、社会、意识等宏大主题。同时,我也想知道,“废墟”和“忧伤”这两个词,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是文学创作的背景,还是作品本身的情感内核?我渴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深入地欣赏西方现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并从中汲取力量,去思考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和人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