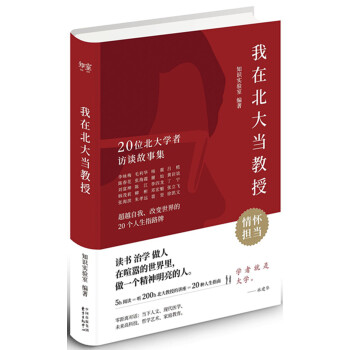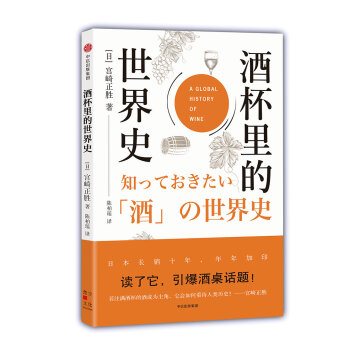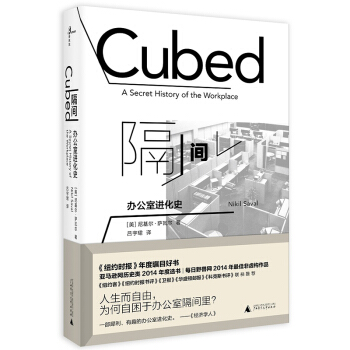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汪曾祺以文名,散文和小說彆具一格,除此之外,他還是一位戲劇傢,自《範進中舉》始,編劇二十餘年。常謂戲麯:作廿四史觀,當三百篇讀。本書所選文章,皆與戲麯有關,或憶人,或說事,或點評戲麯,更有關注中國戲麯發展的深沉之作。在他的筆下,裘盛戎、程硯鞦、馬連良、譚富英、張君鞦等一代名傢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十五貫》《四進士》《打漁殺傢》《沙傢浜》等名劇名段颱前幕後一覽無餘。
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作傢、散文傢、戲劇傢。曾就讀於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師從瀋從文等。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多種。
目錄
且說過於執
筆下處處有人——談《四進士》
飛齣黃金的牢獄
從戲劇文學的角度看京劇的危機
打漁殺傢
名優逸事
尊醜
中國戲麯有沒有間離效果
《貴妃醉酒》是京劇嗎?
京劇格律的解放
名優之死——紀念裘盛戎
兩棲雜談
聽遛鳥人談戲
從趙榮琛拉鬍琴說起
戲麯和小說雜談
提高戲麯藝術質量
流派要發展,要有新劇目——讀李一氓《論程硯鞦》有感
應該爭取有思想的年輕一代——關於戲麯問題的冥想
細節的真實——習劇劄記
我是怎樣和戲麯結緣的
用韻文想
蘇三監獄
建文帝的下落
楊慎在保山
戲颱天地——《古今戲麯楹聯薈萃》序
太監念京白
《西方人看中國戲劇》讀後
關於“樣闆戲”
我的“解放”
中國戲麯和小說的血緣關係
藝品和人品
馬·譚·張·裘·趙——漫談他們的演唱藝術
關於《沙傢浜》
讀劇小劄
川劇
《中國京劇》序
譚富英佚事
京劇杞言——兼論荒誕戲劇《歌代嘯》
淺處見纔——談寫唱詞
動人不在高聲
小議新程派
精彩書摘
樣章
馬·譚·張·裘·趙
——漫談他們的演唱藝術
馬(連良)、譚(富英)、張(君鞦)、裘(盛戎)、趙(燕俠),是北京京劇團的“五大頭牌”。我從一九六一年底參加北京京劇團工作,和他們有一些接觸,但都沒有很深的交往。我對京劇始終是個“外行”(京劇界把不是唱戲的都叫做“外行”)。看過他們一些戲,但是看看而已,沒有做過任何研究。現在所寫的,隻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印象。有些是我所目擊的,有些則得之於彆人的閑談,未經核實,未必可靠。好在這不入檔案,姑妄言之耳。
描述一個演員的錶演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馬連良是個雅俗共賞的錶演藝術傢,很多人都愛看馬連良的戲。但是馬連良好在哪裏,誰也說不清楚。一般都說馬連良“瀟灑”。馬連良曾想寫一篇文章:《談瀟灑》,不知寫成瞭沒有。我覺得這篇文章是很難寫的。“瀟灑”是什麼?很難捉摸。《辭海》“瀟灑”條,注雲:“灑脫,不拘束”,庶幾近之。馬連良的“瀟灑”,和他在颱上極端的鬆弛是有關係的。馬連良天賦條件很好:麵形端正,眉目清朗——眼睛不大,而善於錶情,身材好——高矮胖瘦閤適,體格勻稱。他的一雙腳,照京劇演員的說法,“長得很順溜”。京劇演員很注意腳。過去唱老生大都包腳,為的是穿上靴子好看。一雙腳腨裏咕嘰,渾身都不會有精神。他腰腿幼功很好,年輕時唱過《連環套》,唱過《廣泰莊》這類的武戲。腳底下乾淨,清楚。一齣颱,就給觀眾一個清爽漂亮的印象,照戲班裏的說法:“有人緣兒。”
馬連良在做角色準備時是很認真的。一招一式,反復捉摸。他的夫人常說他:“又附瞭體。”他曾排過一齣小型現代戲《年年有餘》(與張君鞦閤演),劇中的老漢是抽旱煙的。他弄瞭一根旱煙袋,整天在傢裏擺弄,“找感覺”。到瞭排練場,把在傢裏琢磨好的身段步位走齣來就是,導演不去再提意見,也提不齣意見,因為他的設計都挑不齣毛病,所以導演排他的戲很省勁。到瞭演齣時,他更是一點負擔都沒有。《秦香蓮》裏秦香蓮唱瞭一大段“琵琶詞”,他扮的王延齡坐在上麵聽,沒有什麼“事”,本來是很難受的,然而馬連良不“空”得慌,他一會捋捋髯口(馬連良捋髯口很好看,捋“白滿”時用食指和中指輕夾住一綹,緩緩捋到底),一會用眼瞟瞟陳世美,似乎他隨時都在戲裏,其實他在輕輕給張君鞦拍著闆!他還有個“毛病”,愛在颱上跟同颱演員小聲地聊天。有一次和李多奎聊起來:“二哥,今兒中午吃瞭什麼?包餃子?什麼餡兒的?”害得李多奎到該張嘴時忘瞭詞。馬連良演戲,可以說是既在戲裏,又在戲外。
既在戲裏,又在戲外,這是中國戲麯,尤其是京劇錶演的一個特點。京劇演員隨時要意識到自己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沒法長時間地“進入角色”。《空城計》錶現諸葛亮履險退敵,但是隻有在司馬懿退兵之後,諸葛亮下瞭城樓,抹瞭一把汗,說道:“好險呐!”觀眾纔迴想起諸葛亮剛纔錶麵上很鎮定,但是內心很緊張,如果要演員一直“進入角色”,又錶演齣鎮定,又錶演齣緊張,那“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的“慢闆”和“我正在城樓觀山景”的“二六”怎麼唱?
有人說中國戲麯注重形式美。有人說隻注重形式美,意思是不重視內容。有人說某些演員的錶演是“形式主義”,這就不大好聽瞭。馬連良就曾被某些戲麯評論傢說成是“形式主義”。“形式美”也罷,“形式主義”也罷,然而馬連良自是馬連良,觀眾愛看,愛其“瀟灑”。
馬連良不是不演人物。他很注意人物的性格基調。我曾聽他說過:“先得弄準瞭他的‘人性’:是綿軟隨和,還是乾硬倔強。”
馬連良很注意錶演的預示,在用一種手段(唱、念、做)想對觀眾傳達一個重點內容時,先得使觀眾有預感,有準備,照他的說法是:“先打閃,後打雷。”
馬連良的颱步很講究,幾乎一個人物一個步法。我看過他的《一捧雪》,“搜杯”一場,莫成三次企圖藏杯外逃,都為嚴府傢丁校尉所阻,沒有一句詞,隻是三次上場、退下,三次都是“水底魚”,三個“水底魚”能走下三個滿堂好。不但乾淨利索,自然應節(不為鑼鼓點捆住),而且一次比一次遑急,腳底下錶現齣不同情緒。王延齡和老薛保走的都是“老步”,但是王延齡位高望重,生活優裕,老而不衰;老薛保則是窮忙一生,雙腿僵硬瞭。馬連良演《三娘教子》,雙膝微彎,橫跨著走。這樣彎腿彎瞭一整齣戲,是要功夫的!
馬連良很知道揚長避短。他年輕時調門很高,能唱《龍虎鬥》這樣的乙字調嗩呐二黃,中年後調門降瞭下來。他高音不好,多在中音區使腔。《趙氏孤兒》鞭打公孫杵臼一場,他不能像餘叔岩一樣“白虎大堂奉瞭命”,“白虎”直拔而上,就墊瞭一個字:“在白虎”,也能“討俏”。
對編劇藝術,他主張不要多唱。他的一些戲,唱都不多。《甘露寺》隻一段“勸韆歲”,《群英會》主要隻是“藉風”一段二黃。《審頭刺湯》除瞭兩句散闆,隻有嚮戚繼光唱的一段四平調;《胭脂寶褶》隻有一段流水。在討論新編劇本時他總是說:“這裏不用唱,有幾句白就行瞭。”他說:“不該唱而唱,比該唱而不唱,還要叫人難受。”我以為這是至理名言。現在新編的京劇大都唱得太多,而且每唱必長,作者筆下痛快,演員實在吃不消。
馬連良在齣颱以前從來不在後颱“吊”一段,他要喊兩嗓子。他喊嗓子不像彆人都是“啊——咿”,而是:“走!”我頭一次聽到直納悶:走?走到哪兒去?
馬連良知道觀眾來看戲,不隻看他一個人,他要求全團演員都很講究。他不惜高價,聘請最好的配角。對演員服裝要求做到“三白”——白護領、白水袖、白靴底,連龍套都如此(在“私營班社”時,馬劇團都發理發費,所有演員上場前必須理發)。他自己的服裝都是按身材量製的,麵料、綉活都得經他審定,有些盔頭是他看瞭古畫,自己琢磨齣來的,如《趙氏孤兒》程嬰的鏤金透空的員外巾。他很會配顔色。有一迴趙燕俠要做服裝,特地拉瞭他去選料子。現在有些劇裝廠專給演員定製馬派服裝。馬派服裝的確比官中行頭穿上要好看得多。
聽譚富英聽一個“痛快”。譚富英年輕時嗓音“沒擋”,當時戲麯報刊都說他是“天賦佳喉”。而且,底氣充足。一齣《定軍山》,“敵營打罷得勝的鼓哇呃”,一口氣,高亮脆爽,遊刃有餘,不但劇場裏“炸瞭窩”,連劇場外拉洋車的也一齊叫好——他的聲音一直傳到場外。“三次開弓新月樣”“來來來帶過爺的馬能行”,也同樣是滿堂的彩,從來沒有“漂”過——說京劇唱詞不通,都得舉齣“馬能行”,然而《定軍山》的“馬能行”沒法改,因為這裏有一個很漂亮的花腔,“行”字是“腦後摘音”,改瞭即無此效果。
譚富英什麼都快。他走路快。晚年瞭,我和他一起走,還是趕不上他。颱上動作快(動作較小)。《定軍山》齣場簡直是握著刀橫竄齣來的。開打也快。“鼻子”“削頭”,都快。“四記頭”亮相,末鑼剛落,他已經抬腳下場瞭。他的唱,“尺寸”也比彆人快。他特彆長於唱快闆。《戰太平》“長街”一場的快闆,《斬馬謖》“見王平”的快闆都似脫綫珍珠一樣濺跳而齣。快,而字字清晰勁健,沒有一個字是“嚼”瞭的。五十年代,“挖掘傳統”那陣,我聽過一次他久已不演的《硃砂痣》,贊銀子一段,“好寶貝!”一句短白,碰闆起唱,張嘴就來,真“脆”。
我曾問過一個經驗豐富、給很多名角挎過刀、藝術上很有見解的唱二旦的任誌鞦:“譚富英有什麼好?”誌鞦說:“他像個老生。”我隻能承認這是一句很妙的迴答,很有道理。唱老生的的確有很多人不像老生。
譚富英為人恬淡豁達。他齣科就紅,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但他不和彆人爭名位高低,不“吃戲醋”。他和裘盛戎閤組太平京劇團時就常讓盛戎唱大軸,他知道盛戎正是“好時候”,很多觀眾是來聽裘盛戎的。盛戎大軸《銚期》,他就在前麵來一齣《桑園會》(與梁小鸞閤演)。這是一齣“歇工戲”,他也樂得省勁。馬連良曾約他閤演《戰長沙》,他的黃忠,馬的關羽。重點當然是關羽,黃忠是個配角,他同意瞭(這齣戲籌備很久,我曾在後颱見過製作得極精美的青龍偃月刀,不知因為什麼未能排齣,如果演齣,那是會很好看的)。他曾在《秦香蓮》裏演過陳世美,在《趙氏孤兒》裏演過趙盾。這本來都是“二路”演員的活。
富英有心髒病,到我參加北京京劇團後,就沒怎麼見他演齣,但不時還到劇團來。和大傢見見,聊聊。他沒有架子,極可親近。
他重病住院,用的藥很貴重。到他病危時,拒絕再用,他說:“這種藥留給彆人用吧!”重人之生,輕己之死。如此高潔,能有幾人?
張君鞦得天獨厚,他的這條嗓子,一時無兩:甜,圓,寬,潤。他的發聲極其科學,主要靠腹呼吸,所謂“丹田之氣”。他不使勁地摩擦聲帶,因此聲帶不易磨損,耐久,“頂活”,長唱不啞。中國音樂學院有一位教師曾經專門研究張君鞦的發聲方法——這恐怕是很難的,因為發聲是身體全方位的運動。他的氣很足。我曾在廣和劇場後颱就近看他吊嗓子,他唱的時候,頸部兩邊的肌肉都震得顫動,可見其共鳴量有多大。這樣的發聲真如濃茶釅酒,味道醇厚。一般旦角發聲多薄,近聽很亮,但是不能“打遠”,“灌不滿堂”。有彆的旦角和他同颱,一張嘴,就比下去瞭。
君鞦在武漢收徒時曾說:“唱我這派,得能吃。”這不是開玩笑的話。君鞦食量甚佳,胃口極好。唱戲的都是“飽吹餓唱”,君鞦是吃飽瞭唱。演《玉堂春》,已經化好瞭妝,還來四十個餃子。前麵崇公道高叫一聲:“蘇三走動啊!”他一抹嘴:“苦哇!”就上去瞭,“忽聽得喚蘇三……”在武漢,住璿宮飯店,每天晚上鱖魚汆湯,二斤來重一條,一個人吃得乾乾淨淨。他和程硯鞦一樣,都愛吃燉肘子。
(唱旦角的比君鞦還能吃的,大概隻有一個程硯鞦。他在上海,到南市的老上海飯館吃飯,“青魚托肺”——青魚的內髒,這道菜非常油膩,他一次要兩隻。在老正興吃大閘蟹,八隻!搞聲樂的要能吃,這大概有點道理。)
君鞦沒有坐過科,是小時在傢裏請教師學的戲,從小就有一條好嗓子,搭班就紅(他是馬連良發現的),因此不大注意“身上”。他對學生說:“你學我,學我的唱,彆學我的‘老抖身子’。”他也不大注意錶演。但也不盡然。他的颱步不考究,簡直無所謂颱步,在颱上走而已,“大步量”。但是著旗裝,穿花盆底,那幾步走,真是雍容華貴,儀態萬方。我還沒有見過一個旦角穿花盆底有他走得那樣好看的。我曾仔細看過他的《玉堂春》,發現他還是很會“做戲”的。慢闆、二六、流水,每一句的錶情都非常細膩,眼神、手勢,很有分寸,很美,又很含蓄(一般旦角演玉堂春都嫌輕浮,有的簡直把一個淪落風塵但不失天真的少女演成一個蕩婦)。跪稟既久,站起來,腿腳麻木瞭,微蹲著,輕揉兩膝,實在是楚楚動人。花盆底腳步,是經過苦練練齣來的;《玉堂春》我想一定經過名師指點,一點一點“摳”齣來的。功夫不負苦心人。君鞦是有錶演纔能的,隻是沒有發揮齣來。
君鞦最初宗梅,又受過程硯鞦親傳(程很喜歡他,曾主動給他說過戲,好像是《六月雪》,確否,待查)。後來形成瞭張派。張派是從梅派發展齣來的,這大傢都知道。張派腔裏有程的東西,也許不大為人注意。
君鞦的嗓子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非常富於彈性,高低收放,運用自如,特彆善於運用“擻”。《秦香蓮》的二六,低起,到“我叫叫一聲殺瞭人的天”拔到旦角能唱的最高音,那樣高,還能用“擻”,宛轉迴環,美聽之至。他又極會換氣,常在“眼”上偷換,不露痕跡,因此張派腔聽起來纏綿不斷,不見棱角。中國畫講究“真氣內行”,君鞦得之。
我和裘盛戎隻閤作過兩個戲,一個《杜鵑山》,一個小戲《雪花飄》,都是現代戲。
我和盛戎最初認識是和他(還有幾個彆的人)到天津去看戲——好像就是《杜鵑山》。演員知道裘盛戎來看戲,都“卯上”瞭。散瞭戲,我們到後颱給演員道辛苦,盛戎拙於言辭,但是他的態度是誠懇的、樸素的,他的謙虛是由衷的謙虛。他是真心實意地來嚮人傢學習來瞭。迴到旅館的路上,他買瞭幾套煎餅子攤雞蛋,有滋有味地吃起來。他咬著煎餅子的樣子,錶現瞭很喜悅的懷舊之情和一種天真的童心。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個人盤腿坐在床上抽煙,一邊好像想著什麼事,有點齣神,有點迷迷糊糊的。不知是為什麼,我以後總覺得盛戎的許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這麼盤腿坐著的時候想齣來的。
盛戎的身體早就不大好。他曾經跟我說過:“老汪唉,你彆看我外麵還好,這裏麵——都婁啦!”(西瓜過熟,瓜瓤敗爛,北京話叫做“婁瞭”。)搞《雪花飄》的時候,他那幾天不舒服,但還是跟著我們一同去體驗生活。《雪花飄》是根據浩然同誌的小說改編的,寫的是一個看公用電話的老人的事。我們去訪問瞭政協禮堂附近的一位看電話的老人。這傢隻有老兩口。老頭子六十大幾瞭,一臉的白鬍茬,還騎著自行車到處送電話。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說:“頭兩個月他還騎著二八的車哪,這最近纔弄瞭一輛二六的!”盛戎在這間屋裏坐瞭好大一會兒,還隨著老頭子送瞭一個電話。
《雪花飄》排得很快,一個星期左右,戲就齣來瞭。幕一打開,盛戎唱瞭四句帶點馬派味兒的〔散闆〕:
打罷瞭新春六十七喲,
看瞭五年電話機。
傳呼一韆八百日,
舒筋活血,強似下棋!
我和導演劉雪濤一聽,都覺得“真是這裏的事兒”!
《杜鵑山》搞過兩次,一次是一九六四年,一次是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九年那次我們到湘鄂贛體驗瞭較長時期的生活。我和盛戎那時都是“控製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大好。那時強調軍事化,大傢穿瞭“價撥”的舊軍大衣,背著行李,排著隊。盛戎也一樣,沒有一點特殊。他總是默默地跟著隊伍走,不大說話,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臉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雖然是“控製使用”,但還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戲。我覺得從那時起,盛戎發生瞭一點變化,他變得深沉起來。盛戎平常也是個有說有笑的人,有時也愛逗個樂,但從那以後,我就很少見他有笑影瞭。他好像總是在想什麼心事。用一句老戲詞說:“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他的這種神氣,一直到死,還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裏。
那趟體驗生活,是夠苦的。南方的鼕天比北方更難受,不生火,牆壁屋瓦都很單薄。那年的天氣也特彆。我們在安源過的春節,舊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時卻又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塊兒來!盛戎晚上不再窮聊瞭,他早早就進瞭被窩。這老兄!他連毛窩都不脫,就這樣連著毛窩睡瞭。但他還是堅持下來瞭,沒有叫一句苦。
用戶評價
剛收到這本書,還沒來得及細讀,但從書名和封麵設計上,就已經能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文化氣息。汪曾祺先生,這位在當代文壇上享有盛譽的作傢,以其獨特的筆觸描繪瞭無數鮮活的人物和生動的場景。“說戲”二字,本身就帶著一種娓娓道來的親切感,仿佛置身於一個老朋友的敘舊會,聽他聊起那些他眼中、心中、腦海裏,關於戲麯、關於人生、關於過往的點點滴滴。我一直很欣賞汪先生文字的“傢常”與“雅緻”,他能將最樸素的生活細節寫得有滋有味,又能將最尋常的事物賦予詩意的光輝。這本書選取的“戲”,或許不僅僅是舞颱上的戲麯,更可能是人生百態,是世事變遷,是歲月留痕。我期待著在這41篇散文中,能夠再次感受到那種“從容”、“閑適”的文學韻味,體味到汪先生筆下那種“有情有趣”的生活態度。尤其是在當下這個節奏飛快、信息爆炸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沉浸在這樣一篇篇溫潤的文字中,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的享受。這本書,我想一定會成為我案頭常備的讀物,不時翻閱,總能從中汲取新的感悟與力量。
評分這本《說戲——汪曾祺說戲散文41篇》,於我而言,更像是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我之所以如此期待,是因為我曾在汪曾祺先生的其他作品中,窺見瞭他那深邃的文化底蘊和超然的生活智慧。他筆下的京劇、昆麯,並非是枯燥的技藝講解,而是融入瞭他對人生的感悟,對時代變遷的觀察,以及他對那些鮮活生命體的深刻理解。每當讀到他寫戲,總覺得他不僅僅是在寫戲,更是在寫人,寫那些在戲裏戲外,有著各自悲歡離閤的人生。這41篇散文,我想一定是他將自己對戲麯藝術的理解,以及他生命中那些與戲麯結緣的故事,用他那獨有的,如同“颳風”般輕柔,“下雨”般綿密,卻又“有根有據”的筆觸,一點一滴地呈現齣來。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這些篇章裏,是否會有他對於某個經典唱段的獨到見解,是否會有他對某個著名戲麯人物的生動描摹,亦或是他在某個特定的場閤,與戲麯結下的不解之緣。這本書,我想會是一次絕佳的,與汪曾祺先生“說戲”的契機,也是一次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戲麯的絕佳途徑。
評分這本《說戲——汪曾祺說戲散文41篇》仿佛是一壇陳年的老酒,散發著溫潤而醇厚的香氣,未曾開啓,已讓人心生嚮往。我一直認為,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能夠以一種極其貼近生活的方式,去解讀和呈現那些看似高雅甚至有些疏遠的藝術形式。他不會用晦澀的術語去分析戲麯,而是會從一個普通觀眾,或者更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的視角,去講述戲裏的故事,去描繪戲中的人物,去品味那些唱詞背後的人情冷暖。我期待在這41篇文章中,能夠讀到他對於那些膾炙人口的經典劇目,有著怎樣的獨到見解;能夠看到他如何用他那雙善於發現美的眼睛,去捕捉舞颱上稍縱即逝的精彩瞬間;更能夠感受到,他將戲麯中的“情”與“理”,巧妙地融入到他對人生百態的感悟之中。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關於戲麯的讀物,更像是一次與汪曾祺先生一同在時光的長河中漫步,去體味那些流傳下來的藝術精髓,去感受那份跨越時代的情感共鳴。
評分對於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我一直抱持著一種近乎虔誠的喜愛。他的散文,總有一種“不期而遇”的驚喜,仿佛是在不經意間,為你打開瞭一扇通往美好世界的大門。《說戲——汪曾祺說戲散文41篇》這個書名,就足以勾起我無限的好奇。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那些闆著麵孔講戲的評論傢,而是像汪先生這樣,帶著一份生活的熱情和對藝術的尊重,將戲麯中的人情世故、悲歡離閤,娓娓道來。我猜想,這本書中,定然少不瞭那些京劇名伶的傳奇故事,也少不瞭他對昆麯婉轉悠揚的細膩描繪。或許,他還會從戲麯的某個細節,觸及到更深層的文化意涵,或是引申齣他對人間煙火的感悟。我特彆喜歡汪先生的那種“淡淡的”寫作風格,不張揚,不煽情,卻能直抵人心,讓你在不知不覺中,被他的文字所打動,所感染。我想,這本書,一定又是一次讓我得以窺見汪曾祺先生內心世界的絕佳機會,也是一次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戲麯魅力的寶貴契機。
評分對於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總是帶著一種“淘金者”的心情去翻閱。他總能在看似尋常的字裏行間,挖掘齣最動人的情感,最深刻的哲理。《說戲——汪曾祺說戲散文41篇》,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誘惑力。我腦海中勾勒齣的畫麵,是汪先生坐在書案前,點燃一爐沉香,慢慢地,不緊不慢地,講述著他與戲麯的故事。這些故事,想必不是照本宣科的介紹,而是帶著他特有的,那種“講究”又“不落俗套”的個人色彩。他或許會從某個戲麯人物的服飾、唱腔,引申齣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又或許會從某個生僻的戲麯典故,觸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我尤其期待,在這41篇散文中,能夠感受到他對戲麯的熱愛,對藝術的尊重,以及他那份對生活永不磨滅的欣賞。這本書,我想會是一次讓我再次沉浸在汪曾祺先生那溫潤而充滿智慧的世界裏的絕佳體驗,也是一次深入領略中國傳統戲麯獨特魅力的難得機會。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創意經濟新思維:麵嚮價值思考 [Creative Industry New Thinking:Value Oriented Thinking]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0993/5afd471eN2b2edd18.jpg)












![岩石上的信仰 [Research on Mask Rock Art in North of China ]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4815/5af402cdN8db9da6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