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内容搜集详尽、全面,精心设计,精装打造,出版规模为历次*大。
2、包括首次整理出版的各种珍贵手稿,如日记、书信、散佚片断文章等,全面展现了这位四川老作家的创作历程和风格面貌,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学史研究价值。
内容简介
《沙汀文集》收录了沙汀自一九三一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至今存世的全部作品,含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日记等。《文集》共十卷十一册,各卷按中长篇小说(一、二、三卷)、短篇小说(第四、五卷)、报告文学·散文(第六卷)、文论(第七卷)、书信(第八卷)、日记(第九卷,上下册)、回忆录(第十卷)编序。本次整理出版,搜集详尽、出版规模大,意在全面展现这位四川老作家的创作历程、风格面貌以及他与现代文坛众多作家的创作交流、生活故事、情感联系,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史料补充、作家作品研究都具极高的价值。
作者简介
沙汀(1904-1992),成名于于左翼文坛,被鲁迅誉为*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以社会剖析的手法和含蓄深沉的风格,描绘了旧中国四川乡镇和农村的生活画面,刻画了一系列基层统治者的丑恶嘴脸。抗战爆发后回川,曾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卷 淘金记 困兽记
第二卷 还乡记 闯关
第三卷 木鱼山 青�h坡 红石滩
第四卷 短篇小说(1931-1944)
第五卷 短篇小说(1945-1984)
第六卷 报告文学 散文 剧本
第七卷 文论
第八卷 书信
第九卷 日记 上册
第九卷 日记 下册
第十卷 回忆录
精彩书摘
十一
林幺长子的来访,完全出于寡妇意料之外。因为对于白酱丹以及幺长子这一类人,她都一例存着戒心,不敢沾惹。但是,白酱丹很会装点自己,看起来好像多少顾点体面,幺长子却是什么也不管的,所以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极端无赖的恶棍。
而且,就在最近三五年间,寡妇还曾经尝过幺长子的苦头。那是三年以前的事,在那照例算是一个光棍头子的收获期间的新年当中,由于青年人的轻浮,同时也由于北斗镇的特殊风气,人种被幺长子骗上手了。说好拿出一百元入流,开个五排。后来尽管给寡妇反对掉了,没有当成光棍,但是幺长子却照旧要去了那笔不小的货礼。
有着这样的认识以及经验,所以当幺长子跑来造访的时候,寡妇不能不吃惊了。但她并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妇人,而在事实上她也对付得很好。甚至当那老流氓起身告辞的时候,她还觉得他给她的印象,并没有她所想象的那样恶劣。虽然她也同样的不痛快,以为幺长子显然企图趁她的不幸来加深她的创痛。
寡妇是聚精会神来张罗幺长子的。当她庆幸自己竟能那样圆满地渡过难关,而一面又暗中悲痛她那时常都在遭受欺凌的孤苦的处境的时候,她又出乎意外地碰上了白酱丹,她的正式的对手,这却使她不能够自持了。而正像一般陷在悲痛郁闷里的人们那样,经过一度发泄,用哭诉和叫嚷把白酱丹送走了,这才稍稍爽快了些。但是她的怨气并没有完全吐露出来。尤其因为她还不能判断,她的抗争所能发生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大。那个外表毫无变动的人,是被她吓退了,或者加深了敌意?……
在大厅上休息了一会,她就一径走往内院里去;而且忍不住尽情哭泣起来,一面抱怨着儿子、自己的亡夫,以及命运。她就坐在堂屋门边的矮圈椅上,媳妇同孙表婶带着惶惑不安的神气守护着她。人种是就在厢房的卧室里的,但他毫无反响。两次来客的经过,早已由妻子告诉他了,他深陷在追悔里面,觉得自己做了笨事。
人种早就隐约地觉察到,自己的行为是有些轻率的。他对母亲的责斥没有坚决反驳,原因也就正在这里。自从同寡妇发生口角过后,他就一直没有出街,这一方面是感觉得太难为情,一方面也幻想事情或许可以就此阴消下去。而他一两天来的赌气,则只是想维持自己的自尊心。然而,现在他却没勇气这样做了。因此,寡妇虽则连声责嚷,人种不仅没有还嘴,晚饭时候,他还厚着脸皮劝她,请她不必生气。仿佛那种种纠纷的制造者并不是他,倒是另外一个什么人一样。
“我还懒得怄气!”他俨然地说,“他再扯,陪他打官司就是了!”
寡妇没有理他,她深知同他拌嘴并无益处。
“好呀,”随后,她忍不住冷冷地说,“看又什么人去顶状嘛。”
寡妇的想法是这样的,根据经验,告状的结果只能使他们的地位更加恶劣,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会加深仇恨,而白酱丹干坏事的本领又很有名的,什么恶毒办法他都想得出来,而由此他们的麻烦也就更加多了。
但她依旧不能放心,猜不透事情将会怎样发展。能够由她那场哭诉阴消下去,自然很好,但是经过考虑,她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当她一想到白酱丹的沉着冷静,以及他在镇上无数具体的恶行的时候,她的心情又立刻被失望填塞满了。
晚上,寡妇又特别把人种叫了来,追问了一番事情的详细经过。他们是怎样提起挖金的事的,他的答复又是怎样。虽然这是她早已问过无数次的了,但她还想听取一些她所不曾知道的有利的关节。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人种的诉说,照旧是粗枝大叶的,深怕有人怀疑他提供过什么过分糊涂的诺言。
当人种说完过后,寡妇深深叹了口气,用了猜测眼光一径凝视着他。
“事情不做呢,已经做了,你不要瞒我啊?”她又试探地说。
“我瞒你做什么呀!”人种不快地回嘴了,真像蒙了不白之冤,显出一副受屈神情,“要是认真说过什么,他们早就搞起来了,——还亲自跑来交涉!”
人种的态度、口气,无疑发生了相当大的效力,因为寡妇听了以后,显然安静多了。而且立刻觉得白酱丹的不很自然的神气,以及他的故意回避本题,甚至匆匆忙忙就走掉了,都看成没有严重约束的佐证。而这场淘气将会无形中阴消下。
但是,就在次一日下午,白酱丹又来访问来了。不只是他一个人,彭胖也在一道。彭胖是白酱丹邀来的,一方面他自己也愿意。因为能够当场看个究竟,在他绝不是一桩无益的举动,反而倒有十分的必要。彭胖曾经仔细地打听过,寡妇的态度和白酱丹说的相差颇远,是并不轻松的;于是他更怀疑他的谈话欠缺诚实,愿意亲自看看。
他们的匆促的造访,是临时决定的。若依白酱丹的意见,还该拖后两天,但是彭胖坚决反对。这因为,第一,姚老五回来了,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雇了工匠,买了必需的用具;其次,街面上突然流行着一种传闻,为了要抵制白酱丹,寡妇正在同人商量,要自己开发筲箕背了。这两点都使彭胖异常感到不安。白酱丹虽然一再声称,彭胖听来的尽是谣言,它不是从幺长子那里来的,便是出于误会。姚老五的回来,也不能成为把访问提前举行的理由。他已经给过保证,纵使事情失败,彭胖垫出的费用,他是准会拿回来的。然而,他的辩解丝毫没有用处!……
当彭胖答应白酱丹一道前去访问的时候,曾经笑着申明,去,他是去的,却不能够说话,做正式说客的一个帮手。而且他还暗示,他去,不过因为白酱丹情面太大,事实上他倒很不愿意。所以访问当中,他总一直带着一种难乎为情的傻笑。
他们在客厅里冷坐了好一会,寡妇才走出来。而在守候当中,他们彼此都沉默着,只于那个给他们拿烟倒茶,神气显得不很安静的仆人两次不在的时候,彭胖才叽咕了几句,重新笑着申明:他只能做个陪客。正在这时,寡妇庄重地走出来了。
同上一次的访问两样,寡妇显然是有了准备的。为了要给来客一种不可轻侮的印象,她还特别打扮了一番,阴丹布罩衫,里面是黑缎旗袍。头面也是重新梳洗过的,而从她的神气看来,仿佛这不过是个通常的会见,并不怎么严重。
说过几句照例的套语,她就首先若无其事地闲谈起来。
“听说又要收军粮了,”她挂虑地说,“这个日子怎么过呀?”
“是的,有这个事,”白酱丹承认着,文绉绉地点一点头,“不过还是要给价的,照市价给。还有一种是捐献,就是大家随意乐捐,愿意出多少都行。”
“这个办法倒好。那些田亩多的,倒该多捐献一点。”寡妇装穷卖富地说。
“不过,听说会议上还是决定摊派。”白酱丹微笑着说明。
“现在的话都是说得好听!”彭胖仿佛吵架似的插嘴说了,“简直像扯谎坝卖狗皮膏药的一样!”他觉得当粮户真是太难,随即摇头叹气起来。
“派也好呀!”寡妇毫不经意地说,“只要派得公平。”
谈话一时间中断了,彼此都落在沉默里面。寡妇的满不在意的态度,无疑是做作的,因为她正为着那些新的花头感到焦灼,预想到一种新的不平的迫近。默默地抽着水烟的白酱丹猜透了她的心意,于是他思索着,觉得这个机会可以利用。
但是寡妇忽然又开口了。她意义不明地叹了口气,接着淡淡地说:
“这个仗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打得完啊。……”
“恐怕快了。”白酱丹说,从沉思里抬起头来,充满慰藉地微微一笑,“听说日本人已经要打不起了。他现在成了骑虎之势,想下台都下不了啊。”
彭胖不大耐烦地苦笑一下,意思是说:我们像又下得了台!
“说实话,我们也算顶好了啊!”神气活现地扬扬眉毛,白酱丹接着又说,“就只出几个钱嘛,难道他还打到四川来了?好多的天险!……”
“阿弥陀佛,这样已经够了!”寡妇摇头叹气。
她已经被这个秉性柔韧的来客黏得不自在了。
“再这样下去,恐怕连人也活不下去了!”她感慨万端地接着说,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目标,“昨天菜油又涨价了。肉也涨了!连土火柴,也要两角钱一包了。钱也越来越不成话!你们看那种新一分的钱吧,先前的铜纽扣,也比它大。”
“城里听说毛钱也当一分用了。”白酱丹补充道。
“我倒宁肯用毛钱好些!……”
彭胖语气非常严重;但他没有说得完备:他宁肯用毛钱,因为毛钱有着小孔,可以用麻绳穿起,不容易失掉。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的肥腮巴绯红了。
彭胖自己清楚,他红脸,这不仅因为他的话突然而来,突然而止,实际上,对于白酱丹老是避开本题,他已经感到很难受了。他认定双方都不愿意抢先开口,都在等候一个更好的发言机会,于是开始考虑是否应该修正一下自己的诺言。
彭胖决心不再当一个旁观者了。他向白酱丹已经使了两回脸色,叫他见机而作;但是毫无效果!现在,为了掩饰他的狼狈,他就更加不能自持起来。
“唉,”他装傻地笑着说,“你不是要向大太太说话吗?”
白酱丹对他扬扬眉毛,没有回答出来。
“什么话?”寡妇假意地问。
“你说不一样么?”白酱丹找出答语来了。
“哪里哟!”彭胖忸怩起来,“你开玩笑!……”
在初,白酱丹是颇不满意彭胖的急躁的,因为他认定现在还不是提谈严重问题的适当时机。然而,寡妇的反应未免出乎意外,她是很平静的,并不显得大惊小怪,因此立刻提出来谈,也许不能算冒险了。
白酱丹有一种成见,以为处身在任何困难的交涉当中,最怕的是对手失掉理性,或者一句话就把调停之门封了,使你天大的理由都得不到考虑的余地。虽然寡妇目前的情形不是这样,他也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交涉拿戏谑来开场。这做起来很自然,因为彭胖的狼狈,就正是他所以想到以戏谑开始的有力暗示。
“你问他吧!”他搭讪地说,用下巴指点一下彭胖,“怎么,还害羞吗?”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说的!”彭胖生气着,以为受了调摆。
“你赌个咒?……”
白酱丹做作得比彭胖更加认真,但他没有引起什么真心的欢笑。
“好吧,”接着,他又故为幽默地说了,黄而浮肿的脸上充满笑意,“让我来开头吧!不过,出去的时候,你不要抱怨我哇,怪我把你的生意抢了。”
彭胖咕哝了一句什么,寡妇佯笑起来;但却掩盖不掉她的惶惑疑惧。
隔了一会,白酱丹这才停止了抽烟,带点微笑凝视着寡妇。这凝视包含着讨好的成分,但那最隐伏的意义,却是企图猜透对方心里深藏着的重要念头,以便决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接着,他就显出一点假装的腼腆,把他要说的话说开头了。
白酱丹的声调,比平常更从容、更迂缓,好像那从他蓄着胡子的嘴唇当中吐出来的每一个字,他都称量过似的,以免使对方感受任何刺激。这在他看来,也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而且经常使用;虽然对于那种直率人却也往往一筹莫展。
白酱丹开始诉说事件的经过。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说的,因为极力审慎,寡妇听起来却像在做善意的解释。然而,当一接触到人种的约束,情形就两样了。
“他晓得什么哇!”寡妇突然切断了他,“他只晓得烧烟,打牌!”
白酱丹同彭胖互相望了一眼。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过就事说事罢了!”白酱丹微笑着解释,“不管怎样,事情的真相总该闹明白的,免得大家发生误会。……”
“对,大家发生误会就不好了。”彭胖帮着腔说。
“我也不过顺便说说,”寡妇紧接着说,情真地赔着小心,“本来也是不懂事呀!当到这几个老前辈面前,又没外客,未必我还好意思说假话?……”
“好吧,那你就再说下去吧!”彭胖说,抬了抬他那变化多端的下巴。
“要得。……”
白酱丹承认着,但却舒舒服服抽了口烟,这才开口。
“哦,事情不是就这样说起来了啊,”他慢慢吐出烟雾,接起已经中断的话头,“可是我们想,好,那里有别人的祖坟!这怎么使得?虽然大家现在都不相信这一套了,总不大好,还是先看看再说吧。所以,有一天下午,顺便转耍一样,我就约了彭大老表,我说,有工夫吧,我们去看看怎样?……”
彭大老表便是彭胖,他机敏地点点头,表示有那回事。
“那对坟地毫无关系!”彭胖同时插入一句。
“对啰!”白酱丹接着说,“一看,窝路离坟还远得很!这一来我们想,不错呀。隔一天大少爷请我们吃饭,又向我提起,我说,可自然可以啰,还是等你们老太太回来再说吧。他讲没有关系。我们想,既然伤不到坟,你又是二三十岁的人了……”
“!他就活到一百岁也不会懂事的!”看出问题的关键就在儿子的约束上面,寡妇赶紧阻止地插嘴了,“别的人不知道,三老表和彭大老爷,一定很清楚的。不管我一个人累死也好,你们看吧,我要他经手过一件事情没有?我倒宁肯拜托外人,——说起来倒二三十岁了,什么事情都不懂呀!”
白酱丹、彭胖感觉棘手地相视一笑。
“并且,”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开口,寡妇就又接着说下去了,“并且,我自己的人,我也多少晓得一点。没有我,他也不敢做主;他还没有这么胆大!”
寡妇带点自负地笑起来,以为她的说辞已经有了效果。
“总之,这一点我是信得过的!”她又加重地说。
“那倒像我们发了疯了!”白酱丹说,不大服气地笑了,笑声带点邪恶味道,“他没有答应,我们就四面八方集股,请工匠,买家具,这里那里……”
“三老表倒不要误会,”因为对方口气太重,寡妇心里一急,赶紧忙着解释,“我不是怪你们,我自己的人,当然也有不是的地方。不过,这只怪他的老子太死早了,”她继续说,眼圈红润起来,“我又是个女流之辈,不会教育,这要请大家原谅。……”
因为要尽力止住哽咽,寡妇于是乎住了嘴。
“当然啊!”白酱丹接着说,忽然摆出一副宽大而又自信的神气,“可是,既然伤不到坟,大表嫂又何必一定这样固执?就不说挖几千几万吧,——起眼一看,大家也不一定要靠这碗饭吃!——现在政府正在提倡开发后方,抗战建国,我们当老百姓的,没有上前线拼命,难道连这点事情也好推脱不干?”
他带着一种教训人的神气凝视着寡妇,希望他的正大堂皇的言辞,能够使她回心转意,不要固执;但这却反而把寡妇激恼了,觉得白酱丹小看了她。
“总之,”寡妇突然地嚷叫道,“就是老子死早了,丢下这个祸害给我!……”
于是寡妇既不看望来客,更不留心他们的话语;仿佛这是用不着的,她就那么沉在一种自伤身世的感情当中。而她没有料到,她把局势扭转来了。
白酱丹感觉到狼狈了。因为他看出来,他的巧辞已经成了废话,再不能对寡妇发生任何有效的影响。因为情势非常清楚,寡妇现在连大门也关了!最后,他想先劝住她,然后重新敷叙种种足以使任何一个顽固者软化的巧妙理由,打破这场僵局。但是毫无效果,而这就使得那在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暴戾发作起来。
沉默一会,他那微瘪的嘴唇边忽然掠过一丝毒狠的狞笑。
“哭,解决不了问题啊!”白酱丹终于警告似的说了,显然认为和善的说服已经绝望,只好另外再来一套,“我们是好好来商量的,有话拿出来说呀!”
“我没有什么说的!”寡妇边哭边说,“要挖,你们把我活埋了就是了!”
“现在是堂堂的党治国家,一切都有法律保障!……”
“有法律就好呀!”
“怎么不好?”白酱丹反问,更加激动起来,“法律不会允许人讲了话不算事!否则还成世界?在法律上,他是应该负责的人了,他不是小孩子!……”
“啊哟!”彭胖插进来了,装着好人,“不必说那么深沉啊!”
“是她要往严重方面说呀!”白酱丹颦蹙着呻吟了,“你是很清楚的,我的本意,是想闹得大家不痛快么?嗯?……嗯?……”
他摊开手臂,皱起眉头,求助似的盯着彭胖,仿佛连话也急得说不清了。但这虽是实情,一半也出于佯装,想叫寡妇感觉得他是在委曲求全。因此,他随即忍气吞声地叹一口气,就又轻言细语地叙述了一番他的访问的动机,仿佛彭胖倒是一个颇识好歹的第三者一样。他说得婉转而使人信服。
“你想吧,”他苦恼地继续说,“这都不算仁至义尽,做人也就难了!”
然而,不管怎样,寡妇的答复,依旧是些不着边际的自怨自艾的断句,一直回避着本题,而且不再进行任何辩解。事情显然是不能立刻得到结果的了。
……
前言/序言
我的传略
沙汀
我生于一九○四年农历冬月十三,原名杨朝熙。四川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改名杨子青。“沙汀”是我一九三二年出版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后改名《航线》)用的笔名。我还用“尹光”这个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一个短篇,并出版过一本名叫《孕》的短篇集。
我父亲是前清的廪生。祖父经历不详,只听说书法方面小有名气。我五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留下约五十亩田产,一座院子。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叔伯们为家产问题把母亲纠缠得很苦。对于县城和县属一些场镇的社会生活,印象也深。因为少小时候,我曾经常跟随我舅父坐茶馆和四处做客,接触过各色各样人物。我只有一个长兄,曾经在地方部队上干过事,早死了。
省师毕业后,我曾经到过北京,准备投考北大。因为听说鲁迅先生已去南方,考期又错过了,遂于当年初冬返回四川。其时北伐军已占领武汉,时间是一九二六年。次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初夏,领导我工作的成都地方共青团的负责人周尚明和其他几位同志在敌人屠刀下牺牲了,白色恐怖日益猖獗,我于一九二九年春,前去上海。因为碰见一些流亡上海的四川同志杨伯恺、任白戈等,后来共同集资组织过一个出版社,叫“辛垦书店”。一九三○年,偶与阔别多年的同班同学汤道耕即艾芜相遇,于是拉他住在一起,共同研究小说创作。因为企图较好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以期有助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又感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未见能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鲁迅先生的回信,就是那封题名《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封信给了我们很大鼓舞。《航线》出版后并曾受到茅盾同志的评介,对我的帮助也令人难忘。
我是一九三二年离开辛垦书店后参加“左联”的,并于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三三年曾一度做过“左联”常委会的秘书。当时的常委有鲁迅、茅盾和周扬诸位。这年秋天,因为反动派大肆逮捕革命同志,我奉命由越界筑路地段转移到旧法租界,因而改任小说散文组组长。前后分别参加过这个组的同志有好几位。最早的是杨刚,叶紫、杨潮(又名羊枣)和杨骚参加的时间较后,都先后逝世了。杨潮是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被蒋匪帮杀害的。欧阳山和草明同我一道工作的时间最久。尽管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我是赞成“国防文学”,他们赞同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是我们照旧时有往来,关系一直都好。
“八一三”爆发后,我回到成都,一面在协进中学教书,一面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做些文学界的统战工作。当地的李劼人和由北方转移到四川的陈翔鹤、何其芳、卞之琳同志等,都是我在那时候结识的。同时也为车耀先所编《大声》写过稿,并一道做过一两次街头宣传,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及至一九三八年将近暑假,看了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后,我感觉在成都待不下去了,在得到组织批准后,决定同我爱人一道到延安去,到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
在得知我将去延安、去前线的消息后,何其芳、卞之琳跑来找我,表示他们也不想在所谓大后方待下去了,强烈要求和我采取一致行动。在我向当地党组织请示后,我们很快就一同去了延安,把我留下的工作,包括我在协进中学教的课程全都留给了陈翔鹤。一到延安,我们都要求看望一次毛泽东同志。在周扬同志的安排下,我们的伟大领袖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并对我们到前线去的要求给以莫大鼓励。此后的经过,我在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悼念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谈得较详,这里不多写了。
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五○年上半年我在成都川西区文联做负责工作,下半年西南局又调我到重庆筹备成立西南文联的工作,后来任西南文联副主任。一九五二年冬奉命同马烽去东德访问。回国后,又奉调来北京任“作协”总会新成立的“创委会”副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一九五五年,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回四川搞创作。但是,由于四川省文联成立时,我已被选为主任,回到四川后仍然没有摆脱行政组织工作。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只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主要是自己没有认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事,尽管行政组织工作对搞创作也有一定妨碍。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锻炼,当然也受到一些“四人帮”的折磨。特别经过三次抄家,我历年收集的创作素材,包括一九三八年夏在晋西北冀中前线所作笔记、日记,几乎失散殆尽。而且,将近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九七六年冬获得解放后,我在《四川文艺》编辑部过组织生活,但未担负任何工作。一九七七年秋写了一个中篇,叫《青坡》。一九七八年二月,省委宣传部任命我做一个筹备恢复“四川文联”和各协会的领导小组成员,随又奉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工作。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发表东西,直到“八一三”后离开上海,我出版了《航线》《土饼》《苦难》和《祖父的故事》四个短篇集。前三个集子作为巴金同志主编的《文学丛刊》,均先后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一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因纸型毁于日本帝国主义“八一三”事变时的狂轰滥炸,实际并未出书。此书是郑振铎同志所编一套创作丛刊之一。
从“八一三”到一九四九年冬四川解放,我先后写了和出版了以下一些散文和长篇、短篇小说。
《记贺龙》,初版本叫《随军散记》。《敌后琐记》,共包含散文十二篇,从各个方面报道了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新面貌,发表时曾遭到反动派的删削,而由于“四人帮”肆虐,连存稿也散失了!幸而经过一位热心肠的同志费时数月,已经帮我查出八篇,并已编入《涓埃集》中。为了反映有关敌后的生活斗争,我还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闯关》。这本东西的出版周折较多,甚至连原稿也被检察机关扣留了,后来由出版单位通过请客送礼,才将原稿取回,并改名《奇异的旅程》,在一家小书店出版。
一九三九年冬从延安返回四川以后,我曾在重庆工作过一年多,于皖南事变后疏散还乡,在县属雎水关生活了七八年,避居在山沟里从事创作。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大部分创作都是暴露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僚、地主如何假抗战之名压榨老百姓、迫害知识分子的。我的三个长篇《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是企图从三个方面来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淘金记》是揭露地主阶级为发“国难财”彼此间的内讧;《困兽记》是揭露反动派对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小学教师的艰苦生活;《还乡记》是一九四四年我奉调去重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返回故乡隐蔽在秀水镇一家锅厂里写成的,主要取材于我在刘家沟写《困兽记》时那段生活经历。我相信,如不学习《讲话》,《还乡记》的思想内容可能更差。
在我蛰居故乡那些年中,我还写过一些短篇,出过两本短篇集:《堪察加小景》和《播种者》。此外还有好几篇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如《医生》《酒后》《炮手》等篇,甚至未曾发表,因为它们是反映蒋政权崩溃前夕四川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斗争的。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选》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祖父的故事》,大体已经将我解放前所写,而自觉尚可保留的短篇,都选入了,共四十篇以上,约占我所作短篇十分之六左右。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修改
用户评价
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的阅读投资。我一直认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经典,不在于它是否迎合了某一时的潮流,而在于它对人性的探讨能否持久地引发共鸣。沙汀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既有北方作家的厚重感,又不失四川文学特有的灵动与细腻。读起来很流畅,但每一句话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千钧之力。特别是关于家族伦理和土地情结的探讨,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我特别推荐给那些对社会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提供的原材料是如此的扎实和鲜活。收到货时,看到这整整十一册,心中涌起一股敬意,这不仅是一套书,更是一座文学的宝库。
评分说实话,我刚开始接触沙汀的作品时,还有些担心会过于沉重晦涩,毕竟那些历史背景对我来说有些陌生。然而,这套文集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他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情节跌宕起伏,让人欲罢不能。比如那部中篇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操控,起起落落,每一次转折都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最让我欣赏的是他对细节的把控,那些日常的琐事、不起眼的物件,在沙汀的笔下都充满了象征意义。阅读的过程像是在剥洋葱,一层层深入,揭示出社会结构下个体的无奈与抗争。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也很有质感,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翻阅起来也是一种享受。对于想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的读者来说,这绝对是一套不可或缺的收藏。
评分我最近一直在寻找那种能够沉下心来慢慢品味的文学经典,这套《沙汀文集》恰好满足了我的期待。与一些追求快节奏和强情节的小说不同,沙汀的文字需要你静下心来,去体会那种缓慢流淌的生活气息。我尤其喜欢他作品中那种淡淡的忧伤,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悲情,而是源于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他描绘的那些乡村生活,虽然充满了艰辛和不易,但其中也蕴含着一种淳朴的美感和生命力的顽强。我常常会暂停下来,回味那些描写劳作场景的段落,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听到镰刀划过稻谷的声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时代,让你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五星推荐给所有热爱深度阅读的朋友。
评分老实讲,我对这套文集的期待值本来挺高的,但实际阅读下来,感受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和复杂。沙汀笔下的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光明与黑暗并存,愚昧与智慧交织。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那种微妙的心理活动,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他都捕捉得极其精准。我甚至觉得,书中的某些人物的困境,在今天的社会依然有着某种隐喻。这不是一本“读完就忘”的书,它会像一枚小小的种子,在你心底生根发芽,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些新的感悟。这套书的体量虽然大,但每一册的阅读体验都是独立的,可以分开来欣赏,也可以合起来感受他宏大的文学构建。
评分这套《沙汀文集》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尤其是那些关于底层人民生活细致入微的描摹,简直是把那个年代的社会百态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我记得有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偏远山村里,人们为了争夺一口井水而发生的纷争,那种生命力在困境中挣扎的韧劲,读来让人心酸又敬佩。沙汀的文字功底确实了得,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堆砌辞藻,而是用最朴实、最贴近生活的语言,勾勒出复杂的人性。他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有血有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矛盾挣扎,都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弦。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仿佛真的走进了那个时代,亲身经历了他们的苦难与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像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值得反复品读和思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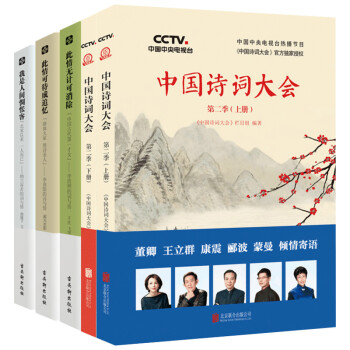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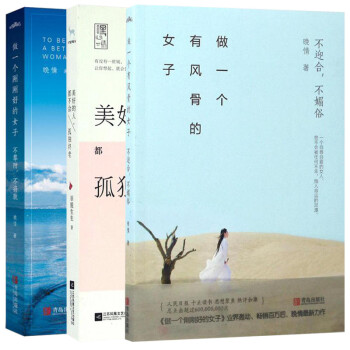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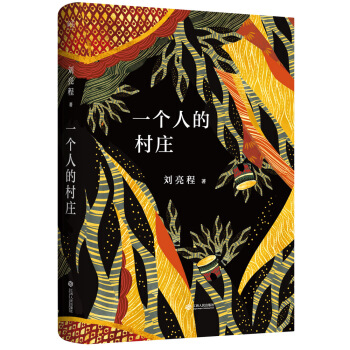

![日本神话故事与传说(戈布尔插图本) [Green Willow and other Japanese Fairy Tal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1439/5a20f14fNa467e79e.jpg)






![蜗牛童话房子 想当星星也可以吗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2064/5a38ba78N173f1ac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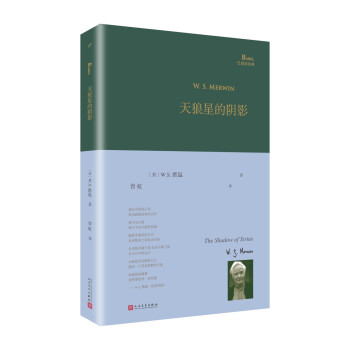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译文纪实)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2619/5a37b094N29c3b34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