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从“二战”前巴黎家庭的起居室到战时法国男男女女的生活,从塞林格式的残忍小事到一九四○年的大溃败,借助“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一位小说家勇敢而敏锐地记录下了时代变局中社会与人心的裂隙。这部短篇集是《法兰西组曲》作者、传奇犹太女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罹难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写给未来世代的文学见证。
内容简介
《星期天》首次出版于二○○○年,共收入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十五篇短篇作品,其*早一篇创作于一九三四年,*晚一篇写成于一九四二年初——同年七月,内米洛夫斯基被捕,一个月后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从战前巴黎家庭的起居室到战时法国男男女女的生活,从塞林格式的残忍小事到一九四○年的大溃败,借助“短篇小说”这一形式,内米洛夫斯基勇敢而敏锐地记录下了时代变局中社会与人心的裂隙。
作者简介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1903-1942),一九○三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随家人移居巴黎,入读索邦大学。一九二九年,她凭借处女作小说《大卫?格德尔》迎来文学上的成功,并就此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巴黎文坛。然而,由于其犹太人身份,尽管她于一九三九年皈依天主教,仍无法获得法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大逃亡之后,她躲在法国东部一个小镇里,后遭法国宪兵逮捕,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二○○四年,内米洛夫斯基的长女将母亲遗物中找到的未完成小说《法兰西组曲》整理出版,获得当年度法国雷诺多文学奖,这是该奖历史上首次颁给一位去世作家。
精彩书评
内米洛夫斯基是懂得如何把灵魂的撕扯和自我的分裂描绘出来的二十世纪作家。我们永远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的存在历程就是试图把分裂的自我整合起来。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迷宫里,写作试图辟出一条认清自我、平息痛苦的道路。——法国作家 劳拉·阿德莱尔
很少有书像《星期天》意义昂扎根于那个时代(1934—1942),其中的十五个短篇小说,从塞林格式的残忍小事到一九四○年的大崩溃,再现了历史的轮廓和细节。
——法国《观点》杂志
内米洛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和她的长篇小说一样,明显受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她对法国社会的犀利观察和对战争围困中的法国的再现,是毫不夸张的。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目录
序言(劳拉·阿德莱尔)星期天
幸福的堤岸
阿依诺
同胞
醉意
血缘
老实人
火灾
陌生人
知己
唐璜之妻
巫术
女魔头
看客
罗斯先生
精彩书摘
拉卡斯街静悄悄的,好似盛夏季节,每扇敞开的窗户上都遮着黄色的帘子。明媚的日子又回来了。这是春天的第一个星期天。暖和、急切、躁动,它催促人们去屋外,去城外。晴朗的天,柔美的阳光。能听见圣克洛蒂尔德广场上鸟儿的鸣唱,带着些许惊讶、慵懒的婉转啁啾,在那些寂静或喧闹的街道上,是出发开往乡间的汽车刺耳的噪音。碧空万里,只有一小片白色贝壳般的游云,曼妙地卷起,飘了一会儿,继而羽化在无垠的湛蓝里。行人抬起头,带着惊喜而信任的表情,呼吸着春风,微笑着。阿涅丝半关上百叶窗:太阳很热,玫瑰盛开得太快,败得也快。小娜奈特跑进来,一蹦一跳的。
“您允许我出去吗,妈妈?天气那么好。”
弥撒已经做完了。在拉卡斯街上,穿着浅色衣服的孩子们已经从门前走过,光着胳膊,戴着白手套,牵着堂区信友,簇拥着一位初领圣体的小姑娘,女孩胖嘟嘟的脸蛋在她的面纱下红扑扑的,她光着的脚踝粉粉的,金黄的,毛茸茸的像只水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但教堂的钟声还在敲响,缓慢而忧郁地,它们仿佛在说:“去吧,善良的人们,多么遗憾我们不能把你们挽留更久。我们已经尽可能久地庇护你们了,但我们不得不把你们还给你们的时代,还给你们的烦恼。现在走吧。弥撒已经结束了。”
当钟声沉寂了,热面包的香味弥漫了街道,从敞开的面包房一阵阵地飘散开来,可以看见面包房里新洗过的瓷砖明晃晃的,镶嵌在墙上的窄窄的镜子在阴暗处泛着幽光。
阿涅丝说:“娜奈特,去看看爸爸是否已经准备好,并告诉娜蒂娜午饭已经上了。”
季尧姆走进来,身上散发着她一直都闻不惯的上好雪茄和薰衣草香水的味道。他比平时更壮,沉稳又开朗。
一坐到桌前,他就宣布:
“我告诉您我午饭后就出发。在巴黎憋了一星期,这至少……说真的,您就不动心吗?”
“我不想撇下小女儿。”
季尧姆笑着扯了扯坐在他对面的娜奈特的头发:前一晚她还发烧了,只是烧得一点都不厉害,甚至没让她水灵灵的肤色变得苍白。
“她病得不重。胃口也很好。”
“哦,她没让我担心,感谢上帝。”阿涅丝说,“我会让她出去待到四点钟。您要去哪里?”
季尧姆脸色明显一黯。
“我……哦,我还不知道……您就喜欢什么事都事先定好……去枫丹白露附近或者沙特尔,随便,爱去哪儿去哪儿……那,您陪我去?”
“要是我答应,指不定他什么表情呢!”阿涅丝思忖。她抿紧的嘴角一抽,露出的微笑让季尧姆有些着恼。但她像往常一样回答:
“家里我还有事要做。”
她心想:“现在又会是谁?”
季尧姆的情妇们。她嫉妒的焦虑,无眠的夜晚。这一切现在都已经那么遥远。他长得又高又壮,有点谢顶,整个身子墩实匀称,头结结实实地支在粗壮的脖子上;他四十五岁,这是男人最强壮、最稳重的年龄,顶天立地,热血澎湃。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颌向前突出,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几乎没有黄垢。
“你啊,”阿涅丝想了想说,“当你笑的时候,你有一副狼、野兽的怪模样。”想必他听在心里觉着说不出的受用。他以前可没这习惯。
她记起以前,每场艳遇终结后他都要在她怀中哭泣,短促的抽泣从他唇上传来,他微张着嘴,好像要把自己的眼泪吮干似的。可怜的季尧姆……
“我呀,我……”娜蒂娜说。
她每次开始说话都这样。不可能从她的思想、她自己的言语中找到一个字眼是不谈论她自己的,总是她的装束,她的朋友,她漏了针的袜子,她的零花钱,她的种种乐子。她是……那么容光焕发。她的皮肤洁白如某些毛茸茸的水果,苍白而有光泽,就像茉莉花、茶花,但隐约又能看到年轻的血在下面涌动,冲到脸颊上,鼓在唇上,像是可以挤出葡萄酒般热烈的玫瑰色汁水。她的绿眼睛神采奕奕。
“她二十岁。”阿涅丝心想,再次努力闭上眼睛,以免被这太明亮太鲜艳的美丽、这爽朗的笑声、这自私、这年轻的热情、这钻石的硬度所刺伤。“她二十岁,这不是她的错……生活会让她变得和其他人一样黯淡、柔顺、平静的。”
——摘自《星期天》
……
前言/序言
作者/劳拉·阿德莱尔(法国作家)首先是孤独。像求生的本能,像被禁锢的快感,像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是一个执意孤独的作家。这种孤独在今天像一个召唤,一种自我升华。
从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知道自己不是母亲所期望的: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束缚在上个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的种种社会规范里,要被调教成贤妻良母,上流社会的女子。不,她是野性的,暴烈的,睁大眼睛看着世界,被一个梦的宇宙所占据。少女时代,她的白日梦越发幽深了:她发现了文学。她不是阅读,而是在吞食。或许在那个时候,她发誓她要成为作家。文字的世界将彻底成为她的世界,学到的文字、潜移默化的文字还有放在自我和世界之间的文字,如同壁垒的文字。
母亲讨厌她痴迷于阅读——“意淫”的堕落的乐趣,这并非出于偶然。母亲早已明白小女孩已经逸出了她的掌控,或者说几乎。
革命的喧嚣,离乡背井,躲在莫斯科的一间公寓里,闭门索居,把自己孤立在阅读中、在一个不愿意明白世界在改变的家庭里,这一切让这个刁蛮少女的个性变得越发孤僻、越发决绝。
在内米洛夫斯基的世界,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氛围:脆弱的和平、模糊的身份、正在消解的行动、濒临堕落边缘的人物、缓慢的退化。内米洛夫斯基的风格就是攫住读者,让他困惑,让他置身危境,一边思忖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捕获,到底哪里才是极限。
她的文风所流露的现代性,尤其是通过纠缠在她所有作品中萦绕不去的主题所维系的,那就是模糊性。形势的模糊,人物的模糊,存在的模糊。内米洛夫斯基是懂得如何把灵魂的撕扯和自我的分裂描绘出来的二十世纪作家。我们永远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的存在历程就是试图把分裂的自我整合起来。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迷宫里,写作试图辟出一条认清自我、平息痛苦的道路。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写作:母亲和犹太性。她并不是从母亲或犹太性的中心出发去写作。不是,而是像一个探索深知其为危险领地的猎人,她尽量去靠近却不不开一枪。她带着内心的恐惧,却从来都不舍弃。或许这就是读者从中获得的乐趣,欣赏她选择猎物的方式,把它们展示给我们看,奄奄一息,虚弱不堪,但永远都不是瘫死在地上。母亲是猎物之皇后:哪怕正当她风华正茂,女儿也把她描写成笨重、严肃、哀怨。是的,可是……女儿永远都不会反抗一位凶狠、不称职的母亲,因为她为人母、为人妻的角色和社会原因举止不得体的母亲。女儿对这位母亲所怀有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她既懂得如何去谴责她的过错——重读《舞会》不难发现——也让读者对这个女人油然而生一丝怜悯:她在自己女儿身上看到自身苍老的迹象和一个竞争对手的诞生。伊丽莎白?吉尔在她写的关于她母亲的杰作《屋顶观景台》中,并没有错综复杂地去描写她祖母的行为,当她和她姐姐,1945年奇迹般地从父母都死在里头的集中营里逃生出来,在波尔多一个地下室被关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回到巴黎,按响了家族唯一的幸存者的门铃:她后来称呼她为狼。狼,童年让我们吓得发抖的大恶狼,那头大恶狼这样回答陪德尼丝和伊丽莎白回来的夫人:“我没有孙女。”夫人坚持着,谈到了伊丽莎白的胸膜炎。狼咕哝着:“有收容穷孩子的疗养院。”
这种对后代的抛弃就像一个预感回响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母女间的斗争,人们总是表面上装出温情的样子,但是面具终究会扭曲。最好是不要说出真相:它总会让人心灵受伤。这里,尤其是在《星期天》和《幸福的堤岸》中,母女间的沉默说明了在命运为她们准备的残酷现实面前谁都不傻。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绝望地想相信自己的幸运之星:她懂得挑战母亲让她忍受的不幸和羞辱,她懂得很快、很强势地让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她寄给一家出版社的第一本小说竟然没有写地址……是有意忘记还是命运的捉弄?出版社不得不刊登了几则启事来找到作者,而当时,她有比看报纸更好的事情要做,她正在照顾她刚刚出生的女儿。
书出版了,成功接踵而至,还有对她的承认。三十年代初就成了文学世界的公主,文学评论大家推崇她的风格,从开篇就惜墨如金的对人物的描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完全契合别人眼中的她的形象:从俄罗斯流亡到法国的作家,的确如此,但她是法国作家。她的身份折磨着她,就像这本集子里面名叫《同胞》的那篇小说中的故事。不容置疑的古以色列人,因此是富有的,但不完全是犹太人。被同化了,她自己这样认为。此外,当她读到布拉西拉赫对她的溢美之词,当她在《甘果瓦》杂志上发表很多文学作品的时候,而这本杂志同时也刊登那些非常反犹的文章,她如何能怀疑这一点?
她女儿说,在她被捕的时候,别人原本给了她逃脱的机会。她回答说:“不要二度流亡。”土地,是法国,她唯一的祖国:法语。少女时代,她以为死者都会还魂:她说得没错。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和伊丽莎白?吉尔的书的再版,都见证了她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用户评价
这本集子简直是夏日午后阳光洒进老旧书房里的味道,那种混合了纸张的陈旧气息和墨水淡淡的香气,让人瞬间沉浸其中。我拿到手的时候,光是触摸到那软精装封面的质感,就觉得心情舒畅了不少,不像有些硬壳书那样给人一种拒人千里的距离感。里面的篇幅设计得极为巧妙,每一篇都像一颗精心打磨过的鹅卵石,圆润、光滑,握在手里(或者说,捧在眼前)时,总能感受到一种恰到好处的重量感和分量。我尤其欣赏作者处理细节的方式,那种不动声色的细腻,比如对一个角色眼神瞬间变化的捕捉,或是对某个场景光影流动的描摹,都显示出一种深厚的文学功底。读完一篇,我常常会合上书,闭目回味好一阵子,仿佛那些文字不仅仅是印在纸上的符号,而是真正活在了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余韵。这绝对不是那种快餐式的阅读材料,它需要时间,需要你放慢呼吸,去细细品味每一句话的内涵和韵味。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暂停键”。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艺术品,放在书架上,它不张扬,却自带一种低调的质感。那“软精装”的处理,使得它既有精装书的耐翻性,又兼具平装书的轻便易携。我试着把它塞进随身的小包里,发现它柔韧度很好,不会像硬壳书那样占用太多空间或硌着手。从内容上来说,这些短篇作品的结构完整性令人惊叹,每一篇都像一个打磨精良的袖珍剧本,开端、发展、高潮、收尾,一气呵成,没有丝毫拖沓。这对于碎片化时间阅读来说简直是完美适配——你可以在通勤路上读完一篇,立刻获得一次完整的阅读满足感,而不是被一堆没头没尾的章节困扰。我很少能在这么短的篇幅里,体验到如此丰富的情感层次,作者对叙事节奏的把控功力可见一斑。
评分我通常对所谓的“精选集”不太感冒,总觉得它们更像是一个出版社的库存清理或者市场策略的产物。但这次的体验完全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这本《星期天》系列,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位资深学者经过数十年沉淀后,才忍痛割爱挑选出来的珍藏。它的跨度很大,涵盖了不同的情绪基调和叙事风格,但奇妙的是,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整体感,仿佛是同一位智慧长者在不同心境下的耳语。阅读它,就像是跟一群有趣且深刻的灵魂进行了一次私密的会面,他们不谈论时髦的热点,只关注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理。我尤其喜欢它带来的那种“被理解”的感觉,好像作者早已预料到了读者在某个瞬间的困惑与挣扎,并用最优雅的文字予以回应。这是一种难得的、能让人感到心灵被抚慰的阅读体验。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断舍离”。我最近的状态比较浮躁,总觉得思绪被各种信息流拉扯得七零八落。然而,一旦我开始阅读这本选集,那种嘈杂感便奇迹般地消退了。它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周遭的喧嚣隔绝开来,只留下文字本身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其中几篇关于“孤独”和“等待”的作品,作者的笔触极其克制,没有过度的煽情,却能精准地击中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读到某些句子时,我甚至会忍不住在脑中“复盘”自己的人生片段,思考那些未曾深究过的情感动机。这种自我对话和反思,是阅读最宝贵的馈赠之一。它不是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你自己去看清自己。对于想提升内心定力和审美品味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值得反复翻阅的良伴。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对“短经典精选”这种标签是抱有一丝保留态度的,总觉得精选出来的东西难免失之偏颇,或者为了凑数而硬塞一些水货。但翻开这本书后,我的疑虑彻底烟消云散了。这里的每一篇选文,都展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它们讨论的主题虽然也许源于过去,但其内核——关于人性、关于选择、关于时间——却是永恒的。更令人称道的是排版和字体设计,那种恰到好处的字号和行间距,简直是对眼睛的一种温柔呵护。我近视度数不低,但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只是感到一种充实,而非疲惫。这种对读者体验的重视,在现今的出版界越来越少见了。感觉编辑团队在筛选和校对上花了不少功夫,几乎找不到任何让我出戏的错别字或排版错误。这让阅读过程无比顺畅,心神完全可以集中在故事本身,而不必被外界的瑕疵所干扰。
评分才气情调俱一流,细读一遍还不过瘾。时而尖锐冷讽,间或悲天悯人,很赞。
评分书已收到,京东快递员很负责任。囤积起来,有时间有心情时慢慢看吧。
评分才气情调俱一流,细读一遍还不过瘾。时而尖锐冷讽,间或悲天悯人,很赞。
评分短经典很好的一个系列,精装本捧在手中感觉更棒。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吧,就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评分包装太差 书都皱了 无奈 只能麻烦换货了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吧,就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评分多搞活动,多囤书,京东又嗨了!
评分实惠值得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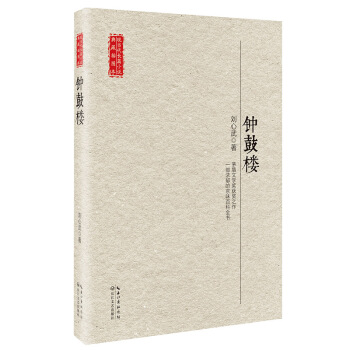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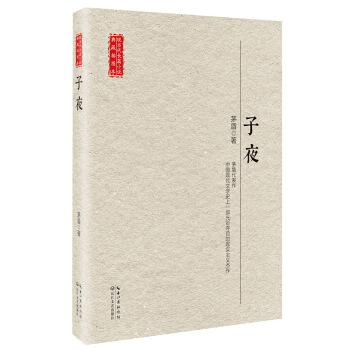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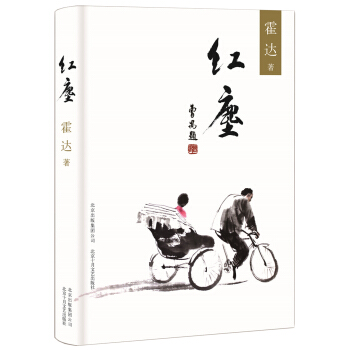







![双身记:一部虔诚的小说 [SECOND BODY Pious novel New expanded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38495/5a24e3c7N15cb691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