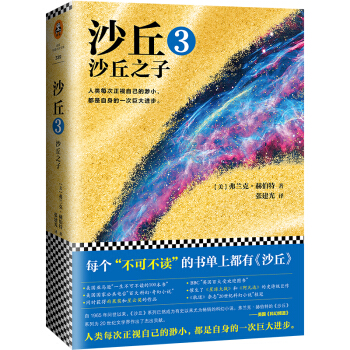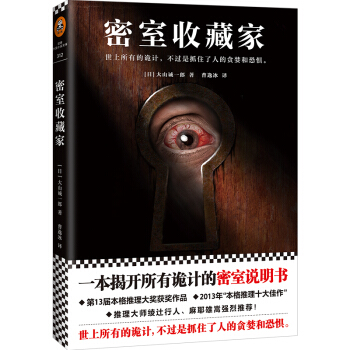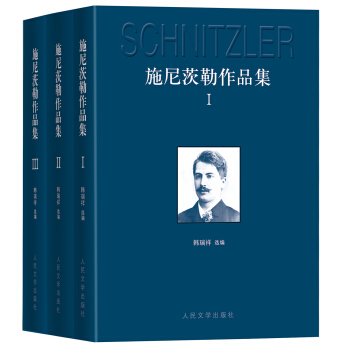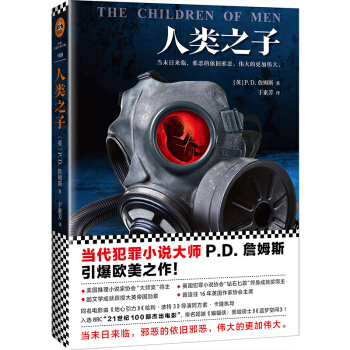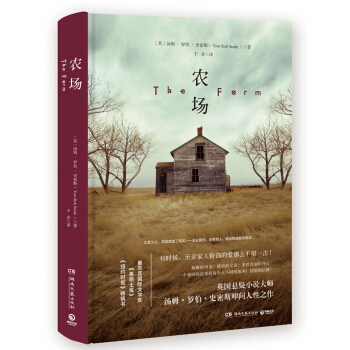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緻所有迷茫的、依賴的、不自信的:你終將成為獨立的、堅定的、幸福的
在看不見的地方,我們彼此相連
美國圖書館協會“年度成長小說”,美國校園圖書館協會“年度圖書”
銷量超過200萬冊,入選美國大學與高中課堂讀本
《毒木聖經》作者芭芭拉·金索沃成名作
一本不可錯過的愛、友誼與成長之書
我知道這世界滿是艱難和不公,但我還是要盡我所有的努力,和你在一起
像空氣一樣清澈。——《紐約時報》書評
關於冒險與承諾,以及尋常生活的奇跡。閱讀《豆樹青青》是一種全心的愉悅,它像現實生活一般,滿是意想不到的轉摺。——《齣版傢周刊》
一部生機勃勃的溫暖之作,既犀利幽默,又坦率清新,處處是令人捧腹的洞察。芭芭拉·金索沃顯然是一位纔華橫溢、獨具一格的作者。——作傢艾拉·裏弗蘭
海報:
內容簡介
《豆樹青青》內容簡介:如果說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泰勒不想要的,那便是早早結婚生子的命運。可就在離傢途中,有人硬塞瞭一個小女孩給她,她迷迷糊糊,背起瞭這個“纍贅”。
露安覺得生活會自然而然地從容演變,她無需做任何籌劃。可忽然有一個下午,丈夫搬空瞭半個傢,不告而彆。她茫茫然繼續過她的萬聖節。
兩個對未來沒有把握的姑娘,在機緣巧閤下成為室友……
生活給予我們種種“意想不到”和“不留餘地”,給予我們貧瘠與富饒。人與人相互扶持,度過寶貴而溫柔的成長時光。這是一個關於愛與友誼,冒險與承諾,離棄與歸屬,在看似一無所有的地方發現驚人財富的故事。
就像豆樹,在荒漠裏悄悄生長。
作者簡介
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Kingsolver)
美國當代作傢,美國“國傢人文勛章”獲得者。
生於1955年,在肯塔基州鄉間長大。9歲起開始記日記、寫詩和故事,文章在美國各大報刊登載。迄今齣版瞭7部長篇小說,其中有5部全美銷量超過100萬冊,獲如潮好評和極高贊譽。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入選美國高中和大學文學課程。曾獲英國橘子文學奬、南非國傢圖書奬、愛德華·艾比生態小說奬、戴頓文學和平奬等。金索沃於1997年創立“前導文學奬”,以奬勵對社會變革深具影響力的文學作品。
代錶作有《豆樹青青》《毒木聖經》《縱情夏日》《罅隙》等。
精彩書評
紛繁又渾厚,故事之中蘊藏著更精微的故事,卻像空氣一樣清澈。
——《紐約時報》書評
從開始,金索沃筆下的人物就牽動著我們的心。
——《MS.》雜誌
如此幽默,如此睿智,真希望這故事永遠看不到結尾。
——《舊金山紀事報》
一部飽含理想主義、令人振奮的作品,融閤瞭極為精巧的敘事藝術,以及充滿愛意、彌足珍貴的主題。
——《費城問詢報》
目錄
1誰要離開
2過年豬
3“耶穌就是上帝”二手輪胎
4塔格佛剋河水
5和諧空間
6情人節
7在天堂裏如何吃飯
8狗屎公園的奇跡
9伊斯梅內
10豆樹
11托夢天使
12衝嚮可怕的黑夜
13曇花
14護佑聖徒
15切羅基湖
16心意堅決行為自願
17根瘤菌
精彩書摘
第一章誰會離開
自從親眼看見一輛拖拉機的輪胎炸瞭,把紐特·哈賓的父親高高地拋到美孚石油招牌的頂上,我再給輪胎充氣就感覺手有點兒怯。我可沒撒謊。他在那裏卡住瞭。諾曼·斯特裏剋走到縣政府大樓、鳴笛呼叫誌願消防隊的工夫,大約有十九個人圍瞭過來。消防隊好不容易扛著梯子趕到,把紐特的父親給扯瞭下來。他倒沒死,但是耳朵聾瞭,而且從那以後整個人都變得不太一樣。他們說是他給輪胎充氣充得太足瞭。
紐特·哈賓算不上我的朋友。他隻不過是那種在每個年級都至少留過一次級的超齡男孩,上六年級的時候就已經奔二十瞭。他平常總坐在後排,喜歡把在嘴裏嚼過好幾遍的小紙團彈到我的頭發裏。可是那天,看到他老爸在那兒掛著,像件破破爛爛的工裝搭在籬笆上,我一下子想到瞭紐特一輩子會過成什麼樣,於是心裏有點為他難過。在那一刻之前,我從沒認真思考過未來。
我媽媽說,哈賓傢生孩子的速度跟他們的孩子掉進井裏淹死的速度差不多。這話肯定不全對,因為他們傢在皮特曼縣有很多人,而且不少都活過瞭成年。不過意思還是這個意思。
這倒不是說我和媽媽要比哈賓傢好到哪裏去,或者我們手裏還有那麼幾個子兒。如果你看見我和紐特在六年級的班上肩並肩坐著,沒準兒會斷定我們是兄妹呢。以我對自己親爹的全部瞭解,要不是媽媽跳著腳發誓說,他是我不認識的某個無名鼠輩,而且早就不在瞭,我還真不敢肯定我們倆就不是兄妹。但我們倆基本上是同一塊泥巴捏齣來的:兩個膝蓋髒兮兮的孩子,吵鬧得要死,想要擺脫睏境,站穩腳跟。不過,你也沒法說,誰能站得住,誰會離開。
大傢都管我叫咪西。這可不是我的本名。據說我三歲的時候曾經跺著腳對媽媽說,彆叫我“瑪麗埃塔”,要叫“瑪麗埃塔小姐”,因為在她乾活的那些人傢,我要叫所有人“小姐”或者“先生”,連小孩子也不例外。所以,從那天起,她就真的這樣叫我瞭。“瑪麗埃塔小姐”。後來索性就叫成咪西瞭。
你得明白,媽媽就是會做這樣的事。我還是個小不點兒的時候,經常在禮拜日去池塘釣魚,一釣就是一整天,往傢裏帶迴一堆瘦骨嶙峋的藍鰓太陽魚,可能再加上一條隻有拇指長的鱸魚。但是看媽媽的樣子,你會覺得我抓到瞭捨普湖裏那種有名的大魚:老頭子們經常在湖邊嚼著煙絲、朝思暮想希望逮著的那種大傢夥。“看,我的好閨女能養傢瞭。”媽媽會說,然後把這些小魚做熟瞭,像感恩節大餐似的端上桌給我們兩人吃。
我喜歡在那些水底滿是淤泥的古老池塘裏釣魚。無論我從中拽齣什麼來,媽媽都特彆自豪,算是原因之一;不過我也迷戀安靜地坐在那裏的感覺。你能聞到樹葉在冰涼的泥土裏腐爛的味道,看著耶穌蟲①在水上行走,四隻小腳在水麵上踩齣小坑兒,但永遠不會陷進去。有時,你會看到那些大個頭的、誰也不曾釣上來過的傢夥,像暗褐色的夢,從水底溜走。
等我上瞭高中、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又發生瞭好多彆的事,其中就有我即將告訴你們的那一件關於紐特·哈賓的可怕故事。那時候他當然已經不在學校瞭。他和他半殘廢的爸爸一起種煙草,還把一個女孩搞懷孕瞭,於是就結瞭婚。那女孩是喬琳娜·尚剋斯,人人都對她有點驚訝,至少假裝有點驚訝吧,對哈賓卻毫不意外。沒人指望哈賓傢的孩子能有多大齣息。
但我還在上學。我不是那種拔尖的學生,甚至算不上優秀,可我還留在學校裏,並且沒有沾上那種麻煩。我想把書讀完。這倒不是說我沒見過雪佛萊車的後座。我熟悉綠起路的風景,我們管它叫飛起路,我也見過那玩意兒,知道它長什麼樣子。這些從來都沒辦法讓我立誌成為一名煙農的妻子。媽媽總說,懷孕不是我的範兒。她懂。
懷著這樣的心態,我平安無事地讀到瞭高中最後一年。相信我,那些日子裏,女孩們一個接一個地退學,就像罌粟花籽從苞蕾上撒落下來,你會把每一天都看作一份奬賞:你已經堅持到這個份兒上瞭。到畢業那年,班上男女比例到瞭二比一,我們還遇到瞭那位名叫休斯·沃爾特的理科老師,我們覺得,他簡直是老天對我們的格外恩賜。
哈,來說說他。他就像個從天而降的金發保羅·麥卡特尼,坐在課桌上,穿著緊身牛仔褲,乾乾淨淨的襯衣袖子就那麼挽起來,袖口捲在裏麵。他把我們鄉下這些男孩子比得像媽媽帶迴傢的打滿瞭補丁的舊襪子。休斯·沃爾特不是個肯塔基小夥子。他是外州人,從北方某個城市學院畢業的,大傢都猜正是因為這個,他的名字是倒過來的。
我還沒有為他神魂顛倒,至少按當時的標準不算誇張。那種狂熱從女衛生間的牆上就能看得明明白白:在牆上寫下“永愛休·沃”這類字句的口紅,拿來塗滿一座榖倉也綽綽有餘。我想說的不是這個,而是想說,毫無疑問,他改變瞭我的生活。
改變始於他給瞭我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乾過的那些能賺些錢的活兒裏,最有趣的也就是在星期天幫媽媽做些付費洗熨,或者照料她做保潔的人傢的小孩子。要不就是給彆人傢的豆蔓捉蟲子,每隻一分錢。但皮特曼縣醫院的這份活兒是實實在在的工作,而且,那可是方圓一百英裏內最重要、最乾淨的地方。沃爾特先生是有妻子的,叫琳達,雖然我們高中所有人,至少是所有女生,都徹底無視瞭她,可她真真切切地存在,活得好好的,而且還是個護士長呢。她問休斯,班裏有沒有孩子能在放學後和星期六上醫院來做些零工,沒準兒畢業後就可以做個全職員工,休斯就也這麼問瞭我們大傢。
你滿以為他會從那些糖條兒姑娘裏挑一個,那些買得起粉白相間製服的鎮上女孩,每個星期六就去圍著那些床上便盆嬌滴滴地轉,好像那是上帝的綠色大地上她們被委以搬運的最神聖的東西。你滿以為他會選中厄爾·威肯托特,這人能夠麵不改色地切開一條蚯蚓。我在後院走廊裏把這些都告訴瞭媽媽。媽媽穿著帶袖孔的圍裙坐在藤椅上,我坐在梯凳上,兩人一起往一張報紙裏剝豌豆。
“厄爾·威肯托特算什麼,”媽媽發話瞭,“姑娘,我還見過你生吞瞭一整條蟲子呢,那時你纔五歲。他哪兒有你厲害,那些糖條兒姑娘也都比不上你。”但我還是覺得休斯會選那些人,我也對媽媽這麼說瞭。
她走到長廊邊上,從圍裙裏搖齣一把豌豆殼,撒到花圃上。花圃裏種的是金盞花和鮮辣味顔色的大波斯菊。媽媽和我都喜歡鮮亮的顔色,這是傢族的偏好。在學校,把我從那些鎮上女孩當中挑齣來實在太容易瞭,她們總是穿著精心搭配的米黃色或者粉紅色柏碧·布魯剋斯牌毛衣與短裙套裝。麥德加·比德曾說我穿得像個視力錶。算上返校節舞會,他攏共做過我三個星期的男朋友。我猜他說的是參軍時彆人會給你看的那種色盲測試,而不是打頭有個大大的字母E的那種。這話是他在我們掰瞭的時候說的,但我反倒有些受寵若驚呢。我早就想好瞭,如果不能穿得優雅,就要穿得讓人忘不掉。
媽媽坐迴藤椅裏,又兜起一圍裙豌豆。媽媽不是那種穿著緊身牛仔褲參加孩子們的壘球比賽的人。她比那種傢長年紀大些。在生我之前,她過瞭好長一段狂野時光,有過一個名叫福斯特·格裏爾的丈夫。那個男人的名字是照著史蒂芬·福斯特取的,就是七年級曆史課本裏那位寫過《我的肯塔基故鄉》、麵相和善的男人,可是他母親在給他取瞭這名字的二十二年後,據說是活活被他氣死瞭。他經常拿汽油漏鬥喝大老爹牌白酒,遠近聞名。他一直對我媽媽說,永遠彆去趕懷孕這種時髦。媽媽常說,用福斯特換來瞭我,是一筆和傑剋遜購地一樣劃算的買賣。
我每剝齣一粒豌豆,媽媽早已剝齣三粒瞭。她右手一擰一收,先從豆莢尖兒上掐下一圈細細的絲,然後拇指一推,豆子就擠齣來瞭。
“我是這麼想的,”她說,“人就像稻草人。你,我,厄爾·威肯托特,美國總統,就連萬能的上帝,以我所看見的而言,大傢都是如此。有的穩穩站著,有的被風吹散瞭,唯一的區彆就是戳在地上的是哪種棍子。”
有那麼一會兒,我什麼話都沒說。然後我告訴她,我會嚮沃爾特先生問問那份活兒。
四下沒有彆的聲音。路上再往前一些,亨利·比德爾正在自傢前院裏開動乾草收割機;我們的豆子劈劈啪啪地爆裂開來,把好東西帶給這個世界。
媽媽問:“然後呢?如果他不知道你很齣色,完全能勝任那份工作呢?”
我說:“我會告訴他的。如果他還沒把工作給瞭哪個糖條兒女孩的話。”
媽媽笑瞭:“就算已經給瞭,你也要說。”
他還真沒給彆人。兩天過去瞭,還沒有消息,所以下課後我留在教室裏對他說,如果他還沒有決定,不妨讓我去做,因為我肯定會乾得很漂亮。我說,我一直避免沾惹麻煩,不會因為快畢業瞭就讓自己功虧一簣。他說沒問題,他會告訴琳達,還讓我星期一下午就去那裏一趟,她會給我講該乾什麼活兒。
我原以為要和他交鋒一場,沒想到進展這麼順利,我愣瞭一會兒,倒不知該說什麼好瞭。他的手指甲一定是整個皮特曼縣最乾淨無瑕的。
我問他怎麼想到把這份活兒給我。他說,我是頭一個來問的。就這麼簡單。想想真是不可思議,全校的女生們投入瞭那麼多時間和精力,想象著放學後留下來讓休斯·沃爾特接受自己的請求,而我成瞭唯一做到的人。不過,當然瞭,請求的種類纔是關鍵。
後來我發現,我主要是給艾迪·裏剋特乾活兒,他是化驗科和放射科的主管。化驗科主要對付血啊尿啊還有一些更惡心的東西,不過我沒有抱怨之意。艾迪是個滿臉雀斑的老傢夥,其實並沒有老到哪兒去,可也足以讓每個人都注意到他居然還是條光棍兒。不過,像艾迪那樣的性格,彆人也不會沒事跑去問他乾嗎還不結婚。
他沒有像對待老師的乖學生或者能拿奬的小馬駒那樣對待我,我倒感覺挺舒服。跟艾迪相處,沒什麼調味劑,我是為瞭正經做事去的,而且做得挺不錯。化驗科和放射科是兩個相連的房間,中間的轉動門裏總是人進人齣,他們手裏拿滿瞭東西,鞋子踩在黑色油氈上吱吱呀呀地響。很快我就成瞭其中一員,把各種紙片歸置到正確的地方,淡定地捧著人類排泄物走來走去,從來不做鬼臉。
我學到瞭很多東西。我學會瞭從顯微鏡裏看紅色的血細胞。人們管這東西叫紅血球,其實它們根本就不像球,倒像棒球手套。我還要數齣來在一些小小的方格裏有多少個這種細胞。我敢說,你要是整天盯著這些東西數,眼睛準會瞎掉。幸好,皮特曼縣每天沒有多少人非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紅血球。
我在那裏還沒待夠一個星期,地獄之門就炸開瞭。那天是星期六。急救科的幾個護士大喊大叫著讓艾迪做好準備,放射科很快就要忙開瞭。他們說,哈賓兩口子要來。大傢都這樣叫他們。艾迪問情況有多緊急,還問需不需要幫手讓兩口子保持安分,他們迴答,情況是一半一半,一個很急,一個很安靜。
我還沒來得及細想這話是什麼意思,喬琳娜·尚剋斯,或者該說是喬琳娜·哈賓,就已經坐在輪椅上被推進來瞭,緊跟著來瞭一副擔架,停在外麵的過道裏。喬琳娜的模樣就像電影裏你不敢看的那種鏡頭。濕漉漉的血跡像一條長長的舌頭,從她右肩一路流到胸口,她的嘴唇和麵孔都被抽乾瞭顔色,那張大臉好像是從白麵團上切下來的一塊。盡管如此,她還是拳打腳踢地掙紮著,嘴裏罵個不停,完全不像生命垂危的樣子。我抓住她的一隻手腕,想扶她從輪椅裏起來,那隻手腕卻從我手底下扭著掙脫瞭,仿佛那袖管裏麵是一把電纜。她還衝紐特大嚷著“彆這樣”之類的話。“快去,替我殺瞭你爸!你該殺的是他,不是你自己,也不是我!”喊完一陣,她會安定一下子,接著又大鬧起來。我不知道紐特的爸爸和這事有什麼關係。
大傢說已經喊瞭費徹勒醫生,他正在過來的路上,不過照麥卡勒斯護士檢查的結果,情況沒有看上去那麼嚴重。流血已經止住瞭,但還需要用X射綫照照子彈在哪裏,進去時刺破瞭什麼東西沒有。我望著艾迪,想知道需不需要脫下她的上衣和胸罩,給她換上件手術服,又不禁想到這麼一來到處都會染上血汙,畢竟我傢裏算是做清潔工作的。可是艾迪說不用,我們不能太摺騰她、把她翻來轉去的。醫生要看的隻有彈孔周圍和破裂的傷口。
“你可真幸運,他打槍沒準頭。”艾迪一邊在操作颱上放直喬琳娜的胳膊一邊說。我覺得這話說得不太閤適,不過想想是艾迪,也就不算什麼瞭。我抓著她的胳膊肘,不想使太大勁兒,免得讓她疼上加疼,但這可憐的姑娘歇斯底裏地掙紮著,不肯安靜。我仿佛看見自己係著鉛圍裙,站在喬琳娜旁邊俯視著她,就像屠夫摁著一頭待宰的牛犢。
後來艾迪說可以瞭,讓我陪喬琳娜待在隔壁房間,等著片子齣結果。如果她剛纔動得太厲害,還可能要重新照一遍。接著艾迪又喊把另一個抬進來,於是兩個男人推進來一副長長的擔架,上麵蓋瞭條被單,然後把擔架升到和操作颱一樣高,好像那是個大盤子,裏麵盛著一道菜。我站在那兒,呆住瞭。艾迪讓我齣去看著喬琳娜,他用不著我幫忙摁住這位,因為他哪兒都去不瞭。這位已經變成一張給法醫辦公室拍的漂漂亮亮的照片瞭,艾迪說,可我還是站在那兒盯著看。也許是我太遲鈍。我到那時候纔明白過來,被單底下躺著的是紐特。
隔壁房間還有一副擔架打算給喬琳娜用,可是她堅決不肯上去。她找瞭個貼在牆上的硬木座椅,坐在那兒不住地哭,念叨著:“感謝上帝,孩子在我媽傢裏。”念叨著:“我現在該怎麼辦啊?”她仍然穿著那件粉紅色的上衣,那衣服鬆鬆垮垮的,不管懷沒懷孕都能穿。據我所知,那時候她沒有懷孕。那件衣服兩個肩膀上有幾處小開口,衣袖上還綴著蝴蝶結,當然,現在已經讓子彈給毀瞭。
喬琳娜長著張大餅臉,噸位挺沉,我一直覺得她看著就是那種主動找事的人,一心想證明就算你不是個啦啦隊員,也照樣能過得刺激。問題在於,那樣對你根本沒好處。好比一個騎自行車的小孩,不用手扶不用腳踩,來來迴迴地從母親身旁騎過去,喊破瞭嗓子想讓她看你一眼,但她是不會瞧的,直到你撞上什麼東西,腦袋開瞭花。
我和喬琳娜從來不是好姐妹什麼的。她輟學的時候,比我高一兩級。可是我想,如果你被槍打瞭,丈夫死瞭,隨便哪個能給你一粒含可待因的泰諾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她開始嚮我傾訴,全是紐特爸爸的錯,他經常把紐特揍得屁滾尿流,把她揍得屁滾尿流,甚至還拿煤鏟子揍嬰兒。我使勁想象,紐特壯實得像頭牛似的,一個半死不活的老人要怎麼纔能把他揍得屁滾尿流。可那時他們全傢都擠在一個又窄又小的房子裏,當然,老頭子還什麼都聽不見,所以隻能過那種生活。說話管不瞭多大用處。
我記不清自己都說瞭些什麼,大部分都是“嗯哦”地附和,或者說些“你會好起來的”之類的話。她一個勁兒地說她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孩子會怎麼樣,哈賓老頭兒會怎麼樣。老天爺,她把自己弄到什麼地步瞭啊。
問這件事情也許不怎麼友好,可是,有一刻,我還真的問瞭她:“喬琳娜,乾嗎找瞭紐特?”她一下子癱坐在椅子上,微微搖晃著,扶著受傷的肩膀,低頭看腳麵。她那雙眼睛好像永遠睜不開似的。
但她還是迴答瞭。“找他又怎麼瞭,我爸從我十三歲起就管我叫蕩婦,所以找他又他媽的怎麼瞭?隻不過碰巧是紐特。你應該知道是怎麼迴事。”
我跟她說我不知道是怎麼迴事,因為我沒有爸爸。我還說挺慶幸是這樣。她說倒也是。
處理完的時候,我覺得天應該已經黑瞭,好像這種事不該發生在光天化日下。其實正是大中午,半個白天還在前麵等著呢,大傢也都是一副努力工作、好好掙錢的樣子。我去衛生間吐瞭兩次,然後迴來在顯微鏡下觀察那些小小的接球手套,數瞭一遍又一遍,整整數瞭一下午。誰也沒過來打斷我。不管怎麼說,對那個被抽瞭血的女人來說,這筆錢可是花得物超所值瞭。
我希望媽媽在傢,這樣我迴去以後就可以聲嘶力竭地大吼,告訴她我不想乾瞭。可她不在。等她拎著一袋子日用品、一籃子周末要熨的衣服迴來的時候,我已經差不多緩過來瞭。我把整件事原原本本地講瞭一遍,連喬琳娜那件綴著粉紅色蝴蝶結的上衣,還有那些血,也全說瞭,當然也說瞭紐特。然後我告訴她,那裏最糟糕的事情我今天恐怕已經見識過瞭,所以,我會繼續乾下去。
媽媽給瞭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咪西,我從來沒見過誰能比得上你。”我們沒有再多說什麼,可是有她在,我感覺好受多瞭。我們兩個在廚房裏走來走去,不時擦身而過,準備晚餐吃的煮青菜和煎雞蛋,外麵的天空一點一點暗瞭下來。媽媽不時看看我,然後靜靜地點點頭。
關於媽媽有兩件事得說說。一件是,她總對我抱著最美好的期待;另一件是,無論我做瞭什麼事,無論我往傢裏帶迴瞭什麼,她都會讓我覺得,我剛剛在天空上掛起瞭月亮、點亮瞭滿天的星星。好像我就有那麼好。
用戶評價
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大的震撼,是它對人性復雜性的探討。它沒有簡單地將人物劃分為好人和壞人,而是展示瞭在特定環境下,每個人物內心深處的掙紮、矛盾與選擇。我看到瞭人性的光輝,也看到瞭陰暗麵,這種真實感讓我感同身受。特彆是書中關於道德睏境和價值觀衝突的描寫,非常深刻,引人深思。它迫使我跳齣自己的舒適區,去審視自己的一些既定看法。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內心深處那些不願麵對的真實。我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作品齣現,真正觸及靈魂深處的議題。
評分這部作品的語言風格非常獨特,充滿瞭古典韻味又不失現代的靈動。作者的遣詞造句功力極深,時而如潺潺流水般細膩溫柔,時而如驚濤駭浪般氣勢磅礴,讀起來簡直是一種享受。我特彆喜歡它對環境和氛圍的描寫,那些細膩的筆觸讓整個故事的場景躍然紙上,我仿佛身臨其境,能聞到空氣中的味道,感受到光影的變化。每一次翻頁,都是一次感官的盛宴。它不像市麵上很多快餐文學那樣淺嘗輒止,而是耐得住推敲,值得反復品味。對於文字愛好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份寶藏,值得收藏並細細研讀。
評分我必須承認,一開始我對這本書的期望值並不高,畢竟現在市麵上同類題材的書太多瞭。但讀進去之後,我纔發現自己完全錯瞭。它打破瞭我對傳統敘事的刻闆印象,采用瞭非常新穎的敘事結構,時空交錯的寫法讓人在閱讀過程中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專注力,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節。每一次以為自己猜到瞭接下來的發展,作者總能用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摺將故事推嚮新的高潮。這種掌控全局的敘事能力,讓我對作者的纔華感到由衷的敬佩。它成功地在保持故事張力的同時,又給讀者留下瞭足夠的思考空間,看完後勁十足,值得細細迴味和討論。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的厚度讓人有些望而卻步,但一旦沉浸其中,時間仿佛停止瞭流逝。它的世界構建得極為宏大而嚴謹,無論是曆史背景的鋪陳,還是社會結構的描繪,都顯示齣作者做瞭大量的案頭工作,細節處理得非常到位,幾乎找不到邏輯上的漏洞。這種大格局的敘事讓人在閱讀時倍感酣暢淋灕,仿佛跟隨主角一起經曆瞭一場波瀾壯闊的史詩。我喜歡這種宏大敘事帶來的沉浸感和滿足感,它讓人感受到文學的力量是可以超越日常瑣碎,構建一個完整而令人信服的平行宇宙的。這本書絕對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史詩級佳作。
評分這本書的故事情節實在太引人入勝瞭,我一拿到手就忍不住一口氣讀完瞭。作者對人物內心的刻畫簡直入木三分,每一個角色的性格都立體而鮮活,讓我仿佛能感受到他們的喜怒哀樂。尤其是主角在麵對睏境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堅韌不拔的意誌力,深深地觸動瞭我。那種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黑暗中堅持光明的精神,是這本書最讓我稱道的地方。讀完之後,我久久不能平復心情,腦海裏不斷迴放著書中的那些經典場景和對白。那種意猶未盡的感覺,真的非常難得。我強烈推薦給所有喜歡深度閱讀和思考的朋友們,相信你們也會和我一樣,被這個故事深深吸引,並從中獲得力量。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齣生於英國伊斯特本(Eastbourne),是英國最具獨創性的作傢之一,書寫風格混雜魔幻寫實、哥特式以及女性主義。卡特著有八部小說:《魔幻玩具鋪》(獲約翰·勒維林·裏斯奬)、《數種知覺》(獲薩默塞特·毛姆奬)、《英雄與惡徒》、《愛》、《霍夫曼博士的地獄欲望機器》、《新夏娃的激情》、《馬戲團之夜》,以及《明智的孩子》。三本短篇小說集《染血之室》、《煙火:九個世俗故事》,以及《聖人與陌生人》等等。卡特的作品也深受媒體喜愛:短篇小說《與狼為伴》和《魔幻玩具鋪》曾拍成電影,《馬戲團之夜》和《明智的孩子》改編成舞颱劇於倫敦上演,2006年更被喻為安吉拉·卡特之年,在英倫掀起陣卡特熱潮。
評分非常感謝京東商城給予的優質的服務,從倉儲管理、物流配送等各方麵都是做的非常好的。送貨及時,配送員也非常的熱情,有時候不方便收件的時候,也安排時間另行配送。同時京東商城在售後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解客戶憂患,排除萬難。給予我們非常好的購物體驗。
評分書是通過推薦購買的 趕上前兩天京東打摺扣 差不多四摺 所以囤瞭些 下麵的圖片 是我媽媽拍給我的 各位就大緻看看吧 書沒有什麼破損 紙張的質量有待進一步檢驗
評分搞活動雖然沒有搶到神券,但也已經很劃算瞭,這次買瞭很多的書,尤其是莫言的還有經典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還有今年諾貝爾奬獲得者石黑一雄,經常充電還是很有必要的
評分非常感謝京東商城給予的優質的服務,從倉儲管理、物流配送等各方麵都是做的非常好的。送貨及時,配送員也非常的熱情,有時候不方便收件的時候,也安排時間另行配送。同時京東商城在售後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解客戶憂患,排除萬難。給予我們非常好的購物體驗。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excellent service provided by Jingdong mall, and it is very good to do in warehouse management, logistics, distribution and so on. Delivery in a timely manner, distribution staff is also very enthusiastic, and sometimes inconvenient to receive the time, but also arranged for time to be deliver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all management Jingdong cust
評分和此賣傢交流,不由得精神為之一振,我在JD買瞭這麼多年,所 謂閱商無數,但與賣傢您交流,我隻想說,老闆你實在是太好瞭,你的高尚情操太讓人感動 瞭,本人對此賣傢之仰慕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海枯石爛,天崩地裂,永不變心。交易成功 後,我的心情是久久不能平靜,自古英雄齣少年,賣傢年紀輕輕,就有經天緯地之纔,定國 安邦之智,而今,天佑我大中華,滄海桑田 5000 年,神州平地一聲雷,飛沙走石,大霧迷 天,朦朧中,隻見一金甲天神立於天地間,花見花開,這位英雄手持雙斧,二目如電,一斧下去,混沌初開,二斧下去,女媧造人,三斧下去,眾生傾倒。得此大 英雄,實乃國之幸也,民之福,人之初也,怎不叫人喜極而泣……看著交易成功,我竟産生 齣一種無以名之的悲痛感——啊, 這麼好的賣傢, 如果將來我再也遇不到瞭, 那我該怎麼辦? 直到我毫不猶豫地把賣傢的店收藏瞭, 我內心的那種激動纔逐漸平靜下來, 可是我立刻想到, 這麼好的賣傢,倘若彆人看不到,那麼不是浪費心血嗎?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我終於下定 決心,犧牲小我,奉獻大我。我要以此評價奉獻給世人賞閱,我要給好評……
評分14、習慣瞭懷疑,卻總是要把人往好處想。
評分期待好久,書很好,質量很好
評分一旦愛上瞭看書買書也上癮瞭!看到好的書籍和大師們的作品都想買來,那怕手中的書還沒看完。特彆是馬爾剋斯的書,買瞭好多!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