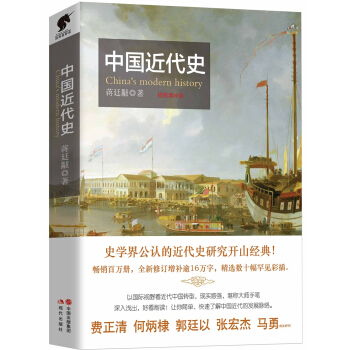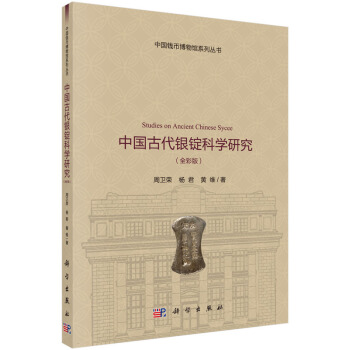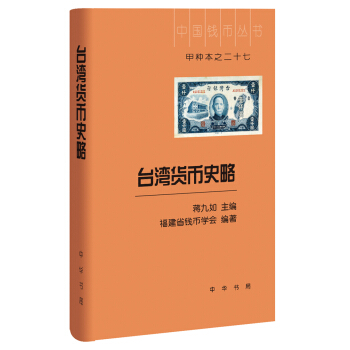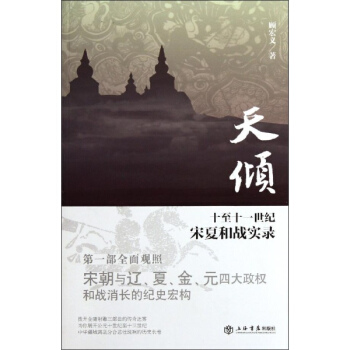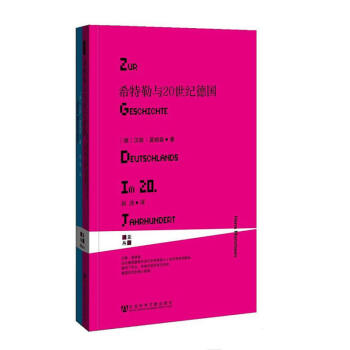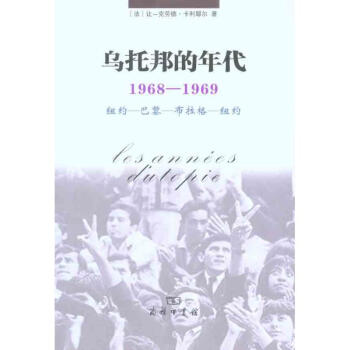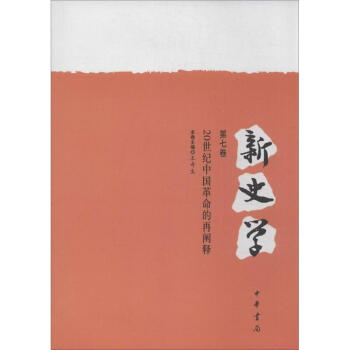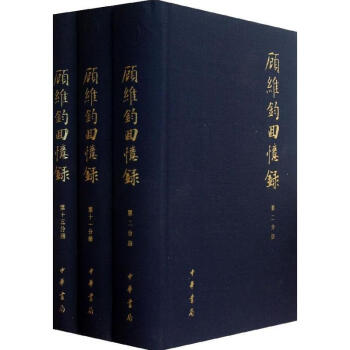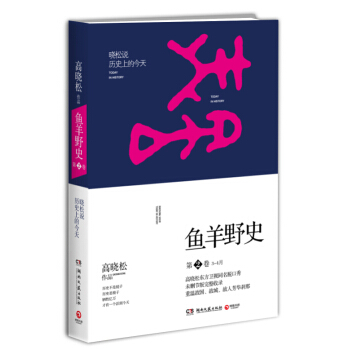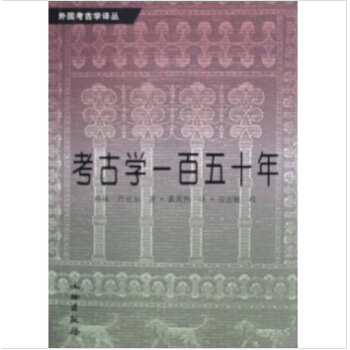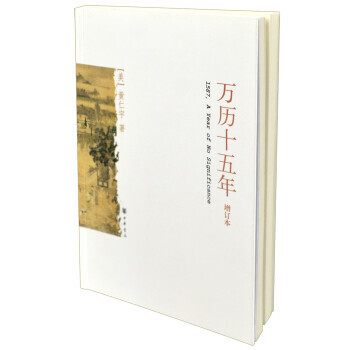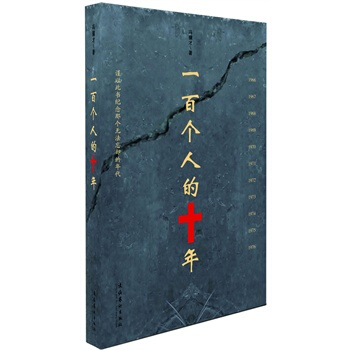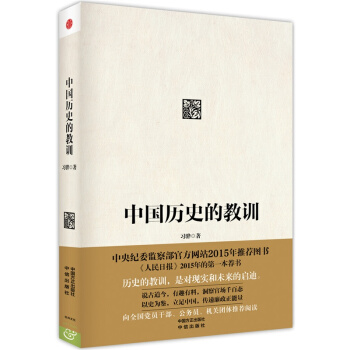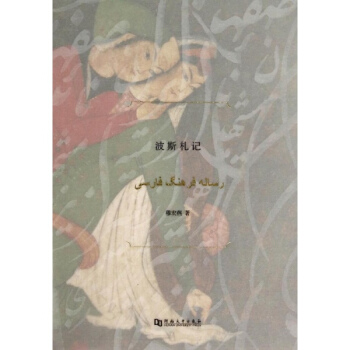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西域史、明史、中西交通史、民族史、亚欧大陆交流史、丝绸之路研究人员,“一带一路”政策执行者,地方志机构工作者,高校历史学、边政学民族事务治理学、历史地理学等方向师生、文史爱好者辑录前人未曾利用过的罕见资料,增补学者近年所得的zui新研究,大家著作修订再版。
浏览明代西域地方政权概况的全景视窗,填补哈密吐鲁番地区文明空白的鸿篇巨制。
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觅史料,用严谨专业的态度考证历史,明代哈密与吐鲁番地区史料的zui全汇总。
内容简介
本书是14世纪到17世纪时期明代哈密、吐鲁番地区资料汇编,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风土人情、地理概貌, 还反映了当时中央政权与哈密、吐鲁番地方政权之间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密切关系。本书为修订再版,此外,除了改正错讹外,作者在原作基础上又新增补了一批资料,同时将所写《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一文作为附录收入,对土鲁番的概况、统治者世系及其与明朝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丛书简介: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急起直追。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体现在成果发表方面则为: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不但chao越了单纯的再版,借此也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者简介
陈高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历史所宋辽金元研究室副主任、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兼攻明代史、中国绘画史、中外关系史。代表作为《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元大都》。
目录
第一部分 传记
一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
二 《明史》卷三百三十
第二部分 编年
一 明洪武时期(1368-1402)
二 明永乐时期(1403-1424)
三 明洪熙时期(1425)
四 明宣德时期(1426-1435)
五 明正统时期(1436-1449)
六 明景泰时期(1450-1456)
七 明天顺时期(1457-1464)
八 明成化时期(1465-1487)
九 明弘治时期(1488-1505)
十 明正德时期(1506-1521)
十一 明嘉靖时期(1522-1566)
十二 明隆庆时期(1567-1572)
十三 明万历时期(1573-1619)
十四 明天启时期(1621-1627)
十五 明崇祯时期(1628-1644)
第三部分 其他资料
一 《大明会典》(节录)
二 《大明一统志》(节录)
三 《高昌馆课》
四 《写亦虎仙供词》
五 《西域行程记》(节录)
六 《西域土地人物略》(节录)
七 《哈密分壤》
八 《进哈密事宜疏》
九 《论土鲁番入贡事》
十 《甘肃边论略》
十一 《筹边疏》
十二 《议处夷情以固边防疏》
十三 《应诏陈言边患疏》
十四 《继世纪闻》(节录)
十五 《哈密志》
十六 《肃镇华夷志》
附录 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
引用书目
索引
精彩书摘
附录 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
明代,我国西北新疆地区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其中,土鲁番政权势力较大,与明朝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关于这一时期土鲁番政权的状况,迄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本文拟就搜集到的汉文资料,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土鲁番地面的土地和人口
唐代后期,回鹘西迁,其中一支迁到今新疆东部,占有高昌(今土鲁番)、别失八里(今吉木萨)等地,史称高昌回鹘。12世纪末13世纪初,通称高昌回鹘为畏兀儿,畏兀儿王称为亦都护。此时,别失八里是畏兀儿亦都护居住之所。畏兀儿一度臣服西辽,蒙古兴起后,转而归顺成吉思汗,成为大蒙古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概在13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亦都护已由别失八里迁居哈剌火州(即高昌)。忽必烈称帝,改国号为大元后,西北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诸王接连举兵反抗,哈剌火州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地区,连年遭受兵祸。亦都护被迫内迁永昌(今属甘肃)。14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元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对哈剌火州的控制。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葡萄酒”。自此以后,迄止元亡,文献中再不见有关哈剌火州的记载。
明朝建立(1368)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剌火州不曾与明朝发生直接的联系。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遣使前往别失八里,途经土鲁番、哈剌火州、柳陈三城,“赐其王采币”。土鲁番、哈剌火州、柳陈三城,都属于前代的哈剌火州地区。土鲁番城即今土鲁番县所在地,哈剌火州在土鲁番城东一百里,柳陈则在火州东七十里。 c 自此以后,土鲁番等三城不断遣使入贡。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遣李达、陈诚等护送中亚哈烈等处使臣还国,途经上述三城。据陈诚记述,土鲁番“城方一二里,居平地中”。“广有屋舍。信佛法,僧寺居多。”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惟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柳陈“城方二三里”。这时的哈剌火州与前代的哈剌火州显然是同一个地方,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它已趋于萧条衰落了。土鲁番则是这一时期新兴的居民点,前代未见记载,但是当时规模并不大。陈诚等还说,这“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有为回回体例者”,“有为畏兀儿妆束者”,“方音皆畏兀儿语言”。可见,当地主要是畏兀儿人。所谓“为回回体例者”,应指畏兀儿人中信奉伊斯兰教者,所谓“为畏兀儿妆束者”,应指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畏兀儿人,他们中有很多是佛教徒。 e 还值得注意的是,据陈诚等说,鲁陈、火州、土鲁番三地,并非独立的地方政权,它们当时都在别失八里政权的“封域之内”。别失八里政权的统治者是元代察合台系宗王的后裔。鲁陈、火州、土鲁番三地的首领也应该是察合台系宗王的后人。
别失八里王歪思汗(1418—1428年在位)西迁到伊犁河流域,自此改称亦力把里。歪思汗死后,其属部分裂。土鲁番逐渐强大,在15世纪中叶,吞并了柳陈(鲁陈)、哈剌火州二处,然后把目标指向哈密。哈密是受明朝直接管辖的藩属,其首领是元朝贵族豳王纳忽里的后裔,被明朝封为忠顺王,“给与印信,掌管哈密城池”。15世纪上半期,哈密受到瓦剌等游牧部落侵扰,势力逐渐衰弱。天顺四年(1460),忠顺王卜列革卒,无子,由王母弩温答失里主事,内部更加动荡不定,“国无其主,众叛亲离”。土鲁番首领速檀阿力乘机多次“引兵劫掠哈密诸部地,已略尽”。到了成化九年(1473),便攻破哈密,执王母,夺明朝赐予的金印,留人据守。明朝政府闻讯,立即遣李文、刘文二人到甘州(今甘肃张掖),策划恢复。第二年,李文等派遣千户马俊到土鲁番,“往谕速檀阿力,俾还哈密城,及归王母”。马俊的使命并未成功,但对土鲁番的情况有所了解,据他回报说:“速檀阿力所部精兵不过三百,马步兵不满二千”。依此估计,这时土鲁番全部人口估计不到万人。哈密地区的居民为数更少,估计不过三四千人。
成化十八年(1482),明朝组织力量,支持哈密首领罕慎夺回哈密。但罕慎在哈密的统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速檀阿黑麻以结亲为名,将他诱杀,哈密再次为土鲁番占有。四年(1491),速檀阿黑麻将哈密城和金印献还明朝,明朝政府从河西安定卫选择蒙古贵族后裔陕巴(与原哈密王室有亲属关系),立为忠顺王,镇守哈密。弘治六年(1493),阿黑麻又发兵攻占哈密,执陕巴去。明朝政府派遣张海等前往甘肃处理这一事件。弘治七年,张海上安边方略七事,其中谈到了土鲁番的情况:“今访之,土鲁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营者三,小如堡者十六。戈甲不满三百,兵马不满三千。亲党俱亡,止兄一人,与相仇杀。左右亲者十一人,与治国事。”这里所说的“土城大如营者三”,应即土鲁番、哈剌火州、柳陈(鲁陈)三城。而所谓“戈甲”,显然就是上面马俊所说的“精兵”,“兵马”则应是马俊所说的“马步兵”。二十年前,“马步兵不满二千”,此时则“不满三千”,说明在此期间已有所增加。
16世纪20年代,土鲁番速檀满速儿进攻甘肃,号称“二万骑”。 这次事件使明朝政府大为震动,痛感有了解土鲁番情况的必要。大臣桂萼“以平日所闻,参互考证”,并且“数以质之前在陕西实心经理其事者”,写成材料,呈报皇帝。据他说:
一, 回夷(指土鲁番—引者)疆土。东至哈密界六百里,西至曲先有七百里,南北相去约有百里。北山后为瓦剌达子,南山后为番子。大小城堡共有十五六座,每堡一头目掌管。速檀满速儿居一土城,周围约有二百里(“百”字疑衍—引者),南北土门两座。城北墙有高土台一个,阔数丈,名曰土剌,速檀王子居于其上。台上有吊桥,夜则悬之。城郭内外俱有居人,烟火林木宛如中国。
二, 回夷部落。其部下男女约有一万余人,除老弱,其余可以上马挽弓者止六七千人。秋冬居城郭,春夏随水草孳牧,或各山川种田,或打围射猎。速檀亦不时出猎,其妻皆随之。
大概与桂萼同时,另一位大臣李承勋在奏疏中也说:
其土鲁番国势,昔有人自其国逃来言:彼国都东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人以种植、田猎为业。帐族散处,每帐能战者三分之一,通国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数月而后合。
桂萼和李承勋所说的情况大体是相同的。从他们所述看来,这时土鲁番的全部人口不到两万,其中可以用来作战的不过三分之一,即五至七千人。那么,上面提到满速儿率领的“二万骑”又从何而来呢?当时已有人指出,土鲁番“势驱沙、瓜,姻连瓦剌,借名诸番,拥众二万”。 除了土鲁番人之外,还包括哈密以北的瓦剌人,沙州(今甘肃敦煌)罕东左卫所属的帖木哥、土巴部,以及瓜州(今甘肃安西)的一些部落。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从15 世纪末到16 世纪20 年代,大约三十年左右时间内,土鲁番可以用来作战的土兵增加了一倍,由不满三千增加到六七千人。可以推知,土鲁番全体居民人数增加的比例大致也应是如此。土鲁番人口的这种增长速度,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增殖的结果,而应是不断发动战争兼并、掳掠的结果。而人口的增加,对于土鲁番首领的对外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在15世纪下半叶,土鲁番只有二三千名可用来作战的士兵,只能侵扰、掠夺邻近的哈密;到了16 世纪上半期,它的武装力量增加了一倍,因而就敢于裹胁其他部落,远道向甘肃进犯了。
了解土鲁番疆域的人口,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土鲁番的发展及其与明朝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过去有不少记载对土鲁番的人口做出了夸大的结论。例如,明代史家王世贞说:“土鲁番,强番也,控弦可五万骑。” c 这个说法与事实相去太远。固然,速檀满速儿在进攻甘肃时曾经声言:“会众番王备下人马五万又有五千至此。”但一则是虚声恫吓,数字定有夸大;二则明言“会众番王”,并非土鲁番一家的人马。因此,是不能据此断言土鲁番有五万骑兵的。现代有的著作说速檀阿力时土鲁番即有“军队五万人”, 不知何据。前面我们征引的官方报告说明,速檀阿力“马步兵不满二千”,“五万人”之说是无法令人置信的。
二、土鲁番速檀的世系
永乐五年(1407),土鲁番地面三城首次入贡,哈剌火州的首领是王子哈散,土鲁番是万户赛因帖木儿,柳陈是万户瓦赤剌。显然,哈剌火州的首领是伊斯兰教徒,土鲁番和柳陈的首领尚保留元朝的官衔,还不是伊斯兰教徒。
15世纪中期,土鲁番强盛,兼并哈剌火州、柳陈,其首领也密力火者“遂僭称王”。从这个首领的名字来看,大概是一个伊斯兰教徒。15 世纪60年代,土鲁番首领阿力自称速檀(Sultan),这是伊斯兰国家中君主的称呼。也密力与阿力交替的准确年代,尚难确定,但至晚在成化五年(1469),阿力已成为土鲁番的首领了。在速檀阿力统治时期,发生了第一次土鲁番兼并哈密事件。
成化十四年(1478),速檀阿力死,子阿黑麻承袭。阿黑麻既称速檀,又称可汗, 同时采用两种称号。这说明他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阿黑麻“亲党俱亡,止兄一人,与相仇杀”。他的兄长速檀马黑麻,与明朝往来甚少。在速檀阿力与速檀阿黑麻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速檀兀也思王”,也可能和阿黑麻即是一人。在阿黑麻统治期间,土鲁番势力有所发展,发生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侵吞哈密事件。
弘治十七年(1504),阿黑麻死,长子满速儿嗣立。满速儿兄弟五人(一说四人),同母弟把巴乂(一译把巴歹),异母弟一名忍帖木儿,一名真帖木儿,另一不可考。 i 真帖木儿一度被明朝拘留于甘州,后遣还。把巴叉占据阿速城(今新疆阿克苏)。明朝第二次恢复哈密,立陕巴为王。陕巴死后,子拜牙即嗣立。正德八年(1513),拜牙即投奔土鲁番,即被安置于“阿速城速檀满速儿之弟把巴歹之所”。把巴乂与满速儿之间“兄弟不和”,明朝政府曾“宣谕”把巴乂,要他将拜牙即“送回本国”,但这道敕书及赏赐只能由“土鲁番进贡头目同哈密都督头目”赍往阿速城开读,显然,这是满速儿从中阻挠,故意不让把巴乂直接与明朝发生联系。据记载,把巴乂与满速儿之间不和,是因为他“嗔伊兄(指满速儿—引者)做歹,把金路断了”。所谓“做歹”是把满速儿屡次用兵,以致明朝宣布闭关绝贡,停止中原与新疆地区的贸易往来。“金路”就是指贸易的路线。除了把巴乂据有的阿速之外,满速儿还曾“调察力失人马,要来汉人地面”抢掠。察力失在土鲁番之西,即今新疆焉耆。据此,则察力失与土鲁番亦有隶属关系。嘉靖十六年(1537),严嵩说:“自土鲁番到乂力失六、七百里,即汉之盐泽,皆土鲁番种类。”说明当时明朝政府就把察力失(乂力失)看成土鲁番政权属下的一部分。桂萼说把巴乂“居察力失城,在吐鲁[ 番] 城之西,约有四五百里,其部下约有一二千人”。 这与其他记载(把巴叉居阿速城)不符,也许他先居察力失后居阿速,也许是误传,但在满速儿统治时期察力失和阿速均属土鲁番政权,看来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在16 世纪上半期,土鲁番的势力是相当大的。
嘉靖二十四年(1545),“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嘉靖四十四年(1565)或四十六年(1566)初,“沙速檀潜掠北虏(指瓦剌—引者)部落,中流矢死。马速其弟也,拥众嗣立”。但是,马速在位时间并不长,隆庆四年(1570),速檀马黑麻“因旧土鲁番马速[ 与] 已故沙王子是远房伯叔,不该做王子,伊兄弟系亲支,该做土鲁番[ 王子],把马速王父子俱绑在牙儿坎地方去了”。马黑麻自己成为土鲁番统治者,向明朝进贡。牙儿坎即今新疆莎车。这个新上台的速檀马黑麻有兄弟九人,其中同时向明朝进贡的还有速檀琐非、速檀虎来失、速檀阿卜撒亦三人。速檀马黑麻夺得统治权后,土鲁番王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未了结,万历三年(1575),“土鲁番酋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新立为王”,遣使向明朝进贡。派来的使者火者马黑木报告说:“先年土鲁番王沙速檀病故,将叔伯弟速檀马速立为王,并弟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俱在土鲁番住坐。后被牙儿坎地方叔伯弟琐非速檀等兄弟四人领人马来到土鲁番,强占为王,伊将旧王马速并弟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二人,俱绑往迤西撒马儿罕地方去了。将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丢在撒马儿罕,把他哥哥马速着往水西阳地方远处去了。将琐非速檀第三的弟马黑麻在土鲁番为王坐了四年有。土鲁番守城头目们因马黑麻为王不仁,众人商量要害他。马黑麻听见了,自家回往牙儿坎地方去了。众人打听着,才把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打撒马儿罕取着来立王。”
这段记载非常宝贵。从中可以看出,隆庆四年(1570)自立为王的速檀马黑麻兄弟,来自牙儿坎地方。他们是速檀沙的叔伯兄弟。前面已经说过,土鲁番的满速儿与镇壇守阿速的把巴乂是亲兄弟,阿速与牙儿坎相去较近,很可能速檀马黑麻兄弟就是把巴乂的后人,故与速檀沙是叔伯兄弟。而马速则应是满速儿另一兄弟的后人。马黑麻绑走马速自立为王,主要理由是“伊兄弟系亲支”,后来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为王,理由也是“原系土鲁番王亲支,先被马黑麻强占为王,将伊兄弟逐害”。 c 他们都以土鲁番王室“亲支”自我标榜,其实血缘关系应是一样的。由此看来,至少在16 世纪(甚至更早)南疆各割据地面的首领,大都有亲属关系。此外,马速被绑送撒马儿罕等地,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撒马儿罕地区的统治集团与南疆各割据地面的首领们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
《明史? 土鲁番传》说:“嘉靖二十四年,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隆庆四年,马黑麻嗣兄职,遣使谢恩。其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遣使来贡。”这段话是很含糊的。首先,在速檀沙之后根本没有提到速檀马速,这样很容易使人理解为马黑麻直接继承速檀沙的王位,例如《维吾尔史料简编》(上册,第137 页),就是如此。第二,这段话也容易使人将嗣位的马黑麻和原来占据哈密的马黑麻视为一人。其实,前者是速檀琐非的兄弟,与速檀沙是叔伯兄弟;后者则是速檀沙的叔伯兄弟。二者名字相同,但并非一人。
速檀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在位的时间不长。万历七年(1579),“土鲁番速檀阿卜纳西儿阿黑麻袭立为王”。新速檀与原速檀之间是什么关系,无记载可考。万历十一年(1583),又换了一个新速檀:“土鲁番速檀马黑麻虎答遍迭新立为王。” 万历二十年(1592),土鲁番王哈剌哈失进贡。 万历二十二年(1594),“土鲁番速檀阿黑麻王等五十九王各遣使贡马乞赏,土鲁番速檀虎答遍迭等五十二王各遣使贡诸方物乞赏”。按,嘉靖二年(1523)、八年(1529) 起,“ 土鲁番称王号者始多至十一二人”。嘉靖十二年(1533),竟多至七十五王。这是因为明朝对使巨人贡的人数有限制,所以用多立名号的办法,多派使臣,多得回赐和更多地进行贸易。明朝政府不得不加以限制,规定“每国称王只准一人,余俱作头目字样”。但事隔六十年,土鲁番称王者竟达一百十一人,而明朝政府也改变过去的态度,加以承认。这时土鲁番的真正统治者应是阿黑麻或虎答遍迭,也许是两人并列,处于分裂状态。此后,天启元年(1621),“土鲁番王阿都剌因遣使进玉石、钢钻等方物”。这是见于明代记载的最后一个土鲁番速檀。崇祯十一年(1638),土鲁番仍入贡,但其速檀名字不见记载。《明史? 土鲁番传》终于隆庆四年马黑麻入贡,对以后的土鲁番速檀名字,均失记载。有的研究著作更断言马黑麻速檀“以后世系不明”,这是沿袭《明史》之说未加考究之故。
这里顺便说一下土鲁番的政权组织情况,从现在一些记载看来,土鲁番的政权组织是相当简单的。前面已经提到,在速檀满速儿统治时期,整个土鲁番地区“大小城堡共有十五六座,每堡一头目掌管”。各堡头目之上,便是速檀。土鲁番不过一万余人,各城堡头目所管辖多者千余,少者数百。这就是说,速檀和各城堡头目,组成了土鲁番的统治集团。在此以前,阿黑麻速檀时“左右亲者十一人,与治国事”,这十一人也应即是各城堡的头目。此外,满剌(伊斯兰教士)也有很大的势力,除了偷盗和打死人的案件由速檀处理外,“其争斗及犯奸者告满剌处责治”。显然,当地通行的是伊斯兰法典。但是当时教权与政权还是分离的。
前言/序言
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对于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来说,发掘整理有关的文献资料,更是重要。我们编辑这本资料,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新疆历史研究的开展。
百余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新疆的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明代是个薄弱的环节,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没有得到认真的发掘和清理,研究工作的成绩相对来说也要少些。迄今为止,关于明代新疆历史的许多问题,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因此,搜集整理明代新疆的历史资料,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有汉文的,也有其他文字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从明代汉文的各种文献中辑录有关哈密和土鲁番的资料。明代的汉文文献,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们所接触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已经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一)土鲁番内部的状况
明代中叶,土鲁番势力强盛,曾一度对明朝发动过战争。但在有关的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对它的内部状况做过说明,因而也便难以就明朝与土鲁番的关系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这与资料的欠缺是有关系的。其实,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有的。例如,在桂萼的《进哈密事宜疏》和李承勋的《论土鲁番入贡事》(均见本书第三部分)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都有不少的记载。土鲁番政权“东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一说“南北相去约有百里”)。“大小城堡共有十五六座”,“人以种植田猎业”,“秋冬居城郭,春夏随水草孳牧”,“其部下男女约有一万余人,除老弱,其余可以上马挽弓者止六、七千人”(一说“通国一起[能战者] 可五六千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明代中后期速檀满速儿当权时的情况。在此以前,在速檀阿力时,“所部精兵不过三百,马步兵不满二千”。到速檀阿黑麻时,还没有多大发展,“戈甲不满三百,兵马不满三千”。到了速檀满速儿时,如上所说,兵力增加了一倍,再加上威胁其他部落,“势驱沙、瓜,姻连瓦剌,借名诸番”,号称“拥
众二万”。因此,我们看到,在阿力、阿黑麻时,土鲁番只能抢夺哈密,而到了满速儿时,就敢于公开向明朝武装挑衅,要“插旗甘州城门上”了。明代有的记载说土鲁番“控弦可五万骑”,则是靠不住的。速檀满速儿时,土鲁番送交明朝的书信中也只是说“会众番王备下人马五万又有五千至此”,“众番王”指南疆其他封建割据政权。联合起来自吹自夸也不过这点人马,单是土鲁番本身的兵力自然还不及此数。至于有的研究著作说速檀阿力时即有“军队五万人”,那就更成问题了。
土鲁番军队数量已如上述。值得注意的是,军队不是常备的,而是临时抽充的,“差头目数人,分投于各族抽取”。出战以前召开军事会议,“众论纷纷,取其长者用之”。这些地方都和北方游牧民族差不多。交战时,“有金鼓旗帜,行列部伍,其阵森严整齐”,“ 每战虽败不退,最能持久”。
有的研究著作推测15世纪下半期后,土鲁番居民“当有随着[王室]改信伊斯兰教的可能”,态度是审慎的。现在,根据桂萼所述,土鲁番居民“凡女子十一二岁者,皆从满剌读书写夷字,只礼拜天地,不信佛教”。争斗及犯奸等民事纠纷,“告满剌处责治”。满剌是伊斯兰教僧侣。从这些叙述可知,至迟在16世纪上半期,土鲁番居民均已信奉伊斯兰教。
(二)土鲁番速檀世系
土鲁番地方政权的首领称为速檀,汉文译为王子。对于满速儿速檀以后的世系,有的研究著作列如下表 :
吐鲁番速檀世系表(满速儿速檀以后)
王名 与前王之关系 在位年代 大事
满速儿
沙 长子 1546—1570
1545 年,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
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
马黑麻 弟 1571— 马黑麻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以后世系不明。
这份世系表是以《明史? 土鲁番传》为根据的,其实有不少问题。沙速檀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与瓦剌作战时“中流矢死”的,“拥众嗣立” 的是他的堂弟马速。隆庆四年(1570),马黑麻速檀“因旧土鲁番马速[与]已故沙王子是远房伯叔,不该做王子。伊兄弟系亲支,该做土鲁番[王子]。把马速王父子俱绑在牙儿坎地方去了,亲王子马黑麻做了”。隆庆五年(1571),派遣使臣向明朝进贡谢恩,也就是要明朝政府承认他的地位。马黑麻速檀兄弟九人,琐非速檀是长兄,马黑麻是三弟,随同马黑麻进贡的有琐非等兄弟四人,“兄弟五人,各据一方,自立为王”。所谓“马黑麻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是不准确的。没有多久,“土鲁番守城头目们,因马黑麻为王不仁,众人商量着要害他”,马黑麻惧怕逃走,这些头目们就从撒马儿罕把马速速檀的弟弟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取着来立王”。这大概是万历二年(1574)的事。万历三年(1575),这位新速檀又遣使进贡谢恩。在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之后,相继嗣位的土鲁番速檀还有阿卜纳西儿呵黑麻(万历七年进贡)、马黑麻虎答遍迭(万历十一年进贡)、哈喇哈失(万历二十年进贡)、阿黑麻、虎答遍迭(万历二十二年进贡)、阿都剌因(天启元年进贡)等。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上引速檀世系表是有重大缺陷的,它既忽略了沙速檀与马黑麻速檀之间的马速速檀,又武断地断言马黑麻“以后世系不明”。现在根据有关的奏疏,与《明实录》相参证,可以对明代后期土鲁番速檀世系有更多了解。
弄清楚土鲁番速檀的世系,可以增加对土鲁番内部政治状况的认识,而土鲁番统治家族的动乱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个地方政权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从马速—马黑麻—马黑麻阿力卜把都儿的更迭,可以看出土鲁番与南疆其他地区(如牙儿坎)以及中亚撒马儿罕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很可能都有血缘联系。
(三)哈密、土鲁番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明代,哈密、土鲁番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很密切的。当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采取朝贡的形式。哈密和土鲁番不时派遣庞大的使节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常达几百人之多。朝贡的经济目的有二:一是向明朝政府进贡的物品都有一定的价格,可以得到相应的“回赐”。“回赐”主要是绢匹、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钞。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的性质。此外,明朝政府还要给赏,哈密、土鲁番的头目还可以指名“乞讨”,“其获利数倍”。这些方面都已形成制度,在《大明会典》中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是利用“朝贡”的时机,携带各种土特产品到内地贸易,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明朝政府“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允许贡使在进贡之后,于会同馆开市五日,“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其获赐而鬻之者”,亦听其自便。有时还允许他们在河西临洮府等地贸易。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开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购买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锅、犁铧)、药材等。
哈密、土鲁番地区“服食器用,悉仰给于中国(指中原地区—编者)”。“缎匹、铁、茶”等物,都是“彼之难得,日用之不可缺者”。无论哈密或是土鲁番,对于“通贡”都是十分重视的,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而当土鲁番占据哈密或进犯明朝时,明朝政府就用断绝贡路作为手段,迫使土鲁番就范。“彼绝贡路,彩缎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畜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虺蛇之
害。”明朝政府曾对土鲁番头目说,通贡“实尔国无穷之利,比之据守孤城,自阻道路,其得失无难辨者”。事实正是如此。土鲁番与明朝之间曾多次发生矛盾冲突,但每次都很快便以土鲁番“悔过”而得到解决,主要原因是它依赖“贡路”而生存。新疆其他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们称“贡路”为“金路”,可见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这就是说,土鲁番、哈密等地,尽管地处西北边疆,但它们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地区密不可分。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本书辑集的一些资料,有助于明代哈密和土鲁番历史的研究。对于某些具体史实的考订,本书的某些资料,也提供了新的线索。例如,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主张,中亚西部的蒙古人自称为“察合台人”,而把东部(今新疆境内)的蒙古人轻蔑地称为“察台”,即抢劫者之意。然而,我们在文献中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哈密人就称土鲁番人为察合台,他们中有人在遭土鲁番掠夺后说:“比先我们种著哈密地方过活,吃用都有,今被察合台将地方夺了。” 沙州一带少数民族则称“土鲁番察台人马”。明朝官员也有“察台”之称。看起来“察合台”和“察台”并没有多大差别,而当时中亚东部的蒙古人既称“察合台”,也称“察台”。哈密王室虽然也是元代蒙古贵族之后,但并非察合台系,故他们不在“察合台”之列。 又如,原来土鲁番、哈密通用回鹘文,现存《高昌馆课》中收录的土鲁番、哈密文书都是用回鹘文写的,当时简称“番文”、“番书”。至迟到16世纪,开始出现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文书,叫做“回回字文书”,或者称为“高昌话回回字番文”,“高昌话”指回鹘语,“回回字”即阿拉伯字母。这时土鲁番政权送交明朝政府的文书,既有“番书”,又有“回回字文书”,两种文字并用。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是有关系的。随着伊斯兰教日益深入,回鹘文逐渐没落,最后为阿拉伯文字所代替。
为了便于读者使用,我们将搜集到的资料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传记”,将《明史》中的土鲁番、哈密以及有关的几个传记辑录在一起。《明史》叙事简明扼要,可以给人们以比较完整的概念。当然其中也有错误,如以哈密、哈梅里为二地。第二部分“编年”,以《明实录》有关记载为纲,将其他资料凡年代可考者均与《明实录》记载一起,按年编排。第三部分“其他资料”,凡不便编年或正确年代难以确定者均编入这一部分。所有资料都加标点,明显的错讹加以校正。有些地方略加按语,予以说明。原书注文用圆括号(),脱漏补入用方括号[ ]。《明实录》的有关资料,年月日与正文之间常有删节,为避免出现过多的删节号,也用方括号来表示。本书辑录的史料,有个别字句,原书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则以虚缺号□标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辑集的资料均出自封建官僚或地主文人之手,他们一般都怀有偏见,对兄弟民族常有污蔑之词。为了保持资料原文的完整起见,我们原则上不加删节。还应该提到的是,不少资料中常有“中国”一词出现,但当时的“中国”概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而言。管辖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就可以自称“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方活动时,就曾称当时元朝控制的北方为“中国”,建议四川明玉珍与他联合起来,“与中国抗衡”。可见,他就是把中原看成“中国”的。后来明朝统一北方,控制中原,当然也就可以“中国”相称了。本书中许多资料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中国”这个名称的。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统一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两回事。
本书在编辑时,对于那些内容大致雷同的资料,尽量舍去不录,例如,明人编著的《皇明四夷考》(郑晓)、《四夷考》(叶向高)、《鸿猷录》(高岱)等,本书都没有选录。《全边略记》所记和《明实录》基本上一样,我们只选了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哈梅里即哈密。《皇明经世文编》一书,历来评价极高,实际上此书编者对选辑的文章往往任意删削,不做交代,而且错讹甚多。因此,我们尽可能从原来的文集、奏疏中征引。只有在找不到原书的情况下,才用此书。我们虽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点搜集和整理的工作,但限于学识和时间,一定还会有许多问题。资料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整理加工肯定也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用户评价
我对这类边疆史料的兴趣点在于,它往往能揭示出“边缘”地带的运作逻辑与中原王朝“核心”区域的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的张力与互动。明朝对这两个遥远绿洲的治理,无疑是其庞大帝国体系中的一个特色章节。我猜想,这本书会包含大量的“题本”和“奏疏”的摘录,这些直接反映了地方官员在执行朝廷政策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地方特殊性。比如,在对待当地不同宗教派系的态度上,官方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当地的商贾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仅仅是“汇编”二字,就暗示着它提供了大量可供后人解读和再阐释的原始材料。这种“留白”和“丰沛”正是史料的魅力所在,它让研究者可以跳出既有的框架,去发掘新的解释角度。
评分这本书,光看名字就让人对它背后的历史厚重感充满了好奇。我个人一直对明代边疆地区的动态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交汇点上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这类资料的汇编,往往是研究历史细节的一手宝藏。我期望能从中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官方文书、地方志记载,甚至是私人信札的片段。想象一下,那些关于哈密和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如何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与西域各部的关系中周旋与平衡,这本身就是一出精彩的戏剧。如果这本书能提供详实的原始文本和清晰的考证,那么它无疑是填补历史研究空白的力作。我特别期待看到那些关于屯田、商贸往来、以及朝廷对当地宗教和民族政策的具体记录,这些往往能揭示出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实际操作痕迹。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带着一种古老的韵味,让人联想到远方的驼队和漫漫黄沙中的烽火。我购买这类书籍,主要是希望能从中汲取一些异域风情与民族交融的史料。哈密和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明代的控制,无疑给这段历史增添了独特的色彩。我期望能看到一些关于人员流动、文化传播的具体记录,比如外来的信仰或技术是如何被吸纳或排斥的。这种汇编如果能做到对不同来源资料的交叉印证,那就更好了,比如将官方文书与同时期西域其他政权的记录进行比对,从而还原出一个更立体、更具多重面向的历史图景。它应该是梳理明代对西域“柔性”与“刚性”治理手腕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评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边疆史研究的学者,我对这种“资料汇编”的价值深有体会。它不像纯粹的通史叙述那样宏大叙事,而是提供了一种更为扎实的“砖块”。这些砖块往往是散落在各种档案库和地方志中的零散信息,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业的眼光去收集、整理和辨伪。这本书若能成功地将明代在这两个重要节点上的档案系统地整理出来,其学术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我特别关注那些涉及军事部署和外交活动的记录,因为哈密和吐鲁番的位置决定了它们是明朝应对蒙古部落和中亚局势的前沿观察哨。整理者的工作量和严谨程度,直接决定了这部汇编的可靠性。我希望看到的不仅是资料的堆砌,更是在梳理过程中体现出的深厚功力,比如对异文的校对,对时间线的精确梳理,以及对背景知识的必要注释。
评分说实话,我对这种专注于特定区域和特定时段的专业书籍总是抱有一种既期待又略带忐忑的心情。期待的是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那些能让我触摸到当时人们生活脉络的碎片;忐忑的是,这类汇编的易读性往往不高,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密集的古文和繁复的注释可能会成为一座高墙。然而,如果它真的能将明朝中央政府与哈密、吐鲁番的复杂关系梳理得井井有条,比如双方的朝贡体系、贸易协定,乃至冲突爆发的导火索,那么它就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个人更偏爱那些能够提供清晰的年代顺序和主题分类的编排方式,这样即便是初次接触这段历史的读者,也能顺藤摸瓜地建立起一个基本框架。这本书如果能兼顾学术的深度与基本的导览功能,那简直是太棒了。
评分这个商品很不错!我很满意!
评分书没问题,大家多看书,启智!但是仓库还是运输过程中,书来了,封面总是牢牢一层尘土!买别的东西都没这样,有塑封也不行!灰尘!烦躁!我家又有上万本书,还在买更多,就是擦拭!
评分书没问题,大家多看书,启智!但是仓库还是运输过程中,书来了,封面总是牢牢一层尘土!买别的东西都没这样,有塑封也不行!灰尘!烦躁!我家又有上万本书,还在买更多,就是擦拭!
评分书没问题,大家多看书,启智!但是仓库还是运输过程中,书来了,封面总是牢牢一层尘土!买别的东西都没这样,有塑封也不行!灰尘!烦躁!我家又有上万本书,还在买更多,就是擦拭!
评分研究明代西北史的工具书,非常方便
评分这个商品很不错!我很满意!
评分比较不错的
评分送朋友的书 他很喜欢 京东购物体验也超级好
评分研究明代西北史的工具书,非常方便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