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谁的青春不腰疼?谁的心底没有藏着中二和文艺?不如快马加鞭,将这份真挚的感情一路挥洒;不如逍遥漫游,看尽所有的寂静与繁华;不如各奔东西,在时间上相聚分离,在空间上千里奔袭。跟着龙哥一起,用旅行将青春保鲜,在相机的快门声中做那个有种的文艺青年。
内容简介
这是时光的力量,作者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自己的生活娓娓道来。在香港,在北京,在越南,凡是所到之处总会有气息和痕迹留下来,编织成一个一个的故事,点缀在生命里。
作者简介
杨正龙,旅游卫视主持人,行者,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游历世界40余个国家,100多个城市。大学时代开始主持节目,后赴香港读书生活,旅行各地,时居北京。系中国zui有影响力的旅行节目主持人之一,曾获中国电视艺术协会zui佳主持人奖。
目录
序 追风筝的人
站台
那个身怀春光的少女Ⅰ
身怀春光的少女Ⅱ
庙街里失传的美味
那些名字
珠峰路上捡来的
没人知道那场漫天大雪
上北京
这就是青春吗
露天厕所
一天
色达的旁观者
不 改
自 语
在旅馆和旅馆之间,我是失忆的
那个来自文明世界的承诺
恋恋菜市场
旅行的真相
马桶上的哲学家
斯里兰卡的神秘咒语
耶路撒冷的好
职业撒谎者的坦白
你已经变成那个无聊的大人了吗
有种,当一辈子文艺青年
久留
火车旅行爱好者
榴莲发烧友
高棉食物
越南有好吃的吗
“分手”之旅
比吴哥城更古老的发现
二手时光
加油站,火车和汽车旅馆
来不及告别的旅人
老爸的旅行
离岛的纯良和人情
精彩书摘
2016年12月4日晚北京站台
那个身怀春光的少女Ⅰ
台风快要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马路上,没有撑伞。为了告别我的大学时代,2011年一个潮热的下午,我随意在论坛里进了一个北疆约伴的帖子。帖子很吸引人,于是打包好行李,一个人从香港飞往乌市。
发帖人就是妖。那晚,我们约在五一夜市吃夜宵。沿街羊肉串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大桶大桶的啤酒,毛豆配花生。夜市里人头攒动,每一个犄角旮旯都塞满不大不小的桌子,五六个人叉着腿尽情吃喝。妖是最后一个到的。那晚,我们如网友见面,例行自我介绍。她小脸儿煞红,梳了一头非洲脏辫,一口闽南口音。
还好都是旅行中人,不扭捏造作,立马就熟络起来。一路上,她总是靠在半开的车窗上,脏辫甩在日光充足的公路上。在天山南北的光景里,我们说说笑笑,消耗着生命。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车开到琼库什台,那是一条只能徒步穿越到喀拉峻的古道。下车后,我们收拾好行李,随手找了根木棍,就进山了。走着走着开始下雨,后面还下起了冰雹。妖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六月下冰雹的。我们只好避雨。夜色渐黑,体力透支,加之没水没食物,已经赶不到预定的上车点,手机也没了信号。
妖冲我喊:“你这个混蛋,下雨天非要走这条野路子!”
当时,我也很慌,从没见过这种环境和场面,不知如何是好。
“总要找个地方先睡一晚吧,在外面会被冻死的。”说完,妖就拿着手电筒,把冲锋衣武装到鼻子,只露出眼睛,甩着一头脏辫,右手拿着木棍,消失在黑夜里。那一刻,她像身怀武功的女侠。
妖再跑回来,已是半小时后了。她找当地村民借了一个牛棚暂时落脚,弄了几床被子、一桶水。我们吃了最后一碗泡面,汤渣都喝得精光。雨还在下,牛棚漏雨,门也关不紧,雨滴淅淅沥沥落在被子上。两个无助的小混蛋在苍茫山野的一个小牛棚里分享食物、水、温暖和秘密。
第二天一早,眼睛被木门缺口射进来的光线刺醒。妖打开门,打了一个激灵——下了一整晚的大雪,草原已经被埋在下面。雪还在下,妖裹着被子站在门口,白雪把她的脸映得很白。我坐起来帮忙生火,火起来的时候牛棚里烟雾缭绕。那一刻,我坐在一团烟雾里,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英雄主义,像一个劫后余生、满血复活的小战士,庆幸自己还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再后来,警车开上山巅……我们被50公里外赶来的110救走。
在青春里,我们总会有这样误打误撞的旅行、任性不设防的相遇,来去自由,果敢倔强。我们在路上分享阳光和秘密,惺惺相惜,微风拂过,带来的都是美好的音乐。在这条公路上,你与遇见的人,或挥手告别,或继续同路,他们是时光里的旅人,身体里分泌着引人入胜的春光。
身怀春光的少女Ⅱ
2011年的最后一天,妖对我说:“我想去冰天雪地看一场壮美的日出!”
于是,我买了2张去坝上的火车票,坐了8个小时,又转乘7个小时的汽车,裹上这辈子穿过的最厚的衣服,套上最多层的袜子,戴着最傻愣的帽子和耳罩,赶在2012年第一个日出前到达了那里。
回北京后,我带妖逛胡同,北二环护国寺旁有一个百花深处胡同。狭窄的胡同儿口,墙壁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胡同儿里很多人家在二楼养了鸽子,所以经常看到它们掠过头顶,却很少有人问津。她说想要一个百花深处胡同儿的铁皮门牌号,一直想要。于是,我们挨家挨户敲门,有的炒着菜当作没听见,有的理都不理直接把我俩看成怪物。
妖说:“我们偷一个吧?”
我哪儿偷过东西啊,但不知怎么回事在妖的推推搡搡下居然同意了。
第一次作案是当天晚上。我们在胡同儿口吃好晚饭,等待夜幕降临。妖在胡同儿口把风,我作案。那是第一次做贼,没有经验,心里跟吃了炸药似的,怦怦乱跳,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猫叫狗叫,就立马收手。其实,我俩紧张得很,大概在胡同儿里盘旋了10分钟,偷门牌的事就无疾而终了。
妖回厦门后,一直惦记着她的铁皮门牌。那一年她生日,说无论如何也必须给她弄一个。那天,我下班后,专门找后勤阿姨借了一个扳手,坐着地铁,路上一直在想这次应该怎么偷,万一被抓了应该说什么。到了百花深处已经是晚上了,几个大爷在胡同儿里遛弯儿,窗内时不时飘出做饭的气味,头顶的鸽子有节奏地拍打翅膀。每次,当你觉得四下无人准备举起工具动手时,总会从黑暗尽头驶过一辆自行车,或从墙上窜出一只猫,吓得你魂飞魄散。
我在胡同儿里来回踱步,拿起电话拉大嗓门假装与人通话,或是停在路边像是离家出走的少年,踩一踩脚下的易拉罐儿,弄出一点儿动静,或者扮成一个迷路的游客走走停停,好像被此处吸引又不得不离开的样子。整场表演,没有一个观众,黑暗的胡同儿里,我像一个带了妆的孤独小丑,演了好几出没有人看的肥皂剧。
终于,四下都安静了,炒菜的关了窗户,大爷们回家泡脚,阿猫阿狗也都累得趴在一边。我拿起螺丝刀,蹭到一户人家门口,刺啦一下就把门牌抠了下来,脱下衣服包裹起来,撒腿就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一路惊魂未定,时不时看看衣服里的门牌,还在,就好。
再后来,我们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写了一些矫情造作的文字,骄傲地宣告我们都过得很好。回望那个在乌市初次见面的夜晚,根本就不会想到两人一起冒险,做了这么多混蛋的事情。每当想起5年前无意中点开那个帖子,那一坨励志要环游世界的傻子,居然在后来的某个夜晚,成为一个赴汤蹈火、有情有义的小偷。嗯,掐死她的心都有了。
庙街里失传的美味
药劲上来的时候,我穿过狭窄的楼道,按下电梯,汇入庙街的灯红酒绿中。四面传来人们的交谈声、商铺里的砍价声、酒杯碰撞声、歌厅的歌舞声,乱七八糟地在耳边嗡嗡作响。因为感冒的缘故,脑袋一阵绞痛,霓虹变成虚影,在眼前晃来晃去。此时,只有一碗滚烫的粥能解救我。
这就是住在庙街的好处,24小时都能吃到想吃的食物。找一处摊位坐下,一碗窝蛋生滚牛肉粥上桌,稠稠的白米在碗里冒着气泡,趁热咕噜咕噜喝下去,出一身大汗,感冒已好了一大半。我在庙街住了一年有余。刚来香港的时候,觉得这里很酷,一副港片里打打杀杀的模样,每个细节都充满故事性,仿佛一阵迷迭香飘来,肉身便被这味道深深蛊惑。于是,很快找了房子,交了租金,买床、买柜、买厨具,从内地抱来被子和棉絮,就在庙街安了家。参差不齐的灯箱和广告牌是香港的专属美学。沿街凉茶铺就有好几家,我爱喝夏菇草,清热解肝火。便宜好吃的烧腊店是我每周末的加餐食堂。到了夜晚,街道上支起摊位,霓虹从地上一直亮到几十米的高台,这里的黑夜没有尽头,灯火不灭。各色小吃摊位好像从地下莫名其妙地钻了出来,白天的花店变成小吃摊,五金杂货铺变成小吃摊,连无人问津的一根电线杆旁也支起了小吃摊,大家张灯结彩,拒不收摊。直到每个人的细胞都被美食填满,云层才舍得遮住月亮,渐渐收拢。
那时还是穷学生,庙街刚好是平民消费,每晚熬夜苦读后就会去楼下吃宵夜。我住的四喜楼出门直走,过两个路口左转,有一家非常小的泰餐店。没有门面,整间屋也就10平方米,所有的家当都摆在面儿上。老板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在炎炎夏日能挤死好几只苍蝇。老板娘是泰国华侨,每月往返泰国和香港两地,把当地的食材带回来。那天晚上,有些凉意,雨丝儿胡乱飘着,依然有些学生仔和老街坊在路上晃悠。我饥肠辘辘地坐下来,老头儿给我做了饭,然后撑起一把大伞。老板娘又回泰国去了,他一个人照看着店面,索性坐下来和我聊天。他是一个乐天派,聊到高兴的事情会开怀大笑。在香港,会笑的人都很珍贵。当朋友间相互打趣时,他的笑声响亮、坦诚、真实。他的脸上仿佛写着“好心肠”三个字,因为他经常会免掉我的一些零碎钱,也会在炒饭时多给我加几片肉,或用温柔的语气说一声“再见”,从不冷脸对人,更不会像有些店家那样把盘子冷冰冰地放到桌上,脸都不转过来。
他炒菜也很好吃,热心肠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多半也不会差。店里的主厨、店长、服务员都是他,有时老板娘会来搭把手,但做菜的一直是他。我喜欢他做的香叶肉碎炒饭、冬阴功汤,还有咖喱牛肉,量足管饱。他的水平不像大厨,却贵在家常。他的厨房就是一个露天灶台,看起来并不干净,却每每做出光洁如新的厨房也诞生不了的美食。这是一个神奇的露台,只见他挽起袖子,几滴油入锅,手里的大勺在铁锅里来回翻动,不用怀疑,肯定有了。
在漫长的庙街岁月中,我成了他的常客,有时一坐下来,不必点他都知道我要什么。说来,自从17岁离家至今,一路北上南渡,吃过的各地风味数不胜数,大多也就停留在“好吃”的程度。但这个老头儿做的菜,却能让人吃出纯棉的质感,冷的时候吃了暖和,热的时候吃了清凉。一边吃一边还有人笑眯眯看着你,让你慢点儿吃,说着“锅里还有”。
毕业后我就离开香港,成为一名“北漂”。5年后,我回了一趟庙街,穿过几条街,就找到了那家店。老头儿在里面摆弄着什么,门口摆满了各种香料,露台和铁锅都不见了。他抬了抬头,看到我,笑眯眯地说:“我记得你啊,是那个大学生啊,好久没看到你了。”
“你的店怎么变样了?还做泰国菜吗?”我说。“早不做了,没人过来吃,年纪也大了,就关掉了。现在卖一些泰国的特产,我老婆从泰国进的。”他答道,面孔一点儿没变,热情,爽朗。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觉得他家的味道就是最正宗的。如今他年纪大了,不做菜了,想是连铁锅都拿不动了,这一脉,算是失传了。
那些名字故事的开头发生在我的大学教室。在南方那个潮湿的天气里,除了铁,什么东西都会发霉。教学楼的小格子里,每天重复的事情单调而沉闷,似乎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晚上,自习室往往只有两三个人,都低着头认真温习英文。我是到教室蹭网的。白炽灯吱吱地响,几只不怕死的蛾子扑在上面。外面黑得出奇,一过傍晚就暴雨倾盆,下个没完,总让人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
……
前言/序言
序追风筝的人其实,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把Word文档都删掉重新来过的感觉。我始终有一些心虚。将自己的文字白纸黑字装订成册,将自己的内心诚实赤裸地和盘托出,如同一丝不挂站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表达体验。每到夜里,这些文字和日子就会从脑海的暗处爬出来。它们躁动不安,渴望找个出口。它们像血液一样贯通全身,最终流至指尖。我不确定我的手是否能将这些坐立不安的时光准确翻译出来,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从洗漱池抬头看着镜子。日子在走,但丝毫看不出痕迹。是啊,唯有当它们被记录下来的时候,才能触手可及,否则就像一片云一样,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些慌张、易碎又容易被遗漏的风光,恰恰是我生命中的宝贝,细腻、柔软,带着光。它们是有主人的,如今一一被记录下来,有时自己都觉得不太真实。它们从我的记忆深处飘出来,一颗一颗的,闪着光芒,扑腾着翅膀,带着颤音,最后变成一串故事。
小时候,我是一个爱撒谎的人。给自己的考卷签字,听写背书也模仿父亲的笔迹,还曾和我姐狼狈为奸:为了买一个牛角面包,硬是骗爷爷说是去买作业本,拿了一块五毛钱撒腿就跑,然后狂笑不止地消失在马路尽头。那时候,我以为大人的世界都太好骗了,似乎只要蒙住眼睛、堵住耳朵、假装隐形,世界就是我的。如今,撒谎成了职业,面对镜头说着不得不说的话,反倒没有小时候那么开心自在了。往往觉得无法自欺,像失了魂魄般找不到支点,心慌气短地过着日子。写作倒是一个让人变诚实的方法,越长大越想诚实地面对自己,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如果对自己都不诚实,即便活出一副华丽的皮囊,也很难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我真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那也没办法,我还是得诚实。
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有点啰唆和跑题。那么,来讲个故事吧。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老家读小学。那座小城里的生活极其单调,周而复始,按部就班。除了整天撒谎不写作业,我还喜欢到处去闲玩,每天都要把一身用不完的力气耗尽才罢休。外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周末都会带我去市郊的教堂聚会。说是教堂,其实就是一处两层楼高的水泥平房,是一个姊妹的居所。在教堂里,我结识了一帮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于是,每周末都聚在一起玩儿。那个地方在很远的郊野,要穿过一片芦苇荡和一条废弃的铁轨,杂草在那里野蛮地生长。那时,我连省会武汉都没去过,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那条铁轨后面的教堂。教堂后面有一座野山。我没爬过那座山,估计那帮小朋友们也没爬过。不知道是谁提议“我们去山上放风筝吧”,所有的小笨蛋都眼睛发亮地点点头。于是,我们上了山。我一边拿着新买的风筝,一边随手折了一根树枝。野山上没有路,我们一路向上兴奋地狂奔,手臂都被倒刺划破了好几道口子,爬得越高,越有一种所向披靡的狂喜。我看到前面的小伙伴白衣白鞋,衬衫扎在短裤里,跑起来的时候风灌进去,显得身体鼓鼓的。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画面和气息。我们一路冒险,追跑打闹,开辟了一条上山的小路。当然,也有走错的时候,所幸山不大,原路返回又继续前进。
慢慢接近山顶再也无法前进。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天地,可以俯瞰整座城市,遥遥可见房屋的轮廓和烟火,芝麻大点儿的人影在田间忙碌。那时,太阳刚好落至山巅,金黄色的光芒开始在地平线以上蔓延。我把手放到眼前,手指分开,眯着眼睛看太阳,耳边的风声转着弯地吹向远方。那时,总有用不完的力气,跑到山巅,用力把纸做的鸟儿往空中一抛,手中的线慢慢放长。我顺着风越放越高,旁边的小伙伴也都张罗起来,三四只鸟儿在比山更高的空中翱翔,用上帝的眼睛俯瞰这座城市。一阵大风刮来,我手中的线突然被刮断了,那塑料纸做的小鸟儿呼的一下就蹿到了更高的地方。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我追着风筝失了心地奔跑,小伙伴在身后叫我也听不见。眼看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而我就一直跑一直跑,想知道它到底要飞到哪里去。
当然,它还是飘走了,我没有追上。后来,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荒野,四下无人。天色暗下来,黑色的风在耳际盘旋,不见一丝灯火。我大叫一声给自己壮胆,然后一路小跑下了山,路上踩断好多树枝,隐隐约约看到挂在树上的破烂衣服,似乎还听见只在夜里才有的声音。但我一直鼓足了劲儿往下跑,头都没有回过。看到人烟的时候,我的衣服裤子都已经破了,脸上脏兮兮的。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要是在山上跌倒或者迷路,我肯定是爬不起来的。
直到过了很久,我依然心心念念那只断线的风筝,它像是儿时的一个魔障,飞在空中,去到更远的世界。那个世界是这个小城市以外的空间,是远离这个轨道的神秘国度,是儿时的我去不了的地方。我看见那只塑料纸做的鸟儿,歪着身子一直向东北方向飘去,飘得比云还高,比星辰还远。它一定看见了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是它自愿的,还是被风硬拽着去的。
一晃二十多年了。后来,我所见的世界比那只风筝大得多,远得多。有时,我觉得自己和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很像,有些事情是自己想去经历的,有些是被命运裹挟着不得不去经历的。从线断的那一刻,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回不了头,也只能继续往前飞。我想,人生看似很多选择,但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我之所以想把它们都写出来,是因为时间和记忆本身就在那里,它们早早地就准备好了。而这些年,我走过的每一段路,吹过的每一阵风,看过的每一道光,都成就了我的身体、脑袋和价值观,它们幻化成我眼中的神和脚底的纹,结实、勇敢,充满细节和柔韧,一闭眼就能看得见。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来自时间里的人,被我揪出来,按到纸上,他们在我的字里行间跳动,冒尖儿。这种记忆是任何事情都打不垮,任何人都拿不走的,上帝作证。
用户评价
这本书就像一杯陈年的威士忌,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受到它深邃而复杂的层次。它不像那种一饮而尽的爽快,而是需要你放下浮躁,静下心来,去感受它醇厚的香气,去捕捉它在舌尖留下的余韵。我并没有从书中找到某个明确的主题,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写照,一种人生阶段的缩影。它里面的人物,他们可能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他们的生活,却真实得让人心疼。那种在平凡生活中,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的疏离感,那种“不如各奔东西”的无奈,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喜欢这种不动声色的叙事,它不煽情,不刻意渲染,却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读完这本书,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人生,那些曾经的遇见与告别,那些曾经的坚持与放弃,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某种共鸣。
评分《不如各奔东西》给我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体验,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却在一种极其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我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静静地看着一群人的故事缓缓展开,然后又悄悄地走向各自的终点。这种“各奔东西”并非都是悲剧,有时它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新的开始,是一种对自我更深层次的探寻。我喜欢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那些细腻的情感波动,那些不易察觉的思绪转变,都被作者捕捉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一本让你感到轻松愉快的书,但它却能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仿佛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本书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那些曾经的遇见与告别。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真是绝了,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不如各奔东西”,这四个字带着一种疏离感,又隐隐透着一丝不甘心。翻开书页,我期待的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冒险,而是那种藏在生活细微处,那些因为时间、空间、或者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渐行渐远的磁场而最终走向不同方向的故事。我总觉得,最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拥有后,却不得不放手的无奈。也许这本书会描绘一些人,在关系走到尽头时,那种沉默的接受,那种体面的告别,又或者是不那么体面的拉扯。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处理这种情绪,是带着淡淡的忧伤,还是尖锐的现实,抑或是某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的,关于成长和告别的寓言。这本书会不会让我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或者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一种理解和释怀?这种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张力,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索它所能触及的深度。
评分读完《不如各奔东西》,我脑海里萦绕的不是一个清晰的叙事脉络,而是一系列破碎而鲜活的画面,像是蒙太奇手法在脑海中快速切换。它没有那种线性的、一气呵成的故事,更像是在描绘一个时代背景下,几个独立个体命运的交织与分离。我读到了一些人物,他们身上有着时代赋予的烙印,他们的选择,他们的迷茫,都像是那个特定时期某种群体的缩影。我喜欢这种不刻意去“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它允许读者自己去填补空白,去连接那些看似无关的片段。那种无声的张力,那种欲言又止的表达,反而更能触动人心。这本书没有给我直接的答案,而是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关于选择,关于妥协,关于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该如何寻找到自己的方向。它不是一本让你读完就合上,然后什么都不留下的书,它会在你的脑海里发酵,让你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些人物的眼神,那些场景的细节。
评分这是一本充满了“留白”的艺术品,它的魅力恰恰在于那些没有被说破的东西。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和象征,将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情感的暗涌,以一种含蓄而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仿佛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淡淡的、难以言喻的情绪,那是关于错过,关于遗憾,也关于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书中的人物,他们可能有着相似的起点,却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各奔东西”并非都是绝望的,有时也是一种必然的成长,一种对自我更清晰的认知。我喜欢作者对细节的捕捉,那些微小的动作,那些不经意的对话,都承载着巨大的信息量。它不是那种需要你全神贯注去追逐情节的书,而更像是需要你沉浸其中,去感受字里行间流淌的情感。读完后,你会发现,它并没有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却让你对生活有了更深的体悟。
评分非常不错的书,物美价廉,值得一看.
评分嗯快递送货速度特别快一晚上就到了要给好评,但是呢书外面的盒子包装不是太好,九本一起买的有点重盒子不太结实,希望改正。
评分书很新还有很重的油墨味道
评分好,以后还会买希望多做活动
评分我女神推荐的书必须看
评分内容不错,通俗易通,分析到位收获多,值得一看
评分还可以吧 不错
评分信任京东,多快好省,快递给力
评分彩色精装书这个价位简直太良心了,作者是旅游卫视主持人,文笔细腻,真情流露,读起来满满的都是感动。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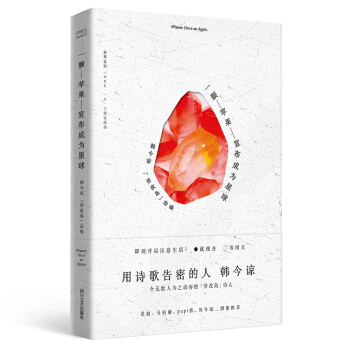


![君伟上小学:6年级怪事多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07821/rBEhWFMpUHIIAAAAAANh8LHRvZYAAKWGAN1nMsAA2II106.jpg)


![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Chinese Literatu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36477/5767b1e4N35c135bf.jpg)


![10元读书熊·儿童文学名家名作:长颈鹿的长脖子(注音版)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63334/591bfa75N17d39fd6.jpg)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小飞侠彼得·潘(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975/rBEbRVNrVx4IAAAAAArAlUkHKLUAAAWngFIXUcACsCt840.jpg)


![辫子姐姐长大有意思(套装共5册) [8-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84491/561c6a88N31410185.jpg)
![《中国卡通》蓝漠的花7(漫画版)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86260/561ef927N6a2e7f1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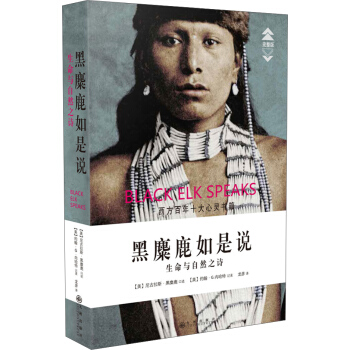
![喵卷卷来了(套装1-6册) [8-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94367/56f0a114Nffe2ba48.jpg)

![海明威书信集:1917-1961(套装上下册)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1917-1961)]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64821/5811db11N7fa4ac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