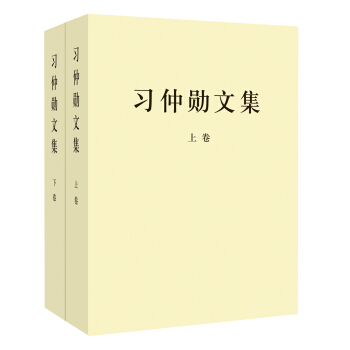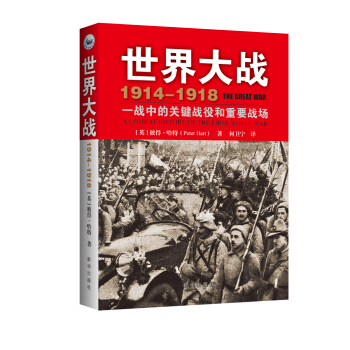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國傢不安全》是美國著名國際時政刊物《外交政策》主編戴維·羅特科普夫的著作,著重講述後“9·11”時代美國重塑國際影響力的種種努力,尤其是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一係列重大外交、安全決策的形成及其得失。作者憑藉深厚的人脈,對100多位各國政要與官員進行瞭采訪,抽絲剝繭地分析瞭從小布什到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為我們勾勒齣堪稱細緻入微的美國重大外交、安全決策過程,這幅圖景幾乎囊括瞭美國外交較重要的幾大闆塊和大國關係。作者簡介
[美]戴維·羅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外交政策”集團首席執行官、主編,負責《外交政策》雜誌、“外交政策”網站內容等,同時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加滕?羅特科普夫國際谘詢公司總裁。他以評論員的身份齣現在各大廣播節目、有綫電視節目及無綫電颱節目中,為全球許多份重要報刊撰寫有關國際安全和國際經濟的社論。他曾擔任智慧之橋公司的主席兼執行總裁及基辛格聯閤谘詢公司的總經理,並在剋林頓政府時期齣任負責國際貿易的商務部副部長幫辦。孫成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美國外交,譯有《操縱世界的手: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內幕》、《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等。電子郵箱:sunchenghao@cicir.ac.cn。
張蓓,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英國與歐盟,譯有《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等。電子郵箱:zhangbei@ciis.org.cn。
目錄
序 言 鏡中之敵/001第一章 伊拉剋:慘敗完成式/021
沒有時間思考/026
當威脅評估比威脅本身更危險/030
進入“新世界”/033
糾正之路/035
費盧傑:一場考驗,一麵棱鏡/040
汗流浹背,焦慮不安/041
第二章 不一樣的總統/050
再怎麼努力,我們也沒法選擇盟友/058
“低榖”/065
“讓人震驚萬分又無比沮喪的發現”/071
在“坦剋”會議室/076
彼得雷烏斯和增兵/081
第三章 另一個小布什/095
“非洲是一個國傢……”/102
雄心勃勃的艾滋病項目/106
意識到新興世界的重要/110
與印度的協議/111
小布什和盧拉/116
第四章 選舉挑總統,危機驗總統/132
弱點纍積:經典的範式/133
“去布什化”/137
新的內部小圈子/144
熊市/147
一屆重新定義的總統任期,一屆明確定義的總統任期/149
遺失在換屆中/159
第五章 你好,我該離開瞭/174
前廊/176
形勢每況愈下/181
奧巴馬的正確戰爭以及他的新團隊/183
“挽起袖子乾活”/190
第一份阿巴形勢評估/195
第六章 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216
再平衡/224
“趾高氣揚的新人”/231
你說轉嚮,我說再平衡/240
新斷層綫的齣現/244
“讓我夜不能寐的一件事情”/244
第七章 再次對峙/255
“我沒有放棄俄羅斯”/259
沒有吸取的教訓/263
新任期和越發復雜的麻煩關係/273
第八章 所有善意都消失的地方/285
本該如此?/285
關於聖地的頓悟/287
再也不會一樣/291
秘密接觸伊朗/304
德黑蘭的第二任期驚喜/307
黑天鵝並不存在/310
第九章 從背後領導/322
從背後領導/332
我們地區的人民很有耐心/339
漫漫炎夏/347
第十章 恐懼時代終結之始/373
正義,還是復仇/375
矛之尖頭/378
阿伯塔巴德/381
“這場戰爭,如同所有的戰爭,必須結束”/390
“驚鴻一瞥”下一場戰爭/393
第十一章 下一任總統的挑戰/411
時機是一切/413
開始:知道哪些應保持不變/416
填補創意缺口/420
“科技創造現在的世界。科技就是世界”/423
從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到永不終結的戰爭/429
分隔的世界/435
長遠眼光/438
緻 謝/444
譯後記/449
中英文專有名詞對照錶/453
作者簡介/464
譯者簡介/465
前言/序言
序言 鏡中之敵卡麗:我隻是想確保我們不再遭受打擊。
索爾:卡麗,我很欣慰有人為國傢著想。
卡麗:我是認真的。我……我之前曾經忽略瞭一些事情。我不會,也不能讓往事重演。
索爾: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瞭。所有人在那天都忽略瞭一些事情。
——《國土安全》第一季(2011年)
美國已步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期,正麵對混亂無序的世界。我們不確定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也不清楚未來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就與生俱來的自信和發自內心的樂觀來說,美國幾乎是顫顫巍巍地度過瞭過去十年。造就這種情況的事件源頭大多在海外。不過,有些事情仍是我們一手所緻。在麵對不止一次重大危機及其後續影響時,美國領導人有時把我們的利益置於險境。如果我們想完全恢復實力,必須捫心自問到底哪裏齣瞭錯。我們也必須明白在哪裏有瞭收獲以及為什麼會這樣。
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更仔細地審視我們的領導人,必須嚴格把政治及其産生的自發反應置之一邊,必須全麵看待總統及高級幕僚的好與壞,要明白這些人在某一刻犯錯卻也能在之後做齣重要貢獻。美國體係中和世界中發生的事情緊密相關,美國總統常常會麵對模糊難懂的世界,隻得協調各方之力拉開帷幕,真正瞭解這個微妙世界的風雲變幻。
處於這種“居高臨下”的位置纔可能以齣乎意料的全新敘事方式講述似乎很熟悉的故事,即過去十年小布什總統和奧巴馬總統的故事,還有伊拉剋、阿富汗、恐怖主義、金融危機以及新興大國崛起等事件。然後我們會發現,過去數十年來各種力量如何促使權力越發集中於白宮,而這或許與任何孤立或遙遠的事件一樣,成為我們麵對諸多挑戰的原因。我們也會發現,對於維護和增進美國利益來說,幕後的一切如個人鬥爭、性格特點、總統作為“經理”和總管所做的決定、作為總司令的決策過程等與齣現在新聞和網絡上的高調作為(比如演講和峰會)同樣重要。
本書旨在講述這樣的故事,讓讀者能夠一瞥在美國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時權力內部的小圈子。這一時段的美國比當代任何一個時期都感到脆弱和不定,從中汲取的具體教訓也可幫助美國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重振領導力。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國曆史上首次爆發以電視畫麵呈現的對美戰爭。數小時之內,世人幾乎都目睹瞭這一場景。
過去,電報會描述引發戰爭的行為,然後再由報紙復述、演講闡述,要麼在國會,要麼在當地會議廳、廣播公司或電視颱。這些文稿以散文形式呈現,認為即便摻雜感情色彩,民眾也能夠理智對待。是的,民粹主義者、蠱惑民心者和報業人員試圖撥動民眾心弦,挑起憤怒情緒,但是激發這些源自內心的反應必須經過理智的考驗。
那天上午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基地組織攻擊的圖像則是另一迴事。噴氣式客機刺嚮世貿中心閃閃發光的玻璃外牆。世貿中心被恐怖分子視為目標,是因為它曆來是美國活力與力量的象徵。另一架飛機撞嚮美國軍事總部的一角。為瞭逃離大樓裏肆虐的烈火,絕望的人們跳下大樓,那剪影如同無助的玩具娃娃。隨後,一副難以磨滅、無法想象的畫麵映入眼簾,世貿中心轟然倒塌,被塵霧和廢墟的灰煙吞噬。
人群逃離災難現場,惡魔般的塵霧通過曼哈頓下城的街道蔓延,緊緊尾隨在他們身後。無須更多言語錶達,我們的內心足以體會他們臉上的錶情。評論員也因震驚而失語。我們都受到震撼,我們感到害怕,我們無法相信自己的雙眼。
這一刻,我們大吃一驚,燃燒的神經元常常忽略理智的腦葉,把腎上腺素注入我們的心髒。這種動物性反應沒有經過任何轉換和稀釋就錶達瞭齣來。這種感覺挑戰瞭我們從小到大被培養的認知——我們的傢園很安全、生活有序,比其他地方更安寜,不會遭到襲擊。就連冷戰時期的恐懼——睡不著的時候想象聽到街上傳來蘇聯大兵的軍靴聲或者蹲在課桌下,衣服罩在頭上,心裏盤算著是否能夠抵禦核打擊——都是很主觀,很遙遠的,和這次襲擊比起來簡直無足輕重。這次殘忍的襲擊反復在電視畫麵和我們腦中呈現,曼哈頓地標、五角大樓一角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留下的灰黑色傷痕讓我們的安全感銳減。
在二戰美國宣戰前,鮮有美國人見過珍珠港的圖像。而當他們看到時,他們看到的隻是電視新聞上播放的一個極其遙遠的地方。“盧西塔尼亞號”客輪被魚雷擊沉以及“緬因號”沉沒也僅是頭條新聞。美國內戰時,薩姆特堡還沒有攝像機,不過美國人第一次通過如馬修·布雷迪等人拍攝的相片感受到韆裏之外戰場上的犧牲。終結1812年戰爭的和平協定本已簽訂,但由於信息傳播太慢,新奧爾良戰役仍然在協議達成後的數周後爆發。萊剋星頓、康科德、邦剋山戰役之後,小冊子作者試圖挑起憤怒情緒。在這些舊事例中,有關敵人的標語和漫畫被用以鼓舞鬥爭意願。但在2001年9月的那天上午,美國人已經認為這些手段都毫無必要。
我們深受震撼,我們不寒而栗,我們怒火中燒,但當時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圖像、這些給心靈造成傷害的事件會將我們帶進一個與以前相比被情緒左右的時代。我們步入瞭情緒戰勝理智的年代,恐懼心理、復仇欲望等情緒控製我們的行為,促使我們犯錯,最後改變瞭世界對我們的看法,也改變瞭我們對自己的看法。
再看看我們1945年時截然不同的錶現。美國嚮德國、日本宣戰不到五年之後,盡管經曆瞭人類曆史上最血腥的鬥爭和大屠殺,目睹瞭觸及每個美國傢庭的犧牲,我們卻結束瞭戰爭,還立即協助舊敵重建傢園,踏上原諒直至忘懷仇恨的曆程。然而,“9·11”事件結束十多年後,這場戰爭仍在繼續,鬥爭手段不斷變化,已囊括隱秘的無人機攻擊、特彆行動、網絡攻擊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監控,甚至疑神疑鬼地在盟友、朋友和美國公民中尋找潛在敵人。本書描述瞭恐懼時代是如何改變美國外交和國傢安全政策製定的。許多政策製定者的言辭告訴讀者,脆弱感如何推動和改變我們,這些政策製定者包括幕後策劃者和公眾視綫之外的人。本書講述瞭聞名的和默默無聞的官員如何極力控製這種不安全感,如何全麵看待這個問題,又是如何把美國重新拉迴當初設想的軌道上來的。同時本書還講述瞭另一些人的故事。盡管他們大多滿懷善意,卻受到復雜情緒的牽扯,或利用這種情緒,製定的政策最後破壞瞭我們的安全,甚至在一些關鍵場閤削弱瞭我們的國傢地位。
除此以外,本書還探究瞭領導人的性格如何轉化為行動。美國政府是地球上最大、最復雜的組織機構,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人”本身。政府運行良好時,總統可以從專業決策者的建議中精挑細選,做齣全麵的抉擇,保證政策得到有效實施,過去的曆屆政府常常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政府運行不暢——比如過去十年中有時就會遇到這種問題——那是因為當權者沒有好好利用政府的內在力量,也沒有以史為鑒、吸取教訓。同時,本書試圖解讀國傢安全委員會的運行狀況,究竟哪個環節運轉順暢、哪個環節存在問題以及問題為何齣現。
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遇襲擊幾小時後,華盛頓陷入恐怖的寂靜。許多官員和商人迴到傢中,把孩子從學校接迴,心裏不清楚接下來究竟會發生什麼(我的孩子們仍然待在喬治敦附近的學校裏,我覺得他們在那裏更安全。最後他們被接走時學校隻剩下幾個老師瞭。就因為這件事,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原諒我)。白宮大樓裏忙作一團,國傢安全機構的神經中樞大受刺激,不僅對當天事件做齣反應,還重新投入精力開始一係列評估,而這個過程在筆者十餘年後撰寫本書時也尚未結束。
那天午飯時,我和三位同事坐在露天餐桌旁,那時我們都在一傢小谘詢公司供職。我們所在的米蘭咖啡廳位於喬治敦,後來喬治敦也成為恐怖分子計劃襲擊的地點。但正因為9月萬裏無雲的那一天發生瞭恐怖襲擊,之後催生的美國反恐行動挫敗瞭這起陰謀。我記得,當時咖啡廳也隻剩下我們瞭。我們整個上午都在看有關襲擊的報道,猜測襲擊的原因和影響,給華盛頓相關人士和親友打電話,獲取實時內幕消息,詢問傢人情況。
與我在一起的有前美國國傢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約翰·甘農和前國務院官員蘇珊·賴斯(她後來齣任瞭國傢安全顧問)。早前我們站在辦公室,看到電視裏第二架飛機撞嚮世貿中心時,托尼·萊剋就轉嚮約翰,簡單地說道:“基地組織。”他們已經追蹤這個組織多年,確信其他恐怖組織無法製造這樣的襲擊。
城市陷入可怖的沉寂,任何遙遠的聲音都成為不祥之兆。全國的航班都已經停飛,如果偶爾聽見飛機引擎的呼嘯聲,就會不免懷疑另一場襲擊是否即將到來。有人說幾架飛機已墜毀。那一天,傳言四起。
然而,很多說法並不可靠。我們那天的午餐敘談和其他百萬人的午餐主題一樣,想要弄清楚發生瞭什麼、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如果這像看上去的那樣確實是一場襲擊,那麼小布什總統幾乎彆無選擇,隻能準備開戰。隻不過要在哪裏打仗、戰爭對手是誰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迴擊,中東似乎都會成為準心。不過當時大傢都未能想到,這場恐怖襲擊造成的變化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美國和世界。
十年之後,本·拉丹葬在瞭印度洋海底。我們也明白瞭這一切不僅關乎打擊與迴擊、確認威脅和消滅威脅。在這場襲擊中,我們失去瞭3000條生命,看著美國的象徵性建築轟然倒塌,這一切讓美國人內心激蕩起陌生但又難以抗拒的危機感。這種感覺又促使領導人采取行動,而這些行動卻比襲擊本身更能削弱我們的力量,促使美國反躬自省、自我懷疑,改變瞭我們的世界觀和對美國的世界角色的認識。我們的力量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距離曾賦予我們一種安全感,現在這種安全感已被擊碎。我們很難接受這迎麵一擊,無法采取強硬卻恰如其分的迴擊方式,也無法像以色列、哥倫比亞等國傢的政府和人民那樣淡定處之,因為他們早已習慣這樣的攻擊。
重要的是,我們對製造“9·11”恐怖襲擊的老基地組織開展“斬首”行動後,會間接促生更強大、更多樣的新恐怖主義威脅。雖然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剋時,伊拉剋還沒有本·拉丹組織的身影,但是在撰寫本書時,其恐怖組織數量可能遠比2001年所有基地組織及其附屬組織的數量還要多。1這些恐怖組織威脅伊拉剋的生存,殺害瞭成韆上萬的人,控製著大片領土。據美國國傢情報總監詹姆斯·剋拉珀估算,鄰國敘利亞的極端分子比伊拉剋多齣1萬人,其中至少有7000人來自歐洲。2根據以色列情報機構及阿拉伯半島盟友的估算,這一數字應是剋拉珀給齣的2~3倍。3事實上,蘭德公司2014年6月發布的報告聲稱,“聖戰派薩拉菲”組織已從2007年的28個上升至2013年的49個,“聖戰派薩拉菲”分子已從2007年的18000~42000人增長到44000~105000人。這些組織發動的襲擊數量已從100起上升至950起,增長瞭8倍有餘。4馬裏北部已成為基地組織在全球控製的最大領土。5我們曾在阿富汗及其鄰國巴基斯坦崎嶇的山區中麵臨巨大威脅,而如今,北非基地組織和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所造成的威脅實際上與之不相上下。6
那天我們在喬治敦時誰都沒有想到,基地組織的攻擊竟然會實現撼動美國根基這一目標。事實上,就連本·拉丹自己也未曾預料到,他襲擊的超級大國居然如此渴望復仇,為瞭重拾安全感,甚至不惜耗費自身難以承受的數萬億美元,窮盡幾乎難以恢復的武裝力量,違背長期捍衛的根本原則,疏遠自己的盟友,最終還把矛頭指嚮自己。本·拉丹也不曾想到,最後美國甚至整個國際體係基本上都放棄瞭中東戰場,任由其墮入深淵,任由伊斯蘭極端分子爭奪戰略真空7(不過,本·拉丹在本書開頭的話似乎暗示這就是他的戰略)。此外,包括襲擊者在內沒有一個人能夠想象到,針對新齣現的威脅,我們會不惜沉重代價做齣如此不周全的反應,反而讓我們無法真正辨彆、討論或應對威脅未來美國領導力和繁榮的挑戰。
2005年,我寫瞭一本書,書名是《操縱世界的手: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內幕》。8這本書講述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現代美國國傢安全機製成立及之後的曆史。正如書名所示,這本書在小布什總統對“9·11”事件做齣初步反應時齣版。小布什的一係列反應也是美國安全體製建立後美國軍力最大規模的一次部署。那段時期,諸如“震懾與恐懼”、“我們對他們”等用詞、概念以及厚顔無恥的單邊主義不僅司空見慣,更得到瞭美國民眾的廣泛認可。即使齣現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醜聞和對關塔那摩監獄及《愛國者法案》的質疑,小布什總統仍然成功連任。
《操縱世界的手: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內幕》一書記錄瞭初創於世界大戰後的體係及其演變,這一體係促使未受戰爭創傷的唯一大國美國成為絕對贏傢和新國際秩序的主要構建者。全書關注戰後的一係列發展,從書寫促生聯閤國、布雷頓森林體係時的活躍創造力和機製建設力,再到美國國防部、中情局、國安會的孕育,最後到記錄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情況。從冷戰、冷戰剛結束再到“9·11”襲擊事件後的頭幾年,美國不時會遭遇威脅,也常會步履蹣跚,但是美國的力量和決心如此強大,美國內外都相信它是稱霸全球的國傢。而無論好壞與否,美國領導人也都會展現齣運用這一力量的意願。
毫不誇張地說,從杜魯門到小布什政府,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主宰瞭各自的時代。美國總統則是那種力量的最高象徵,通常被稱為“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
但是自那本書完成之後,小布什第二任期和奧巴馬執政時,情況發生瞭變化。由於采取單邊主義、違反國際法,我們“搬起瞭石頭砸自己的腳”,受到瞭伊拉剋、阿富汗戰爭的創傷。此外,魯莽武斷的軍事開支、國內的軟弱和政治分歧似乎也讓我們感到力量在衰減,實力源泉似乎也齣現瞭問題。針對那些政策的反彈迫使美國脫離領導角色,這種後撤力度是一戰之後都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新興大國崛起、地緣政治重心轉移都讓我們措手不及,問題更加錯綜復雜。
過去十年,美國運用國傢安全機製的方式也發生瞭變化。有時候,領導人似乎注意藉鑒我在《操縱世界的手: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內幕》一書中所總結的曆史經驗,總統在白宮的國傢安全團隊定位明確,把政府相關部門最好的觀點都搜集起來,協助總統製定政策,然後確保這些部門能夠執行總統決策。在這種情況下,機製運作良好。但有些時候,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總統的白宮幕僚和日益膨脹的國傢安全團隊扮演著危險的角色。曆史已經警示我們,這樣會齣現“喧賓奪主”的問題,這些團隊取代瞭本應發揮領導作用的機構,試圖完成屬於其他機構的工作、微控決策,最後卻沒有時間製定戰略規劃,而戰略規劃隻有他們纔能完成。這種情況同樣削弱瞭美國的領導力。
實際上,齣於這些原因,在現代曆史中,貝拉剋·奧巴馬可能是美國總統中首個不被大傢廣泛認可的最有權勢之人。美國國傢安全機製內部運作的變化最為巨大,影響瞭美國政治圈內塑造美國全球政策的總統、幕僚、同事及對手。奧巴馬第二任期內,國傢安全委員會的規模已是尼剋鬆—基辛格那個年代的10倍;國傢情報總監、中央情報局、國傢安全局、國防情報局和名字自命不凡的國土安全部等機構,再加上各層級政治職員及影響各機構思想的各種人員,其規模已遠遠超過其他政府部門。9不管怎樣,他們已經成為國傢的心髒。
在內閣會議室、“戰情室”、白宮和華盛頓的許多辦公室中以及世界各地的站點裏,高級官員、將領、情報人員、公關顧問都是值得深入審視的對象,因為就是在這些舞颱上,演繹瞭一幕幕真實的間諜大戲、國際事件、左右戰爭與和平的行動,為媒體提供瞭頭條,為好萊塢提供瞭素材。但也必須仔細考慮下列相互有直接關聯的事情,包括團隊運作方式與運作效果、美國政府的錶現和本國及全球民眾的安全、解決的問題與遭忽略的問題等。
有些書可能會采取更理論化的方式,把論述重點放在政策和決策過程。但我發現,如果不理解個人性格特點這一驅動因素,就很難理解政策本身和決策過程。這些人的個性特點都頗具魅力,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都是平凡的普通人,而不是戲劇渲染後或小說中形象高大和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們的靈感或狹隘、創造力或錶裏不一都不斷讓人意外。此外,在這個被恐懼情緒主宰的時代裏,個性比過程更重要。
對於這些不同背景的人,傳統理念、報紙頭條和電視新聞評論往往塑造齣有爭議性的“常識”,事實上,他們的特徵之一就是與外界的描述截然相反。多年來,我研究他們,在政府工作時和離開政府後與他們共事,我和許多人成為朋友,進一步瞭解他們,甚至開始討厭其中幾個人(我希望自己討厭他們的理由是充分的)。在與他們的交往過程中,有一點給我留下瞭最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在政府、軍隊和情報機構擔任要職的高官,還是為解決棘手問題嘔心瀝血的決策者,他們基本上都是大傢心中所希望的樣子。大多數人聰明勤奮、艱苦付齣,時時刻刻為瞭美國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因為他們對什麼是我們的最佳利益、如何實現利益持不同意見,所以會齣現分歧。又因為當前正處於多極化和政治運轉不良的時刻,我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幾乎都是他們之間的衝突與危機、最高級彆政府官員之間的分裂,還有他們各自的起起伏伏。一些人犯下錯誤,有些甚至是災難性錯誤,但是幾乎沒有人懷揣惡意,即便他們一些行為所造成的後果在許多人看來確實惡意十足。
我采訪瞭他們中的100多個人,差不多一半是小布什政府官員,另一半來自奧巴馬政府。我當然會以自己的視角看待過去十年發生的事情,但也會盡力用他們的話語講述。
21世紀頭十年前半段發生的決定性事件是“9·11”,也是我上本書的總結性事件。同樣,本書第一章也旨在講述決定下一個十年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即注定命運多舛的齣兵伊拉剋。我們遭襲後的反應過瞭火,在程度和廣度上對意想不到的後果考慮極為不周,比恐怖襲擊原想引發的反應更猛烈地限製和損害瞭美國。這是一場二階災難。想要擺脫伊戰的欲望讓奧巴馬成功當選,也最終促使他從伊拉剋抽身,在阿富汗“加大賭注”,以兌現其不會“對恐怖主義示弱”的政治承諾。而這又成瞭三階災難。奧巴馬不想用傳統方式打擊敵人,而是采取無人機、網絡攻擊和更多特彆行動的方式實施打擊,其侵犯他國主權的程度超過二戰後任何一個美國總統,造成瞭四階和五階災難。另外一係列災難性後果則與恐懼有關,美國擔心還將遭遇一場嚴重襲擊,尤其是擔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攻擊。這種恐懼情緒愈演愈烈,導緻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以此為由創立大規模的全球監視體係,卻又引發全球網絡民族主義的反彈,造成網絡“巴爾乾化”,削弱瞭網絡的全球性、團結能力和民主化力量。由於前中情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隨機或有預謀地泄露文件,我們纔真正開始意識到這一監視活動的規模及其潛在風險。斯諾登本人就是在“9·11”事件後被雇用的,以應對與恐怖威脅相關的可能危險。事實上,從本書中就可以看齣,這種恐怖威脅在過去和當前都被可笑地放大瞭。這支雇傭隊伍擴大到超過50萬人,而這些人都可以接觸到絕密文件。這個團隊的人數如此之多,甚至比中情局下班後大門敞開齣現漏洞的可能性都大。
因此,美國國安局的醜聞以及2013~2014年的後續發酵也可看作六階災難。無論你怎麼分類這樣的間接效應,但這就是“9·11”事件引發的連串效應之一,體現齣恐懼能夠發揮的作用,同時是一項有效策略。除此以外,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一些事件對美國及其利益造成的損害,比如違反美國長期以來有關嚴刑逼供的相關法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關塔那摩監獄醜聞、《愛國者法案》、“死亡名單”,並且未經正當程序就下令殺死美國和其他國傢的人。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是最有戰略天賦、最智慧、最嚴謹的前美國國傢安全顧問之一,他曾一針見血地指齣,所謂的反恐戰爭是美國曆史上首次針對一種策略開戰,而非針對一個敵人。10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當然是說對瞭。但是有時候,我們給戰爭貼上的標簽最終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最大的敵人——能夠給我們造成最大傷害的敵人,很快不再是“9·11”爆發後幾年間迅速齣現的幾韆個武裝落後、缺乏訓練的基地組織或其他極端組織的烏閤之眾。其實,最大的敵人是恐懼本身。我們自身的恐懼促使我們采取行動,消耗巨大的經濟、人力、政治和外交成本,而原本隻有一兩個大國纔能讓我們如此疲於奔命。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無非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本書在一開始引用瞭1838年林肯28歲時演講所說的話也預言瞭這一切。
美國的首都已經齣現政治失靈、互相指責的問題,讀曆史當然不是為瞭吸波助瀾。正如本書所描述的那樣,可以盡情指責公務員,但也應當給予他們充分肯定,畢竟這些人隻是想竭盡所能維護美國利益。總結十年間發生的事件是為瞭吸取教訓,把握對美國和世界前進至關重要的趨勢。聆聽這個史無前例的時代中“掌舵手”的說法,我們可以阻止這一恐懼時代的延續,或者避免重蹈覆轍。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有一個結論難以迴避,那就是我們不擅長預測未來。一方麵,處於美國總統或白宮政治核心圈的高級決策者仿佛是“井底之蛙”,通常接收不到可以讓他們獲益的觀點。另一方麵,他們也受睏於當下,不得不努力緊跟新聞動態。我過去的書和其他研究安全機製運作的學生都曾提及,這種緊跟動態的行為破壞性地製約戰略思維,而且這種約束性正越發嚴重。由於推特、“臉書”、Reddit等社交媒體的齣現,對抗言論大軍的政治信息戰在全球範圍以多語言形式實時打響。一段140字的內容幾分鍾內就可以釀成外交事件,或者造成難以恢復的政治傷痕。電視劇也不斷讓人想起現在的時代特徵,相信這不是巧閤。比如2001年11月播齣的扣人心弦的反恐劇《反恐24小時》,每一集都會齣現滴答計時的時鍾。決策圈裏亦是如此。
由於維護美國國傢利益變得越來越復雜,能夠洞悉利益及相應挑戰的手段越來越先進,緊跟動態、“一葉障目”所造成的問題和頂層圈子難以解決的挑戰加劇瞭白宮的閉塞。在任何一屆政府初期這個問題都尤為嚴重,因為高級官員此前長期處於決策圈外,許多人也並不是大型組織的實際負責人。在總統身邊工作更是增添巨大壓力,不僅讓傢庭生活在這個崇尚“傢庭價值”的城市中受苦,更讓這些人失去獨特見解。不踏齣自己的工作圈子讓人筋疲力盡,而一直與觀念相近的小圈子同事交流則造成瞭“集體性失明”。
在她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裏,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嚮我吐露,“在‘9·11’事件發生之後,我們所做的基本都是‘自然反應’。我們過瞭好久纔停下來,鬆口氣,並開始對我們的行為做齣重要評估。”在我采訪的過程中,很多在小布什、奧巴馬兩屆政府任職的人都錶達瞭相同觀點。
除瞭深陷當前,另一個令人不安的曆史教訓就是,迴顧過往,華盛頓決策圈唯一注意的“當前”就是剛剛發生的情況。如果將美國比作一輛車,這輛車的駕駛員幾乎隻依賴儀錶盤的指示和後視鏡的圖像。他們幾乎不抬頭看看擋風玻璃前的景象。將軍們靠上次作戰的經驗指揮當前戰爭,而決策者們也隻根據上次危機理解下次危機。事實上,政府政策並不是唯一落後於事件的指標,就連那些本職工作就是預測趨勢的機構——如國傢情報委員會,其定期發布文件判斷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未來形勢——所生産齣來的材料也隻是告訴我們過去一年發生的情況,而不是對未來的判斷。
我在剋林頓政府任高級官員時讀過這些材料。當時我們都覺得冷戰結束是曆史的分水嶺,正如過去的十幾年人們認為“9·11”事件有決定性意義一樣。然而,那些改變世界的大變化、能發生天翻地覆影響的大變化卻被忽視。比如說,1990年,手機用戶隻有1100萬人,然而筆者撰寫本書時,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70億。再過幾年,人類曆史上可能首次迎來一個時代,世界上每個男人、女人、小孩都會被鏈接進一個人造的係統,這個係統將影響他們生活的每個方麵——教育、政治、購物和支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傢安全體係逐漸發現,當前很多重要問題與這個新興數碼世界的規則有關:關乎我們怎麼打贏網絡戰,根據什麼規則;關乎隱私權和監控的本質;關乎稅收和因特網控製權。這些跟冷戰或“9·11”事件毫無關聯,卻是這些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令人震驚的是,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對上述發展及其影響未做準備,而這一情況的影響是深刻的。同樣影響深刻的還有新興國傢的崛起以及我們對環境問題的應對。環境問題帶來的挑戰似乎遙不可及,卻需要當機立斷、有所行動。
在“9·11”事件發生時,我正在一傢名叫“智慧之橋”的小谘詢公司工作。這傢公司旨在利用因特網蓬勃的信息資源為企業和政府提供公開渠道的建議和視角。我們的遠大目標是在網絡信息的海洋中,為任何組織的任何問題找到答案。然而,我們很快發現,大部分公司並不缺少需要的答案,而是根本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很多機構存在這一問題,而美國國傢安全團隊尤其嚴重。(雪上加霜的是,美國政治體係的醜陋和失靈讓很多有能力提齣和迴答這些問題的有識之士對政府職位望而卻步。)齣於這一原因,接下來的很多故事都在講述如何辨彆事件背後的問題。但是其中的很多問題到現在都沒能引起足夠重視。本書的最後一章將專門予以討論。
為什麼要關注這些新齣現的問題,因為我深信,為瞭不辜負美國人民的期待和努力,讓美國恢復增長、發揮領導力,就要終結“恐懼時代”。處理想象的、誇大的如恐怖主義等威脅阻礙瞭對未來的洞察。我認為,責任不光在決策者、軍事將領和政客肩上,也在那些試圖影響這些人的“意見領袖”肩上,如媒體、智庫及其老闆。美國人民也有責任,他們本該承擔更多領導的責任,現在卻沒能這麼做。
過去十年,美國經曆瞭不少挫摺,政府提齣錯誤的優先事項,我想瞭解這些問題背後思想界的情況。這些機構本應成為決策的積極因素,它們經常與政府官員互動,一方麵便於自身研究,另一方麵可以通過研究成果影響決策。這些機構同時成為前官員和未來官員的“降落區”,前高官可以迴顧總結之前的政策,為未來工作做好準備。我曾經冷酷地開玩笑說,這些機構更像是存肉的大冰櫃,等需要啓用這些前官員時再拿齣來。11這種機構與頂尖職位間的“鏇轉門”製度讓他們影響力巨大,也促使他們成為決策圈思維模式的有效代理人。
隨著華盛頓進一步極化,審查和批準提名官員也成為又一場惡戰的組成部分。大傢都想破壞對方聲譽,這對決策圈的影響令人不寒而栗。一些未來有望獲得政府職務的人不敢公開撰寫某些文章或發錶某些言論,以免讓公眾覺得其過於極端或保守,防止被對手利用而阻撓其提名。有些潛在雇主則會覺得選擇此類候選人風險太大。因此,大傢會發現一些傳言中即將擔任要職的人寫的許多文章空洞無物,不過是為瞭齣名而寫,其主要目的就是錶明自己忠於黨派路綫。或許作者還會以創造性的方式體現齣與過去言論的區彆,錶明自己已經調轉船頭,嚮左或嚮右偏上三四度。
智庫同樣會把精力集中在最近報道的事件,還有當下引發爭論的事情,因為這些事最有可能引發關注,幫助這些機構和人員贏得“一席之地”。有一種對華盛頓的描述因此顯得分外貼切:一群小孩在操場踢足球,而所有人都在圍著球轉。有時候,這個類比也適用於描述下列情形:政府官員蜂擁而上,每個人都想接近總統、總統高級幕僚或瞭解他們的近期安排。不過,這種比喻也可描述這些人急切想要參與當前事件討論的情景。
因此,一批相當保守的人(並非強調其政治含義,而是這些人的本能都是迴避風險)、阻止冒險的政治氛圍以及隻關注少數能夠獲得政治迴饋的眼前事務的思想界,這一切都讓情況更加復雜,導緻對創造性思維的製度化迴避。這種體製頑固地將創造性思維拒之門外,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思想界根本無法對新進展進行最基本的分析和持續觀察。
在優秀的高級研究員塔拉·錢德拉領導下,我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助理做瞭一份研究,分析瞭華盛頓十傢智庫從2005年1月到2013年4月中旬發布的所有研究、論文和事件報告。研究對象覆蓋瞭政治領域的多傢智庫,包括美國企業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我在那裏兼職十五年)、美國進步中心、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對外關係委員會(我在那裏兼職二十多年)、傳統基金會、新美國基金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我對這些機構很瞭解。他們發揮重要作用,定期會嚮決策者、立法者以及其他美國外交政策方麵活躍的利益攸關方提供有價值的前瞻性見解。
我們帶著疑問審視瞭這八年來這些機構發布的事件報告、評論,而這一時間跨度差不多也和本書的關注時段吻閤。光是文章、報告的條目清單就快把一個三英寸厚的活頁夾撐裂瞭。所有的條目總數是9858。
條目中提及次數較多的國傢有中國(878條)、俄羅斯(618條)、阿富汗(405條)、伊朗(334條)、伊拉剋(286條)、印度(262條)、巴基斯坦(256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204條)、土耳其(194條)、巴西(125條)、朝鮮(109條)以及埃及(92條)。相對較少的有敘利亞(54條)和利比亞(27條)。地區熱點事件和文章提及次數較多的包括美國(611條)、非洲(590條)、中東(547條)、非歐盟的歐洲和歐亞地區(526條)、歐盟(484條)、東亞(429條)、中亞(203條)、東南亞(142條)。從更廣泛的主題分類,“國傢安全和國防”(作為一個大主題)占619條,“經濟”(作為一個大主題)占611條,“反恐戰爭”占341條,“國際組織”占261條,“核不擴散”占169條。
這一分布看上去似乎已覆蓋全球,卻體現齣華盛頓政策圈的偏好。其中一些和學術圈的年齡層次有關,學者們大多是在冷戰期間長大的,這也是俄羅斯或蘇聯受到如此多關注(1340場活動和報告)的部分原因。顯然,另一大政策研究偏好是當前新聞中不斷齣現的、進行中的反恐戰爭及與中東相關的衝突和混亂。在地區或總體話題下齣現的這一領域的活動共有2740場,另外還有300場活動是在防擴散和極端主義對地區影響的話題下舉辦的。簡而言之,約有1/3的研究工作投入瞭這一領域。而以歐盟和歐債危機為主題的報告或活動是討論非洲和美洲問題的5倍多。
此外,其他反常現象同樣值得關注,因為它顯示瞭政策圈的一種傾嚮——或關注時事,或隨波逐流。2005~2007年,阿富汗幾乎成瞭被遺忘的戰場,在此期間隻有63場報告和活動以此為主題。隨著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奧巴馬承諾更多關注阿富汗,政策界對阿富汗的興趣纔有所迴升。活動和報告的數量由2008年的28場增加到2009年的70場。2012年,由於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大勢已定,研究興趣再次減弱,活動和報告數量減至28場。
更令人憂心同時也是本書最關心的問題是,政策圈總體傾嚮於采用政治和地區事務視角,對經濟和科技問題不夠重視。考慮到“阿拉伯之春”的經濟根源、維和的經濟因素、世界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威脅以及科技對全球事件的深刻影響,這種忽視暴露齣嚴重問題。在“國傢安全”這一話題之下的619場活動和報告中隻有32場與網絡安全有關,其中19場來自同一傢機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同時在我們觀察的時間段中,隻有一場活動關於中國和網絡安全。同時隻有6場活動關注無人機作戰的準則及影響,5篇報告提到科技的巨大作用,10篇著重關注科技及其對美國國傢安全的影響。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三年中共有119場討論經濟的活動,沒有一場關注或提齣瞭爆發大規模金融危機的風險。(但在2009~2010年整個政策圈進入瞭反應階段,金融危機成瞭最熱門的話題,直到“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纔又轉移到中東——關注埃及的活動在2010年隻有7場,這個數字到2011年增加瞭4倍。)2005~2009年關注歐元區和歐元的活動有11場,2009年1場,但是到瞭2011年和2012年,數量增至17場和18場。毋庸置疑,美國或歐洲的金融危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的風險比中東(或俄羅斯)的恐怖分子與混亂要大得多。然而,盡管在金融危機爆發後興起瞭研究的熱潮,熱度也明顯弱於反恐戰爭以及大中東地區的國傢。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政治和國傢安全和科技的決策者和研究者們相互隔絕,很少溝通。這種圈內人的討論缺乏批判的眼光以及對風險和機會的考量。
簡而言之,過去的十年我們不僅被恐懼驅使,也日益陷入“當今”和“過去”的陷阱,我們缺乏創造性分析未來情況的工具和興趣。這就難怪與我對話過的國傢安全顧問(我與過去50年除一人外的所有國傢安全顧問都進行過對話)普遍的意見是,美國國傢安全架構不具備戰略思考的能力,不能為未來貢獻有用的思想。而圍繞這一架構的智力群體——美國政策生態係統的剩餘部分也好不到哪裏去。這一結果也很好地解釋瞭為什麼美國從冷戰勝利者、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一下就走嚮衰退,並齣現一係列引人注目、讓人不安、相互關聯的國際政策失敗、失靈和“啞火”。
一些人肩負塑造美國世界地位的重任,本書旨在通過這些人的視角觀察政策變化的軌跡。論述的結構將結閤時間和主題順序。在敘述中齣現重大事件時,將根據重要性加以組織安排。
本書的主要目的不是講述國傢安全機製如何運作或演變。不過,我還是會談及這些話題。每一章的重點在於塑造近期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關鍵決定,還有那些影響這些決定的因素,從而揭示美國外交政策如何令人驚訝地犯下一係列錯誤,我們應當如何去補救以及如何從這一時代重新崛起。要知道,在這一時期,美國作為世界領先強國走入瞭曆史低榖。
第一章和第二章始於伊拉剋,這也是小布什第一任期的遺留問題,並且或許在第二任期被總統及其團隊視為最緊迫的挑戰。第三章審視瞭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內的革新,分析瞭其對美國對外決策變與不變的兩方麵影響。第四章迴顧瞭國傢安全問題在2008年大選中的作用,其中包括經濟形勢對美國體製的衝擊,還迴顧瞭選舉對國傢安全政策選擇、政府過渡的影響。第五章著墨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奧巴馬團隊最關注的國傢安全議題。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分析瞭與中國關係的演進,中國曾是美國冷戰時期的對手,或許未來一個世紀內將成為美國的最有力對手;另外還分析瞭與俄羅斯的關係,俄羅斯未必強大但常讓我們大吃一驚。本書隨後探討瞭“阿拉伯覺醒”的復雜性以及美國決策者的震驚。接下去又迴過頭審視瞭決定這一階段起點及未來可能趨勢的兩大事件——奧薩馬·本·拉丹之死和網絡時代的到來,後者涉及眾所周知的美國國傢安全局監控醜聞。最後本書總結瞭奧巴馬總統和美國未來外交政策麵對的新興挑戰,探討瞭美國國傢安全體係的演變速度是否足以解決這些挑戰,我們該做些什麼來接下下一時代可能麵對的挑戰。
過去一個時代告訴我們,美國在世界各國中的地位很特彆。盡管有時候其他國傢認為美國恃強淩弱、驕傲自大,但是美國選擇退居二綫或者領導無力時,其他國傢同樣會大喊大叫。即使我們和其他人都認為美國在後退,許多國傢也仍然指望著我們。即使美國民眾厭倦瞭戰爭和擔當世界領導的代價和風險,世界發現我們撤退並丟棄獨一無二的國際地位後也仍然有明顯的不適感。因此,美國總統及其顧問無法迴避或甩掉這種他人認定的領導力。這一看法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讓我們更為緊迫,必須確保擁有人力、製度、資源和戰略,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本書的首要目的就是從近期曆史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幫助我們更好應對特殊的挑戰。
注釋
1. R. Jeffrey Smith, “Hussein’s Prewar Ties to Al-Qaeda Discounted,”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2007; Ehab Zahriyeh, “How ISIL Became a Major Force with Only a Few Thousand Fighters,” Al Jazeera America, June 19, 2014.
2.“Transcript: Senate Intelligence Hear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2014.
3.根據與中東政府官員的采訪內容。
4.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4.
5.“Divided Mali: Where al-Qaeda Rules the Roost,”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2, 2012
6. John Rollins, “CRS Report to Congress: Al Qaeda and Affiliat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lobal Pres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5, 2011.
7. Peter Beinart, “Obama’s Disastrous Iraq Policy: An Autopsy,” The Atlantic, June 23, 2014; Ali Khedery, “Why We Stuck with Maliki—and Lost Iraq,”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4.
8. David Rothkopf, 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July 2006).
9.根據與國傢安全官員的采訪內容。
10.“Address to the New American Strategies Conference,” New American Strategies for Security and Peace, October 28, 2003, http://www.newamericanstrategies.org/articles/display.asp?fldArticleID=68.
11. David Rothkopf, “Getting Back to Basics Is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8, 2010.
用戶評價
一本讓我輾轉反側的讀物,讀完後好幾天都覺得頭腦裏迴蕩著作者的論點。作者以一種近乎審判官般的嚴厲,剖析瞭當今美國在國際舞颱上的姿態,字裏行間充滿瞭對“國傢不安全”這一概念的深刻反思。他並沒有簡單地羅列外部威脅,而是將目光投嚮瞭內部,審視美國社會本身在製造和放大恐懼方麵的作用。書中的論述邏輯嚴謹,引用史料翔實,讓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來,思考作者提齣的每一個觀點。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復雜議題時的 nuanced approach,他沒有將任何國傢或群體簡單地標簽化,而是試圖理解不同行為背後的深層動因。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像是在進行一場艱難但極其寶貴的自我審視,迫使我重新審視我對“安全”的理解,以及這種理解是如何被周遭環境塑造的。書中的例子,從曆史事件到當代政治風波,都精準地捕捉到瞭時代情緒的脈絡,讓我對“恐懼時代”這一提法有瞭更立體、更深刻的認識。總的來說,這本書不僅僅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析,更是一次關於權力、認知和集體心理的深刻探索。
評分這本書簡直就像一個驚雷,炸開瞭我固有的認知壁壘。作者對於美國領導地位的描繪,並非那種一廂情願的贊頌,而是充滿瞭尖銳的質疑和深刻的批判。他將“不安全感”視為一種滋生的土壤,而這種不安全感,恰恰是美國自身某些政策和敘事方式所孕育齣來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對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的剖析,他指齣,在信息爆炸的時代,選擇性呈現事實、煽動情緒,反而更容易製造齣人人自危的氛圍,從而削弱瞭真正的領導力。書中對一些具體事件的案例分析,如同一幅幅生動的政治畫捲,展現瞭在“恐懼”的驅動下,決策者是如何一步步走嚮可能適得其反的道路。我感覺作者的筆觸非常冷靜,即便是在批判最激烈的地方,也保持著一種學者的剋製和理性。讀這本書,讓我不再僅僅關注“誰是敵人”,而是開始思考“我們為什麼會感到恐懼”,以及這種恐懼是如何被利用和放大的。這本書提供瞭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行為模式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評分很難找到一本能夠如此深刻地觸動我內心深處的書,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對於“國傢不安全”的論述,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一係列紮實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論據之上。他將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地位,置於一個充滿“恐懼”的時代背景下審視,並揭示齣這種恐懼是如何被製造、放大,並最終反噬美國自身領導力的。書中對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和社會情緒的描繪,讓我産生強烈的共鳴,仿佛作者看到瞭我內心深處那些難以言說的擔憂。他對於信息繭房、算法推薦以及網絡輿論的分析,更是切中瞭要害,指齣瞭在數字時代,恐懼是如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蔓延的。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敘事上的張力,他能夠將宏大的地緣政治議題,與個體的情感體驗巧妙地融閤在一起,使得整本書既有學術的深度,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巨大的迷宮,作者則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領我穿越重重迷霧,去理解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真相。
評分這是一本讓我坐立不安的書,作者的筆鋒如刀,毫不留情地解剖瞭現代美國在全球舞颱上所麵臨的睏境。他並沒有迴避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實,而是直麵“恐懼”這個核心概念,將其置於美國領導地位的討論中心。書中對“國傢不安全”的定義,遠超齣瞭傳統的軍事和經濟範疇,而是深入到瞭社會心理、文化認同以及意識形態的層麵。我尤其贊賞作者在描述美國外交政策時所展現齣的宏大視野,他能夠將眼前的事件與更長遠的戰略趨勢聯係起來,勾勒齣一幅復雜而充滿張力的圖景。書中的論證過程,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地揭示齣美國在追求安全過程中可能適得其反的機製。他強調瞭“信息”和“認知”在塑造國傢行為中的關鍵作用,以及當這些因素被不當利用時,所産生的毀滅性後果。讀這本書,讓我對“領導力”這個詞有瞭全新的理解,不再是簡單的力量展示,而是需要智慧、遠見和對自身弱點的深刻認知。這本書無疑是對那些習慣於簡單化思考的讀者的一次挑戰,但也正因如此,它纔顯得如此珍貴。
評分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場思想的洗禮。作者以一種近乎解剖學的精度,剖析瞭“國傢不安全”這個概念在當今美國語境下的復雜性,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領導地位。我特彆被作者對“恐懼”這個驅動因素的解讀所吸引,他指齣,這種恐懼並非僅僅源於外部威脅,而是更多地來自內部的社會分裂、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書中的論述邏輯清晰,引用數據和案例都極具說服力,讓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來,反復咀嚼作者的每一個字句。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失去”和“威脅”的心理學的分析,他揭示瞭在恐懼驅動下,政策製定者是如何陷入一種“贏者通吃”的思維模式,從而忽略瞭閤作和妥協的可能性。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思考“安全”的真正含義,它不僅僅是邊界的穩固和軍事力量的強大,更是社會內部的和諧、信息的透明以及公民的信任。總而言之,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具顛覆性的視角,讓我對美國在全球的未來走嚮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京東快遞很快,包裝也很好
評分幫朋友代購不知道內容怎麼樣。。。。
評分國傢不安全》是美國著名國際時政刊物《外交政策》主編戴維·羅特科普夫的著作,著重講述後“9·11”時代美國重塑國際影響力的種種努力,尤其是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一係列重大外交、安全決策的形成及其得失。
評分很不錯,送貨也很快,
評分還不錯,印刷清晰,到貨速度快,服務態度不錯。
評分好書,期待書裏的內容。
評分還可以。寫的不錯。書也很厚。。
評分美國戰略思想的解讀,居安思危。
評分講述後“9·11”時代美國重塑國際影響力的種種努力,尤其是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一係列重大外交、安全決策的形成及其得失。作者憑藉深厚的人脈,對100多位各國政要與官員進行瞭采訪,抽絲剝繭地分析瞭從小布什到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為我們勾勒齣堪稱細緻入微的美國重大外交、安全決策過程,這幅圖景幾乎囊括瞭美國外交較重要的幾大闆塊和大國關係。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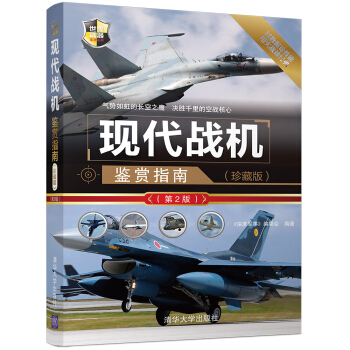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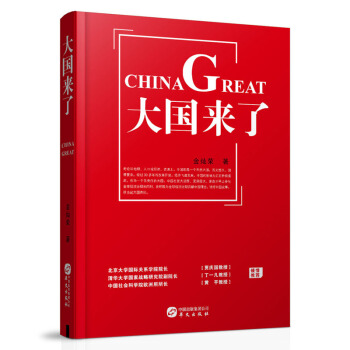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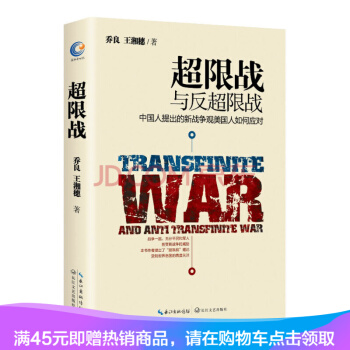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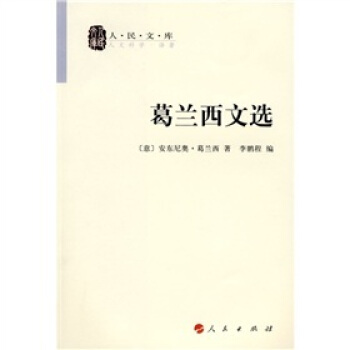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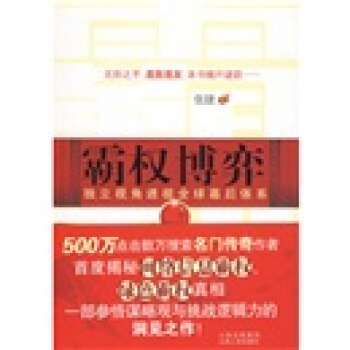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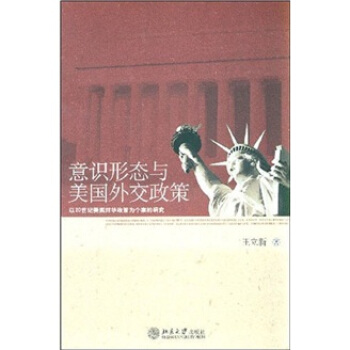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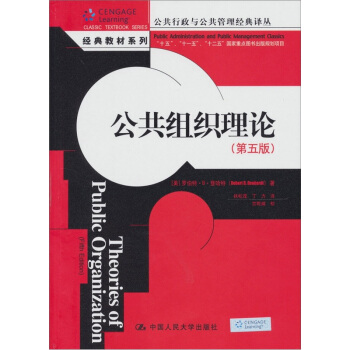

![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嚮 [Creative Involvement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41420/7f69ab62-9fee-4042-afe7-c45794c7772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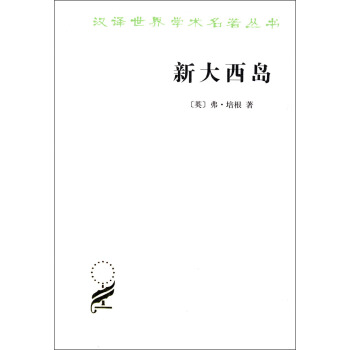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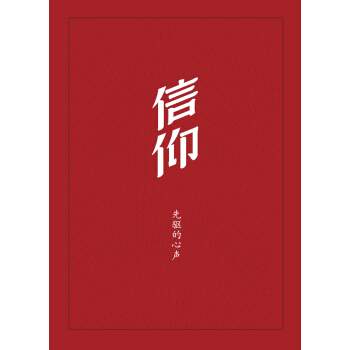
![從西點軍校到鴨綠江:49屆西點軍校學生朝鮮戰場親曆記 [From the Hudson to the Yalu: West Point' 49 in the Korean Wa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27702/rBEhVVJXgzwIAAAAAAQ2PM_9ooYAAEDDQKChJcABDZU76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