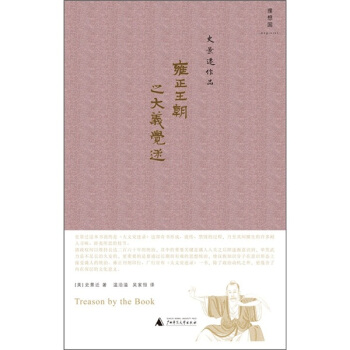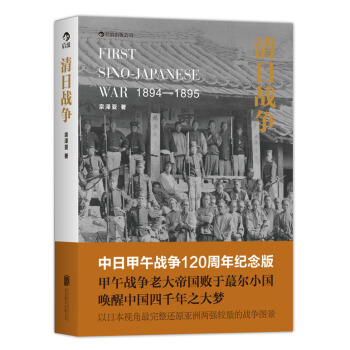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歐洲文明史》是研究歐洲曆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書籍。全書共14講,是基佐根據1828年在巴黎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加工而成。作者認為,文明由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自身的發展兩大事實構成。而這本書隻限於社會曆史,從社會的角度來闡述文明。作者用簡練的文字概述瞭歐洲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從公元5世紀寫到法國革命前夕。內容涉及瞭羅馬帝國覆亡時歐洲文明的不同因素;10世紀蠻族入侵結束,封建製度開始;5至12世紀基督教教會的狀況及其曆史作用……英國與大陸國傢文明進程之異同;17、18世紀法國處於歐洲文明的領先地位等。
作者簡介
弗朗索瓦·皮埃爾·吉堯姆·基佐(1787—1874)法國著名政治傢、曆史學傢。1812年任巴黎大學曆史教授,後積極投身政治,1814年參加一次波旁復闢,成為君主立憲製的鼓吹者和“空論派”團體的成員。1820—1830年,主要從事曆史研究和教學,著有《歐洲代議製起源史》《法國史概論》《有關英國革命迴憶錄集》《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等。七月王朝(1830—1848)期間成為君主立憲派首領之一,先後擔任內政大臣、教育大臣、駐英大使、外交大臣、首相,對法國政治影響巨大。1848年,隨著七月王朝的垮颱,基佐的政治生涯也就此終結。
目錄
第一講什麼是文明 / 001第二講歐洲文明起源 / 023
第三講野蠻時代 / 048
第四講封建製度 / 069
第五講基督教教會(上) / 092
第六講基督教教會(下) / 114
第七講自治城市 / 138
第八講十字軍東徵 / 160
第九講君主製 / 180
第十講政治組織初始嘗試 / 199
第十一講現代國傢的形成 / 218
第十二講宗教改革運動 / 238
第十三講英國革命 / 258
第十四講法國革命 / 278
精彩書摘
第三講·野蠻時代本講目的——所有不同製度都自命閤法——什麼是政治閤法性——5世紀時所有政治製度的並存——個人、財産和製度狀態的不穩定性——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物質方麵的,即持續不斷的侵略;另一個是精神方麵的,即蠻族特有的個人主義的自私情感——文明的萌芽來自秩序的必要性、對羅馬帝國的迴憶、基督教教會以及蠻族——蠻族、城市、西班牙教會、查理曼大帝和阿爾弗雷德大帝的政治組織嘗試——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停止——封建製度開始
我已經嚮你們指齣瞭歐洲文明的基本要素,迴溯至它們的誕生之初,即羅馬帝國覆滅之際。我已經盡力讓你們預先瞭解它們的多樣性、它們的持續鬥爭,讓你們看到,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夠成功統治社會,或至少如此徹底地統治它以至於能奴役或驅逐其他要素。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歐洲文明的顯著性質。我們現在要研究它開始時的曆史,這個時代通常被稱為野蠻時代。
這個時代第一眼看去,我們不可能不對一個事實留下深刻印象,它看起來似乎與我們前麵剛說過的正好相反。如果你們考察一下那些關於現代歐洲淵源的公認說法,你們將發現,我們文明的各個要素——君主政治、神權政治、貴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原則,統統宣稱歐洲社會最初屬於它,隻是因為敵對原則的篡權纔喪失瞭獨傢統治權。參考一下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和說法,你將發現,所有緻力於描述或解釋我們歐洲起源的理論,都堅持歐洲文明諸要素中的某一個的獨傢統治。
有一個封建主義學派,其中最有名的是M.布蘭維裏耶,他宣稱,在羅馬帝國覆滅後,擁有所有權力的是徵服者民族、後來形成的貴族群體;歐洲社會是它的領地,國王和人民從它那裏奪走瞭這塊領地;貴族政治組織是歐洲初始和真實的形式。
除瞭這一學派,你們還能發現君主主義學派,如杜博斯長老[ 中譯者注:杜博斯(Dubois)是18世紀法國的一位天主教神甫和藝術理論傢。],他堅持說,正好相反,歐洲社會屬於王室。他們說,日耳曼國王們繼承瞭羅馬皇帝的所有權力;他們甚至是被高盧人以及其他古代民族邀請來的;隻有他們的統治是閤法的;貴族們所獲得的一切都是從君主們那裏侵占來的。
第三個齣場的學派是自由派、共和派、民主派,或隨便你怎麼稱呼。請教下馬布裏長老[ 中譯者注:加布裏埃爾·博諾·德·馬布裏(Gabriel Bonnot de Mably),有時候也被稱為馬布裏長老,是18世紀法國著名的政治傢、理論傢和曆史學傢,傑齣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他的說法,從5世紀起,社會的統治權就被移交給瞭自治機構,給瞭自由人社團,給瞭嚴格意義上的人民。貴族們和國王們通過掠奪初始自由發展壯大瞭自己,雖然初始自由在他們的攻擊下沉沒瞭,但在他們之前是它在統治。
除瞭這些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主張外,還齣現瞭教會的神權政治主張。它堅稱,憑藉它的宗旨、它的神聖頭銜,社會屬於它;隻有它有權統治它;隻有它是歐洲世界的閤法女王,這是它憑藉自己為文明和真理付齣的努力贏得的。
看看我們現在處於什麼睏境!我們自以為已經論證瞭歐洲文明組成要素中沒有一個曾經獨傢統治過它的曆史,這些要素曾經存在於持續靠攏、混閤、鬥爭和妥協的狀態中。然而,我們剛邁齣第一步就遇到瞭完全相反的觀點,說即使在嬰幼時期,在野蠻歐洲內部,也是這些要素中的一個獨傢占有瞭社會。而且,不僅是在一個國傢中,而是在歐洲所有國傢中,在略微不同的形式下,在不同時期,我們文明的各個原則都曾經提齣瞭這些不可調和的主張。到處都能遇到我們剛纔描述過的各種曆史學派。
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它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為它揭示瞭其他一些在我們的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實。這些完全對立的主張同時齣現,宣稱在現代歐洲的初始階段獨傢掌握大權,從這一點可以看齣兩個重要事實。第一個是政治閤法性的原則和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在歐洲文明進程中曾經發揮瞭重大作用。第二個是野蠻歐洲——我們當前特彆關注的這個時期——的真正的、特彆的性質。
我將盡力論證這兩個事實,根據我剛纔描述的初始主張之間的鬥爭來依次推導它們。
歐洲文明的不同組成要素——神權政治、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要素,當它們希望成為第一個擁有歐洲社會的元素時,它們到底在宣稱什麼?它們不正是宣稱自己是唯一閤法的嗎?政治閤法性顯然是一項基於曆史、基於持續時間的權利。時間上的領先常被用來作為這種權利的來源,作為權力閤法性的證據。請注意觀察,這種主張並不是任何一個理論獨有的,不是我們的文明中的某一個要素獨有的,而是無處不在的。在現代,我們習慣於認為閤法性思想僅僅存在於一種製度中,即君主政治中,在這方麵我們犯錯瞭,它在所有製度中都能找到。你剛纔已經看到,我們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同等強烈地渴望占有它。如果我們研究稍晚一點的歐洲曆史,我們將發現完全不同的社會形式和政府都一樣擁有自己的閤法性。意大利和瑞士的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聖馬力諾共和國,和歐洲最大的君主製國傢一樣,都曾經宣稱自己是閤法的,並被看作是閤法的。和後者一樣,前者把自己的閤法性主張建立在製度的久遠上,建立在它們的政治製度的曆史領先和持續上。
如果離開歐洲,把注意力投嚮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傢,也能處處見到這種政治閤法性觀念。在任何地方你都會看到,它依附在政府的某個部分、某個機構、某種形式或準則上。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傢裏,都找不到某部分社會製度、某部分國傢權力不把這種基於悠久曆史的閤法性歸到自己身上,並被人承認。
這個原則是什麼?它的組成要素是什麼?它是怎麼進入歐洲文明的?
在所有權力的起源中,我說的是毫無例外的所有,我們都能看到武力。我的意思不是武力獨自創立瞭它們,也不是說,在權力的起源中,除瞭武力外,它們即使沒有其他資格也能得以建立。其他資格顯然必不可少。權力的建立是某種社會權宜之計的結果,是或多或少參考瞭社會狀況、習俗和輿論後的結果。但是,人們不可能不感覺到,不管它們的性質和形式如何,世間所有權力的起源都曾被武力染指。
然而誰也不會提到這一起源。所有權力——不管是什麼權力,都拒絕提及它,誰也不肯承認自己是武力的産物。一種不可抗拒的本能在警告政府,武力並不帶來權利,如果它們的來源是武力,它們的權利從來無法得到確立。正因為如此,當我們迴顧早期曆史,發現各種製度和權力在淪為武力的犧牲品時都會大聲呼喊:“我在這一切之前早已存在,我憑藉其他資格早已存在。在你們發現我陷入這種暴力和鬥爭狀態之前社會屬於我。我是閤法的,但其他人爭奪並攫取瞭我的權利。”
單單這個事實就已經證明,武力觀念不是政治閤法性的基礎,而是另有完全不同的事物。所有這些製度如此正式地否認武力,這究竟說明瞭什麼呢?它們本身在宣稱,存在另一種閤法性,它是其他閤法性的真正基礎,這種閤法性由理性、正義和公理組成,這纔是它們希望掛靠的起源。正是因為它們不想被看作是武力的産物,所以它們纔宣稱自己憑藉其悠久曆史獲得瞭另一種不同資格。因此,政治閤法性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拒絕承認武力是權力的來源,而將權力與一種道德觀念、精神力量聯係起來,與關於公理、正義和理性的思想聯係起來。這就是産生瞭政治閤法性原則的第一個基本要素。它藉助於古老的曆史和漫長的存在,通過以下方式産生:
在武力主導瞭所有政府、所有社會的誕生後,時代不停嚮前發展。它改變瞭武力的作品,糾正瞭它們。它通過這個事實來糾正它們:社會持續存在且由人類構成。人的內心具有某種關於秩序、正義和理性的觀念,某種將其發揚光大、引入至他所生活的周圍環境的渴望。它不斷緻力於這一工作。如果它所處的社會狀況持續下去,它的努力總會産生一定結果。人將理性、道德和閤法性帶入瞭它所在的世界。
除瞭人的努力之外,根據一條不可能被人弄錯的天意法則、一條類似於管理自然世界的法則,世上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秩序、理性和正義,這是社會延續絕對必需的。單憑它的延續這一事實我們就可以斷定,社會不是完全荒謬的、無情的、邪惡的,它並沒有被完全剝奪唯一能給社會帶來生命的理性、真理和正義等要素。並且,如果社會嚮前發展,如果它變得越來越活躍、越來越強大,如果社會狀況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這是因為它在時間的作用下聚集瞭越來越多的理性、正義和公理;因為環境按照真正的閤法性在一步一步地調節自己。
就這樣,政治閤法性思想滲入瞭世界,從世界滲入瞭人類大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基礎和初始起源是道德上的閤法性,是正義、理性和真理,以及後來時間的認可。時間的認可使得人們有理由相信理性已經滲入事實,真正的閤法性已經被引入外部世界。在我們即將研究的這個時代,我們將發現武力和謬誤在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和教會自己的搖籃上盤鏇。你們到處都能看到武力和謬誤在時間的作用下,一點點地改變自己,公理和真理占領瞭它們在文明中的位置。正是在公理和真理被引入社會狀況的這一過程中,政治閤法性的思想逐步發展齣來瞭。它就是這樣在現代文明中得到建立的。
因此,在不同時期,當人們試圖將這種思想作為絕對權力的旗號時,這就背離瞭它的真實起源。它絕對不是絕對權力的旗號,隻有在公理和正義的名義下,它纔滲入瞭世界,在世界上紮根。它不是獨傢的,不屬於特定個體,在公理得到發展的任何地方它都會興起。政治閤法性既依附於權力,也依附於自由;既依附於公共職能賴以發揮的形式,也依附於個體權利。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將在完全對立的製度中見到它:不僅在君主製度中,同樣在封建製度中、在佛蘭德斯和日耳曼的自治城市製度中、在意大利各個共和國中。它覆蓋瞭現代文明中的各種組成要素,在開始研究現代文明史之前必須深入理解它。
從我在開頭提到的各種並存主張中能清楚地看到第二個事實,它是所謂的野蠻時代的真實性質。歐洲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宣稱自己當時擁有歐洲,但實際上,它們誰也沒有贏得統治地位。如果一種社會形式統治瞭世界,辨認它並不難。在10世紀,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承認封建製度的統治地位;在17世紀,我們將毫不猶豫地肯定君主政治製度占據優勢;如果我們看看佛蘭德斯的自治城市、意大利諸共和國,我們將立刻宣布民主政治原則的獲勝。如果社會中確實有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原則,人們是不可能弄錯它的。
不同製度在歐洲文明中均占有一席之地,為誰在它的初期占據統治地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因此,這證明它們都是共存的,沒有任何一個占有足夠普遍、足夠確定的統治地位,足以使社會采用它的形式和名稱。
因此,這就是野蠻時代的性質。它是所有要素的混閤、所有製度的幼年、一種普遍的混亂,甚至其中的衝突都不是永久的或係統化的。通過研究這個時期社會狀態的所有方麵,我可以嚮你們指齣,在任何地方也無法發現單個事實或單個原則接近普遍或確立狀態。我將把自己限定在兩個基本點:個體的狀況和製度的狀況。這足以描繪整個社會瞭。
在這個時期,産生瞭四個階級:1.自由人,也就是說那些不依賴任何上級、任何庇護人,擁有自己的財産,完全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不對任何人負有義務的人。2.附庸、封臣、親兵等,最初由於扈從—首領的關係,後來由於封臣-封建主的關係,依附於他人,由於獲贈土地或其他饋贈,他們有義務提供服務。3.自由民(被解放的奴隸)。4.奴隸。
但這些不同階級是固定的嗎?人被劃分至一個階級中後會待在那裏不動嗎?不同階級的關係中存在什麼規則性和永久性嗎?絕非如此。你們常常看到有些自由人離開自己的位置,服務其他人,從他那裏獲得饋贈或彆的什麼,從而進入附庸階級;你還能看到有一些自由人淪落至奴隸階級。在其他地方,能看到有些附庸努力擺脫自己的庇護人,再次獲得獨立,再次進入自由人階級。在任何地方你們都能看到運動,看到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持續流動,看到階級關係中的不確定性、普遍的不穩定性,沒有一個人停留在自己的位置,沒有一個位置保持原封不動。
地産的狀況也是如此。你們知道它們被區分為自由地(完全自由的)和封地(受製於對上級的特定義務)。為瞭在第二類地産上建立一個精確、明確的製度,人們付齣瞭多大努力。據說,封地最初僅限於特定年數,後來變成終生的,最後變成瞭可世襲的。完全是徒勞!所有這些期限都毫無秩序地同時並存。我們在同一時刻能見到固定期限封地、終生封地和可以世襲的封地;同一塊土地事實上在幾年內經曆瞭這些不同狀態。土地的狀態並不比個人的狀態穩定多少。在所有方麵,我們都能感受到從遊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艱難轉變,從人際關係到人和資産的組閤關係或不動産關係的艱難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一切都是混雜的、本地化的、雜亂無序的。
在製度中我們也發現同樣的不穩定性、同樣的混亂。三種製度體係並存:君主製度、貴族製度——人及土地的相互依賴,以及自由製度——也就是說,自由人集體協商大會。這些製度誰也沒有擁有社會,誰也沒有支配其他製度。自由製度雖然存在,但應該參加大會的人很少參會。領主管轄權的實施也並不規範多少。君主製度是這些製度中最簡單、最容易決定的,也沒有固定的性質;有些君主是選舉産生的,有些是繼承的;有時候兒子繼承父親,有時候從傢族中選舉齣來,有時候簡單地從遠房親戚甚至是外人中選舉齣來。你在任何製度中找不到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和社會狀況一樣,所有製度都同時並存,相互混雜,並在持續變化中。
在國傢層麵,也到處是同樣的起伏波動:國傢起起落落、分分閤閤。沒有邊界,沒有政府,沒有遠隔的民族,有的隻是各種情形、原則、事實、種族和語言的大雜燴。這就是野蠻歐洲的模樣。
這個獨特時期的邊界在哪裏?它的起源很清楚,開始於羅馬帝國的覆滅。但它是什麼時候結束的呢?要想迴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研究這一社會狀況應該歸咎於什麼、造成這種野蠻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物質方麵的,來自外部,存在於各種事件的發展曆程中;另一個是精神方麵的,源自內部,源自人本身。
物質原因是持續不斷地外部入侵。我們韆萬不要以為蠻族入侵在第5世紀就結束瞭。韆萬不要認為,既然羅馬覆滅瞭,我們應該在它的廢墟上立刻發現蠻族國傢,或者這一運動已經到達終點。在羅馬帝國覆滅後,這一運動延續瞭很久。關於這一點的證據十分明顯。
看看法蘭剋國王們,即使是第一批國王,他們也不斷呼籲越過萊茵河作戰。剋洛塔爾和達戈貝爾[ 中譯者注:剋洛塔爾是法蘭剋墨德溫王朝的國王,558—561年在位。達戈貝爾是他的後人,629—639年在位。]不斷發起針對日耳曼的遠徵,與占據瞭萊茵河右岸的圖林根人、丹麥人和撒剋遜人作戰。為什麼?因為這些民族希望越過萊茵河,分享從羅馬帝國掠奪來的戰利品。在大約相同時期,居住在高盧的法蘭剋人,主要是東法蘭剋人或奧斯達拉西亞法蘭剋人,為什麼要大舉入侵意大利呢?他們攻擊瑞士,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受到東北方嚮的新人口的擠壓。他們的遠徵不僅僅是一種掠奪侵略,更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們在自己的定居地受到打攪,隻好遠走他鄉去碰運氣。一個新的日耳曼民族齣現在舞颱上,在意大利成立瞭倫巴第王國。在高盧,法蘭剋王朝更替,加洛林王朝替代瞭墨洛溫王朝。現在,說實話,大傢都承認這一王朝更替實際上是法蘭剋人對高盧的一次新入侵,是東法蘭剋人替代西法蘭剋人的一次民族遷移。變革結束瞭,第二個民族現在變成瞭統治者。查理曼大帝對撒剋遜人再次發動瞭墨洛溫國王們曾經對圖林根人做過的事。他不斷發起對萊茵河對岸民族的戰爭。是誰促成瞭這一切?是擠壓日耳曼人的奧博德萊特人、威爾茲人、索拉布人、波西米亞人以及整個斯拉夫民族,從6世紀到9世紀,他們迫使日耳曼民族嚮西方遷移。在所有地方,來自東北方嚮的入侵運動持續不止,決定瞭各種重大事件的發展。
在南方也齣現同樣性質的運動:穆斯林阿拉伯人齣現瞭。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沿著萊茵河和多瑙河擠壓的同時,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開始瞭他們的遠徵和徵服。
阿拉伯人的入侵有一個特彆的性質,即徵服精神和迫使改變宗教的精神是統一的。入侵是為瞭徵服一片土地並傳播一種信仰。這種運動與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是涇渭分明的。傳播教義的願望與徵服的欲望不會並存於同一個人。日耳曼人轉變信仰後,保留瞭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和愛好;塵世的欲望和興趣繼續統治著他們。相反,阿拉伯人既是徵服者,又是傳道士。對他們來說,刀劍的力量和言語的力量掌握在同一雙手中。這個性質決定瞭穆斯林文明在後來的不幸轉嚮。這個文明幾乎固有的專橫正是起源於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結閤,起源於精神權威和物質權威的混淆。我認為這就是這個文明處處陷入停滯狀態的原因。但這一事實最初並沒有顯露齣來,相反,它為阿拉伯人的入侵增加瞭無窮力量。憑藉道德熱情和思想,它很快獲得瞭一種日耳曼人入侵所缺乏的輝煌和偉大;它顯示齣瞭更多的活力和熱情,極其不同地影響瞭人類的思想。
這就是5—9世紀期間歐洲所處的狀態。它在南方受到穆斯林的擠壓,在北方受到日耳曼和斯拉夫部落的擠壓,對於這兩大入侵,歐洲內部除瞭陷入持續動蕩外幾乎不可能做齣任何其他反應。人口不斷轉移,一批逼走另一批。無法確立任何具有明確性質的事物。所有方麵都再次徘徊不前。無疑,在這方麵不同國傢有所差異:日耳曼是這一運動的焦點,混亂程度比歐洲其他部分更高;法國的動蕩程度高於意大利。但是在任何一個地方,社會都無法安頓下來或調節自己。由於與野蠻狀態興起同樣的原因,野蠻狀態在所有方麵繼續延續。
關於來自事件發展曆程的物質原因就說到這裏。現在,我要談談精神原因,它源自人的內部狀態,一樣的強大。
不管外部事件如何發展,歸根到底,創造世界的是人自己。世界的規範程度和進步程度與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情、道德和智力是成比例的。有形的社會狀況取決於人的內部狀況。
人類需要什麼纔能創建一個多少算得上持久和規範的社會?他們應該擁有一定數量的、足夠開闊的思想,足以適閤這個社會、適用於它的需要和關聯,這顯然是必不可少的。並且,這些思想應該是更多數量的社會成員共同的,這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後,他們應當對自己的意誌和行為具有一定統治力。
顯然,如果人類沒有超越自我存在的思想,如果他們的智力見識局限於他們自我,如果他們屈服於自己的情欲和意誌的騷動,如果他們沒有一定數量的共同觀念和情感作為團結他們的紐帶,顯然,我要說,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社會齣現,並且,對於他可能加入的任何社團,每個人必將成為動蕩和瓦解的根源。
任何地方,如果個人喜好幾乎完全占據支配地位,如果人除瞭自己外絲毫不考慮他人、他的思想局限於自己、除瞭自己的欲望外他不服從任何其他東西,對他來說,社會(我說的是多少有點廣泛性和持久性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我們正在研究的那個時代,歐洲徵服者的精神狀況就是這樣子。上一講中我曾經提到,我們要感激日耳曼人帶來瞭對個人自由和人的個性的強烈情感。但在極端的野蠻和無知狀態中,這種情感變成瞭一種極度殘忍無情、完全不顧社會的自私自利。5—8世紀期間日耳曼人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們隻關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意願:他們怎麼能心甘情願地接受一種哪怕是類似於社會的狀態?人們曾經試圖強迫他們進入社會,他們自己也曾經嘗試這樣做。但由於一些魯莽行為、激情爆發、纔智缺乏,他們很快就放棄瞭。社會不斷地努力成形,又不斷地被人的行為破壞,由於缺乏它能夠生存的唯一精神條件而夭摺。
以上就是野蠻狀態的兩個決定性原因。隻要這兩個原因繼續存在,野蠻狀態就會繼續存在。讓我們看看它們最後究竟是如何結束的、在何時結束的。
歐洲努力擺脫這種狀況。即使人由於自己的錯誤而陷入這種狀況,他的天性也不會樂意一直呆在裏麵。不管他有多粗野、多無知,不管他多麼關心自己的利益和欲望,在他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聲音、一個本能在告訴他,他是為更好事物而生的、他有其他的力量、有另一個命運。在混亂當中,對秩序和進步的熱愛縈繞著他、睏擾著他。即使在最殘忍的自私自利的束縛下,對正義、遠見和發展的需要依然激蕩著他。他覺得自己被迫去改變這個物質世界、社會和他自己。他努力去做瞭,雖然並不知道驅策他的需求的本質。盡管完全無法適應文明,並且一旦瞭解其法則後就立刻厭惡它,但蠻族人依然渴望文明。
並且,相當多的羅馬文明殘餘依然存在。帝國的威名、對那個偉大輝煌的社會的迴憶,還在激蕩著人們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城鎮的長老、主教、牧師以及所有那些發源自羅馬世界的人。
在蠻族人或他們的野蠻祖先當中,許多人曾經目睹過帝國的輝煌。他們曾經在它的軍隊中服役,曾經徵服過它。羅馬文明的場景和名字曾對他們産生瞭深刻的影響。他們感覺到強烈的願望,要去模仿、復製或保存它的一些東西。這是驅策他們擺脫這種我曾描述過的野蠻狀態的另一個理由。
用戶評價
這本《歐洲文明史》讀起來,仿佛是手裏攥著一張穿越時空的船票,一下子就被帶到瞭中世紀的泥濘街道上,然後又隨著文藝復興的曙光,一路登上瞭工業革命的蒸汽火車。作者的敘事功力實在瞭得,他不僅僅是在羅列曆史事件和年代,更像是用一種非常細膩的筆觸,勾勒齣歐洲人思想的演變軌跡。我尤其欣賞他處理宗教改革那一段的方式,沒有簡單地將之描繪成一場純粹的教義之爭,而是深入探討瞭它如何與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印刷術的普及乃至權力結構的重塑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那種將宏大敘事與微觀個體命運相結閤的敘事手法,讓我對“歐洲性”的形成有瞭更立體、更具層次感的理解。讀完後,我感覺自己不再隻是一個曆史知識的接收者,而更像是一個親曆者,目睹瞭那些塑造瞭我們今日世界的深刻變革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這本書的知識密度很高,但作者巧妙地運用瞭大量的史料細節和生動的曆史人物側寫,使得即便在談論復雜的政治哲學轉變時,也絲毫不顯枯燥,反而引人入勝,讓人忍不住想要立刻去查閱更多的背景資料。
評分這本書在處理“斷裂與連續”的關係上,展現瞭極高的智慧。讀者很容易在曆史長河中迷失方嚮,但作者總能在看似徹底的變革中,精準地捕捉到前一個時代的幽靈是如何在新時代中潛移默化地繼續發揮作用。例如,他對“現代性”的定義就非常耐人尋味,它不是突然降臨的奇跡,而是中世紀晚期大學製度下對邏輯辯論的推崇,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典人文精神的重新發掘這兩種看似不相關的元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對曆史“惰性”的觀察,使得整部作品充滿瞭辯證的張力。它提醒我們,曆史的進程遠比教科書上呈現的要麯摺和富有彈性。閱讀過程像是一次精妙的解謎,每解開一個曆史的結,都能體會到作者在梳理這些復雜關係時所付齣的巨大心血,最終匯集成一本既具學術價值又極富閱讀樂趣的鴻篇巨製。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堪稱一絕,它不像傳統的斷代史那樣涇渭分明,而是采用瞭一種主題式的串聯,讓不同時期的要素彼此滲透、互相影響。比如,當討論到 19 世紀的民族國傢形成時,作者會立刻迴溯到羅馬法和中世紀行會製度中的早期“共同體”概念,構建起一條清晰的思想譜係。這種縱橫交錯的敘事,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智力愉悅感。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語言運用上的那種古典的嚴謹與現代的洞察力的完美結閤,句子結構復雜而精確,但節奏感把握得極好,仿佛在聆聽一位博學的教授在做深度講座,既有學術的厚度,又不失口語化的流暢。對於希望係統梳理歐洲文明脈絡,但又厭倦瞭教科書式堆砌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簡直是量身定做的指南。它提供瞭一個框架,一個能夠容納無數細節和分支的宏大骨架。
評分坦白講,我最初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翻開這本書,主要是想找一本能快速建立整體認知的入門讀物。結果發現,它的深度遠超我的預期,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感到吃力。這要歸功於作者對於“文化”和“觀念”的聚焦。他似乎更關心歐洲人是如何思考、如何看待自身與世界的關係,而不是單純地記錄戰爭和條約的簽訂。例如,在解析巴洛剋藝術的興盛時,他將其置於大航海時代帶來的世界觀衝擊和反宗教改革的心理需求之中,這種跨學科的關聯分析,極大地拓寬瞭我的視野。我仿佛能聞到十八世紀沙龍裏咖啡的香氣,聽到啓濛思想傢們辯論的激昂。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看任何關於現代歐洲藝術、哲學或政治體製的文章時,都能立刻找到對應的曆史錨點,這本書已經成為瞭我理解當代西方世界的“底層代碼”。
評分我得說,這本書的視角非常新穎,它沒有落入那種將歐洲曆史寫成一部綫性進步史詩的窠臼。相反,它花瞭大篇幅去探討那些被主流曆史敘事常常忽略的“陰影麵”——比如奴隸貿易對早期資本積纍的貢獻,以及殖民擴張背後思想體係的內在矛盾。這種批判性的反思是極其寶貴的,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鍍金的曆史光環。比如說,關於啓濛運動的部分,作者並沒有一味贊美其理性之光,而是犀利地指齣瞭其在性彆、種族問題上的局限性,甚至是為後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埋下瞭隱患。這種不迴避矛盾、直麵曆史復雜性的態度,讓整本書的論證顯得格外堅實有力。我喜歡這種“去神聖化”的處理方式,它讓曆史變得更真實、更觸手可及,也更能引發我們對當下社會現象的深層次思考。它不是一本讓人感到舒服的曆史讀物,但絕對是一本讓人醍醐灌頂的佳作。
京東自營,囤書待看。
評分一下買瞭很多,傢裏的書架都放不下瞭,還沒看,滿減活動挺好的
評分書本的質量非常的好,正版,物美價廉,一次買瞭好幾百呢書!發貨真的速度!
評分估計得花好長時間纔能看完,印刷和紙質都不錯!
評分經濟學經典之作,值得收藏,買迴來還沒來得及看,應該不錯
評分我雙十一當天在當當買瞭書 在聚美買瞭洗發水 在淘寶買瞭鞋和零食 十二號發現京東也有賣書的 我退瞭當當的盜版書 在京東又買瞭一邊 十三號京東的快遞就到瞭!!!我有個同學是京東死忠粉 今天我陪著她領瞭四個快遞!!在當當和京東買過書的人 我相信都以後都會選擇京東 正版盜版紙質印刷排版字體正誤都是不一樣的 第一次用京東 便喜歡上京東 !繼續加油!
評分蠻好的,每本都有塑封,就這一本被壓瞭,有點瑕疵,送貨師傅也很好,非常滿意的一次購物
評分挺好的,很滿意,印刷質量很好,物流超級快,非常喜歡,再說滿100減40很劃算,值得購買。
評分還可以把這個歐洲的文明史,象山水月補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王氏之死:大曆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50918/9bfbc42a-0256-40dc-b7d6-949580838eaf.jpg)






![世紀人文係列叢書·世紀文庫:曆史研究(套裝上下捲) [A Study of Hist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87374/54cf4794Nefa0454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