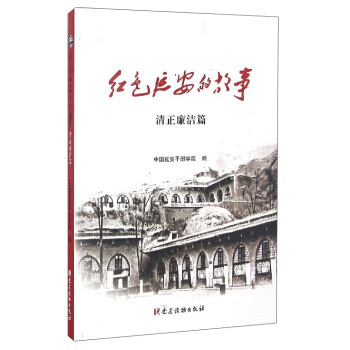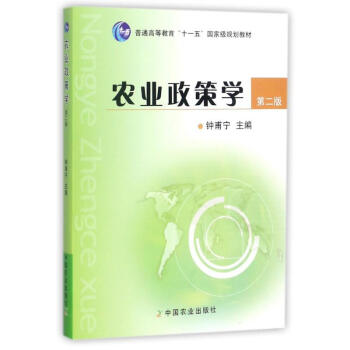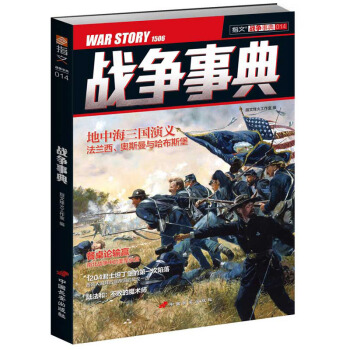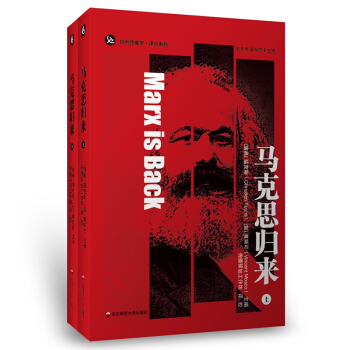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西方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大型全新研究成果1. 在当今之世界,毫无疑问,马克思是所有伟人中被曲解或误读非常多的一位。这种曲解似乎不仅是“现在进行时”,还将是“未来进行时”,只要“资本”还支配着这个世界。
2. 事实上,马克思始终都有其现实性,只是这种现实性在今天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并没有被充分重视,马克思总是被曲解或误解。本书批驳了这些曲解或误解,并说明当下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内容简介
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部,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层面之外,“马克思回来了”之于从事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学者们而言又意义何在?《马克思归来》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回应。《马克思归来》文集为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于2012年出版的特刊,聚焦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了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器武装自己,以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再出发的努力。
《马克思归来》提醒我们:马克思从未离开我们,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他。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应该始终成为我们手中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不是一种装饰或修辞。
作者简介
主编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现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信息与媒介系担任媒介与传播学教授。Triple 杂志编辑,著有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2008),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1),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即将出版)等。主编 莫斯可(Vincent Mosco)加拿大皇后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首席研究员,以及皇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期著作包括: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with Catherine McKercher,2008),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econd edition,2009),以及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edited with Ursula Huws and Catherine McKercher,2010)。
精彩书评
那句昔日共产主义政党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直到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启示。当历史跌跌撞撞地走向核战争和环境灾难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清醒地反映出现实了。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资本主义就是我们的末日。——伊格尔顿
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通过把现实、权力和能动者归于无生命来使自己神话化。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
我们需要反思马克思。若想寻求资本主义的解救之道,那就要去研究这个体系zui伟大的批评者。
——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 Europe, February 2nd , 2009)
目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赵月枝) 1导论:马克思归来/1
第一篇 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27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65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92
反商品化/116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149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168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196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238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283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332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350
第二篇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389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418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499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535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556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579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611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642
第三篇 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665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698
第四篇 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717
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754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787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814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830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Diaspora/870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905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931
精彩书摘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关于《马克思归来》的翻译
赵月枝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虽然每章分别有译者和校对者的署名,但是,本书的“总译者”是“传播驿站”。在我眼里,这是一个比所有署名译者和校对者简单相加更博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通过批判地引介国外“批判传播学”文献来培养中国传播学术自主性理想的承载者,也是一株充满成长的喜悦、痛苦和烦恼的学术新苗。
由于早年留学,我本人很少阅读翻译成中文的传播学术著作,但是,在与国内传播学界的交往中,我逐渐认识到准确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中的学问。正是这一不断强化的认知,孕育了“传播驿站”的最初胚芽。那是2005年,我第一次应邀在复旦大学“中外传播理论和方法论暑期班”讲学。整整3天,共讲了18个小时,累得我几乎没力气开口。这时当年有位正在翻译一本美国传播学专著的年轻学者,拉着我问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包括good一词的在某一句子中的译法。我并没有受过翻译的训练,但看了前后文,觉得不应是翻成英语初学者都知道的“好”,而应该是“良”,犹如good governance翻成“良治”。这位学者大喜。虽然自己当时真的很累,但看着她那激动的样子,我为自己对别人“有用”而感到满足。这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明,而是我从中悟出,一个人在翻译中寻找汉语表达时,需要一双新鲜的眼睛来重新看待那些看起来简单但怎么翻译也不妥贴的字眼。
2006年,还是在复旦大学暑期班讲学期间,我第一次体验到,错翻一个词是多么倒胃口。这年,我在讲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经典文本《“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一文,当我发现在国内某文化研究刊物上已有译文时,喜出望外,这下可以更方便学员们阅读了。可是,当我阅读这篇中译文时,这篇我曾熟读于心的文章却变得非常陌生,甚至十分难懂。当我读到译文中的“贸易联合会”,而我的英文文献记忆中却没有任何霍尔讨论什么“贸易联合会”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译者望文生义,居然把英文中常见的固定名词trade union,也即代表劳工的组织“工会”翻成了一般是代表商人、资本家的“贸易联合会”了!我进而小题大做地胡思乱想起来:在英语语境里,文化研究最初可是关注工人阶级的学问啊,何以这个简单的涉及劳工的词汇经过学术翻译,到中国就成了有关商人的词汇呢,这是偶然的文字错误,还是整个工人阶级被遗忘的后改革时代中国文化研究及其阶级立场的知识症候?是有人把这个词刻意过滤掉的结果,抑或是学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知识结构、语言选择或不够认真导致的?在我眼里,此词的错译几乎是对文化研究和霍尔的极大讽刺和颠覆。我对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2008年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范式恢复了可预期生机。在西方传播学术界,面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危机,许多批判传播学者发现,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通过重读原著来用新的批判武器武装自己,在批判学术道路上重新出发。在此语境下,有了这本致力于信息时代的批判传播研究的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的特刊——《马克思归来》。我也曾受邀参与为该特刊写文章,但一来忙,二来自己当时指导的一名优秀博士生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正在潜心阅读马克思,并有理论创新,且有意参与这个项目,所以自己不参与也就释然了。不过,我当时推测,中国批判传播学术的青黄不接和冷战意识形态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的长期影响将意味着,在中国这个虽然有一批学者因通晓马克思著作和研究马恩列斯新闻传播思想而获博士学位的国度,却可能不会有任何人是这本特刊的作者。
这更加催生了我组织翻译这本特刊的热情,我希望通过集体翻译活动,从一个字、一个词、一篇文章的翻译开始,通过相互协作和翻译工作坊的形式,训练年轻华人学者群体的批判学术意识和对英文文献的分析能力。当时,我正好在筹划成立中国传媒大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以就把这项工作当作这个研究所最主要的奠基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两位学者朋友的鼎力支持:一位是本丛书的主编之一吕新雨教授,一位是在华人传播学界译作颇丰、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翻译经验的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我们一致认为,把这辑特刊当作书系中“译丛”系列的一种,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中国传播学界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需要知道国外学者是如何重新开始的;另一方面,由于这本特刊的作者并不都是名家,而是有像我的博士生那样初出茅庐的西方作者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这就有利于打破国内学者对国外文献的“经典”性和权威性的既有假定,而以更平等和更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文献。
于是,“传播驿站”应运而生。当时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即将毕业的博士生龚伟亮以很大的热情投入了初期的工作。我们在“招兵买马”的“启事”中写道,这是一个主要由处在学术起步阶段的博/硕士生和年轻学者组成的翻译团体,旨在批判性引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以及训练青年学人在对原著的译介和批评过程中获得学术思考的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厉兵秣马,从而进一步“获得学术萌芽的养料与思想入门的钥匙。”“启事”还充满期望地认为,“传播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批判传播学的价值支持与重新定向,同时也亟需一批有历史视野、中国立场,同时又有国际眼界的知识青年的薪火相传”。因此,这个从翻译工作入门、围绕一个“译”字的“传播译站”,“愿意成为为年轻学生(学者)提供批判视野的给养、助力他(她)在学术征途中策马扬鞭的学术‘驿站’”。“启事”最后写道,这个学术新生事物“将以蓬勃的朝气和反思的锐气、主体的自觉与智识的品格,以及严谨的学风和友爱的精神树立批判传播学术译介的旗帜与品牌,推动有学术志向的青年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促进批判传播学的发声与发展,以具有扎实独立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后备军的培养为基础,为中国批判传播学学术影响力与团队学术声势的壮大以及整个传播学学科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有高远立意的最初“启事”的涵义上,我们把这本书译者的署名位置给予了“传播驿站”。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个“驿站”的协调机构和活动平台依托我们几位所在的院校,采取统一协调(共同遵守一致的时间统筹与技术规范)、分头运作的工作方式,以我们周边“有志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年轻学子力量为中坚,辐射和带动京沪等地其他高校以及海内外的年轻学生(学者)共同推动批判传播学著作的引介与批评”。我们希望,这一方面可为本书系中的“译丛”系列提供优质稿源,另一方面也为本书系中的“文论”系列以及为以新锐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学术工作坊(类似2012年成功举办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工作坊”)培养和输送梯队人才。
“传播驿站”以引介国外大型有影响或有里程碑意义的批判传播学文献为己任。按照“传、帮、带”的学术承传理念,我们组织有志于批判学术的年轻博士生做翻译者主体,让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做译校,以单篇文章为单位组织团队进行工作。翻译阶段的工作流程包括组队、选译、试译、初稿、一校、二校等步骤,每篇文章的译校以不同层次学者互助合作的方式协作完成。完成初步译校后,我们组织工作坊,让译者和校对者就翻译中的难点和问题交流意见,寻找解决方法;与此同时,让参与者对所负责的文章结合中国的学术语境进行批判分析,以求共同提高,并在此过程中对国外文献进行甄别和“去魅”,培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总之,工作坊既是一次译介成果展示,又是一次可以提升翻译水准的集体校阅,更是促进思想的批判性吸收的头脑风暴。
《马克思归来》成了我们“初试牛刀”的实验。项目参与者很多,大家热情也很高。2013年盛夏,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为期两天的“《马克思归来》翻译工作坊”上,海内外年轻华人学子,包括冯建三教授团队中来自英国等地的年轻学者,围绕一篇篇文章的认真讨论场面令人激动,我至今记忆犹新。正是在这个工作坊上,我看到了华语批判传播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未来希望。
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学术工作是辛苦的、繁琐的;翻译工作很难,同时又被认为是“低端”的,甚至是学术“绩效”上不算数的。随着项目进入“深水区”,有人中途而弃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而且影响到了这个刚呱呱坠地的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然而,也许正是有了“驿站”这个理念所内涵的精神,个别人的“掉链子”并没有拖垮整个共同体的集体意志,大家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步一步把工作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积累经验,之后才会少走弯路,做得更好。
我感谢所有参与过本书翻译工作的年轻学者——包括一些参与过这个项目不同阶段和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最后并不在译者或校对者署名中出现的学生和学者,包括冯建三教授和邱林川教授。无疑,这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大家精诚协作、团结友爱的结晶。
这里,我有必要提及一些特殊的个体。首先,我要由衷感谢吴畅畅,他不仅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这个项目的上海团队组织工作,而且在这个项目推进最困难的时候,不但默默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还负责了多篇文章的校对,以及组织了整部书最后的统筹和校对。在“传播驿站”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吴畅畅无疑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其次,我要感谢张志华,为了推进项目进度,无论翻译、校译还是其他相关的组织工作,他都不计分内分外地全力以赴踏实工作,甚至不惜推迟了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博士论文的进度。另外,姬德强、高明等也自始至终积极参与本项目的工作,为校对稿子花费了不少心思。特别是项目收尾的关键时刻,张韵、沙垚、范松楠、朱清河、张晓星和陈思博等人对“传播驿站”工作无条件接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满满的认真、大度和宽容——她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准备了近两万字的工作坊笔记,这些笔记最终以综述的方式在此书以附文的方式出版,读者因此可以管窥工作坊的一斑。
最后,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和彭文曼编辑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以及他们的耐心。殷鹏博士为本书的最后统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特此致谢。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作为本书的轮值主编,我愿对本书翻译中的不完善之处负责,欢迎读者帮助纠错和批评。
本书是“传播驿站”这个集体译者的第一部习作。在漫长的3年工作过程中,我们这支团队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我们经历了成长的痛苦,甚至挣扎和失望。但是,我们汲取教训,改进方法,整合团队,重新上阵。2014年盛夏,我们以新的姿态和新的阵容,在复旦大学围绕《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的译介,成功举办了第二期翻译工作坊。我们请来该书的两位编者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在工作坊上与参与者交流,深入讨论本书的背景、编辑理念和主题思想。我们不但在工作坊上热烈讨论了书中的观点立场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还请每篇文章的译者或校者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写出作为文章导读的重要内容。本书的注释保持了单篇的统一。
作为“驿站”概念在中外学术交流和批判传播学者代际承传与超越意义上的演绎,在2014年的工作坊上,我们还请来了我的加拿大博士生、《马克思归来》的作者之一罗伯特?普雷(Robert Prey),分享他在博士论文中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史上知名的“盲点争论”的最新颠覆性挑战观点。普雷这位学术新秀与当年这一争论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雷厄姆?默多克教授在复旦大学面对面讨论,使一看来是初学者“练兵场”的翻译工作坊成了国际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术的最前沿阵地。现在,普雷的博士论文尚未答辩,就凭着自己的理论创新和优异学术成果成了荷兰知名的格罗宁根大学助理教授了。在与我道别的午餐上,他还念念不忘他的中国之行在他学术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归来》付梓之际,《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的译校工作已近尾声,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播驿站”还会有第三部、第四部译作问世。“驿站”本身就意味着永远再出发。实际上,在国内的一些学术场合,当我听到有人自我介绍说听过我在复旦暑期班的演讲,还有人自我介绍参与过“传播驿站”的工作,当我碰到年轻学者问我是否还继续翻译工作坊时,我知道,“传播驿站”这朵批判传播学中的“奇葩”,已经发挥了她的作用。她不是当下流行语中作为耻笑对象的“奇葩”,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让人惊艳的花朵。在当下充满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浮躁情绪的学术圈里,以她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在学术百花园中扎根,有一席之地。诚邀本书的所有读者一起培植她,使她结出更多、更丰硕的好果实。
谨此,是为序。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绝对是一本能够挑战你认知边界的书。我起初以为它会是一本相对“硬核”的理论著作,但实际读起来,它更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对话,一场思想的盛宴。作者的论述方式非常独特,他(她)并不急于抛出结论,而是层层递进,引导读者自己去发现、去理解。那些看似晦涩的概念,在他的(她的)笔下变得生动而易于把握,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感。我最欣赏的一点是,这本书并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将经济、政治、哲学、社会等多个维度融会贯通,形成了一个宏大而严谨的逻辑体系。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反复思考作者提出的观点,并对照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这种阅读体验是极具启发性的,它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学会了如何更深入地剖析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这本书像是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更深层思考的大门,让我看到了许多之前从未注意到的联系和规律。
评分我向来不是一个喜欢读理论书籍的人,但这本书却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它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阐释了一些宏大且抽象的概念。作者的叙述方式充满了智慧和幽默感,他(她)善于用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那些复杂的原理,让原本遥不可及的思想变得触手可及。我尤其喜欢他(她)在书中展现出的那种批判性思维,他(她)并不盲目崇拜权威,而是鼓励读者独立思考,质疑一切。这种精神在当下尤为可贵。阅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它让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一些固有观念,并且尝试着用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去面对世界。这本书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引导我去探索问题,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理解。我非常享受这种思考的过程,它让我感到自己正在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评分我是一个对历史题材的书籍情有独钟的读者,而这本书无疑是我近期阅读中最具震撼力的一部。作者的功力体现在他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上,那些被遗忘的年代、被忽略的事件,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了生机。他(她)并不只是简单地复述史实,而是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逻辑,探究人物行为的动机,以及这些选择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一些复杂的历史矛盾时,展现出了极高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他(她)并不预设立场,而是将不同派别的观点和立场都清晰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种严谨的态度,让我对书中内容的信任度大大提高。此外,本书的叙事节奏也非常吸引人,时而紧张激烈,时而舒缓深沉,仿佛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史诗,让人欲罢不能。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亲眼见证了那些重大的历史变革,感受到了人物命运的无常与抉择的艰难。
评分这本书拿到手的时候,我就被它的封面深深吸引了。那是一种带有复古感的色彩搭配,还有一些我不太理解的符号,但整体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历史感,仿佛一打开就能穿越回某个时代,窥见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火花。迫不及待地翻开第一页,我就被作者流畅而富有张力的文笔勾住了。他(她)的叙事方式并非那种按部就班的流水账,而是巧妙地穿插了各种视角和叙事线索,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拼接,就像在解开一个复杂的谜题。我尤其喜欢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时那种细腻入微的刻画,每一个角色的内心挣扎、每一次情感的波动,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而且,作者并没有刻意去拔高或者贬低任何人物,而是以一种近乎客观的态度,将他们置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展现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困境,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让我觉得,书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被简单地符号化。阅读这本书,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深度对话,与历史,与思想,与人性。
评分作为一名对社会议题比较关注的读者,我发现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且深刻的分析框架。作者的切入点非常新颖,他(她)并没有选择从宏观的角度去进行泛泛而谈,而是从一些具体的、往往被我们忽视的细节入手,逐渐揭示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我喜欢他(她)那种抽丝剥茧式的论证过程,每一个论点都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和严密的逻辑之上,让人无法辩驳。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许多我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并且开始思考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作者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温度,读起来不会感到枯燥乏味。相反,他(她)的文字常常能够触动人心,引发深思。这本书让我对社会结构、权力运作以及个体在其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更多的思考。
评分挺不错的,送货速度也很快,好评
评分老婆买来看的书,还行
评分京东图书,双十一活动入手!
评分帮同学买的,独特的视角
评分不错
评分老婆买来看的书,还行
评分京东图书,双十一活动入手!
评分京东图书双十一大促,3-2!
评分京东图书,双十一活动入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闪电战:日本陆军在东南亚的猖狂进攻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19647/58466a6bNe9aea02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