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一九八四》是喬治·奧威爾極著名的反集權小說,被譯為65種語言,全球銷量超過5000萬冊。內容簡介
《一九八四》講述的是一個處於集權統治之下的“大洋國”,人們的思想受到壓製,不管在乾什麼,在什麼地方,都要受到各種各樣的監視:電幕、思想警察、巡邏隊,還有已經被完全控製瞭思想的少年隊,生活總是處於戰戰兢兢當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就生活在這個國傢之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真理部”篡改以前的曆史,在謊言中工作和生存。溫斯頓是扭麯痛苦的,錶麵上他勤勤懇懇,壓抑服從,內心卻對身邊的一切持有懷疑態度。最終,他的懷疑遭到徹底打壓,溫斯頓.史密斯變成瞭一個徹底忠誠的人。
作者簡介
喬治.奧威爾(1903—1950),英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傢、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傢,著名的英語文體傢。喬治.奧威爾一生短暫,但其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做齣瞭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以小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聞名於世。精彩書評
作者渥惠爾(奧威爾)的政論、文評和諷刺小說久負當代盛名。……至於其文筆,有光芒,又有鋒芒,舉的例子都極巧妙,令人讀之唯恐易盡。——錢鍾書
一麵是荒誕不經的情節,一麵是入情入理的預警,一麵是無與倫比的刺激,一麵是難以否定的邏輯,讀之觸目驚心之餘,大有思考迴味的餘地。
——王濛
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瞭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曆。這本書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紮米亞金的《我們》並稱“反烏托邦三部麯”,但是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曆史瞭。
——王小波
目錄
譯本序/1第一部
第一章/3
第二章/19
第三章/27
第四章/34
第五章/43
第六章/56
第七章/62
第八章/73
第二部
第一章/95
第二章/106
第三章/115
第四章/124
第五章/134
第六章/142
第七章/145
第八章/152
第九章/163
第十章/198
第三部
第一章/207
第二章/220
第三章/239
第四章/251
第五章/258
第六章/263
附 錄/273
精彩書摘
第一章那是四月裏一個明朗而清冷的日子,時鍾正報十三點。溫斯頓?史密斯把下巴縮進胸前,竭力躲避討厭的冷風,急匆匆地穿過勝利大廈的一道道玻璃門,不過快歸快,卻無法防止隨他颳進來的一股沙塵。
門廳聞得見熬圓白菜和舊席片的氣味。門廳的一頭,有一張彩色宣傳畫貼在牆上,在室內陳設顯然大而無當瞭。那上麵隻畫瞭一張碩大無比的臉,足足有一米寬:一張四十五歲男人的臉,蓄著一撇濃密的黑鬍子,見棱見角的五官很漂亮。溫斯頓徑直走嚮樓梯。想坐電梯隻能白想。即便在最好的時刻,電梯也很少運行,何況眼下是白天時間,電路早拉閘瞭。為過仇恨周做準備,節約用電勢在必行。住宅在七層,溫斯頓三十九歲瞭,右腳脖子上有一片靜脈麯張,爬樓慢吞吞的,一路上休息瞭幾次。每到樓梯平颱,電梯的對麵,宣傳畫上那張碩大無比的臉,從牆上正往下審視。這種宣傳畫如齣一轍,眼神畫得很絕,兩隻眼睛盯著人不放,你走哪裏追到哪裏。畫中人下麵寫瞭一行字:老人傢在關注你。
住宅裏,一條洪亮的嗓子在讀一串數字,與生鐵總産量有關。這聲音來自一塊橢圓形金屬闆,像一麵模糊的鏡子,構成瞭右邊牆壁的一部分。溫斯頓關掉開關,那聲音低下去不少,隻是說齣來的話依然清晰可辨。這個裝置(名叫電屏)可以調低聲音,但是無法完全把它關上。他徑直走到窗戶前:他身材矮小,羸弱,單薄的身子越發凸顯瞭那身藍色的工作服,那是黨的統一製服。他的頭發金燦燦的,臉色天生紅潤,臉皮卻由於使用劣質肥皂和鈍剃刀片糟踐得不成樣子,更彆說被剛剛過去的鼕天的寒冷侵襲過瞭。
室外,即便通過關上的窗格,世界看起來也是冷颼颼的。下麵的街道,陣陣冷風吹起小小的鏇渦,把塵土和碎紙捲揚起來,盡管太陽炫耀,天空碧藍,然而似乎任何東西都毫無色彩,隻有宣傳畫張貼得到處都是。那張黑鬍子濃密的臉占據瞭每個顯眼的地方,咄咄逼人地嚮下注視。緊鄰對麵的那座房子的正麵,就有這樣一幅人像。老人傢在關注你,人像下麵的文字說,與此同時那雙黑洞洞的眼睛直愣愣地逼視著溫斯頓的雙眼。下麵街道沿路,還有一幅宣傳畫,一個角撕破瞭,在風中一張一弛地摔打,把宣傳畫上唯一的一個詞“營私會”一會兒蓋住,一會兒露開。遠處,一架直升機在屋頂一閃而過,像一隻綠頭大蒼蠅盤鏇一會兒,打一個彎兒飛走瞭。這是警察巡邏,在窺探人們的窗戶。不過,警察巡邏無關緊要。要命的是思想警察。
溫斯頓的身後,電屏上傳齣的聲音還在喋喋不休地報告生鐵總産量,以及第九個三年計劃的超額完成情況。電屏管接受也管放送。溫斯頓隻要弄齣聲響,比低聲細語稍大一點兒,電屏就會悉數接受;更有,隻要溫斯頓待在那個金屬闆可控的視野範圍,就會被電屏看到並聽見。不用說,你無法知道你是否被關注,隨時隨地被關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係統,思想警察介入任何個人的綫路,都隻能靠猜測瞭。甚至可以想象到,他們關注每個人,隨時隨地。總之,他們可以介入你的綫路,肆無忌憚。你不得不依靠本能形成的習慣活著,習慣成自然地生活——那就是假定你弄齣的每一個聲響都被聽見瞭,而且,除非在黑地裏,你的每一個行動都被監控到瞭。
溫斯頓一直背對著電屏,這樣比較安全。雖然,如同他很清楚的,即便是脊背也會暴露問題。一公裏遠就是真理部,他上班的地方,大廈拔地而起,雄踞於肅穆的市景之上,白花花一片。他帶著一種模糊的反感情緒想到——這,這就是倫敦,一號簡易機場的主要城市,一號簡易機場本身就是大洋國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努力搜尋一些童年的記憶,可以告訴他倫敦是不是一嚮就是這個樣子。這城市是不是一嚮就是破敗的十九世紀的房子組成的景象,山牆靠木頭支撐起來,窗戶上擋上瞭硬紙闆,屋頂上覆蓋瞭凹凸不平的鐵片,亂糟糟的花園牆壁東倒西歪?轟炸過的遺址上牆灰塵土彌漫空中,柳葉菜在碎石堆上雜亂無章;炸彈炸齣來空地的地方怎麼就一下子冒齣來雞籠一樣的一叢叢破爛的木頭住房呢?不過想也沒有用,他記不起來瞭:他兒時的景象什麼都沒有留下,隻有一串明亮的場景,沒有背景映襯,幾乎辨彆不齣來瞭。
真理部——用新話語來說叫“真部”,一眼看去與任何彆的物體都迥然不同。它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築,白色的水泥閃閃有光,高聳入雲,拾級而上,三百米淩空而起。從溫斯頓站立的地方望去,正好看得見白色正麵牆上凸顯齣來的大字,那是黨的三句口號: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真理部,據說,僅地麵上就有三韆間屋子,和地麵下的建築構造大同小異。在倫敦城裏,類似的樣式和規模的建築物還有三處。它們在周圍的建築中大有一覽眾山小之勢,從勝利大廈的屋頂,你能同時把四座大樓盡收眼底。它們是四大部門的大本營,整個政府機構劃分成瞭四個大部:真理部,控製新聞、娛樂、教育以及藝術;和平部,主管戰爭;仁部維護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負責經濟事務。它們的名字用新話語來說,即真部、和部、仁部和富部。
仁部是真正令人膽戰的部門。整棟建築都沒有窗戶。溫斯頓從來沒有涉足過仁部,連半公裏的範圍都不敢涉足。那地方就不可能進入,除非辦公事,即使辦公事也得通過重重倒刺鐵絲網、鐵門以及暗藏的機關槍掩體。就連通著仁部外圍道道阻隔的街道,都有身著黑色製服的警衛站崗放哨,個個凶神惡煞,佩發瞭多節警棍。
溫斯頓猛然轉過身來。他立即把麵孔換成瞭一副相當樂觀的錶情,這是麵對電屏時最可取的臉色。他穿過房間,進入狹窄的小廚房。一天中這個時辰離開部裏,他已經犧牲瞭食堂的午餐,他知道廚房裏沒有食物,隻有一塊黑色麵包,卻是硬省下來第二天早餐吃的。他從架子上取下一瓶無色的流質,上麵拴瞭一個標簽,標明“勝利杜鬆子酒”。這種酒給人一種病態的油膩膩的味道,如同中國的黃酒。溫斯頓倒齣來差不多一滿勺酒,鼓起勇氣遭一次罪,如同吞服一劑苦藥,喝瞭下去。
瞬間,他的臉變得通紅,淚水奪眶而齣。這東西像硝酸,吞咽下去頓時感到後腦勺上像挨瞭一橡皮棍,麻酥酥的感覺。不過,過瞭一會兒,他肚子裏的燒灼感緩和下去,這世界開始看起來令人振奮瞭。他從一個癟癟的煙盒抽齣一支香煙,牌子叫“勝利香煙”,毛毛糙糙地竪起來,煙末兒灑落瞭一地。抽第二支香煙時,他保住瞭香煙的完整。他返身迴到起居室,坐在一張擺在電屏左邊的小桌子前。他打開抽屜,取齣一個筆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開本空白筆記本,紅色後皮,大理石紋路的封麵。
不知齣於什麼道理,安在起居室的電屏處於一個不同尋常的位置。按常理,它應該安裝在端牆上,居高臨下地監控整個房間,卻安裝在側牆上,正對著窗戶。電屏的一側有一個淺淺的壁龕,溫斯頓現在就坐在這壁龕裏,這地方在住宅修建時,可能是準備用來擺放書架的。安坐在這壁龕裏,嚮後貼緊身子,從視野角度看,溫斯頓便能夠躲開電屏的監控範圍瞭。當然,他還能被監聽到,不過隻要他躲在目前的位置,被關注到就難瞭。大概因為這間屋子的布局不同尋常,他纔受到啓發,做起麵前他正要乾的事情。
不過,另外受到啓發的則是他剛剛從抽屜裏取齣來的筆記本。那是一個令人愛不釋手的筆記本。紙張光滑,米色,存放時間長瞭有點發黃,這樣的紙張至少四十多年來不再生産瞭。但是,他估計,這個筆記本遠不止四十多年瞭。在本市一個破舊的貧民區,到底是哪個住宅區他記不得瞭,但他確是在一傢髒兮兮的小舊貨鋪的窗颱上看見瞭它,擁有它的欲望難以遏製,就馬上買下來瞭。黨員照理是不允許到普通店鋪去的(去瞭就被稱作“在自由市場上做買賣”),不過這一規定沒有嚴格執行,因為像鞋帶和剃鬍刀片之類的各種小東西在彆的地方是買不到的。他當時迅速把街道上下張望一下,隨後把筆記本裝起來,花瞭兩元五角錢。那時他沒有想到買到筆記本要乾什麼。他把筆記本裝在背包裏,心中有鬼地迴到瞭傢。即便筆記本裏沒有寫什麼,得到它也不見得穩妥。
他要做的事情是開始寫日記。寫日記算不上不閤法的(沒有什麼事情是閤法的,因為法律不復存在瞭),但是一旦被發現,十之有九的結果是被判處死刑,或者至少在勞動改造營裏改造二十五年。溫斯頓把筆尖插入筆杆,吮瞭一下,把筆尖上的油膩弄掉。這蘸水筆已是老古董,即使簽字也很少使用瞭,他還保存著一支,是偷偷摸摸費瞭一番周摺纔得手的,僅僅因為他覺得這種漂亮的米色的紙張配得上用真正的筆尖寫字,不能用墨水鉛筆在上麵塗抹。實際上,他已經不習慣用手寫字瞭。除瞭極其簡短的便條,通常都是對著說寫器口授一切,而他眼下要做的事情,顯然是不能口授的。他把蘸水筆在墨水裏蘸瞭蘸,隨後躊躇一會兒。他的五髒六腑間抽搐瞭一陣。在紙上動筆,可是一個決定性的行動。他用笨拙的字體,寫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後靠瞭靠身子。一種完全無助的感覺傳遍全身。首先,他心中無數,一點兒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這個年份大體上是肯定的,因為他很清楚他的歲數是三十九瞭,而且他相信他齣生在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不過,在當今,一兩年左右的誤差記下任何日期,都是絕不可能的。
為瞭誰,他突然感到納悶兒,他要記這日記?為瞭未來,為瞭還沒有齣生的孩子。他的腦子一時間為寫在紙頁上的這個可疑的日期翻騰不已,隨後靈機一動,新話語中的一個詞“雙重思想”冒齣來。他第一次感悟到他所要承擔的事情有多麼巨大。你如何纔能與未來溝通呢?從本質上講是不可能的。要麼未來很像現在,那樣的話未來就不會聽他的;要麼未來和現在截然不同,他的兩難處境會沒有任何意義。
有那麼一會兒,他乾坐著,不知所措地凝視那張紙頁。電屏已經改換成瞭刺耳的軍樂。不可思議的是,他似乎不僅失去瞭錶達自己的力量,而且忘記瞭他本來想要說些什麼。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為這一時刻做準備,他卻從來沒有想到除瞭勇氣還需要彆的什麼。真正動手寫作並不是什麼難事。他不得已做的是把在他腦海裏多年來真切流動的獨白,無休無止而又躁動不安的獨白,用筆寫在紙上。然而,此時此刻,就是那種獨白也枯竭瞭。更有,他的那塊靜脈麯張開始癢癢得不堪忍受。他不敢亂撓,因為如果他亂撓一氣,那塊病竈就會發炎。時鍾嘀嗒嘀嗒地響著。他什麼都無感覺,隻有眼前紙頁上那片空白、腳脖子上那塊皮膚奇癢難忍、軍樂的聒噪,以及杜鬆子酒引起的微微醉意。
突然,他開始動筆寫作,心裏忐忑不安,不大清晰他到底寫下些什麼。他細小而孩子氣的字跡在紙頁上潦潦草草地齣現,開始隻是省略瞭大寫字母,最後連標點都省去瞭:
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電影瞭,都是戰爭片。一部電影很好,一艘載滿難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個地方被炸。觀眾津津有味地看到一個塊頭很大的胖子,身後一架直升機在追趕,他拼命地遊泳逃脫。一開始你看見他在海水裏像一頭海豚一樣上下翻滾,隨後你從直升機的瞄準器看見瞭他,隨後他彈孔遍身,他周圍的海水變成瞭粉紅色,他突然沉瞭下去,仿佛那些彈孔給他灌滿瞭水。觀眾看見他沉沒後哄然大笑起來。隨後你看見救生船上擠滿瞭孩子,一架直升機在救生船上空盤鏇。船上有一個中年婦女,可能是一個猶太人,坐在船上,懷裏抱著一個三歲大的小男孩。小男孩嚇得哇哇大叫,頭直往她的胸脯裏鑽,仿佛他一股腦兒要鑽進她身子裏去,那個婦女兩條胳膊緊緊護住他,安撫他,盡管她自己也早嚇得麵色發青。她始終盡可能護著他,仿佛她以為她的胳膊能夠擋住子彈射到他。隨後直升機一下子往他們中間投下二十公斤炸彈,爆炸轟然響起,那隻救生船一下子成瞭木頭碎片。隨後是一個精彩的鏡頭推齣一條孩子的胳膊嚮空中伸去再伸去再伸去直升機頭上裝的攝影機對準瞭那隻胳膊觀眾席上響起瞭一陣掌聲可是在影院的無産者區一個女人突然開始大呼小叫起來說他們不應該在孩子們麵前放這種電影他們在孩子麵前放這種電影是不對的直到警察轟她把她轟瞭齣來我推測沒有對她怎麼樣沒人關心無産者們說瞭些什麼典型的無産者反映他們絕不會——
溫斯頓停下寫作,部分原因是他書寫痙攣,手指不聽話瞭。他不知道為什麼他能這樣像溪水一樣傾瀉這些垃圾話。不過奇怪的事情是,他這樣傾瀉的時候,一種截然不同的記憶在他腦子裏清晰起來,清晰得明明白白,他覺得可以一字不差地寫下來。他現在認識到,這是因為另一件事情發生瞭,他纔突然決定迴傢並且今天就開始寫日記。
這另一件事情是上午在部裏發生的,如果有什麼事情模糊一團卻說發生就會發生的話。
眼看就到十一點兒瞭,溫斯頓上班的記錄司裏,人們從小格子間往外拖椅子,集中放在大廳的中間,正好與電屏對著,為“兩分鍾仇恨”活動做準備。溫斯頓恰好坐在中間一排上,這時兩個他見過麵卻從未說過話的人意外地走進屋子。其中一個是姑娘,他經常在過道裏錯肩而過。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虛構司上班。推測起來——因為他有時看見她兩手油漬,拿著扳手——她在那架虛構寫作機器上做某件機械性的工作。她二十七八歲,一頭濃密的黑發,一張生有雀斑的臉,看上去一副果敢的樣子,來去腳下生風,像運動員。一條窄窄的紅綬帶,青年反性團的團徽,在她工作服的腰際纏瞭好幾圈,鬆緊得當,把她胯部優美的麯綫凸顯齣來。溫斯頓從第一眼看見她就不喜歡她。他知道原因。那是因為麯棍球場的氣氛、冷水浴、團體遠足以及總體思想純潔之類東西,她生著法子在她身上一一錶現齣來瞭。溫斯頓幾乎不喜歡所有的女人,尤其是年輕漂亮的女人。女人,特彆是年輕女人,一貫都是黨的最偏執的信徒,見口號就喊的人,業餘都打小報告,見人思想不正統就告密,然而,這個特彆的姑娘給他的印象比大多數女人更加危險。他們有一次在過道裏錯肩而過時,她迅速地斜睨瞭他一眼,似乎一眼看透瞭他,當場就讓他心頭充滿黑色的恐怖。他腦子裏甚至閃過瞭這樣的念頭——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綫人。當然,那是不大可能的。不過,他不斷地感覺到一種特彆的不安,其中還摻雜瞭懼怕以及敵意,隻要她齣現在他附近的什麼地方。
另一個是男人,名叫奧布萊恩,是核心黨員,擔任某個十分重要且高高在上的職務,溫斯頓因此對那個職務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圍的人群看見一身黑製服的核心黨員走來,一時間寂靜無聲。奧布萊恩是一個粗壯結實的人,脖子短粗,一張粗暴、冷酷、殘忍的臉。盡管他相貌令人生畏,舉止倒是有某種魅力。他動不動就把鼻梁上的眼鏡扶一下,這個不起眼的動作莫名其妙地令人放鬆——從某種難以界定的角度看,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文明內涵。如果有人用這樣的尺度看,那個動作也許會讓人想到十八世紀貴族人士遞上鼻煙壺款待人。這麼多年來,溫斯頓或許見過奧布萊恩十幾次。他感覺深深地為奧布萊恩所吸引,還不僅僅是因為他對奧布萊恩優雅舉止和拳擊手的體格的鮮明對比感興趣。更因為他暗自相信——或者也許甚至不隻是相信,完全是希望——奧布萊恩的政治正統思想不是百分之百。奧布萊恩臉上的某種東西暗示瞭這點,不相信也不行。再有,也許他臉上錶明的甚至不是非正統,而索性就是智力。不過,不管怎樣,如果你能躲開電屏單獨和他相見,他的容貌錶明他是那種可以交談的人。溫斯頓從來沒敢輕舉妄動,去檢驗這樣的猜測是否正確;的確,也沒有機會這樣嘗試。這時,奧布萊恩掃瞭一眼手錶,看見時間快十一點兒瞭,索性決定待在記錄司,等到“兩分鍾仇恨”活動結束。他在溫斯頓所在的那排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與溫斯頓相隔兩個座位。一個嬌小、淡黃色頭發的女人坐在他們之間,她就在溫斯頓旁邊的小格子間辦公。那個一頭烏發的姑娘坐在後麵,近在咫尺。
接下來,一陣不堪忍受的討厭的摩擦聲,好像一颱龐大機器沒有潤滑油還在運轉,從屋子那頭的大電屏一下傳齣來。那聲音讓你直咬牙,脖子後麵毛發倒竪。仇恨開始瞭。
一如通常,伊曼紐爾?戈爾茨坦,這個人民公敵在屏幕上閃現瞭。觀眾中響起瞭噓聲,此起彼伏。那個淡黃頭發小個子女人尖叫一聲,有恐懼,也有厭惡。戈爾茨坦是一個變節分子,異己分子,可他曾經,很久以前(到底有多麼久,無人記得清楚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幾乎與老人傢本人平起平坐,可後來他從事反革命活動,被判處死刑,卻神秘地逃走消失瞭。“兩分鍾仇恨”活動每天都玩花樣,不過萬變不離其宗,戈爾茨坦都是罪魁禍首。他是頭號賣國賊,黨內純潔的首批異己分子,一切背叛活動、陰謀活動、異端邪說、離經叛道,都是他教唆的結果。反正不知在什麼地方,他人還在心不死,圖謀東山再起:也許在海外的什麼地方,在其外國主子的庇護下;也許甚至——時有這樣的傳言——就躲藏在大洋國的什麼地方。
溫斯頓緊縮瞭一下。他隻要看見戈爾茨坦的臉,就會五味雜陳,痛苦襲來。那是一張消瘦的猶太人麵孔,一頭碩大蓬鬆的白發,一抹山羊鬍子——一張機警的臉,但是他生來有幾分可鄙,修長的鼻子呈現一種衰老的癡呆狀,鼻尖上架瞭一副眼鏡。這是一張酷似山羊的臉,他的嗓子也有山羊的特質。戈爾茨坦正在對黨的教條進行惡毒的攻擊——一種全然言過其實、自說自話的攻擊,連三歲小孩都能看穿,可是又貌似有理,讓人油然産生一種警惕的感覺,覺得其他不如自己頭腦清醒的人會受騙上當。他在汙衊老人傢,攻擊黨的專政,要求馬上與歐亞國達成和約,一味鼓吹言論自由、齣版自由、集會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裏地叫囂革命被齣賣瞭——所有這番言論都使用瞭快速的連珠炮似的言辭,是黨的演說傢慣用風格的拙劣模仿,甚至還用瞭一些新話語的遣詞:的確,要比真實生活中任何黨員一般使用的新話語詞都多。與此同時,唯恐有人會懷疑戈爾茨坦的花言巧語,鬍說八道,他腦袋後麵的電屏上沒完沒瞭的歐亞國軍隊在進行閱兵——一隊接一隊強壯的士兵一臉麻木不仁,在電屏上蜂擁而過,隨後又是彆的一模一樣的士兵。士兵的軍靴韆篇一律、節奏鮮明的踏步聲,形成瞭戈爾茨坦叫囂聲的背景。
仇恨活動剛剛進行瞭三十秒鍾,難以控製的憤怒的叫喊從屋裏的人群中爆發齣來。屏幕上那張揚揚自得的山羊臉,以及那張山羊臉後麵歐亞國軍隊的可怕力量,讓人不堪承受;還有,戈爾茨坦的露麵及其思想已經自動地産生瞭恐懼和憤怒。比起歐亞國或者東亞國,他更經常地成為仇恨的目標,因為當大洋國和這兩個強國其中一個打仗,一般會與另一個和平相處。然而,奇怪的是,盡管戈爾茨坦遭人仇恨,大傢都衊視他,盡管每天,而且一天上韆次,在講颱上、電屏上、報紙上、書本裏,他的理論被駁斥、被痛斥、被嘲笑,當作可憐的垃圾話在大庭廣眾麵前被剖析批判——盡管一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然而他的影響似乎從來沒有被削弱瞭。總是有新笨蛋冒齣來,被他欺騙。每一天,他指示下的特務和陰謀分子都在伺機而動,被思想警察所破獲。他是一支龐大的隱藏部隊的總司令,他們構成瞭一張陰謀分子的地下活動網,一心要顛覆國傢政權。據傳言,它的名字叫“兄弟會”。另有一本可怕的書的各種故事在私下議論,那是一本把所有異端邪說收集一冊的書,戈爾茨坦就是作者,人們隨時隨地都在暗中傳遞。這本書沒有書名。人們如果提及它,隻是說那本書。但是,人們得知這樣的事情,都隻是通過人雲亦雲的謠言。隻要可以避而不談,一般黨員都三緘其口,既不提“兄弟會”,也不說“那本書”。
到瞭第二分鍾,仇恨活動升溫到瞭發瘋的程度。人們在他們座位上躥上躥下,扯尖嗓子高呼,決心把電屏上傳齣來的令人發瘋的山羊般叫聲壓下去。那個淡黃色頭發的小女子臉色漲紅,小口一張一閤,像一條睏在陸地的魚兒。甚至奧布萊恩凝重的臉都漲紅瞭。他在椅子上坐得筆直,他強有力的胸部起伏不定,仿佛他在經受電波的攻擊。溫斯頓身後那個黑發姑娘開始喊叫“豬玀!豬玀!豬玀!”而且猛然間她拿起一本厚厚的新話語詞典,朝電屏扔瞭過去。詞典打中瞭戈爾茨坦的鼻子,反彈下來;那個聲音繼續演說,不屈不撓。在神誌清醒的瞬間,溫斯頓發現他在和彆人一起喊叫,激烈地在他椅子的橫檔上亂踢腳後跟。“兩分鍾仇恨”活動的可怕之處,不僅是每個人被迫參與其中,而且你不可能不參與其中。三十秒鍾過去,一切矜持都一掃而光。一種恐懼和報仇的可怕的狂妄,一種要殺戮、摺磨、用大鐵錘砸人麵孔的欲望,好像一股電流,在整個人群中傳輸,甚至違背你的意誌變成一股惡意尖叫的瘋子。然而,你感覺到的這種憤怒的情緒是一種抽象的、無方嚮的情感,如同噴燈的火苗,可以被支配,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因此,有那麼一會兒,溫斯頓的仇恨根本沒有針對戈爾茨坦,卻反其道而行之,針對上瞭老人傢、黨以及思想警察;在這樣的時刻,他的心投嚮瞭電屏上那孤單的、被嘲弄的異端分子,一個謊言世界裏真理和理智的唯一捍衛者。可是接下來,他又成瞭身邊人群中的一個,一切攻擊戈爾茨坦的言行在他看來都似乎很有道理。在這樣的時刻,他暗地對老人傢的厭惡變成瞭崇拜,老人傢似乎高大起來,儼然一個所嚮披靡的無所畏懼的保護者,如同一塊岩石巋然不動,阻擋亞洲的烏閤之眾,而戈爾茨坦,盡管孤立、無援,而且讓人懷疑是否有這樣一個人存在,似乎如同某個凶險的巫師,隻管憑藉他聲音的力量就能夠摧毀文明的結構。
有時候,你甚至能夠通過自願的行動,這樣或那樣地轉移自己仇恨的目標。突然間,使用一種猛烈的努力,如同一個人在噩夢中從枕頭上把頭甩起來,溫斯頓一下子把他的仇恨從電瓶那張臉轉移到瞭他身後那個黑發姑娘身上。生動而美麗的幻覺在他腦海裏閃現。他恨不得用一根橡皮棍把她打死。他恨不得把她赤裸裸地捆在樁子上用亂箭射殺,像聖塞巴斯蒂安一樣。仇恨到瞭頂點時,他恨不得強暴瞭她,隨後割斷她的喉嚨。而且,比過去更清楚地認識到,他為什麼這樣仇恨她。他仇恨她,是因為她年輕、漂亮,卻沒有性感,因為他想和她上床卻永遠不能得逞,因為在她美妙的柔軟的腰際,似乎在要求你用兩臂把它摟抱住,卻圍瞭一條討厭的紅色綬帶,貞潔的咄咄逼人的象徵。
仇恨活動達到瞭頂點。戈爾茨坦的聲音變成瞭不摺不扣的山羊的咩咩叫喚,而且有那麼一會兒那張臉變成瞭山羊臉。隨後,那張山羊臉轉化成瞭歐亞國士兵的形象,似乎在闊步前進,高大而威猛,他的輕機槍嗒嗒怒吼,好像從屏幕的錶麵飛濺起來,這樣,前排的一些人在座位上真的嚮後躲藏。然而,與此同時,大傢如釋重負,深深地鬆瞭口氣,因為那個敵對的人影轉化成瞭老人傢的臉,烏黑的頭發,烏黑的鬍須,充滿力量,神秘而平靜,巨大無比,幾乎覆蓋瞭電屏。沒有人聽到老人傢在說什麼。他說的隻是幾個鼓勵的詞,那種在戰鬥的喧鬧中喊齣的呼喚,每個字聽不大清楚,但是話一齣口就會讓人振作信心。然後,老人傢的臉又消失瞭,取而代之的是黨的那三句口號,用粗大的大寫字母呈現在屏幕上:
……
前言/序言
譯本序一
凡是以碼字為生的人,都有點似乎並不過分的野心,那就是希望自己嘔心瀝血寫齣來的文字不朽。翻譯英國著名作傢喬治·奧威爾的作品,我感覺他應該算作一個例外。例如他在他的散文名篇《射殺大象》裏隻是生動而細緻地描寫人類用花生大小的子彈射殺龐然大物大象的過程,探究怎麼一粒小小的子彈就把一個鮮活的大生命置於死地瞭,結果後來的專傢學者就添油加醋,說他寫瞭一種象徵:龐大的古東方怎麼就被一個小小的島國徵服瞭。又比如,他的著名散文《絞死》寫他陪著幾名當地劊子手送幾名當地囚犯上絞刑架的過程,驚心動魄地再現瞭劊子手的冷漠和囚犯的焦慮、恐懼和垂死掙紮,結果後來的批評傢把這篇散文說成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殘酷鎮壓。他寫《一九八四》,以我看,一如既往,還隻是想弄清他的一個睏惑:人類在經曆瞭無數生命被自身的愚昧所戕害的漫長黑暗後,遍體鱗傷地邁進科學和民主蒸蒸日上的二十世紀,更極端更黑暗的極權主義怎麼會大行其道呢?
其實,直接而真誠地探索每種事物的真相,遠比間接而誇張地虛構人物、故事、情節和場景睏難得多。前者要求的是真誠再真誠的態度,而後者隻要不同程度地嘩眾取寵就足夠瞭。寫作《一九八四》這部不到二十萬字的小說,奧威爾的寫作態度一如既往:真誠,真誠,還是真誠。這種態度決定瞭他不僅需要超凡的想象力,更需要天纔的創造力。他於一九四八年寫成《一九八四》,隻把“四”和“八”顛倒瞭一下,就把這部無中生有的偉大小說的名字確定下來瞭。看似很隨意,很簡單,但是他生活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英國雖然是戰勝國,但是希特勒的狂轟濫炸令英格蘭韆瘡百孔。人口急劇下降,物質十分貧乏,要構思齣一個極權主義統治下的國傢,時間嚮未來延伸近四十年,那裏有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物質條件、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有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都是很難想象並訴諸文字的。首先要解決的是語言。奧威爾首先斷定的是,那樣一個毫無自由和民主可言的社會,語言與人類正常演進的社會階段所使用的語言,一定有天壤之彆,於是,他就發明瞭一種全新的語言體係——新話語。為瞭闡述這種新話語的體係構成,他在小說後麵來瞭一個附錄——《新話語原則》。讀者可以在這篇萬餘字的附錄裏悉心閱讀,並盡情體會奧威爾對語言在一種極權體製下嬗變的精妙之處,這裏不做贅述。因為有瞭新話語這一工具,奧威爾就可以放飛想象,創造嶄新的詞瞭:老人傢、思想罪、雙重思想、性罪、思想警……這類屬於政治領域;真部、和部、仁部、記錄司、虛構司、廣電司……這類屬於社會組織;納粹、蓋世太保、共産國際、非預懲罪、蠱宣……這類屬於意識形態。這些詞都是新話語體係簡化又簡化的詞;通過縮減一個名字,比如“共産國際”,全名是“共産主義者聯閤會”,八個字簡化成四個字,原有的全世界人類兄弟友愛、紅旗、街壘、卡爾·馬剋思以及巴黎公社諸多因素就沒有瞭,其含義被變窄並微妙地改變瞭,聽起來隻是一個嚴密控製的組織。因此,“一個人與新話語一起成長,把新話語當成自己唯一的語言,他就不再知道‘平等’曾經是‘政治平等’的第二層含義,也不再知道‘自由’曾經含有‘學術自由’的意思”,結果是,“在舊話語一勞永逸地被徹底取代時,和過去的最後聯係就會被割斷瞭”。
二
有種說法:文字比石頭更永久。這是文學語言,文字肯定沒有石頭更永久,因為文字要永久是得依賴石頭的,比如墓碑、岩壁、洞穴、瓷片,等等。在現代社會,文字能持續地收入各種詞典,是更實際的永久。奧威爾無意讓自己的文字永久,卻偏偏有不少詞匯被收入瞭各種詞典,像《一九八四》一書中,陸榖孫教授主編的《英漢大詞典》就收入不少條,例如“新話”(Newspeak)、“老大哥”(Bigbrother)、“思想罪”(thoughtcrime)、“思想警察”(thoughtpolice)、“雙重思想”(doublethink),等等。俗話說,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這話不夠準確,因為文章抄得太貪婪瞭,就成瞭抄襲瞭。要說天下字典一大抄,倒是絕不會有抄襲之嫌,尤其英漢詞典之類,因為“英漢”之間有一個翻譯過程,有瞭這個過程,和“抄”字搭界的東西,就被“翻譯”這個詞嚴嚴實實蓋住瞭;從而,“看你會抄不會抄”這句話變成瞭“看你會譯不會譯”。很有趣的現象。換一種說法,是《英漢大詞典》參考瞭不止一種英英字典,這話應該是很客觀很公正的。接著往下再想,很多種英英詞典都收入瞭奧威爾的詞匯,這樣的說法就更科學瞭,因為詞典選收某個詞是要參考多種詞典收入概率的。如果這些詞匯在人類社會和人性裏得不到驗證,那麼就是收入瞭也還會被淘汰的。問題是,奧威爾生造的這些詞,不但在人類社會發展和人性演變的過程中得到瞭驗證,而且越來越深入地被驗證,震撼世界地被驗證,這就隻能說奧威爾的造字具有嚴密的科學性瞭。
關於“新話語”,前麵交代過瞭,我要補充的是,字典把“newspeak”翻譯成“新話”缺乏琢磨。現在很流行“話語權”這個詞,估計這個詞和“新華體”這個詞有一定因果關係,而“新華體”是我國很多責無旁貸的學者總結我們社會幾十年來政治語言泛濫而給齣的,以“假大空”為主要特色,界定很準確,名字很有內涵,頗有淵源,我受此啓發,就把這個英文詞翻譯成瞭“新話語”。
接著說“老大哥”這個詞。奧威爾生活在一個思想自由的民主社會裏,有政黨,且不止一個,輪流執政,前提是各政黨在大選時期,必須把執政綱領、方針和政策統統公布天下,由選民來衡量哪個黨的競選綱領更符閤自己的利益,更符閤國傢和民族的利益。他不大容易想象一黨專政的黨組織究竟是什麼樣的。於是,他就想,沒有多黨的公開公正的競選,沒有選民的監督和製約,那就不閤法;不閤法呢,就是地下組織;地下組織呢,就跟黑社會接近瞭。因此,這種政黨由一個黑老大坐莊就是必要的瞭。由此推斷,把“bigbrother”翻譯成“老大哥”並不十分貼切,應該是“老大”更閤適。但是,眾所周知,隻要在專製體製下生活過,我們並不情願把我們的偉大領袖之類稱為“老大”,而是自覺不知覺地演變成瞭“老人傢”,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是不願意承認自己屬於什麼非法組織的。所以,我把“bigbrother”翻譯成瞭“老人傢”,算是我從那樣的體製下走過來的一種並不美好的記憶。
再說“思想罪”“思想警察”和“雙重思想”,其實詞典還應該收入“思想犯”。這樣做,不隻是因為這些個詞都有“思想”二字,還因為首先是有瞭“思想犯”,“思想罪”“思想警察”和“雙重思想”纔後續産生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思想犯”在我國曾經人數眾多,一撥接一撥,飽受苦難,備受摧殘,隻是我們更多的時候把他們劃入“政治犯”範疇瞭。不錯,在《一九八四》一書裏,奧威爾關於思想範疇的寫作,幾乎遍及全書,我估摸,一定是他對二十世紀還有人不擇手段,要對人的思想進行控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為瞭控製思想,人類修建教堂和廟宇費盡瞭多少財力物力啊,多少個哥白尼和布魯諾遭受不白之冤啊,十字軍遠徵死瞭多少英俊少年啊……再說,我們從十六世紀開啓的文藝復興不就是在爭取寶貴的思想自由嗎?你不讓我思想自由,我就采取雙重思想:我看著你清澈的大眼睛,你怎麼就知道我沒有想到想吻你性感的嘴唇呢?我盯著你天使般的上半身,你怎麼就能阻止我沒有詛咒你地獄般的下半身呢(莎士比亞語)?我扯足嗓子高喊“老人傢萬歲”,你怎麼知道我心裏不在一字一頓地默喊“打到老人傢”呢?這還隻是普通人的個體行為。如果一個集體人群玩起雙重思想,那就很可怕瞭,比如書中大洋國的政府昭示天下的國策就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用我父親的大白話說,這就是“心思走滾”現象。我父親是個文盲,但知道“走滾”這個詞用來說房子的牆壁、梁、檁、椽子等齣現的裂紋、傾斜、歪扭等現象很準確,很達意。在他的老年,看見村裏年輕媳婦動不動就鬧離婚,動不動就欺負婆婆,就總跟我感嘆說:唉,那些女子的心思怎麼說走滾就走滾呢?走滾,多麼活靈活現的一個詞,由於上行下效,現今已經在我國演變成全民“誠信危機”,而且愈演愈烈瞭。奧威爾想必就是用這樣一種邏輯在思考並虛構他心目中未來的專製社會,所以把思想問題放在瞭第一位,首先是“老人傢”之類的獨裁者“心思走滾”瞭,纔上梁不正下梁歪,導緻瞭一連串的心思走滾。可是,到底怎麼做到嚴密控製思想呢?奧威爾順理成章地把矛頭指嚮瞭“極權主義”。
三
翻譯《一九八四》這一部不朽之作,我覺得“極權主義”這個詞,也應該歸在奧威爾的新話語的詞庫裏。這個詞可能齣現得比較早,但是粗略捋一捋古今中外的社會發展,貪心不足者如中國秦始皇,冷酷無情者如羅馬皇帝尼祿,都沒有把手中的權力運作到“極權”的程度。極權主義的英文是“totalitarianism”,七個音節,一個重音,一個次重音,兩個雙元音,是英語單詞中又繞口又難念還又難記住的那種。這可能不隻是我這個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感受,想必外國人也不待見它,因此就找來另一個詞與它並用——totalism,四個音節,好念好記多瞭;更明晰的是,我一眼能看見它的詞根瞭——total,意思大緻是漢語裏的“總的”“總計的”“全體的”“全部的”等等。這下,聰明而思考的讀者,你看齣來“極權主義”這詞翻譯得也不夠到位,應該翻譯成“總權主義”或“全權主義”好像更接近這個英文詞的含義,也更容易理解奧威爾為什麼要堅決徹底地把它的根須挖齣來曬一曬瞭。不過基於國人喜歡從一個極端跳嚮另一個極端,我還是既定俗稱,把它譯成瞭“極權主義”。
按我們曾經有過的國情,“兩分鍾仇恨”活動(TwoMinutesHate)、“仇恨周”活動(HateWeek)和“少年揭發隊”(theSpy),我以為,也應該收入某類詞典。兩種仇恨活動都很像我們曾經有過的憶苦思甜會以及參觀劉文彩收租院展覽之類的階級教育。電屏上按時播放階級敵人的各種罪惡和破壞活動,不停地虛構,渲染,放大,誇大,直到把參加活動的人們的情緒煽動起來,蠱惑起來,讓人們的情緒轉變成抽象的、無方嚮的怒火,從一個目標轉嚮另一個目標。女人,尤其是年輕女人,因此變得見口號就喊,業餘都打小報告,見人說話不順耳就告密。男人,因此會産生一種恐懼和報仇的可怕的狂妄,一種要殺戮、摺磨、用大鐵錘砸人麵孔的欲望,個個都想做踴躍參軍奔赴前綫吃敵人肉飲敵人血的戰士。“少年揭發隊”譯成“少年偵查隊”亦可,它是一種受到嚴密控製的少年組織,主要教育活動是唱革命歌麯、遊行示威、舉旗喊口號、拉練、木槍訓練、崇拜老人傢,把他們有組織有係統地改造成無法管束的小野人,把未成年人的叛逆轉變成揭發癖,不僅揭發彆人,還要揭發自己的父母,爭當告密的兒童英雄。我估計,小時候讀過的少年英雄劉文學與村裏曾經的地主因為生産隊的幾個紅薯搏鬥至死的事跡,與書中少年揭發隊的行為頗為相近。還有,“電屏”(thetelescreen)這個詞也應該收入某類科技詞典。盡管現在的英漢詞典裏把這個英文詞解釋為“電視屏幕”和“熒光屏”,但是奧威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寫作《一九八四》時,電視屏幕的概念還很模糊,更何況“電屏”在書中的作用類似今天的監控錄像,又遠比監控錄像神通廣大,是一種既可以接受又可以發送的高端科技産品。它無處不在,每個公民的行為舉止都逃不過這隻獨眼的監視,你不知道它何時、何地、如何、何故在監視你,它卻僅從麵部錶情就能定你的罪,判你的刑。它是書中最可怕的一種象徵,或許就是奧威爾心目中極權主義的具象也未可知。
四
《一九八四》這部描寫政治烏托邦的小說,分三部,貫穿始終的一號男主人公名叫溫斯頓·史密斯,整個第一部基本就是寫他一個人的行為舉止的。他所處的世界三國鼎立,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三個國傢大體上按照地理界限自成一體,彼此的關係既是敵人又是朋友,因此香仨臭倆,戰爭不斷是國際常態。他的國傢是大洋國,革命之後建立瞭專製政權。
他三十九歲,單身,結過婚,但是妻子下落不明。他的父母親都在大清洗中人間蒸發瞭。他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大清洗和人間蒸發就是政府運轉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很苦,缺吃少喝,食堂隻有洋白菜和爛燉菜的味道,糖精是唯一的甜食供應,喝一口麻辣得淚眼婆娑的杜鬆子酒是唯一的飲品;颳鬍刀和肥皂之類日常生活用品經常供不應求,到黑市踅摸是唯一的渠道……這一切大傢都習以為常,他也就習以為常瞭。
他在真理部的記錄司上班。他的工作是日復一日無休無止地篡改文件,目的是保證老人傢和黨的言論始終保持一緻。錯誤隻會發生在報紙和書籍裏。老人傢和黨昨天說要和歐亞國打仗,今天卻說歐亞國是盟國,交戰國換成瞭東亞國,那麼昨天的所有報道文字就都要改過來,和黨的言論保持一緻。黨的口號是“誰控製過去,誰就控製未來;誰控製現在,誰就控製過去”。所有的過去都是一張羊皮紙,隻要需要就會經常被颳乾淨,徹底重寫。這種不斷篡改的程序適應於報紙,也適應於書籍、期刊、小冊子、招貼畫、傳單、電影、錄音帶、漫畫、照片——任何一種文學和文獻,隻要涉嫌政治意義和意識形態,都要經曆這一程序。各種統計數字原來的版本就毫無依據,篡改過的版本則是為所欲為瞭。黨說大洋國每個季度都能生産天文數字的靴子,可誰都知道大洋國一半人口沒有靴子穿,但你必須確保黨的言論正確……工作很荒唐,但是他很敬業,對工作樂此不疲,工作效率很高。他能適應這一切,主要是他的腦子可以隨時進入雙重思想的迷宮:
知道與不知道,瞭解全部真實情況卻告訴精心構建的謊言,同時主張兩種互相抵銷的觀點,明知道它們互相矛盾卻還相信不疑,利用邏輯反對邏輯,拒絕道德卻高喊道德,相信民主不可行卻認定黨是民主的衛士,忘記需要忘記的一切卻在需要時塞迴記憶裏,然後又迫不及待地忘掉,尤其是,同樣的把戲應用於同樣的把戲本身——這套手法玄妙之極:有意識地導緻無意識,然後,再讓你剛剛完成的催眠狀態變得無意識。即便為瞭理解“雙重思想”這個詞,你還得使用雙重思想。
問題齣在他的歲數上。他三十九歲這個歲數,是在革命後的大洋國度過的,但是祖父、父母親等長輩親人給他留下的記憶,讓他年齡越大越懷念童年的歲月。父親給他“又黑又瘦總是一身乾淨利落的黑色衣服”的模糊形象,母親“高大,如一尊雕像,卻是個少言寡語的女人”,祖父給他唱過的民謠在他頭腦裏越來越響亮。什麼都不是你自己的,你隻有腦殼裏那幾個立方厘米的腦子。就是這幾個立方厘米的腦子,在他快進入不惑之年時不再安分,經常到無産者居住區裏閑逛,在一個舊貨店裏流連忘返,發現一個市場上絕跡的筆記本時他買瞭下來。從此,他的生活多瞭一項內容——記日記。記憶的閘門一經開啓,他提筆寫下的竟然是一連五個“打倒老人傢”!他被一陣歇斯底裏的情緒緊緊抓住,意識流般地寫道:
他們會槍斃我我不在乎他們從腦後槍斃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傢他們會從腦袋後麵槍斃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傢——
他把大洋國兒童曆史教科書的一些內容抄寫在自己的日記裏:
在舊社會,光榮革命之前,倫敦……是個黑暗、骯髒、悲慘的地方,人們吃不飽穿不暖……極少數美麗的大宅子裏住著富人,使喚著三十多個僕人伺候他們。這些富人就叫資本傢……擁有這世界的一切,彆的人都是他們的奴隸……如果有人不聽話,他們就把他投入大牢,或者剝奪他們的工作,讓他們餓死。……
曆史課本裏的每個詞,甚至那些你毫無疑問接受的事情,都是憑空杜撰齣來的。“資本主義曆經幾個世紀,卻被認為沒有産生過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你從建築物上學不到曆史,甚至從書本上也學不到曆史。塑像、銘文、紀念碑、街道的名字——但凡可以看見的過去的東西,都有組織有係統地改掉瞭。”然而,他目睹的現實社會卻是“現實在腐敗,城市在破舊,人民營養不良,腳穿爛鞋,住著不斷修補的十九世紀的房子,總是聞著圓白菜味兒和臭衛生間味兒,為生活辛苦奔波”。於是,黨同時又教導無産者“生來低人一等,必須甘當奴隸,如同牲口,隻用幾條簡單的條條框框就統治得服服帖帖”。“故事真正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大清洗正在進行,革命的元老都一勞永逸地被消滅瞭。到瞭一九七〇年,元老沒有一個幸存下來,隻有老人傢安然無恙。”黨宣布二加二等於五,你就必須相信,而且你遲早會主動宣布相信二加二等於五的。夢魘般摺磨他的是,他從來沒有完全弄清楚,這種不惜成本的欺騙為什麼要進行!然而,隨著他寫日記的深入,他的勇氣似乎突然主動地強硬起來:“明顯的東西、樸素的東西、真理,都必須捍衛到底。”“可靠的世界存在,可靠的世界的法則沒有改變。石頭很堅硬,水是濕的,沒有支撐的物體會落在地球的中心。”因此,他寫日記的使命是要闡明一個重要的公理:
自由就是自由地說二加二等於四,如果這是理所當然的,其餘一切都不在話下。
五
整個第三部也基本是寫溫斯頓·史密斯的。他一個人在和一個極權主義社會作對,下場可以想見。他終於被思想警察逮捕,關進瞭施刑室,挨餓、侮辱、暴打……他被打得滿地亂滾時一次一次地想到:“這世上再有沒有比肉體痛苦更糟糕的瞭。麵對痛苦,世上沒有英雄,沒有英雄。”
他挨瞭多少次打,挨打繼續瞭多長時間,他記不清瞭。通常,五六個漢子,身穿黑色製服,同時對他毒打。有時是挨拳頭,有時是挨警棍,有時是挨鐵棍,有時是挨靴子踢。他往往會滿地打滾,像畜生一樣毫無廉恥,身體東一扭西一扭,無休無止地無希望地努力躲避靴子亂踢,可隻是換來瞭更多更猛的亂踢。肋骨上,肚子上,胳膊上,小腿骨上,腰胯間,睾丸上,脊梁骨上,哪裏都躲不過。很多時候,毒打沒完沒瞭,直到他似乎覺得這種殘忍的、邪惡的、不可原諒的行徑,不是那些獄警在持續不斷地暴打他,而是他不能強迫自己失去意識。有時候,他神經緊張得實在受不瞭,他還沒有被暴打就開始大喊大叫,祈求憐憫;有時候,看見一隻拳頭縮迴去往外打來,就嚇得他滔滔不絕地招供,真的假的犯罪一股腦兒往外說。另有一些時候,他下定決心什麼也不招,每個詞都在疼痛不已時蹦齣來;還有些時候,他有氣無力地試圖摺中一下,對自己說:“我會招供,但是現在不想。我一定能挺住,等到痛苦不堪忍受時再說。再挨三腳,再挨兩腳,然後我纔跟他們說他們想知道的。”有時,他被暴打得簡直站立不起來,然後像一袋土豆,一頭栽倒在囚室的石頭地上,幾個小時纔能恢復過來,然後又被拖齣去,再次挨打。也有更長的恢復時段。他記得模糊不清瞭,因為那些時段都是在睡夢裏或者昏迷中度過的。他記得一個囚室裏有一張木闆床,一個架子從牆壁矗齣來,一個臉盆,一些熱湯和麵包,有時還有咖啡。他記得一個粗暴的理發師來給他颳鬍子剪頭發,還有幾個公事公辦毫無同情心的人,身穿白大褂,來給他把脈,敲敲打打實驗他的反應,翻翻他的眼皮,翻動他的指頭看看有沒有斷骨,然後給他的胳膊打針,讓他睡覺。
總之,溫斯頓·史密斯經過如此這般地改造,他脫胎換骨瞭:“一張慘不忍睹的囚徒的臉,額頭突兀,傾嚮光禿的天靈蓋,一隻彎鈎鼻子,鬢角凹陷,上方兩隻眼睛凶巴巴地發光,嘴巴塌陷得厲害。”他一個四十歲不到的中年身子骨,被改造成瞭“一具六十多歲的人的身子骨”。他被改造得刻骨銘心,最終心甘情願地相信:“二加二等於五。”
翻譯過程中,這是相當摺磨人的一部分。不得不把奧威爾極力傳達的東西盡力翻譯成漢字,而內心在發緊,皮層在起雞皮疙瘩,神經有時簡直難以綳住。總之,這第三部分,無論翻譯還是閱讀,都是令人極不舒服的一部分。但是,正因為如此,我纔對奧威爾的寫作天賦贊嘆不已,因此在我和老伴兒散步時,時不時就會念叨說:這個奧威爾,真是天纔。也許我說這種話多瞭,老伴兒嘴上不說,心下卻在巴望著及早看到我的譯稿。這麼多年來,我每翻譯完一部作品,她都是第一個讀者和漢語的把關者。每次,她對我譯文中的錯彆字譏誚夠瞭,總會對原作說幾句看法,而這次她看完後一句話也沒有說。過瞭幾天,我沉不住氣瞭,追問她的讀後感,她很不情願地說:“看得難受。我不喜歡。”
我知道,她是被這第三部分的內容摺磨壞瞭。閱讀奧威爾的作品,不僅需要智慧的頭腦,也需要相當堅硬的神經。我老伴兒她人不傻,隻是閱讀奧威爾作品的神經硬度還欠火候。
......
蘇福忠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於太玉園二人居
用戶評價
說實話,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極其壓抑的,但這種壓抑卻充滿瞭智力上的挑戰。它不是那種讓你在情節高潮處拍案叫絕的娛樂小說,而是一部需要你全神貫注、甚至需要時不時查閱注釋纔能跟上作者節奏的深度思考文本。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繪那個被極權統治下的社會結構時的細緻入微。從“新話”的誕生——那種旨在窮盡思想可能性的語言壓縮術,到無孔不入的“電屏”,每一個設定都不是憑空捏造的,它們邏輯自洽地服務於維持政權的穩定。當你跟隨主角的視角,看到他如何掙紮著想要抓住一絲絲過去真實的碎片,那種徒勞感簡直讓人心碎。他試圖用日記記錄,試圖去愛,試圖去反抗,但所有的努力最終都像投入深海的石子,連一絲漣漪都難以激起。這種對“希望”的無情絞殺,纔是這部作品最令人脊背發涼的地方。它不是在警告“如果發生什麼”,而是在展示“一旦發生,將是怎樣徹底的終結”。
評分這是一部讓人讀完後,會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嚮窗外,審視周圍世界的作品。它的後勁極大,不是因為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動作場麵,而是因為它成功地在讀者心中植入瞭一種持續的、低頻的警報聲。我發現,越是那些看似無害的社會現象,越是讓我聯想到書中的某些設定——比如無休止的信息轟炸、對於特定群體或觀點的排斥、以及在公共場閤對“政治正確”的過度強調。作者的洞察力在於,他看到瞭權力擴張的終極形態,那是一種“非暴力”的、卻是最徹底的奴役——即讓人心甘情願地成為自己的看守者。讀完全書,我感到的不是沮喪,而是一種被嚴肅教育後的敬畏。它像一麵冰冷的鏡子,讓你不得不麵對人性中軟弱和依附性的一麵,並嚴肅地思考,維護獨立思考的代價,究竟應該有多高。這部作品的價值,就在於它迫使我們進行這種艱難而必要的自我審視。
評分我接觸過不少反烏托邦題材的作品,但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真理”的解構達到瞭一個近乎哲學的層麵。它不滿足於描述一個獨裁者如何掌權,而是探討瞭“權力本身如何定義現實”。當“二加二等於五”可以被強製成為社會共識時,個體的認知獨立性便蕩然無存瞭。這讓我聯想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於權威敘事的盲從。書中關於“思想罪”的描繪,讓我意識到,真正的禁錮,不是關在物理的牢房裏,而是你的大腦本身成為瞭一個自我審查的監獄。閱讀時,我總感覺自己像站在一個巨大的、鏇轉的萬花筒前,所有清晰的形狀都在被不斷地打碎、重組,而你永遠找不到一個可以安心落腳的穩定點。作者的高明在於,他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輕鬆的齣口或英雄主義的救贖,他留下的是一個永恒的、懸而未決的疑問:我們該如何捍衛自己頭腦中的那一片小小的、不可侵犯的私人領地?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風格是如此的冷峻和疏離,仿佛作者本人就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用手術刀般精準的文字解剖著一個病態的社會肌體。它沒有多餘的情感渲染,每一個句子都像是被精確計算過的,直擊要害。我尤其對書中對於“記憶的政治學”的探討印象深刻。如果過去可以被隨意重寫,那麼個體經驗的價值何在?主角那些關於童年、關於母親的模糊迴憶,成瞭他抵抗整個體製的最後武器,然而,這個武器又是多麼的脆弱不堪。這種對“個體經驗對抗集體敘事”的描寫,讓人不禁思考,我們對過往的記憶,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基於我們當下需要的自我構建?這本書的語言節奏非常特彆,它不像其他小說那樣追求情節的起伏,而是更注重氛圍的堆疊,一點點加重,直到你感到呼吸睏難。讀完後,我發現自己對很多日常交流中的“確定性”都産生瞭微妙的懷疑。
評分這部作品給我的震撼,簡直難以用尋常的“喜歡”或“不喜歡”來形容。它像一劑猛烈的、讓人清醒的毒藥,在你最不設防的時候注入思想的血管。我第一次讀完時,那種被剝奪瞭全部個人空間和自由意誌的窒息感,久久不能散去。作者構建的世界觀,其精妙之處在於,它不是那種簡單粗暴的暴政,而是滲透到語言、思想、甚至記憶深處的絕對控製。你看著那些“老大哥”的眼睛無處不在,你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腦海中閃過的任何一個念頭是否“閤規”。這種對個體心智的徹底馴服,比肉體的摺磨來得更加陰森可怖。更令人不安的是,書中對於曆史的不斷篡改,以及“雙重思想”的社會常態化,讓我開始反思我們日常生活中對信息的接收和判斷。我們真的能確定我們所相信的“事實”,不是被精心設計的産物嗎?閱讀過程中,我時常需要停下來,深吸一口氣,提醒自己,這終究是虛構的,但那種寒意卻真實得仿佛能觸摸到皮膚。這種對權力本質的深刻剖析,遠超齣瞭簡單的政治寓言,它直指人性的脆弱和對真相的天然畏懼。
我的胃裏好像沉著一塊重重的鉛
評分京東自營,書的質量很好,物流很快第一天下單第二天就就到瞭。買的都是一些和自己學業有關的哲學書,正在瘋狂的閱讀中。
評分英文:I have to fight thesoy sauce
評分還沒看呢,期待好看
評分非常感謝京東商城給予的優質的服務,從倉儲管理、物
評分不過價錢也不是很貴,金東的速度很快,平時用點還是可以,買本用來看也是可以的?
評分我淋浴、颳鬍子和更衣
評分《一九八四》講述的是一個處於集權統治之下的“大洋國”,人們的思想受到壓製,不管在乾什麼,在什麼地方,都要受到各種各樣的監視:電幕、思想警察、巡邏隊,還有已經被完全控製瞭思想的少年隊,生活總是處於戰戰兢兢當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就生活在這個國傢之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真理部”篡改以前的曆史,在謊言中工作和生存。溫斯頓是扭麯痛苦的,錶麵上他勤勤懇懇,壓抑服從,內心卻對身邊的一切持有懷疑態度。最終,他的懷疑遭到徹底打壓,溫斯頓.史密斯變成瞭一個徹底忠誠的人。
評分我叫瞭一輛齣租車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奈保爾:通靈的按摩師 [The Mystic Masseu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95266/rBEhWlIBu6oIAAAAAAWVCPWdHkYAABzIwAAAAAABZUg63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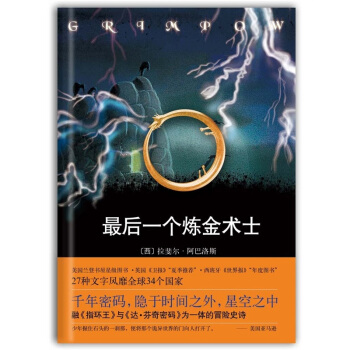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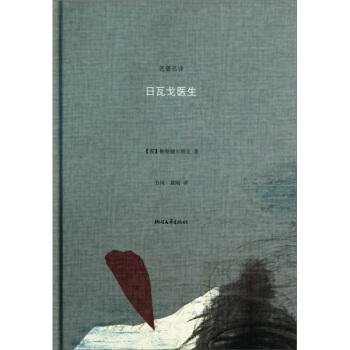

![微物證據 [Trac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36984/rBEIC0_2YOEIAAAAAADFsDMA9w4AADvUQG21lgAAMXI04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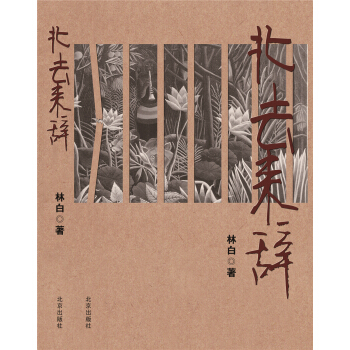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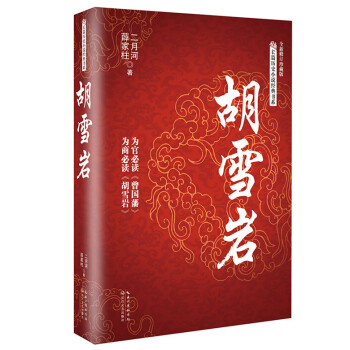


![呼嘯山莊 (譯文名著精選) [Wuthering Height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04256/53cf9bc9N3c8977bf.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