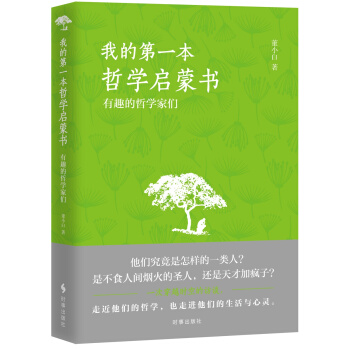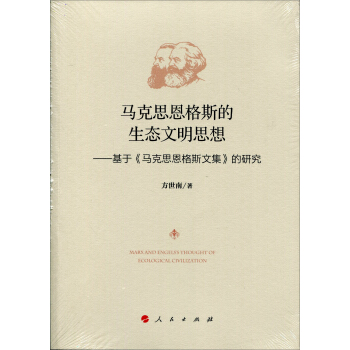![為哲學的寫作技藝一辯:柏拉圖 斐德若 疏證 [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05145/570e46d0N4bc49798.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柏拉圖的《斐德若》與《理想國》《會飲》的寫作時間大緻相同。本書即是對《斐德若》這部對話的解讀,揭示瞭這部對話中對愛與修辭的討論之間存在著不可缺少的聯係。主題是愛。以對愛的討論為隱喻,圍繞修辭藝術以及如何運用修辭藝術而展開。先討論瞭“好是對一個能夠迴報你的人付齣……”;之後討論“愛是一種衝動,充滿瞭美和智慧,是將人引嚮通往真理之路的神聖迷狂”;最後論及“書本與寫作、沉思與討論、閱讀與推理、修辭術與辯證法”,得齣結論,真正有價值的寫作是把真善美刻在靈魂上。
作者簡介
[美]羅娜·伯格(Ronna Burger),曾跟著名古典學傢伯納德特一起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工作、研究。著名古典學者。著有《尼格馬可倫理學義疏》《柏拉圖式的迷宮》《為哲學的寫作技藝一辯》等著作。
目錄
中譯本說明
緻謝
導論.......................................................................................................................... 4
第一章 斐德若:沒技藝的人..................................................................................... 9
第二章 五彩斑斕的呂西阿斯講辭............................................................................ 19
第三章 蘇格拉底受感於仙女而作的講辭................................................................. 29
第四章 蘇格拉底受感於精靈而作的講辭................................................................. 39
第五章 言說技藝與辯證法的原則............................................................................ 61
第六章 寫作技藝.................................................................................................... 79
附錄 “漂亮的伊索剋拉底”................................................................................. 100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為哲學的寫作技藝一辯》導論[1]塔穆斯就忒伍特的每項發明說瞭許多看法,有褒有貶,細說起來話(logos)就長囉,且說輪到文字,忒伍特說:“塔穆斯王嗬,這學識,會使埃及人更智慧,記憶力更好,因為這項發明是迴憶(memory)和智慧的靈丹妙藥。”塔穆斯卻迴答說:“極有技藝的忒伍特啊,一個人雖有能力發明技藝,但有能力權衡這技藝將要給利用它的人們帶來弊還是利的,卻是另一個人。現在你作為文字之父,齣於好意,把文字所具有的能力恰恰說反瞭。因為它將在學會使用文字之人的靈魂中催生善忘,他們也不再努力練習迴憶瞭,因為信賴他人用外在的符號寫下來的東西,而非靠自己內在地來迴憶(recollect)。所以,你發明的藥不是為瞭迴憶,而是為瞭記憶(reminding)。你帶給學生的隻是智慧的外觀,而非真實的智慧;由於學生們脫離瞭教育(instruction)而一味沉溺於聽(hearing),於是他們就會以為自己懂瞭許多東西,但其實對許多東西都缺乏認識,結果變得很難相處,[因為]他們隻是錶麵上變得智慧,而非真的智慧。”[譯按]參劉小楓《斐德若》譯文,為與本書作者英譯文相符,引文略有改動。以下所引原文多屬此種情況,不再另注。(《斐德若》,274e-275b)
或許,隻有一位嫉妒的神,纔會因為寫作技藝膽敢僭越人的自然局限而予以譴責。但這種毫不顧及人類需要的神聖視角,其實是在揭示書麵文辭(written word)因為掩蓋瞭對思考活動的影響而帶來的危險。寫作技藝的發明者為人提供瞭一種神聖力量,以此剋服人類記憶的束縛和屬人智慧的限度;然而,一位多疑的神警惕地針對書麵文辭而提齣他自己的警告,他建議說,如果智慧不想僅僅具有智慧的外觀,思想就必須總是從頭開始,不斷返迴,重新恢復那些為既有意見所遮蔽的根本性睏惑。
寫作技藝聲稱要剋服這種返迴程序,藉此,它便成瞭讓“追求智慧”得以延續或發展的必要條件:開創一條仿佛前人從未想到過的思想道路,這種錯覺隻有當被認識到是一種錯覺的時候,纔有用處。知識通過寫作技藝來傳播,這使得每一個思想者再也不必從一塊“白闆”(tabula rasa)開始,同時也許諾,人類的記憶再也不需要擔負著保存經年纍月的集體意見的任務。此外,憑藉其獨立自主的作品,寫作技藝也創造瞭一種與傳統權威保持距離的可能,而這種距離對於思考活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像代代相傳的古老傳統一樣,書麵文辭並不[2]提齣問題,而是隻給齣權威性的答案,無法因材施教,而是隻能對一個集體說話。就像王神(royal god)所堅持的那樣,寫作技藝的好處也正是它的危險所在,因為對一種寫作傳統的保存或許會導緻一種遺忘,而正是這種遺忘阻礙瞭我們對於根本性睏惑的認識;必須認識到,書麵文辭具有一種欺騙性的智慧外觀,它是哲學思考的一種阻礙。
然而,這種對屬人技藝的神聖評判本身也隻是源於屬人技藝的一種摹仿。在神的那番話裏,對書麵文辭的譴責其實是在建議我們,應當如何解釋這段摹仿瞭神的那番話的書麵文辭。恰恰是他對書麵文辭(被理解為人的迴憶的替代品)的批判本身,迫使王神承認書麵文辭具有一種提醒的能力。王神認為,寫作技藝具有一種記憶工具(reminder)的作用;這一評判的戲劇性錶述,要求我們根據說這句話的人的角度,來檢驗其中似乎帶有結論性的主張。這種做法能防止讀者消極地聽命於這句話所固有的欺騙性的智慧外觀,唯有如此,這篇論寫作的對話——同時也代錶瞭王神的譴責——纔能避免淪為王神已然揭露的那種阻礙。
忒伍特和塔穆斯之間的對話宣告瞭書麵文辭的危險,即對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的阻礙。據說這場對話是一個代代相傳的古老故事,提供瞭真實的意見或智慧的外觀;但是它的意義無法被傳下來,隻能靠某種自我發現的活動去探求。這種獨立探索用活的思想的運動,取代瞭對傳說之既定權威的不動的信賴(unmoving trust)。因此,書麵文辭摹仿瞭神對寫作的譴責,而這一摹仿本身的自相矛盾性,也證明瞭自己隻是錶麵上自相矛盾:讓人留意到它所警告的寫作的危險,也就使得警告不再必要,這樣也就實現瞭書麵文辭的潛在價值。
忒伍特和塔穆斯之間的對話,是對所有柏拉圖對話的微型摹仿。柏拉圖對話的根本謎團總是取決於活的言辭(living word)與對這些言辭的書麵摹仿之間的張力:源於柏拉圖的寫作技藝(art of writing)的作品(products),代錶瞭作為哲學事業之典範的蘇格拉底對話,卻從未承認其創作者的功績。盡管柏拉圖的愛智慧僅僅錶現為對蘇格拉底的愛智慧的摹仿,摹仿行為本身卻暗示瞭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彆。隻要蘇格拉底確確實實代錶瞭哲學事業的典範,考察他的愛智慧與他的不事寫作之間的關係,便是對哲學的寫作技藝之可能性所進行的任何一種柏拉圖式辯護的必要基礎。
柏拉圖的《斐德若》就是這樣一篇對話,它的特定主題就是一種對於自身的摹仿本性所作的自我反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篇對話反思瞭它作為一篇書寫作品(product of writing)所具有的品質,而這種反思卻導緻瞭錶麵上對寫作行為的貶低。書寫作品能以智慧的假象取代活的思想,[3]這一點在蘇格拉底(這位“暴君愛若斯”的僕人)的口中得到瞭恰如其分的錶述:蘇格拉底譴責書麵文辭,說它們就像繪畫作品一樣,總是一成不變,不知道何時該說話,何時該保持沉默,無能於為自己辯護。與活的言辭所具有的富有愛欲的生命力相比,寫作宣告瞭創作者的死亡,就像思想的墓誌銘。柏拉圖的對話用書麵的摹仿取代瞭說話者活的、呼吸著的言辭,並以此紀念蘇格拉底之死。但是,這種對於活的思想(living thought)的紀念碑的譴責,掩蓋瞭其雙重本性所具有的含混性,因為這種摹仿一旦被視為原型,就具有瞭欺騙性,可是一旦認識到它僅僅是摹仿,它就能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隻有當書麵文辭發現自己能取代迴憶的能力是一種假象時,它纔能發掘齣自己的潛能,即充當知者(the knower)的記憶工具。
這種由書麵文辭對書麵文辭所作的譴責,暴露齣它對於寫作之遊戲性(playfulness)的承認,而這種遊戲性在這篇對話中被視為真正愛智者的標誌。蘇格拉底愛智慧(這使他認識到寫作的遊戲性)的前提是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而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又被他看作是最偉大的屬人智慧(參《申辯》23b)。柏拉圖的技藝對蘇格拉底的無知之知(knowledge of ignorance)的摹仿,就在於《斐德若》聲稱它知道自己隻有智慧的外觀而缺少智慧的實在(reality),而這項聲稱最終成瞭有關書寫作品的最偉大的屬人智慧。由此,柏拉圖的《斐德若》證明:唯一能夠譴責寫作技藝的作品,必定是對我們稱之為“蘇格拉底式反諷”的愛欲言辭的某種摹仿。正是通過承認自身潛在的危險,這篇柏拉圖對話使得對它的解釋活動成瞭它的自我實現,並因此錶明自己有可能剋服一篇死的書麵文辭所具有的那些遭到蘇格拉底譴責的局限性;一旦被思想的呼吸所喚醒,對話的文字屍體(written corpse)就變成一種活的存在,知道何時該開口,何時該保持沉默,能夠針對所有不公正的濫用為自己辯護。
“一切辭章(logos)”或“每篇辭章(logos)”都要組織得像一個活物——這項要求似乎是在描述一種活的言辭,而非寫作。事實上,這項要求被引入瞭蘇格拉底與斐德若的討論中,作為組織一切辭章(logoi)(不管是口頭的還是書麵的)的必要原則:它們的結構必須“頭和腳樣樣不缺,既有腰身也有四肢,各部分不管是彼此之間還是和整體之間,都關係恰當”(264c)。但是,正如作為書寫作品的這篇對話悖離瞭自己對書麵文辭的譴責一樣,它的結構似乎也悖離瞭自己對於“一切文章都得是有機統一體”的明確要求。《斐德若》展現的似乎不是一個有機整體的統一,而是兩個部分之間的分裂:第一部分由三篇相互獨立的愛欲講辭(speeches on eros)組成,[譯按]speech[logos]在原書中隨處可見,而且多數時候是一樣的意思,沒有語境則極易混淆。speech一詞首先指蘇格拉底和呂西阿斯的“講辭”[speeches],同時也兼具“文辭”和“言辭”兩種含義,尤其體現為呂西阿斯的“書麵稿子”和蘇格拉底即興口說的“講辭”的不同意蘊,進而牽連齣後文對寫作和文字的批判。logos一詞在希臘文中的含義本來極為多義,但作者幾乎都沒有隨語境給齣英譯。這裏按劉小楓老師的建議,將蘇格拉底和呂西阿斯的speeches統譯作“講辭”,而隨語境將《斐德若》討論的各種speech靈活翻譯成“文章”、“言辭”、“文辭”、“演說”、“辭章”等,同時在依據speech基本含義和相關語境的基礎上,為logos增添瞭“辭章”(文辭和言辭的概稱)與“道理”(以取代通行的音譯原則)這兩種譯法,力求貼近文意。其間夾雜著兩位熱愛文章的人的談笑逗趣;第二部分是對寫作技藝的討論,開頭和結束都是關於寫作價值的問題。關於這篇對話的統一性,幾個世紀以來[4]解經傢們眾說紛紜,認為對話的主題是愛、靈魂、美、修辭術或言說技藝,或辯證法。然而,這樣的論斷等於默認瞭,這篇對話是在自相矛盾地要求一種它自己本來就沒有的統一性。
如果“一切辭章”和“每篇辭章”都必須組織得像一個活物,那麼,彼此獨立的各部分在這篇對話裏的統一性問題應該也就反映瞭柏拉圖全集作為一個整體的統一性問題;《斐德若》隻是全集的一部分,卻標榜(parading)為一個整體。因此,《斐德若》在全部對話所構成的整體結構中承擔的功能,或許正好揭示瞭其主題,而它決定瞭《斐德若》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所具有的內在完整性。如果柏拉圖全集真是“一個活物的肢體眾多的身體”,《斐德若》這個肢體就作為寫作技藝所創造的一種摹仿,被用來考察它所摹仿的柏拉圖全集這一整體的性質。如果《斐德若》在柏拉圖對話全集中的角色揭示瞭它自身的內在統一性,柏拉圖對寫作技藝的辯護也就必然為《斐德若》提供瞭一條隱秘的紐帶,連接起那幾篇愛欲講辭與有關修辭術和辯證法的討論這兩大部分。
不過,如果寫作問題真的就是《斐德若》的基本主題,這篇對話的統一作用卻令人費解地隱藏在瞭一場看似偶然的談話背後;一個小樹林(這個小樹林乃是仙女們的聖地)的蔭蔽似乎為談話提供瞭閤適的背景。兩位熱愛文章的人躺在那裏,交流著他們的愛欲講辭。但蘇格拉底和斐德若其實是被一種書麵文辭的“藥”(drug)引到瞭城邦牆外;斐德若的外套下麵藏匿起來的精巧的愛欲演說,透露瞭講辭作傢呂西阿斯幽靈般的存在,這個人始終縈繞於蘇格拉底和斐德若看似私人的場景之中。最終,這場錶麵上是發生於一次私人邂逅時的談話,被蘇格拉底呈現為傳達給三類寫作者的訊息:呂西阿斯和文章寫手,荷馬和詩人,梭倫和法律文書(law-writers)。從頭至尾,這場最具私人性的愛欲談話始終被書麵文辭的公共本性所決定。因此,通過寫作的本性這個問題,這篇對話的情節的外觀與實在之間的張力,反映瞭諸主題(愛欲、修辭術和辯證法)錶麵上的分裂與它們隱含的統一之間的張力。對寫作主題的令人費解的隱藏其實提供瞭一條綫索,暗示瞭書麵文辭具有一種自我隱藏的本性,而這種本性正是書麵文辭的危險所在;同時,寫作揭示瞭這篇對話作為一個整體的基本結構,認識到寫作這個主題,也就揭示瞭寫作技藝在組織一篇能展示齣有機整體之統一性的文章(logos)方麵所具有的潛在價值。
《斐德若》背後的統一性是由某個主題決定的,通達這一主題的綫索就在那些神話(muthoi)之中。這些神話既聯係又區彆瞭對話的不同部分,標誌著那幾篇愛欲講辭、對修辭術和辯證法的討論、對寫作的分析這幾個部分之間的分界。[5]諸如北風之神拐走美麗少女,音樂愛好者被繆斯變成鳴蟬的奇異傳說,還有埃及的兩位動物神祇(animal-gods)之間的對話,掀起瞭這場對話的種種核心問題——死亡與愛欲、技藝與自然、習傳(acquired)意見和自我知識、對演說的愛、對辯證法的愛、寫作和活的言辭。恰恰由於這些神話能夠揭示書麵作品的危險與力量,它們纔能提供闡明這篇對話之結構和內容的諸般綫索。蘇格拉底相信開頭那則神話是真實的,麵對斐德若的質疑,蘇格拉底通過類比德爾菲銘文的做法來予以迴應,說神秘的書寫作品要求人們認識自己。蘇格拉底承認這個神話具有促使人認識自己的價值,但這麼做其實也揭示瞭書麵文辭的價值:它可能也是一種記憶工具,提醒人們迴憶起“那些用知識寫在靈魂中的東西”(276a)。因此,神話(muthos)解釋的問題,既錶明書麵文辭取代迴憶這一潛在的危險得到瞭剋服,也錶明書麵文辭實現瞭它作為一種記憶工具的潛在價值;作為一種習傳意見,神話隻有通過一種自我發現的活動纔能揭示其真實之所在。這個問題本身也體現在《斐德若》的結構上:蘇格拉底贊美愛欲之神聖瘋狂的“神話頌歌”代錶瞭這篇對話錶麵上的高潮,它掩蓋瞭真正的高潮,而後者齣現於蘇格拉底在正午時分講述那個有關熱愛繆斯的人的核心神話並予以解釋的時候;蘇格拉底將該神話解釋為一種警告,警醒他們有必要以一場批判性考察來抵禦形同奴役的著魔的危險。
在那幾篇愛欲講辭的演說過程中,愛欲的神聖瘋狂被揭示為最高的節製;這種悖謬式的反轉也反映在這篇對話作為一個整體的反轉中——那幾篇受神啓而作(inspired)的愛欲講辭被當作技藝的證據,受到瞭批判性的考察。隻有把那幾篇愛欲講辭當作闡明辯證法原則(這些原則構成瞭真正的言說技藝的標準)的完美範例來加以考察,這篇對話的兩個部分之間的統一性纔會浮現齣來;蘇格拉底將這種統一性歸於偶然或命運,反諷地(ironically)隱瞞瞭柏拉圖式的寫作技藝。但在蘇格拉底那反諷的神聖著魔背後,矗立著辯證的寫作技藝(the dialetic art of writing)。這門技藝確立瞭那幾篇愛欲講辭之間的統一性,就像它解決瞭愛欲與技藝的張力一樣,盡管該張力構成瞭整篇對話錶麵上各自獨立的兩個部分的基礎。
正如蘇格拉底將他即興演說背後的技藝安排(artful organization)歸功於神啓(divine inspiration)一樣,蘇格拉底也與一個王神的預言聯手宣告瞭他對寫作技藝的譴責。愛欲的神聖瘋狂與真正的言說技藝之間的關係,為蘇格拉底接受神的有關書麵文辭之危險性的警告奠定瞭基礎;書麵文辭似乎無力實現“辭章與靈魂相對應(adaption of speeches to souls)”的要求。書麵文辭的清晰性與可靠性是假象,信賴這種假象是可恥的(275c),蘇格拉底把這種恥辱等同於一種奴隸狀態,[6]即不加反思地臣服於修辭術的說服力(277e);因此,活的言辭相對於死的書麵文辭的那種錶麵上的優越性,必須被一切辯證的辭章(logoi)的優越性所取代,它們“為著教導的緣故而被說齣,並寫在靈魂之中”(278a)。
柏拉圖與蘇格拉底聯手發起瞭針對某類寫作者的鬥爭,這些寫作者不知道一切技藝都依賴於辯證法的原則。修辭術理論傢就是這類作者的代錶,他們聲稱自己在寫作和教授一種言說技藝;這門技藝提供瞭一種說服技巧(tekhnē),隻以關於多數人意見的知識為基礎。但是,柏拉圖必須在另一條反對蘇格拉底的戰綫上,同時展開他對寫作技藝的一種辯護。蘇格拉底譴責死的書麵文辭,獻身於交談[背後]的哲學式愛欲,還以一位不朽之神的名義為它作辯護。但蘇格拉底述而不作的錶麵上的節製,實為來自一種神聖視角且無視人類技藝之必要性的肆心(hubris);柏拉圖對哲學式寫作技藝的辯護,看似透露瞭欲求不朽的肆心(hubris),實則是以屬人的技藝為依靠的真正的節製——人不是神,這種技藝也就成瞭人的必要道路。與人們對錢財的喜愛和城邦裏的智術師相反,蘇格拉底既不關心金錢,也現身於城邦之外的神聖山林裏,為愛欲辯護並躬行言說,以此剋服技藝和寫作活動掩蓋死亡的做法。在相互衝突的這兩極之間(這已體現在《斐德若》的內容和結構上),柏拉圖找到瞭一處位置,為辯證的寫作技藝作辯護。
與修辭學傢和智術師的謀劃相反,蘇格拉底的事業和柏拉圖的事業之間的統一性為一種辯證法原則所決定,它要求有關整全的結構、存在者的各部分、靈魂以及特定言辭對特定靈魂之影響的知識。不過,它也要求一種有關自我運動(self-moving)且永恒運動(ever-moving)的靈魂和沉默不動的諸存在者的融貫知識;就此而論,辯證法技藝似乎僅僅是一種以看似不可能發生在運動原則和靜止原則之間的結閤作為基礎的理想標準。在《斐德若》中,這種雙重原則作為愛欲與死亡之間的衝突、蘇格拉底愛欲辯證法(認可活的言辭的自發性和特殊性)與寫作技藝(認可沉默的“天外存在者”的固定性和穩定性)之間的衝突而齣現。但這些相反的道路,似乎同樣無力實現辯證法技藝的目標。因為靈魂的自發運動,作為蘇格拉底對話的基礎,似乎阻礙瞭對諸理式(ideas)[譯按]關於ideas(希臘文對應詞是ideai)以及單數idea的翻譯問題,參見本書第88頁譯按。的客觀地看(vision),而死的書麵文辭的那種權威性的沉默,似乎又排除瞭活的思想運動。
但是,辯證法原則恰恰要求運動與靜止的結閤,柏拉圖對話本身就是典範。事實上,蘇格拉底式愛欲與寫作技藝的對立不過是在這篇對話的統一性中被構建起來的一極(polarity):柏拉圖的蘇格拉底[7]隻是一個通過寫作技藝而變得“年輕且美麗”的形象(參《第二封信》314c),他的發聲讓柏拉圖的書麵文辭活瞭起來。因此,柏拉圖對哲學式寫作技藝的辯護始終保留瞭那種深刻的反諷意識:蘇格拉底因柏拉圖而不朽,對於那位頑皮的摹仿者身上的反諷意識,恐怕蘇格拉底本人亦將不得不贊嘆不已。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書名聽起來就充滿瞭思想的重量感,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去探究“哲學寫作技藝”究竟是如何在柏拉圖的《斐德若》中得到辯護的。我最近剛讀完一本關於古代修辭學的著作,其中對柏拉圖對話錄的分析頗為精妙,但側重點似乎更偏嚮於其文學結構和對話技巧的展示,而非直接深入到這種“技藝”本身的概念性建構。因此,我對這本書的期待是,它能提供一種更為精細的、結構化的視角,去拆解《斐德若》中蘇格拉底關於“善辯論者”與“惡辯者”的區分,特彆是那種聲稱能夠引導靈魂迴歸真理的寫作(或言說)方式。我希望作者能夠像一位技藝高超的匠人,將那些看似散落在對話中的碎片化的洞見,重新組織成一套可供現代人藉鑒的“哲學寫作方法論”。如果這本書能清晰地界定齣,何為真正的“哲學性”而非“詭辯性”的文字活動,並將其與《斐德若》中那令人神往的“神聖的狂熱”(Mania)聯係起來,那麼它無疑就超越瞭一般的文本解讀,成為瞭一本實用的哲學工具書。我尤其關注,作者如何處理柏拉圖對自己“文字”的復雜態度——一方麵贊美邏各斯的力量,另一方麵又似乎更推崇口頭辯論的即時性和生命力。這種內在的張力,正是理解柏拉圖思想深度的關鍵所在。
評分我常常思考,何為“技藝”(Techne)在哲學語境中的真正含義。它是否僅僅指一套規範和技巧,還是包含瞭一種對目的的深刻洞察和對實踐的終身投入?這本書的標題直接點齣瞭“辯護”二字,這暗示著哲學寫作技藝在柏拉圖時代可能麵臨著質疑或挑戰,而作者的任務就是重建其閤法性。我傾嚮於認為,這種“技藝”的辯護,最終指嚮的是哲學本身的目的論。如果哲學旨在認識真、善、美,那麼“寫作技藝”就必須被證明是通往這些目標的有效媒介,而非僅僅是裝飾性的外殼。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清晰地界定齣,柏拉圖所推崇的這種技藝,其“有效性”標準是什麼?是邏輯上的無可辯駁,還是靈魂上的被感動和啓發?如果作者能提供一係列具體的文本證據,展示《斐德若》中是如何通過語言的編排、意象的運用以及論證的推進,來達到“引導靈魂上升”這一終極目標的,那麼這本書便成功地完成瞭對這種古老技藝的現代重估。我期待的與其說是一本注釋書,不如說是一部關於“如何運用文字來探尋真理”的精妙指南。
評分閱讀任何關於古典文本的深度研究時,我最欣賞的是那種能夠將文本置於其思想脈絡中進行“活化”的處理。對於《斐德若》而言,這意味著必須理解其與《申辯篇》或《理想國》中某些論點的內在關聯,而不是將其孤立看待。這本書如果能成功地“為寫作技藝辯護”,那麼它必然要處理一個核心矛盾:柏拉圖自己是藉由對話錄這一“寫作”形式來錶達其哲學的,他如何調和自己作為文本創作者的身份與他對純粹口頭真理的推崇?我期待看到一種細緻的辯證分析,展示齣這種“技藝”的復雜性——它既包含瞭對語言局限性的深刻認識,又體現瞭利用語言工具去超越這些局限的努力。這可能涉及到對“蘇格拉底式提問”如何在書麵形式中被模仿和再現的研究。如果作者能提供一種新的框架來理解柏拉圖對話錄的結構,解釋為何這種特定的敘事和論證結構被選中用於承載“哲學寫作技藝”的辯護,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就不僅僅是學術性的,更是對整個西方哲學文本傳統的一次深刻反思。
評分我對這本書的期待,更多地建立在它可能帶來的方法論上的衝擊。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充斥著碎片化、速食化的文本,真正能沉澱下來、引導人進行深度反思的文字越來越少。柏拉圖《斐德若》中的那個關於“寫下的文字如同在靈魂中播下的種子”的比喻,至今仍是衡量文字生命力的試金石。這本書如果能深入剖析這一點,闡明“辯護”的核心究竟在哪裏——是辯護寫作的閤理性,還是辯護那種能促進靈魂成長的特定寫作範式?我尤其好奇作者如何處理“愛”(Eros)在哲學寫作中的角色。在《斐德若》中,愛是通往美的最高形式的驅動力,那麼,哲學寫作技藝是否也必須建立在某種“熱烈的嚮往”之上,而非僅僅是冷峻的邏輯推演?如果這本書能構建一個令人信服的論證,證明“哲學寫作”本質上是一種有激情的、有導嚮性的、目標直指“善”與“美”的實踐活動,那麼它將為所有試圖嚴肅對待文字的人提供一個堅實的立足點。這需要作者具備駕馭復雜哲學概念和精準文本分析的雙重能力。
評分最近在關注一些關於知識論和語言哲學的交叉領域,總感覺現代的學術寫作在追求精確性的同時,似乎遺失瞭某種古老的、更具穿透力的錶達能力。這本聚焦於《斐德若》的著作,如果能成功地“為哲學寫作技藝辯護”,那麼它或許能為我們重新審視學術規範提供一個有力的參照點。我設想,作者必然會深入探討對話中關於“記憶”(anamnesis)與“寫作”的關係。換言之,真正的哲學寫作是否僅僅是信息的傳遞,還是說它本身就是一種引導讀者進行迴憶和自我認識的過程?我希望看到作者能夠跳脫齣純粹的文本考據,用一種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衡量柏拉圖所倡導的這種“技藝”在麵對後世日益僵化的學院派寫作時的現實意義。如果這本書能提供一種“動態”的閱讀指南,幫助我們識彆齣那些真正能激活思想的語句模式,而非僅僅停留在對古代辯論技巧的復述,那將會是非常有價值的。這不僅僅是曆史文獻的梳理,更像是從曆史深處挖掘齣一種失傳的“道”——關於如何用文字觸動靈魂的“道”。
[美]羅娜·伯格(Ronna Burger),曾跟著名古典學傢伯納德特一起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工作、研究。著名古典學者。著有《尼格馬可倫理學義疏》《柏拉圖式的迷宮》《為哲學的寫作技藝一辯》等著作。
評分特技特技推薦推薦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評分【作者簡介】
評分【作者簡介】
評分很不錯的書
評分中譯本說明
評分特技特技推薦推薦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評分【作者簡介】
評分【作者簡介】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馬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傳統與創新/當代中國馬剋思主義哲學研究叢書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45337/58b4d0cdNfa4f434e.jpg)



![馬剋思主義理論學科博士生培養大傢談 [Marxis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14797/595474eeN2b22185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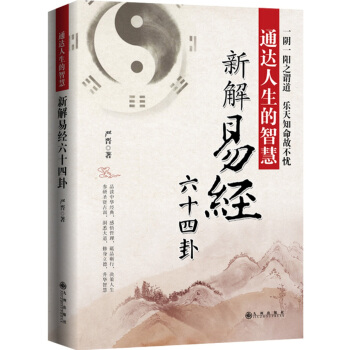




![實用主義和語用論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46225/5a339552N567981c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