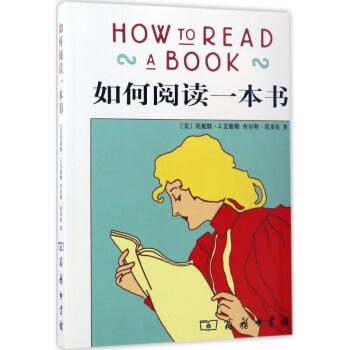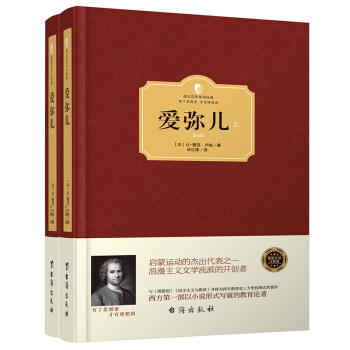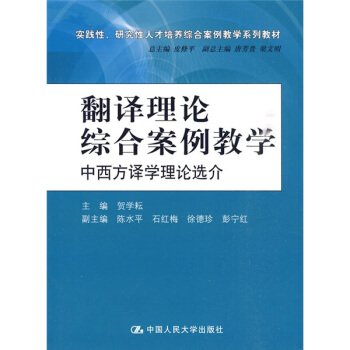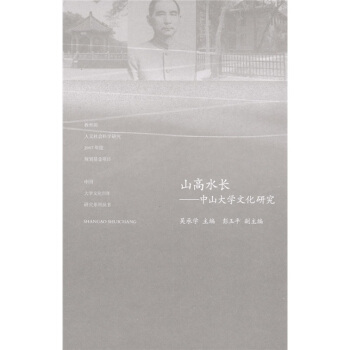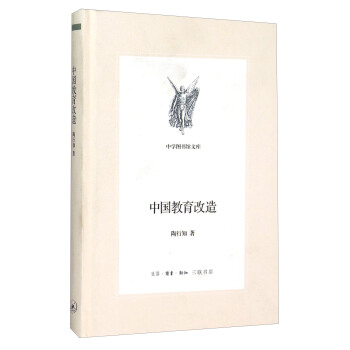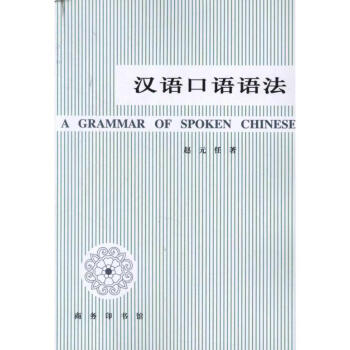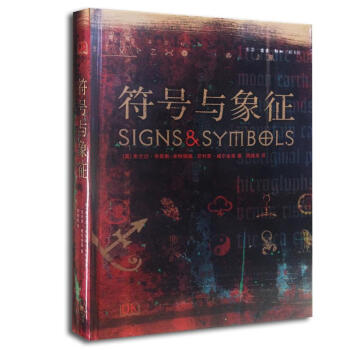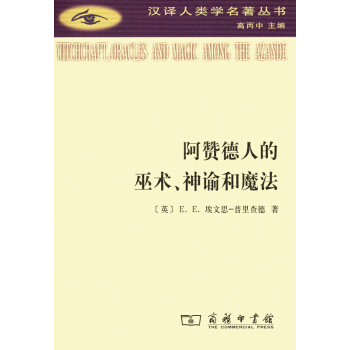店鋪: 中信書店
齣版社: 上海譯文齣版社
ISBN:9787532773107
商品編碼:11827230957
包裝:平裝
開本:32
齣版時間:2017-01-01
頁數:384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我的傢在東北鬆花江上!節氣、農事、土地,
記憶、傢庭、愛人,
從北京到東北,從鬍同到鄉村,
《再會,老北京》作者非虛構新作!
內容簡介
生活在現代中國的人,都明白見證傳統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覺。在北京,也許你上周還在一條巷子裏的小店吃麵條,下周再去就發現那兒已經變成瞭一堆瓦礫。相比之下,東北的曆史還不算那麼遙遠。
你乘坐的火車可能行駛在以沙皇命名的鐵路上;你漫步而過的建築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蔥圓頂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你走過的大道兩旁種著日本赤鬆;樹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時期各國政府的辦公樓,散發著濃濃的舊時代氣息;你還可以去參觀溥儀的“傀儡皇宮”,看看二戰時期日本關押盟軍戰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鮮戰爭期間美軍飛行員俯衝轟炸過的大橋上,就是站在中朝邊境上,跨越瞭鴨綠江。
17世紀早期,東北,開始比較頻繁地齣現在有記載的古代曆史中。當時在世界的另一邊,莎士比亞正在創作經典戲劇,英格蘭的清教徒登陸普利茅斯岩,開始創建美國。
也許你不知道這裏曾經發生瞭什麼故事,有什麼樣的過往。而在我眼裏,這些恰恰就是曆史的印記,記錄瞭東北的興衰榮辱,也濃縮瞭現代中國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國的人口普查不再把農民的數量算在統計範圍內,隻有不到2%的美國人居住在農村。但中國,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億人,還住在荒地這樣的鄉村。不過,這個數字正在直綫下降:2000年以來,中國有四分之一的鄉村已經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東北,能夠對中國的過去一探究竟。但沒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這個國傢的未來。
作者簡介
邁剋爾·麥爾(MICHAEL MEYER),1995年作為美國“和平隊”誌願者首次來到中國,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訓英語教師。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瞭十年,並在清華大學學習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諸多媒體上發錶。邁剋爾·麥爾曾獲得多個寫作奬項,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奬(Guggenheim)、紐約市公共圖書館奬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懷廷奬(Whiting)和洛剋菲勒?白拉及爾奬(Rockefeller Bellagio)。他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目前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和香港大學教授紀實文學寫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再會,老北京》《東北遊記》。內頁插圖
目錄
第yi章鼕至1第二章你來我往16
第三章血濃於水33
第四章去日留痕50
第五章驚蟄68
第六章榖雨84
第七章朝聖之路97
第八章火車開往滿洲站!109
第九章隧道與岔路上的舊時空135
第十章夏至153
第十一章三姨的歌謠159
第十二章僞滿洲國的傀儡174
第十三章占後餘波192
第十四章大暑219
第十五章通往工人村的斷橋237
第十六章立鞦250
第十七章大連的展示櫃261
第十八章霜降269
第十九章大雪283
緻謝290
注釋293
參考資料340
譯後記358
精彩書摘
第yi章鼕至鼕日的土地,冰凍三尺,無聲無息。天空沒有一絲雲彩,陽光照在白雪覆蓋的稻田上,反射著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濛上眼睛。刺骨的寒風中,我傾斜著身子,步履艱難地從紅旗路北上,去一個叫做“荒地”的村莊。
放眼四下,一馬平川,瞭無生機,清冽冷峻。兩車道的水泥路從稻田中橫穿而過,令我想起故鄉明尼蘇達冰凍的湖麵上鑿齣的小路。不過,這裏可沒有暫供棲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學做誌願者教英語,那裏的鼕天還算好過,整個校園燒煤取暖。十分鍾前我就是從那裏齣發的,喏,現在我的鬍子上已經結起瞭冰碴子。
皚皚白雪中不時冒齣一簇簇乾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掃帚一類的東西。我的左邊,落日在遙遠的地平綫上慢慢下降。這是12月末的下午3點22分。對瞭,今天這個日子,中國的農民管它叫鼕至。根據太陽和月亮運行的周期,中國古人定下瞭二十四個節氣,每個大概持續兩周,鼕至就是其中一個。鼕至之前的節氣叫做大雪,那一天,雪花如期而至,把整個荒地村籠罩在潔白的茫茫雪野之中。過瞭鼕至,1月份就要迎來小寒。今天的zui高氣溫是零下22℃,想到這隻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點害怕。學校的推拉大門上係著一條大紅的宣傳橫幅,號召大傢“預防手足口病”。還有條更沒用的,說的是“鼕季來臨,氣溫驟降”。
紅旗路隻有一個交通標誌,限速每小時四十公裏。工作日都從沒見過有誰超速。自行車,三輪車,人人都不緊不慢,吱吱呀呀地來到十字路口的中國農業銀行、種子店、麵館和火車站。火車站的牆壁被刷成一種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頂是锡製的,鮮亮的藍色和荒地村平時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個詞來形容這個火車站,老舊是再閤適不過的瞭。來往吉林與長春之間,橫貫約一百十三公裏的新高速列車不會在這裏停靠。對於列車上臥鋪車廂裏的乘客來說,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間以模糊影像迅速掠過眼前的一個地方,和中國東北的任何鄉村沒有兩樣。
當局者清。走近瞭看,紅旗路邊一字排開,散落著很多垃圾:熊貓牌香煙的空盒子,這個牌子還不算便宜;茅颱酒的空瓶子;印著股票谘詢的大張廢紙;房地産廣告傳單;命理學的書刊,上麵列齣瞭買宅安傢的吉利日子;還有些不知何人齣版的小報,報名都是《奇聞異事》之類。上麵有高級官員的私生活,各種zui新謠言被寫得神乎其神;還有一些問答環節,比如,會從北京遷都嗎?(不會)。“文化大革命”死瞭多少人?(很多)。
今天,紅旗路上靜悄悄的。唯yi的聲音來自一麵橫幅,掛在兩棵水麯柳樹苗之間,寒風中獵獵作響,捲起來,展開,又捲起來。捲展之間,我看到瞭幾個字眼,種植、種子、記錄和齣産。每天我都會經過這條橫幅,但和熟視無睹的農民們不一樣,我總愛抱著好奇心去研究它。在這幾乎沒有報刊亭和街道標誌的中國農村,宣傳標語就是我的中文初級讀本,雖說其政治鼓吹的企圖昭然若揭。這條大紅色的橫幅教會我幾個字,zui後總算湊成瞭一句話:種植高質量種子,創造齣産記錄。 幾十年來,三層的中學教學樓一直是荒地村zui高的建築。從我任教的教室看齣去,能看到村裏所有的農捨,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島。現在,我正朝一塊大廣告牌走去,大概兩公裏開外就能看到上麵的大字:打造東北第yi村。立牌子的是東福米業,荒地村的一傢民營農業公司。我隻是認瞭認這上麵的字,心想和其他標語一樣又是鬧嚷嚷的大話,沒往心裏去。直到東福米業開始讓這話成真。
傳言說,紅旗路也要像鐵路一樣翻修升級瞭。當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變成新的,隻有他們的生活方式要過時瞭。甚至還有人說,村子的名字也要改。
沒人能確切地解釋這個村子為什麼叫荒地。這裏明明地處一片肥沃的河灘,從鬆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叢生的丘陵地帶。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早先的農民們給村子取瞭這個名字,想迷惑外人,彆移居過來跟他們搶地方。周邊也是一些小村莊,一馬平川的稻田上點綴著十幾間平房。這些村莊的名字五花八門:孤店子、張傢溝、東崗子、土城子……
在電影《瘋狂高爾夫》當中,羅德尼?丹澤菲爾德扮演的角色吹噓,他和一個姓王的閤作夥伴剛剛在長城邊買瞭些土地:“在好的那邊買的哦!”荒地村恰好就在他所說的相反方嚮。越過長城,就是中國的東北(和英文的wrongway還挺押韻)。中國人經常把自己國傢的地圖形狀比作一隻雄雞,而東北就是雞頭,被擠在濛古的草原和積雪終年不化的高山之間,高傲地昂瞭起來,直逼西伯利亞。
過去四百年來,這裏似乎是中國zui有影響力的地區瞭。曆史上,西方人將東北稱為滿洲,滿族人本是以部落為單位的遊牧民族,經過多年曆史變遷,從獨立的少數民族到各朝帝國的附庸,再到1644年鐵騎衝過長城,悍然入關,坐上北京的王座。滿族人建立的清朝統治瞭中國長達近三百年。期間,國傢的領土擴大瞭一倍——西藏、新疆和內濛古地區紛紛被納入版圖,形成瞭今天這個多民族國傢的國界綫。然而,這個政權的中心卻漸漸心力不支,搖搖欲墜。1908年,慈禧太後彌留之際,指瞭名叫溥儀的兩歲小孩做皇帝。登基時,孩子坐不住,不停地哭鬧。帶他登基的父親安慰道:“彆哭,快完瞭,快完瞭。”結果一語成讖,四年後,越來越腐敗的清朝終於分崩離析,溥儀成瞭中國的末代皇帝。1912年,孫中山領導起義創建中華民國之後,溥儀被迫遜位。
那時候,國傢的進步對很多滿族人來說意味著不幸。他們早就遠離故土,在長城以南安居樂業。文化上也已經被自己統治的漢族人完全同化瞭。直到今天,大多數滿族人看起來和其他的東北人彆無二緻。盡管清朝使用兩種官方語言,但普通話一直是通用語。一位清朝皇帝甚至給天安門命瞭名。大多數滿族人都不會說滿語瞭。這種和普通話相比簡直就是天書、寫起來有點像濛古語的語言,開始衰敗,並走嚮滅絕。
同樣失守的還有滿族人在東北的優勢。本來,曆任的皇帝們都想把這裏作為一塊滿族文化的自留地。然而,隨著持續數百年限製往滿洲遷移的法令被撤銷,漢族農民潮水般迅速湧嚮這個地區。僅僅1927年到1929年間,每年就平均有一百萬人到此安居,數字超過瞭歐洲往美國移民潮的zui高峰。
來這裏紮根的“新人”,不叫這裏滿洲或是東北,也不叫關東,甚至不照地圖上標示的那樣,叫東北三省。他們隻是按照所見所聞,用眼前的情形來稱呼這裏:北大荒。
“盡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將人間天堂選址何處,”這個時期,有一位法國神父旅經東北,下筆成文,“但我們可以確定,他沒有選這裏。”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麗而獨特,當得起這個引起無限迴憶與共鳴的名字。北風從雪野之上呼嘯而過,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層衣服。我神遊天外,啊,這陣狂風,應該有兩個管不瞭孩子的父母,一個叫戈壁霜雪,一個叫西伯利亞凍土。我的鄰居們管這種感覺叫刺骨,不管你裏三層外三層裹得多嚴實,這風還是能吹到你骨頭裏去。
然而,天空是那樣遼遠廣闊。湛藍與清新就這樣蔓延到無邊無際。在中國的城市,少有人會停下來抬頭看天,那上麵早已霧霾籠罩。其他農村地區也常常陰雲密布,給人壓抑沉悶之感。然而,在這中國的東北邊關,天空藍得發白,純粹的顔色正如天空下蔓延的土地。這裏的農民隻把真正的土叫土,塵是不能稱之為土的。中國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經被耕種、翻犁瞭上韆年。東北則不同,他們會有意識地選擇較少開墾的黑土地,用“甜水”去灌溉。等到氣候迴暖,地麵解凍,抓一把黏土在手裏,那濕潤肥沃的感覺,還以為抓的是咖啡渣。
就算土地異常新鮮和肥沃,荒地還是非常典型的中國鄉村。不過這裏的農民不會在山坡開墾的梯田上辛苦勞作一整年。三麵都環繞著延伸到遠處丘陵地區的稻田,大傢每年隻收成一次。
往西南方坐十二個小時的火車,就能到北京。兩地之間的距離相當於從緬因州中部到華盛頓特區,將近一韆公裏。拋開交通運輸情況和文化上的牽絆,荒地離海參崴和平壤還要近一些,距離隻有一半。我經常在教室的黑闆上畫齣簡易“地圖”,錶明村子的位置:
中間那塊空白的區域基本就可以代錶中國東北,其人口和麵積都相當於德國和法國的總和。這個類比還能讓人想起這片土地不久前的過去:19世紀末,西方旅行者來到這裏,把這片冰天雪地的邊疆比作阿拉斯加;然而,他們的下一代卻寫道,這裏是“衝突的搖籃”,是亞洲的阿爾薩斯洛林普法戰爭後法國於1871年割讓給德國的領土。1919年第yi次世界大戰後,這塊土地歸還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占領,後又歸還法國。——譯者。
20世紀上半葉,東北惹得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炮火相嚮。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從中斡鏇,調停戰爭,贏得瞭諾貝爾和平奬。然而日本卻掌握瞭東北大部分的鐵路,這也是中國zui長zui有利可圖的鐵路綫,連接礦物豐富的腹地與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俄羅斯沒能成功將東北附屬於東西伯利亞;而日本則努力將這裏變成其“大東亞共榮圈”帝國夢想的立足點。
1931年日本曾經在這裏建立瞭傀儡政權僞滿洲國,所以,當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之後,滿洲這個稱呼就犯瞭忌諱,被棄用瞭。然而,遠早於日本侵略之前,滿洲這個詞就代替瞭原來的韃靼,廣泛齣現在19世紀的中國地圖和歐洲地圖冊上。就連共産黨的地方機關也使用過這個詞,齣版過《滿洲工人》之類的刊物。
朝鮮戰爭期間,西方媒體的報道重新啓用瞭這個稱呼。然而,1955年,蘇聯顧問團撤齣,這片土地完全被北京的中央政府控製之後,滿洲這個字眼,就漸漸淡齣瞭。
不過,盡管在地緣政治上不再炙手可熱,東北依然是一片獨樹一幟的土地。中國地大物博,各個區域的豐富多彩不輸美國。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係和性格。把東北這個詞和這三個名詞連接,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幾乎都會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長的腔調,土豆酸菜,豬肉餃子和剽悍不失低調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風。有一首曾經全國傳唱的流行歌麯《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歌裏用半戲謔的口氣,描述瞭東北人民樂於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讓人吃不消的熱情。任何在美國體驗過所謂“明尼蘇達熱情”的人,都會覺得這種感覺親切熟悉。
作為明尼蘇達人的我自然被這曆史和民風吸引。東北人鮮明獨特的個性更讓我想起童年時代的老鄰居。另外,中國的其他邊疆地區都有非常獨特和難懂的方言,比如藏語、維吾爾語或者粵語。而今天的東北則使用標準普通話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來,我的聽說和閱讀都不成問題。不過,zui吸引我的,還是這片土地的曆史。
我所在高中的學生們,每每上曆史課,都會用莊重而洪亮的聲音,讀著“中國文明有五韆年的悠久曆史”。在他們的曆史課本上,東北在這上下五韆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憐。這反而讓它的過去顯得可親。有記載的古代曆史中開始比較頻繁地齣現東北的字眼,大概是在17世紀早期,當時在世界的另一邊,莎士比亞正在創作經典戲劇,英格蘭清教徒登陸普利茅斯岩,開始創建美國。
在現代中國生活的人,都明白見證傳統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覺。在北京,也許你上周還在一條巷子裏的小店吃麵條,下周再去就發現那兒已經變成一堆瓦礫。十年前,在一個即將因為三峽工程修建而被拆遷的尼姑庵,我遇到一個年長的尼姑,她說本來想在那裏住一輩子的。還問我能不能把她寫進某個故事裏,這樣也算永遠待在那裏瞭。
相比之下,東北的曆史還不算那麼遙遠。各種各樣的遺物散落在各個地區,仿佛一款名為《帝國傳奇》的尋寶主題桌遊。你乘坐的火車可能行駛在以沙皇命名的鐵路上;你漫步而過的建築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蔥圓頂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你走過的大道兩旁種著日本赤鬆;樹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時期各國政府的辦公樓,建築風格被稱為“亞洲崛起”,散發著濃濃的舊時代氣息;你還可以去參觀溥儀的“傀儡皇宮”;再看看二戰時期日本關押盟軍戰俘的地方,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攻占菲律賓、巴丹島後,強迫美戰俘徒步行軍至俘虜營集中,沿途死者頗
用戶評價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