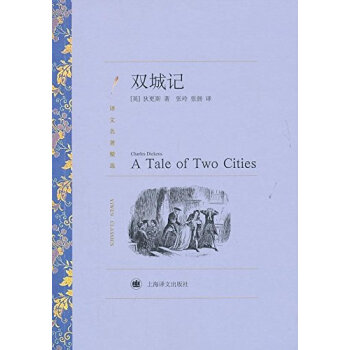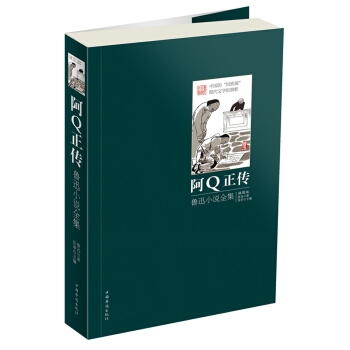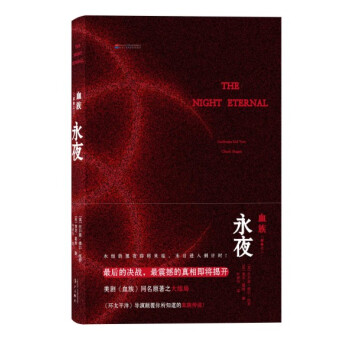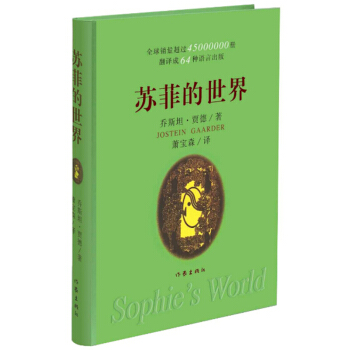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2015年8月出版英文版《少年巴比伦》获美国图书销售往亚洲文学排行榜首位,严肃文学zui受关注作家前十,被美国图书销售网评为“中国的塞林格”。★《慈悲》路内现实主义力作,艰难时世中人性的良善,隐忍的生以及沉默的爱
★这是近年少有的具有《活着》气质的作品,悲悯而克制,清醒而不苛刻,现实又不乏温情
★毕飞宇、徐皓峰张悦然联合推荐阅读
★只要活着,终会有好事发生。慈悲,则让我们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内附路内精彩短篇小说一册抢先阅读,此小说由路内担当编剧,即将改编成电影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路内的作品,可选择从《慈悲》开始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一五年度小说家奖。他的小说,他笔下的青春,不仅是年华,也是灿烂的心事,不仅常常受伤,也饱含生命的觉悟。
内容简介
水生十二岁那年,村里什么吃的都没了。水生的爸爸在田里找到了最后一根野胡萝卜,切开了给一家四口吃下去。水生的爸爸说:“再不走,全家饿死在这里了。”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水生的爸爸背着水生的弟弟,去城里投靠叔叔。自此,水生的父母与弟弟的生死不知。二十岁那年,水生进入化工厂,生命中有了玉生、根生、复生……,然后,又只剩下他一个了。
老家早已凋敝,他得活着,他要为玉生,为父亲,辩认回家的路,为复生留一条回家的路……
作者简介
路内,1973年生,现居上海。优秀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曾获《智族GQ》年度人物之2012年度作家,近年只于《收获》《人民文学》连发六部长篇小说的七〇后作家。著有“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以及《云中人》《花街往事》。精彩书评
路内大多关注边缘地带的边缘人群,对人物内心和社会环境观察冷静、准确解剖,并以机敏、感伤而又纵情自如的率性笔调,将一群都市青年成长中的迷惘与苦闷、青春中的叛逆与放纵,时光流逝的无奈与酸楚,作了极富质感的呈现。路内有别于人们对青春题材小说的惯有评价,他拓展了成长小说的疆域,让读者看到繁华都市的背面,草根生命令人辛酸的挣扎与突围,边缘青春里仿如摇滚乐般自我放逐的反抗力量,有着近于偏执的真诚。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一五年度小说家:路内的小说是一代人的精神镜像。他笔下的青春,不仅是年华,也是灿烂的心事,不仅常常受伤,也饱含生命的觉悟。他的长篇小说《慈悲》,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熟和从容。从伤怀到悲悯,从锋利走向宽阔,路内的写作已不限于个人省思,而开始转向对平凡人生的礼赞,对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写。他如此专注,又如此谦卑。他的文字,敛去了一切怨气,有着仁慈的暖意,这种和解与饶恕,是对写作跨越性的艰难跋涉。
——★《人民文学》“娇子·未来大家”top20评语
精彩书摘
长途汽车缓缓开上渡轮,水生坐在车上,隔着茶色的玻璃看到外面,云变得格外清晰,一朵一朵,像是刻在了天上。向后看,苯酚厂的烟囱和厂房已经不在了,它们变成了一块工地,正在盖沿江高层住宅。水生想,这房子只能骗骗傻子了,内行都知道,化工厂的地基污染严重,一百年内住在这里的人恐怕都比较容易生癌。水生下了长途汽车,阳光正猛,他抱着玉生的骨灰盒靠在栏杆边看江水,以及被水淹没的沙洲。江水一层一层,涌来,涌去。水生的身边,是一个和尚,穿着灰色的僧服,看上去也快要六十岁了。不知道为什么,水生觉得和尚很熟悉,又看了几眼,看到和尚头顶上有七个淡淡的疤,那不是香疤,现在的和尚已经不点香疤了。七个疤是无序地排列在头顶,水生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伸手拽住了和尚的袖子说:“你是我弟弟,你叫云生。”
和尚也回过头来,看着水生,两个人长得很像。和尚愣了好一会儿,说:“水生,哥哥啊。”
水生立刻问:“爸爸呢?”
弟弟说:“爸爸已经死了五十年了。妈妈呢?”
水生说:“一样。”
水生早上没哭,上午没哭,到了这个时候忽然哭得涕泪纵横。渡轮仍在江上缓行,水生蹲在地上,弟弟也蹲下了,默然看着他哭。水生说:“云生,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是你头上的疤。你还记得这七个疤是怎么来的吗?”
弟弟摇头说:“不记得了。”
水生说:“那一年,全村人都饿得发疯了,谁家烟囱冒烟,生产队长就会带着人来。爸爸拉我到村里食堂找吃的,其实是偷,捉到了就打死了。爸爸不怕了,食堂也没有人了,他找啊找啊,在一个麻袋里找到了黄豆,只有七粒。我抓起黄豆就想吃,爸爸说,生豆子吃了会拉肚子,比不吃还糟糕。他把这七粒黄豆带回家,在一口锅里炒豆子。只有七粒黄豆啊,它们在锅里滚来滚去,我闻到黄豆的香味,馋得要死要活。这时生产队长带着人来了,爸爸急了,抓起七粒豆子,不知道往哪儿放。这时你也在边上,爸爸一把摘下你的帽子,把七粒黄豆放在帽子里,扣在你头上。你大哭起来,生产队长查了半天,没有找到吃的,就问这小孩为什么哭,爸爸说,饿的呗。生产队长就走了。我们揭开帽子一看,豆子太烫了,在你头顶烫出了七个水泡。这七个水泡,后来全都变成了疤。”
弟弟问:“豆子呢?”
水生说:“我们分着吃掉了。你两粒,我两粒,妈妈三粒。”
弟弟说:“爸爸一粒都没吃。”
水生问:“这些年你又在哪里呢?”
弟弟说:“一言难尽,我慢慢说给你听。爸爸死后,我被一个老和尚收养了,老和尚把我带到外省,他圆寂以后,我也没有做和尚,在一个矿上挖煤。挖煤太苦了,而且很危险,有些人运气不好就死了,我一辈子没有结婚,赚了一点钱,又回到这里。五十年过去了,我寻访了一阵子,没有你们的下落。”
水生问:“你为何又做和尚了?”
弟弟一笑,说:“我这个和尚,是假的。有一家东顺公司,本地大企业,想必你也知道。他们在这里大兴土木,买了地皮造别墅,把农田都推平了。老板突发奇想,在江边造了一座寺庙,投资五千万。他们要招聘工作人员,我就去做了和尚,剃了光头,上班也在庙里,住宿也在庙里。我的法号,叫做慧生。”
水生说:“东顺坏事做得太多,造庙宇,想积德吗?”
弟弟说:“也是想赚钱。县里没有一座庙,过去烧香都要过江进城,现在大家都富了,日子过得安稳,香油钱很多。五千万投资,三五年就能收回本钱,二期开发还会追加一亿。”
水生叹了口气,讲了讲妈妈是怎么过世的,叔叔是怎么过世的,自己这次去石杨,是给玉生落葬。弟弟说:“阿弥陀佛,生亦苦,死亦苦,人间一切,皆是苦。”
渡轮开在江上,并不是直线行驶,到某一处沙洲附近便绕了个大弯,顺着江流开了一段。水生叨咕说:“玉生啊,船在江上拐弯了,你要跟住我。”他和弟弟两人站在甲板上,买了一点水喝着,继续说话。
水生问:“爸爸是怎么死的?”
“爸爸就死在我们等会儿要上岸的地方,那个渡口。”弟弟指了指江对岸,“当时我还小,有些事情记不清了,记得爸爸背着我到了渡口,那时渡口只有木船。我们一到江边,就被民兵管起来了。他们知道我们要渡江,不给。”
水生问:“后来呢?”
弟弟说:“关进了一间破房子,里面全是人,饿得奄奄一息。我们在里面蹲着,也没有吃的,等了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爸爸说,云生,他们不会给我们吃的了。爸爸找到一个墙洞,半夜里用手扒洞,扒开了,爸爸说,云生,这个洞不够大,但我真的扒不动了,你钻出去吧。我钻到洞外,爸爸说,云生,你看看外面有没有草啊树叶啊,拔一点给我吃,我胡乱摘了一些。爸爸又说,云生,不要拔了,动静太大,你往回走,如果记得路,就去赶上你妈妈和哥哥。我太小了,记不得路。爸爸就哭了,说云生,你试试看能去哪儿就去哪儿吧,你不要钻进来了,明天一早我就会死掉了,你钻进来只能看着我死掉。我趁夜跑出去,转了很久,遇到了老和尚。我说,我要去找妈妈和哥哥,老和尚说,不要去找了,跟我走吧。他给了我一点吃的,我就跟着他,越走越远。”
水生说:“这么说来,你也没有见到爸爸是怎么死的。”
弟弟说:“我没有。但我知道,爸爸是往生了。”
水生说:“我去问别人,他们都说,那一年走到江边的人都消失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也没有尸体。”
弟弟指着江对面说:“我回来以后,找人问过,这个码头就是当年渡船的地方,此岸彼岸,彼岸此岸,人们就是在这里往来过江。”
水生说:“云生,我要去看看爸爸死掉的地方。”
弟弟说:“五十年了,我也只能记得一个大概。我今天回庙里,顺路带你去看看。”
水生说:“云生,不要做假和尚了,我的女儿现在在深圳工作,我一个人住着很寂寞,你可以来陪我住着。”
弟弟摇头说:“虽说是假和尚,但我心里早已皈依了,住在庙里比较合我心意,不想再过俗世的生活。人生的苦,我尝够了。”
水生冷笑说:“东顺的庙,有什么皈依可言?一座假庙而已。”
弟弟说:“世间本来就没有真庙假庙。我有一天看到个破衣烂衫的老太,腿都残疾了,她知道县里有了庙,就爬着来进香。在山门口,她虔诚磕头,非常幸福。庙是假的,她的虔诚和幸福是真的。真庙假庙,都是一种虚妄。”
水生沉默良久,与弟弟失散了五十年,此时竟无话可说了,心里想,弟弟活着就好。又过了很久,渡轮轻轻靠岸,水生和弟弟来到码头上,举目张望,弟弟说:“好像还得往北走一段。”水生抛下了长途汽车,跟着弟弟,顺着一条小路,沿江走去,嘴里仍在念叨着:“玉生,转弯了。”穿过一座水泥厂,渐渐荒凉,四周都是芦苇,脚下的土地变得湿软。
弟弟说:“仿佛就是这里,我也记不清了,过去有房子,后来大概都推平了。”
水生说:“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又走了半个小时,弟弟说:“前面就是庙宇了。”这一带芦苇长得很高,挡住了视线。水生说:“我就不往前走了,东顺的庙,我决计不会踏进一步。”
弟弟说:“阿弥陀佛,勘破生死,放下执念。”
水生摇摇头说:“不要再说了。”
起了一阵风,芦苇簌簌摇动,水生闭上眼睛,想听到更多的声音。水生说:“爸爸,我来看你了。”等了很久,仍是只有风声,细小的蠓虫扑到脸上,像被人的发梢拂过。水生睁开眼,揉了揉眼睛,对弟弟说:“你既然要回庙,我们就在此分手了。”
弟弟说:“庙里还有工作,要考勤的。照理,我应该陪你去石杨镇。”
水生说:“保重。”留下电话和地址。弟弟双手合十,颂了一声佛号,穿过芦苇丛,走了。
水生独自往回走,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乌云正从江上升起,渐渐浓重。大中午的,庙宇的钟声传来,一声,一声,亦真亦幻,水生静立在原地,直等到钟声停下、飘散,世间的一切声响复又汇起,吵吵闹闹,仿佛从未获得一丝安慰。
水生俯身,抓了一把土,轻轻塞进胸口的麻布包裹里,口中念道:
“玉生,爸爸,转弯了。”
“玉生,爸爸,你们要跟我走,走到石杨镇。”
“玉生,爸爸,跟紧水生,不要迷路。”
……
前言/序言
我既不擅长写散文也不擅长写序,假如有人要我好好地说真话,我想说,不如我们来读小说吧。但虚构的叙事有时也会遇到些小麻烦,比如望文生义,比如吊打在世的作者,要求上缴苦难。假如别出心裁地上缴了一份顽皮,就不得不哭丧着脸说其实我口袋里还有苦难,那么我是在和谁玩游戏呢?假如我上缴的必须是苦难,就像交税似的。
写一部小说,如果作者非要站出来说自己写的都是真事,这就会变得很糟糕。纳博科夫曾经嘲笑过的。偶尔也有例外,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写到脑浆沾在街道上这一节时,曾经加了一句话:这不是编的,我编这种故事干什么?
这种句法在小说中非常罕见,它漂亮得让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也因为王小波是一位擅长虚构的作家,他有资格这么写。
我曾经为《收获》杂志的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慈悲》的文章,那是我写得较好的散文,但编辑说仍是有小说恶习。我重写了一次,希望它比较真实些,但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好转:
九十年末,我们家已经全都空了,我爸爸因为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我妈妈在家病退多年,我失业,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我买辆摩托车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陷于破产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游手好闲的爸爸,曾经暴揍过我的三流工程师(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曾经在街面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谊舞的潇洒中年汉子(也被我写进了小说里),他终于发怒了,他决定去打麻将。
我妈妈描述他的基本技能:跳舞,打麻将,搞生产。他曾经是技术标兵,画图纸的水平很不错,在一家破烂的化工厂里,如果不会这一手,凭着前面两项技能的话基本上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现在,国家不需要他搞生产了,他退休了,跳舞也挣不到教学费了,因为全社会都已经学会跳舞,他只剩下打麻将。
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麻将馆了,合法小赌,心旷神怡,都是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我爸爸决定去那儿试试运气。我妈妈是个理智的人,知道世界上没有必胜的赌徒,大部分人都输光了回家的。尤其是,我们家的赌金就是菜金,输了这一天的就只能吃白饭了。
然而我爸爸没给她丢脸,每个下午他都坐在麻将馆里,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砍下来几十块钱。这种麻将,老头老太玩的,赌得太大会出人命,赢几十块钱属于相当不容易。有时候赢一百块,为了不让对方上吊,他还得再输回去一些。后来他告诉我:“我六岁就会打麻将了,我姑妈是开赌场的。”
每一天黄昏,我妈妈就在厨房望着楼道口,等我爸爸带着钱回来,那钱就是我们家第二天的菜金。他很争气,从未让我妈妈失望,基本上都吹着口哨回来的。我们家就此撑过了最可怕的下岗年代,事过多年,我想我妈妈这么正派的人,她居然能容忍丈夫靠赌钱来维生,可见她对生活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
这故事简直比小说精彩,可惜从来没有被我写进小说,因为它荒唐得让我觉得残酷,几乎没脸讲出来。在厚重的历史叙事面前,这些轻薄之物一直在我眼前飘荡,并不能融入厚重之中。
《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慈悲本身并非一种正义的力量,也不宽容,它是无理性的。它也是被历史的厚重所裹挟的意识形态,然而当我们试图战胜、忘却、原谅历史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我父亲去打麻将时的脸色,那里面简直没有一点慈悲。他觉得真庙都是假的,而麻将馆才是赢得短暂救赎的地方。
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写的三部曲是“砖头式”的小说,似乎砖头很不要脸,我想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可能仅仅让我自己好受些。
谨以此为后记,并谢谢我所有的编辑们。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的节奏感处理得非常巧妙,读起来完全不像是在“读”一本厚厚的书,而更像是在“经历”一段漫长而富有张力的旅程。起初的铺陈显得缓慢而扎实,像是在为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做序曲的调音,每一个音符都看似不紧不慢,但你总能感觉到背后蕴藏的巨大能量。随着故事的深入,特别是当主要冲突开始爆发时,节奏骤然加快,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让你不得不屏住呼吸,一口气读完那些高潮迭起的章节。而作者高明之处在于,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他也能精准地插入一些极富哲理性的停顿,让读者得以喘息,消化刚刚发生的一切,这种张弛有度的把控,使得阅读体验跌宕起伏却又始终保持着一种优雅的平衡感。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的心率和情绪也跟着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般的起伏,回味无穷。
评分从主题深度上来说,这本书探讨的议题极具穿透力,它触及了人类社会中那些最基本、也最难以言明的情感纠葛和道德困境。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或廉价的慰藉,而是将一团复杂的线球扔到读者面前,让你自己去尝试理清。我读它的时候,经常会陷入长久的沉思,思考书中人物在特定情境下所做的艰难抉择,并联想到我们自身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相似的悖论。作者似乎对人性中的灰色地带有着近乎残酷的坦诚,揭示了光鲜外表下隐藏的脆弱和自私,同时也捕捉到了那些微弱却坚韧的光芒。这种对复杂人性的不回避、不美化的态度,让我感到震撼,因为它拒绝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而是拥抱了人性的全部光谱。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们得以直面那些我们倾向于忽略或压抑的内心真实。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说实话,初读时有些令人却步,充满了古典的韵味和一种近乎仪式感的书面语,与我日常接触的阅读材料风格迥异。一开始我担心自己会无法适应这种略显沉重的笔调,但坚持下去后,我开始体会到这种用词的精准和力量。它不是为了炫技而堆砌辞藻,而是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准确地击中了情绪的核心。那种描绘景物的笔法,简直可以用“挥洒自如”来形容,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立体感十足的画面,让人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的气味,感受到光线的温度。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处理内心独白时的那种克制与爆发的平衡,情感的汹涌被包裹在一层冷静的叙述之下,反而更具震撼力。这本书无疑提升了我的阅读品味,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文学表达的深度,明白真正的文字功力,不在于华丽,而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准确性。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结构简直是一场精妙的迷宫探险,作者在构建世界观和人物关系时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与洞察力。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沉浸其中,因为它并非那种直来直往、一目了然的故事。相反,它要求读者像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那样,去细致梳理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和场景转换。那些潜藏在平淡生活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随着情节的推进,才缓缓显露出其狰狞或温柔的面貌。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时间感的处理,时而拉伸,时而压缩,使得关键转折点充满了宿命般的无可逃避感。读到后半部分时,我甚至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对照着前文的伏笔,那种“原来如此”的顿悟感,是阅读体验中最令人愉悦的部分。它不是那种看完就忘的快餐读物,更像是一部需要反复咀嚼的文学艺术品,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像是拨开了一层又一层的迷雾,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寓意。那种对细节的极致打磨,让角色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活生生、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个体,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无不牵动着读者的心弦。
评分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本书给我的整体感受,那便是“共鸣的复杂性”。我很少遇到一部作品,能让我对其中多位角色的立场产生强烈的理解,即使他们的行为在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作者塑造人物的功力,在于他赋予了每个人物都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即便是反派,其行为逻辑也建立在自己独特的痛苦和信念之上。这迫使我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和情感代入,我不再是单纯地评判他们,而是试图去感受他们的处境。书中某些场景的描绘,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对归属的渴望,让我几次停笔,望着窗外发呆,因为那些文字精准地捕捉到了我生命中某些难以言喻的片段。它不是那种让你看完后拍案叫绝的爽文,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到灵魂深处的触动,让人在合上书页后,依然能感受到角色们呼吸的痕迹,以及他们未竟的心愿在自己心中回荡。
评分还不错吧,隔日达很速度。。。。。。。。。。。。。。
评分很好的一本书
评分这本书写的故事看完挺揪心的
评分挺好的
评分京东618活动买的,199-100之后白条又200-80,觉得超合适,给自己也充点电。
评分纸张不错,养成好好看书的习惯,睡前看二十页
评分收到了,快。
评分朴素平实,却引人共鸣
评分非常不错的一本书,装帧很精美,版本也不错,还实惠!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