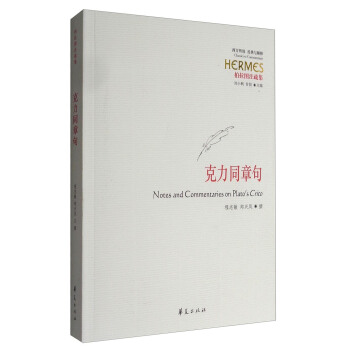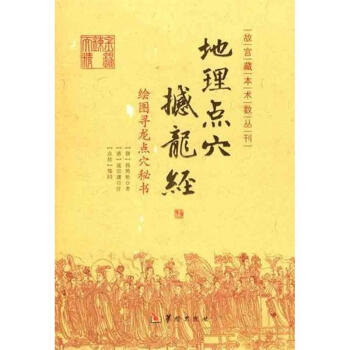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 《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是施特劳斯的得意弟子伯纳德特的经典代表作。2. 与许多伟大天才具有相同的命运,伯纳德特的重要性,在他身后才格外显现出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将长久不可磨灭。
内容简介
苏格拉底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分开,出其不意地迫使我们起而顿悟。《王制》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针对美、善和正义,是就这些东西对我们理解正义有所贡献而言的。分析的程序是双重的: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并置,又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分开。它既分隔又结合,然而分隔和结合使得任何论辩都不能平滑地前进,因为,正是论辩中出乎意料的断裂和出乎意料的接合,构成了形式分析的行进路线。作者简介
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1932-2002),美国著名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1950年代于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伯纳德特与布鲁姆(Allan Bloom)、罗森(Stanley Rosen)等师从施特劳斯。自1965年起,伯纳德特任教于纽约大学,在教书和研究的40年中,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上。伯纳德特的代表作有《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情节中的论辩》、《生活的悲剧与戏剧》、《道德与哲学的修辞术》、《美的存在》等。
伯纳德特的重要性,在他身后才格外彰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将长久不可磨灭。
目录
致谢 / 1导言 / 1
第一部分(卷一) / 7
1.苏格拉底(327a1-328c4) / 7
2.克法洛斯(328c5-331d3) / 10
3.珀勒马库斯(331d4-336a8) / 16
4.忒拉绪马霍斯[上](336a9-347a6) / 20
5.忒拉绪马霍斯[下](347a7-354c3) / 27
第二部分美(卷二—卷四) / 35
6.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357a1-368c3) / 35
7.两个城邦(368c4-373e8) / 46
8.哲人-犬(373e9-376c6) / 58
9.教育(376c7-378e3) / 62
10.神学(378e4-383c7) / 68
11.勇气和节制(386a1-392c5) / 70
12.效仿与模仿(392c6-398b9) / 75
13.音乐和体操(398c1-412b7) / 79
14.高贵的谎言(412b8-417b9) / 83
15.幸福(419a1-422a3) / 86
16.战争与革命(422a4-427c5) / 88
17.正义(427c6-434c6) / 90
18.勒翁提俄斯(434c7-441c8) / 100
19.自然与种(441c9-445e4) / 114
第三部分善(卷五—卷七) / 117
20.女人-戏剧(449a1-452e3) / 117
21.平等(452e4-457b6) / 122
22.共产主义(457b7-466d5) / 126
23.战争(466d6-471c3) / 130
24.言与行(471c4-474c4) / 133
25.知识与意见(474c5-484d10) / 140
26.哲学禀性(485a1-487a6) / 152
27.哲人-王(487a7-502c8) / 157
28.善(502c9-506d1) / 168
29.太阳、线、洞穴(506d2-516c3) / 173
30.上升与下降(516c4-521b11) / 197
31.数学与辩证法(521c1-541b5) / 201
第四部分正义(卷八—卷十) / 207
32.堕落(543a1-550c3) / 207
33.寡头政治(550c4-555b2) / 213
34.民主政治(555b3-562a3) / 218
35.僭主政治(562a4-576b6) / 223
36.三个比较(576b7-588a11) / 228
37.诗(588b1-608b10) / 235
38.灵魂(608c1-612b6) / 247
39.关于厄尔的神话(612b7-621d3) / 250
主题索引(汉-英) / 255
主题索引(英-汉) / 266
讨论过的《王制》段落索引 / 277
精彩书摘
1.苏格拉底(327a1-328c4)[9]使用象征手法能使主题得到方便的表达。《王制》是从叙述一个受阻的上升过程(thwarted ascent)开始的。苏格拉底是故事的讲述者。苏格拉底好像纯属偶然地遭到阻拦,从而有机会讨论正义。他计划去庇莱厄斯(Piraeus)参拜色雷斯女神本狄斯(Bendis),观看了节日的第一场庆典以后就回家。和他一起的是格劳孔(Glaucon),即阿德曼图斯和柏拉图的兄弟。苏格拉底的参拜和观礼是不同的,这似乎指向这样一种区别,一方面是言辞中的最优城邦(the best city in speech),实现它所需要的条件非人类手段所及(450d1,456b12,499c4),另一方面是发现政治事物的本性,与之相伴的是关于乌托邦的详细描述(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2.31)。[52]在我们的书写传统中两种形式的名称恰好保留了这个区别,即Politeia与Politeiai,和Regime与Regimes。([译注]这两组词中的后一个都是前一个的复数形式。)无论是否是必要的虚构,作为一的最优政体包含了作为杂多的所有次级政体([译注]这里的英文原文是“… the one best regime comprehends the manifold of all inferior regimes.”)作者希望强调一(one)与杂多(manifold)的对照关系,故用意译。。即使从未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它也指导着人去理解政治生活。
作为一的最优政体,其功能与《王制》本身的叙述形式如出一辙。苏格拉底既作为自己,又扮演着所有其他角色。我们通过他的眼睛看所有事情,而听不到他刻意忽略的东西(342d2-3,350c12-d1)。他向我们介绍珀勒马库斯(Polemarchus),就好像他已经在那里。其时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正要离开,珀勒马库斯看见他们,命奴隶跑过来叫他们等他过来(327b2-4)。苏格拉底没有说他是如何推断出这一情况的(参见328c2)。他没有这样开始自己的讲述:他的长袍突然被拉住,奴隶的请求使他转过身来问珀勒马库斯在哪里。他省掉了依据经验进行推断的过程,给出的叙述极其顺畅。如果他们还是不得不等珀勒马库斯赶上来,那么奴隶必定已经跑过来了;至于珀勒马库斯要他跑过来——他没有要他抓住[10]苏格拉底的长袍——这一点苏格拉底还是可以单从他所了解的珀勒马库斯的专横脾气推断出来。与苏格拉底的胸有成竹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珀勒马库斯本人关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计划的猜测(327c4-6)。苏格拉底并不否认他的猜测。但是,苏格拉底的胸有成竹更多体现在叙述上的不动声色。由于是通过他来了解一切,我们往往忽略了在应召而来的布景中,他的实际在场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跟随着论辩过程一路前行,而没有从这个过程退后一步,去注意苏格拉底的作用。从珀勒马库斯的奴隶前来找他,到他开始与克法洛斯讨论,苏格拉底确实把其他人都置于次要位置。格劳孔决定让大家等珀勒马库斯(327b7-8);格劳孔再次宣称,如果珀勒马库斯不听,谁也说服不了他(327c13);和珀勒马库斯一起来的阿德曼图斯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328a1-2);苏格拉底服从格劳孔留下来的决定(328b2-3)。苏格拉底一直在谈话,而对事情不作任何安排。他好像整个被卷进了谈话中,而无力控制局面。
珀勒马库斯从苏格拉底看到了自己这帮人数目众多来推断,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如果不留下来,就是在证明自己更强大(stronger)。他用的“更强大”(kreittōn)也是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us)在把正义定义为更强大者的利益时使用的那个词。但这个词是含混的。一旦忒拉绪马霍斯承认自己并没有用“更强大”来意指摔跤手波吕达马(Poulydamas)(338c5-d4),就恢复了它“更好”这一较宽泛的意义,从而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是否在论辩与忒拉绪马霍斯同样的问题。珀勒马库斯总是以强力相威胁,并决意对苏格拉底提供的让人信服的其他方式充耳不闻。珀勒马库斯的威胁和顽固都不是认真的。阿德曼图斯会攻击自己的亲兄弟吗?况且,既然珀勒马库斯不能阻止任何人听苏格拉底说完,他最后不也落得个势单力孤吗?
珀勒马库斯先是极力推行多数人统治的绝对正确性,但到后来,在格劳孔肯定谈话是让人信服的唯一方式以后,他又承认多数人的正确性并非牢不可破。珀勒马库斯问苏格拉底,他是否能够避开无理地拒绝听他讲道理而造成的障碍。《王制》这篇对话就是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格劳孔插进来中断了它,但如果不是格劳孔的插入,我们就听不到这个回答。诉诸武力会导致不光彩的冲突,而如果另一种达到信服的方式生效,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就将继续上路回城;[11]正是两者的妥协,使关于正义的讨论得以发生。阿德曼图斯问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是否知道定于当晚举行的火炬赛马,从而为妥协创造了条件。他希望比赛的场面能够化解苏格拉底和珀勒马库斯之间的分歧。苏格拉底一再表达对新鲜事物的兴趣,以便珀勒马库斯有机会挽回面子。珀勒马库斯表达的强权意志,使他显得很难友好地发出宴会和观看表演的邀请,于是就插进来补充说,苏格拉底可以和到场的许多年轻人聊天。足以让人愉悦的夜间活动就这样定了,它取代了珀勒马库斯令人不快的插曲。但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攀谈起来,把娱乐节目晾在一边。尽管武力威胁已不复存在,在《王制》持续到很晚的谈话中,苏格拉底似乎还是处于某种被强制状态(472a8,504e6,509c3)。苏格拉底可以借格劳孔与阿德曼图斯之力来抵挡珀勒马库斯,但他难以抵挡包括忒拉绪马霍斯在内的多数人意见(450a4-5)。苏格拉底对谈话的控制显然使得这种意见似乎在暗地里背离他的意志滋长。不管怎样格格不入,它对他本人来说仍然是有好处的。谁能说,一个以反讽和自我认识著称的哲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让事情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一系列挫折开启了《王制》,并标出了整个进程。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没有启程回家,他们也未能到珀勒马库斯家就餐然后去看接力赛。讨论伊始苏格拉底就相信,自己在表达了对过于贪心地接受的忒拉绪马霍斯假想的款待的失望之后,就已经退出了(354a10-c3)。此后,正当他建议对腐败的政体给予解释时,听众的反对再次打断了他,他不得不引入哲人-王这个概念。伴随哲人-王而来的是“善的理念”(idea)。这里,苏格拉底似乎有机会报复了,因为他拒绝直截了当地告诉格劳孔他关于这一点的意见(533a1-5)。使得关于正义的理解成为可能的限制,似乎也限制了关于善的理解。《王制》似乎不能使苏格拉底受阻的上升之路得到补偿。
2.克法洛斯(328c5-331d3)
[12]克法洛斯承认,自从感受身体快乐的能力(而不是欲望)减退以后,谈话的欲望和乐趣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了,于是苏格拉底就问他年老的感觉如何,因为这是他自己也会不得不承受的事情。他引用诗句“在垂暮之年的门槛上”来形容克法洛斯即将到来的生命岁月。这个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没有说是离开生命之屋还是进入哈德斯(Hades)的地界([译按]指阴曹地府)。克法洛斯的同辈人确实相信,随着老年的来临,一切都随之而去,唯有怀着遗憾回首往事。但克法洛斯本人似乎还在期待另一种生活,无论这种生活是奖还是罚。他还没有马上谈到哈德斯,但随着苏格拉底婉转的探问,当问题由节制转向正义,这个话题还是冒了出来。克法洛斯说,年老本身不是导致晚年凄凉的原因,但他马上又自相矛盾地说,他的同龄人向往青年时代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他们已无力享用了,因此对他们来说,年老仍然是一种罪过。克法洛斯责怪他们,不是因为他认为爱欲或其他快乐不应当作为标准,而是因为他们不愿认同年老本身带来的平和。他们不去看看年老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他对那些对他的性功能探头探脑的人大为光火,这说明他那放纵无度但他又显然无力控制的青年时代,如今是他乐于摆脱的。尽管承认庄重与平和在一个人的年轻时代也会有,对克法洛斯来说,老年人的脾性(tropos)似乎就是顺命。然而,说顺命似乎还嫌不够,因为按克法洛斯的想法,人到了老年欲望不再急迫,就好像从众多野蛮狂暴的奴隶主手上解放出来了一样。但由于克法洛斯的同龄人在想象中肯定仍然屈从于欲望,他似乎把“脾性”与从诗人的格言里获得的信念等同起来,从这些格言,人们可以了解欲望的真相。在诗歌提供的想象中,在那种语言里,老人找到了[13]令人愉快的补偿和表达不满的合用手段。克法洛斯通过诗来理解自己的状况,但却丢掉了诗意。他不仅把索福克勒斯诗作中单称的奴隶主改成了复数,而且把原句中的“宛如”(hōsper)也弄丢了。他所说的野蛮狂暴的奴隶主们是完全真实的。
苏格拉底不想揭穿克法洛斯在解释上的混乱,按这种解释,年龄和脾性都是平和的唯一原因;相反,他表达了普通人的这样一种观点,克法洛斯的财富使他更容易忍受衰老——“他们说,财富是大大的慰籍”。金钱引起了正义[问题]。克法洛斯并没有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纵欲无度当成道德问题,从而担心死后遭罚。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表明了托马斯主义所描绘的,存在于异教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之间的区别(托马斯[Thomas]《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12ae CIII,4,3m)。正是因为金钱减轻了他的恐惧,希望所带来的快乐取代了身体的欲望,他才从快乐和欲望谈起。克法洛斯承认,财富确实是一种条件,而他的同龄人的看法对那些贫穷但是正派的人来说是正确的。老来确实不易,不过他接着说,单靠金钱是不能消除不满的。克法洛斯再次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依据,不过这次不是诗人,而是一个政治家。
有一次,住在塞利福斯(Seriphos)岛上的一个人挖苦忒米司托刻勒(Themistocles),说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所在的城邦,而不是因为他本人如何。忒米司托刻勒回答说,如果他是塞利福斯人,他会仍然是个无名之辈,而那个塞利福斯人如果是雅典人,情况也是如此。忒米司托刻勒的伟大对于雅典的伟大来说,就像克法洛斯的平和之于他的财富。克法洛斯不惮于赞美自己得体的谦逊。他暗示了如下四种相似之处:(1)把忒米司托刻勒放到塞利福斯就像让克法洛斯失去财产;(2)作为雅典人的忒米司托刻勒犹如克法洛斯拥有财富;(3)塞利福斯人作为塞利福斯人就好像贫穷而心怀不满者;(4)把塞利福斯人放到雅典,犹如让不满者拥有财富。克法洛斯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正如塞利福斯人之所以爱挖苦人,是因为他是塞利福斯人,贫穷的不满者可能是因为贫穷才不满。苏格拉底因而想知道,“老而有财”是否真是心境平和的条件,是否是克法洛斯不为挣钱而操心,才让他生活更加自在。克法洛斯生气地问苏格拉底,怎么能把他想成一个一门心思赚钱的人,这样他就已经承认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祖父很能赚钱,他本人则浅尝辄止,因为他的性格不让他去把自己的遗产增长到能够满足他三个儿子需要的程度。如果一直耽于挣钱,他就不会这么平易近人了。
……
前言/序言
导 言[1]本书的标题暗指在《斐多》(96a6-100b3)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自述思想历程时使用的短语。克贝(Cebes)对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死的论证提出了反论,苏格拉底的反驳以讲述自己的故事起头。克贝同意,灵魂如果从来没有占据身体,也就不会[从身体中]逝去,但他不解的是,何以证明灵魂的不断转世是没有止境的。他尤其被这样一个显然的矛盾所困扰:灵魂就其独立于身体而言本身就是善的,但却必须与身体结合在一起。他问道,为什么这里是“形成”(becoming),而不是“存在”(being)?克贝的问题引发了苏格拉底关于因果的讨论,以及在灵魂本身的善所引发问题的基础上,关于与目的论相关联的质料因和动力因的讨论。
苏格拉底区分了关于原因的不同问题,这些问题他在着手哲学思考时提了出来。他还区分了按前哲学的方式(prephilosophically)所能给出的不同回答。然而,他给出的前哲学的回答连最粗略的推敲都通不过,它们不满足因果解释的最低条件。苏格拉底所能设想的所有因果解释,都在根本上具有要么是加法要么是减法这样的算术操作特征。他知道,相反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由此得不到因果解释。但是,机械地描述一与一之和,这与对某个东西一分为二的机械描述没有什么区别。把两个一拉到一起,这对于二来说,与把它分开是一回事;两个一的合并对于一来说,也与把它们分开别无二致。把身体和灵魂合在一起得到一,它们还是二;分开看的身体与灵魂合为二,但每个还是一。因此,作为分离,死就是从一得到二,而作为结合,生就是从二得到一,但这样一来,生与死就都既是一,又是二。
苏格拉底于是意识到,只有当结合与分离是心灵(mind)的作用,这些荒谬的结果才会消失。然而,由于两个理由,阿纳克萨戈拉式的心灵[2]在此不能胜任。阿纳克萨戈拉(Anaxagoras)允许所有事物先于心灵的作用而结合。心灵只是一种分离的力量。但是,既然心灵必须也是结合的力量,那么除非事物已经为心灵所结合或分离,它们就从来不曾结合或分离。阿纳克萨戈拉曾尝试把不会超距发生的机械因果作用,与一种理解原则结合起来,该原则将对机械的因果作用不断运转不可避免地产生的那些杂凑进行规整。然而,一旦接近和远离都是心灵作用的结果,事物就既结合又分离了。心灵的规整作用于是就产生一种因果的算术。但这是有代价的。心灵规整事物,但并不是为了善而规整。现在,心灵成了唯一的原因,但它却不合理性(rational)。原来的困难是,灵魂与身体一起何以既是一又是二,现在这个困难在心灵内部重新出现了,这就是目的合理性与秩序合理性的分裂。事物的秩序与事物的善并不相谋,要结合它们,就会发现因果运算是不可能的。要是某个要素把某物的善赋予这个某物,所涉及的加法操作就会与分离的作用一样,不会导致结合。因此,合理性(rationality)的两个方面所需要的结合不可能通过任何一方达成——一个方面的不可能是因为这样把秩序与善既放在一起又加以分离,另一个方面的不可能是因为善不是机械地建立事物的秩序。善既不可能是事物之和,也不可能是事物中的一个。
风停的时候,水手就改用桨。他不再依赖外力之助。就我们从柏拉图那里所知道的而言,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这种类似于再次起航的举动。苏格拉底告诉克贝,在悟出他想在阿纳克萨戈拉的书中得到什么之后,他失望地发现阿纳克萨戈拉没有将其作为善的原因而求助于心灵。苏格拉底知道如何能够无误地探知心灵的存在(presence),但他不知道阿纳克萨戈拉会如何着手证明心灵既存在于每一事物又存在于所有事物,因为赋予一事物的任何善都能证明是对它和另一些事物的恶,而且,一起而不是分开赋予它们的任何善,都能进一步证明是对它们和另一些事物的恶。目的论必定是一种建筑术。但是,如果善由于不依赖于其他东西而位于序列的末端,那么序列就能够垮掉但无损于善;而如果善分配于序列,那么,在把善赋于序列中的任何东西之前,[3]就需要知道整个序列。终极因似乎是一个必要但又不可能运用的原则。
苏格拉底援引自己的情况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能在说苏格拉底做了所有依照心灵所做的事情之后,在解释他所做的每件事的原因时,说苏格拉底坐在牢房里是因为他的肌肉和骨骼按某种方式加以摆放并具备某种能力,说他与克贝谈话是因为耳朵里的振动和空气中声音的运动。只要不忽略导致囚禁和谈话的真正原因,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援引这些原因;他真正反对的是,在解决任何因果的算术必须面对的困难之前,就把机械的原因和真正的原因混杂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是双重的:雅典人的意见是,最好对苏格拉底加以处罚;接着,由于这一点,苏格拉底所持的意见是,最好呆在牢房里,服从他们规定的任何处罚都比逃走更为正义。苏格拉底放弃了阿纳克萨戈拉式心灵的作用,代之以关于善的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苏格拉底是不正义的,另一种主张他是正义的。如果苏格拉底所做之事是依照心灵,那么雅典人做的事情就不可能出于心灵,因为,否则,由于这是按相反的路线达到同样的结论,心灵就是完全不合理性的。雅典人认为死是恶而生是善,苏格拉底应该遭受恶;但苏格拉底告诉他们,他不知道死是不是恶,而在《斐多》里他通篇都认为这对他来说是善的。即使苏格拉底一被指控就遭逮捕并严加看守,使他的朋友们不可能帮他偷逃出去,这对他的意见也没有影响,而他遭到的责罚与他的死,则以一种离奇的方式表现了心灵的作用。理由(reason)的不合理性无疑区别于机会的随机性和因果之链的必然性,但是,也很难因为阿纳克萨戈拉在主张心灵的支配地位时忽略这样一种原因,就对他加以指责。
支持苏格拉底呆在牢房里的那些依据看来是过头了,它们彼此也不融贯。要么,他自己的意见不产生效果,或者附从于雅典人的意见,并在原则上与之矛盾的同时,在结论上支持它;要么,雅典人认为的死刑实际上是自杀,而苏格拉底利用公开的事件来掩盖私己的利益。他的对话者们[4]至少在一开始认定这是自杀,如果离开《斐多》中的政治考虑,很难说他们最后是否改变了想法。苏格拉底自己的说法是,按照对目的论任何一种通常的理解,“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这种意见驱使”(99a2),他的肌肉和骨头早就在麦加拉(Megara)和波俄提亚(Boeotia)一带活动,因为对于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兼具身体和灵魂的活人来说,善必定是生命的维持。如果善不能归于必要和充分条件的结合,目的论就是不可能的。由于意识到自己发现不可能解释所需要的结合,苏格拉底遇到了引发苏格拉底式转向(Socratic turn)的困惑。通过重新表述他拒绝逃离牢房的原因,苏格拉底指出了一条出路。他相信留下来更正义,也更高贵(或更美)(99a2-3)。苏格拉底从善出发,接着把它分成正义、高贵和善。善现在成了三个东西的复合物,对此结合起来看与分开看一样令人困惑。这样就能够着手把雅典人错误的意见,和苏格拉底正确的意见,都理解为心灵作用的结果。善表现于意见的零碎片断,这与在由心灵真正地规整的整体中,还不是一回事。在因果问题表明不可能以直接的方式思考事物之后,苏格拉底所求助的言论和意见就是这样一些零碎片断。这些片断的言论作为一些整体或形式(eidē)相继展示(《治邦者》262a5-263b11),而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从它们推进到真正的形式(eidē)。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形式分析,就是想无论是关于心灵还是关于善,都坚定地取代而不是放弃目的论。
脱离辩证法的实践就无助于展示形式分析。因此,在导论里对柏拉图的论辩做简单的说明,要更合适一些。一般说来,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给出了两种类型的论证。这些论证或者势若爆发,或者形似纤丝。有时,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清晰有效,不仅是对话者,就连读者也立即承认其说服力。苏格拉底针对克法洛斯(Cephalus)的反例(331c1-d1)就是这样一种爆发式的论证。然而爆发式的论证很少用来解决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苏格拉底提出的论证似乎是演绎性的,但我们感觉到在论辩过程中,新的前提被偷运进来,或者词义一再变动,以至于就像阿德曼图斯(Adimantus)所抱怨的那样,[5]我们觉得自己是被诱骗而不是被说服(487b1-c4)。纤丝式论证意在产生转化(periagogic or conversive)效果(518d4)。它们让我们转向一些东西,如果不是苏格拉底以一种并非十分直接的方式赞同,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些东西。他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些东西与另一些东西分开,出其不意地迫使我们起而顿悟。《王制》就是一次形式分析,它之针对美、善和正义,是就这些东西对我们理解正义有所贡献而言的。分析的程序是双重的: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并置,又把正义与其他东西分开。它既分隔又结合。然而分隔和结合使得任何论辩都不能平滑地前进,因为,正是论辩中出乎意料的断裂和出乎意料的接合,构成了形式分析的行进路线。
用户评价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具有挑衅性。它不是那种平铺直叙、让你安心的传记文学,而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迷宫,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和逻辑上的陷阱。作者似乎故意将时间线打散、重组,用一种近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式来重述某些核心事件,使得读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去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基于对核心思想的再诠释和升华。我特别注意到,在描述某些关键性的思想冲突时,笔触极其冷峻,没有丝毫煽情,反而通过大量的留白和精确的细节捕捉,将人物的内心挣扎呈现得淋漓尽致。这需要作者对文本源头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和驾驭能力。对于那些习惯了线性叙事的读者来说,初读可能会感到吃力,甚至有些许的挫败感,但这恰恰是本书的精妙之处——它拒绝被轻松消化,它要求读者付出相应的认知努力。最终,当你拼凑起那些碎片化的信息时,收获的绝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更复杂、更具层次感的历史洞察力。
评分当我合上书页的那一刻,最大的感受是“清醒”。这本书的整体基调非常具有反思性,它似乎在不断地叩问我们现代社会的某些基石。作者没有直接给出结论,而是通过对往昔智慧的梳理,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对照组,让你在对比中审视当下。它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将宏大的历史背景,浓缩在了几个关键人物的日常互动之中。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在与人辩论,而是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期时,知识分子所能采取的最激进也最温柔的反抗方式。这种对“行动中的哲学”的捕捉,非常精准。我特别喜欢作者处理争议性话题时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力量,他将那些激烈的、甚至带有冒犯性的对话,包装在了一种极其冷静和优雅的叙事外衣之下,反而使得其中的思想张力更加强大,让人在阅读时感受到一种内在的震颤,而不是表面的喧哗。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是极其典雅,却又不失尖锐的批判性。它在构建场景和描绘人物心理时,那种词汇的精准度和句式的变化,达到了极高的文学水准。我常常会因为某个恰到好处的比喻或者某个出人意料的动词而停下来,反复品味。这不像是一本严肃的哲学解读,更像是一部精心打磨的史诗剧本,每一个角色的出场和退场都带着命运的重量。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引用和转述那些晦涩的古代思想时,没有采用那种僵硬的学术腔调,而是通过现代读者的视角进行了一次有温度的“翻译”。这种翻译不是简单的词汇替换,而是对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让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听起来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争论。对于我这样对古代思想有一定了解,但又渴望看到新鲜解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参照系,它证明了伟大的思想是可以被用最精致的文学形式来承载和再现的。
评分这本书在结构上展现出一种近乎建筑学的美感。它不是简单的线性时间推进,而更像是一个多层结构的螺旋上升体,每一层都回扣前一层的内容,但又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更深的理解。作者似乎精通于如何运用“重复”的力量,通过不同场景对同一核心概念的反复打磨和侧面烘托,使得这个概念最终牢牢地嵌入读者的认知结构中。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在选择材料时的那种近乎偏执的严谨,每一个引用的对话,每一个场景的描述,似乎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以确保它们能够最大化地服务于整体的哲学目标。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韵,没有一处显得多余或牵强。对于那些真正热爱沉浸式阅读体验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场盛宴,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信息,更是一种完整的、有节奏感的精神漫游。它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慢下来,去欣赏思想碰撞时所产生的那些火花,那种细微但又极其关键的差别。
评分这本新书读下来,感觉作者对那个古老时代那种微妙的、游走在边缘的智慧,把握得相当到位。它不像那种教科书式的、把苏格拉底塑造成完美圣人的作品,反而更像是一份考古发掘报告,揭示了那些被时间尘封的、充满烟火气的对话片段。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文本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克制,没有过度渲染戏剧性,而是让哲学的光芒自然地穿透历史的迷雾。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能闻到雅典城邦黄昏时分泥土和汗水的味道,那些街头巷尾的辩论,不仅仅是抽象概念的交锋,更是关乎城邦存亡、个人道德困境的真实挣扎。作者没有试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巧妙地设置了一系列让人难以回避的悖论,迫使读者必须亲自参与到这场智力探险中去。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远超出了单纯阅读传记或历史的范畴,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些“常识”。那种在对话中步步紧逼,却又处处留白的叙事手法,让人欲罢不能,读完后很久都无法从那种思辨的氛围中抽离出来,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也被悄悄地重塑了。
评分《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还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还可以。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评分公元前407年20岁跟随苏格拉底学习,此前曾向克拉底鲁学习赫拉克利特哲学;向赫莫根尼学习巴门尼德哲学。据说曾想写戏剧,给苏格拉底看,被否定。
评分游学12年
评分游学12年
评分绝对好 强烈推荐 喜欢
评分伯纳德特作品,还不错,这一系列出的太多,记不清常会买错:(
评分伯纳德特的重要性,在他身后才格外彰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将长久不可磨灭。
评分公元前407年20岁跟随苏格拉底学习,此前曾向克拉底鲁学习赫拉克利特哲学;向赫莫根尼学习巴门尼德哲学。据说曾想写戏剧,给苏格拉底看,被否定。
评分公元前390年出访:毕达哥拉斯学派掌握的政权等。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不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导读 [How to Read Plato ]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07216/56613408N3b4cdf3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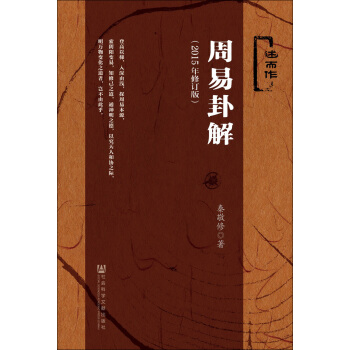



![理想国 [The Republic]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9836/579f2027Ncc53c0c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