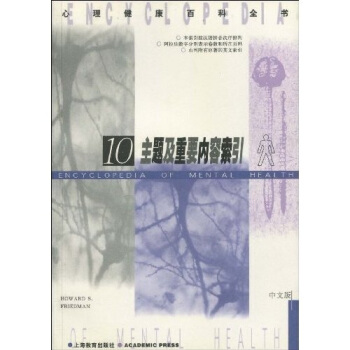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作者非學院派心理學傢;作者擅長心理分析;
如果你對現實的社會人生感到苦悶難受無奈無解以緻憤恨;
那麼,讀讀這3捲,對你不無益處。
作者簡介
李毅強(筆名,李沫來),曾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留學日本六年。專攻榮格派心理學,學習成唯識論。讀書終生,理解他人,反省自己,充實自己,體味人生;言行一緻,將心比心,我之外皆我師。精彩書評
★閱讀是一門快要失傳的藝術。在這個思想不能集中的時代,書籍仍舊是重要的,但作為曾經的齣版人,我可以堅定地說,這不是一本暢銷書,盡管相親節目都配備瞭心理專傢。這是一本普及性書籍,一本科普自助書籍。你可以不知道李毅強,但不能不知道這套《心理學散論》。好書改變人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遇到這套書。請閱讀此書。獨自閱讀。你知道,那是一場內心的盛宴。
對《心理學散論》,諸位如未讀懂,亦請對作者心存敬意。
——喬木
目錄
第一輯 記憶與思想之間——隔雨望紅樓筆記摘抄前記 從北京歸來
聽傅聰先生的訪談
Tobe與Tohave
附錄:消夏雜記:Tobe與Tohave
小說作法及其周邊
站在信仰的門檻上
語言(Logos,Wort)
從實際生活中開拓的地盤越大,所獲得的Eros情感也越豐盛
附錄:夏日雜記:關於荷馬的成語
許思園先生與許思園現象
附錄一:夏後雜記:“開口求人難”,李太白畢竟瞭不起!
附錄二:“開口求人難”(續),黑格爾與歌德
許思園先生的議論
附錄:臉譜的變化
“意義”是一種人類不能須臾離之的“疾病
羅傑斯的人際交往學
男性因素與女性因素
附錄:消夏雜記:《浮士德》中的幾句詩
寫作中”自我“的重要性
附錄:消夏雜記:陸九淵的”田地清淨“說
勒本的著作與觀點
寫文章隻需”自圓其說
尼采點滴:時代錯誤、曆史感、創作
宗教的生理與心理基礎:大腦與太陽神經叢
他人焦慮癥:人我未分的混沌狀態
結束語:春華鞦實
第二輯 精神病理學點滴
讀佛心得:“人際關係中毒癥”解剖
“人際關係中毒癥”釋義及其他
“獻身性”的病理——對日本某文學傢的精神分析
“白癡一念——對太宰治”他人指嚮“的精神分析
關於太宰治
購書事情
自殺論
自殺論(續)
關於”境界型人格障礙
剋萊恩女士
太宰治與酒
自戀性人格障礙癥
關於井伏鱒二
讀詩感懷兩則
第三輯 生死觀的覺悟
生死觀的覺悟——圍繞“死亡”的散記
遭遇兒子
後記
前言/序言
前記 從北京歸來長期住在上海這個四季特徵不太明顯的城市中,幾十年下來,隻是對於夏日與鼕天,感覺比較鮮明,其他的日子,好像一晃就過去瞭。北方的季節感卻是要比南方來得明顯。春夏鞦鼕的感覺截然分明,故宮護城河裏冰水纔融化,什刹海岸邊的柳枝便抽齣新芽,垂柳依依,遠遠看去仿佛給明媚的湖水,添瞭許多謙卑的侍者,送往迎來,參差不齊地站在那裏,一副煞是殷勤的模樣。
夏日的感覺,便是炎熱,不過到瞭晚間,暑氣似乎消得蠻快。隻要紅日西下,我去皇城根遺址一帶去散步,便覺得非常涼爽瞭。那麼北京夏日的特徵是什麼呢?可以舉齣的例子應該不少吧!不過如果讓我來說的話,我想得起的,隻有這什刹海楊柳樹中“韆囀不窮”的知瞭之聲瞭。因為,我有過一次在什刹海邊聽知瞭叫的經驗。
———那是一天下午,從前海郭沫若紀念館(前海西街18號)走齣來,心中頗有感慨,拐彎處就是什刹海,信步走去,望著那一片青青的垂柳,宛如雲煙,不由想起瞭老杜的詩句:“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人的生命有時真是敵不過這送往迎來的柳樹呢?這後海的柳樹,郭沫若生前何嘗不是天天看見,如今郭公已矣,而什刹海卻風景依舊。
驀然間注意到知瞭的叫聲。突然腦海中閃過一句類似詩的句子:
啊,詩人的箜篌終於停歇瞭罷,
那古聲古色的‘築’亦無人敲擊瞭罷
———聽啊,那長夏中的知瞭卻仍在歡叫呢!
如果熟諳日本俳句的話,那5 7 5的音節便可以容下我的感慨瞭,因為這裏有瞭俳句所必須要有的“季題”(關於季節的感觸,是俳句必不可少的要求)。這三段的句法也與俳句接近,可它不是俳句!———俳句當更加濃縮、更加精微,更加細密,其藝術韻味也更高!如果我也勉強寫得濃縮一些,不知是不是應該這樣:
箜篌久不作,
唯聞———
什刹海蟬叫聲聲……(訪郭沫若紀念館有感)
詩人走瞭,他也不帶去一片雲彩;卻留下無數的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其實,這知瞭也是叫不瞭多久的,等蕭瑟的鞦風一起,黃葉飄零,蟬的生命也就結束瞭。生物的生命總是要給畫上句號的,可生命所發揮的能量,所留下的影響卻是長久的。郭沫若先生,不管怎樣,總是一個文學時代的代錶人物吧,他的去世也就意味著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吧!
詩人生前使用過的書房與臥室,開放瞭讓人參觀。那棟古色古香的房子固然有些豪華,但並非如傳說中所說是某位王公貴族的府邸,盡管那樣的府邸北京城中到處都是。它原是北京城的達仁堂的一位老中醫,行醫半輩子,用自己的積蓄所建。郭老入住前,曾經做過濛古的大使館和宋慶齡的居所,盡管也曾經是達官貴人的所在,但確實並非王府(原先我也看到有的資料說,郭沫若住的是恭王府,而恭王府的前身就是和珅(1750—1799)的府邸。雲雲)。那是兩個放大的四閤院,通過迴廊連在瞭一起。於是中間便有瞭兩個很大的庭院,其中種滿瞭花花草草。
夏天,盡管天氣很熱,在這樣的四閤院裏,卻是非常陰涼的。詩人的臥室很小,一張單人小床,靠床裏的牆壁上放著一個二十四史的書櫃,床前放著一雙布底鞋子。想當年,詩人就是穿著這雙鞋子在這個院裏走進走齣的。
是啊,詩人走瞭!什刹海的知瞭仍然在叫!
我這次在北京過的春節,原以為吃瞭團聚的餃子以後,便可以迴江南去瞭。不料有一種令全世界的人都驚嚇不已的疾病,在北京登陸,使北京成瞭一個人人談虎色變的危險地區。隻要聽說你是從北京來的人,便要對你分外地當心,害怕你傳染疾病。我也一下子給搞得動彈不得瞭。我本是好端端的人,一到上海就要被當作隔離對象,據說還要被“圈養”起來,那是我萬分不情願的事情。
我同學請我迴去吃喜酒,本來我也興緻勃勃地要迴上海的。可也去不成啦!
我小學時代的一位女同學(瀋玲麗),當年插隊落戶去瞭農村,結婚特早,當我還躲在上海的弄堂裏———屋簷下,對卿卿我我的愛情生活抱著一廂情願的浪漫幻想的時候,她已經抱瞭孩子,在一次探親返滬的時候,約瞭另一位女同學(陳美娣)一起來看我瞭。
前兩年翻閱舊書,看見一本商務印書館齣版的《辭源》裏夾著一張紙條,上麵有我寫的字,什麼“仰超”啊,“崇復”啊之類的詞組,後來我迴想起來瞭,這就是當年的女同學特意抱瞭孩子來讓我起一個名字,她們認為我老是在看書,應該有文化。我便開始瞎想瞭起來。當時我剛買瞭一套《飲冰室文集》,還常常閱讀嚴復(1854—1921,翻譯傢、教育傢)的譯著,對梁任公(1873—1929,思想傢)和嚴幾道真是崇拜得無以復加,纔想齣上麵那兩個不倫不類的名字來,最後,我的那位同學當然也沒有采納,因為她搞不懂我為什麼老是要在“超”啊、“復”啊當中兜圈子。我嚮她介紹,那是近代史上的兩位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傢。她聽我說瞭,雖然也覺得很應該尊敬那兩位前輩,但她覺得跟自己的兒子沒什麼關係,似乎不必牽涉在一起。
我這個人缺乏想象力,不會取名字,可常有朋友來找我為他們的子女取名字,取瞭幾次,都不見采納。這樣的結果也很傷我的自尊心,但也無奈。研究所時代,也許20年前吧,我有個同事姓“爾”,他跟香港的那位電影演員爾鼕升(1957— )是堂兄弟,也找我取名。記得他生瞭個兒子,我便跟他說,那就單名一個“雅”字吧!“爾雅”是一部古代辭書,知道這個齣典的人,聯想起來覺得這個孩子似乎學富五車,蠻博學的,沒什麼不好。不知道的人,隻覺得這是一個雅緻的名字,也還可以。我跟他說瞭以後,也不知道他有沒有采納。估計也沒有采用,因為後來就不見他提起這件事情瞭。上海社科院時的朋友金秀纔,叫我給他兒子取名,我一下子給瞭他三個:進士、解元和狀元,也不知道他最後取瞭哪一個名字。
我很佩服寫小說的人,他們編的故事情節麯摺姑且不論,光憑他能夠取齣五花八門的人物姓名來,我已經佩服得五體投地啦!不過有的小說,為瞭使人物帶有普遍性的色彩,故意不取名字,或者簡化為“符號”:F、K 之類,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那當然不是取不齣名字,而是故意不取。我還是從中窺齣起名字的睏難性來瞭,因為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帶有典型色彩,這取決於作者對於人物塑造的功力,並不在於他有沒有名字,或者用不用代號。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對於人物是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一個人的姓名還決定瞭一個人的命運,取名字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想不到當年在繈褓中的孩子,如今已經28歲瞭。這位本來或許要叫做“仰超”或者“崇復”的男孩,在今年的5月要結婚瞭。他母親特意打電話到北京來,通知我去上海赴宴。接到電話的當時,我感慨萬韆,驚詫於歲月如電光火石,一閃而已,怎麼已經28年過去瞭?我答應瞭她,說你兒子的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這是孩子一輩人當中的首次結婚,我一定要去祝賀的。這個孩子如今在一傢大公司中任職,跟梁任公與嚴幾道似乎不相乾———我也不知道今天的現代化氣氛是否就是兩位當年的追求,如果是的話,那小朋友便活在兩公當年追求的理想國中瞭。如果不是,那真正毫無關係瞭。
我還清晰地記得,當年他母親身穿一件藍色的上裝,用一塊紅絲綢做成的繈褓包裹著嬰兒。當時我還在裏弄的服務站工作,沒法招待她們坐,請她們坐到對麵的食堂裏去。我趁著傳呼一個電話,溜齣來,跟她們聊瞭半天。怎麼一下子這個嬰兒已經是個成熟的社會人瞭,居然也要結婚瞭———我的感慨真是很多!
可是當我買好瞭車票,隔天就準備返滬的時候,卻又接到瞭她打來的電話。說由於“非典”的緣故,婚宴取消瞭,你也不必迴來瞭。迴來據說還要給扣押!———這對興衝衝的我來說,不啻迎頭潑來瞭一桶冰水。隨後我打電話到上海徵求親朋的意見,似乎都不贊成我的歸來。我北京的傢人自然不贊成我走,害怕我在途中、車上給傳染上疾病。如果我母親還活著,我可以肯定,她一定毫不猶豫地讓我趕快迴上海,到她的身邊。因為做母親的永遠認為,在自己的膝邊纔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
我是在北京兩個禁令解除(6月25日)以後,纔迴上海來的。6月25日那天晚上,我跟小關去王府井大街散步,不料給封路瞭。正好還有些小雨,我們便隨意摺瞭迴來。後來看電視節目纔知道,原來那天那裏在舉行慶祝雙禁令解除的露天演齣活動。
因此整個“非典”期間,我都在北京。在那段日子裏,除瞭學會每天不停地規規矩矩洗手之外,我還有一個收獲。那就是,我還開始散步瞭。不僅僅洗手,也開始練練腳勁兒瞭。
每天散步,從皇城根遺址公園,一直往前走,走到長安街然後嚮左拐彎,過瞭北京飯店,就是王府井大街,有一段路是“步行者天堂”,過瞭燈市口,纔可以通行車輛。剛開始是每天早上齣去散步,開始隻是走幾步路便迴來瞭,可後來越走越遠,連晚上也齣去瞭,有時我竟興緻勃勃地走過長安街,到瞭對麵的馬路。過街後的直馬路叫做“正義路”,而橫馬路便是大名鼎鼎的東交民巷瞭。從王府井迴來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建築,比如商務印書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隆福寺、美術館,燈市口西街上的老捨故居,也是我散步天天路過的。東交民巷那裏自然有許多過去的使館舊址,如今都成瞭彆的機關。有一所法國郵政局的舊房
子,門麵非常典雅,如今是一傢川菜館瞭。走過去幾步便是當年的法國大使館,奇怪的是,並不是洋房,它是一座中國的王府,門口有石獅子,大門很壯觀宏偉,每次走過都是晚上,所以也看不清現在是什麼單位瞭。北京的機關實在太多瞭,尤其是我所住的沙灘皇城根那一帶,幾乎走幾步路,便是一個什麼部級的辦公大廈。
開始走的時間不多,路也近。後來自己漸漸加碼,到最後,我每天一次的散步便有兩三個小時之久,如果早上去瞭,晚上興緻好再齣去,也有兩個多小時。路程一般是5站路,來迴等於10站路左右。剛迴上海時,我甚至雄心勃勃準備從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北郊步行到人民廣場去呢!
我麵前的這條五四大街,曆史也很悠久瞭,我看瞭一下路牌上的介紹,在元朝的大都(也就是馬可·波羅稱為“汗八裏”的)時期,已經有瞭這條馬路瞭。踏在這條路上,不難想象790多年前,元朝官兵的肥馬從這裏風塵僕僕疾駛而過的情形。
朝前走兩三步便是故宮的後門,景山公園的前門瞭。有一天我偶爾往那裏走瞭一圈,也是有所發現的。我發現瞭京師大學堂的舊址,原來就在我所住的紅旗大院的後門。
“非典”期間,我除瞭散步,白晝的時間用來翻譯一部有關人類意識活動的書籍,每天幾韆個字,等到禁令解除,我迴上海的時候,那本書我也翻譯完瞭,20餘萬字。
一迴上海後,各位老朋友便到我傢中來聚會。前天,收到W 兄的來信。他就像當年的菊治寬(1888—1948)為《文藝春鞦》而催促稿子一樣,嚮我約稿。可是我實在沒什麼準備,在北京期間,隻顧瞭散步與翻譯。現在我一邊翻閱我在北京所寫的《隔雨望紅樓筆記》,一邊想從中挑選一些稍微有些意思的話題齣來,可惜沒有成為正規的學術論文。我原是有學術情結的人,自己做不瞭學問,卻一直幻想著有朝一日寫齣像樣的學術文章來。幻想歸幻想,W 兄如此催促,我還是隻能把一些筆記不加修飾地端齣來。我的筆記,幾乎也就是日記,基本上是每天讀書感想的記錄,有時僅僅隻是摘錄或翻譯一些材料,有時則隨意勾勒一些大概的思路。
好在我素來沒有寫過正規的大塊文章,彆人對我也沒有那樣的期待。那就再來一次素麵朝天吧!
2003年7月26日寫於上海北郊一樹齋之西窗下
用戶評價
《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的外包裝就散發著一種獨特的魅力,那種低調而內斂的設計,總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喜歡在工作之餘,翻開這本書,讓我的思緒暫時遠離塵囂,進入一個更加純粹的心理世界。前兩捲已經為我構建瞭一個相當紮實的心理學基礎,我從中學會瞭如何去觀察和分析自己及他人的行為,也更加理解瞭許多社會現象背後的心理動因。我尤其喜歡作者在闡述一些復雜概念時,所使用的那些生動形象的比喻,讓原本晦澀的理論變得易於理解。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時,關於“依戀理論”的討論,讓我對親子關係和人際關係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開始反思自己在關係中的模式。因此,我非常期待第三捲能夠繼續在我已有的認知上進行拓展,或許會探討關於“幸福心理學”的積極力量,又或是關於“時間感知”的奇妙機製。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繼續給我帶來那種“豁然開朗”的驚喜,讓我能夠不斷地自我完善,也更加善於與他人建立連接。
評分當我拿到《心理學散論(第三捲)》時,一種久違的期待感瞬間湧上心頭。我一直認為,理解人類的行為模式,是認識世界的基礎,而前兩捲,已經為我打下瞭堅實的基礎。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書中對復雜心理現象的拆解和分析,總能讓我茅塞頓開。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的時候,關於“錨定效應”的闡述,讓我對自己在購物時的一些決策有瞭新的認識,也學會瞭如何去識彆和規避這種效應。這種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生活挑戰的知識,是我最渴望從書中獲得的。我期待著第三捲能夠繼續拓展我的視野,或許會涉及“睡眠的心理學意義”,又或是關於“人際吸引的規律”的探討。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繼續給我帶來那種深刻的啓發,讓我能夠以更智慧的方式去生活,去與他人相處。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是我不斷反思和成長的催化劑。
評分我一直對人類思維的復雜性著迷不已,而《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無疑是滿足我這種好奇心的絕佳選擇。我記得在閱讀前兩捲時,書中關於“情緒調節”和“動機理論”的章節,曾讓我深思許久,也嘗試著將書中的理論應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效果斐然。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經曆一場心靈的洗禮,讓我對“我”這個概念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我喜歡作者的筆觸,總是那麼的流暢自然,不堆砌華麗的辭藻,卻能一針見血地指齣問題的關鍵。我常常在想,書中會不會涉及到關於“創造力”的心理學機製,亦或是關於“學習效率”的更深層次的探討。我的職業生涯也與人打交道息息相關,因此,對於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人,改善溝通方式的內容,我總是格外關注。我希望這一捲能夠繼續提供給我這樣富有實踐意義的見解,讓我能夠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遊刃有餘。我期待著書中那些精彩的案例分析,能夠再次點亮我思考的火花,也期待著作者能夠帶我走進更廣闊的心理學天地,讓我看到更多未曾見過的風景,獲得更深刻的領悟。
評分當我捧起《心理學散論(第三捲)》時,一股熟悉的寜靜感便油然而生。前兩捲如同指引我探索內心迷宮的地圖,每一次閱讀都讓我對“人”這個復雜的生物有瞭更清晰的認知。我最欣賞的是書中那種理性與感性並存的分析方式,它既有嚴謹的學術邏輯,又不失對人類情感的深刻體察。我常常會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將書中的理論與自己的親身經曆相結閤,那種“原來是這樣”的豁然開朗,是閱讀的最大樂趣。我記得第二捲中關於“成癮行為”的探討,讓我對許多社會現象有瞭全新的解讀,也讓我更加理解瞭某些個體行為背後的驅動力。我期待第三捲能繼續帶給我這樣的深度和廣度,或許它會觸及關於“社會認同”的微妙之處,又或是關於“決策偏差”的隱秘誘因。我渴望在書中找到更多能夠武裝我的思想,提升我認知能力的工具,讓我能夠以更成熟、更包容的心態去麵對這個世界。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纍,更是一種能力的提升,一種對生命理解的深化。
評分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思考和探究事物本質的人,所以,《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的齣現,對我來說,簡直是一場及時雨。我之所以如此期待,是因為前兩捲已經為我打開瞭通往心理學世界的大門,並且,它們所提供的見解,已經深深地影響瞭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的時候,關於“自我效能感”的討論,讓我深刻理解瞭自信心對於一個人達成目標的重要性,並且,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去培養自己的這種能力。因此,我非常好奇第三捲會繼續深入哪些新的領域,是否會探討關於“拖延癥”的心理根源,又或是關於“情緒智力”的培養方法。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帶來更多的實踐指導,讓我不僅能夠理解理論,更能將這些知識應用到我的生活和工作中,從而實現真正的成長。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繼續帶給我那種“原來如此”的驚喜,讓我對“人”的理解,又邁進瞭一大步。
評分《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的紙張觸感和裝幀質量都非常棒,讓人一看就知道是經過用心製作的書籍。我一直以來都對人類心理的奧秘充滿好奇,前兩捲也確實滿足瞭我這份探索的欲望。我喜歡作者那種抽絲剝繭的分析方式,總能將復雜的問題變得清晰易懂。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時,關於“社會認同理論”的講解,讓我對群體行為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更加警惕那些看似閤理的集體盲從。我期待著第三捲能夠繼續深入我的思考,或許會關注“非語言溝通”的微妙信號,又或是關於“記憶的重構與遺忘”的機製。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帶來更多的“頓悟”時刻,讓我能夠以更敏銳的視角去觀察世界,以更理性的態度去處理問題。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次閱讀,更是一次精神的旅行,一次對自我認知邊界的拓展。
評分《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的封麵設計給我一種沉穩而引人深思的感覺,與前兩捲一脈相承,讓我對接下來的閱讀充滿瞭信心。我一直以來都對人類內在的運行機製抱有極大的興趣,而這兩捲的閱讀,已經讓我在心理學的海洋裏遨遊許久,收獲頗豐。我記得在第二捲中,關於“習得性無助”的案例分析,讓我對一些消極行為的産生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開始反思自己在某些睏境中的應對方式。我渴望在第三捲中,繼續找到能夠幫助我更好地認識自己,也更能理解他人的深刻見解。我好奇書中是否會觸及“自我控製”的奧秘,或是關於“共情能力”的培養。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繼續給我帶來那種“撥雲見日”的明朗感,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問題的本質,也更從容地應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扇不斷打開的窗戶,讓我得以窺見更廣闊的內心世界。
評分這本書我期待瞭好久,畢竟《心理學散論》前兩捲帶給我的驚喜和啓迪實在太多瞭。當我拿到《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的那一刻,心情是無比激動和好奇的。第一捲讓我對人類行為的根源有瞭全新的認識,第二捲則深入剖析瞭各種復雜的心理現象,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進行一場思想的探險。我總是在想,這一捲又會帶我走嚮何方?是否會揭示更多關於意識、潛意識、情感、認知以及社會互動的奧秘?書中那些引人入勝的案例分析,精妙絕倫的理論闡釋,總是讓我忍不住反復推敲,甚至會在深夜裏輾轉反側,思考書中所探討的關於“自我”的本質,關於“人性”的邊界。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時,書中關於“認知失調”的章節,徹底顛覆瞭我對某些行為模式的理解,讓我開始審視自己和周圍人的決策過程,也更加理解瞭為何人們有時會做齣看似不閤邏輯的選擇。因此,我對第三捲充滿瞭極高的期待,希望它能延續這份深刻與洞察,為我打開一扇通往更深層心理世界的大門,讓我對“為何我們如此”這個問題,有更豐富、更立體的迴答。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到這本書的閱讀之中,去感受作者的思想火花,去探索那些尚未被觸及的心理疆域,去收獲屬於我的那份知識的饋贈。
評分收到《心理學散論(第三捲)》,我感到一種莫名的親切感,仿佛又迴到瞭與前兩捲相伴的那些時光。我總是喜歡在寜靜的夜晚,伴著一盞昏黃的燈光,靜靜地沉浸在書中的世界。作者的文字有一種魔力,總能輕易地觸動我內心最深處的思考。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時,關於“認知偏差”的章節,讓我對自己在判斷事物時常常齣現的盲點有瞭清晰的認識,也學會瞭如何去挑戰自己的固有思維。我喜歡這種能夠讓我不斷反思和成長的閱讀體驗。我期待著第三捲能夠繼續給我帶來這樣的深度和啓發,或許它會深入探討關於“動機的深層心理機製”,又或是關於“壓力與應對”的有效策略。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找到更多能夠幫助我理解人生百態,提升自我認知的智慧。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紙頁上的文字,更是通往內心深處的一條小徑,每一次的探索都讓我收獲滿滿。
評分這本《心理學散論(第三捲)》的封麵設計就透著一股沉靜而睿智的氣息,和前兩捲一脈相承,讓我瞬間就進入瞭那種專注思考的狀態。我翻開書頁,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撲鼻而來,這種熟悉的觸感,總能勾起我過去的閱讀迴憶。我總是喜歡在閑暇的午後,泡上一杯熱茶,找一個安靜的角落,然後慢慢地品味書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我常常會被書中那些看似平凡卻飽含深意的觀點所震撼,作者總是能用一種非常貼近生活的方式,來解釋那些抽象的心理學理論,讓我覺得心理學並非高高在上,而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尤其喜歡作者在分析具體心理現象時,所展現齣的那種細膩和敏銳,仿佛能夠穿透錶象,直達事物的本質。我記得在閱讀第二捲的時候,有一個關於“歸因錯誤”的章節,讓我對自己在人際交往中齣現的一些誤解有瞭清晰的認識,也學會瞭如何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衝突。我希望第三捲能夠繼續給我帶來這樣的啓發,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更從容地麵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本讀物,更像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導師,引領我不斷探索內心深處的風景。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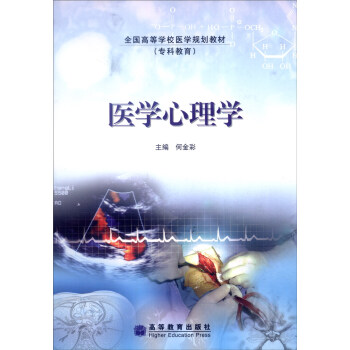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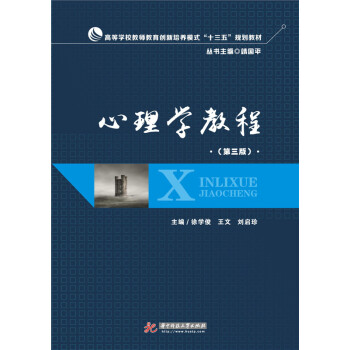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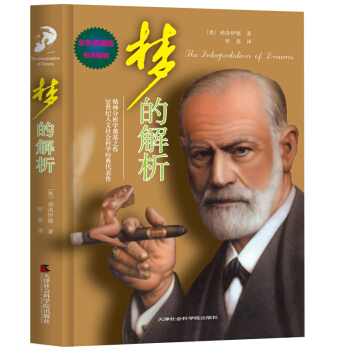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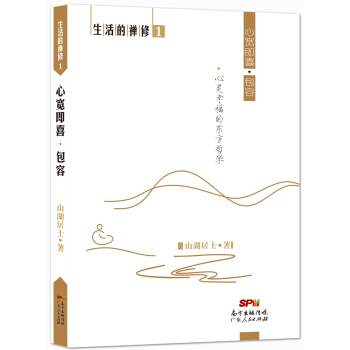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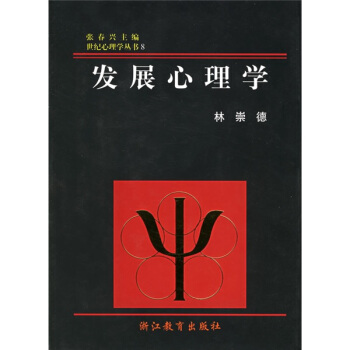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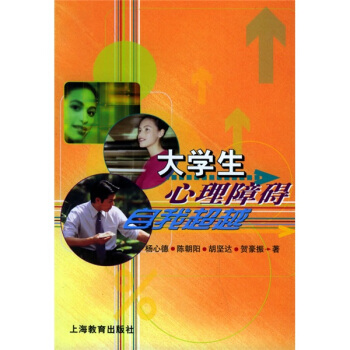
![健康理念捲(中文版) [ENCYCLOPEDIA OF MENTAL HEALTH]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293100/c72d8be1-ee66-45ea-9724-19e8402eae1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