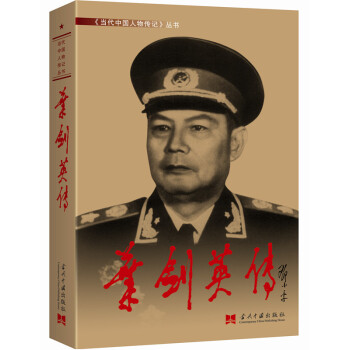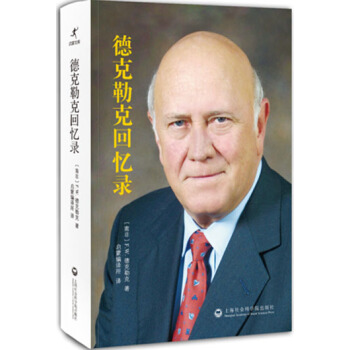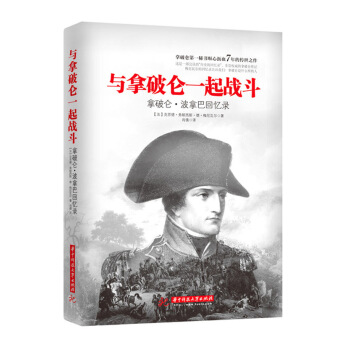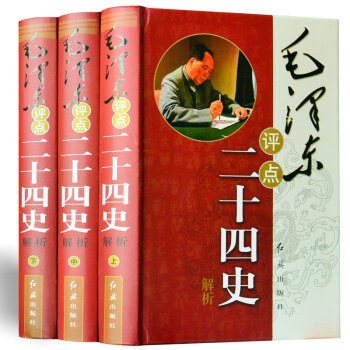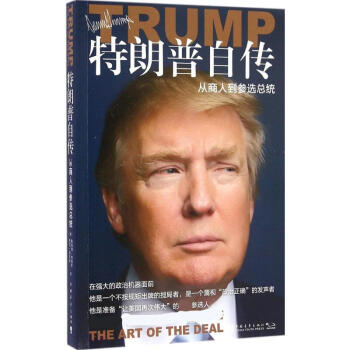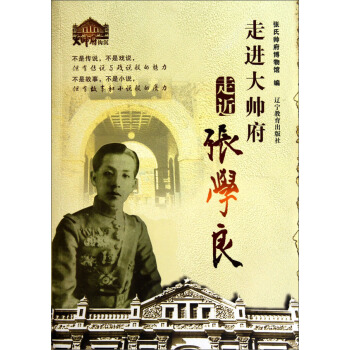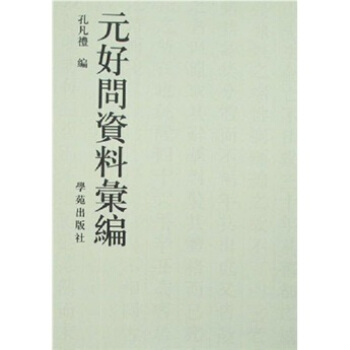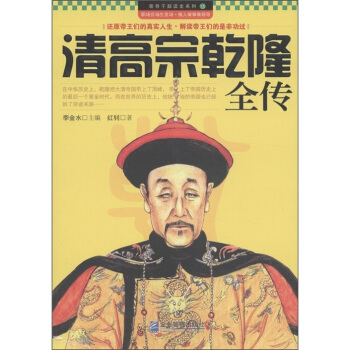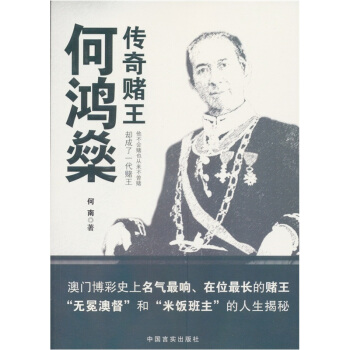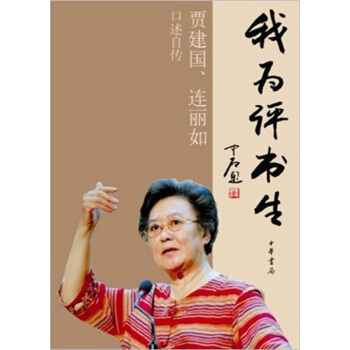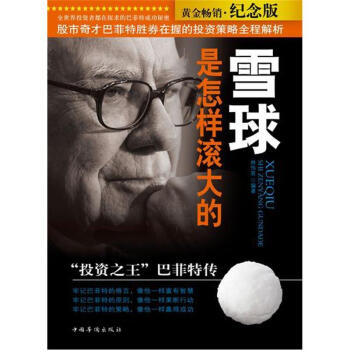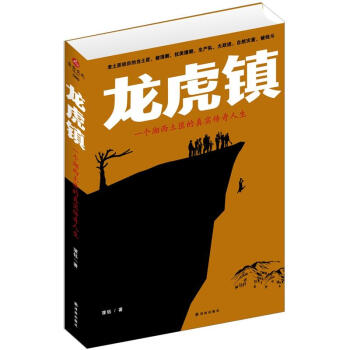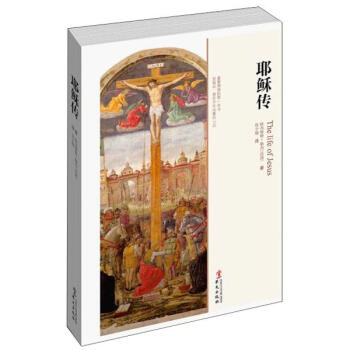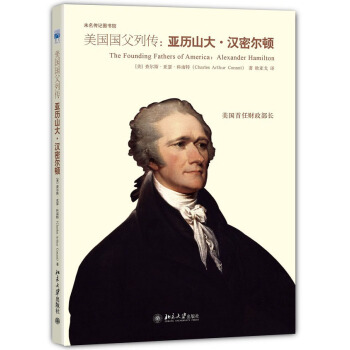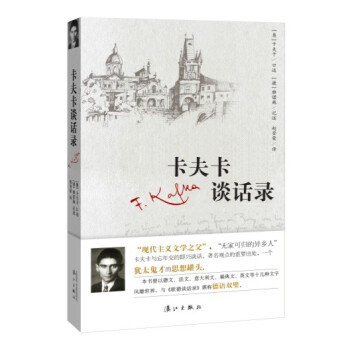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外国文学、卡夫卡粉丝谈话的即兴式和交流的无拘束,决定了该书"思想罐头"似的什锦面貌和浓缩程度,为卡夫卡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和佐证,并成为人们现在引用卡夫卡一些著名观点的重要出处。
内容简介
《卡夫卡谈话录》是由卡夫卡的忘年交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即兴谈话录,雅诺施比卡夫卡小二十岁,是其同事的儿子,经常去卡氏就职的布拉格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探访他。卡夫卡作为“相当富有的父母的儿子”和公司法律处处长,一辈子生活在威压当中,其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性格专横如暴君,对幸存的长子卡夫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大学时甚至逼其放弃酷爱的文学专业,改修法律,影响笼罩其一生。“富二代”的身不由己和小职员生涯的万般无奈,令表面的卡夫卡之下顽强生长着一个文学的卡夫卡。本书谈话发生的时间跨度,在1920年3月底雅诺施初次拜访卡夫卡和1922年7月初卡夫卡退休离开保险公司去疗养之间。两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工间休息见缝插针的聚谈,或是漫步在布拉格老城环形道的边走边聊,见证了晚年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
作者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奥地利德语小说家,犹太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生前比较寂寞,逝后才为世界所惊觉,从而赢得盛名。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古斯塔夫·雅诺施,1903年生于多瑙河支流德拉瓦河畔的马尔堡(1918年归南斯拉夫,南名为马里博尔,今属斯洛文尼亚,临近奥地利),在布拉格长大,先后在布拉格、埃尔博根和维也纳上大学。他创作轻音乐,著有以音乐和音乐家为题材的书籍多种,因而在家乡颇享盛名。二次大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1968年在布拉格逝世。
赵登荣,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资深翻译家,曾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副主任、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德语组组长等。主要译著有《井中男孩》、《荒原狼》、《保护网下》、《悲剧的诞生》、《致亲爱的母亲》、《海涅全集》第九卷、卡夫卡短篇小说等。
精彩书评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特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马克斯·博罗德
★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他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他,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他是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雅诺施
★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平原。我像一个球那样向安静滚去。这是一个弱点,有了这个弱点,一个人很容易失去镇静。
——弗兰茨·卡夫卡
目录
译本序 叶廷芳本书的历史(自序) 古斯塔夫·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
精彩书摘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l95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读者、报纸与广播电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诉讼》、《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兰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地、然而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忧郁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以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以外,对他的书籍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的笨重难看的暖气上放着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我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到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漩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
前言/序言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日常的言论由别人记录成书而成为名著者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准。但在提及这类书籍的时候,其中有一本大概谁都不会忽略的,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诗中圣哲”,他的言论被人们视为至理名言是不难理解的。但无独有偶,同属于德语文学的另一部谈话录,即由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谈话录”三十多年来正随着谈话者的名字蜚声国际文坛,而且在《歌德谈话录》新译本(选编)在我国出版仅仅十三年之后的今天,其首译本也已在我国问世。如同《歌德谈话录》体现着作者在“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晚年,亦即在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智慧的结晶一样,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也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纵览”了一遍世界,即思考了一辈子人生真谛后的产物,全面反映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或思想火花,人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一些卡夫卡的著名观点,都出自这部书。可以说,如果没有卡夫卡的这部“谈话录”,则尽管有他那许多半自传性的长短篇小说和大量书信、日记,他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就不如现在这样全面而丰富。因此这部书的诞生和存在进一步加强着人们对德语作家的这一印象:作家兼哲人的品格。或许有人会问:在谈论卡夫卡“谈话录”的时候,难道有必要与《歌德谈话录》相联系吗?难道前者的重要性堪与后者相提并论吗?这样的疑问如果出自一个对卡夫卡还不甚了解的读者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对卡夫卡是有所了解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要义有所领悟的,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性的回答。诚然,卡夫卡的年寿只有歌德的一半,而且作为业余作家,就知识之渊博、产品之丰富而言,他确实是与歌德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凡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作家存在的特殊价值,主要的并不取决于其知识积累的程度和作品的多寡,而取决于他对时代的独特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看他对他的时代的某种潜精神的洞见,并通过文学手段对之作了预言性的、启示性的表达。无疑,歌德作为德国古典文学鼎盛时期的代表,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属于他的时代,而且也是开启未来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吸取不尽他那丰富文学遗产中的艺术养料。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于是,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一跃而为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并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从而获得了传奇性的色彩,成为20世纪国际文坛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有人甚至认为,“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堪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如果说,这些评价不过是些专家、学者的看法,那么,1985年西欧五个文学大国英、法、德、意、西的诸家重要报纸联合举办的“已故十大欧洲作家”评选的结果,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看法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根据那次评选揭晓的名单看,卡夫卡被排在“十大”的第五位:名列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下,而在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莫里哀、乔伊斯、狄更斯之上。当然,有时候时代是会错爱一个人的,那么,就由历史去作最后结论吧。但在历史作出最后结论以前,我们把两者作这样的比较,该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在我们把德语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师相联系的时候,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卡夫卡作为以“反传统”出名的“现代派之父”,他不仅不反歌德这位最重要的德国古典作家,相反,他是歌德的最热烈的崇拜者。在他大量的书信、日记中,被提及得最多的是歌德,在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一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卡夫卡之所以推崇歌德,主要认为歌德的作品有一种“持久性的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卡夫卡崇拜歌德并不是表现在把歌德单纯当作偶像加以顶礼膜拜,而是把歌德的杰出之处例如艺术的“持久性”切切实实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了,无怪乎他那些生前并未激起普遍反响的作品具有那么大的“后劲”,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广大的地域。这一事实说明,卡夫卡是歌德艺术遗产的最好的继承者。但歌德的艺术之所以具有“持久性”,关键性的一点是强调自己的创造。对于这一艺术要旨卡夫卡也牢牢把握住了。在1912年2月8日的日记里,他单独记下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我对创造的兴趣是无止境的。”显然,卡夫卡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其说停留在被动的接受上,毋宁说表现在对它的精神的把握。如果说,卡夫卡不跳出前人的雷池,根据自己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心当代人的根本命运,并善于相应地捕捉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那么,他的作品是不可能打动今天的读者的心灵的。可见,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创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懂得依样画葫芦地继承前人、仿效别人的作家是不会有前途的。卡夫卡在这方面与歌德是一脉相通的。
用户评价
坦白说,初次接触这本书时,我并没有抱有太大的期待。我只是抱着一种“随便看看”的心态。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被书中那种独特的氛围所吸引。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发现,作者的文字非常擅长捕捉那些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中的复杂情绪。我常常在阅读时,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共鸣,仿佛书中描绘的正是我的内心世界。这种感觉非常奇妙,既有被理解的欣慰,又有被揭示的些许不安。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那些我曾经忽略的、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发现,在作者的笔下,那些平凡的生活场景,都充满了哲思的意味。我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开始主动地思考,主动地去寻找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就像一位沉默的朋友,它不会强迫你去做什么,但它会用一种极其温柔而有力的方式,引导你去发现自己内心的声音。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相当独特,更像是一系列不期而遇的片段,却又恰到好处地串联起了某种内在的逻辑。我常常在阅读某个段落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啊,原来是这样”的顿悟感,又或者是一种“我怎么从未想过”的惊奇。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鲜明,既有诗歌般的凝练,又有散文般的自由。这种语言的魅力,让我沉醉其中,甚至会在读完一个句子后,反复回味其背后的深意。我发现,我不再是以往那种以情节为导向的读者,而是更注重文字本身所传递的情感和思想。我开始关注那些细微之处,那些被他人轻易忽略的细节,因为我知道,它们往往蕴含着最深刻的智慧。这本书也让我对“沟通”这个词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换,更是一种心与心的碰撞,一种思想的交流。我开始反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交流方式,试图去理解那些隐藏在言语之下的真实意图。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让我看到了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刻联系。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而富有质感,淡雅的色调和考究的字体,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目光。翻开扉页,一股淡淡的书香扑鼻而来,仿佛能嗅到纸张本身承载的岁月痕迹。迫不及待地进入正文,我发现自己被带入了一个充满思想碰撞与灵魂审视的奇妙空间。作者的文字如同一泓清泉,时而潺潺流淌,时而激荡澎湃,每一次阅读都像是与自己内心的深处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那些看似零散的片段,却在不经意间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思想网,将我牢牢地网住。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种种,那些被遗忘的梦想,那些被压抑的情感,那些在生活洪流中渐渐模糊的自我认知,都在这本书的引领下,重新浮现,清晰而深刻。每一个字句都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仿佛是作者在黑暗中点燃的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也让我更加理解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我常常会在某个章节停下来,久久地凝视着,让那些文字在脑海中反复回荡,试图从中汲取更多的力量和智慧。这本书不是那种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快餐读物,它更像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老酒,每一次打开,都能品尝出新的滋味,获得新的感悟。
评分我承认,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它所探讨的主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只是被封面上那种难以言喻的氛围所吸引,一种掺杂着忧郁、迷茫,却又透露出某种坚韧不拔的力量。阅读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灵魂跋涉。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或者说,它提供的答案本身就充满了疑问。我常常被那些句子所困扰,它们如同一个个迷宫,引导着我不断地探索,却又不愿意轻易地走出。有时候,我会因为理解上的困难而感到挫败,甚至想要合上书本,回到那个更熟悉、更舒适的认知世界。但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牵引力,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拾起。我开始明白,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所激起的困惑和不安。它迫使我去质疑那些我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去审视那些被我忽视的角落。我发现,在不断的挣扎与反思中,我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我的视角也更加开阔。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也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评分初拿到这本书时,就被它略显沉重的封面以及扉页上那一串串我尚不熟悉但充满韵味的文字所吸引。随着指尖划过纸张,我感觉自己仿佛踏入了一片未知的领域,一种莫名的期待感油然而生。我并非一个对文学理论有着深入研究的读者,更多时候,我只是沉浸在故事本身带来的情绪波动和思考之中。然而,这本书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我拉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它没有戏剧性的情节,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有的只是如同涓涓细流般的叙述,却蕴含着令人震撼的力量。作者巧妙地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让我能够触摸到那些曾经只存在于脑海深处的想法。我发现,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参与到思考的构建中。那些语句,有时像是一记重拳,击中了我内心柔软的角落;有时又如同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抚慰着我疲惫的灵魂。我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我所处的社会,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现象,在经过作者的笔触描绘后,竟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仿佛世界在我眼前重新被解构,又被以一种更深刻、更真实的姿态重塑。
评分……
评分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评分前言/序言
评分附录
评分我写的书都与你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你的面无法倾诉的话。
评分猫
评分但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钱锺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评分“我是不是打搅您了?”
评分目录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