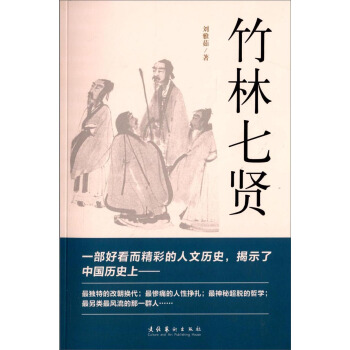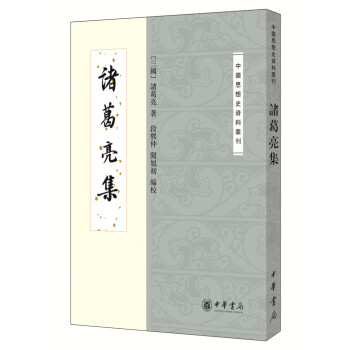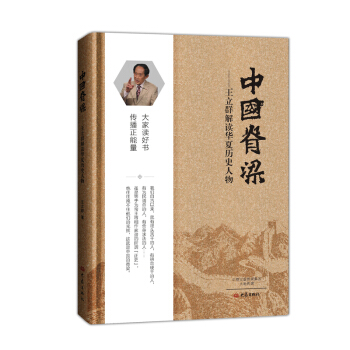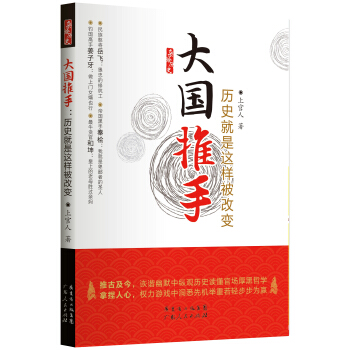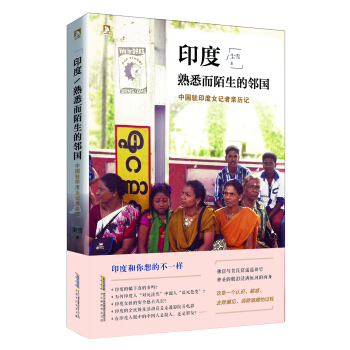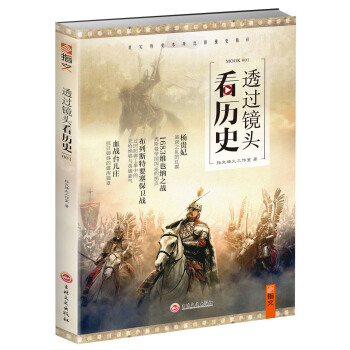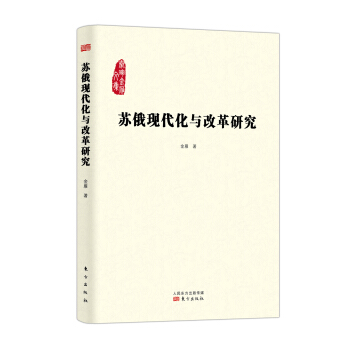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人这个怪圈呢?
作者简介
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
目录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再版序
自序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集体化前“富农”的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
农村“分化”的性质与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政策
20年代苏联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
农村分化统计研究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
“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粮食危机与“富农”问题
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1928-1929年问对富农的政策
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富农标准的下降与“富农”队伍的扩大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消灭富农”与全盘集体化
“消灭富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19世纪俄国的“离土不离乡”: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
“公社世界”的危机与身份壁垒
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
身份制的废除与“离土不离乡”的消失
从奇吉林到鲁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近代史的“怪圈”
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鲁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鲁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斯托雷平改革与村社复兴运动
“分家”:瓦解“公社世界”
改革的原则与特点
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改革走向反动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1905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的双输之局
“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路标”改变之后: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传统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公社世界”
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斯托雷平奇迹”的甜头与苦果
“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1917年革命还是“十月革命”
政治风云与苏联地名学
俄国地名政治性更改的传统
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四次地名更改风潮
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精彩书摘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按照通常说法,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农村中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富矛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盘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发生的“过火”、“冒进”之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错误。但已有学者指出,消灭剥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这场运动的真正思想动因。据查,在“大转变”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原则性地讲到集体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讲的都是集体农庄能够大量提供廉价“商品粮”,而这是国家不可能从小农那里弄到的。实际上,“集体化—消灭富农”运动正是在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从小农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强购廉价粮而遭到消极抵制之后才发动的,它的“原始积累”性质显然比一般的乌托邦狂要实在得多。
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在坚持俄国的公社制度方面,极左与极右离奇地结合起来”。最“革命”的民粹派与最反动的“警察”都在大力鼓吹集体主义、米尔精神、公社制和“共耕制”,极力抵制“个人主义”与自由财产,都力图维护俄罗斯“国粹”而反对“西方瘟疫”,并且为实现这一切又都寄希望于农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怪圈。
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从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到对理论、制度模式的反省。而对于中苏等国来说(与因苏军占领而“输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不同),追溯旧模式的社会—文化根源,对旧模式中反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称为反思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这一阶段在我国已全面展开,在苏联自1987年起也已为少数思想敏锐者所提出。但背着“发达的超级强国”包袱、国内民族问题又十分尖锐的苏联,进行这种反思显然比已在民族危机中挣扎了100多年的中国更困难。西方学者对此虽然注意较早,但出于反社会主义偏见,往往简单地把“斯大林现象”与历史上的沙皇专制作类比,因而也难以科学地看待这一问题。
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1906年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最终使沙俄与改革均被葬送,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间把“路标”转向“保守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成为这一转向的牺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初次翻开这本书,立刻被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所吸引。作者在叙述早期的工业化进程时,并没有采取那种宏大叙事的视角,而是深入到具体的工厂车间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切片中去,让人仿佛能亲耳听到蒸汽机的轰鸣和工人们的交谈。他对农业集体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尤其独到,没有简单地将之定性为成功或失败,而是细致地剖析了其间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不同社会阶层所承受的代价。书中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探讨,也展现了作者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各种图表和模型的使用恰到好处,既不显得晦涩难懂,又能清晰地揭示出体制固有的张力。特别是关于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那几章,提供了许多未曾被主流历史叙事充分强调的细节,让人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工程师群体的挣扎与抱负有了更立体的认识。整体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极为老练,逻辑链条严密,读起来酣畅淋漓,仿佛与历史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远超一般历史读物的水准。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像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和意想不到的转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张力时的那种冷静和克制。例如,书中对赫鲁晓夫时期“解冻”现象的描述,没有落入简单的赞美或批判的窠臼,而是深入挖掘了文化松动背后潜藏的权力博弈和思想解放的脆弱性。作者运用了大量来自不同档案的原始材料,使得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中关于官僚体系内部派系斗争的细致描摹,简直可以媲妆于一部精妙的政治小说,将那些看似抽象的政策变动,还原成了鲜活的权力角力。读到后半部分,尤其是在探讨后期改革遇到的阻力时,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历史宿命般的悲凉感,作者的笔调也变得愈发凝重,但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审慎,没有预设任何结论,而是将判断权交还给了读者,这种开放性的叙事策略,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评分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那种近乎苛刻的求真精神。作者在论证每一个关键论点时,都展现出惊人的耐心,仿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被质疑的环节。我对书中关于技术官僚与意识形态卫道士之间微妙平衡的论述印象尤其深刻。作者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对科学人才的实际使用策略,揭示了实用主义如何在铁幕的缝隙中不断挤压教条主义的空间。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动态,是理解苏维埃模式长期运作的关键。此外,本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时,采用了跨时空比较的视角,将苏俄的实践与同期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了隐晦的对照,这种设置让读者在阅读具体历史事实的同时,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更广阔的思考。它不是在宣扬某个单一的真理,而是在提供一套结构严谨的分析工具,帮助读者理解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现代性实验的得失与教训。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叙事节奏的精妙控制。作者知道何时该加速,何时该慢下来细细品味。在描述重大历史转折点,比如重大战役后的社会动员或关键领导人更替时,行文如疾风骤雨,信息密度极高,让人应接不暇,仿佛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然而,在分析某一特定时期经济政策的微观执行细节时,笔锋又变得极其细腻和缓慢,每一个数据点、每一份会议纪要都被置于显微镜下审视。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布局,有效地避免了长篇历史论著容易出现的疲劳感。更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性把握得极其到位,使得苏俄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看起来不是一连串孤立的事件堆砌,而是一个有机体在不同压力下进行自我调整和演化的复杂过程,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体现了作者对整体历史观的深刻掌控。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其深意。它并非那种可以轻松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需要投入相当精力的严肃学术著作。作者在构建理论框架时,显然参考了大量的西方区域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模型,并尝试用这些工具来解析苏维埃特自身的特有肌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社会控制机制的分析,作者没有停留在政治清洗的表层,而是探讨了从教育系统、工会组织到文化宣传机构,如何构建起一套自我维持和强化的社会反馈回路,这种系统性的解剖,极具穿透力。书中对特定历史人物的心理侧写也极为精准,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的符号,而是有复杂动机和内在矛盾的个体,这使得历史事件的发生更具人性的合理性。总的来说,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叹服,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理论背景,但回报是更为深刻和多维度的认知升级。
评分商品很给力,快递也很给力,快递员都很好。一直在京东买书。
评分金雁老师的书,对中西历史都有深刻研究的专家,很值得一看。
评分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人这个怪圈呢?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评分秦晖先生的文集,好书,值得购买
评分书不错,打包垃圾,大黑手印子让人觉得很恶心!差评给打包-1颗星,物流-1颗星,售后专员邹亮亮-2颗星,最后评分1颗星
评分通过苏俄的历史历程,反思我们自己~秦先生的书,不错!
评分好。。。。。。。。。。。。。。。。。
评分东欧札记二种》为金雁老师早期经典作品《火凤凰与猫头鹰》《新饿乡纪程》合集,记录了一位历史学者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观察与评论。内容包括作者对东欧转轨的研究评述,多篇东欧政坛人物的评价以及东欧相关作品的解读等。正如作者所写,东欧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乐观者宣布“火凤凰已经在灰烬中新生并起飞了”。而悲观者则声称“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会飞”。到底是凤凰还是猫头鹰,作者通过长时段深入而细致观察,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但并非一个明确的结论。
评分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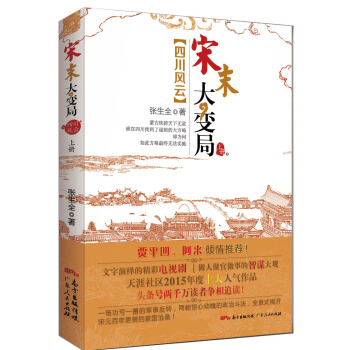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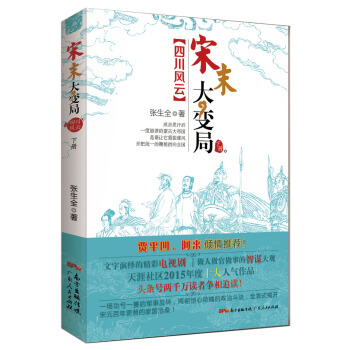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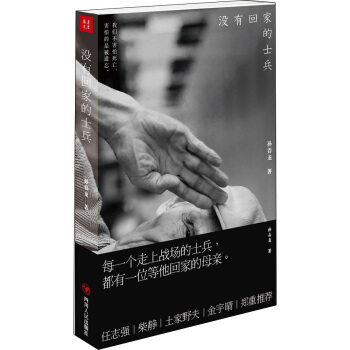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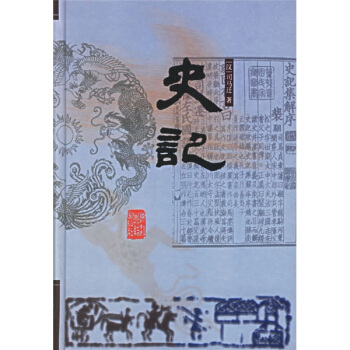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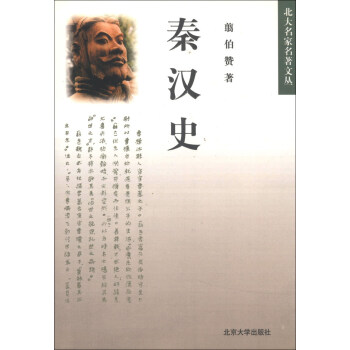
![老照片(第94辑) [Old Photo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5747/537c08f0Neadcc88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