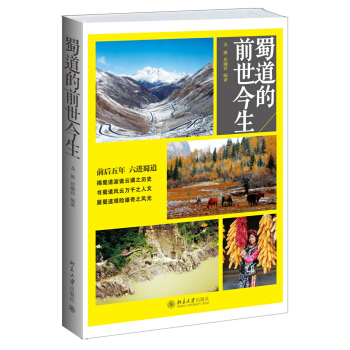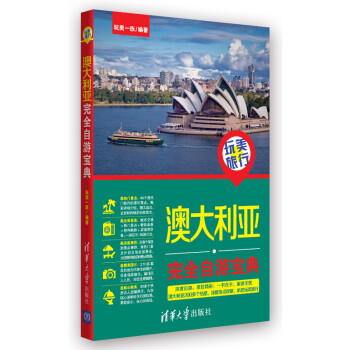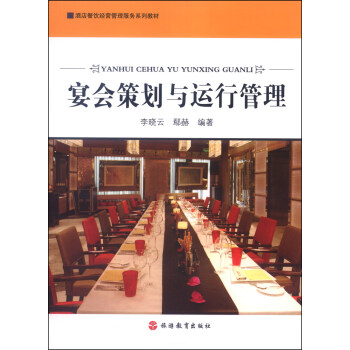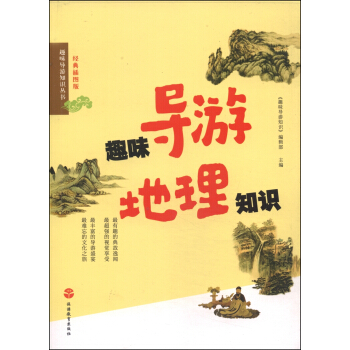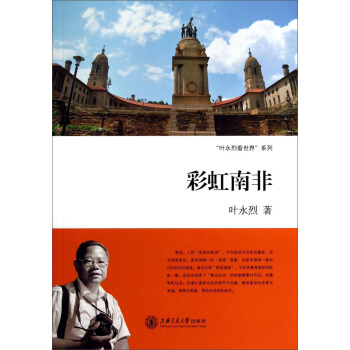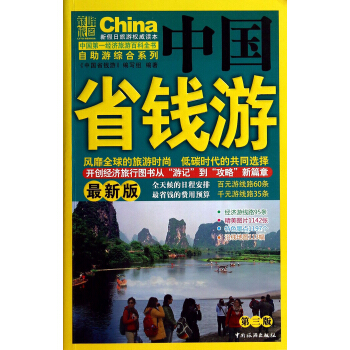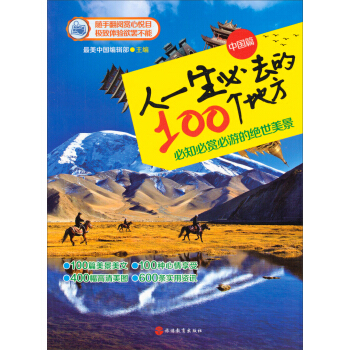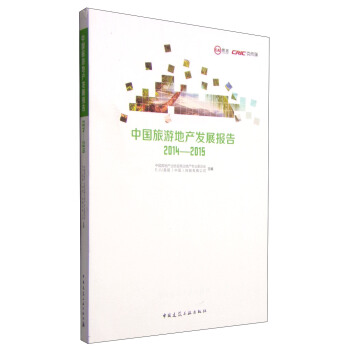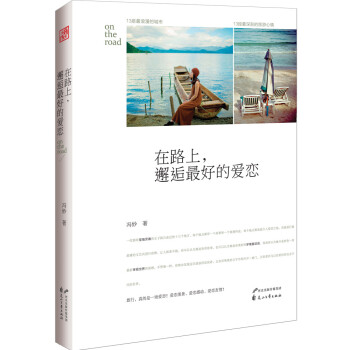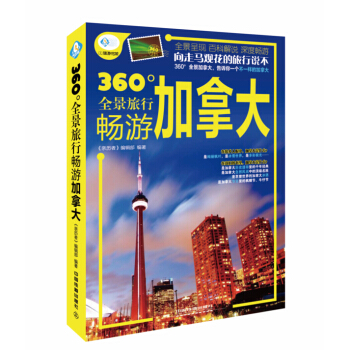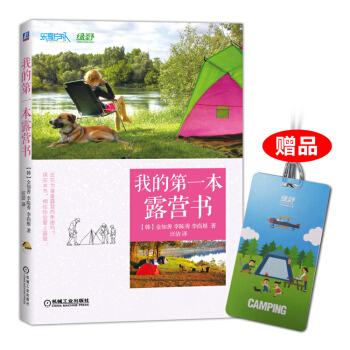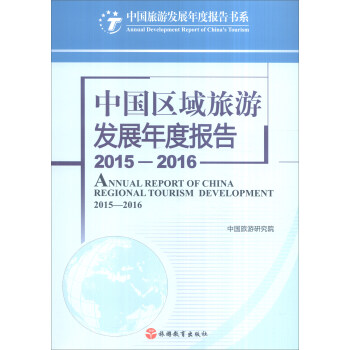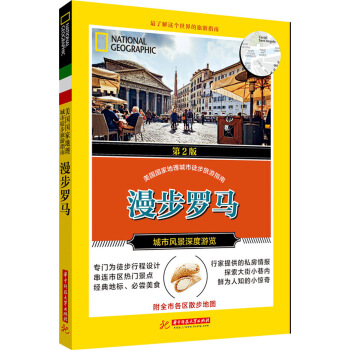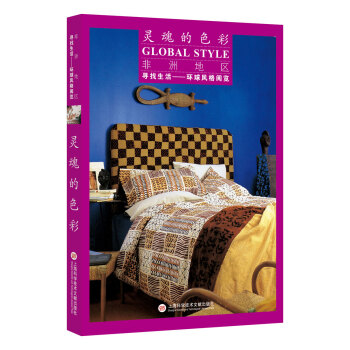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南美,一片神奇的土地。各人种在这里杂居,观念、风俗、想法突破人类的正常想象。这里有着热情绚烂的简单色彩,也有饱含历史感的厚重故事;激情的探戈舞曲时刻在奏鸣,神秘奇幻的印加传奇也将被持久传诵。一个规规矩矩的由国内流水线上出来的女孩怎样跌出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开始她的南美生活?内容简介
一个老女孩流连南美旅行和工作故事。她看到了美丽城市的傲慢与可爱,见识到了南部冻土的凛冽冰封,感知印加帝国的兴亡。三十岁的她依然流连于南美,一次又一次想碰触到生活本质的样子。她希望有一天,站在镜子前,跳一段舞给自己看;有一天,去完成全世界远的旅程,从一个人的心走到另一个人的心;有一天,对所有的人好,不害怕耗竭所有的感情。这是南美大地教给她的一切——聆听自己,顺应天命,做一个热情温暖的女人,不能被漠视的,是生命的意义。作者简介
王觉眠,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常年混迹京西,经常思考,容易喝高,是个常着球鞋T恤的素颜妞。南美工作三年,常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个充满法式石头建筑、热烈花儿和鲜艳涂鸦的城市里,开放出激烈的、喜悦的、伤心的、流着泪却还依然能仰头对着太阳微笑的情感。人生从此不同,着长裙短T外加墨镜,看到了加勒比人的直白和热烈,也学会了阿根廷骨子里的内敛和骄傲。自感人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开始穷游打混,嘴里哼着探戈老调,游遍南美,流连忘返。目录
喝咖啡摆龙门阵爱猫爱狗爱学问
足球是太阳
彩虹旗飘扬
我是“同志”我骄傲
总统吵翻天
他爱上的是大海和那个头发
乱糟糟的女人
梦游印加帝国
帅哥美女满街走的哥伦比亚
文艺女青年的经济基础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唤醒我内心深处的旅行欲望。每一次翻开,都像是一次新的探险。我被作者精妙的构思和流畅的叙事所吸引,仿佛置身于作者所描绘的那个迷人的国度。我期待着书中能够展现出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景致,那些富有历史感的建筑,以及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更令我期待的是,这本书能否通过文字,让我感受到那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我喜欢那些能够让我产生共鸣,让我思考人生意义的书籍,而我相信,这本书有潜力让我看到一些我从未曾想过的事物,并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去探索那些隐藏在未知之中的美好。
评分这绝对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度洗礼。我通常不太容易被一本新书完全征服,但这本书给了我截然不同的感受。它不是那种快餐式的阅读体验,而是需要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就像品一杯陈年的威士忌,越品越有味道。我有一种预感,这本书会用一种非常细腻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将我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期待着作者能为我呈现那些细腻的观察,那些触动人心的细节,比如清晨街角面包店飘出的香气,或者黄昏时分,老人们在公园里悠闲地聊天的场景。我相信,这本书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城市景色的描绘,更会深入挖掘那里的灵魂,那里的人文关怀,以及那些隐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深刻的情感。我喜欢那种能够引发我思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联的书籍,而我坚信,这本书一定会做到这一点。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些我们可能忽略的美好,也可能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
评分这本书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刚拿到手就被它厚实的封面和精美的排版吸引住了,感觉就像捧着一块沉甸甸的宝藏。我一直对那些充满历史韵味和艺术气息的城市充满向往,而这本书的名字,光是听着就有一种拉丁美洲的热情与浪漫扑面而来,仿佛能闻到那里独特的咖啡香和淡淡的探戈旋律。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页,就好像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程,准备去探索那些隐藏在巷弄深处的秘密,去感受那里的文化碰撞和生活气息。我猜想,这本书一定描绘了那里高耸的欧式建筑,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广场,还有那些热情洋溢的人们,他们如何在热情似火的阳光下,又如何在夜色中,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编织出这座城市的灵魂。我特别期待能读到关于那里的历史故事,关于那些塑造了这座城市面貌的时代变迁,以及那些隐藏在街头巷尾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本书就像一张地图,一张通往心灵深处的地图,我愿意跟随作者的笔触,一点一点地去解锁它所呈现的每一个角落,去体验那种久违的,来自异域的感动。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沉醉其中,久久不能忘怀的作品。它有一种奇特的魔力,能够将我从现实的喧嚣中抽离出来,带入一个全然不同的时空。我猜想,作者一定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观察者,他能够捕捉到别人容易忽略的美丽,并将它们用文字转化为触动人心的力量。我期待着书中能够有那些令人惊艳的细节描写,比如微风吹拂过高大建筑的缝隙,或者雨滴落在斑驳的墙壁上留下的印记。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感受到那里的人文温度,那些真实的情感,那些在平凡生活中闪耀的光芒。这本书就像是一个窗口,透过它,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的世界,一个充满故事,充满惊喜的世界。它让我开始思考,除了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还有怎样的精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感官的盛宴。作者的文笔就像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将我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景之中。我能感受到阳光洒在石板路上的温度,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欢快音乐,甚至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淡淡香料气息。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地方的介绍,更像是一次与当地人民的深度对话。我期待能读到那些生动的人物故事,那些充满个性和智慧的对话,它们会让我更真实地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我喜欢作者能够抓住那些最能代表城市灵魂的瞬间,并将它们用文字生动地呈现出来。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我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让我感觉自己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亲身经历着那里的一切。它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对未知的好奇,让我想要去亲眼看看,去亲身体验那些书中描绘的景象。
评分看到这本书,想起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知道博尔赫斯是读到一部叫做《哲学的邀请》中引用的他的话:“时间是一条把我卷走的河流,但我自己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把我撕成碎片的老虎,但我自己就是老虎;时间是一团把我烧成灰烬的火,但我自己就是火。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后来读他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说实话刚开始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读了几遍才领会到那么点意思。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翻了两篇,便开始喜欢上这个博学的老人了。
评分内容还可以,就是书薄了一点。还是可以读读。
评分"[SM]和描述的一样,好评! 上周周六,闲来无事,上午上了一个上午网,想起好久没买书了,似乎我买书有点上瘾,一段时间不逛书店就周身不爽,难道男人逛书店就象女人逛商场似的上瘾?于是下楼吃了碗面,这段时间非常冷,还下这雨,到书店主要目的是买一大堆书,上次专程去买却被告知缺货,这次应该可以买到了吧。可是到一楼的查询处问,小姐却说昨天刚到的一批又卖完了!晕!为什么不多进点货,于是上京东挑选书。好了,废话不说。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它是一个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这么说,不这么写,就会别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调有时候就是“器”,有时候又是“事”,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说,器就是事,事就是器。这本书,的确是用他特有的腔调表达了对“腔调”本身的赞美。|发货真是出乎意料的快,昨天下午订的货,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赞一个,书质量很好,正版。独立包装,每一本有购物清单,让人放心。帮人家买的书,周五买的书,周天就收到了,快递很好也很快,包装很完整,跟同学一起买的两本,我们都很喜欢,谢谢!了解京东:2013年3月30日晚间,京东商城正式将原域名360buy更换为jd,并同步推出名为“joy”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户在输入jingdong域名后,网页也自动跳转至jd。对于更换域名,京东方面表示,相对于原域名360buy,新切换的域名jd更符合中国用户语言习惯,简洁明了,使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同时,作为“京东”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写,jd也更易于和京东品牌产生联想,有利于京东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提升。京东在进步,京东越做越大。||||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本好书:《谢谢你离开我》是张小娴在《想念》后时隔两年推出的新散文集。从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读者面前,几个月的时间,欣喜与不舍交杂。这是张小娴最美的散文。美在每个充满灵性的文字,美在细细道来的倾诉话语。美在作者书写时真实饱满的情绪,更美在打动人心的厚重情感。从装祯到设计前所未有的突破,每个精致跳动的文字,不再只是黑白配,而是有了鲜艳的色彩,首次全彩印刷,法国著名唯美派插画大师,亲绘插图。|两年的等待加最美的文字,就是你面前这本最值得期待的新作。《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当今世界最高明的思想控制与精神绑架,政治、宗教、信仰给我们的终极启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一次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从国家、宗教信仰的层面透析“思维的真相”。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生物学、医学、犯罪学、传播学适用于:读心、攻心、高端谈判、公关危机、企业管理、情感对话……洗脑是所有公司不愿意承认,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潜规则。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无孔不入。阅读本书,你将获悉:怎样快速说服别人,让人无条件相信你?如何给人完美的第一印象,培养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如何走进他人的大脑,控制他们的思想?怎样引导他人的情绪,并将你的意志灌输给他们?如何构建一种信仰,为别人造梦?[SZ]"
评分书内容不错,,图文病猫..可以就是薄了点..一班一班吧。没有宣传等那么好。辰时卒于南安,享年五十七岁。 编辑本段 生平概述 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出生后爷爷王伦给他取名王云,出生的地方从此改名为“端云楼”。后5岁仍不会说话,一和尚说其名破道,家人改名为王守仁。 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很多私塾先生一直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据说他父亲王华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带他去塞外,领略大漠的浩渺。[1] 这一次,王守仁诞生了第一个为国家效力的念头。 一日,庄重地走到王华面前,严肃地对他爹说:“我已经写好了给皇上的上书,只要给我几万人马,我愿出关为国靖难,讨平鞑靼!” 王华沉默了,过了很久,才如梦初醒,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十分激动地顺手拿起手边的书(一时找不到称手的家伙),劈头盖脸地向王守仁打去,一边打还一边说:“让你小子狂!让你小子狂!” 王守仁第一次为国效力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但他并没有丧气,不久之后他就有了新的人生计划,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不久之后的一天,王守仁在街上走遇到了一个道士(王伦请的),道士说,你要做圣贤。王守仁深受触动。据查,发言者王守仁,此时十五岁。 王守仁平静地说道:“我上次的想法不切实际,多谢父亲教诲。” 王守仁故居(20张)王华十分欣慰,笑着说道:“不要紧,有志向是好的,只要你将来努力读书,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用了,出兵打仗我就不去了,现在我已有了新的志向。” “喔,你想干什么?” “做圣贤!” 这次王华没有再沉默,他迅速做出了回复——一个响亮的耳光。完了,完了,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小子手里了。”(明朝那些事) 这位怪人常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当时奸臣江彬为夺平叛之功,令王守仁将朱宸濠交出,为了百姓,王守仁拒绝了,江彬十分生气让张忠带京军入赣,影响社会安定,几次引起百姓叛乱,但都被王守仁的个人魅力压了下去,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后因功高遭忌。 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 编辑本段 相关事件 童年生活 王守仁画像
评分从一面了解点阿根廷和南美
评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有一个如诗般的名字,读起来就有一种和谐悦耳的节奏,一种绵长而婉转的美的感受,怎能不引起诗人的激情呢?更何况这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充满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评分书内容不错,,图文病猫..可以就是薄了点..一班一班吧。没有宣传等那么好。辰时卒于南安,享年五十七岁。 编辑本段 生平概述 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出生后爷爷王伦给他取名王云,出生的地方从此改名为“端云楼”。后5岁仍不会说话,一和尚说其名破道,家人改名为王守仁。 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很多私塾先生一直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据说他父亲王华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带他去塞外,领略大漠的浩渺。[1] 这一次,王守仁诞生了第一个为国家效力的念头。 一日,庄重地走到王华面前,严肃地对他爹说:“我已经写好了给皇上的上书,只要给我几万人马,我愿出关为国靖难,讨平鞑靼!” 王华沉默了,过了很久,才如梦初醒,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十分激动地顺手拿起手边的书(一时找不到称手的家伙),劈头盖脸地向王守仁打去,一边打还一边说:“让你小子狂!让你小子狂!” 王守仁第一次为国效力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但他并没有丧气,不久之后他就有了新的人生计划,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不久之后的一天,王守仁在街上走遇到了一个道士(王伦请的),道士说,你要做圣贤。王守仁深受触动。据查,发言者王守仁,此时十五岁。 王守仁平静地说道:“我上次的想法不切实际,多谢父亲教诲。” 王守仁故居(20张)王华十分欣慰,笑着说道:“不要紧,有志向是好的,只要你将来努力读书,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用了,出兵打仗我就不去了,现在我已有了新的志向。” “喔,你想干什么?” “做圣贤!” 这次王华没有再沉默,他迅速做出了回复——一个响亮的耳光。完了,完了,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小子手里了。”(明朝那些事) 这位怪人常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当时奸臣江彬为夺平叛之功,令王守仁将朱宸濠交出,为了百姓,王守仁拒绝了,江彬十分生气让张忠带京军入赣,影响社会安定,几次引起百姓叛乱,但都被王守仁的个人魅力压了下去,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后因功高遭忌。 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 编辑本段 相关事件 童年生活 王守仁画像
评分疆地旷人稀,举世仅见,益以人事未尽,沧桑迭更,遂使沙漠地区日益扩大,万里膏腴悉成石田,历史名城多已荡然无存。今日本省沙漠地带竞占全面积三分之~强,黄沙千里,浩瀚渺茫,荡漾起伏,望之如大海波浪然,史书称之为“瀚海”。其最著名者,为塔里木沙漠及白龙堆沙漠。前者位塔里木河西南,横亘于塔里木盆地之中,外人呼之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凡一千五百里,南北可三百四十里至七百里,全部为黏土沙砾所组成,厚度最高达二干公尺,最低处亦在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白龙堆沙漠,又名库木塔克,起自塔里木河以东以迄甘肃玉门关,其厚度亦达千公尺左右。其次为天山北路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占面积约一百五十万方里。 沙漠地区,雨量绝稀,气候奇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千里之间,人烟断绝,寸草不生,滴水难觅,夏时常因缺乏水源,旱死沙漠中,行旅视为畏途。沙漠又分真性与假性二种:前者纯属沙质所构成,为绝对不毛之地:后者又名戈壁,上虽砂石,下皆土壤,间或尚见水草,非绝对不毛之地。 南疆各绿洲,星罗棋布于塔里木盆地边沿,因地势辽阔,绿洲与绿洲问,每间以戈壁,其距离远近不等。最大者,为阿克苏至喀什噶尔,戈壁长凡一千一百里,其间约六百里内,皆黄沙大漠,旷绝水草,夏时行旅苟无妥善之准备,非旱死,亦必唇焦肠枯也。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云: “ 从此东行入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顾茫茫,不知所措,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纪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里,至靓货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又东六百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且末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 又一八九五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旅行塔里木大沙漠中,记其时之苦况云: “……初行十二日,尚可掘沙得水,且间有植物,人畜均安,惟沙丘起伏,陟降维艰耳。四月二十二日后,遂八真沙漠,沙丘起伏愈大,幸时有急风,沙丘为削平不少。沙漠中烈日如火,以故水箱之水均热至三十二度左右,人以冀能多出汗,使在风中较为凉爽,以故饮水过多,至此所余仅足二日之需,因不得不深藏之,以供人之所需。牲畜因无饮料,遂渐有倒毙者。途中从仆又多偷饮余水。五月一日,贮水尽罄。从仆伊斯南拜乃杀羊取血,以解烦渴,复接饮驼溺,皆不济事,是日另二仆渴死。”以唐玄奘及近
评分看到这本书,想起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知道博尔赫斯是读到一部叫做《哲学的邀请》中引用的他的话:“时间是一条把我卷走的河流,但我自己就是河流;时间是一只把我撕成碎片的老虎,但我自己就是老虎;时间是一团把我烧成灰烬的火,但我自己就是火。世界很不幸,是真实的;我很不幸,是博尔赫斯。后来读他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说实话刚开始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读了几遍才领会到那么点意思。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翻了两篇,便开始喜欢上这个博学的老人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