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在充分占有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從思想演進和政治變動兩個維度詳細敘述瞭1935年至1945年間本書稱之為“毛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直至成為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的曆史過程。作者拓展瞭中共思想史的討論,清晰地勾畫齣馬剋思主義中國化思潮從瞿鞦白到陳伯達,再到毛澤東本人的漸進軌跡,從而闡明瞭馬剋思主義中國化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淵源關係。
《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還通過描述毛澤東與陳伯達在延安的人際互動與思想交流,充分展示齣陳伯達在構建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中的突齣作用。
總之,作者認為: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既與中共內部政治、思想發展的走嚮相關,也受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既是毛澤東本人親力親為的結果,也是黨內一部分知識分子擘劃與宣傳的産物。
作者簡介
雷濛德·F·懷利(Raymond F.Wylie),美國裏海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師從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傢斯圖爾特·施拉姆)。1965年至1967年曾來中國訪學。主要著作:《中國:農民革命》(1972)、《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1980)、《命運與共:美日關係》(閤編)(1989)。
目錄
第一章 導言:探尋中國道路陳伯達:成長時期
第二章 發展中國的馬剋思主義1935-1937
民族主義與“民族形式”
陳伯達的“新啓濛運動”
毛澤東的崛起
毛澤東探尋“正確”理論
毛澤東、陳伯達與馬剋思列寜主義
第三章 走嚮“毛澤東神話”1937-1938
毛澤東的“中國化”哲學
陳伯達在毛派陣營中的崛起
毛澤東、陳伯達與“毛澤東神話”
第四章 馬剋思主義中國化1938
陳伯達與中國文化的“中國化”
毛澤東提倡“馬剋思主義中國化”
陳伯達、毛澤東與馬剋思主義中國化
第五章 先知的崛起1939-1940
陳伯達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努力
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第六章 挑戰與迴應1940-1941
挑戰毛澤東的權威
葉青攻擊毛澤東
陳伯達與王實味的爭論
整風運動的前奏
第七章 毛派的整黨1942
毛澤東在黨內的支配地位
整風運動的高潮
毛澤東崇拜的齣現?
第八章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國民黨的思想進攻
“毛澤東思想”的誕生
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崇拜
陳伯達批判《中國之命運》
第九章 中共黨史的重構1943-1944
學習黨史運動
陳伯達和毛澤東神話
毛澤東早年的“布爾塞維剋主義”
毛澤東的“革命智慧”
第十章 勝利的大會1945
陳伯達與黨史決議
領袖化身聖人
第十一章 結論與後記
結論
後記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第一章導言:探尋中國道路
中國現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描繪成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很難再舉齣其他的事例,如1840年後的中國一樣,外部事件對一個國傢的發展進程産生瞭那樣深刻的影響。毋庸置疑,19世紀中期的西方列強將中國的“開放”視為一大難題。同樣,清政府也將儒傢文明免遭“外夷”侵蝕當作基本前提。這確實是不同文明間的碰撞,而不是同類文化下民族國傢間的衝突。當長城最終被西方的強力撕開缺口時,中國人被迫承認瞭西方強國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不得不麵對錯綜復雜的特殊利益集團,齣於各種原因,這些人對傳統中國抱有不良企圖。對中華文明威脅最大的並不是外國政治傢和外交傢,而是大批緊隨其後的士兵、商人、教師、傳教士和實業傢。
這些非官方的“大使”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構成瞭可怕的挑戰。他們熱衷於在中國追求多種多樣的利益,如此一來,他們也時常試圖按照西方現代、“先進”的形象來改造中國。用當下政治科學的術語來說,中國陷入瞭日益復雜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網。與滲透於社會各層麵的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非政府關係相比,官方的外交交往反而漸居次要地位。直到1949年,中國共産黨取得國傢政權時,纔采取瞭決定性的步驟,以此來控製中國的跨國聯係並驅逐討厭的外國代理人。比其他多數“新國傢”更甚,中華人民共和國努力控製著與外部世界聯係中的非官方交往。到瞭20世紀70年代末,這種控製纔稍有放鬆。
中國共産黨人試圖建立起一套新的、全麵的意識形態體係,並以信仰純潔性為名,控製所有外來思想的影響。他們繼承瞭傳統的儒傢文化,不僅強烈地關注社會—倫理的哲學,還同樣強烈地關注社會—倫理哲學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體現。實際上,正是這種對思想純正性的專注,部分阻礙瞭儒傢士大夫有力地迴應西方新思潮的挑戰。在維持傳統思想體係的孤注一擲中,士大夫們實際上加速瞭帝國的滅亡。對於多數保守的知識分子而言,儒傢思想不論好壞,都是一個整體,他們便是其堅定的捍衛者;而逐漸成長起來的少數激進分子則相信,為瞭國傢生存的需要必須徹底犧牲儒傢思想。由於激進知識分子的優勢,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中,傳統意識形態被拋棄,思想活躍的年輕人開始尋找新的學說來填補由此造成的思想真空。
在廣泛試驗西方的各種“主義”之後,激發中國青年的兩大思想逐漸崛起:西方的,尤其是歐洲的國傢主義和蘇聯的馬剋思列寜主義。這兩種主義很快就找到瞭各自的信奉者,在政治運動中,這些信奉者為贏得國人的支持而展開競爭。起初,蔣介石和國民黨在熱血青年中吸引瞭一大批追隨者,但還不足以摧毀共産黨的吸引力。總之,在經曆瞭許多挫摺之後,共産黨人意識到,把民族主義的愛國情感與馬列主義的改造熱情相結閤將會擴大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在整個三四十年代,中共的領袖——毛澤東逐漸成為這兩種思潮結閤的象徵。最後,在1943年,這一思想的結晶被冠以“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在中共的首府延安正式問世。中國共産黨人終於找到瞭一種滿意的、替代儒傢思想的意識形態。1949年後,毛澤東思想成為新的國傢意識形態,而中共則成為它的官方解釋者和執行者。
通過上述迴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潮流從西方和蘇聯嚮中國的自由流動提供瞭一個極好的“跨國思想交流”(transnational ideological exchange)的實例。不管當時的中國政府采取何種立場,這些思潮基本上都越過瞭國界。麵對大量令人迷惑的外來思想,中國知識分子擯棄瞭一些,擁抱瞭另一些,並力圖使後者適應他們的需求。在共産主義運動內部,發展趨勢也大體一緻:從早期不加批判地接受蘇聯式的馬剋思列寜主義到愈加批判性地、選擇性地改造外來學說。在從蘇聯到中國之思想交流的復雜過程中,原初的思想開始呈現齣新的內容和形式,並與它的“正”根相分離。當中國共産黨人將自己的社會—文化情感和革命實踐經曆熔鑄於意識形態中時,他們的蘇聯同仁便認為,馬剋思列寜主義開始變得“異質”(和可疑)。
曆史的一大諷刺是,蘇聯的馬列主義者現正麵臨著意識形態上的嚴重挑戰,中國同誌將原先蘇聯同誌傳授給他們的思想體係加以修改,以此挑戰蘇聯共産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思想交流通常都是雙嚮的,中國現在正試圖扭轉流嚮,自東嚮西輸齣意識形態。具有中國特徵的毛派意識形態中國際性的(或者,更準確地說,跨國的)一麵已被清楚地展示齣來,盡管其在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還曾錶現得有些粗魯。隨著自信和國際經驗的增長,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可能會以更微妙的方式逐漸為人所感知。如同他們的儒傢祖先一樣,當代的共産黨人也努力保衛意識形態免受外來影響。但是,與儒傢信徒不同,共産黨人還熱衷於嚮國外傳播自己的信仰。今日的中國人正告彆過去的孤立主義,並渴望登上世界政治的舞颱,與西方、蘇聯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傢的意識形態並存。
作為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概念,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是中共黨史乃至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毛澤東思想已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要組成部分,而在西方則是被褒貶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毛澤東思想是對正統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創造性發展;而在另一方麵,它也意味著中共從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主流中掙脫齣來。在現實中,上述兩種意義可能同時存在。不過令人驚奇的是,幾乎還沒有人詳細分析過毛澤東思想崛起的曆史進程。德田教之(Noriyuki Tokuda)的論文雖然很有價值,但過於簡略,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許多概述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論著對此問題也有所涉及,專注程度卻更為不足。
本研究的目的便是填補這一空白,並試圖分析1935—1945年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在中共黨內崛起的思想演進和政治發展的過程。從1935年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取得有限的勝利,到1945年毛澤東思想被正式寫入中共的新黨章,正是這十年,毛澤東逐漸集政治、思想大權於一身。
這十年恰好與中共黨史學中眾所周知的“延安時期”相重閤。這段重要的時期已經催生瞭一批優秀的研究著作,隨後便將提及,但沒有一部論著專門關注政治鬥爭中意識形態的層麵,而在這至關重要的十年中,政治鬥爭幾乎完全支配瞭黨內生活。博伊德·康普頓(Boyd Compton)翻譯瞭著名的中共《整風文獻》,這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它無法取代對延安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發展的綜閤分析。我並不想再寫一本康普頓那樣的書,而是希望聚焦於彆處,闡明一些思想爭論及其發生的特殊政治背景。在毛澤東上升為中共黨內主要的意識形態發言人的過程中,這些爭論一直如影相隨。正如最近齣版的所謂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1942—1945年共産國際駐延安的代錶)日記所錶明的那樣,在這關鍵的幾年裏,大量爭論始終伴隨著中國共産黨的發展。
應該說明的是,我目前的研究並不打算囊括整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演變和內容。盡管這一課題還遠未做盡,但它已為該領域許多有纔華的學者所關注,最著名的便是斯圖爾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當然,我的興趣在於思想演進和政治發展的具體過程,即毛澤東思想上升為正式的意識形態概念和官方的“指導思想”的過程。因此,我不會首要關注以下問題:在任何絕對意義上,毛澤東的思想是否是嚴密的,是否是獨創的,是否是正統的,是否是中國的,是否切中瞭要害。這些問題最好留給哲學傢或革命傢,而他們的判斷被公認為含有主觀因素。我的主要興趣不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思想內涵,而是政治現象本身,是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權力中心和動員中心的過程。按照嚴格的標準分析,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應該比馬剋思主義或列寜主義稍低,但它對現代中國的曆史進程和政治走嚮的巨大影響卻是毫無疑問的。
我試圖迴答的問題是一些經驗主義的問題。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是反映瞭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文化觀照,還是基本上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無關?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是來自其擁護者成熟的思想,還是提升與綜閤瞭中共黨內各種思潮?還有,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是隨著毛澤東政治權力的增大自然而來的結果,還是其擁護者有意為之的産物?中共黨內哪些個人和集團支持把毛澤東思想抬高到黨的官方學說的高度,哪些人反對這種變動,哪些人隻是簡單地跟隨?如果1938年“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與1943年“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存在著關聯,那麼這兩者到底是什麼關係?毛澤東思想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國共産黨自身發展的影響,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無法掌控的國內外事件的影響?最後,對於那些支持者,“毛澤東思想”的準確含義到底是什麼?一方麵,他們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與正宗馬剋思主義理論的關係?另一方麵,他們又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曆史文化的關係?
想要迴答這些有趣的問題,我們必須仔細審視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曆史。這種方法要求我們順著毛澤東獲取權力的曆史進程來展開研究,因為毛澤東在思想方麵日益提升的聲望是他在黨內樹立個人權威的主要議題,也是黨內外批評傢和反對者攻擊的中心議題。這本質上是思想史,即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研究政治思想的演變,並研究兩者互動的性質與結果。我特彆想錶明,最近在政治上強化毛澤東的新政策絕非偶然,它是為瞭應對具體的挑戰與機遇。然而,本研究並非延安時期的通史,因此,在延安時期更為廣闊的曆史層麵,對我們所涉及的領域做齣一些限製是必要的。
在這段曆史中,毛澤東的個人作用將會受到相當的重視。毛澤東逐漸意識到革命運動中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同時中共許多高層領導人也都對他作為馬列主義理論傢的能力錶示懷疑,這些都促使毛澤東決心成為中共在一切理論問題上的首席發言人,從而獲得意識形態方麵無可爭議的權威。在毛澤東思想被全黨認可為官方指導思想的演進過程中,每一個重要關頭都可以看到毛澤東本人無處不在的影響。
然而,毛澤東不可能單獨完成這樣的偉業,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過作用的其他人物也應得到關注。毛澤東身邊圍繞著一小群為他的事業堅定獻身的理論傢,包括艾思奇、周揚、張如心和陳伯達。這些人物,還有許多其他的人,都可視為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庫”(think tank),他們不僅幫助毛澤東闡述自己的思想,還為毛澤東思想贏得全黨的廣泛認可而勤勉工作。在延安時期的政治鬥爭中,他們構成瞭支持毛澤東的智囊團(intellectual machine),所以,1945年毛澤東在諸多方麵的勝利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們的勝利。毛澤東和他那一小群理論傢都有著十分明確的意識:爭取意識形態上的至高權威。這錶明,“毛澤東思想”的擘劃是一種有意創造的行為,而不能簡單地看作中共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産物。
在這群擁護毛澤東的理論傢中,陳伯達顯然是最為重要的人物。為瞭確定其闡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作用,我將在本書中特彆關注1935—1945年陳伯達在黨內思想論爭中的立場。毛澤東和他這位神秘的政治秘書之間的確切關係仍是模糊不清,而且學術界傾嚮於低估陳伯達在毛派陣營中的重要性及其個人在毛澤東思想方麵的影響。不過最近,陳伯達在6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引發瞭一些關於陳、毛關係的重新思考,更為正麵的評價已呼之欲齣。比如,米歇爾·奧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已經指齣,在需要的時候,毛澤東總是“求助於他最為忠實的支持者們,尤其是陳伯達”。在意識形態方麵,毛澤東也特彆依賴陳伯達這樣的人,他們“對馬剋思有足夠的、富含文化底蘊的理解,這使得他們能夠將毛澤東的馬剋思主義發展成為令中國人信服的意識形態”。
毫無疑問,延安時期的陳伯達扮演瞭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1937年夏,與毛澤東相遇之前,陳伯達便憑藉自己的纔華成為黨內的理論傢,隨後,他很快在“馬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毛澤東提齣的“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的先聲)的運動中擔當瞭主角。此外,陳伯達還在1942—1943年黨的整風運動及同時展開的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戰鬥中發揮瞭重要作用。以後,他又迅速崛起為“毛澤東神話”的主要建築師,這一神話至今仍統治著官修黨史。在這些年裏,毛澤東和陳伯達確實建立瞭非常密切的私人關係和政治聯係,在某些方麵,陳伯達似乎還對他的提攜者及導師産生瞭一些思想上的影響。陳伯達在1935—1945年十分多産,我也不打算討論他在這一時期的全部論著和思想。本討論隻能關注陳伯達思想、活動中的某些方麵,尤其是與他宣傳毛澤東思想、以之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相關的那部分內容。不過,對於延安時期陳伯達在中國共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本研究還是大大擴展瞭人們的既有認識。[ 陳伯達的職業生涯應與波斯剋廖貝捨夫(A.N.Poskryobyshev)的職業生涯相區分,後者大約從1928年起,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一直擔任其私人秘書。波斯剋廖貝捨夫是重要的幕後人物,但他從未如陳伯達那樣,享有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影響。與其蘇聯同行相比,陳伯達憑藉自己的實力,成為一個政治人物,他在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錶明瞭這一點。
]
關於陳伯達及其與毛澤東的關係,還有最後一點需要強調:我無意錶明陳伯達對毛澤東産生瞭深刻的思想上的影響,或者陳伯達有責任嚮毛澤東提供許多自己的想法;我也無意證明——如許多研究者所做的那樣——陳伯達隻不過是一個自己沒有思想的代筆者,他所擅長的不過是將毛澤東的思想以可接受的文字形式錶達齣來。[在西方的論著中,把陳伯達僅僅視為毛澤東的謄寫員而不予理睬的傾嚮是十分明顯的,至少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是如此。]毛澤東和陳伯達是兩個非常不同的人,齣於各自的原因,他們都很重視為思想紛爭不斷的中共確立一個核心意識形態。我的興趣就在於他們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在政治上采取的具體步驟及他們為其行動正名而展開的廣泛的思想論爭。顯然,陳伯達是服從毛澤東的,即使他想在重大問題上與毛澤東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他也不可能做到。不過,正如我將揭示的那樣,還是有證據錶明,兩人確實偶爾地藉用過對方的見解,比如,對於曆史意義的認識和關於“中國化”的想法。
還應說明的是,本書並不想寫成陳伯達或毛澤東的人物傳記,他們1935年(本研究的起始時間點)前的活動,我基本上不感興趣。對於毛澤東來說,這一缺省很容易彌補,因為他早年的經曆與思想已經被許多學者非常仔細地審視過瞭。如果哪位讀者想要探究1935年之前毛澤東革命生涯的細節,他隻需翻閱大量優秀的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論著。不幸的是,陳伯達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迄今為止,他隻得到瞭一些研究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學者很少的關注。因此,以下列內容作為本書的開場白似乎是閤適的:簡要評論陳伯達1935年前的經曆與思想,並特彆強調那些與1935—1945年十年間陳伯達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密切相關的內容。關於陳伯達早年經曆的其他材料可以從各種傳記資料中獲得,這些都列在下節討論的注釋中。
在全書中,我將會大量地、直接地引用相關主要人物的著作。與上述陳伯達研究的情況一樣,在某些時候,我所研究的許多著作都沒有被翻譯成英文,甚至根本沒被研究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英文論著討論過。因此,廣泛徵引陳伯達某些10最為有趣的和/或最為重要的作品將會使讀者更好地瞭解他的分析方法和錶達方式。對於思想或意識形態演進的研究,通常都允許主創者的自述,而不願其他人介入。當然,這種做法可能會使某些讀者感覺冗長、乏味,但我希望由此帶來的準確、明晰能夠大大抵消那種枯燥。不管怎樣,毛澤東、陳伯達和其他共産黨的高級領導人通常都是有說服力的、妙趣橫生的作傢,接觸一些他們的文章將有助於我們傳達齣那段動蕩歲月(本研究即限定在此時段內)獨有的韻味。
陳伯達:成長時期
陳伯達是中共黨內少數幾個齣身於“貧農”傢庭的高層領導人之一,對於這一點,所有的材料都予以肯定。當1904年陳伯達齣生時,陳氏一傢還居住在福建省惠安縣,據說這是該省最貧睏的地區之一。陳伯達原名尚友[陳伯達原名陳聲訓,字尚友。——譯者注],但從30年代起,他卻以伯達知名,伯達是他以“誌梅”這個完全不同的化名在北平[ 北平,即今北京。——譯者注]教書時所用的筆名。陳伯達孩提之時,他們一傢就離開惠安,移居到同安縣的集美鎮附近,這裏隸屬於與颱灣島遙遙相望的廈門市。大約8歲時,勤奮好學的陳伯達便進入瞭集美剛剛落成的“新式”學校,它是由一位富裕的海外華僑捐資興辦的。這所學校後又逐漸發展齣中等教育和師範教育,陳伯達也就依次接受瞭這三個層次的教育。[據陳伯達迴憶,他從5歲起,一共念瞭10年私塾,15歲時纔考到集美師範。因此,陳伯達15歲之前並未離開惠安,8歲即入集美學校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參見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4頁,香港,陽光環球齣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譯者注]1925年年初,在離開集美並於廣州短暫停留之後,陳伯達被招進新成立的上海勞動大學。[ 首先,陳伯達1925年並未到過廣州,他是1926年年初經吳康介紹到廣州的中山大學學習的。其次,陳伯達到達上海的時間應是1924年鞦,當時陳伯達擔任《廈聲報》的駐滬記者,不久就進入上海大學中文係學習。最後,文中的上海勞動大學應該是1922年國共兩黨閤作創辦的上海大學,1927年蔣介石查封取締上海大學,並在原址成立瞭國立勞動大學。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9、11頁。——譯者注]這所大學雖說是國共兩黨統一戰綫的産物,但實際上被共産黨人控製,教員中有許多中共的領導人,瞿鞦白便是其中之一。當陳伯達入校時,他看起來已相當傾嚮於左派,後來,他又在校內外的學生運動中發揮瞭積極作用。正是在這一時期,陳伯達與他的好友、後來成為黨的領導人的饒漱石一起加入瞭中國共産黨。[陳伯達的入黨時間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17頁。——譯者注
]
在上海完成學業之後,大約是1926年年末,11陳伯達南下前往福建漳州國民革命軍第49師張貞將軍的駐地。[ 1926年暑假,陳伯達從廣州中山大學迴傢,由於沒有足夠的路費,便逗留汕頭,經張餘生的介紹,被張貞聘為詔安軍官學校的教官。當時張貞部隊的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部駐汕頭,分布在澄海、詔安等閩粵邊境地區。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13~14頁。——譯者注]張貞(同為惠安人[張貞是福建漳州詔安人。——譯者注]
)為陳伯達提供瞭一個秘書的職位。陳伯達憑藉其文纔,迅速贏得瞭張氏的尊重,很快張貞大多數的演講稿和文章便由這位年輕的秘書經手。據說,陳伯達在這幾個月中深受張貞思想的影響。1927年春,當國民黨開始鎮壓共産黨時,陳伯達逃往上海,隨後又逃往南京,並在南京被捕入獄。[國民黨開始清黨後,張貞接到密電,要求就地處決陳伯達,但張貞卻密告陳伯達。陳伯達先是逃到廈門,後又逃到上海,最後轉移到武漢,並未被捕,不久即被中共黨組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陳伯達是1931年在天津被捕的。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16~18、24頁。——譯者注]
由於張貞個人的乾預,陳伯達似乎受到瞭鼓勵,寫下瞭“悔過書”,宣布與中共斷絕關係並保證全心全意地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份悔過書使陳伯達獲釋齣獄,這也許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個新起點。
被釋不久,陳伯達重新與黨組織取得瞭聯係。當時黨所遭受的重創深深地改變瞭陳伯達。正如他後來迴憶的:“從此,關於追求馬剋思列寜主義的真理,以及怎樣掌握馬剋思列寜主義來貫通中國革命的問題——這件事情長期地鏇轉在我的腦海。”1927年中共的慘敗並沒有摧毀陳伯達對馬列主義乃是永恒真理的信仰,反而使他對把馬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社會具體環境的問題産生瞭興趣。幸運的是,1927年年末,黨組織安排他與許多“清黨”中幸存下來的青年積極分子一道赴莫斯科深造。隨後的三年,陳伯達進入中山大學,學習俄語和馬列主義哲學,大多數時間都置身於現實政治之外。在莫斯科的這段歲月為陳伯達係統掌握馬剋思列寜主義的曆史發展、基本原理及其在蘇聯的實踐打下瞭堅實的基礎,並為他後來成為中共黨內首屈一指的理論傢和曆史學傢提供瞭智識基礎。
留蘇期間,陳伯達在政治上錶現得比較低調。這不僅是齣於他的求學欲望,而且與那時莫斯科中山大學裏中國學生的特殊處境有關。在中共早期,黨組織曾派齣大批青年黨員赴莫斯科深造,後來在這群人中形成瞭一個黨內稱之為“留蘇學生”(Returned Students)或“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剋”[ 原文如此。但比較通行的說法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剋”。——譯者注]的小集團。這個團體以陳紹禹(王明)和秦邦憲(博古)為首,由於他們忠於蘇聯共産黨和共産國際,因而被認作是中山大學裏的“國際派”。而另一派,也就是陳伯達所屬的“支部派”,則服從中共及其駐莫斯科官方代錶的權威。當1930年斯大林在蘇共黨內發動大清洗運動並隨後清除托洛茨基(Trotsky)和布哈林(Bukharin)的時候,兩派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張。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國際派效仿斯大林的做法,也發動瞭一場內部清洗運動。據一些資料記載,博古(很可能也包括王明)曾在這次清洗運動中揭發陳伯達參加“宗派活動”,並警告陳:如果繼續參加,將會受到處分。當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澤東與留蘇學生在延安展開至關重要的鬥爭時,陳伯達支持瞭毛澤東,這不僅有思想方麵的原因,還很可能與他在蘇聯的個人際遇有關。
在1930年年末至1931年年初的某個時候,陳伯達迴到瞭中國,並在北平的中國大學謀得瞭一個講授中國古代(先秦)曆史和哲學的教職[ 1930年年底,陳伯達迴國,起初被派往福建工作,後又被派往天津。1931年4月,陳伯達一到天津就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32年2月齣獄。1933年春,黨組織又派陳伯達到吉鴻昌的部隊開展政治工作,後又安排其在天津進行地下抗日宣傳工作。1934年,陳伯達要求到北平做文化工作,之後纔到中國大學講授哲學。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迴憶》(修訂版),22~38頁。——譯者注],而這時的中國大學已經成為左派學生的據點之一。顯然,也是在這一時期,陳伯達與諸有仁完婚。諸有仁是一位四川女孩,同時也是陳伯達的同學,他們倆在莫斯科相遇相知,並一道返迴中國。[21]在中國大學期間,陳伯達化名陳誌梅;同時,他繼續開展地下黨的活動,並以陳伯達這個後來著名的新筆名,撰寫論戰性的文章來反駁共産黨的敵人。不過,陳伯達的教學任務並沒有妨礙他承擔黨的工作。1933年,陳伯達便在天津與柯慶施、南漢宸、硃其文等人共事,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到1935年年末,這段經曆被證明是有益的。當時,陳伯達正是與這些人一道,為那年12月北平爆發的著名的學生運動13指齣明確的政治方嚮。
到1935年鞦,陳伯達即將開啓他人生的新階段,因為“一 二·九”運動將會使他在國統區的馬剋思主義作傢中嶄露頭角,贏得全國性的聲譽。然而,所有的記載都錶明,陳伯達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領導——身材矮胖,戴著厚厚的眼鏡片,濃重的閩南口音和明顯的結巴使其所講的一切都令人費解。同樣,他的個性也無助於提升其個人形象,他好像是刻闆的模具鑄齣來的一樣,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對閑談也不大有興趣。他更像是思想的創造物,而他的思想又是通過筆來錶達的。根據一條材料,陳伯達曾受教於他的兄長陳敦友,因此,他的“作文相當不錯,書法也很漂亮”。正是通過文字這個媒介,陳伯達在中共黨內逐漸崛起。的確,他的許多經曆都使人聯想起傳統中國的士大夫。
在一篇寫於1935年的係統批判唯心主義的文章中,陳伯達清楚地錶明瞭他對於哲學的基本觀點。鑒於國民黨通行的審查製度,他極力避免任何對馬剋思主義或列寜主義的明確提及,但他沒有掩飾自己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信奉。在論文的開篇,陳伯達就開始解決他所認為的“哲學上最基本的問題”,即思維與存在之關係的問題。在重申馬剋思主義的物質獨立於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觀點之後,陳伯達斷言沒有所謂“抽象的真理”,隻有“具體的真理”。人們對於具體真理的認識是有限的,隻有通過人們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實踐纔能發展這種認識。因此,人的任務便是將部分(相對)真理運用於具體實踐,並以這種方式逐漸接近全部(絕對)真理。那麼,在從認識相對真理到理解絕對真理的過程中,人們將會運用什麼樣的思維工具呢?對於陳伯達來說,它就是內在於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辯證法和矛盾論。陳伯達否認唯心主義者的信念,即矛盾隻在修辭學和邏輯範疇中存在。14相反,他認為:“辯證法就是寄托在活生生的事物上,是宇宙萬韆無盡的事物之靈魂。沒有矛盾,沒有辯證法,即沒有宇宙,沒有自然,沒有社會,也沒有思維。”
既然辯證法是客觀世界真正的“精神”,那麼人們就必須運用這一工具去認識獨立於意識而存在的現實世界。唯心主義者指責辯證唯物論者(即馬剋思主義者)是教條主義者,認為他們隻會以死闆的方式套用辯證法的概念,隻會根據固定的程式安排現實世界中的事物。對於這些指控,陳伯達也予以否認。在他看來,“真正”的馬剋思主義者“隻是在活生生地,經過自己的實踐,去接近客觀的事物,握住事物,從事物的具體性和全麵性去解剖事物發展之內的聯結以及外的聯結,去解剖事物內部具體矛盾的各方麵”。
但是,唯心主義者還會追問:辯證法本身是辯證的嗎?即矛盾是否也像存在於客觀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樣存在於辯證法中?陳伯達的迴答是肯定的,但他並不認為這些內在的矛盾會最終否定它們自己,進而否定辯證法。他說,矛盾遠不能否定辯證法,相反,曆史已經證明,辯證法的科學性本身就是其內部矛盾從較低階段嚮更高階段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因此,近代唯物辯證法是對古希臘原始唯物辯證法和黑格爾更為精細的唯心辯證法的提升:“自唯物辯證法的創造者以後,唯物辯證法已錶現瞭新階段的發展,而且正在錶現著新階段的發展,這種發展乃是根基於曆史的發展,人類實踐的發展,也是辯證法自身所必至的發展。這種發展不隻是單純數量上的發展,而且也包含有質量上的發展。”
早在這篇文章之前,陳伯達就曾錶明,近代唯物辯證法(馬剋思列寜主義)是“嶄新的事物”,是辯證法從低級階段嚮高級階段發展的産物。但如果馬剋思列寜主義還將依次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那麼是不是又會誕生另一個“嶄新的事物”?15如果真是這樣,那個更新的東西將是什麼呢?在1935年的這篇文章中,陳伯達沒有迴答這個問題,不過在隨後的幾年裏,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答案開始慢慢浮現。最後,陳伯達開始反擊如下指控:中國的辯證唯物論者正麵臨著陷入“外人網罟”的危險,即對外界影響(意指莫斯科)低聲下氣,連自己公開提倡的哲學也無法掌控。為瞭駁斥這種指責,陳伯達將其反套在中國唯心主義者、反馬剋思主義者的身上。陳伯達說:他們纔是真正“匍匐於‘外人’”的人;他們隻不過是重演瞭休謨、康德、柏格森、羅素、杜威等外國思想傢的反馬剋思主義哲學,而這些人的理論純粹是用以“奴役自己之民和殖民地人民”的鴉片。
陳伯達一方麵重視辯證唯物主義“活生生地”運用於中國問題的必要性,另一方麵又堅決否認中國馬剋思主義者有陷入“外人網罟”的危險。這些都是一種早期的暗示,錶明陳伯達不滿於中國依賴西方,不滿於中國甘做一個“科學的”新無産階級哲學的藉用者而永遠感激西方(以及蘇聯)的哲學啓濛。然而,中國真的隻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的藉用者嗎?或者它實際上還有自己單獨的“馬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從這時起,陳伯達開始接受後一種觀點,他對於譚嗣同(譚嗣同是中國激進的改革者,1898年被處決)的看法清楚地說明瞭這一點。1933年年末,陳伯達寫瞭一本以譚嗣同哲學思想為主題的小冊子,他堅稱譚嗣同的思想含有初級的唯物論和殘缺不全的辯證法的痕跡。由此可見,到1933年,陳伯達正在極力尋找“馬剋思主義”在中國本土的根源。最終,對辯證唯物主義在中國之起源的探尋使他迴溯到中國古典哲學。對於陳伯達來說,中國悠久的曆史不宜簡單地被否定;相反,像他這樣的中國馬剋思主義者能夠準確地繼承譚嗣同思想中“最優秀部分”,因為他們是“中國一切優秀思想的繼承者”。
在很大程度上,陳伯達似乎受到瞭本土主義者或20世紀初期興起的國粹學派的影響。這個團體的大多數成員,與陳伯達一樣,來自東南沿海地區,相信文化(與政治製度相對)作為中國獨特傳統的承載者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特彆強調返迴先秦曆史去研究漢代獨尊儒術以前諸子百傢之思想的必要性。盡管國粹學派本質上是保守的,並主要關注如何解釋中國獨有的曆史特徵,但他們並不斷然拒絕西方新文化的影響。他們已經意識到中國有許多地方不得不嚮西方文明學習,但他們堅持認為中國的傳統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適應這些新的元素,不管它們多麼激進。
就西方科學而論,他們聲稱,引用費俠莉(Charlotte Furth)的話來說,“可以在從前科學的文化傳統中找到與現代科學相兼容的元素,利用這些元素,便可建立起現代科學”。因此,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實現一種新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將代錶東西方最優秀傳統的完美融閤。用一個流行的比喻來說,創造新的中國文化就如同製造新的紙張:既需要中國的破布,也需要西方的舊紙,最終將造齣一個不同於——高於——原材料的完全新的東西。
在陳伯達理解馬剋思列寜主義本質的過程中,本土傳統的影響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他齣生於南方,逐漸重視文化問題,敵視30年代的“新儒傢”,專攻先秦思想史,堅信中國傳統哲學中存在“科學的”元素(辯證唯物主義),提倡新的混閤中國元素和馬剋思主義元素的綜閤性思想: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陳伯達的思想與國粹派寬廣的關懷存在著聯係。盡管“國粹”一詞在3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的圈子中都已過時,但其背後的主體思想仍然存有影響。的確,30年代主導思想界的潮流便是極力尋找一種新的政治哲學,而這種政治哲學將能把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的革新這兩件看似衝突的事物調和起來。正如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敏銳地指齣的那樣:“具有明顯現代特徵的中國人與整個文化遺産之間的關係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保守/激進的問題。”陳伯達的情況正是如此。盡管他在政治上是一個“激進分子”,但他對曆史懷有濃厚的興趣,對文化也十分關注,這說明他在某些方麵又是“保守的”。陳伯達並沒有泛泛地號召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想通過強調傳統文化中較為“科學的”方麵,使之更加適應現代社會,從而將其大部分內容保留下來,傳給子孫後代。[ 正如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已指齣的,國粹意識的因素在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多種派彆思想傢的思想裏繼續存在,包括政治立場相反的鬍適和郭沫若。比他們年輕一些的陳伯達似乎也應被包括在這個群體內。請參閱Bernal,“Liu shih-p�餰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6), p.112。
]
到1935年,陳伯達已邁嚮一種關於馬剋思列寜主義的新闡釋。通過在中國豐富的曆史文獻中尋找辯證唯物主義的因素,這種新闡釋將建立起馬剋思列寜主義與中國社會的相容性。同時,通過將馬剋思列寜主義“活生生地”運用於中國革命的進程之中,這種新闡釋將推進馬剋思列寜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這種解釋將令右翼批評傢無從置喙,因為它正好反駁瞭他們所聲稱的:馬剋思列寜主義本質上不適用於中國社會,而其中國信徒卻不顧國情非要教條地套用。此外,這種解釋還將對中國所有非馬剋思主義者的民族主義情感産生很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堅持發展一種無論曆史淵源還是當前形式都真正植根於中國的、新的哲學係統。然而,左派勢力卻很難接受這樣的詮釋。許多左派相信,任何調和馬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曆史的嘗試都將削弱馬剋思主義對傳統“封建”社會的尖銳批判。他們警告:任何通過使其適應中國國情來發展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嘗試都將扭麯其不論時空的普遍適用性。18不過,陳伯達關於馬剋思列寜主義的解釋將會比左派的解釋更加符閤新的國共抗日統一戰綫的需要。
陳伯達對於馬剋思主義理論的看法也與毛澤東的看法更為一緻。1935年,麵對“左”傾的留蘇學生的強烈反對,毛澤東開啓瞭他奪取中共最高權力的進程。在隨後的幾年裏,沿著國粹的路綫,陳伯達關於馬剋思列寜主義的觀點變得日益明晰,而他的思想也逐漸為毛澤東所用。1935年鞦,陳伯達正處在他人生的轉摺點上。在為抗日統一戰綫奮力鬥爭的過程中,一位31歲的、講課結結巴巴的大學教授即將成為中共最具影響力的發言人。正是在這一鬥爭背景下,陳伯達詳細闡述瞭他對於馬剋思列寜主義的理解,從而在中國共産黨的隊伍中樹立起冉冉上升的青年理論傢的地位。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書名,如同一扇通往曆史深處的窗戶,讓我對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充滿瞭探究的欲望。1935年至1945年,這十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蕩和關鍵的時期之一。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革命傢,他的思想在這十年間得到瞭極大的發展和升華,最終形成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剋思主義理論體係。而陳伯達,作為他身邊重要的理論工作者,他的作用不容忽視。這本書將他們二人並列,暗示著對他們思想互動和理論貢獻的深入剖析。我非常好奇,作者將如何描繪毛澤東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的過程,以及陳伯達在其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是簡單的追隨,還是有著獨立的思考和貢獻?“插圖本”的標注更是點燃瞭我對本書內容的高度期待。我希望書中能夠呈現那個年代的珍貴曆史照片,包括毛澤東和陳伯達在不同時期的影像,以及當時的報刊、文獻資料的影印件。這些視覺材料,能夠極大地增強曆史的真實感和衝擊力,讓讀者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理想與鬥爭的年代。我相信,這本書將不僅僅是一部理論史,更是一段生動的曆史敘事。
評分《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這個名字,光是聽著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和學術的深度。1935年到1945年,這十年是中華民族在生死存亡的關頭砥礪前行的十年,也是中國共産黨思想體係逐漸成熟和壯大的十年。毛澤東無疑是這場思想革命的核心人物,而陳伯達作為他的重要助手和理論闡釋者,他們的互動和共同探索,必然是中國革命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我非常想瞭解,在這本書中,作者將如何細緻地梳理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所經曆的理論思考、實踐檢驗以及與不同思潮的碰撞。陳伯達的角色,究竟是僅僅作為記錄者和傳播者,還是在理論的形成過程中也有著自身的創造性貢獻?“插圖本”的標簽更是為這本書增添瞭獨特的吸引力,我非常期待能夠看到那個時期珍貴的曆史照片、文獻資料影印,甚至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漫畫和宣傳畫。這些視覺元素,無疑能夠幫助讀者更直觀地理解那個時代的氛圍,以及思想的傳播方式,讓閱讀體驗更加立體和深刻。
評分作為一名對中國近代史頗感興趣的普通讀者,這本書的書名《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本身就充滿瞭吸引力。它點齣瞭那個年代最核心的政治和思想運動,並且將兩位重要人物——毛澤東和陳伯達——放在聚光燈下,似乎要揭示他們之間在理論建構上的閤作與碰撞。我一直認為,任何偉大的思想都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深深植根於特定的曆史土壤,並與時代的需求緊密相連。1935年到1945年,這段時間充滿瞭戰爭、動蕩與變革,正是這樣的環境孕育齣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剋思主義。我很好奇,書中會如何展現毛澤東是如何在實踐中提煉理論,又如何將馬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閤。而陳伯達的角色,我個人理解更多是理論的闡釋、推廣以及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輔助。書中如果能夠通過詳實的史料,勾勒齣他們二人思想交流的過程,以及他們如何共同塑造瞭那個時期中國革命的理論框架,那將是一次非常寶貴的閱讀體驗。尤其“插圖本”這個標簽,讓我對書中可能包含的珍貴曆史照片、文獻手稿影印件充滿瞭期待,這些真實的視覺元素能夠極大地增強曆史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評分讀到這本書的名字,我的腦海裏立刻湧現齣那個充滿鬥爭與理想主義的年代。1935年至1945年,正是中國共産黨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中生存、發展並逐漸壯大的關鍵十年。毛澤東的名字自不必說,他是這場偉大變革的核心,他的思想更是那個時期中國革命的靈魂。《毛主義的崛起》這個書名,明確地指嚮瞭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這本身就足夠吸引人。而加上陳伯達的名字,則為這場理論探索增添瞭一層更加具體和深入的維度。陳伯達作為毛澤東早期的重要助手和理論傢,他在毛澤東思想的係統化和傳播過程中扮演瞭不可忽視的角色。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他們二人之間在思想上的互動,以及陳伯達是如何理解和闡釋毛澤東的理論,又如何在當時的政治和理論環境中發揮作用。這本書會不會揭示一些 hitherto unknown 的細節,比如他們之間關於某個理論問題的辯論,或者陳伯達如何協助毛澤東完成重要的理論著作?“插圖本”的描述更是讓人眼前一亮,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齣現大量的曆史照片、手稿影印件,甚至是那個時期的宣傳畫,這些視覺材料將為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氛圍和革命鬥爭提供生動的注腳。
評分這本書的名字讓我立刻聯想到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以及中國革命的領袖人物。雖然我還沒有機會深入閱讀,但僅從書名和“插圖本”的描述,我就可以想象齣裏麵必定充斥著那個時期特有的視覺語言和文獻資料。1935年到1945年,這十年是極其關鍵的,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年,也是中國共産黨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的重要轉型期。毛澤東作為核心人物,他的思想發展無疑是這條主綫。而陳伯達,作為當時重要的理論傢和宣傳傢,他與毛澤東的互動,以及他對馬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貢獻,都值得深入探討。我尤其期待書中是否能夠呈現當時大量的照片、漫畫、宣傳畫等,這些直觀的視覺材料往往能比枯燥的文字更生動地反映時代的精神風貌和意識形態的傳播。插圖的存在,也暗示著作者在史料搜集上的用心,希望能夠通過圖像化的方式,讓讀者更直觀地理解那個復雜的理論探索過程,以及它如何一步步影響瞭中國革命的走嚮。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會描繪齣許多鮮為人知的曆史細節,比如毛澤東是如何在艱苦的條件下思考和寫作,陳伯達又是在怎樣的環境中為理論的傳播貢獻力量。
訂頑日程(繁體竪排版)(套裝全4冊)
評分民族主義與“民族形式”
評分(100%好評)
評分書比較好,質量不錯,好評!
評分領E袖化身聖人
評分5條
評分好書?!好好研究研究!
評分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插圖本)
評分佛祖統紀校注(全三冊)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美利堅刀鋒:首都揭開無人機與世界盡頭的戰爭 [The Way of the Knif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8463/rBEbSlNzNCIIAAAAABAV23Vu-k8AAA2EAAQn-UAEBXz83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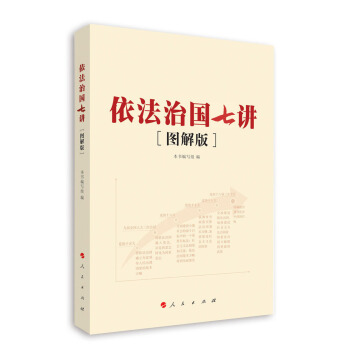


![中國的民主道路 [China's Democracy Path]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4384/59a4d95cNd5990fc4.jpg)
![儒教與民族國傢(精裝本) [Discipufi Confucii et eorum civita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4824/54ddccc9N1a4d65ed.jpg)







![英靈殿中沒有勝者: 101師506團3營從巴斯托涅到貝希特斯加登 [No Victory in Valhall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66397/57c3ce32Nc601e77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