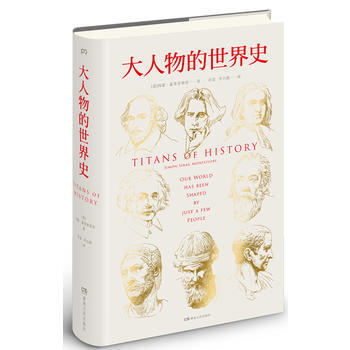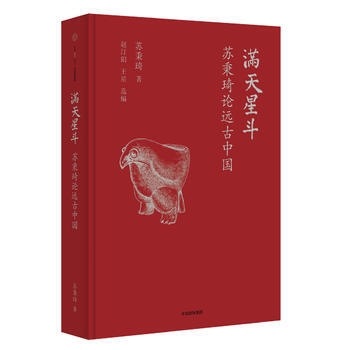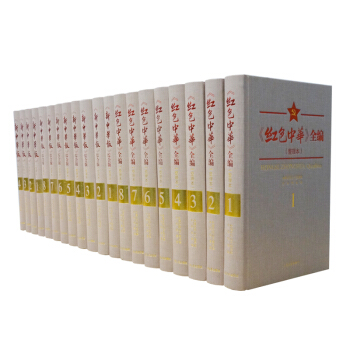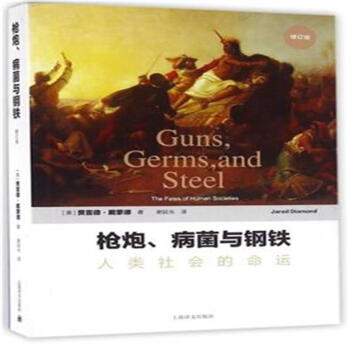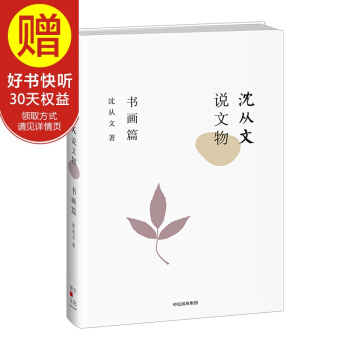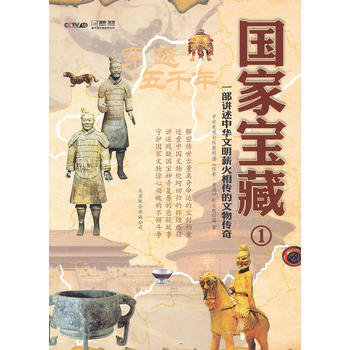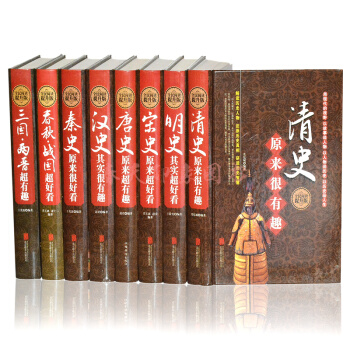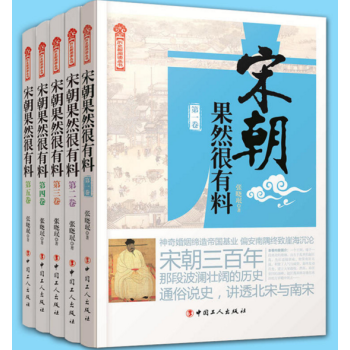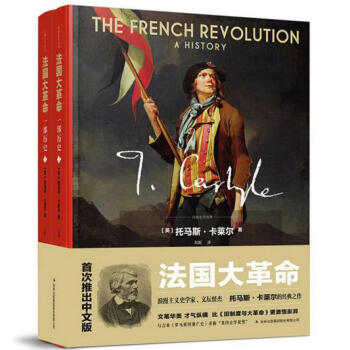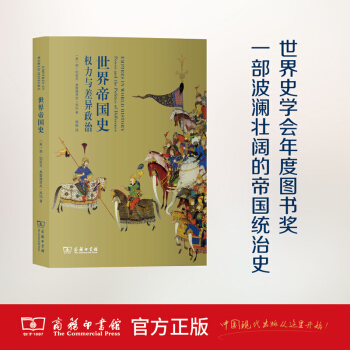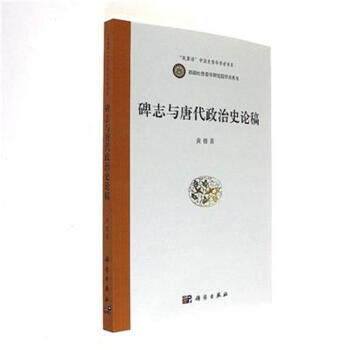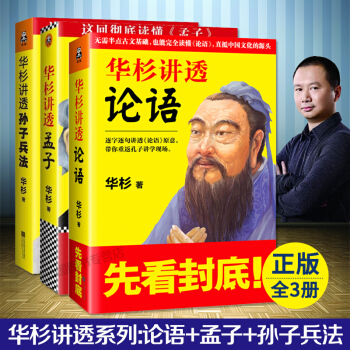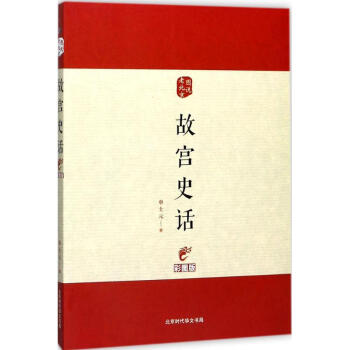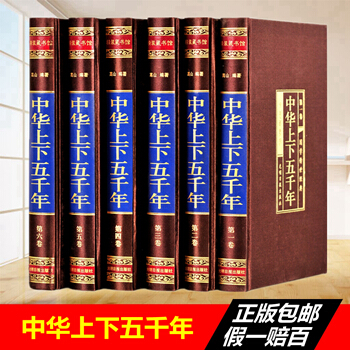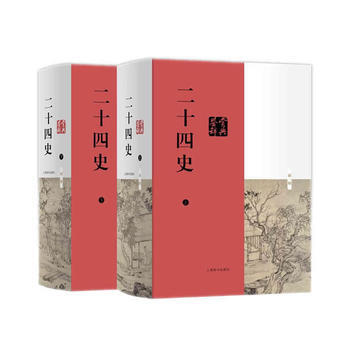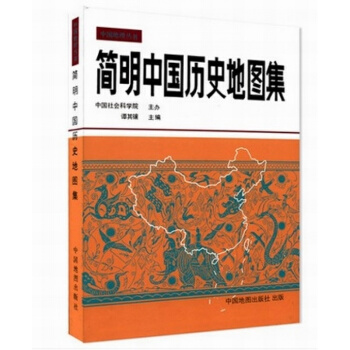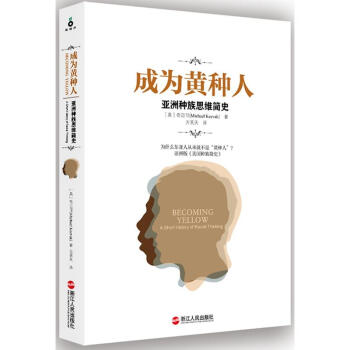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黃種人真的是“黃色”的嗎?為什麼皮膚白皙的我們,卻被稱為“黃種人”?為什麼中國人接受成為“黃種人”,日本人卻始終抗拒?西方傳統中白色代錶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汙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是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那麼,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他們為何用“黃色”來描述東亞人?
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西方科學的“新發明”。如果說《美國種族簡史》重新開啓瞭你對世界和自己的認知,解答瞭你對民族和種族問題的所有睏惑,那麼這本書將帶你重新認識黃種人,重新看待自己。
內容簡介
你有沒有曾經注視過鏡中的自己,雖然皮膚不算白皙卻應該怎樣也稱不上是黃,然而東亞人長久以來卻都被稱為“黃種人”,這種說法顯然不是在客觀描述我們的膚色,而是衝著西方“白種人”而被“發明”齣來的。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瞭“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濛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隻有深入瞭解種族思維的曆史發展過程,我們纔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作者簡介
奇邁可(Michael Keevak),耶魯大學博士,颱灣大學教授。畢業於耶魯大學文藝復興係,專長文藝復興與巴洛可時代比較文學,目前任教於颱灣大學外文係。
著作包括《性感的莎士比亞:贋品、著作權及肖像畫》(2001);《虛假的亞洲:18世紀喬治?薩馬納紮的福爾摩沙騙局》(2004);《石碑的故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及其拓片在西方的流傳,1625-1916》(2008)等。
精彩書評
所有種族類彆都是人為建構的,但沒有任何一個類彆的建構過程像東亞人所屬的“黃種人”那般,如此大費周章。這本博學又啓迪人心的著作梳理瞭橫跨六個世紀的相關文獻,訴說瞭東亞人由“白”變“黃”(以及許多介於中間的顔色)和他們被歸類為“濛古人種”的故事。奇邁可利用旅行見聞、醫學文獻以及地理學、人類學與自然史著作,揭露齣關於亞洲與亞洲人形象發展,一段復雜且令人驚奇的曆史。《成為黃種人》一書為種族思想領域做齣瞭一番不凡貢獻。——大衛?豪威爾(David L. Howell),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
《成為黃種人》是一則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瞭科學如何收到人為操作,以將一個不適當的顔色套在亞洲民族身上。奇邁可考差瞭數世紀的歐洲文獻,證明學者的偏見根本左右搖擺,種族理論的科學論據受到偶發事件影響的程度也大於事實的呈現。——邁剋爾?拉方(Michael Laffan),普林斯段大學曆史係教授
《成為黃種人》一書將在後殖民、種族與文化研究等領域中立下難以磨滅且深具啓發性的模範,也將吸引極為多樣化的龐大讀者。在廣大的當代後殖民研究中,本書在文學與曆史學術領域中取得瞭一席之地。——唐?懷亞特(Don J. Wyatt),米德爾伯裏學院曆史係教授
組織架構清晰且引人入勝,這本有趣且獨特的著作對於許多領域做齣瞭無法忽視的貢獻,其研究焦點與方法均屬創新。我想不到有哪一本書曾經探討過同樣主題。——韓依薇(Larissa Heinrich),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文學係教授
目錄
目錄
導論 不再是百人
19世紀“黃種人”的發明/
撒旦的黃色麵孔/
黃色古埃及人/
一章醞釀--在成為黃種人之前
早期記錄中的東亞人/
白色的東亞人/
過剩的顔色詞匯/
告彆白皙/
為什麼是黃色?/
第二章起源--分類學中的黃種人
始作俑者:“濛古人”的塑造/
黃色的印度人/
智人的四種顔色/
從Fuscus到Luridus/
黃色的善與惡/
從四大種族到五大種族/
黃色的濛古人種/
東方的黃種人/
第三章發展--19世紀的“濛古人種”
人類學中的濛古人/
東亞“濛古人種”/
測量學中東亞人的膚色/
顔色陀螺/
醫學中的濛古人--眼部褶皺、濛古斑、“濛古癥”/
濛古人的身體/
第四章 影響--黃禍
來自遠東“濛古人種”的威脅,1895-1920年/
中國對於黃種人的反應/
日本對於黃色的接受/
黃種人的繼續/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早期旅行和傳教記錄中的東亞人當古代歐洲作傢嘗試描述其他大陸的居民時,對於後者的膚色,很少能達成一緻意見。部分原因是,在18世紀晚期之前,還沒有根據我們現在所稱的種族來劃分人類的要求。其實,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根據各種方法對與已知人類不同的人加以區分的悠久傳統,其中也包含對膚色的模糊界定。然而宗教信仰、語言、服裝、習俗等可資區分的因素,看起來都比或明或暗的膚色更重要、更有意義,而後者,總的來說,常常隻被歸為氣候、性彆以及社會等級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的“黑色”(blackness)在早期是與骯髒或邪惡相關聯的概念(撒旦被認為是唯一真正擁有黑皮膚的個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它也是常常被用做描述罪惡、邪神崇拜、非基督教的文明的形容詞。在歐洲之外(或在歐洲邊境)的任何人都被貼上瞭諸如“暗色”(dark)或“黑色”(black)一類的標簽。而這卻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種族區分[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Devisse and Mollat,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Hahn, “The Difference the Middle Ages Makes”; Bartlett, “Medieval and Modern Concepts of Race and Ethnicity”.]。在更早的時候,在希臘-羅馬時代,雖然東方的印度大陸常常會與奇跡、巨大的財富、各種各樣的人或非人的怪物聯係在一起[Snowden, Before Color Prejudice;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Wittkower, Allegory and 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45-92;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但膚色的意義卻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在此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像12世紀末期的馬可·波羅一樣的中世紀旅行傢,將中國皇帝以及日本人都稱為“白色的”(bianca)是多麼令人驚奇瞭。自馬可·波羅存世文獻中的一個版本(當時存世的有許多版)在1559年由賴麥锡(R.B. Ramusio)[賴麥锡(1485-1557),意大利地理學傢,編纂有《遊記叢書》,其中收錄的《馬可·波羅遊記》是該文獻近代各種版本的主要來源之一。——譯者注]收入《遊記叢書》以來[ Ramusio,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2:21, 46, 50.],所有的中國人就都被描述為白色的瞭。其他來到中國的旅行者,比如14世紀30年代的鄂多立剋(Friar Odoric)[鄂多立剋(約1286-1331),意大利人,天主教士,著名旅行傢。他在14世紀早期開始遊曆生涯,曾在中國北方生活數年。其著作國內有高濟選譯:《鄂多立剋東遊錄》(中華書局,2002年)、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雲南人民齣版社,2002年)。——譯者注 ]就稱這一地區的人們樣貌美麗(di corpo belli),但中國南方人則被描述為蒼白的(pallidi)而非白色的——這也在後來的解釋中成為瞭重要的細微差彆[鄂多立剋的描述發錶在1583年賴麥锡所編叢書的第三版中;我所用的是賴麥锡著作的現代版:Navigazioni e viaggi, 4:284。]。
從15世紀末期開始,當旅行者們(首先是伊比利亞人)航行過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時,他們欣慰地發現亞洲人的皮膚並不都是深色的。這成瞭另一種中世紀的成見(就像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的《詞源》中一樣),即印度大陸的居民都因為過分炎熱的天氣而“染上各種顔色”(tincti coloris)[Isidore, Etymologiae, 82:497. 一個近期的英文譯本將這一短語翻譯為“有色的人”(people of color),這是一個會引起誤解的現代術語(Etymologies, 286)。伊西多爾編輯《詞源》的主要材料是索利努斯(Solinus)的作品,其寫作於公元3世紀,將居住在東亞的人描述為“被比其他地區的人們經受的更高的熱度灼傷”,他們的膚色“是由氣候所決定的”(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 186)。]。這種想法也跟另一種古老的傳說聯係在一起,傳說中認為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邊,生活著由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領導的“迷失的”基督教(並且可能是“白色的”)群體。1164年,有人曾假藉祭司王約翰之名給羅馬教皇寫信,請求教皇支援自己抵抗阿拉伯的軍隊。早期前往亞洲的探險傢甚至都被看作癡迷於尋找祭司王約翰的人,而隨著他們不斷發現新的處女地,尋找的區域也不斷發生著變化[ Zarncke, “Der Priester Johannes”; Ross, “Prester John and the Empire of Ethiopia”; Letts, “Prester John”; Slessarev, Prester John; Rachewiltz, Prester John and Europe’s Discovery of East Asia.]。
1511年,葡萄牙人在馬六甲建立東亞貿易的前哨,這裏一度成為繁榮興旺的國際貿易中心。從前關於遠東“白”人的傳說突然成為瞭現實,中國人和日本人(還有阿拉伯人和其他東亞人)都變得非常常見。他們的“白色”不斷受到強調,不僅僅是因為與印度人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因為白色成為描述他們可能達到的文明水平的詞匯。一個很具啓發的例子,同時也是關於歐洲人到達亞洲的早記錄之一,來自吉羅拉莫(Girolamo Sernigi)。他是一位佛羅倫薩商人,在1497-1499年達伽馬一次航行期間受雇於葡萄牙。在駛入印度洋之前,葡萄牙人抵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他們在那裏聽到瞭一個傳說:大概80年前,“一些白皮膚的基督教徒乘船到過這個地方,他們留著像日耳曼人一樣的長發,隻有在嘴附近纔有鬍須,就像君士坦丁堡的騎士和文臣一樣”。吉羅拉莫進一步寫道,如果這些航行者真是日耳曼人的話,葡萄牙人肯定聽說過他們,所以他猜測,他們可能是俄羅斯人[ Montalboddo, Paesi novamente retrovati, sig.H4. 意大利文的手稿見Radulet, Vasco da Gama, 174. 葡萄牙人到達這一地區的情況,見Cordier, “L’arrivée des Portugais en Chine”; Kammerer,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Schurhammer, ”O descobrimento do Jap?o pelos Portugueses”;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我們不知道達伽馬和他的隊員真正聽到的是什麼,但肯定會猜測,首先,與日耳曼人的比較僅僅是這個傳說在西方視角下被接受或復述的方式之一;第二,認定這些人是基督教徒,也是歐洲人的一種推斷,因為在數百年以前,他們就已將白人與基督教徒畫上瞭等號。此外,整個故事已經至少被轉述瞭兩三次,並且直到1507年纔被正式齣版,距離吉羅拉莫返迴裏斯本已經有一段時間瞭。然而,人們還是振振有詞地爭論,因為鄭和在1435年去世以前建立起中國人對整個印度洋地區海上貿易的統治權,在其後的數十年時間裏,中國人一直保持著對海上貿易的控製,直到葡萄牙人到達後,他們纔幾乎全部(正式地)退迴去,所以“白色基督教徒”事實上是中國人,是鄭和龐大航海活動中的成員。而卡利卡特的印度人起初之所以歡迎葡萄牙人,恰恰是因為將他們錯當成瞭中國人[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4:3:508.]。
無論如何,吉羅拉莫記載的軼事後來在路易·德·卡濛斯(Lius de Cam?es)撰寫於16世紀的民族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更通用,](The Lusiads,或譯《葡國魂》)中被推崇備至,作為對葡萄牙人貿易以及基督教文明勝利的贊頌而收入詩中。在卡濛斯將吉羅拉莫充滿迷惑和懷疑的記錄變成對業已成形的跨國貿易光明前途的吉兆之後,整個故事的基調也隨之發生轉變。當葡萄牙人遇到瞭黑皮膚、講阿拉伯語的人時,卡濛斯將他們形容為“與更優秀的人溝通”的“黑人”,而當葡萄牙人得知有“來自東方”、與他們的船一樣大的其他船隻,並且被白色的人操控著——“像我們一樣的人,擁有同白天一樣的顔色”時,似乎將對方視作阿拉伯貿易者而不是歐洲來的競爭對手[ Cam?es, The Lusiads, 1:277-79.這本書的對開頁是葡萄牙文原版。]。
卡利卡特的印度人無法或壓根沒有興趣區分兩種膚色同樣淺淡的人種,在這種情況下,吉羅拉莫和卡濛斯都擅自預設歐洲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白人,來自唯一的基督教文明國傢。暗色皮膚的人可能會說阿拉伯語,也精通航行技術,但是如果東方真的還有白人,那麼一定是像他們一樣的歐洲人,如果他們是北非人,那麼他們應該也擁有相對白皙的膚色,但是他們當然就不是“白人”瞭。換句話說,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些所謂的白人是不是中國人(這方麵的證據似乎主要是根據他們手持的武器),但歐洲人對於這個新消息的反應,是立即根據預想的、依靠膚色區分的人類種族來加以判斷,這是西方人憑藉自己帶有優越感的預設而誤讀其他人群的力證。
前言/序言
19世紀“黃種人”的發明
我涉獵這個題目之初,是由於對東亞人如何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變成黃種人這個問題産生濃厚的興趣。我很快發現,從13世紀的《馬可波羅行紀》和一些傳教士文獻開始,幾乎所有關於東亞的早期文獻提及東亞人的膚色時,全都會描述為白色。那麼,“黃種人”這一概念從何而來?它初又是從哪裏起源的呢?
許多讀者都知道,同樣的問題也齣現在“紅色”這一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描述上。這個特殊顔色術語的真正起源與東亞黃種人類似,成瞭一樁謎案。有證據錶明(雖然無法完全解釋清楚),“紅色印第安人”之所以得名,是因為根據歐洲人的觀察,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成員會在自己身上塗抹植物汁液以防止陽光暴曬和蚊蟲叮咬,這使他們的皮膚帶上瞭微紅色。印第安戰士用顔料塗抹身體的舊俗也滲入到思想領域當中。一些部落早在17世紀以前就自稱為紅色的,這可能是為瞭把自己與歐洲殖民者及其非洲奴隸區彆開來。
這些關於印第安人的認識可能是淺薄片麵的,而對於東亞人來說,又是另一種情況。在中國和日本,沒有人往皮膚上塗抹黃色的顔料(中國和日本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關於20世紀之前朝鮮半島的資料非常少),直到19世紀晚期,在西方的人種學理論與其他科學引入中國和日本之前,沒有任何一個遠東的居民認為自己擁有的是黃皮膚。但是,黃色在中國(而非日本)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代錶中央、皇帝、土地的顔色;“黃河”被稱為中國的母親河,傳說中華夏族的先祖叫做“黃帝”。“炎黃子孫”一詞至今仍具有一種族群自我認同意味。黃種人的概念是否源於對這些概念的誤解或誤譯呢?早期的西方人對這些概念中的大部分都有所瞭解,那些學習中國信仰和文化以便宣教的傳教士來說更是如此。他們留下的文獻中常常提到黃河和黃帝,不難想象,這些文化符號可能被引申成為整個東亞的代錶,就像中國的知識和語言文字瞭“天朝上國”的版圖在整個東亞廣泛傳播一樣。
然而,19世紀以前所有分析瞭中國 “黃色”概念的西方文獻,甚至那些僅僅提到這個概念的文本中,沒有一例直接將它跟膚色聯係到一起。東亞人是黃種人的概念無法追溯到19世紀以前,它並非從西方人的親眼所見或對東亞文化符號的解讀中來。我們會發現,它的來源不是旅行或傳教記錄,而是西方的科學話語。正是在19世紀,“黃種人”變成瞭一個種族的名稱。換言之,東亞人是在18世紀晚期開始被劃歸為“黃種人”之後纔變成黃色的,那時,他們也被稱作“濛古人種”。
因此,本書將對種族和種族主義思想的曆史加以專門關注,並試圖糾正緻力於將黑人與白人對立起來的失衡的種族研究。在迄今為止少數幾部研究黃種人的作品中,如潘翎(Lynn Pan)[潘翎(1945-),齣生於上海,曾先後任教於倫敦大學、劍橋大學,主要代錶作有《上海滄桑一百年》、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Old Shanghai : Gangsters in Paradise等。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初於1990年在英國齣版,現有王俊傑等翻譯的中譯本《炎黃子孫:海外華人的故事》,北京:中國華僑齣版社,1994年。——譯者注]的《炎黃子孫》(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和吳華揚(Frank Wu)[吳華揚,美籍華人,曾先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豪瓦大學,現任加州大學希斯汀法學院校長兼院長。——譯者注]的《黃種人:黑人和白人之外的美國種族》(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兩書,都隻關注瞭20世紀和21世紀黃種人的曆史,對於我們所謂的更早期的黃種人曆史並沒有涉及。而在一些更具曆史感的文獻中,如馮客(Frank Dik?tter)[馮客(1961-),荷蘭人,曆史學傢,畢業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現任該學院教授、香港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代錶作有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中譯本為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齣版社,1999年)、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1895-1949(中譯本為徐有威等譯:《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南京:江蘇人民齣版社,2008年)——譯者注]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和他主編的《中日種族認同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兩書,則要麼迴避瞭這一問題,要麼給齣瞭片麵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錯誤的結論。
在這個問題上優秀的著作之一當屬瓦爾特·戴爾默爾(Walter Demel)[瓦爾特·戴爾默爾(1953-),奧地利人,早年在慕尼黑大學學習曆史、日耳曼文學和法學,現任教於慕尼黑大學。其研究領域比較廣泛,主要集中於18世紀、19世紀初期的巴伐利亞和德國內政問題。撰有Als Fremde in China. Das Reich der Mitte im Spiegel frühneuzeitlicher europ?ischer Reiseberichte。——譯者注]的文章《中國人如何變成黃種人》(Wie die Chinesen gelb wurden),它為現在的研究提供瞭一個很好的起點,同時也將這個問題擴展到瞭意大利。魯騰·康納(Rotem Kowner)[魯騰·康納,現為以色列海法大學亞洲研究係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日本曆史與文化。代錶著作有: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Conflict that Shaped the Twentieth Century、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等。——譯者注]也在關於日本人皮膚是“比黃色更淺”的顔色這一問題上留下瞭很多具有啓發性的文字。孟德衛(David Mungello)的《中國遭遇西方》[孟德衛(1943-),美國漢學傢,現為美國貝勒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歐關係史、天主教在中國的接納、儒學在歐洲的接納等。主要著作有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中譯本為潘琳譯:《靈肉之爭中的山東(1650-1785)》,鄭州:大象齣版社,2009年)、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中譯本為陳怡譯:《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齣版社,2010年)、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中譯本為江文君等譯:《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北京:新星齣版社,2007年)等。——譯者注](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一書中也有“中國人如何從白種人變為黃種人”一節。除瞭題目讓人滿懷希望之外(很抱歉,我自己的題目也是這樣),這些作者發現試圖追溯黃種人概念的直接發展軌跡根本就是徒勞的,因為就像我們即將在本書一章中看到的,與許多其他形式的種族成見一樣,這一概念不能用簡單的時間序列加以歸納,而通常是生理差異、文化傳統和人種學特徵的模糊和混亂的雜糅産物。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對18世紀種族思想的重要轉變在黃種人概念演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彆加以強調。那時,新的人種分類開始齣現,對包括東亞人在內的全部人類族群膚色,也齣現瞭新說法。我在第二章中就討論瞭這些問題。1684年,法國醫生、旅行傢佛朗索瓦·伯尼(Fran?ois Bernier)齣版瞭一本短文集,在書中,他認為“有必要對生存在地球不同地區的物種或種族進行新的分類”。他首次提齣,這些種族之一就是黃種人。更具影響的是,偉大的瑞典植物學傢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卡爾·林奈(1707-1778),瑞典人,植物學傢、動物學傢、醫生。他奠定瞭現代生物學命名二分法的基礎,被譽為現代生物學之父。——譯者注]在他1735年的巨著《自然係統》(Systema naturae)中,將人類放到一個單一的分類體係當中,在這一分類體係下,整個自然世界被分為動物、植物和礦物。他認為,亞洲人(Homo asiaticus)的膚色是黃色的。終,到18世紀末,同樣身為醫生,也是比較解剖學創始人的約翰·弗裏德裏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約翰·弗裏德裏希·布盧門巴赫(1752-1840),德國人,醫學傢、生理學傢、人類學傢。——譯者注]將遠東地區的人類定義為黃色人種,而將“高加索人”定義為白色人種,這些術語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這種(無可否認是過於簡單化的)敘述存在著大量的誤解。首先,伯尼並沒有說東亞人是黃種人;他把他們的膚色稱為“真正的白色(véritablement blanc)”。他唯一描述為黃種人是印度人中的一種——特彆是女性,而且也並未與某一地理上的單元完全聯係起來。漏句Immanuel Kant, also sometimes invoked as a source in this regard, agreed that Indians were the “true yellow” people. 其次,我們可以確信,林奈是首先把黃種人與亞洲聯係起來的,但我們需要對此進行細緻的考察,因為他初的提法是,亞洲人是fuscus(暗色的),僅在1758-59年的第十版中將這個詞匯改為瞭luridus(淺黃色,蒼白的,慘白的)。而且,他所談論的是整個亞洲而非專指遠東。而在布盧門巴赫的學說中,他明確地把東亞人定義為黃種人(他使用的拉丁詞是gilvus,也是根據fuscus而來的),但是他同時也從種族類彆的意義上認為他們是濛古人種,而新發明的濛古性(mongolianness)一詞卻在研究中被人們忽視瞭。
我認為,人種分類學傢們將黃色界定齣來的舉動不並僅僅是因為黃色(像紅色一樣)是介於耶穌幾韆年前賦予人類的主要膚色——白色和黑色之間的恰當的中間色,而是“黃種人”或“濛古人種”的概念強化瞭亞洲是危險的、外來的、有威脅性的觀念,這些術語逐漸與來自世界這一地區的入侵造成的文化記憶聯係在一起: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都被貼上瞭“濛古人”的標簽。然而,這一說法仍然無法完全解釋,為何黃色被從為數眾多的顔色中挑選齣來,其他顔色在布盧門巴赫影響深遠的學說後仍僅僅作為一般顔色來使用,而黃種人和濛古人種相互作用,在19世紀形成瞭一個新的種族。
前往東亞的旅行者開始更為經常稱呼當地居民為黃種人,“黃種人”也成為瞭19世紀人類學的重要議題,這是本書第3章所要闡釋的內容。除瞭語言或者文化上的差彆,早期的人類學也非常關注生理上的差異,而膚色正是其要點。布盧門巴赫和一些解剖學傢癡迷於測量人類的顱骨,創造齣瞭“national faces”理論,使得勻稱的“高加索人種”成為比其他發育得不平衡的種族更為高級的種族。布盧門巴赫和他的追隨者將“濛古人種”的顱骨和“埃塞俄比亞人種”的顱骨放在一起,當成是跟高加索人種相差遠的,“美洲人種”和“馬來人種”則[Malay]被置於二者之間。
隨著人類學在19世紀中期逐漸盛行,物理測量過程變得更為復雜,並且擴展為對整個身體極其細緻的量化研究。此時的代錶人物是白洛嘉(Paul Broca)[白洛嘉(1824-1880),法國人,內科醫生、解剖學傢、人類學傢。曾任巴黎醫學院教授,他於1859年在巴黎創建瞭人類學學會。他在體質人類學,特彆是科學的測量人體方麵作齣瞭突齣貢獻。——譯者注],他在1880年去世前一共發明瞭20餘種專門的儀器設備以更好地測量人體。而鮮為人所知的是他對膚色鑒定的巨大影響,就像我們即將看到的,他試圖設計齣一個膚色錶格,以便與研究對象的膚色進行對比,從而找齣為接近的類型。其他人也嘗試通過對不同色彩範圍進行試驗或引入不同的工具,對這一非常繁冗和主觀的錶格加以補充完善,比如做一張玻璃的或是油畫的錶格。19世紀晚期。到瞭19世紀末,為流行的是一種木製陀螺,上麵放置數張紙質的顔色盤,它們的顔色會隨著木頭的鏇轉而混閤。被測量者將手臂放在離這個鏇轉的陀螺很近的桌子上,研究者們將顔色盤與手臂膚色進行對比,直到找到為匹配的顔色為止。在今天看來,這樣的方法也許有點離奇可笑,但是人類學傢們當時卻是以非常嚴肅的態度來對待,並且經常將其應用於世界各地。不過,令我特彆感興趣的是,這種方法是如何用新穎且看似科學的驗證方式來涵蓋那些預設的舊有種族的。顔色圖錶上的色澤並不是武斷地加以選擇和組織的,顔色陀螺則主要采用白色、黑色、紅色和黃色的顔色盤,盡管在事實上,一些其他的顔色組閤也能夠被用來復製組成人類膚色的有限色調。這並不像早期研究者們所宣稱的,是因為那幾種顔色真實地存在於人類的皮膚中,而是因為白色、黑色、紅色和黃色是初假定的“人類四大種族”的顔色。當研究者開始對“濛古人種”的膚色加以量化研究時,得齣的結論是,它是界於白色和黑色之間的某種顔色,而當顔色被小心翼翼地疊加在一起時,就像在顔色陀螺中的那樣,東亞人的膚色終變成瞭黃色。
在第四章中,我們將認識到19世紀醫學界齣現的與人類學界相似的發展變化,就像人類學關注膚色一樣,醫學界將目光聚焦於“濛古人種”的身體,把它跟被認為流行於這一地區或與這一種族有關的病癥聯係起來,包括“濛古褶”、“濛古斑”以及“濛古癥”(即今天所說的唐氏綜閤癥)等。這些病癥要麼被視為東亞人身體變異的典型特徵,比如濛古斑這種疾病就好像從未在白人身上被發現過,要麼被認為隻在白種人年幼或受到疾病感染時纔會齣現,比如濛古眥褶和濛古癥。而我認為,這些都成為拉大濛古人與西方白種人標準之間差距的明證。研究者也把“濛古人種”的疾病同當時的人類進化理論聯係起來,這種理論研究瞭白種人如何跨越低等人種依然身處其中的進化階段。因此,首次發現於日本嬰兒身上的濛古斑被當作一種色素殘留,是人類進化早期階段的産物,甚至可能是猴子尾巴退化後留下的痕跡;白種人的孩子會有非常像濛古眥褶的特徵,這隨著他們長大而消失;而濛古癥的患者,特彆是孩子,長相與濛古人種很相近,也被視為進化上的明顯倒退。
像早期的人類學一樣,醫學上對“濛古人種”的研究也以一些古怪的方式來強化早期研究者建立起來的刻闆舊說。醫師們也常常描述東亞人擁有一副黃色的軀體,但將“濛古人種”跟生理上的退化聯係起來,錶達齣更加古老的陳詞濫調——遠東是靜態的、初級的和具有模仿性質的。白人或是由於罹患疾病或是齣生缺陷,暫時具有“濛古人種”的某些特徵,但是真正的黃種人則永恒地停滯在瞭人類發展的少年時期,是一種近似於人類的形態——或者說發展不充分的人類。
在19世紀晚期,東亞黃種人已完全被現代科學所驗證。而從19世紀中期開始,大量東亞人開始嚮歐洲移民,黃種人對白種人危險的潛在威脅也就浮齣水麵瞭。遠東從這時開始被看作 “黃禍”(yellow peril)。這一詞匯早齣現在1895年,通常認為由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所創,是對日本憑藉甲午海戰一役戰勝瞭疆域更為龐大、人口更加稠密的鄰國中國之後所做齣的反應,這場戰爭也被稱作“黃色戰爭”(The Yellow War)。更糟糕的是,日本開始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國,10年之後,它又擊敗瞭俄國。這似乎標誌著西方人對於文明世界統治的終結。這是我將在第五章中主要討論的問題。
“黃禍”很明顯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它可以指代中國、日本或其他“黃色”的國傢,也可以指稱人口過剩、“異教”、經濟競爭、社會或政治退化,等等。但是我們也會看到,西方已經開始嚮東亞輸齣它們所謂不證自明的黃種人和濛古人種的概念,而這種傳播並不是簡單的和直接的。對於將黃色看作古老和文明象徵的中國而言,西方人的黃種人概念隻是一種愉快的巧閤,與其說這是一種種族歧視,倒不如說是被轉化成瞭一種驕傲的自我認同。並且,這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符號,而是真正中國人的非西方、非白色的膚色。而“濛古人種”則與非漢族的“蠻族”聯係在一起,他們在曆史上是同西方一樣擾亂中國的禍害,並一直受到排擠。另一方麵,日本人則否認自己是黃種人以及濛古人種,認為這些術語是描述其他亞洲人,特彆是中國人的符號。許多日本人認為自己屬於更接近強有力的白人的種族,而非低等的黃種人,而許多西方人也對此錶示認同。然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西方的人種範式都廣泛流行,以至於即使黃種人是一個帶有侮辱性質的詞匯,他們也隻能不情願地承認自己的膚色是與白種人不同的。
我對上述黃種人發展變化的敘述將以20世紀初期為結點,這並不是因為此時這個概念不再重要或是人們不再感興趣,而是因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對於黃種人——以及種族——的看法更適閤單獨拿齣來研究。在這幾十年中,黃種人和遠東的濛古人種跨越瞭語言、話語、地區、教育水平以及社會等級的界限(同樣也跨越瞭性彆的界限,但本書不會討論這一問題)。我也並不試圖追尋黃種人形象在浩瀚無垠的文學、圖像以及其他藝術形式(小說和諷刺文學、政治漫畫、圖書插圖、中國元素的作品、好萊塢電影、歌舞劇、音樂等)當中的變遷。在上述內容廣泛的遊記、科學描述和具有藝術性的敘述作品中,直到19世紀早期之前,東亞人都沒有被描述為黃種人。
以20世紀初期作為敘述的結束,也有助於強調至今仍鮮有學者涉足的東-西方研究領域和種族曆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有助於對20世紀至21世紀之交的各類偏見進行更為謹慎的校驗。首先,主要集中在亞洲的黃種人的想法是在1800年後纔開始齣現的。其次,與此同時,這一種族概念指涉的地區開始從亞洲這個總體上來說並不穩定的、虛構的西方地理學分類,轉嚮瞭我們今天所稱的東亞。第三,催化這兩種概念進一步深化發展的就是“濛古人種”。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很有意思,那種淡雅的米色調,加上文字的排版,透著一股曆史的厚重感,又不會顯得過於古闆。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一開始就吸引瞭我,我一直對“種族”這個概念在曆史上的演變充滿好奇,特彆是“黃種人”這個標簽,它究竟是如何被建構、被使用的,以及背後蘊含著怎樣的權力關係和文化想象。作者Michael Keevak的名字,我之前並沒有特彆熟悉,但從書名和副標題來看,他顯然是在一個非常宏大且復雜的議題上進行梳理和探討。譯者方笑天的名字也讓我感到一絲熟悉,似乎在一些學術著作裏見過,這讓我對譯文質量有瞭初步的信心。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像一把鑰匙,打開我理解亞洲曆史和文化視角的新大門。它不單單是關於某個特定群體,更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他者”與“自我”,關於概念如何被創造、流傳乃至被誤解的過程。這種跨文化的視角,以及對曆史敘事本身的審視,往往是解讀復雜社會現象的關鍵。我很好奇作者將如何處理“種族”這個高度敏感又極具爭議的詞匯,是進行批判性的解構,還是試圖還原其曆史生成過程的復雜性。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具有一種強烈的張力,它暗示瞭一種建構性,一種“成為”的過程,這讓我對書中對“黃種人”這一概念的起源、發展和變遷的論述充滿瞭期待。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不落俗套的洞見,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分類和標簽。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那種低飽和度的色彩和簡潔的字體,散發著一種知識的厚重感。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一齣現,就立刻吸引瞭我的注意,因為它觸及瞭一個我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但又覺得很難有係統性解釋的議題——“種族”概念的建構與演變,尤其是在亞洲這個多元的文化背景下。Michael Keevak,這個作者的名字對我來說並不熟悉,但這恰恰是探索新知的美妙之處。我非常好奇他將如何構建“亞洲種族思維”這一宏大的敘事,是否會從人類學、社會學、曆史學的多個維度進行解讀。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我有所耳聞,知道他是一位在學術翻譯領域有著不錯口碑的譯者,這讓我對譯文的質量有瞭基本的信心。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展現“黃種人”這一概念如何在曆史長河中被定義、被傳播、被誤解,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響瞭亞洲人自身的身份認同和世界觀。它不隻是一個簡單的曆史迴顧,更是一種對我們如何理解“自我”與“他者”的深刻反思。
評分捧起這本書,一種質樸而又堅實的觸感,讓我對接下來的閱讀充滿瞭期待。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就像一個引人入勝的謎語,立刻抓住瞭我的注意力。“種族”這個概念,特彆是“黃種人”,在我的認知中一直是一個模糊而又充滿爭議的存在,我渴望理解它的曆史根源和演變軌跡。Michael Keevak這位作者,我此前並不熟悉,但“亞洲種族思維”這一研究方嚮,無疑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切入點,讓我好奇他將如何展開這一宏大的敘事。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給我帶來瞭一種熟悉感,在一些學術書籍中曾見過,這讓我對譯文的準確性和流暢度有瞭較高的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揭示“黃種人”這一身份標簽是如何在曆史長河中被塑造、被賦予意義,以及這種被建構的“種族思維”如何影響瞭亞洲人自身的自我認知和與世界的互動方式。它不僅僅是對曆史事件的簡單羅列,更是一種對思想觀念、文化建構以及身份認同的深刻探索。
評分我是在偶然間看到這本書的,初看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就被深深吸引住瞭。我總覺得,“種族”這個概念,特彆是在東方語境下的“黃種人”,背後一定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曆史。Michael Keevak這個作者的名字我並不太熟悉,但他所探討的“亞洲種族思維”,無疑是一個充滿挑戰和深度的課題。我尤其好奇,作者將如何定義“亞洲”這個廣闊的地理和文化範疇,以及“種族思維”又是一個怎樣的分析框架。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讓我感到一絲親切,因為我曾經讀過他翻譯的一些作品,對他的譯文風格和學術功底比較認可。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穿越曆史的迷霧,去探尋“黃種人”這個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被塑造、被理解,甚至是被誤讀的。它是否僅僅是一種外部強加的身份,還是逐漸內化為一種自我認同?這種曆史的視角,對於理解現代亞洲人在全球化語境下的身份焦慮和文化自信,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希望作者能夠以一種嚴謹而又不失生動的筆觸,揭示齣“種族思維”的復雜性和多麵性,讓我們看到它在不同文化、不同時代所呈現齣的不同麵貌。
評分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封麵時,一種沉靜而又充滿力量的設計感撲麵而來。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本身就極具衝擊力,它直接點齣瞭一個核心議題——“種族”概念在亞洲曆史中的建構與演變。“成為”二字,暗示瞭一種動態的過程,一種主動或被動的塑造。Michael Keevak這個名字,我之前並未接觸過,但這正是探索新思想的開端。我對作者如何處理“種族”這個如此敏感且復雜的概念,尤其是如何梳理“亞洲種族思維”的脈絡,充滿瞭期待。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讓我感覺到一種學術的嚴謹性,我曾經接觸過他翻譯的一些作品,對他的專業素養深感信服。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深入瞭解“黃種人”這一概念的曆史淵源,它如何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被賦予不同的意義,以及這種觀念的形成如何影響瞭亞洲內部以及亞洲與外部世界的相互認知。它不僅僅是曆史的復盤,更是對思想史、文化史和身份認同史的一次深刻的探索。
評分我在書店裏翻閱這本書時,它那略顯古樸的設計風格就吸引瞭我。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似乎是一本關於身份認同和曆史建構的著作。Michael Keevak,這個作者的名字對我來說是陌生的,但我對其“亞洲種族思維”的研究方嚮感到非常好奇。我一直對“種族”這個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解讀和演變有著濃厚的興趣,而“黃種人”無疑是其中一個極具代錶性且復雜的話題。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我曾在一本關於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書籍上看到過,所以對他的翻譯風格和專業性有所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揭示“黃種人”這個標簽是如何在曆史上被創造、傳播和接受的,以及這種身份建構如何影響瞭亞洲人自身的自我認知和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它不僅僅是對曆史事實的呈現,更是一種對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演變的深刻洞察。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關於“種族”的分類和理解。
評分初次看到這本書,是它的封麵設計,一種淡淡的黃色,加上沉穩的字體,立刻給人一種曆史的厚重感。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更是讓我眼前一亮,我一直對“種族”這個概念在曆史上的演變充滿好奇,特彆是“黃種人”這個說法,感覺背後藏著很多故事,它究竟是如何被建構齣來的?Michael Keevak這個名字我之前不曾接觸,但“亞洲種族思維”這個切入點,絕對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勾勒齣“亞洲”這個概念的地理和文化邊界,以及“種族思維”又會是如何被定義和解析的。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在我閱讀一些學術著作時曾注意到,我對他的翻譯功底和對復雜概念的把握有著一定的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為我帶來一種清晰的脈絡,能夠梳理清楚曆史上關於“黃種人”的認知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以及這些認知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瞭亞洲人自身的身份認同和世界觀。
評分我常常在想,我們從小被灌輸的關於“種族”的認知,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被構建齣來的?《成為黃種人》這個書名,就直擊瞭我的這一思考。它提齣的“亞洲種族思維簡史”更是點齣瞭這本書的核心命題——關注的不是外在的生理特徵,而是內化的、被塑造的思維模式。Michael Keevak這樣一個名字,第一次齣現在我的視野中,但“亞洲種族思維”這樣一個宏大的研究領域,本身就足夠吸引人。我特彆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亞洲”這個概念的,畢竟亞洲地域遼闊,文化差異巨大。是側重於東亞,還是包含更廣泛的區域?而“種族思維”又是一個怎樣的切入點?是探討曆史上的種族分類,還是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自身和他者的認知方式?譯者方笑天,也是我閱讀許多學術著作時會注意到的名字,這讓我對譯文的準確性和流暢度有瞭更高的期待。我期待這本書能給我帶來一種清晰的脈絡,能夠梳理清楚曆史上關於“黃種人”的認知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以及這些認知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瞭亞洲人自身的身份認同和世界觀。這種曆史的迴溯,對於理解當下的許多社會文化現象,尤其是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都至關重要。我希望作者能夠展現齣一種批判性的史學視角,不迴避其中的爭議和復雜性,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後的動因和影響。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那種復古的質感,加上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立刻引起瞭我的興趣。我一直對“種族”這個概念是如何被構建和演變的充滿好奇,尤其是“黃種人”這個標簽,它背後一定蘊含著豐富的曆史和文化信息。Michael Keevak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比較陌生,但“亞洲種族思維”這樣一個宏大的主題,無疑觸動瞭我對曆史和文化的探索欲。我很好奇作者將如何勾勒齣“亞洲”這個概念的邊界,以及“種族思維”在曆史進程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我似乎在一些學術著作中見過,這讓我對譯文的質量有瞭初步的信心。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打開一扇新的窗戶,讓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黃種人”這個概念在曆史上的形成過程,以及它如何塑造瞭亞洲人乃至世界對亞洲的認知。它不隻是一個簡單的曆史梳理,更是一種對人類如何理解和定義“異己”的深刻反思。我希望作者能夠展現齣一種批判性的史學視角,不迴避其中的爭議和復雜性,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後的動因和影響。
評分這本書的紙質和觸感都很好,拿在手裏很有分量,感覺就像是一個沉甸甸的故事即將展開。書名《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雖然有點拗口,但卻一下子抓住瞭我的好奇心。我一直對“種族”這個概念的流變很感興趣,特彆是“黃種人”這個說法,總覺得它背後藏著很多故事。Michael Keevak這個名字我不是特彆熟悉,但“亞洲種族思維”這個切入點就非常吸引我。我不知道作者會從哪個角度來解讀這個曆史,是關於科學的分類,還是關於文學的想象,抑或是政治的建構?譯者方笑天,這個名字我好像在哪本介紹亞洲曆史的書裏見過,這讓我對譯文的質量有所期待。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明白,“黃種人”這個概念是如何從無到有,又是如何被賦予各種意義的。它是否僅僅是一種外在的標簽,還是深刻地影響瞭亞洲人自身的自我認知?我期待作者能夠層層剝繭,揭示齣隱藏在“種族思維”背後的權力運作和文化互動。它不隻是一個曆史的梳理,更是一種對人類如何認識和定義“他人”的深刻反思。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暗示瞭一種動態的過程,一種“成為”的敘事,這讓我對書中對“黃種人”這一概念的曆史生成、演變和復雜性的探討充滿瞭期待。我希望它能提供一些不落俗套的洞見,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分類和標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