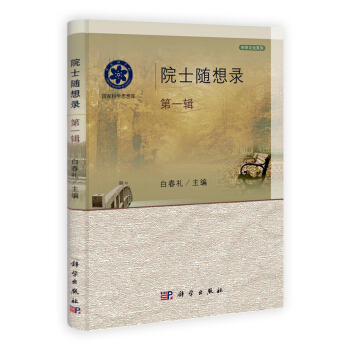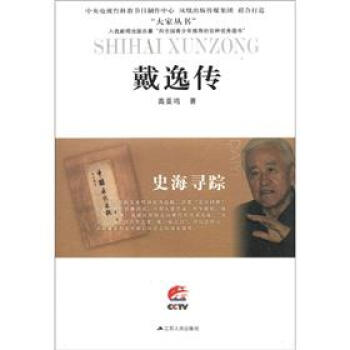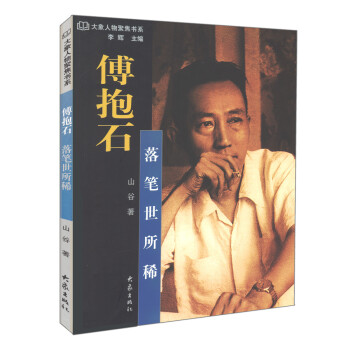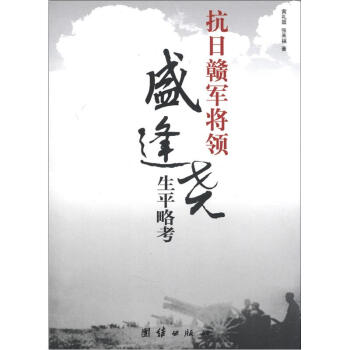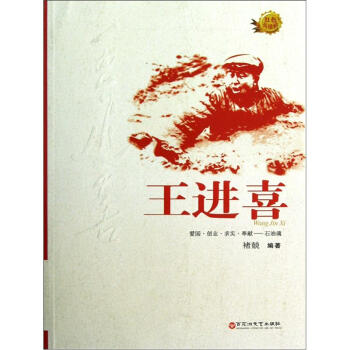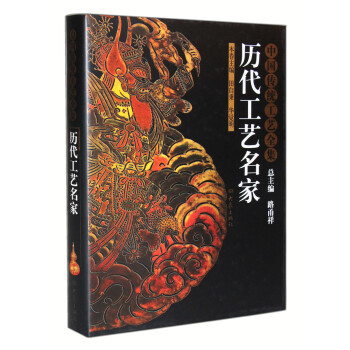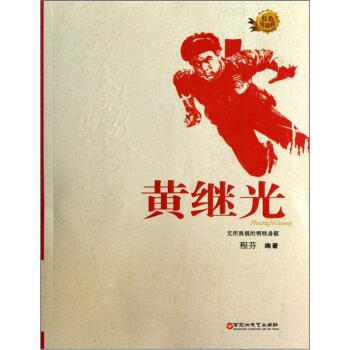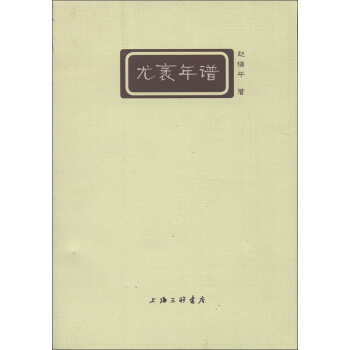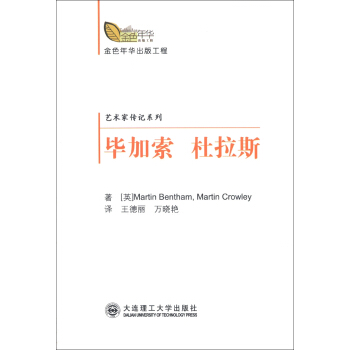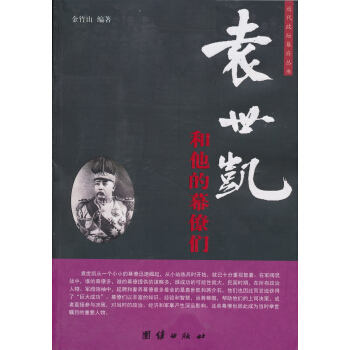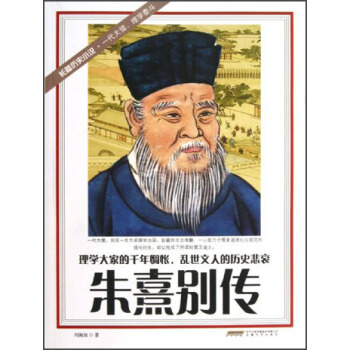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内容简介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作者简介
耿传明,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学术著作有《新时期文学思潮概论》、《独行人踪——无名氏传》、《现代性的文学进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轻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周作人的最后22年》、《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等。目录
引言鲁迅:现代文化的“创世英雄”/001
第一章 故乡记忆与文化渊源/013
1.“居移气,养移体”/014
2.儒、道、墨、释之间/033
3.门第、家世与“遗传”/039
第二章 “英哲之士”与“大独”人格/057
1.“私学”:作育“大师”的文化温床/059
2.“学堂”:制造“人才”的教育工厂/093
3.“帝国之眼”的凝视与超乎国族的立场/097
第三章 苏生与毁灭之间的二元选项/119
1.“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紧张和对立/125
2.个人感情生活的灰暗与亮色/153
3.“借琐耗奇”与颠覆及构建/165
4.“跟上时代”与“四面受敌”/175
5.小说:改造人生与“苦闷的象征”/180
6.杂文:“寸铁杀人”与“活体解剖”/200
7.散文、散文诗:幽深峭拔与独出机杼/203
第四章 “寻找革新的破坏者”/209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鲁迅与授业弟子/210
2.“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鲁迅与文学社团/252
3.“真的恶声”——高长虹其人/270
4.“朝花社”和柔石/286
第五章 “衣钵弟子”与“精神朝圣”之旅/297
1.“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胡风/301
2.“识得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只愁”——冯雪峰/325
3.“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聂绀弩/348
4.“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萧军/364
结语/399
后记/410
精彩书摘
至于礼治文化之下的旧家族是不是只有阴风凄凄、鬼气森森的狰狞一面.也不尽然,它与个人的性格气质,境遇遭际有关,即使是同一文化习俗之下,人对之的感受、体验也会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那种认为一种文化下只有一个“典型”的想法是源于文化决定论的简单化的观念。同是从旧式大家庭中长大,有人的感受就与鲁迅等大不相同。同是五四青年、留美多年又以研究中西政治为业的政治学家萧公权,尚未满月之际,母亲就猝死,以姑为母;长到6岁时,祖父又去世;12岁时,父亲再去世,改由大伯抚养;等其到上海求学时,则是由二伯父照顾。所以他说:“余虽早失双亲,仍得教养成人,拜旧家庭之赐也。”从这种自身体验出发,他在《问学谏往录》中认为…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因为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传统大家庭的存在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缺乏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只有集大家庭之力,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因此相对于生存的需要,其他都只能放置一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鲁、郭、茅、巴、老、首”中,竟然有四位都是早年丧父.1949年前后中国人平均寿命才35岁左右,民国初年更低,没有家族的照顾,失去父母的孤儿存活下来会极为困难。在社会保障阙如的情况下,家族实际担负起了这种社会责任。但既然家族出力将其养大,他自然须对家族尽相应的职责,所以明代李贽在云南当知府时,故乡遭灾,族中上百口到云南找他吃饭,使他大受其苦,但叉无可奈何,
再则对礼治的理解既往也有偏颇和简单化倾向,礼治是因礼而治,并非在上者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而在下者只能忍气吞声、哭告无门,上下的行为必须都符合礼,才具有合法性,所以它对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像鲁迅的祖父介孚公在礼治之下也并非总能孤行己意,为所欲为,周冠五的回忆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介孚公与他的续弦蒋夫人关系非常紧张、冷淡,他将“蒋夫人”称为“长毛妇”(因为其曾被太平军掳掠),经常辱骂。他在金溪做县令时,曾把全家都带去赴任,但是他总是与妾同住,不理会夫人,蒋夫人有一次听窗,结果还被介孚公骂作“王八蛋”。蒋夫人也不甘示弱,第二天设计邀婆婆戴老夫人同往.结果介孚公又骂”王八蛋”,蒋夫人马上说:“母亲在这里,你敢骂母亲是王八蛋!”介孚公即刻出去跪倒,但戴老夫人已因为意外挨骂,痛哭失声!后来介孚公被免职,据说也与此事有关。
还据周冠五记述,周福清其人个性极强: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昔,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于己意、琐碎啰嗦,奴奴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下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份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么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昕,非至其词罄不可。
周福清这种个性也使他吃亏不小,一次他与上司争吵,知府搬出皇上来压他,他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皇上。”结果以“大不敬”被参。
介孚公一辈子不吸烟、不喝酒,尤恨鸦片。严以律己也同样严以责人,所以得罪的人也多,儿子周伯宜去世,他写挽联道:“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这个挽联引起了鲁迅极大的不满,对弟弟说:“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看来介孚公的“词典”里的确没有收入“饶恕”二字。
介孚公给家庭带来的最大的灾难就是“科场舞弊案”,这场巨大的家庭变故不但使周家迅速没落,也使少年鲁迅经历了由“王子”到“乞丐”的巨大的命运反差,并影响到其一生看待世界的基本眼光和立场,也可以说此事构成了初涉世事的鲁迅“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是鲁迅成为“鲁迅”的第一个关键事件。事件的原委据周作人的记述是这样的:1893年,周介孚因母亲戴老夫人去世,从北京赶回绍兴奔丧。这一年是光绪十九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章可能是同年吧,周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当然另有报酬。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兄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实际不是徐福,而是陶阿顺,东家派来帮忙的一个家丁,对此事完全不知情,又比较固执、迟钝,事情就出在他身上,也与介孚公考虑欠周、粗心大意有关)将信附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黔正在主考的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收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
P44-46
……
前言/序言
总序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 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 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 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 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 “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 “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 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 “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 “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 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 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 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 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 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5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 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立场,使他成为现代中国重“问题”不重“主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不少的追随者,以傅斯年、顾颉刚等最为著名。 在学术上,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针,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引、示范作用。 至于周氏兄弟,则分别是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和巨石重镇。 鲁迅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去世时获得了中国“民族魂”的盛誉,围绕他的鲁门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在现代文学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色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鲁迅不同的选择,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这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向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靠拢,他其后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褪掉“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走向平和冲淡,苦涩闲适。 在他身边,围绕着俞平伯、废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带有闲适、冲淡、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周作人又是中国民俗学、古希腊文学、明清文学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继承并发展其民俗学研究的弟子有江绍原,继承其明清文学研究的则有沈启无等。 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是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上急剧“西进东退”的时代,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一生为故国招魂”,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国人必对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对其时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和批驳。 他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是否在现代还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大时代问题,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的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等也都成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学者。
古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选择老师、朋友时,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师生关系也是如此。 特别是私学传统中在师生双向选择下形成的师生关系,更是一种情同父子的关系,选择什么人为师,也就意味着对为师者的志向、人格、学问的整体性的尊崇和认同,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学生对老师有一种孺慕之情,而为师者对学生担负的是与父母一样甚至大于父母的责任,所以这种私学传统中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一种犹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的文化群落。 每个师徒群体自有其特质,成员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价值观比较相近,在思想行为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成员对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种师徒群体的存在除有利于他们勠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之外,还具有满足其群体成员的多种需要的功能,如使群体成员满足亲和与认同的需要,满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心和力量感。 学生为自己所属的师徒群体感到自豪,为师者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提携扶持,不遗余力。 像胡适的弟子罗尔纲专门写了一本书《师门辱教记》,十分动情地回忆了在胡适门下五年得到的言传身教。 胡适对弟子的这本小书也十分看重,曾说此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的 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大。 直到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还自费印行了这个小册子,分赠亲朋。 再如萧军直到晚年还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我是鲁迅的学生!”当别人问他20世纪30年代文坛宗派有哪些时,他的回答是:“别人有没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但是我萧军有宗派———‘鲁宗鲁派’!”①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 这种知识群体中的师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亲密、融洽的,但师生之间也会出现龃龉,像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立场上截然对立、公开辩难,梁启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师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这使得一向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大为光火,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并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当然,两人多年的师生关系、患难之情并不会就此割舍,事过境迁后,仍会重修旧好,做学生的还是要向老师表示歉意和依顺。 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为不满于老师章太炎赞成“讨赤”,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不再认章太炎先生为师。 这虽然从师生感情上来看不无遗憾之处,但也可从中看到现代个人独立意识对于传统单向服从性的师生关系的突破。 与此相应的是为师者将学生革出师门的事也时有发生,像鲁迅之于高长虹、周作人之于沈启无等,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提示我们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发表作品的报纸、杂志多带有同人的性质,社会文化资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 所以被革出师门的沈启无等于被驱逐出了文教界,一时间只能靠变卖东西为生;高长虹则因为受了鲁迅的迎头痛击,长期被视为文坛异类,声名狼藉。 总之,以这种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为单位,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现代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对我们深入了解近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①,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 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 ……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 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①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 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 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 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 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的、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 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入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用户评价
翻开一本以“鲁迅与鲁门弟子”命名的书籍,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回到了那个思想激荡、文字铿锵的年代。鲁迅先生,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代表着对黑暗的批判,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对未来的深切关怀。而“鲁门弟子”,这四个字则引人遐想,那些曾经站在鲁迅先生身边,深受其思想影响,并在文学道路上留下了独特印记的先行者们,他们的故事必定精彩纷呈。我迫切地想在这本书中,看到鲁迅先生是如何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深刻的思想,孕育出如此一批才华横溢的弟子。也许书中会描绘他们之间关于文学创作的辩论,关于社会现实的讨论,以及在艰苦岁月里,他们如何相互鼓励,共同前行。我尤其好奇,这些弟子们是如何在吸收鲁迅先生精神内核的同时,又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鲜活的时代气息和个人体验,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理解鲁迅先生思想影响力的绝佳机会,也是一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群体的致敬。
评分一本关于鲁迅先生的书,光是书名就让我心生好奇。鲁迅,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太响亮了,他的文章如同匕首,直指社会的阴暗,他的思想,至今仍能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而“鲁门弟子”,这几个字更是勾起了我的想象,那些曾经追随鲁迅先生,受他思想熏陶,并在文学道路上有所成就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一定非常精彩。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看到鲁迅先生作为一位师者,是如何以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引导和塑造了一批批年轻的灵魂。或许书中会描绘鲁迅先生在课堂上的身影,亦或是他与弟子们在日常交流中的点点滴滴。我尤其想知道,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鲁迅先生是如何将他的思想火种播撒出去,又是如何激励这些年轻一代去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继续为民族的觉醒和社会的前进而奋斗。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关于一位伟大作家,更是关于一种传承,一种精神的延续。我相信,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以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评分当我在书店看到《鲁迅与鲁门弟子》这本书名时,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便油然而生。鲁迅,这个名字本身就承载着太多的意义,他的思想,他的文字,他的斗争,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的进程。而“鲁门弟子”,这四个字更是像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门,门后是那些曾经追随他,受他感召,并在文学和思想领域闪耀过的名字。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描绘出鲁迅先生作为一个精神导师的形象,他如何以他独特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书中或许会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师生间的交流,那些在困境中互相扶持的瞬间,以及在思想碰撞中产生的火花。我尤其想知道,这些“鲁门弟子”们在继承鲁迅先生精神的同时,又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见解,他们的创作又为那个时代带来了怎样的色彩。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对一位伟大作家及其追随者的记录,更是一次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追溯,一次对思想传承的深刻探讨。
评分读到一本以“鲁迅与鲁门弟子”为题的书,自然会让人联想到那个充满思想碰撞与文学创新的时代。鲁迅先生,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精神的符号,一种不屈的斗志,一种对现实深刻的洞察。而“鲁门弟子”,这四个字又像是一扇门,门后隐藏着一群曾经沐浴在他思想光辉下,并因此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文人墨客。我设想着,书中或许会细致地描绘鲁迅先生与他的弟子们之间的师生情谊,那种既有学术上的严谨探讨,又不乏生活中的温情关怀。也许会有这样一些场景:在寂静的书房里,鲁迅先生伏案疾书,他的弟子们围坐一旁,认真聆听他的教诲;抑或是在某个公共场合,鲁迅先生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他的弟子们眼中闪烁着敬佩与兴奋的光芒。更重要的是,我期待这本书能展现这些弟子们是如何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思想体系,并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里,延续着鲁迅先生那份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怀。这不仅仅是关于文学史上的一个侧面,更是关于一群人如何被一位伟大的灵魂所启迪,并最终成长为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评分对于一本名为《鲁迅与鲁门弟子》的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它触及了一个极具深度和广度的文学话题。鲁迅先生,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战士。他的文字,至今仍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而“鲁门弟子”,这让我联想到的是那些曾经围绕在他身边,受其思想指引,并在文学道路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我猜想,书中大概会细致地梳理出鲁迅先生的学生群体,并逐一介绍他们的文学成就和思想渊源。或许会重点讲述几位代表人物,比如那些在左翼文学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弟子,他们的创作是如何体现鲁迅先生的精神内核,又是如何挑战当时的社会现实。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展现鲁迅先生作为一位导师的独特之处,他是否会鼓励弟子们独立思考,挑战权威,抑或是如何在困境中给予他们支持与力量。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重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机会,更是一次深入理解鲁迅先生思想影响力及其传承的绝佳途径。我希望通过阅读,能够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