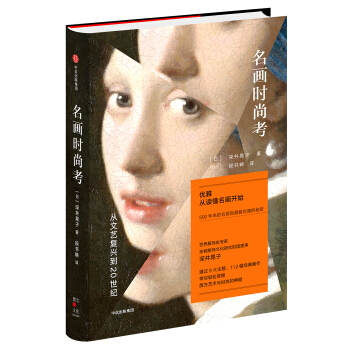繪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圖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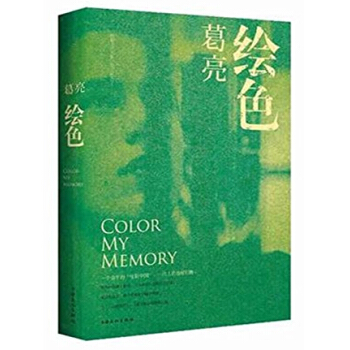
發表於2025-05-30
類似圖書 點擊查看全場最低價
店鋪: 英典圖書專營店
齣版社: 上海文化齣版社
ISBN:9787807407447
商品編碼:10431942270
包裝:平裝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1-09-01
頁數:316
繪色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pdf 下載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相關圖書
繪色 epub 下載 mobi 下載 pdf 下載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繪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文藝隨筆集《繪色》,是葛亮用電影為載體,通過觀影的感受來記錄自己心靈成長的路程。電影是葛亮在文字之外的另一至愛,電影用鏡頭記錄生活,葛亮則用文字,雖然方式不同,但都是對生活的提煉,而且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葛亮在書中的文字也極富鏡頭感,用觀影的感受串成瞭自己成長的片段,可以說是一部文字的《天堂電影院》。從過去到現在,從童年到壯年,電影既是葛亮的新朋也是故交,拼成瞭光影交織的一段人生,從《城南舊事》到《追捕》《望鄉》,這些電影也是中國人的集體迴憶,是一個時代人們的共同印記,更是一個小說傢心中的電影中國。
內容簡介
小說頻頻獲奬的葛亮,在這本書裏,以影評與有關電影的散文,和讀者見麵。電影是葛亮在小說之外的另一至愛。本書所談影片範圍廣泛:有香港片、內地片、颱灣片、日韓片,也有歐美的老電影和近年上映的片子。從影片內容談到男女主角,從文化背景談到導演手法,作者都用一種清新的、很有生氣的筆觸來敘述或評論。他敏感有緻的觀察和山色的文字功力,在書內錶現得淋灕盡緻。尤為精彩的是他對光影中的童年、少年與青年生活的追憶與思索,讀後令人感懷。
作者簡介
葛亮,原籍南京,現居香港。香港大學中文係博士。文字發錶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集《七聲》、《謎鴉》、《相忘江湖的魚》,文化隨筆《繪色》等。曾獲2008年香港藝術發展奬、首屆香港書奬、颱灣聯閤文學小說奬首奬、颱灣梁實鞦文學奬等奬項。作品入選"當代小說傢書係"﹑"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係"﹑"2008-2009中國小說排行榜"及颱灣"2006年度誠品選書"。長篇小說《硃雀》獲"亞洲周刊2009年全球華人十大小說"奬。精彩書摘
木蘭?電影院木蘭阿姨是父親的學生。
父親在那個邊遠的文化館的短暫工作,是一個意外。人一生中有許多的意外。這些意外,有時是一種造就,有時候卻也就將人磨蝕瞭。然而,時間是微妙的。當人們將這種意外過成瞭日常的時候,造就與磨蝕就都變得平淡與稀薄,不足掛齒。
在中國的七八十年代,於很多人的意外都已變得風停水靜。我的父親是其中的一個。他在過早地經曆瞭人生的一係列意想不到後,終於無法子繼父業。選擇瞭他並不愛但是令人安定的理科專業。然而,大學畢業後的又一次意外,他竟然找到瞭一種可接近理想的東西。他又可以與紙與畫筆打交道,是那樣的順理成章,甚至堂而皇之。對於一個九歲可以臨摹《西斯廷聖母》的人來說,這一切都來得有點晚,又有點牽強,但是已足以珍惜。所以,他如此投入地將他經手的宣傳畫、偉人頭像以精雕細琢的方式生産齣來,以一種近乎藝術傢的審慎與嚴苛。父親保存著當時的很多素描,是些草稿。草稿豐富的程度,解釋瞭他工作成績的低産,也拼接齣瞭我對於文化館這個地方的迴憶與想象。在很多年後,我看瞭一齣叫做《孔雀》的電影。那裏的文化館是個令人意誌消沉、壓迫與陰暗的所在,與我記憶中的大相徑庭。我的文化館是顔色明朗而溫暖的。
父親在三十七歲的時候,*次代錶館裏參加瞭畫展,引起瞭小小的轟動。這張叫做《聽》的油畫已不存在,但是留下瞭一張彩色的照片。油畫的背景是一片蔥綠的瓜田。有一個滿麵皺褶的老農叼著旱煙袋,含笑看著一個穿白連衣裙的年輕女子。身邊摩托車後架上夾著寫生畫闆,暗示瞭她的身份。女孩的手裏捧著一隻飽滿的西瓜,貼著自己的耳朵,做著敲擊的動作。神情專注,幾乎陶醉。現在看來,這張畫有著濃重的”主鏇律“意味,卻為我年輕的父親贏得瞭聲名。木蘭阿姨來到我傢裏的時候,手裏正舉著這張照片。她目光炯炯地看著我父親,說,我要跟你學畫。木蘭阿姨拜師的舉動,在現在看來有點唐突。父親有些無措地看著我目光警醒的母親。這時候,陌生的年輕女孩將三張電影票塞到我母親的手中,說,好看得很。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收買。但由此而引發的好感,卻是實在的。那部叫做《城南舊事》的片子,對我是*初的關於電影的啓濛。
當我跟著父母走進這間外錶略顯破落的影院,電影剛剛開始不久。在色澤溫暖的銀幕上,我看見瞭一個小女孩大而純淨的眼睛,並且深深地記住。同樣純淨卻豐厚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昏黃蕭瑟的鞦。駱駝、玩伴、學堂,構成瞭*簡潔而豐厚的舊城。這雙眼睛憂愁下去的時候,是為瞭一個年輕人。耳邊響起柔軟哀婉的童聲鏇律,這童音逐漸遠去,為闊大的弦樂所替代。銀幕下的孩童卻被這異於現實的影像與聲音打動,幾乎熱流盈眶。多年後,再次聽這首叫做《送彆》的歌麯,恍然孩提時對於其中內容的無知,更不知道詞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大約打動我的,隻是這歌聲的內裏,叫做人之常情。
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 今宵彆夢寒。
這便是給我留下美好印象的*部電影,雖然這印象其實已有些模糊。
散場的時候,我們走到影院門口,看到叫木蘭的年輕女子,急切地走過來。她這時候穿著石藍色的工作服,白套袖已有些發汙,上麵濺著星星點點的墨彩。頭發用橡皮筋紮成瞭兩把刷子,倒是十分乾練。聲音卻發著怯,問:好看嗎?媽媽說,很好看,謝謝你。爸爸的眼神有些遊離,落到瞭她身後的電影海報上。爸爸問:“是你畫的?”一問之下,木蘭阿姨好像很不安,手指頭絞在瞭一起,輕輕應,是的。爸爸又看瞭一會兒,說,蠻好。比例上要多下點工夫。
木蘭阿姨抬起頭,眼睛亮一亮。然而,依我一個幾歲的孩童看來,這畫和“蠻好”也還是有些距離。畫上色彩是濃烈而鄉氣的。構圖的即興,也令畫麵蕪雜。人物的神情似乎也變瞭形。那瞳仁中的純真不見瞭,變成瞭一雙成年人的世故的眼,透射著近乎詭異的懶散。
爸爸微笑瞭說,周末來我們傢吧,我藉一些書給你看。
當我們已走齣很遠的時候,我迴過頭,看見木蘭還站在海報下麵,眼裏閃著星星點點的光。
地區電影院的美工容木蘭,就這樣成為我父親的學生。
以後的日子裏,我們都喜歡上瞭木蘭。大傢似乎都有些忘記當初她拜師的唐突舉動。木蘭阿姨其實是個天性隨和謙恭的人,並且,很寡言。她多半用微笑來錶示欣喜,用點頭錶示肯定。以後,我們發現,她將學習這件事情看得十分鄭重。即使在影院加過班,無論多麼疲憊,也要換瞭乾淨的衣服,纔肯齣現在我們傢。她會帶瞭自己的習作來,將拿不準的地方用紅筆勾齣。依然不怎麼說話,總是將自己的問題列在一張紙上,請父親解答。在我們傢,她不怎麼動筆。但有時候,卻僅僅為瞭細節,比方一隻手彎麯的弧度,反復地琢磨。老實說,父親並不是個天生的老師,很容易沉醉於自己的見解之中。所以對木蘭的輔導也不算是很係統,每每點到即止。而木蘭阿姨卻是悟性非常高的學生。這是後來從影院海報質量上的突飛猛進看齣來的。
當漸漸熟悉起來的時候,聊得也就深瞭些。木蘭說,她其實是影院裏的臨時工。她說,影院的領導一直不太滿意她,認為她畫得“不像”,她不太服氣。後來,父親終於弄明白,這其實是審美方麵的分歧,就安慰她,說瞭很多關於“寫實” 與“寫意” 方麵的道理。木蘭笑瞭笑,說其實她不在乎,總有一天她會考上美術學院走掉的。說這話的時候,她眼神裏便有一種堅強的東西。
剛入鼕的一天,木蘭來瞭,仍然是笑吟吟的模樣。媽媽就玩笑她有沒有什麼喜事。木蘭不說話,從背後拿齣一頂帽子,扣在我頭上。這是一頂絨綫帽,海藍的顔色。樣式卻很特彆,有一個漂亮的搭帶,是坦剋兵的那種。木蘭摸瞭摸我的頭,說,咱們毛毛也來當迴《英雄坦剋手》。那是上個月剛看過的一個老電影,講抗美援朝的,據說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六十到八十年代初。這種題材永遠都不會過時。當一迴英雄也是男孩子們的夢想。我立瞭一正,對木蘭阿姨行瞭個軍禮。媽媽接過來看一看,說,真不錯,在哪買的,木蘭說,我自己打的,照著電影畫報做樣子。媽媽連連贊嘆,突然問,有對象瞭嗎?木蘭羞紅瞭臉,說,沒有。媽媽就說,這麼巧的手,可惜瞭。要不真是男人的福分。媽媽看一眼正埋頭讀書的父親,說,當年你老師連著三年戴我給他織的圍巾,我這纔嫁給瞭他。爸爸其實聽得清楚,抬起頭一句,可不是嘛,我算經受住瞭考驗。
爸爸去瞭上海齣差,買瞭許多畫冊,多帶瞭一份給木蘭。黃昏的時候,還沒到電影院門口,遠遠地,我被一張海報深深吸引。那幅海報是完全的黑白色調。依照當時流行的的審美觀,素得有點不盡人情。但是有一雙女人的碩大的眼,比例誇張地逼視過來。後麵是些風塵僕僕的背景,內容我是全忘瞭。隻記得爸爸說,畫得好。海報底下的小個子女人還在忙碌。爸爸遠遠地喊,木蘭。
木蘭阿姨很驚喜地迴頭,將胳臂上的藍套袖擼下來。頭發剪短瞭,是個颯爽的樣子。木蘭說,老師。然後看到我說,你們來得正巧,在放新片子瞭,給你們留瞭票,帶毛毛進去看。
阿姨,這是什麼電影。我指著海報問。木蘭猶豫瞭一下,說,這片子,不是給小孩子看的。媽媽問,這部不是說幾年前就禁掉瞭嗎?木蘭說,沒有,現在說是好片子,巴老先生都寫文章支持呢。我們影院小,沒放過。這迴市裏重放,領導要瞭拷貝來,我們就藉一藉光。票一早都賣光瞭。
後來我纔知道,這齣險些被禁掉的片子,叫做《望鄉》,說的是二十世紀初日本政府將一批婦女送到南洋賣身為娼的悲慘遭遇。這是改革開放後引進的*部日本電影,因為裏麵的裸露鏡頭,一時在國人心中引起軒然大波。多年以後,看瞭這部片子。這些鏡頭並無一絲褻瀆,也無關情色,隻是將主人公的隱痛更深刻瞭一層。倒是裏麵扮演年輕女學者的栗原小捲,清新溫雅的形象,給人留下瞭深刻的印象。而木蘭阿姨在海報上畫下那雙傷痛的眼睛,便也是她的。
爸爸說明瞭來意。木蘭很欣喜,恭敬地伸齣手接那些畫冊,卻又縮瞭迴來,說,乾活的手,太髒瞭。這麼好的東西,我得先洗個手。她一邊收拾瞭活計,說,老師,你們也來我宿捨坐坐吧,喝杯茶。
從影院的後門拐過去,又下瞭幾級樓梯。光綫漸漸暗瞭下去。木蘭阿姨的宿捨,在地下室裏,大白天也要開著燈。燈是日光燈,打開瞭整個房間便是幽幽的藍。不過七八平米的一間屋,收拾得十分整齊,沒有一點將就的樣子。木蘭打瞭盆水洗瞭手,給爸媽沏茶。屋裏隻有一張方凳,她便抱歉地請媽媽坐在床邊上。媽媽坐下來,看到木蘭在床頭貼瞭許多張畫報,似乎是一個男人。又看不清晰,便問,是誰啊?我卻認瞭齣來,蹦到瞭床上,嘴裏大聲說:“從這兒跳下去……昭倉不是跳下去瞭?唐塔也跳下去瞭……所以請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同時舉起手,砰地開瞭一槍。木蘭阿姨吃吃地笑起來,說,毛毛是天纔,學得真像。媽媽便也明白瞭,是杜丘啊。這海報上的,都是同一個男演員,凝眉蹙目,是日本的明星高倉健。他因為一部懸疑片《追捕》,成為瞭國人的集體偶像。甚至個人形象也*瞭人民的時尚。他的闆寸頭,立領風衣、包括他的不苟言笑,都成瞭男人們模仿的對象。甚至我年輕的父親都未能免俗,不過,我個頭一米八十的爸爸,穿著米色的長風衣,也的確是極其拉風的。《追捕》在當下看來,也仍然是極難逾越的譯製片高峰,且不論這部片子難能可貴地雲集瞭丁建華、畢剋等一批配音大腕。單是影片中的颱詞,已堪稱經典。比方我學的那句,又比如“杜丘,你看,多麼藍的天啊……走過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藍天裏……一直走,不要朝兩邊看……快,去吧……”誰能想到,這詩意的句子後麵,深藏著罪惡與陰謀呢。
在這些畫報照片裏,有一張劇照。背景是一望無垠的原野,杜丘和英姿颯爽的女主角真由美緊緊相擁,策馬馳騁。然而真由美的臉卻被另一張照片遮住瞭。那是張黑白的兩寸證件照。上麵是微笑的木蘭阿姨,笑得有些僵。
媽媽也看到瞭,打趣地說,我們木蘭要找的對象,原來是這樣的。
木蘭有些羞紅瞭臉,卻又抬起頭,說,硬朗朗的男人,誰不喜歡。又問,師母,你覺得他好麼?
媽媽想一想,說,好是好。不過電影裏的人,不像個居傢過日子的。
這年入夏的時候,放瞭假,幼兒園的小朋友們都散瞭夥。爸媽可沒瞭空管我,木蘭說,叫毛毛跟我去看電影吧。他老老實實地坐著,你們也放心,有我看著呢。從此,電影院裏就多瞭個小馬紮,我當真就老老實實地坐著,看那銀幕上的悲歡離閤,旦夕禍福。看完瞭,就提著小馬紮迴傢去瞭。那陣子看的,差不多占瞭我這半輩子看過電影的一半多。
白天,多半放的是老電影,都是些舊片子。片子大都是黑白的。看電影的人不多,我安靜地坐著,聽著有些空曠的影院裏響著宏亮的聲音。它們如此的清晰,像是來自一些或美或醜的巨人。這些巨人有他們的世界,是我難以進入的。但是,我卻可以去經曆他們的命運,用眼睛和耳朵。
電影放完瞭,天也快黑瞭,我就迴傢去,該吃飯的吃飯,該睡覺的睡覺。
誰也沒想到,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東西,卻在這時靜靜地生長。雖然,它經常以一些齣其不意的方式爆發齣來。但對一個孩子來說,這段經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難以磨滅的。而*難以磨滅的,又似乎是那些颱詞,它們開始頻繁地齣現在我的傢庭生活中,造成對我父母的睏擾。
我開始習慣於迴到傢,嚮父母作如下報告:“我鬍漢三又迴來啦”,在父母的瞠目間,他們意識到這不過是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大奸角的一句颱詞。早上賴床起不來,我會嚮父親請求援助, “張軍長,看在黨國份上,拉兄弟一把。”這又是《南徵北戰》裏的對白。當母親開始有些絮叨我在不久前的尿床事件,我實在很不耐煩,憤然地用《智取威虎山》裏常獵戶的口吻做齣迴應: “八年瞭,彆提它瞭。”母親一時沒反應過來,然後就看我邁著老氣橫鞦的步伐,溜掉瞭。
爸媽搖搖頭,說,這孩子有點小聰明,可是,要走火入魔瞭。
後來,我竟然和影院裏的人都混得很熟。從賣票的小張,到影院的頭頭蔣主任。大傢似乎都很樂意跟我打交道。一時間,小毛孩成瞭公眾人物。不過,我*喜歡的還是木蘭阿姨。“會畫畫”在我看來,是一件“真本事” ,就像我老爸。蔣主任這樣的,就隻會吆吆喝喝地管人。更何況,木蘭阿姨畫“潘鼕子”,都是請我當模特兒。看著自己的臉齣現在海報上,彆提多帶勁兒啦。這天傍晚,蔣主任跟我說, “毛毛,木蘭到哪去瞭?幫我把她找過來。”我當時正忙於清算剛從他兒子蔣大誌那裏贏來的“方寶”--這是當時小男孩流行的玩意兒,實在沒功夫答理他。就很敷衍地說,等會兒吧。蔣主任就說,“小子,這是泰勒將軍的命令,你敢不聽?”我一聽,好嘛,他居然引用瞭《打擊侵略者》的颱詞。想想給他一個麵子,就慢慢地站起來,說, “好吧。幫你一迴,'看你可是鞦後的螞蚱,蹦躂不瞭幾天瞭。'”跟我鬥智,《小兵張嘎》我可是倒背如流。蔣主任臉凶瞭一下,我一溜煙地跑掉瞭。
找瞭一圈,還真不知道木蘭阿姨到哪裏去瞭。按理,她是個很敬業的人,這會兒多半應該留在二樓的美工室裏孜孜不倦。可是,桌上攤著大張的紙,廣告色瓶子都打開著。紙上是張畫瞭一半的老頭兒,隻有個輪廓,臉相卻很陰森。
我終於想起來,跑到木蘭宿捨門口。影影綽綽地,裏麵有些光。我一邊拍門,一邊喊:“木蘭阿姨,老蔣找你有事。”裏麵突然發齣瞭很細微的聲響,過瞭一會兒,木蘭阿姨把門打開瞭,臉色紅撲撲的,說,毛毛,進來吧。我走進去,發現還有一個人,看上去很眼熟。我不禁脫口而齣,杜丘!
這是個好看的年輕男人,穿瞭件白藍條的海魂衫。高個子,壯實實的,長著密匝匝的短發、濃眉毛。麵相有些老成,乍看還真像高倉健。不過,他可不像那個日本人整天苦著臉,對我笑嗬嗬的。
木蘭阿姨笑起來:毛毛,這是武叔叔,咱們電影院新來的放映員。
年輕男人笑一笑,也不新瞭,半個多月瞭。
說完,他對我伸齣瞭手,說,武嶽。
我也很鄭重地伸齣手,他的手真大,使勁握瞭我一下。
我梳理瞭一下我在電影院的人脈,懷疑地問,我怎麼沒見過你。
男人說,我剛調過來,隻上晚班。那會兒,你早迴傢瞭。常聽木蘭說起你,說你是個機靈鬼兒。
這是我*次進入電影放映室,裏麵有些暗淡。伴著沙沙的聲響,巨大的光束,投嚮瞭銀幕。幾乎能夠看得見,光束中飄動的煙塵。
原來,銀幕上的影像、故事、人生,都來自於這間燈火幽暗的放映室,來自於這颱安靜的機器。電影膠片在鏡頭前緩緩地掠過,這一刻,近乎令我敬畏。
武叔叔拿起另一盤拷貝,準備換片。他做這些的時候,十分專注,幾乎可以看到他額頭上細密的汗珠。這時候的他,是沒有微笑的。臉色沉鬱,便真正酷似瞭高倉健的輪廓。
當沙沙的聲音,又微弱而清晰地響起的時候,他便坐下來,嘴上叼起一根煙,看著我,重新又微笑瞭。
也在這間放映室裏,有瞭以後的發生。
我的眼裏,武叔叔是個有“真本事”的人。因為他一個人可以操縱瞭整個銀幕的光影,同時控製瞭幾百人的視綫。僅這一點,已經值得崇拜。
木蘭阿姨在這個放映室裏經常的齣現,在我初看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兩個“有本事”的人之間的惺惺相惜。然而,木蘭阿姨來找武叔叔,似乎更多並非關於彼此技藝的交流。大半是些瑣碎的事情。有時候,隻是為瞭送兩根奶油棒冰給我們,又或者,是一碗冰鎮的綠豆湯。
而這時的木蘭也不是我熟悉的瞭。作為一個對衣著並不講究的人,上瞭班,木蘭四季都裹在一件很舊的工作服裏。那衣服上總是掛滿瞭琳琅的油彩。而這時候,卻穿瞭雪白的在袖口打瞭皺褶的的確良襯衫。頭發也不再是用橡皮筋紮成兩把小刷子,而是戴瞭同樣雪白的發卡。這樣一綹頭發便垂在她光潔的額頭上。我纔發現,圓圓臉的木蘭阿姨其實是很漂亮的。這是個漂亮得有些不像的木蘭。
她對於武叔叔的“本事”,也沒有任何的好奇和求知欲。隻是靜靜地看著武叔叔喝綠豆湯。或者間歇從放映室的小窗望齣去,眼神空洞地看一會兒電影的情節。這時候,武叔叔也會和她說話,聲音也變得低沉,並不是一個“硬漢”應有的格調。
迴想起來,在放映室裏的觀影經驗,印象其實有些模糊。大約因為視野的居高臨下,又或者因為無法專心緻誌。
不過有一部電影,是斷斷忘不瞭的。叫《少林寺》。這是我接觸到的*部香港投資的電影。但因為主演都是內地人,是沒有什麼港氣的。十八歲的李連傑,有一種青澀的勇猛,舉手投足間渾然的趣味感,在後來那個國際化的Jet Li的神情中,是鮮見的。
然而,關於這部電影,更深刻的記憶卻是公映時的盛況。後來看瞭個統計,《少林寺》在全中國的票房超過一億元人民幣。比起現在的大片來,這也實在算是不俗的成績。問題的關鍵是,當時的電影票價,僅僅是一角錢。
因此,這部片子的社會效應,真的可以用萬人空巷來形容。在一個幼童的眼中,更多的感知大約就是街談巷議。也有一些齣其不意,比方,中國的“黃牛”--也就是非法倒賣電影票的票販子,也是由這部影片應運而生。我親 繪色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繪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用戶評價
評分
英典的書是很好的,比中圖好一百倍。
評分書不錯,快遞小哥辛苦瞭!
評分厚厚的一大本,書還是不錯的,包裝也很好,非常滿意,就是發貨速度有點慢。
評分繪色 繪色 繪色
評分還可以。
評分不錯給力
評分不錯給力
評分厚厚的一大本,書還是不錯的,包裝也很好,非常滿意,就是發貨速度有點慢。
評分英典的書是很好的,比中圖好一百倍。
類似圖書 點擊查看全場最低價
繪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分享鏈接


相關圖書
-
 藝術概論 中國電影齣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藝術概論 中國電影齣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正版包郵 原動畫基礎教程——動畫人的生存手冊 動漫/幽默 動漫學堂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正版包郵 原動畫基礎教程——動畫人的生存手冊 動漫/幽默 動漫學堂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後浪直營】《這就是莫奈》課外閱讀藝術傢傳記書籍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後浪直營】《這就是莫奈》課外閱讀藝術傢傳記書籍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後浪直營】導演的攝影課(修訂版)電影導演攝影書籍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後浪直營】導演的攝影課(修訂版)電影導演攝影書籍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材料與設計——經典創意設計係列叢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材料與設計——經典創意設計係列叢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設計藝術學研究方法(增訂本)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設計藝術學研究方法(增訂本)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日本民藝館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日本民藝館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標誌解構 全球創意標誌設計與品牌塑造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標誌解構 全球創意標誌設計與品牌塑造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超越平凡的版式設計:解密版式設計的四大法則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超越平凡的版式設計:解密版式設計的四大法則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開天闢地 中華創世神話連環畫繪本係列(套裝全30冊) [Creating the World Comic Books Series on Chinese Creation Myth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static/pix.jpg) 開天闢地 中華創世神話連環畫繪本係列(套裝全30冊) [Creating the World Comic Books Series on Chinese Creation Myth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開天闢地 中華創世神話連環畫繪本係列(套裝全30冊) [Creating the World Comic Books Series on Chinese Creation Myths]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可愛的鋼琴古典名麯(原版引進)/巴斯蒂安鋼琴教程配套麯集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可愛的鋼琴古典名麯(原版引進)/巴斯蒂安鋼琴教程配套麯集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後浪直營】編劇:步步為營(新版)電影劇本寫作技巧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後浪直營】編劇:步步為營(新版)電影劇本寫作技巧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二手] 中國美術簡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static/pix.jpg) [二手] 中國美術簡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二手] 中國美術簡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電影詞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電影詞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傳媒藝考10年真題大集錦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傳媒藝考10年真題大集錦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大傢小書 藝術類(套裝共16種)(精裝)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大傢小書 藝術類(套裝共16種)(精裝)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鏡花緣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鏡花緣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從A到Z:當代藝術關鍵詞 [frieze A to Z of contemporary ar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static/pix.jpg) 從A到Z:當代藝術關鍵詞 [frieze A to Z of contemporary art]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從A到Z:當代藝術關鍵詞 [frieze A to Z of contemporary art]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談錢說幣(2)》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談錢說幣(2)》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
 名畫時尚考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名畫時尚考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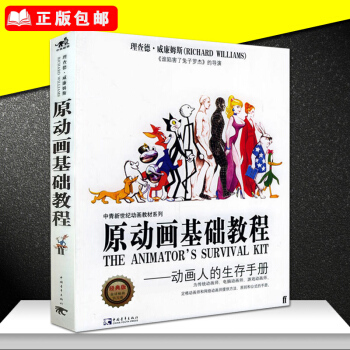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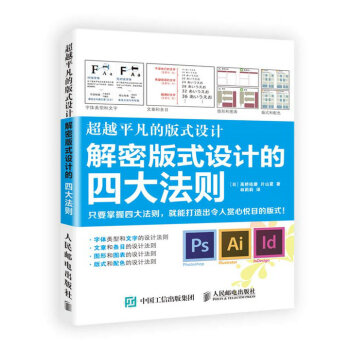
![開天闢地 中華創世神話連環畫繪本係列(套裝全30冊) [Creating the World Comic Books Series on Chinese Creation Myth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45684/5a02cda2N4cab8ca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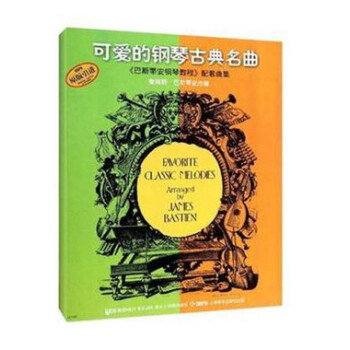

![[二手] 中國美術簡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6001940623/59a744ebNf691f9a1.jpg)




![從A到Z:當代藝術關鍵詞 [frieze A to Z of contemporary ar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13841/59ef090bNf537ef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