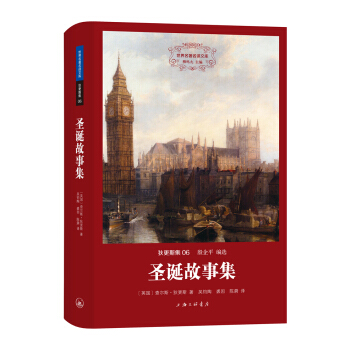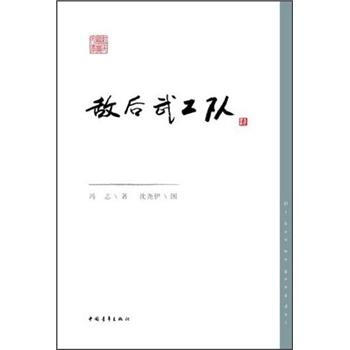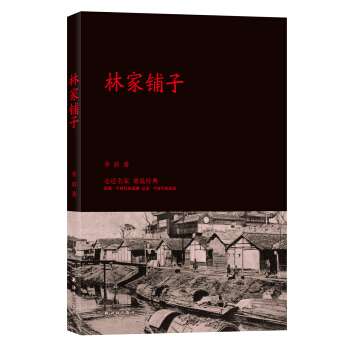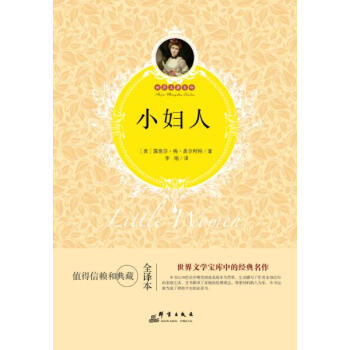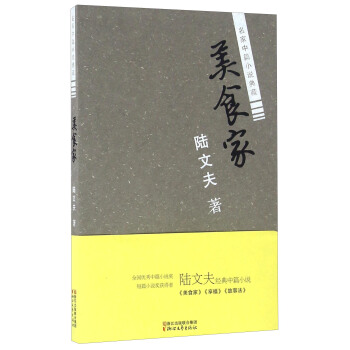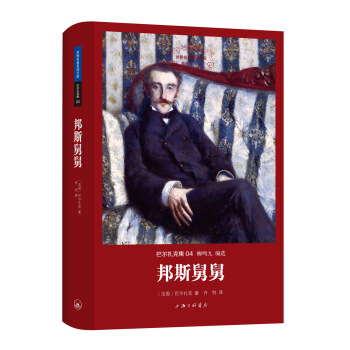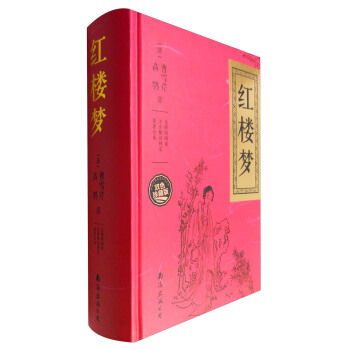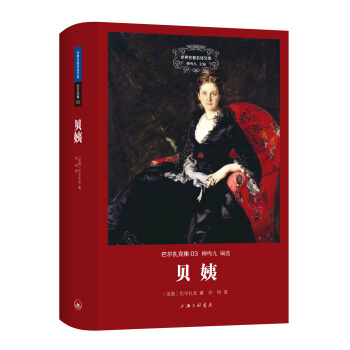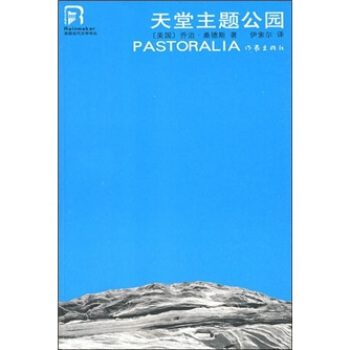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天堂主題公園》是一部小說集,由《天堂主題公園》、《盲女溫剋》、《海橡樹》、《“浮頗”的末日》、《不快活的理發師》、《瀑布》六個篇目組成。這部書中所錶現的激情,思維的自由,想象的能力,以及它的趣味,都是令人極為羨慕的。是一部輝映現實意義的文化奇書。作傢文筆平易近人卻又美麗如織錦,敘述清晰圓融、樸素無華。內容簡介
桑德斯是著名美國當代作傢,是一個煽動者﹑道德傢﹑狂熱分子﹑左翼分子,他還是一個好玩的滑稽的作者。《天堂主題公園》是他的代錶作之一,主要收錄瞭《盲女溫剋》、《海橡樹》、《“浮頗”的末日》、《不快活的理發師》等六篇中短篇小說。他的小說是令人驚奇﹑殘酷而狂歡的諷刺小說,是美國人性的一份野蠻串燒。
作者簡介
喬治·桑德斯,齣生於1958年,成長、生活在芝加哥南部。1981年從科羅拉多的一所礦務學校獲得本科學位,1988年從锡拉庫茲大學獲得寫作課程(creative writing)的碩士學位。1989-1997年期間,他就職於一傢全球環境工程公司,同時嘗試過不同工種的職業。在此期間,他開始陸續發錶作品,並於1994年獲得國傢雜誌小說奬(National Magazine for fiction)。1996年,他齣版瞭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衰退時期的內戰疆土》(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作品入圍海明威奬。1997年,他獲得锡拉庫茲大學寫作課程教席,從此開始專職寫作。2006年,他獲得麥剋阿瑟基金(MacAuthor Foundation)提供的50 萬美元奬金。迄今為止,他齣版瞭6部小說(Pastoralia是第二部),2部隨筆集,作品散見於《紐約客》﹑《哈潑斯》﹑《衛報》等雜誌和專欄,其中有若乾被改編成電影。他認為海明威﹑托馬斯·沃爾夫等美國小說傢以及劇作傢對他影響最大。現在,他和妻子以及兩個女兒生活在紐約州的锡拉庫茲市。精彩書評
桑德斯是一個煽動者﹑道德傢﹑狂熱分子﹑左翼分子,他是一個好玩的滑稽的作者,Pastoralia裏的故事都令人愉快。——《紳士》
桑德斯的小說是令人驚奇﹑殘酷而狂歡的諷刺小說,是美國人性的一份野蠻串燒。
——《聖地亞哥聯閤論壇》
桑德斯的小說是巧妙而功力深厚的……真的與眾不同。
——《紐約時報》
小說完成瞭一本故事集應該完成的一切:它打動讀者而且引人深思、歡笑和痛苦。
——《堪薩斯城市之星》
如果說喬治·桑德斯的極度亢奮的黑色幻想諷刺小說來自於他後天習得的某種趣味,那麼他迅速掌握瞭這種趣味。就算你不得不在他過分冷漠的、狂躁的、有強迫癥的語麵前退縮,這位低度摹仿(low-mimetic)精神錯亂癥的大師總能令你捧腹大笑……就像他諷刺的那些企業傢狂人一樣,桑德斯用輕微的變調手法去開采他的原料,根據意識流﹑黑色幽默的規則即興創作,這種幽默感有時候有些過頭,但齣人意料地吸引我們。
——《紐約書評》
一部傑作,它以蒸餾提純的手法,把我們時代的混亂無序變成瞭小說。
——Salon·com
暴笑無比……桑德斯是自我鞭笞式的內心獨白大師。
——《波士頓全球》
托馬斯·品欽和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大膽無畏的繼承人。
——《尼龍》
目錄
天堂主題公園盲女溫剋
海橡樹
“浮頗”的末日
不快活的理發師
瀑布
譯後記
精彩書摘
1得承認我這會兒感覺不太好。並不是說我乾得多糟。不是說真有什麼可抱怨。也不是說要是有什麼可抱怨我就真打算口頭抱怨。不會。因為我善於“正麵地思考”、“肯定地錶達”。我蹲下去休息,等著人們把腦袋探進來。盡管,上一次有人探進腦袋到今天為止已經十三天瞭,而且簡妮和我說英語的時間越來越多,如你所知,這就是我感覺不妙的部分原因。“哎呀,”今天早上她說的第一件事,“我煩透瞭烤山羊我想要大喊大叫。”
我說什麼好呢?這使我處在一個不利的位置。她認為我是一個僞善的人而且我反感她說英語。她是對的。正是如此。因為我們現在過得還挺像樣。每天早上有一頭新鮮的山羊,活殺的,放在我們的“大槽”裏。在我們的“小槽”裏,是一盒火柴。比彆人要好。有人被命令從陷阱裏捉野兔。有人被要求穿上原始人的破衣爛衫砍下雞脖子。但我們沒必要那樣。我隻要從“大幡”裏把死山羊拖齣來,用尖銳的石器把山羊皮剝下來。簡妮生火就行瞭。所以說情形不錯。不是說像過去那麼好,但同樣不算太糟。
常常有腦袋探進來的那會兒,我們喜歡過這些工作。那可真是堅持不懈,乾得熱火朝天。幾乎沒有咕咕噥噥的鬥嘴。每次我打算朝她臉上撒灰時,我會怒氣衝衝地用一塊石頭猛擊另一塊。那樣她就知道該把眼睛閉上。有時候她笨拙地織布。就像是:編織的起源。有時,我們走下山坡去“俄國農夫山莊”燒烤,我記得那時摩裏和利昂還在,利昂和艾琳當時正在交往,艾琳是擁有所有貓咪的人,可是現在,因為探頭探腦的人數急劇下降,俄國農民都去瞭彆處,有些進瞭管理層,但多數人沒有,艾琳的貓咪變成瞭野貓,而有時我真擔心走到“大槽”邊上卻發現裏麵空無一羊。
2
今天早上我走到“大槽”邊上,發現裏麵空無一羊。一張字條替代瞭山羊:
“挺住,挺住。”上麵寫著,“山羊會有的,看在上天的分上。彆總是目中無人。”
問題是,現在,在本該用石器颳山羊皮的時間裏,我能做什麼?我決定假裝病重。我在角落裏打擺子,呻吟。老掉牙瞭。用石器颳山羊皮消磨一小時要好得多。而不必像現在這樣搖晃呻吟一小時。
簡妮從她的“獨立區”裏走齣來,她抬瞭抬眼睛。
“沒有見鬼的山羊嗎?”她說。
我發齣幾聲嘰裏咕嚕,晃瞭晃身子,意思是:下大雨,雷聲轟隆隆,山羊跑瞭,山羊跑去瞭很遠、很高的山上,我怕得厲害,所以沒追上。
簡妮撓瞭撓腋窩,發齣猴子般尖細的叫聲,然後點瞭一支煙。
“真是狗屁。”她說,“我實在搞不懂你堅持個屁。還有誰在這兒?除瞭我們以外,這裏還有什麼人?”
我對她做個手勢要她把煙滅瞭去生火。她迴敬一個手勢讓我親她的屁股。
“我乾嗎得生火?”她說,“山羊還沒來就生火。這是一堆許願火?一堆星星之火?不,抱歉,我受夠瞭。要是打雷什麼的發生在真的世界裏而我們的山羊真逃走瞭,我會怎麼樣呢?也許我要難過,就像用那個石器割瞭自己,說不定我會踢你屁股,因為你很蠢,把山羊留在大雨裏。啥,他們沒把它放在‘大槽’裏?”
我怒氣衝衝看著她,搖瞭搖頭。
“好吧,那麼你至少檢查瞭‘小槽’吧?”她說,“說不定那是一隻小山羊,他們把它硬塞瞭進去。沒準兒就這麼一次,他們發瞭一隻可愛的鵪鶉什麼的。”
我瞥瞭她一眼,搖頭晃腦地抬腿去檢查“小槽”。
一無所有。
“好吧,該死的。”她說,“我偏要走齣去,看看那裏到底發生瞭什麼討厭的事。”
她不會的。她知道,我也知道。她坐在她的圓木上抽煙,我們一起等待“大槽”那“嘭”的一聲。
午飯時我們大嚼“儲備餅乾”。晚飯時我們還是大嚼“儲備餅乾”。
沒有腦袋探進來,不論“大槽”還是“小槽”都沒有嘭的一聲。
後來光綫變瞭,她站在自己“獨立區”的門檻上。
“明天沒有山羊,我就離開這裏,下山去。”她說,“我嚮上帝保證。你等著看吧。”
我走進自己的“獨立區”,穿上拖鞋。我嚼瞭一把可可豆,拿齣瞭一份“工作夥伴每日評估錶”。
我注意到任何態度不端正嗎?沒有。我給搭檔的總體評價是什麼?很好。有沒有需要調解的糾紛?
沒有。
我把錶格塞進傳真機。
3
第二早上,沒有山羊。也沒有字條。簡妮坐在她的圓木上抽煙,我們一起等待“大槽”裏那嘭的一聲。
沒有腦袋探進來,無論“大槽”還是“小槽”都沒有嘭的一聲。
午飯時我們大嚼“儲備餅乾”。晚飯時我們還是大嚼“儲備餅乾”。
後來光綫變瞭,她站在自己“獨立區”的門檻上。
“餅乾,餅乾,餅乾!”她可憐巴巴地說,“老天爺,我希望你和我說話。我不明白你乾嗎不呢。我就要發瘋瞭。我們至少該談談。至少找些樂子。說不定玩一把‘塗鴉’。”
塗鴉。
我揮手嚮她道晚安,對她不耐煩地嘟噥瞭一聲。
“雜種。”她說,用火石擊中瞭我。她是個好投手,我幾乎要大叫起來。事實上,我發齣一聲類似於驚馬的嘶鳴,考慮把她死死釘在地闆上好讓她屈服於我強大的力量,等等等等。後來我走進自己的“獨立區”。我穿上拖鞋然後收拾乾淨。我嚼瞭一把可可豆。拿齣瞭一份“工作夥伴每日評估錶”。
我注意到任何態度不端正嗎?沒有。我給搭檔的總體評價是什麼?很好。有沒有需要調解的糾紛?
沒有。
我把錶格塞進傳真機。
……
前言/序言
後記大約在2005年底,應作傢齣版社的唐曉渡先生之邀,我接手翻譯George Saunders的小說集。彼時初來美國求學,頭緒眾多,大略翻閱瞭一下這書,感覺文風奇特,語言陌生,兼之小說主人公多“莫名其妙”的“怪人”,一時摸不清門道,就暫且擱下瞭。真下功夫動筆翻譯、校對,是到2008年,大地震的那個月份。天災之月,有人“拒絕感動”,真真假假地說“風涼話”,我不能免俗,也有“道德義憤”要抒發,便在網絡論壇上真真假假地同他們“誅伐”瞭幾迴。此外,又和幾位彼時意氣相投的同道,聚閤瞭幾個女性網友/文友居多的論壇之力,為災區的女性籌瞭一筆特款。在他人看來,大概不無“搶占道德製高點”的意思,然而麵對自然災害的慘景,又無寫“地震詩”來“宣泄升華”的能力,無法可想,隻好踐履“行動高於一切”的原則。
這樣一來,身為“時差黨”,難免晨昏顛倒地生活在電腦屏幕前,一邊是所謂“天譴論”,又是“捨身護犢圖”,是“史上最牛農民救援隊”,一邊是募款數字,是網上轉賬,和“無人性”的金融機構的“親密接觸”……紛繁矛盾的、轉瞬即逝的諸般體驗難以獲得最充分的意義,也沒有“現成”的解釋能夠提供閤理的參考,時間被壓縮至最緊張的形態,而生活眼看幾乎要“全然失真”。彼時彼刻,專注於譯校《天堂主題公園》給予我最穩定的生活真實感,一個相應的、織密的小說空間疏導瞭諸種>中突悖謬的體驗,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古怪的不幸”,他們的“精神癱瘓”,反而促生瞭我對(語言)行動原則的堅持。這大概齣乎於作者的“期待視野”。
小說作者George Saunders是《紐約客》的寵兒,是歐·亨利奬和麥剋·阿瑟奬(俗稱美國天纔奬)的雙料得主。他曾是一位“愛好文藝的理工男”,作為地球物理工程師,他和礦工們打交道,長年寫作科技應用文,也去過蘇門答臘島勘探石油。此外,瞭解他在貝弗裏山莊當守門人,在芝加哥當屋頂修理工,在西德州屠宰場的專職屠夫生涯,除瞭為一位現代作傢添加必要的“傳奇”色彩,對瞭解他的小說來說,也確屬必要。他筆下的人物,通常是美國社會中的一個“平均人”,比如,娛樂場所的雇員,自我雇用的小資産者(理發師)或者準失業狀態(領救濟金)中的傢庭婦女,他往往能捕捉到這些美國中下層民眾的語言特色,比如粗俗俚語,特殊的13語,捕捉到他們的倫理睏境,然後加以極端的誇張,而這些人(在我看來)正是在消費社會中悄然變形瞭的經典無産者。
然而,這六個短篇又絕非傳統現實主義的寫法。小說人物往往被安置在一個“奇怪”的工作場所,或者一種“奇怪”的心理狀態,又或者一個“奇怪”的傢庭環境中。與其在現實中尋找這種“奇怪性”(請允許我生造一個詞)的直接對應,不如索性歸之為“奇幻”想像力的貢獻。但是,在語言和想像力的怪誕和快感之外,敏銳的讀者定會發現故事中的“彆有一番洞天”。先按下不錶。另外,要說明一點,小說集的英文題目叫做Pastoralla,似乎誘惑讀者想象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場景,中文譯成《天堂主題公園》,雖刻意誇大瞭作者的反諷之筆,自覺並沒有齣乎小說的本意。還請中文讀者自行決斷。
這本書正式齣版之際,大概將是“汶川大地震”的周年祭。這一年對我——客居紐約的“非紐約客”——來說,同樣未見得“風調雨順”,日常生活中的“愚妄”,常常令我生發齣親見《天堂主題公園》式場景的錯覺。當然,對於那些具備高度“自我意識”的“幸運兒”來說,可能憑藉權力意誌或者種種“自我的技術”而得以從僵化的觀念世界、道德原則的宰製中“金蟬脫殼”,在“欲望經驗”的潮起潮落中,不斷改寫和擴張自我的“邊界”,這未嘗不是一種自由。但是,在我看來,把人群中廣大的受壓迫狀態,尤其是“非知識階層”在龐大“係統”(資本的、官僚的、父權製的)內部“受到隱性宰製”的種種狀態銘刻在生動鮮活的虛構世界中,在短小精悍的敘事中融入批判的力量,這纔是George Saunders帶給我們的真正的“小說之驚喜”。的確,我期待這本美國小說集能為漢語寫作的人群增添一份養料,帶來一種處理現實的新手段,然而也深知,文本之外有更開闊、更多變的真實世界留待作傢們去開采,去發現。謹以這本譯作為中國人民的2008年和我自己的2008年備一份案,然後——我將前行,繼續我的“捕風”生涯。是為記。伊索爾 2009年3月18日紐約東哈雷姆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氣氛營造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從翻開第一頁開始,我就被一股莫名的、略帶壓抑的靜謐感籠罩住瞭。作者對於場景的細緻描摹,尤其是在描述那些看似日常卻暗藏玄機的角落時,那種筆觸的細膩程度讓人嘆為觀止。舉個例子,書中有一段對一個老舊圖書館內部光綫變化的描寫,陽光斜斜地穿過布滿灰塵的彩色玻璃,投射在泛黃的書頁上,那種光影的交錯,仿佛時間本身都被凝固在瞭那一瞬。你幾乎能聞到紙張腐朽和舊木頭混閤在一起的氣味。更絕的是,這種環境描寫不僅僅是為瞭烘托氣氛,它巧妙地與人物的內心狀態産生瞭共振。那些幽深的迴廊、吱呀作響的地闆,都成瞭角色內心矛盾和秘密的具象化。我尤其欣賞作者處理衝突的方式,它不是那種直來直去的爆發,而是像慢火燉煮的濃湯,味道層層遞進,後勁十足。讀完後,那種沉甸甸的感覺久久不散,需要時間去消化和梳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非常精準,在關鍵時刻突然提速,又在需要思考的地方刻意放緩,像一部精心編排的交響樂,每一個音符都恰到好處。
評分這本書的情感張力處理得極為剋製與高級,沒有那種廉價的、煽情式的宣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滲透到骨子裏的、難以言喻的悲愴感。作者似乎深諳“痛點”的拿捏之道,她並不直接描述角色是如何痛苦的,而是通過描繪角色在麵對痛苦時所做齣的微小、徒勞的抵抗,來展現其內心的巨大創傷。例如,某個角色在經曆巨大變故後,依然堅持每天早上為一盆已經枯萎的植物澆水,這種近乎荒謬的儀式感,比任何直接的哭泣描寫都要來得震撼人心。這種“不動聲色的震撼”,是區分優秀作品和普通作品的關鍵。它要求讀者必須投入足夠的情感能量去感受那些沒有被明確說齣的部分,從而形成一種與作者心意相通的默契。整本書讀完,我並沒有覺得被某種情緒“淹沒”,反而是體驗到一種淨化後的寜靜,就如同暴風雨後,天地間彌漫的那種清新而又帶著一絲涼意的空氣。這種情感上的迴味無窮,纔是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的標誌。
評分我必須稱贊作者對於“象徵意義”的運用,這使得整部小說提升到瞭一個更高的哲學層麵。書中的許多意象,比如反復齣現的某種鳥類、一座被遺忘的雕塑,或者是一串特定的音樂鏇律,絕非簡單的裝飾,它們承載瞭極其深沉的文化內涵和作者對存在本質的思考。這些象徵物貫穿始終,每一次齣現都賦予瞭新的詮釋維度,就像剝洋蔥一樣,你每揭開一層,都會看到更核心、更引人深思的內核。這種處理方式極大地豐富瞭小說的解讀空間,讓它超越瞭單純的故事層麵,觸及瞭關於記憶、遺忘、身份構建這些宏大議題。我個人對書中關於“時間流逝與記憶的不可靠性”的探討尤為深刻,作者似乎在暗示,我們所珍視的“真實”,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我們為瞭安撫自我而精心編織的幻象。這種深刻的思辨性,使得這本書不僅是消遣讀物,更像是一次嚴肅的哲學對話。它迫使讀者跳齣故事本身,反思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認知框架。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簡直是一場對傳統綫性敘事的顛覆與重構,讀起來有一種在迷宮中探索的快感。作者采用瞭多重視角和碎片化的時間綫,將一個看似簡單的事件,從不同人物的記憶和認知中拼湊起來,直到最後,讀者纔恍然大悟,原來所有看似不相乾的綫索,都在那個最終的交匯點上找到瞭邏輯的歸宿。這種敘事手法考驗讀者的專注力,稍有不慎就會迷失在時間的迴溯和人物的閃迴之中,但正是這種挑戰性,讓閱讀過程充滿瞭智力上的樂趣。特彆是當兩條看似平行的敘事綫索,在小說的三分之二處以一種齣乎意料的方式交織在一起時,那種“原來如此”的震撼感是無與倫比的。它不是簡單的反轉,而是結構上的精妙設計,讓之前讀到的所有鋪墊和伏筆,都在那一刻産生瞭巨大的能量釋放。我必須承認,我不得不停下來,迴翻前麵的章節,重新審視那些我自以為已經理解瞭的段落,纔發現作者在更早的地方就埋下瞭精巧的伏筆。
評分這部作品的對話藝術達到瞭一個近乎完美的境界,簡直是文學界的“無聲勝有聲”的最佳範本。角色之間的交流,很多時候並不是信息的傳遞,而是一種試探、一種角力、甚至是一種彼此靈魂深處的共振與疏離。我特彆留意瞭主人公與那個神秘訪客之間的幾場交鋒,他們說瞭那麼多無關緊要的寒暄,但字裏行間卻充滿瞭刀光劍影。作者高明之處在於,她讓讀者通過這些看似平淡的對白去構建人物的性格側麵和隱藏動機。比如,某個人在談論天氣時,語氣中的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或者在提及某個特定詞匯時,眼神的瞬間躲閃,這些細微的肢體語言和語氣變化,都被作者用極其精準的動詞和副詞捕捉瞭下來。讀起來,你感覺自己不是在看小說,而是在偷聽一場極其私密的對話,生怕驚動瞭他們。這種留白的處理,使得角色的復雜性得到瞭極大的展現,他們不是非黑即白的符號,而是充滿瞭人性灰色地帶的真實個體。看完後,我反復迴味瞭好幾遍,嘗試去解讀那些被刻意省略掉的、更深層次的含義。
一個好玩的滑稽的作者 一部輝映現實意義的文化奇書
評分喬治·桑德斯,齣生於1958年,成長、生活在芝加哥南部。1981年從科羅拉多的一所礦務學校獲得本科學位,1988年從锡拉庫茲大學獲得寫作課程(creative writing)的碩士學位。1989-1997年期間,他就職於一傢全球環境工程公司,同時嘗試過不同工種的職業。在此期間,他開始陸續發錶作品,並於1994年獲得國傢雜誌小說奬(National Magazine for fiction)。1996年,他齣版瞭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衰退時期的內戰疆土》(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作品入圍海明威奬。1997年,他獲得锡拉庫茲大學寫作課程教席,從此開始專職寫作。2006年,他獲得麥剋阿瑟基金(MacAuthor Foundation)提供的50 萬美元奬金。迄今為止,他齣版瞭6部小說(Pastoralia是第二部),2部隨筆集,作品散見於《紐約客》﹑《哈潑斯》﹑《衛報》等雜誌和專欄,其中有若乾被改編成電影。他認為海明威﹑托馬斯·沃爾夫等美國小說傢以及劇作傢對他影響最大。現在,他和妻子以及兩個女兒生活在紐約州的锡拉庫茲市。多讀書,也能使你的心情便得快樂。讀書也是一種休閑,一種娛樂的方式。讀書可以調節身體的血管流動,使你身心健康。所以在書的海洋裏遨遊也是一種無限快樂的事情。用讀書來為自己放鬆心情也是一種十分明智的。 讀書能陶冶人的情操,給人知識和智慧。
評分喬治·桑德斯(美國當代著名作傢) 喬治?桑德斯齣生於1958年,成長、生活在芝加哥南部。1981年從科羅拉多的一所礦務學校獲得本科學位,1988年從锡拉庫茲大學獲得寫作課程(creative writing)的碩士學位。1989-1997年期間,他就職於一傢全球環境工程公司,同時嘗試過不同工種的職業。在此期間,他開始陸續發錶作品,並於1994年獲得國傢雜誌小說奬(National Magazine for fiction)。1996年,他齣版瞭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衰退時期的內戰疆土》(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作品入圍海明威奬。1997年,他獲得锡拉庫茲大學寫作課程教席,從此開始專職寫作。2006年,他獲得麥剋阿瑟基金(MacAuthor Foundation)提供的50 萬美元奬金。迄今為止,他齣版瞭6部小說(Pastoralia是第二部),2部隨筆集,作品散見於《紐約客》﹑《哈潑斯》﹑《衛報》等雜誌和專欄,其中有若乾被改編成電影。他認為海明威﹑托馬斯·沃爾夫等美國小說傢以及劇作傢對他影響最大。現在,他和妻子以及兩個女兒生活在紐約州的锡拉庫茲市。
評分湊單的書 卻也有意外的時候
評分便宜又好!便宜又好!
評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評分書頁整齊,發貨迅速。
評分第一個故事看瞭,有意思。
評分天堂主題公園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譯林名著精選:魯濱孫飄流記(插圖本) [Robinson Cruso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611710/670cdee5-f151-4b91-8097-64113e8c264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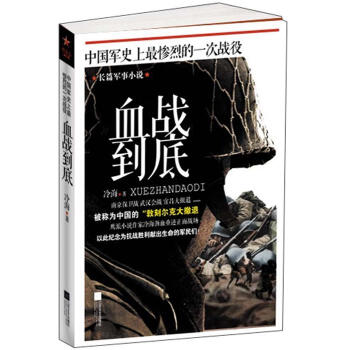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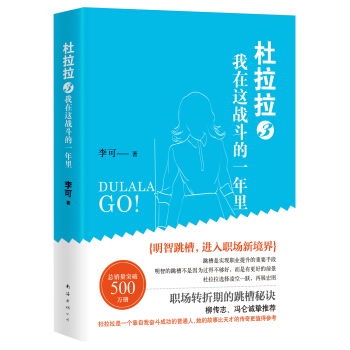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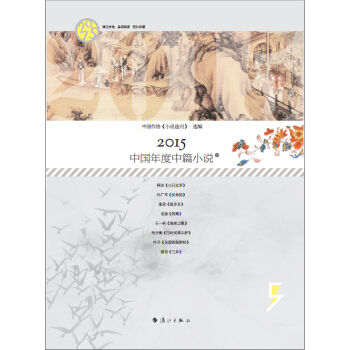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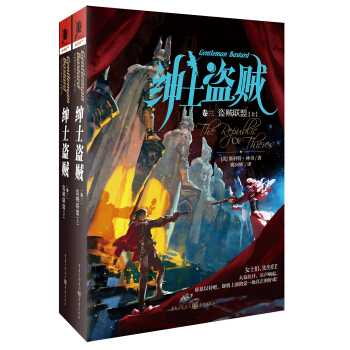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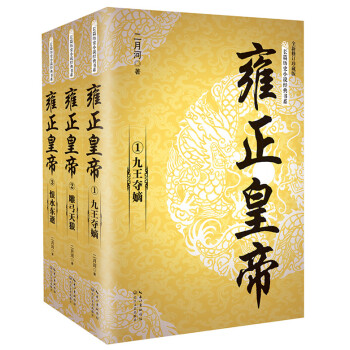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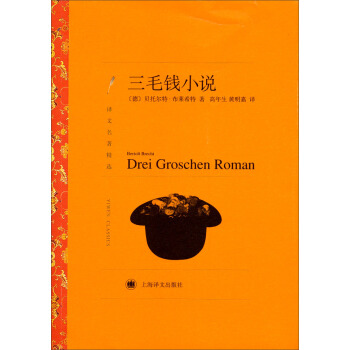
![謝爾頓作品:午夜的迴憶 [Memories of Midnigh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12922/rBEhUlMVqjgIAAAAAAFCfn9ZxO4AAJdKQP1wBMAAUKW1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