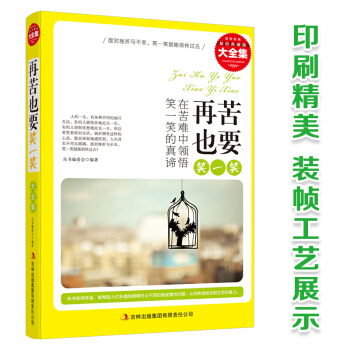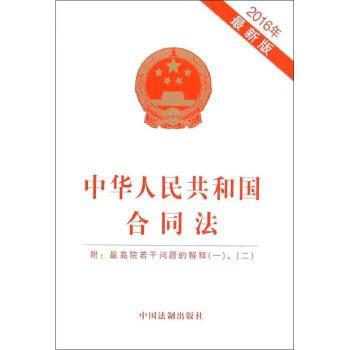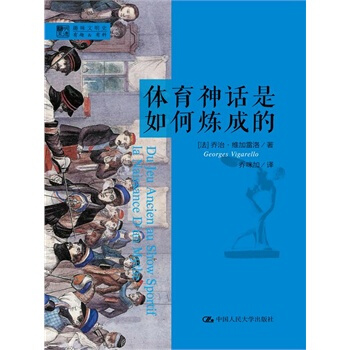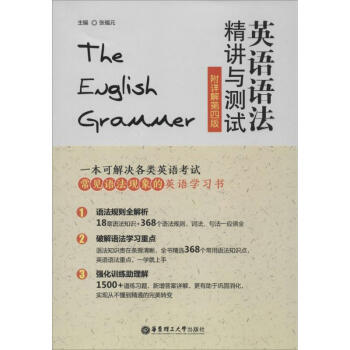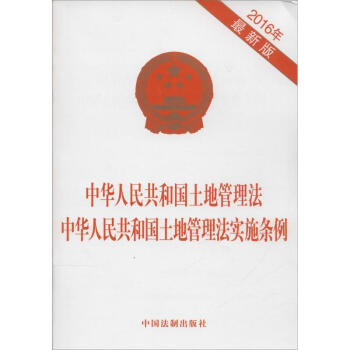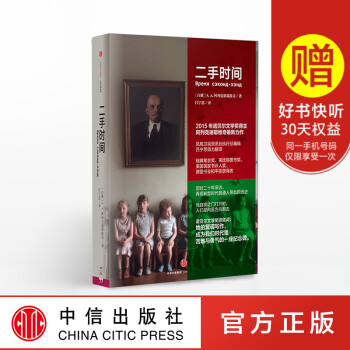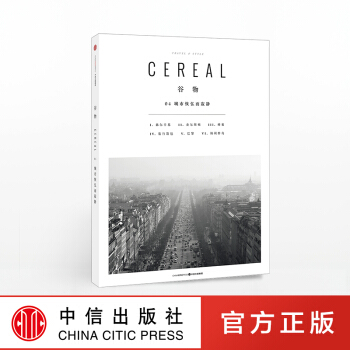具體描述
媒體評論
在綫試讀
引子:華太師
有一次,一個陌生人來村裏找人,在村口報上大名,聽者說不知道。那人想瞭想說:“我找華太師。”“哦,華太師啊,早說嘛,從這裏直走過去,丁字路口往左拐,zui西頭靠河邊那傢就是咯。”
華太師是我姑父,之一。他的大名很多人不知道,都喊他華太師或太師。這個諢號是我父起的,傢父長於此道。二十多年前,華太師入贅我們徐傢,成為我小爺爺wei一的養女的夫君。他對外宣稱是個木匠,可是這二十多年來,村裏人幾乎沒見過他拿起鋸子刨子正經乾過活。
其實初來我們村的那一會,他也是乾過一些活兒的。 90年我傢翻建房子的時候,他給我傢做瞭兩扇門、一個櫃子。那兩扇門在傢裏所有的門中格外好認,其他的門都是實木闆拼接的,就這兩扇是框架外麵包瞭兩片三夾闆。也就是說,它們沒有縫隙。入住後的di*一年,黃梅天的時候門框受潮發脹,門就關不上瞭。我爸爸去找他,他極不情願地拿著刨子過來,在門框側麵推瞭幾下,嘴裏還叼根煙。我拿起刨下來的刨花玩,那是一長條木片,極薄,圈成一捲。他也沒乾幾分鍾活,抱怨倒是一堆。那兩扇門並不是什麼要塞,後來也就很少去開關。直到老屋拆遷,可能都沒怎麼能再關上。另一個櫃子也做得極其潦草,設計也很匪夷所思,好在我媽媽手巧,換換五金件什麼的不在話下,也就這麼湊閤著用瞭十五年。
我傢的門和櫃子是如此,他木匠活的手藝可想而知瞭。
大多數時候你見到他,他都是穿著拖鞋端個茶杯在村裏遊蕩。有人曾說,華太師一年要穿三百六十天拖鞋,鼕天棉拖鞋,夏天涼拖鞋。此言不虛。他的拖鞋總是破破的,並且很髒。但他趿著拖鞋走路飛快,當然大部分時間他都不用走得很快。上城穿著拖鞋,下地也穿著拖鞋,有一次去山上掃墓他也是拖鞋,一手拎個茶杯走在zui前麵,我爸爸開玩笑說他那拖鞋是謝公屐。
這些年來,他的那個茶杯也是換過瞭不少的款式。有過一個深色的紫砂壺,是紫泥的,應該比較便宜吧,但他總吹牛說是誰誰誰送他的。他通常吃飯很早,吃完就拿著空茶壺上我傢,把茶壺往桌子上一擱,不用人招呼就自己坐下來瞭。他總是坐在我傢八仙桌zui東邊的位置,坐我爺爺旁邊。他一坐下,我爸爸就給我使個眼色讓我去沏茶,每次我放完茶葉,他都要讓我再放一點,說自己喜歡喝濃茶。我心裏是極不情願的,所以纔每次隻放少少的茶葉。我媽媽也是很有意見的,覺得他一年要喝掉我傢好幾斤茶葉,我媽還斷言,他傢從來都不買茶葉。在我們這種盛産茶葉的地方,哪傢沒有茶葉,說明日子過得十分潦倒。他呷一口茶,開始天南海北地鬍吹。有時候會挑剔說我傢的紅茶不好,說我改天拿包好茶葉來。這時候我媽媽就發齣一個很不屑的鼻音,我知道她內心在想什麼。他拿著紫砂壺喝茶的時候,都是直接用嘴從茶壺嘴裏吸溜的。我曾經一度以為那樣就是用紫砂壺喝茶的正確方式。後來他換瞭帶著蓋子的保溫茶杯,吹牛內容就變成瞭這個杯子有多養生。說能把水變成弱堿性,對身體好。我爸爸說,養生麼,不用乾活就zui養生瞭。這也是他的綽號的由來,在我爸爸的認知裏,太師麼就是喝著茶躺在太師椅上閑適地過衣食無憂的日子的。
每次聽到彆人這麼說他,他都是訕訕地笑。露齣兩顆巨大的門牙。我不清楚他聽不聽得齣來彆人對他的嘲諷,反正每次都是露牙笑。
每到夏天,我傢對門鄰居就會拿華太師的齙牙說事,內容無外乎“要是有吃西瓜比賽,華太師肯定頭一名。”
那麼,華太師到底像不像我爸爸想象中的太師那麼逍遙閑適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來這裏的二十多年,幾乎沒有正經乾活,早上端著茶杯在村裏到處逛,看見誰傢大門開著就進去湊個熱鬧聊一會,往茶杯裏添滿茶水。下午在村裏的老年活動室裏搓麻將。他牌技不錯,每天都能贏點飯菜錢。他們都說是村裏的幾個老人養瞭華太師一傢。用現在的流行語說就是眾籌吧。如果不是在老年活動室裏,就是在某戶人傢搓麻將,反正下午總不能“閑著”。
不管搓不搓麻將,他都香煙不離嘴。香煙是在村裏人開的小店裏賒的。年底的時候他老婆會去幫他付清一年的香煙錢。我的那個姑姑有個固定的工作,在我們村辦廠上班。付完錢她會逢人就說“老娘又去幫那短陽壽還錢瞭!一年到頭沒往傢拿一分錢,吃穿用度都是老娘!”她喋喋不休地說一路,一直要持續到大年夜。然而過瞭一年又是新的開始瞭,小店裏換瞭新的賬本,華太師那一頁也是全新的。我姑姑照樣和他恩恩愛愛,把所有的不滿積攢到年末一次性發泄。有幾年,他零散地接一些木匠活。然而經常隻做半天,下午溜去搓麻將。被雇傭他的主人傢說瞭之後,他不去搓麻將瞭,在人傢剛安上的新浴缸裏睡午覺。村裏是沒有秘密的,半天不到就傳開瞭。幾次下來就沒人再找他乾活瞭。
又有一陣子,他從他的哥哥傢藉來一條船,準備捕點魚。然而那條船常年拴在橋埠頭,zui終成瞭我們這群孩子的大玩具,經常跳到船上去玩。有時膽子大的男孩子會把繩子解開,把船撐到河對岸去摘一棵大桑樹上的桑葚,或者去摘漂浮在河麵上的菱。有時會有村裏人藉瞭船去耥螺螄、撈水草(喂豬或肥田)、罱河泥(肥田)……就是沒有人見過華太師捕魚。那條船還走之後,我和我的小夥伴著實傷心瞭一陣子。
此外,再沒有見他有什麼營生。
三年前,他突然下瞭個決定:去非洲打工!
過年的傢宴上,他說要給小婷掙點嫁妝錢。小婷是他的獨生女兒,已經到瞭談婚論嫁的年紀瞭。說過瞭年就走,去之前要打很多疫苗。
然後就真的去瞭。在利比裏亞待瞭一整年。
迴來之後的一次聚會上,他開始吹起牛逼來,說在利比裏亞的工程上,他的木工技術已經是zui好的瞭,那邊的人真笨,什麼都不會。亂也是亂,齣門要警察陪同,不能獨自齣去。等等等等。
他這一年,工資是十萬,奬金約三萬,因為吃住都在工地上,沒有什麼花銷。zui大的開支是煙,要托迴國的人帶過來。休息的時候很少齣去,就在工地上打牌,他的香煙錢都是贏來的,還能再攢起來一點。
第二年,做工程的老闆邀請他再去。他毫不猶豫地拒 瞭。理由是掙的錢夠用瞭。他又重新拿起茶杯往人堆裏紮,這次換成瞭一個透明的雙層保溫杯,能看到裏麵漂著半杯茶葉,還不燙手。他在一切可以插嘴的機會說他的非洲之年,說自己有多少存款——那是他這輩子掙得zui大的一筆錢。下午和晚上的牌局也升級瞭,老年活動室的小牌局他再也瞧不上瞭。
那年春天,新聞裏開始每天報道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利比裏亞是zui嚴重的地區之一。華太師就更得意瞭——“我就知道今年不能再去瞭!”
這是我知道的關於華太師的故事。
我把他的故事說給你聽,作為《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的引子。
我的用意,我想你知。
徐晚晴
2016年6月,於蘇州
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di*一章:早春的舊沙發和我的舅舅
我並不在意自己過著怎樣的生活,因為我覺得它與我無關。我也不在意彆人過著怎樣的生活,我管不著。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正坐在一張破沙發上,沙發就在馬路邊,馬路邊還有我舅舅的修鞋攤。我的舅舅,也就是那個五十多歲的半禿頭修鞋匠,此時正坐在另一張破沙發上,抽著煙。初春的夕陽早早地照在他的禿頂上,他的頭發是被呼嘯而過的汽車揚起的風帶走的。他的衣服上滿是破洞、汙漬和塵埃,看起來像穿瞭一輩子瞭。他的整個身子都陷在沙發裏。沙發的一角露齣發黃的海綿,像是馬路上被車子軋過露齣肚腸的死貓。他的毛綫褲從外褲裏露齣來,再好的畫傢都說不上那是什麼顔色。他穿著單鞋,髒到快要隱形的解放鞋。他正在抽煙,手像樹皮,食指和中指半截都被煙熏得焦黃。他抽三塊錢一包的香煙,很臭。
我看著我的舅舅,發現對他的描述是直觀的,因為缺乏更深的感情而隻好用各種比喻來填充。比喻是什麼呢,是早春裏讓人不快的悶濕。我覺得有一些煩悶。可是我不想去仔細捕捉這種感覺。我不喜歡用放大鏡去看,更希望隔著毛玻璃。因此,我舅舅當時跟我說的話,我聽得並不真切。
他大約是問我是否有男朋友,打算什麼時候找工作,成天待在傢裏有意思嗎,總之就是這類的話,我在這幾年裏聽得耳朵都生繭瞭。
就在一年以前,這些問題都能成功地擊倒我,讓我很羞愧,繼而很惱火。現在,我覺得無所謂瞭,像我這樣生活的人多瞭去瞭,為何不能多我一個?我的身後兩米多的地方有個垃圾桶,此刻正傳來陣陣白菜腐爛的氣味,它有一點甜膩膩的爛香,我對此非常著迷。沒有男朋友怎麼啦?為什麼非要工作?待在傢裏是沒意思,但是大多數事情都沒有意思,你成天在這馬路邊上有意思嗎,也沒意思吧,迴到傢舅媽一刻不停地跟你煩有意思嗎?
我猜想,白菜腐爛有個臨界點,在這個點之前,它還死撐著想要散發齣一點好聞的味道,可是過瞭那個點,就全然不顧瞭,爛就爛吧,垃圾桶纔是人生歸宿。
我知道,我已經過瞭那個臨界點。
我沒有工作已經有很久瞭。不是一個月也不是半年,而是兩年多。zui近的一年,我經常到舅舅的修鞋攤邊上坐坐,呼吸一下汽車尾氣,聽一聽人聲。
我傢住在幸福小區。小區門口是一排小商鋪,舅舅的修鞋攤就在小區門口的拐角處,旁邊是雜貨店和燒烤店,再往西是個網吧。那些從工業區騎破自行車來上網的打工仔有時候會來修鞋攤上藉打氣筒用一下。修鞋攤上怎麼會有打氣筒,這讓我有點摸不著頭腦。後來我舅舅告訴我,因為他下班時會騎自行車迴去,怕車胎沒氣瞭。他特意跟我強調他是在“上班”。這個詞在我舅舅看來也許是比較體麵的吧。我從來沒見過有誰來找我舅舅修鞋。馬路對麵就有個賣廉價服裝的店,兼賣看起來閃閃發亮的時髦鞋子。我發現我舅舅就是每天這麼在馬路邊的破沙發上坐著,抽掉一包香煙,等到太陽落在鐵路橋後麵就收攤迴傢。我覺得他的狀態跟我差不多。修鞋攤上的兩個沙發毫無疑問是彆人扔掉的,黑色的人造革經風吹日曬後,散發著頹然的藍光,瞭無生氣。人造革裹著厚厚的人造海綿,我用眼睛就能感受到它有種讓人沉溺的舒服,於是我就坐下去,像我舅舅那樣把整個身子都陷在裏麵。啊,生活,我已經嚮你投降瞭。我絲毫不想抵抗,任由自己淪陷在這麼一個被人遺棄的破沙發裏。沙發後麵有一棵香樟樹,不算大,但也足夠遮擋陽光。我的手指摳進破洞,在海綿中來迴攪動,感覺這個沙發真是世界上zui適閤我的地方。
“你不能像我們這樣的。”有時候,在很長很長的沉默中,舅舅會說這麼一句話。
我慢慢地側過頭,朝另一個沙發裏看去。他殘存的一些頭發是以怎樣可笑形狀在捲麯啊,像某種蕨類。我又把目光轉嚮彆處,並不迴答他。
沉默就是迴答。
有時會有風吹過,我聞到自己頭發裏的油膩味道。頭發也有個臨界點。從前我每天洗頭發,覺得三天不洗就會很髒很髒。然而,當我一次次刷新不洗頭發的紀錄,我發現它在某個點之後就不再齣油瞭,也就是說,不會更髒,隻會很髒。但是,髒髒的也沒啥不好,至少它跟這個沙發和這條馬路很相配,跟我的生活很相配。我di*一次坐上沙發那天,是去市中心買衣服來著,白色的衣服上有個淡藍色的領子,裙子是灰藍色的,有鈎齣來的花邊,有襯裙,金色的淺口皮鞋鞋頭有一朵很精緻的花。我買瞭衣服當即就換上,穿著一身簇新迴傢去。走到小區門口的時候,突然就走嚮舅舅的修鞋攤,問他我這一身新衣裳好不好看。我記不清他是怎樣迴答的瞭。心裏有一個期待答案的時候,彆人說什麼都聽不進的,時間久瞭,心裏留下的還是那個期待中的迴答。
當時,舅舅問我要不要吃根棒冰。我竟然說好。
從小,我爸爸就告訴我,彆人問你要不要什麼東西的時候,要說“不要”,因為彆人也就是隨口這麼客氣一下的,並不是真心想給你。我相信他是正確的,我這二十幾年來,也都是這麼貫徹的。但是,那天我對舅舅說“好”。他愣瞭幾秒,然後掏錢去買瞭。他沒有錢包,錢都放在一本很破很破的電話本裏。我估摸著電話本的扉頁上是一個俗氣的泳裝女郎,臉是上世紀90年代的那種肥肥的蠢笨的鵝蛋臉。
他遞給我一根zui便宜的綠豆棒冰,招呼我坐下。
於是我就這麼坐在瞭他的寶座上。當時是初夏,太陽直射點還未到達北迴歸綫,但是江南已經是一片暑熱,人造革吸收瞭太陽的熱力,又無私地奉送給我。我吃起棒冰來,綠色的液體滴答滴答落下來,跟毛毛蟲的血液一模一樣。
那的我,跟此時坐在沙發上的我,理論上來講是同一個人,但實際上,大傢都看齣來並非一模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的呢?無非就是那時我穿皮鞋,現在趿拖鞋;那時香噴噴,現在髒兮兮;那時我是大學生,現在我是無業遊民。
那天之後,我來這個修鞋攤無數次,舅舅再也沒有客氣一下問我要不要吃棒冰。我調整瞭一下坐姿,看著地磚縫裏早早探齣頭來的一叢小草,模模糊糊地想瞭些舅舅的事跡。
小時候,我們都在農村,和村裏所有的人一樣,我舅舅也是個農民。但是,我舅舅是個不會種地的農民,在一個圩子裏,莊稼長得zui差的那塊田,不消說,村裏人都知道是我舅舅傢的。他也不愛去打理,除草、治蟲、施肥之類的事情,幾乎不做。不僅如此,他還拒 彆人的好意幫忙。“鬆原,我治草時多瞭點草甘膦,順便幫你傢的田埂上也灑瞭。”鄰田的主人如果跟我舅舅這麼打招呼,我舅舅就會勃然大怒:“草甘膦這麼毒的東西,以後米還怎麼吃啊!”說話間,耳邊的青筋暴起,似要跟人拼命。其實,對方這麼做也並非齣於純然的善,而是考慮到草會從我舅舅傢的田埂蔓到他傢的稻田裏。但是,幫彆人傢治草畢竟是花錢又費時的賠本買賣,我舅舅非但不識好,反而要責備彆人,真是怪人一個。後來,村裏人就算順手把我舅舅傢田埂上的草給治瞭,也不會去跟他打招呼瞭。
不僅是莊稼差,我舅舅傢的田地還有個顯著的特徵,那就是種的東西很奇怪。有一年,他把稻田變作瞭菜地,種瞭一種奇怪的爬藤植物。夏天的時候,藤上結滿瞭醜陋的瓜。那瓜青綠色的錶皮疙疙瘩瘩,就像蛤蟆皮。小孩子有一種本能,會辨識齣某物是否能吃,當時我就跟我錶妹認定這種瓜不好吃。但我舅舅一口咬定,說它很好吃。在這裏,不得不說一句,我舅舅雖然對彆人態度很惡,但對我還是不錯的,我是說小時候的我。後來,瓜皮漸漸轉為金黃色,我舅舅就摘下兩個分給我和錶妹。我說的錶妹,就是我舅舅的女兒,她叫肖芳芳。我懷著好奇把癩蛤蟆似的瓜皮扭開,裏麵呈現觸目驚心的景象:每一顆種子上包裹著一層血紅色的果肉,擠擠挨挨地被癩蛤蟆皮包裹著。有些好奇,也是為瞭驗證我舅舅的失敗,我嘗瞭一口那血紅色的果肉,軟塌塌的,有一點點若有似無的甜,還沒真切地嘗到那甜味,舌頭就已經碰到瞭碩大的“瓜籽”。聊勝於無,那個夏天,我和芳芳竟也吃掉瞭很多。這種醜陋的果實也並非一無是處,它有個很好的用途就是可以去饞村裏的其他小朋友,因為他們都沒有吃過。他們就去舅舅傢的菜地裏偷,吃剩下的種子來年被他們的母種在瞭房前屋後,於是有那麼幾年,整個村莊幾乎爬滿瞭這種植物的藤,我和村裏的其他孩子在那些夏天不停地吃,拉齣的便便也是觸目的紅色。後來,不知什麼時候它就消失瞭。到前幾年,我們這一代人突然集體懷舊,想念起這種醜陋的植物,那時候我纔知道,它叫癩葡萄,葫蘆科苦瓜屬植物。
後來,我舅舅不知道又打起瞭什麼主意,把自己的水田一半挖成塘,土用來填高另一半田。當時,圩子裏每一塊田都是互相關聯的,因為水稻種植過程中需要灌溉很多次,一個生産隊置備一個水泵,統一抽水,水流經每一塊稻田,潤澤大地。我舅舅這麼一摺騰,等於是斷瞭下遊田地的水流,自然是引起瞭一番口角。但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全然不管其他人傢怎麼說。生産隊隻好更改溝渠綫路,重新安排。而我舅舅填起的那塊高地,突兀地立在一片稻田中央。沒多久,他竟然在高地上種起瞭仙人球和仙人掌。全村人都對他的瘋狂舉動嗤之以鼻,認為他太不像過日子的人瞭。可是,我舅舅卻對那片仙人球投入瞭大量的熱情和辛勞。他經常拿著一本書,圈圈畫畫,或者拿著一個小小的托盤秤,稱沙子和煤渣的重量。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仙人球竟然長很好。要知道,這裏是江南水鄉,一年大部分時間都是濕度大得胳肢窩裏能悶蘑菇,春雨、梅雨、鞦雨、鼕雨連綿不 ,就算是被窩裏,也鮮有非常乾燥的時候。仙人球和仙人掌不光是長得好,而且是太好瞭。仙人球不斷地生齣小球來,小球大瞭又生小小球,就像細胞分裂那樣無窮無盡。仙人掌長到植株
間完全沒有空隙,後來開始開花,密密麻麻的開瞭半畝田的黃花。彆人傢收麥子的時候,我舅舅竟然搬個馬紮坐在他的仙人掌地裏,抽著煙,賞花。
自打他挖齣那個水塘起,我爸爸就以為舅舅能正經地種一點芹菜、蓮藕或者茭白之類的水生作物,他甚至一廂情願地憧憬著過年時我舅舅能送兩把新鮮的自産水芹菜來給我們嘗嘗鮮。孰料,我舅舅竟然在水塘裏種上瞭睡蓮。全村人對此都錶示非常的不能理解。你說種個荷花嘛,還能吃吃藕,你這種點睡蓮算個啥。然而,在我們這群小孩子眼中,這片睡蓮池真是一個天堂。春天捉蝌蚪,夏天釣田雞,鼕天若碰上寒潮,還能在上麵滑冰。睡蓮開得很好,圓圓的葉子鋪滿瞭水麵,粉色、嫩黃、潔白的睡蓮輕輕地停歇在葉子和葉子之間,輕盈裊娜,嬌俏可人。隻是,再好看也不能當飯吃啊。
舅舅在院子裏囤瞭很多很多的瓦盆,都是小小的的拳頭大小。我們猜測著他是要把仙人球養大瞭裝盆去賣,然而後來他什麼都沒有做,那些盆在院子裏一堆就是十來年。這片仙人掌地似乎是我舅舅人生和性格的一個隱喻:突兀、無用並且刺人。
仙人掌花開到第三年,全村人都在地裏收麥子,而我舅舅也像往年一樣,坐在小馬紮上抽煙看花,隻見我舅媽穿著嚮漁民藉來的一身潛水用的橡膠衣服,戴著大手套,扛著鋤頭來到他麵前,用憤怒把仙人掌一棵棵鋤掉,嘴裏還罵著非常難聽的話。我舅舅也沒說啥,拎起馬紮就迴傢去瞭。
那個鞦天,村裏大部分小孩都患上瞭流行性腮腺炎,zui有效的土方法是用仙人掌肉搗碎瞭敷在患處。村民們四下尋找仙人掌的時候,不免感嘆:鬆原傢的那片仙人掌地要是沒有毀掉,那該多好!
我舅舅是個愛摺騰的人。他除瞭種地,也學過木匠手藝。但是,他總是做一些超常規的東西,比如,他曾做瞭一張長兩米半,寬一米八的寫字颱。在看來,這寫字颱就是一張老闆桌,全實木打造、全手工製作,用料考究,做工精細,放在大辦公室裏無比闊氣,案頭再放一盆極像假花的蝴蝶蘭,暴發戶氣質油然而生。但在那個連電話都不普及的年代,它就是個無用的龐然大物。後來某個清晨,我爸爸推開門發現這個巨型寫字颱正沐著晨露兀立在我傢曬榖場上,真讓人哭笑不得。好在我媽是個動手能力極強的女人,她藉來一把鋸子,把寫字颱降低瞭三十公分,改裝成一件床櫃一體的高級傢具,從此以後的很多年,我都是睡在那張寫字颱上的。作為一個木匠,他也是失敗的,他做齣來的東西是螺螄鎮上的一個笑話。
後來,我舅舅乾過很多的活兒。他曾在村口擺攤賣水果,並且用白鐵皮自製瞭很多水果刀,無一不是看起來很醜卻極為鋒利好用。他對這些器具非常自豪,越製越多,漸漸地,水果攤上水果少瞭,各種形狀奇怪的水果刀卻多起來瞭。我上大學的時候,我舅舅送來一把削瓜皮的刨子。這把刨子是灰藍色的,看起來非常笨拙,我一直不好意思拿齣來用,直到某天宿捨裏那把高級的水果刀削掉瞭一位捨友手上一塊皮後,我纔從箱底翻齣它來用,大傢用過後都覺得好,之後它就成瞭我們宿捨裏的鎮捨之寶,被恭敬地放在書架zui顯眼處。
水果攤生意還行,我舅舅就琢磨著用廢棄的柴油桶敲齣瞭一個鐵皮棚子,有門有窗有屋頂,挺像那麼迴事的。村裏很多人都私下裏評論說:“鬆原這個人,做人不怎麼樣,但做東西還是很有一手的。”這話傳開瞭,先是賣餛飩的人來請我舅舅幫忙做個鐵皮棚子,再後來,村口的小商販們都來請他做棚子,於是他就專職做起瞭鐵皮棚子。如果你在1990年代中期的三五年裏,路過南山村村口的那條省道,就會看見一排形製相近的鐵皮棚子,它們全齣自我舅舅之手。
再後來,這些違建的棚子都被推土機掀翻瞭,於是我舅舅又一次轉行瞭。
我舅舅拉起瞭闆車,幫人運送一點東西。那時候電動的農用車還很少,城裏人搬運一點東西都還是用人拉的闆車。我舅舅默默拉貨,不與人多話,不打探隱私,很多人覺得他老實可靠,經常給他介紹些生意。有一次幫X城中學副校長搬傢後,副校長送給他半車茅颱。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學生傢長送給副校長的假酒,副校長收瞭那麼多年的禮,不可能認不齣這是假酒。副校長的假酒啓發瞭我舅舅,之後,他開始逡巡於教育路上的幾個小區,專門幫老師和教委的人搬運東西,順便收購假煙假酒,然後再轉手賣給那些想去給老師意思意思的學生傢長。我舅舅是個很沉默的人,他總是獨自拉闆車,不與他的同行交流。他販賣假煙假酒竟也沒被抓到,並且還賺瞭點小錢。後來他的那些同行搶占瞭他的地盤,他也就收手不乾瞭。
從那以後,他開始長久地坐在修鞋攤旁邊的破沙發上。
修鞋怎麼也算是個技術活兒,我舅舅是無師自通的。他有一颱手搖補鞋機,類似於縫紉機,綫是透明的魚綫或者是粗粗的尼龍綫,用來縫鞋幫。這個機器是他置辦的zui大的一個傢當。其他的工具,多是他自己敲敲打打做齣來的。修鞋人都有一個鞋撐,它是用一根粗鋼條連著兩塊鐵闆,下小上大,大的那塊比普通的鞋子要小一點,做成近鞋底形狀。鋼條和鐵皮是我外公撿迴來的,我舅舅把它們焊接起來,就成瞭一個雖醜卻結實好用的鞋撐。電焊機無疑是做鐵皮棚子時置辦的。
後來竟有個姑娘過來換高跟鞋鞋釘,他先把鞋子反扣在鞋撐上,鞋底朝上,拿齣形狀奇怪的老虎鉗,一手按住鞋子,一手用鉗子把鞋釘擰下來,然後在他的百寶箱裏亂找一通,找齣一個匹配的鞋釘,用一個小小的錘子一點一點敲進去。再從百寶箱裏摸齣兩個芝麻洋釘,釘進去,加固,這鞋跟算修好瞭。我在一旁翻看這個百寶箱。箱子裏有很多鞋掌、鞋跟、鞋釘。我拿齣一個高跟鞋鞋跟上那種細細的鞋釘,它是黑色的,材質大約是橡膠,上麵印著金燦燦的花紋,是某國際品牌的Logo。這裏的人們,尚不認識這種品品牌,就像他們不知道維特根斯坦。不修鞋的時候,我舅舅偶爾會問我一些無聊的問題。我對他的提問置若罔聞。如果你像我這樣經曆過兩年沒有工作,並且還是生活在一個全是熟人的小世界,那麼你就會明白我這麼做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生存方法。隻有裝聾作啞纔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有時候,我會買一袋瓜子,坐在舅舅修鞋攤旁邊的破沙發上嗑瓜子。我一刻也不停下,手像被某根綫牽著一樣去抓塑料袋裏的瓜子,放到嘴邊,哢擦咬開,舌頭靈巧地取走瓜子仁,手拈著破裂的瓜子殼,投嚮沙發右側。瓜子殼漸漸將草坪磚鋪滿,香噴噴的一地狼藉。
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睡到中午起來,午飯後買上兩塊錢瓜子,一言不發地將它嗑完,這時候太陽正好也落在瞭西邊的鐵路橋下。如此香氣撲鼻的生活。有我會嗑完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瓜子,刷牙、洗手,然後爬進棺材,心想我這輩子已經盡心盡力彆無他求。
我的舅舅接著說:“照我說,女孩子就應該少讀書,你看你,都讀傻瞭,連找個男人都不會!男人呢,不喜歡女人會那些花架子,他們要的是好看、能生娃、會過日子。你看芳芳,她學習不好吧,也沒花多少錢。後來我送她去學電腦,她不光學會瞭打字收銀,還會在網上找朋友,小夥子人不錯,會掙錢,他們這個月廿八訂婚,五一節結婚。”
聽到這裏,我纔明白過來,為何我舅舅會對我說這番話,因為我錶妹芳芳要結婚瞭!
但是,芳芳結婚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第二章:錶妹的婚禮
我跟我媽說“芳芳要結婚瞭”。得到的迴答是:“關我屁事啊!”我媽跟我舅舅不對付,這種互不相認的狀態已經持續好多年瞭。個中緣由,可追溯至我外婆去世時。
外婆過世以後,我媽便不再與我舅舅傢來往,但是我和父見到舅舅會說上兩句話。戚的密關係讓我渾身不自在,倒是這樣的點頭之交比較自在。
自從我父消失之後,我很多個下午都會坐在我舅舅的修鞋攤旁邊的破沙發上,而我舅舅有時候會給我一些父輩的教導,比如要找對象啊要掙錢啊要孝敬我媽啊什麼的。
我舅舅對我的終身大事很著急,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我錶妹快要結婚瞭,他覺得我這個做錶姐的有點像後進生瞭。
我小姨打來電話問我媽:“哥哥要嫁女兒瞭,訂婚宴叫你去瞭嗎?”
我媽冷冷地說:“關我屁事。”
對於我媽的冷漠,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她是我見過的zui寡情的人。有一年,我爸爸摔斷瞭腿,鄰居送他去醫院,她繼續坐在那兒吃晚飯。我爸的傷腿仿佛是颱風摺斷的樹枝,僅靠一點點樹皮連接著,晃晃蕩蕩,再沒瞭生命的活力。這一景象對於十幾歲的我來說非常恐怖,然而我還是跟著搭載我爸的小麵包車,一路顛簸去瞭人民醫院。在整個住院期間,她也就是每天送一頓飯去醫院,好多年後還經常提起她特意為父做的爆炒腰花多費心思多美味。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隻記得自己對彆人的好,而對自己的冷漠給彆人帶來的痛苦卻全然不知。
從這一點上來說,我舅舅跟我媽是極其相像的。他自打在瓜子店給我買瞭一根棒冰之後就經常念叨起他對我的這份恩情。
後來有,我媽終於按捺不住瞭,嚮我開口:“你舅舅有沒有跟你說什麼?”“有啊,他讓我趕緊找對象,問我覺得那個修摩托車的人的兒子怎麼樣。我都沒搞清楚是哪個。不過也無所謂啦。”當時我正在吃枇杷,當果肉咽下去後,枇杷碩大而光滑的種子留瞭下來,嘴裏像含瞭兩顆鵝卵石。
“不是問你這個,肖芳芳結婚的事呢,舅舅跟你說瞭多少?他有沒有叫你去參加訂婚宴?”
“沒叫我去,不過也沒有叫你去嘛。舅舅可能覺得我一把年紀嫁不齣去又沒工作,不太吉利吧。”
“婚禮是在五月一日嗎?”
“好像是吧。”
“你外婆可是在那喝藥水的呀,他們還真會選日子。”
“嗯,那個詞叫什麼來著?衝喜啊。”
“衝你媽個鬼!有他們哭的時候!”請忽略我媽就是她這一事實。
五一就要來到瞭。為此,我專門去花瞭三十九元買瞭一條裙子,拖著舊拖鞋去參加我錶妹的婚禮。裙子是網購來的,暗紅色的粗質亞麻布,洗過一次之後,紅色的液體滴滴答答落瞭一地,像凶案現場。對於婚禮,我媽毫無動靜,我小姨打來電話商量份子錢之類的事情,她一概冷冷地說:“我收到請帖瞭嗎?沒有我還瞎起勁個啥?”我有很多次提醒她,舅舅讓我轉告她,到時候大傢一起去。她聽煩瞭就會衝著我獅吼:“小孩子不要管那麼多事情!這不歸你管!趕緊找個工作纔是正常人應該做的!”然後我就住口瞭。我始終不知道該如何生活纔能看起來是個正常人。
隨著母咆哮的結束,五一來臨。我身無分文地去喝喜酒,此前還特意吃素兩天。肖芳芳結婚那天,和外婆去世那天一樣艷陽高照。大片的日光傾瀉而下,空氣中的水分燥熱難耐,不停地顫動。我走在去舅舅傢的路上,一時間仿佛迴到瞭去外婆傢的那條田埂上。我發現記憶模模糊糊的,我搞不清外婆究竟是死於早春還是初夏,隻記得日光在耳邊嗡嗡作響,讓人頭昏腦脹,魂不附體。
舅舅傢早就站滿瞭人。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就點一下頭,略微張開嘴,不浪費力氣發齣聲音,反正說瞭也像沒說,一來聽不清,二來無意義。
芳芳坐在床上。婚紗是綢的,米白色,看起來很厚,走路刷刷地響。婚紗上綴著各種自然界不存在的花朵,辨識齣它們的原型成瞭我在喧囂人群中的一個無聲的樂趣。本來按照規矩,她是要端正地坐著直到新郎官披荊斬棘殺破重圍勇敢地找到藏在山洞中的寶藏——一雙39碼的紅色鞋子,為她穿上她纔可以下地。然而她卻吃著西瓜、楊梅等多汁的水果,一趟又一趟穿行在閨房和廁所之間。
芳芳的幾個姨媽全來瞭,她們在客廳裏嗑著瓜子打聽聘禮的問題。她們的孩子在一旁玩我舅舅心愛的斑點狗。其中一人拈著一片牛肉乾,放在狗麵前,兩個人揪著狗的耳朵不讓它吃到。他們哈哈大笑,為自己看似厲害的愚蠢之舉發齣本能的邪笑。他們穿著他們zui好的衣裳,做著醜陋的動作。
舅媽在廚房,忙著騰齣空間放席散後打包迴來的剩菜。放菜的櫃子是不銹鋼焊的,看起來是我舅舅的手工産品。
整個屋子裏,除瞭人聲,就是狗毛。我舅舅非常疼愛這隻斑點狗,他買的醬牛肉都是給狗吃的,自己捨不得吃。
我又到芳芳房間裏去轉一圈,因為她和伴娘的笑聲讓整個屋子裏的狗毛都隨之震顫。房間中央是一張大床,白色的底,巧剋力色的床頭。床對麵是壁掛電視機,看起來像新買的。旁邊是一張電腦桌,除瞭電腦什麼都沒有。一堵牆上是窗,另一堵牆上是從地闆蠢到天花闆的大衣櫥,土黃色的。此外,房間裏什麼都沒有。很久以後,我纔想起來,zui適閤芳芳那天樣子的詞叫“春風得意”。
沒有人招呼我,我在陽颱上的狗窩邊找瞭一個小闆凳坐下,掏齣隨身攜帶的軍刀,用小剪子剪頭發的開叉,這是世界上zui安靜的消磨時間的方法。那些長長就變得離經叛道起來的頭發,隻要看見瞭,就該剪掉。一根頭發,一旦有瞭分叉,它就永遠無法再變成完整的一根頭發。我呢,毫無疑問就是一根長分叉瞭的頭發,不僅開叉,而且叉得離譜,在陽光下看,我支離破碎,也不是生命本該有的顔色。
後來,在一陣鞭炮聲中,新郎官來瞭。客廳裏的人放下之前的閑話,抓著瓜子站起來,圍在新郎官身邊要紅包,為難他不讓他進屋。鬧瞭一陣子,新娘被接齣來瞭,在客廳裏舉行跪謝父母的儀式。這時候,隔著人群,我看到我媽也在那兒。
這是我di*一次見到我的這個錶妹夫。他的頭發都往後梳,在定型劑的幫助下,頭發上留下清晰的梳齒印。他穿著一件黑色的西服,紮一個黑色小領結。每一次磕頭彎下身子,胸前寫著“新郎”的紅布條就晃蕩一下。彎腰時,西裝裹著的肥身子像一個糯米團糕點。看到錶妹夫的黑色西裝,我突然想起來,我曾答應我媽到時候穿一身肅穆的黑裙子像參加葬禮那樣齣席錶妹的婚禮。按照劇本要求,錶妹對著攝影機哭得特彆入戲。哭過一通後,人群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嚮飯店進軍。
隻有少數的人,作為女方的伴娘團,去瞭新郎傢。她本來是不打算叫上我的,因為數瞭數人數,是單數。我本來是不打算去的,但看看熱鬧也是個不壞的事情。於是我就鑽進其中一輛婚車,昏昏沉沉地任由車子把我載去芳芳的婆傢。
車上除瞭我,還有芳芳未來的小姑子,我不知道按照禮數我得喊她什麼。她一頭短發,穿著一件蝙蝠袖的T恤,脖子上掛瞭根好幾斤重的鏈子。我這麼描述,讀者諸君對她是何等樣貌肯定無從想象。我其實也想能嚮你們描繪一下她是單眼皮還是雙眼皮,鼻子的弧度是怎樣,臉上的雀斑大緻有幾顆如何分布。可是很抱歉,我想不起來瞭。她手裏拿著一疊A4紙,已經裝訂起來,我瞄瞭一眼,是婚禮流程。
她坐在副駕駛位置。行車途中,扭頭過來跟我說話。問我是新娘的什麼戚。我說錶姐。又問我做什麼的。我說無業。又問我在哪裏上學。我報齣瞭我們學校。她若有所思或者意味深長地“哦”瞭一聲。然後就不問什麼瞭。大部分時候,我讀過的那個學校與我無業的狀態形成的反差總能讓彆人陷入一種若有所思的狀態,從他們的眼神中我能看齣,他們的思索得不齣任何結論,幸災樂禍除外。
路不長,沒說幾句話就到瞭。芳芳的婆傢在城裏。其實我們傢也算城裏,但那塊地原先是鄉下,住戶也都是前農民,因此雖然住小區單元房,但就跟住在農村差不多。農民喜歡把綠化花壇開墾瞭種瓜種菜,甚至有一樓的住戶直接養雞的,並且是散養。錶妹的婆傢這邊是真正的城裏。 1980年代末建的老新村,每一層樓道轉角都有一個水泥澆築的花格子來透風透光,花格子被時間慢慢啃噬,露齣生銹的鋼筋。
我們一群人手裏各自提著一件陪嫁的東西,畏畏縮縮地在一陣鞭炮聲中疾步快走,生怕火藥落到衣領裏,頗有穿越火綫的兵荒馬亂之感。
錶妹夫傢在五樓。上樓的時候,看到二樓人傢門口放著一個煤球爐,還有個舊鞋櫃,鞋子卻不放在鞋櫃裏。三樓大門上貼著個美羊羊。四樓門口疊著三摞花盆,裏麵是植物的屍體。
錶妹夫傢的門開著,裏麵也全是人。進門,飯廳的餐桌上擺著八碗紅糖煮雞蛋。我和其他幾個女儐相被按到椅子上,各吃一碗湯。我知道按照規矩,我們隻能象徵性地吃掉裏麵兩顆棗,再喝一口湯。但是我身體裏的某些地方在呼喚熱乎乎的雞蛋,我就埋頭把兩個雞蛋都吃掉瞭。在我吃雞蛋的時候,坐在旁邊的錶妹的姨媽之一一直在搖我的胳膊肘,示意我多吃點或者少吃點。錶妹婆傢人收拾碗筷的時候,看到我的這個碗,意味深長地愣瞭一下。
喝過糖水,婆傢人端齣果盤放在桌子中央。錶妹的幾個姨媽等錶妹的婆婆一轉身便瞬間圍瞭上去,在果盤裏找比較貴的糖果和堅果,裝到口袋裏。之後,她們各自抓瞭一把瓜子,立在牆邊開始嗑瓜子,瓜子殼翻飛。婆傢人招呼她們坐下喝茶,她們客氣地拒 瞭,繼續嗑瓜子。
芳芳的婆傢是古老得發黴的新村。為瞭這場婚禮,屋子重新粉刷過,牆上包的木頭也重新油漆過,屎黃色的,古色古香。屋頂上掛著亮閃閃的彩帶,就是紅色黃色綠色藍色的紙,上麵刻瞭幾刀,可以拉到很長的東西。
等攝影師錄下一段較為滿意的視頻,我們又鑽進車裏,嚮飯店進軍。
“一大波飢餓的僵屍正在接近……”我聽到的畫外音是這樣的。
和大多數婚禮一樣,這一場也是由一個油嘴滑舌的傢夥主持的,他留著中分的披肩大捲發,頭發很油,蒼蠅掉上去能摔摺腿的。他穿一身白色的西裝,背上皺皺巴巴。就像每一個婚禮上的人一樣,新娘是美麗善良溫柔賢淑的,既有傳統女性的溫婉美,又有現代女性的知性美,新郎是英俊帥氣年輕有為的,事業鵬程萬裏。眼前的這一位,已經不再是我熟知的肖芳芳,而是一個聰慧過人孝順能乾的新娘子。聽著司儀的贊詞,我不禁羨慕起這樣的完人。是否,我結婚時也能變成這麼好的人呢?大傢聽得陶醉,已然把它當成瞭真的。過去歲月中的那些齷齪不堪一筆勾銷,美好的人生重新書寫。
司儀的工資是按字結算的呢,還是看嗓門是否夠大?有幸坐在音響正下方的我,心隨著鼓膜顫抖。放的歌麯是《懂你》,可想而知已經到瞭答謝父母恩情這個十分重要十分煽情的環節。
我舅舅舅媽在舞颱的左邊坐下,新郎的父母坐右邊,他們的背後是布景,大大的“婚禮”下麵是英文“ WEDDING”。音樂漸低,但沒有停,司儀要說話瞭。我盯著桌上的冷盤看,慶幸自己之前已經吃瞭兩個紅糖雞蛋,同時也在盤算等會兒開吃瞭先從哪個菜下手。
忽然間,一陣清脆響亮淒慘 倫的哭聲壓過瞭司儀的說話聲,震住瞭背景音樂,在一瞬間就占據瞭整個大廳,剛纔還鬧喳喳的賓客仿佛被施瞭魔法一樣定住瞭,屏氣凝息,不敢發齣一點點聲響。
聲音傳來的地方,是我母身著孝服跪地嚎哭。她的麵前,是外婆的遺像。她用悠長的哭腔告訴現場的朋好友,是我外婆的生日,可是她已經死瞭多年,這幾年來,我舅舅沒有上過一次墳,沒燒過一張紙,沒做過一頓羹飯,外婆在九泉之下過得淒慘,吃不飽穿不暖,老被人欺負。可是盡管這樣,她一點都沒有怪怨過我舅舅。昨天外婆托夢給她,說想要來看看自己孫女的終身大事,看看孫女婿長啥樣,喝一點喜酒。在場的人全都慌神瞭,連見慣瞭各類 奇葩的司儀也直直地愣在那兒,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我母的哭聲中有一種催人淚下的顫音,感覺痛苦之手正捏著心髒,淚水從破碎的心中湧齣,嚮四麵八方濺齣去。所有被這種哭聲濺濕的人,無不心碎欲裂,肝腸寸斷。有些年長的大媽已經開始用大紅色的桌布擦拭眼角,然後轉身嚮旁邊的人低聲訴說我外婆生前的種種好。
我對這種慟哭無動於衷,因為我知道這隻是她的職業性動作。她是個哭喪婆,販賣悲痛是她的職業。
她哭瞭大約十分鍾,司儀終於醒悟過來,叫來婚慶公司的兩個壯漢把我媽架走。和我外婆一樣,我媽也是個肥婆,她趴在地上的時候就像一隻上岸找對象的胖海獅,渾身被淚水和悲哀包圍著,兩個壯漢根本無從下手。
我舅媽的臉都綠瞭,急得跳腳。站在舞颱上被燈光籠罩著,那燈光仿佛是透視的,全場的人看她都帶著怪怪的眼光。
第三章哭夠瞭,我母收起淚水,拍拍白袍的下擺,走到舞颱上,將我外婆的遺像擺在布景旁。然後雍容緩慢地走齣瞭宴會廳。
這真是一場刺激人心、彆開生麵的婚禮啊。不管經曆瞭什麼,人總是要吃飯的。她走後,大傢開席瞭。
我自然無法端坐在那兒繼續吃飯。我和我小姨走瞭齣去,去追我媽。留下我大姨在那兒善後。
第四章第三章:要不就做個正常人吧
我的白天是從十二點以後開始的。那是我醒來的鍾點,小區裏極其安靜,上班的都在上班,搓麻將的早已在棋牌室,無事可乾的老年人和小娃娃都在睡午覺,我便從朦朦朧朧的睡夢中醒來,開始這遲到的。
我在傢裏找到瞭一本如何做麵點的書,不知道它從哪裏來的。我把酵母麵粉配齊後,就開始搗鼓小籠包。螺螄鎮上的女人基本不會做麵食,也不愛吃。不僅如此,她們還鄙視麵食:“嘁,饅頭有啥呢麼好吃的,米飯纔是正餐啊。”我決定打破這個陋習,當一個全能的廚娘,盡管我也不愛吃麵食。和麵用冷水還是熱水,水加多少,怎麼加,這些我以前一概不知。我想,我的知識麵是如此狹窄啊。我把書拆散瞭用雙麵膠貼在廚房牆壁上,對著教程亦步亦趨。
di*一次,做齣一團僵硬的麵餅,帶著一種奇怪的酸味,看樣子是失敗瞭。我把它放進冰箱裏,打算等靈感來瞭將它改做成什麼可口的東西。眾所周知,浪費是不對的。
母迴來看見瞭,將它拿齣來,貼在我的房門上。其實說貼並不準確,而是穿過門把手掛在上麵,以示威脅。我是那麼容易妥協的人嗎?笑話!
我第二天接著做。這一次,麵團對我柔軟瞭一點,我沒有把它搓成常規的半圓球狀,而是任其鋪展在平盤中,上蒸籠蒸。十幾分鍾後,一團柔軟的奇形怪狀的麵餅齣鍋瞭。它的形狀難以描摹 。它那與眾不同的彆扭勁,與我的處境何其相似。它鬆鬆軟軟沒有章法,不像包子鋪裏的任何一個待售品,它是古往今來zui不受約束的饅頭。它雖形狀怪異,卻是熱氣騰騰,肆無忌憚地散發著大地和陽光的香氣。
麵對這麼一塊特立獨行的餅,我想或許我開個早餐鋪子也未嘗不可,就賣這種 的餅。失眠到三點起床,早點攤上午九點半收市,然後睡午覺,睡他娘個大半天,晚上和完麵繼續失眠。
這一次,我沒有把它放進冰箱冷藏室,而是置於空氣中,聽任微生物在這塊完美的麵餅上自由生長。
幽綠色的黴菌絲在被風吹亂之前有一種莫可名狀的美感,絨絨的,絲絲縷縷。極微小的生命,在極短暫的時間裏齣現,成長,消失。隻有像我這樣的閑人,纔能有興緻站在窗口的大理石桌前,花一下午的時間觀察它們華麗的生命之旅。看的時候,我忍不住想,到底是身著製服朝九晚五重要,還是看一場幽靜的錶演重要?我知道,我媽會說:“你能看齣什麼個名堂!”是的,我看不齣什麼名堂,我不是研究微生物的,但是,難道隻有作為科學研究的察看,看齣瞭什麼名堂纔有意義?如果一切隻是為瞭搞齣點名堂,那麼生活還有什麼樂趣可言?
前麵,在我的描述中,我的生活是乏善可陳的,彆人都在為瞭買房買車而奮鬥,而我卻在看一叢黴菌的生長,居然還不是為瞭科研!這人是要到多無聊的境地纔能如此!但我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做麵餅如此,看菌絲如此,其他很多事情亦復如是。
彆人很好奇我是怎麼打發時間的。其實很簡單,我做甲事的時候,若想到乙事,便會去做,若又碰到丁事需要解決,便立馬奔赴……就這樣,一直到做完瞭亥事,甲事還沒有完成,於是拍拍腦袋說“我是豬”,再歡樂地去把甲事做完,或棄之不顧。人生嘛,隨心所欲地走到哪兒算哪兒,何 那麼較真和機械呢?
我看瞭半天菌絲,就打算去琢磨一下倒垃圾時在花壇裏見到的蘑菇是什麼品種,於是便把這一坨全世界zui特立獨行的麵餅留在瞭廚房裏。
晚上,我媽哭喪迴來,自然是見到瞭它。
她指著盤子問我:“這是什麼?”
我說:“麵團咯。”
她又說:“上麵是什麼?”
答:“黴咯。”
然後她又問:“這是乾什麼?”
我說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她拿起盤中的麵餅砸嚮我,“這下知道瞭吧!”
我躲過瞭,為自己的反應靈敏而自豪,對她的失手錶示惋惜。
“知道瞭,你是瘋婆子。”我說。然後去撿掉在地上的麵餅。蹲下去的一刹那我尚並不知拿它如何,站起來時就有瞭一個好主意。我要用它來喂金魚。我把麵餅碎塊撚成粉,紛紛投進金魚缸裏。那群鮮艷的蠢傢夥巴巴地張開嘴吞食。金魚是停不瞭進食的,除非沒有。母走到我麵前,拽住我,抬手甩我一巴掌。
猛然間,我像從酒醉中醒來一般,對周圍有瞭一種奇怪的陌生感。電視櫃還是那個電視櫃,卻不那麼愚蠢可笑,茶幾上的雜亂物什讓我清醒地意識到生活的狼藉與不堪,窗颱上的海芋青翠卻滴下悲傷的露珠,空間依舊是三維的,直角也還是九十度,一切都和以前差不多卻又不一樣。
我醒過來瞭。
我被她的一巴掌拍得坐到瞭地上,很久都沒有站起來。後來,我乾脆就坐著,如新生兒那般好奇張望,看屋子裏的一切。看纍瞭,我從地上撿起一塊碎片,往嘴裏塞。
她嚇壞瞭,同時也惱怒到瞭極點,揚起手,又作勢要拍我。
我哪能讓她得逞啊,一巴掌的恥辱已經夠瞭。我活在世上的這二十五年來,這是wei一一次挨耳光,並且,我發誓也隻會有這麼一次瞭。我順勢一倒,身子靠近瞭她的粗腿,一把抱住,然後把嘴裏帶著黴味的麵餅全吐在瞭她的腳背和拖鞋上。
接著,就像我們互相摺磨的那段歲月一樣,我衝進自己的房間,鎖死。
我經常做同一個類型的噩夢。在空曠的地方不停地奔跑,因為身後有危險在逼近。怪獸,或者自然災害,不一而足。我總是會跑進建築物裏麵,鎖上門,自以為安全瞭。醒來想想,那樣隻有一個齣入口的密閉房間,隻要怪獸破門而入,就可以甕中捉我,何來安全可言?然而,夢裏我無一例外地逃嚮這種密閉空間,在自我封閉中尋求安全感。
此時,我的門外就有一頭凶猛可怖的怪獸,她吃掉我的夢想又用眼睛噴齣有毒的淚水將我化成屍骨,然後用毛綫連起骨骼,做成一個木偶。她將我隨身攜帶,隨意展示,操控自如。我不要這樣的結局。我逃進房間,這似乎還不夠。我躲進內心的核裏,就像一個桃子,留下軟軟的果肉任憑人食鳥啄蟲噬腐爛,厚厚的桃核是我zui後一道防綫。如果遇上小時候的我,被她用石塊敲開,那麼我隻好讓自己散發齣一陣難聞的氣味,將討厭的小孩驅趕走。現在的我,也確確實實成為瞭一顆臭烘烘的桃仁,所幸堅硬的桃核還沒碎。
考慮到躲避怪獸和 地求生的雙重需求,我的房間通嚮一個小小的陽颱,陽颱上的防盜窗在安裝的時候就預留瞭一個活動的門以備逃生。這是一個好時機,我可以在房間裏通過那個不太惹眼的小門逃走,逃離這個父缺失、母暴戾的傢,和這個充滿瞭怨念的屋子。逃吧,逃到廣闊的遠方去。
然而,當我走到陽颱上的時候,我隻是搬瞭個小凳子坐下來看花。這是一片我付齣瞭誠意勞動的地方,三十幾個花盆,它們沒有辜負我,慷慨地獻齣瞭綠葉和花朵,不問我活得成功還是失敗。
這裏的花草,很多都經曆過瞭多次劫難,其中大部分來自我的母,她看不慣我成天無所事事隻養花種草,我那退休乾部的生活方式和閑情逸緻總能在瞬間點燃她的怒火。她曾當著我的麵用熱水澆灌一株金邊瑞香,也曾趁我不在傢的時候偷偷把一盆長瞭五年的玉樹齊根摺斷。把餿掉的鼕瓜湯倒在碗蓮盆裏。把糖抹在葉片上吸引螞蟻來啃咬。植物是堅忍的,它們能忍受自然中zui惡劣的環境,也能熬過人類zui惡毒的摧殘。被摺斷的玉樹的葉片紛紛落下,沾到盆土便開始生根,一片皺巴巴的老葉片帶著一株嫩生生的小苗,沒有比這樣的景象更能給人力量瞭。那盆大玉樹後來變成瞭十盆!這讓母的怒火也翻瞭幾番。
第五章毫無疑問,如果她不是我母,我是不會喜歡她的,不想與這樣的人交朋友,甚至連打交道也是能避免就避免。她是個非常自私的人,暴戾而敏感,非常的神經質。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裏,並且隻愛她自己。
然而,她是我的母,我 須愛她。她把自己的骨血分贈給我,又用淚水換迴喂養我的糧食。在漫長的歲月裏,她給予我壞脾氣和痛苦,讓我體會到來自生命zui柔弱處的疼痛和哀傷,還有無可奈何。
很長的時間裏,我並不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可是我清楚地知道,我zui不想成為她這樣的人,我也不想我將來的女兒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時候,心裏wei一的想法是不要成為我這樣的人。
可是,我愈是想要走齣母對我的控製,卻愈發看清操控我的綫是怎樣牽引著我。她自私,我又何嘗不是如此?她給我摺磨,我也沒讓她省心。她想通過我獲得榮光,我就焚毀自己讓她丟盡顔麵。一切都是相互的,互為因果,唇齒相依。
我di*一次發現這一點是在大學裏。有一次與室友吵架,大傢都提高瞭嗓門,忽然間,我聽到自己的聲音並不是我所以為的那個聲音,而更像是我母的,無論是音色還是語調都一模一樣,就連刻薄的方式也如齣一轍。我分不清是記憶裏她的聲音在腦子裏作祟,還是我在憤怒的時候就變成瞭她——一個渾身充滿瞭淚水的巨型怪物,綠巨人的妹妹。這一發現讓我驚呆瞭,繼而是無盡的失望和喪氣。所有逃離的努力都變作瞭把我拉嚮她的反作用力,就像打彈弓時綳到自己手一樣既窩囊又生氣。
想到自己一輩子都無法逃脫我所厭惡的那種自己,真讓人痛不欲生。不想,卻 須。恐怕這要屬人生中 須麵對的di*一個問題瞭吧?接受它是痛的,但不接受就是滅亡。想到這裏,我覺得的人生還是有點意思的。
那個夜裏,我翻齣抽屜zui裏邊的那張紙片,那是郵遞員羅師傅給我的一張寫有傢教中心電話號碼的包裹通知單。
紙上,我用紅筆寫著:“決鬥吧,狗日的生活!”
三小時後,我撥通瞭那個電話。對方“喂”瞭一聲之後,我立馬認齣那是我高二數學老師叢老師的聲音。
那位老師給我留下瞭極深的印象,首先因為他總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而我對這一類人都抱有同情式的好感,因為我們都是對生活漫不經心的人。我也從另外的渠道瞭解到,他的睡眼惺忪很可能是因為從賭桌上下來後就直奔課堂。沒錯,他是我父的賭友。正因為如此,我打算去他那兒看看,麵個試,因為直覺知道這事會挺好玩。
根據電話裏的提示,一個小時候後,我到達瞭距離幸福小區三個街口的“康樂花園”。叢老師的輔導學校位於沿街店鋪的二樓,由一個很小的樓梯上去,樓梯上寫著“從這裏走入名校”、“一步一個新颱階”、“高分的選擇”等,黃底紅字,看得人眼花繚亂,險些栽倒。
我離開高中已經有七八年瞭。這些年中大傢都有變化,叢老師比以往老瞭些,卻至今沒有睡醒。此時正值暑假,來補課的學生很多,他們一臉漠然,好像是烈日下枯藤上的一根老絲瓜,對周遭的一切漠不關心,雙目茫然地做著題目,腦子是停止運轉的,答案從筆尖流齣,純屬慣性所緻。曾經的我想 也是這副樣子,wei一不同的是,由於身體太差,我每到暑假都會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像個遊魂,因此就免除瞭暑假補課的勞役之苦。
經過這七八年,較之以前,我也隻不過是胃口稍好,不再疰夏。沒精打采不變,無所事事不變,漫不經心不變,依舊一事無成,依舊狗屁不是。
作為往日學校裏的好學生,自然是會得到多一點善待的。叢老師給我倒瞭一杯純淨水,示意我坐下,開始和我攀談。
“你專業學的什麼?”
“城市規劃。”
“……這個啊,打算去哪裏?建設局?”
“我不知道,也許拆遷隊?”我撇撇嘴,實在不知道這個問題該怎麼迴答。
“那你英語幾級?”
“四級。”我本想說考六級那天睡過頭瞭就沒去考,猶豫兩秒還是算瞭。
“數學你還記得多少?忘光瞭吧?”
我想瞭一下,“貌似無理數什麼的還記得。開方也還行。啊,我懂黎曼幾何。我有一陣子對非歐幾何非常著迷。”
他做瞭一個意為“這些都是沒用的東西”的手勢,我就住口瞭,不往下談非歐幾何對我世界觀的改造之類的廢話。
“其實,比起給學生輔導功課,我更喜歡打掃衛生。叢老師,您這裏要清潔工嗎?”我這突如其來的建設性意見讓他驚訝瞭幾秒鍾。
“為什麼呢?”他不解地問。
“因為我喜歡打掃。我喜歡讓髒兮兮的地方變得一塵不染,喜歡把淩亂不堪的地方歸置得整整齊齊,喜歡把衰敗的景象一掃而光,變得欣欣嚮榮。”然後做瞭一個“就是這樣”的手勢,“我大學期間,基本上宿捨衛生都是我一個人做的,次次被評為衛生zui優宿捨。這是我喜歡做的事,也是我zui願意做的事。”
這話一說齣來,我自己都被自己打動瞭,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讓人神清氣爽。一縷陽光透過雲層照射下來,穿過樹葉,照到樹根旁的一個牛屎菌上。
於是,我開始在“叢老師高分學校”做起瞭清潔工,按照當地人的說法,我成瞭阿姨。梅雨季節也開始瞭,這不是比喻。
早上,我穿著洞洞鞋打著傘走在新鋪好的柏油路上,雨簾把人和車都相互隔開,有一種穿著隱形衣的安全感。路橫跨過好幾條小河,因為橋是平的,河幾乎被忽略瞭,幾天大雨就把河水灌得滿滿,垂柳的梢頭輕沾水麵,畫齣一個個圈圈,也不知是在詛咒誰。河水漫到堤岸,仿佛一腳就能跨進河裏,這樣的深水反倒給瞭我一種很安全的錯覺。路邊的店鋪都是新的,卻有老人坐在門口看店。看店是次要的,坐在那兒什麼都不做,隻是看著大雨從天而降,順著低窪處的導流槽,流進一條看不見的大河,與生命中的每一場落雨交匯,帶走時間,讓一切歸於寜靜,纔是重要的。坐在門口看雨的狗是百無聊賴的,而貓卻是另一番興緻,在五金店櫃颱上的那隻黑狸貓,齣神地凝望著充滿瞭雨的世界,似乎在看著一些人類無法望見的東西。柏油路很神奇,看著沒有積水,可腳踩上去竟能擠齣很多水來。我之前堅持“下雨天不齣門”原則,所以不曾見過這個現象,此時竟覺得非常有意思。我這麼邊走邊踩水,走過一個街口,忽然悲從中來:這種童年樂趣,我竟然在二十五六歲纔體驗到。
鬍思亂想地又走過一個街口,收傘,抖掉水滴,鑽進逼仄的樓梯。叢老師有三套房子,他把其中門對門的兩套中間打通,做瞭個兩百六七十平方米的大教室,但裏麵是隔開的。學生年齡不等,小學三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都有,共二三十個。我剛去的時候,學生們都在呆傻地做試捲,一旦發現瞭我的真實身份,就不再假裝瞭,丟紙團會故意往我身上丟,或者明明可以把橡皮灰用草稿紙接住扔進垃圾桶,卻直接撇在地上。有些調皮的男生直接把口香糖吐在地上,往地上吐瞭痰後用鞋底塗開,沒痰的就吐點唾沫。至於鼻屎沾在桌肚背麵那種事,簡直就是舉手之勞,貼完撚一下手指,嚮我做個“不成敬意”的錶情。
我對這些小孩的惡作劇漠然處之。他們現在這麼囂張跋扈,儼然世界之王,可是要不瞭十年,一旦他們走齣校園就會發現,自己隻不過是“教育”這個小黑屋裏釋放齣來的一個低能者,既沒有賴以為生的一技之長,又沒有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情懷,甚至連安貧樂道的態度都沒學會。zui後,女的當瞭售貨員,因為琳琅滿目的不屬於自己的物品多少帶來一些虛假的滿足感,而鼕暖夏涼的工作環境符閤這些貪圖安逸、無法吃苦的小姑娘對工作環境的大體要求。男生麼,要麼去當推銷員,名片上印著“銷售經理”就真以為自己是個人物瞭,要麼就去開個挖土機,靠著父輩的人脈四處塞紅包,換來承包些土方工程,一年能掙上十幾二十萬,吃飯喝酒吹牛的時候,眉宇間流淌著未來暴發戶的氣質。我有個同學,沒上大學。在我們大學畢業前夕,他在高中同學的QQ群裏說:同學們,我的洗浴中心越做越大,急缺人手,各位女同學如果找不到工作,可以來我洗浴中心做小姐,待遇從優。
我默默地清理掉這些未來的售貨員推銷員和挖土機司機故意製造齣的垃圾,把課桌擺整齊,把他們昨晚變成廢紙的捲子收拾起來,紮成捆。叢師娘,或者說老闆娘要把它們留著當廢紙賣。捲子變成廢紙的過程,恰如一個學生走入社會。看著這群沒心沒肺又帶著天然的惡的小孩,我想用一個很大的黑色塑料袋,把他們裝進去,一並扔進垃圾箱。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不費腦子的事,身體的疲勞會取代心靈的焦灼,酸痛感由肌肉和關節逐漸滲透至內心,把心裏的巨大空洞填滿。漸漸地,當這種酸痛的勞纍也消失無蹤的時候,人完成瞭某種形式的脫胎換骨。天突然就晴瞭,日光,不留一絲空隙。
我開始打傘走在上班路上。上班這個詞真是百搭。看著馬路邊新樓盤外麵的廣告,心裏盤算著自己的收入何時能買下這麼一間“風華 代”的小屋。我現在每天去補習學校兩次,每次打掃兩個小時,一個月給兩韆,無休,不給繳納社保。錢雖不多,但工作也不算辛苦,我是說當我習慣瞭彎著腰拖地之後。經曆瞭這兩三年的無收入生活之後,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也降到瞭zui低點。我穿的褲子是超市買的處理品,二十九元一件,棉中帶滌綸,寬鬆而舒適,配上一雙布鞋或者洞洞鞋,基本就算是清潔工阿姨的標準行頭瞭。我穿的T恤衫都是大學時代的,那時候比較捨得花錢,或者說我媽比較捨得給我花錢,耐剋阿迪的衣服囤瞭一些,足夠我再穿個三年五年。一件新T恤固然有著“新東西”的諸多令人賞心悅目的因素,可是舊衣裳自有它的好,在長久的磨閤中,它漸漸記下瞭穿者的形狀,變成瞭“自己的東西”。從前的我是不會有心去感受外物的這種天長日久纔能顯現齣來的改變,因此也就不會去在意一件衣裳對人生的意義。當我讓自己的生活更加儉樸更加簡練時,漸漸發現,越來越多買來的東西變成瞭自己的東西。乾清潔工這事我媽並不知道,我隻是告訴她,我去以前老師辦的輔導學校做事。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成瞭我去當老師,還囑咐我不要嫌錢多錢少,多學點東西,下半年去報名考一個市教委的教師考試,以後好好當一個老師也不錯,至少一年有三個月的寒暑假。我媽並不理解,並非人人都想當老師。叢老師為何不在學校裏繼續教書呢?這個問題我悄悄偵查、打探過。他起初是因為經常賭博上課沒精神,遲到被扣工資,後來有學生傢長嚮校方檢舉他賭博一事,學校要處分他,他索性辭掉瞭公職。那位學生傢長與叢老師是在賭桌上認識的,後來在傢長會上發現他竟然是自己孩子的數學老師,可憐天下父母心,他雖然很欣賞叢青雲的賭品,但作為教自己孩子的叢老師,他就無法接受瞭。在他看來,一個老師 須為人師錶道德高尚操行優良,決不能沾染黃賭毒,甚至連說葷段子都有失體麵。這位傢長的想法,大多數學生傢長都是認同的吧,也隻有我父這樣的人覺得無所謂,書教得好就行瞭,人無完人,要是沒有那麼一點小嗜好,人生有什麼樂趣呢?辭掉瞭工作之後,叢老師索性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當起瞭職業賭徒。既然教書並非樂趣所在,不如乾脆依著自己的心意來。他做的di*一件事是約那位舉報他的學生傢長齣來一賭泯恩仇。
當然,是叢老師贏光瞭該名學生傢長口袋裏所有的錢。我父跟我說過,賭錢叢老師很內行,賭品也很正,不耍滑頭,靠的是腦袋贏錢,因此行裏的人都很敬重他。順便說一句,我父這輩子乾過很多行當,wei一不變的身份就是賭徒。叢老師的賭博生涯大約持續瞭兩年半,收手是因為賺夠瞭錢,他買下瞭現在用作教室的房子。也有人說,是輸傢抵押的。
總之就是,他收手瞭,繼續當老師,扮演“教育者”這個比較體麵的社會角色。據他自己說,無非為瞭不讓子女看不起他,不讓子女被人看不起。叢老師並不愛教育這個行當,他有時候會跟我聊天,說:“小姚,你說人生圖什麼呢?”我一邊擦桌子一邊說:“圖個樂子唄,我覺得抹桌子比當公務員有趣一點,所以我就乾。”
為瞭打發時間,我認認真真把清潔這種事情做得一絲不苟。我想,如果我是一個城市規劃師,我一定要把城市建成一個迷宮,讓再熟悉城市的人都會迷路,這樣每天上班的路就豐富多彩充滿瞭探險意味,從甲地到乙地有無數條路可走,有無限可能性。這樣多好玩啊,空間因為重復而增值,生活因為多樣性而有趣。但這 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上班遲到怎麼辦?約會找不見人怎麼辦?好無聊的現代人,你們就用GPS找尋捷徑走你們的路吧。
所以,我的城市隻存在於我的幻想中。這是讓人掃興的事。但是打掃衛生不一樣。乾淨的就是乾淨的,如果彆人不記得髒時的模樣,那麼我工作的意義就是讓彆人忽略掉我的工作,以為整齊整潔是天然的。就像印度教的大神,zui厲害的是濕婆,他可不是什麼善類,他是毀滅之神,但毀滅的同時也是創造,這一點也啓發瞭有關部門,隻有大拆纔能大建。而另一位保護神毗濕奴就低調多瞭,總是做做修整工作,就像我這樣。我一邊鬍思亂想著,一邊用濕抹布擦除試捲架上的灰塵。接著又想,我真他媽太會給自己臉上貼金瞭。
因為時間太充裕瞭,我便著手尋找第二傢做,而且很快就找到瞭。任何行業都是相似的,隻要你進瞭這個圈子,一切就會容易很多。
這戶人傢位於康樂小區以東的彆墅區,隻有女主人和一個蒼白的少年。女主人個子高挑,已過四十,“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這個詞像是為她量身定製的。她總是衣著得體,說話和善,但是總像有一層憂鬱之光籠罩在她身上,看起來是一個標準的有錢寡婦。那個蒼白的少年被稱作淇淇,看上去十七八歲的光景,個子目測一米八,奇瘦,不僅瘦,而且骨骼似乎都是彎麯的,沒有伸展開來,像一根在極其狹小的空間裏生長瞭很久的韭菜,蜷麯的,缺少生命應有的鮮活顔色。他的頭發是黃的,皮膚極白,仿佛從未見過陽光。他確實也很少齣門,盡管他們傢門口有一塊很大的綠地,長著野花野草,他卻像從來不曾發現。他極少從他自己的房間裏齣來,少有的幾次見他走路,發現他總是沿著某條看不見的直綫在走,轉彎是直角,不像一般人那麼走一個弧綫。直覺上知道這個少年有一些問題,但到底是什麼又說不清。
這個彆墅區有聯排的,也有獨棟的,我打掃的這傢屬於後者,花園很大,但基本撂荒。由於女主人非常大方,我收拾一次得三百,一周四次,每次不過兩小時。晚上在網上跟一個同學聊天,她在五道口某高校當兼職老師,每周上十六節課,一節課四十元。起先,我的心裏稍稍平衡瞭一點,因為清潔工的收入不比高校教師差。過瞭一會兒,我又覺得太過分瞭,她連續四節課已經上得筋疲力盡,隻能拿到一百六,而我兩個小時的洗洗刷刷,居然有三百。於是,我決定幫彆墅女主人稍微拾掇一下院子,以安撫我那同學躁動不安的心。大概花瞭我十幾個小時,花園就有點樣子瞭,其實它的底子不差,有池子有花架的,隻是欠打理。我的工資是日結的,乾一次給一次錢,隨時可以滾蛋,這與輔導學校不一樣。當花園恢復秩序和生機之後,女主人多給瞭我一韆塊錢。她說:“要不是住東邊靠河那傢來問這花園是誰收拾的,我還真沒仔細瞧它的變化。這麼一收拾,就像個傢瞭。小姚,謝謝你。”
東邊靠河那傢的女主人,也就是我的第三個客戶。說客戶似乎有點可笑,但這次是她主動找上我的,並不是要請保姆,而是想重新規劃一下花園。我不太記得是否曾和第二傢的女主人聊起我的專業,可能是說瞭吧,我不用擔心彆人因為我的學曆高而解雇我,大多數人會覺得一個聰明一點的小保姆好於蠢笨的,我也不覺得在給母校丟臉,反正它也沒讓我添過什麼光彩,況且,我做什麼樣的職業它並無關係,也管不著。
我是個植物愛好者,江南的園藝植物能認個七八成,加上做設計圖又是一把好手,連夜,我就給第三戶人傢繪瞭個設計圖,隻是簡易的效果圖,太復雜的一般人看不明白反而容易否定掉。客戶看瞭挺滿意的,就開始照著施工瞭。十幾天的工夫,花園就有模有樣瞭。望著煥然一新的院子,我忽然有一種“在這一行做得風生水起”的自豪感。
我依然做著清潔工的活兒,同時乾三傢,一月有四韆五,偶爾還為人策劃一下庭院改造,日子竟然也充實起來。
*愛的讀者,如果你愛看勵誌文,我建議你把這個小說的原有順序打亂,章節順序變成:六、四、五、一、二、三。這樣,它就成瞭一個嚮死而生、在徘徊中逐漸走嚮光明的故事瞭,而標題也可以改成《我終於知道該如何做個正常人瞭》。
..........
用戶評價
《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這本書,與其說是在閱讀一個故事,不如說是在體驗一種情緒。它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沒有激昂澎湃的宣言,卻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觸及瞭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作者的筆觸,如同探入人心深處的探針,精準地勾勒齣那些我們常常試圖掩飾,卻又無處不在的焦慮和不安。它讓我看到瞭,在光鮮亮麗的現代社會背後,隱藏著多少個不為人知的掙紮。那些關於自我認知、人際關係、以及對生活意義的追問,都被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麵前。閱讀這本書,就像是在一個深夜,獨自一人,對著鏡子,看清瞭自己那些不完美卻又真實的存在。它沒有給我提供“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的指南,而是讓我開始理解,為何我會感到“不正常”,以及這種“不正常”背後可能蘊含的獨特生命體驗。它是一種釋放,也是一種和解,讓我開始接受那個不夠“標準”的自己。
評分“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這個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直擊人心的共鳴。翻開書頁,仿佛推開瞭一扇塵封已久的門,裏麵湧齣的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種最真實、最赤裸的情感流露。讀者的心緒,就如同被這書名輕輕撥動,然後跟著作者的文字,一點點沉入一種復雜而又微妙的境地。它沒有給齣明確的答案,反而拋齣瞭更多的問題,讓你不得不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審視自己,反思自己。那種“不正常”並非是指離經叛道,而是那些深埋於心底、難以啓齒的睏惑,那些在彆人看來微不足道的,但在自己生命中卻如影隨形的掙紮。書中的每一個字句,都像是一麵鏡子,照齣瞭我們可能不願承認,卻又真實存在的脆弱與迷茫。它讓我想起那些無數個夜晚,獨自一人坐在房間裏,感受著周遭的喧囂與內心的孤寂,那種格格不入的感受,那種對“正常”生活的渴望,以及那種對如何抵達“正常”的無力感。這不是一本告訴你“該如何做”的書,而是一本讓你“看見”自己,並開始理解自己的書。它提供瞭一種空間,讓你可以在文字中找到一個可以棲息的地方,一個可以喘息的角落。
評分我不得不說,《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這本書,真的是一種奇妙的閱讀體驗。它並沒有試圖去“教育”或者“說服”我,而是用一種非常平和,甚至可以說是有些疲憊的語調,嚮我展示瞭一種真實的存在狀態。我仿佛不是在翻閱一本紙質的書,而是在與一個靈魂進行深度的對話。它讓我意識到,那些曾經讓我倍感睏擾的“與眾不同”,或許並非是我個人的失敗,而是構成我生命獨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書中的每一個字句,都帶著一種淡淡的,卻又異常堅韌的生命力。它描繪齣的那種在“正常”的洪流中,小心翼翼地尋找自己位置的個體,讓我産生瞭強烈的共鳴。我不再急於去尋找改變自己的方法,而是開始嘗試去理解,去接納,去擁抱那種“不完美”。這種接納,並非是對現狀的妥協,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自我認知和自我關懷的開始。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書,不如說是一個邀請,邀請我停下腳步,審視內心,然後,以一種更溫柔的方式,繼續前行。
評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衝擊,遠超齣瞭我對一個普通讀物的預期。它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情感風暴,席捲瞭我的內心,留下瞭層層漣漪。我並非輕易被觸動的人,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卻以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瓦解瞭我慣常的防禦。它沒有使用華麗的辭藻,也沒有刻意營造戲劇性的情節,而是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齣一種常態下的“非正常”。這種“非正常”,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隱藏在現代社會中,無數個沉默的靈魂的共同體。作者的文字,精準地捕捉到瞭那些我們常常被壓抑、被忽略的情緒和體驗。那些對自我價值的懷疑,那些在人際交往中的小心翼翼,那些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它們都被毫無保留地呈現在讀者麵前。閱讀的過程,更像是一場深入靈魂的對話,我與作者,也與我自己。每一次翻頁,都是一次自我剖析的深化,我開始審視那些曾經被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開始質疑那些被社會定義為“正常”的標準。它並沒有提供治愈的良方,卻提供瞭一種深刻的理解,讓你明白,你不是一個人在孤獨地承受著這一切。
評分初讀《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便被其獨特的書名所吸引。然而,真正讓我沉浸其中,無法自拔的,是它所呈現齣的那種細膩且極具穿透力的情感描繪。這本書並非一本提供解決方案的指導手冊,而更像是一麵映照現實的鏡子,讓讀者在其中看到自己曾經的影子,以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掩埋的真實。它讓我重新審視瞭“正常”這個概念,發現所謂的“正常”,或許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而是一種個體在特定環境下,通過不斷摸索和適應所形成的生存狀態。書中的敘述,帶著一種淡淡的憂傷,但絕不至於令人絕望。反而,它提供瞭一種溫暖的陪伴,仿佛有一位知己,靜靜地傾聽著你內心深處的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我開始反思自己過往的許多選擇,那些曾經讓我感到睏惑和不安的時刻,似乎都在書中的文字裏得到瞭某種程度的印證。它讓我明白,那些看似微小的、不閤時宜的想法,其實都是個體生命經驗的獨特體現,而並非是“病態”的信號。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