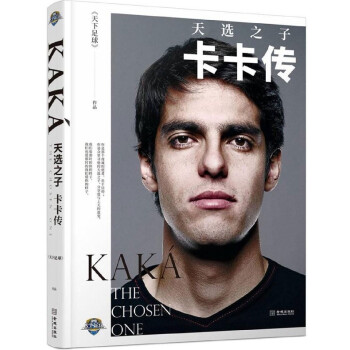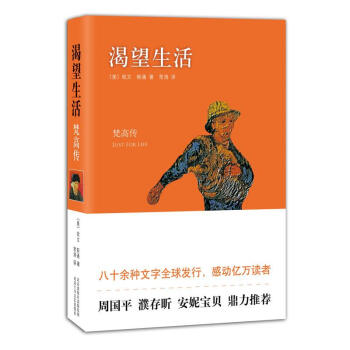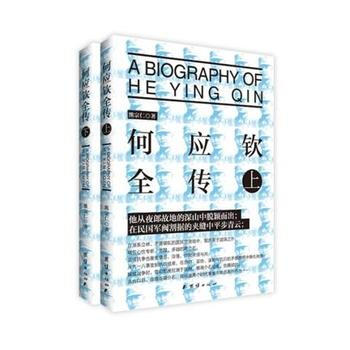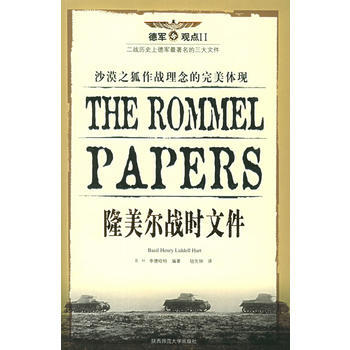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此为国内首本真正意义上用蒋介石日记研究蒋介石生平的著作。2.三位作者都是研究民国史的大家,在学界有较高的口碑。
3.本书虽为学术著作,却文字通俗。
内容简介
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仅有的。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寿终正寝”。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吧。本书是几位作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利用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画,也许可以称为几位作者的尝试。至于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而求实的历史评价,远非几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担当,或许还有待于学界将来的不断努力吧。
作者简介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代表作有《中华民国史》第四、十一卷,《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十卷,《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等。目录
一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二 屡仆屡起
三 关键的一年
四 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
五 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
六 削藩安内:昆明事变
七 家国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
八 一党训政下的多党合作
九 挽救危局与"戡乱动员"
十 后的改革:金圆券发行
十一 蒋介石的阅读史
精彩书摘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父去世时,蒋母32岁。除9岁长子外,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寡母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困苦不难想见。蒋介石日记中,屡屡回忆其幼年失怙后,孤儿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压:
“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高权力并以革命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佳素材:
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
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他出路。”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
“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之孤苦伶仃矣。” 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身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溪口乡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使母在乡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
扬眉吐气的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携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归来,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十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四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 “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 “心术不可复问”等等。
玩劣的孩子,难免厌学。蒋回忆其童年说:“每遇放学,视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在私塾时代,厌学玩劣的孩子难免受到老师的严加管教。在蒋的童年记忆中,教过他的多位塾师皆“无善足述”,有的甚至成为他切齿痛恨的对象。直到晚年,谈及任介眉、蒋价人等塾师,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
60岁回忆: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跪罚、毒打、痛骂、诅咒几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严师,实是毒魔。如任师当年不死,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
66岁回忆: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蒋价人(谨藩)间亦任意使气,以学生为囚徒视之。其他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当十二岁时,蒋师之苛刻虐待后,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不至矣。
天地君师,父既“不忍言”,塾师都“无善足述”,甚至视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邻里乡也无情无义。蒋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记中写道:“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除了满清压迫,劣绅欺凌,更加戚轻侮,学友嫉视,父兄无情,乡邻无义,周遭竟没有一个“好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生存境遇,多么阴暗凄惨!这样的早年成长经历,又将如何铸造蒋的人生和个性特质?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
除母子之外,天下决无义友仁爱,无事则首聚谈心,似为至交,有事则彼此避匿,一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骂,幸灾乐祸,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诚待友乎。
近日愤激不绝,以友人伪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为公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独善我身,断绝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
吾友除孙先生以外,诚意待我者极少,昔日以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
直率公道难容世,阴险骗诈反成名。以人人为莫逆,便知处处要留心。人心虚伪,社会陆沉,绝无容身余地;风波险恶,沙漠荒凉,创造渡世津梁。
国中皆荆棘,世上无知音。
人心险诈恶劣,畏我者固为我敌,爱我者亦为我敌,必欲我皆为其利用而后快心,稍拂其意则妒忌交至,怨恨并来。政治社会之卑污毒狠如此,岂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则惟有另辟途径,独善其身,而使若辈自争以还我清白之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
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
父母妻子之外,皆无诚意己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
蒋介石认为:“天下事之难,莫难用人及用于人也。”恰在“用人”和“用于人”方面,蒋表现出特异之个性。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蒋介石总是回忆他小时候,孤儿寡母如何受人压迫,受人欺负,受人冷眼。因此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国民党前辈中,蒋仅服膺陈英士、孙中山等一两人。陈英士是蒋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由于得到陈英士的充分信任和赏识,蒋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辛亥革命后,他挺身暗杀了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蒋自称处世交友,“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1916年陈英士被刺身亡后,蒋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文:“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
陈英士死后,蒋与孙中山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1917-1924),蒋对孙中山一直若即若离,欲迎还拒。对于孙中山交办的任务,并不积极,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有时孙中山函电交催,他却有意延搁。之所以如此,除了正值孙中山事业低谷外,是蒋认为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但蒋上任不久即辞职。辞职的借口是学校经费不济,负责供应经费的禁烟督办杨西岩故意刁难。深层原因其实见诸蒋致孙函:“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测。”并称:“中正与英士共事十载,始终如一,未尝有或合或离之形神”,“乃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岂复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
不仅渴望孙中山如陈英士那样充分信任他,还要求党内其他同志也象陈英士那样容忍体贴他。他致书胡汉民、汪精卫曰:“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今弟做事,既无人督责如先慈,又无人体贴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转以偾事也。”只有母、英士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当这两人都死后,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过着一种漫无目标的游荡生活。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任职时间,长的一次也不到半年,短的一次只有。往复到职、离职,“事近儿戏”。“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辞职独行”蒋也自省“赌气即走,是吾之过”。辞职的理由,不外乎上司信任不专,以及同侪疑忌排挤。每次辞职借口,大多是“不见信”、“不见谅”于总座。不能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样一种抗拒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当其“用于人”时,他希望上司同侪对他深信不疑,以慈爱至诚待之。当他执掌高权力以后,却很少有人长久不衰地受到他的信任。蒋介石用人,重忠诚。然而,对上,对下,对同辈,他又常怀疑忌。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即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而信如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亦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同样是拥蒋派系,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足鼎立。抗战时期成立三青团,又有意使党、团互相制衡。特务系统也是中统、军统双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部下信任不专,有意使部属之间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
翁文灏日记中曾转述美国大使詹森(Y.F.Johnson)对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的观察和评价:胡汉民思想坚决,但教条,窄隘,不易与人合作;汪精卫善于变化,但无甚原则;蒋介石“目光动人,但对人从不信任,各事劳”。翁认为詹森的观察颇独到,显然深有同感。
抗战中,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国军不能练精,由于蒋先生不善治军耶?由于不能执简御繁耶?由于防下过甚耶?”;“……委员长不能执简御繁,用人不疑。”
在蒋看来:“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则不如求己。无论友盟人之如何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不可恃之物也。”又认为:“无论何人为汝尽力,必欲称功望恩,而实患难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用户评价
这本书让我对“历史人物”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历史人物就是书本上的名字和事件,但《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却用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视角,将蒋介石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又从泥淖中抬起。书中关于他家庭生活、个人信仰、甚至是一些细微的性格特征的描写,都让我觉得这位历史巨人变得触手可及。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某个深夜,他在灯下批阅文件,眼神中流露出的疲惫与坚定;或者在与亲人相处时,那一丝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情。 尤其让我感触良多的是,作者对于他晚年退守台湾后的心境描绘。那种“失土”的痛苦,那种对曾经辉煌的追忆,以及对未来局势的担忧,都通过文字传递得淋漓尽致。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即使身处逆境,他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执着,更是一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沉重感。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放下书本,静静地思考。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究竟有多少是时代赋予的,又有多少是自身决定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启发。
评分最近读完《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这本书,实在有些意犹未尽,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坦白说,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片段,以及一些笼统的标签。但这本书却以一种极其细致入微的笔触,将一个鲜活、多面的蒋介石呈现在我面前。它不仅仅是梳理了这位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更深入地挖掘了他内心的挣扎、情感的起伏,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决策背后所蕴含的复杂考量。 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伟光正的英雄,或者一个纯粹的反派。相反,我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伟大,在权力巅峰时的踌躇满志与内心的孤寂,在重大决策时的果断与偶尔的迟疑。比如,书中对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部署、对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以及他在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微妙斡旋,都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这些分析并非空泛的论调,而是基于大量的史料和细节,使得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事件,瞬间变得更加立体和深刻。我开始思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必须面对的抉择,其背后究竟有多少的无奈与牺牲。
评分《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这本书,让我对“历史”二字的理解,从冰冷的事件堆叠,变成了鲜活的人物群像。我之前对蒋介石的印象,大多来自一些刻板的描述,但读完这本书,我才真正开始理解,一个人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做出那些看似简单,实则无比艰难的选择。 我特别喜欢书中对蒋介石处理内政的一些描述,比如他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对社会改革的尝试,以及他在面临国内政治动荡时的应对策略。这些方面常常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掩盖,但这本书却给予了它们足够的关注。我开始思考,一个国家的崛起,除了军事和政治斗争,还需要怎样的内部建设和治理。书中关于他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应对内部矛盾,都让我看到了一个领导者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智慧和挑战。
评分最近读完《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我感觉我的历史观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以往我们谈论蒋介石,总会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和评价,这本书却像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复杂,也更加真实的蒋介石。它不是那种枯燥的历史陈述,而是充满了故事性和人情味,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沉闷。 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那种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很多选择都是在极端困难和危险中做出的。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让我看到了当时双方领导者之间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亲眼目睹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感受到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巨大力量。
评分《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历史传记,不如说是一次深入的“人物访谈”。虽然我知道书中记录的是过去,但作者的叙述方式,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在娓娓道来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让我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从未想过,一个在宏大历史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其内心世界可以如此丰富且充满矛盾。 书中对蒋介石军事生涯的描写尤其精彩。他如何从一个青年军官成长为掌握百万雄师的总司令,中间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付出了多少代价,都在书中得到了详尽的呈现。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一些关键战役的分析,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得失,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融入,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些战役的意义。它让我意识到,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多个层面的较量,而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硝烟弥漫。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