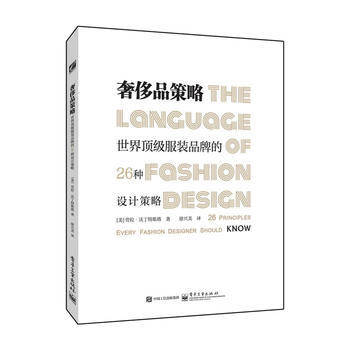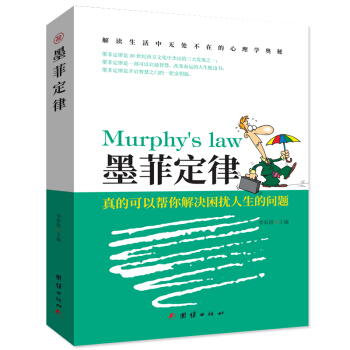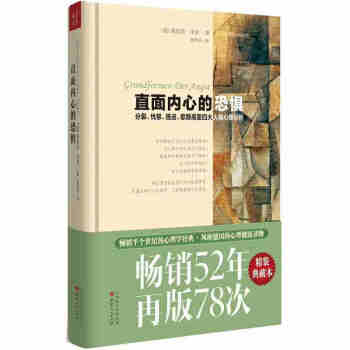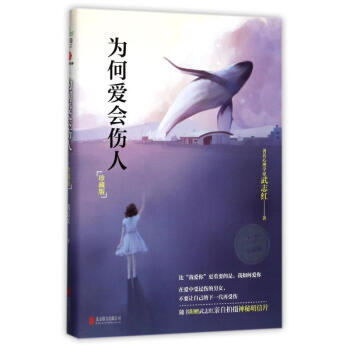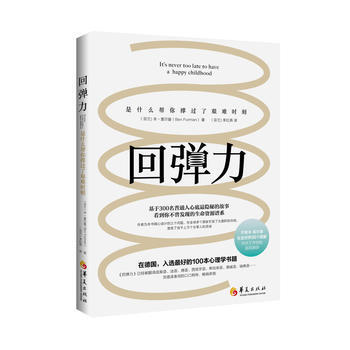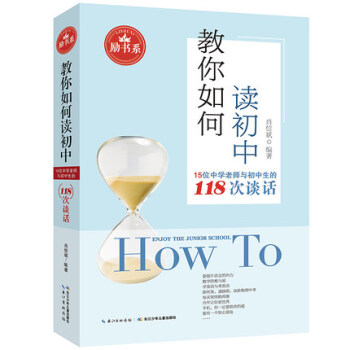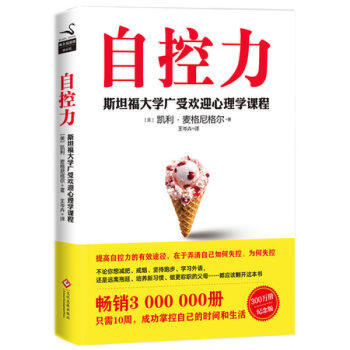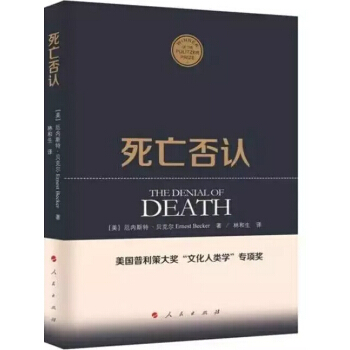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书名:死亡否认
定价:49.0元
作者:(美)厄内斯特·贝克尔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9-01
ISBN:9787010151137
字数:
页码: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大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内容提要
正如作者贝克尔所说:“并非自然的动物本性,而恰恰是对惊恐(panic)的掩饰,让我们活在丑陋之中。”一直以来,罕有作者这样真诚的努力,向世人揭示一个颠覆性的真理:死亡并不必然产生恐惧,然而,恐惧的人生却虽生犹死。作者进一步深刻指明:人们常常用欲望来掩饰恐惧,殊不知欲望恰恰是恐惧的结果,如此文饰,相当于饮鸩止渴。因此,吾人别无他途,唯有直面恐惧,向死而生。
目录
作者介绍
E.贝克尔(1924.9.27-1974.3.6),欧洲犹太人后裔,生于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赴欧作战,参加过解放集中营的战斗。之后返美,就读于纽约州雪城大学,毕业后派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约1954年重返美校,攻读文化人类学,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近十年间先后执教于雪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等,因坚持正义、支持学生而饱受官方排挤,直至1969年获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职位。著有《禅:一个理性的评判》《有意义的生与死》《精神疗法的革命》《异化》《恶的结构》《身着甲胄的天使》《失落的人学》《死亡否认》和《逃避罪恶》。其代表作《死亡否认》获1974年普利策大奖(文化人类学专项)。
文摘
总观精神病
……所有孤立的、个体的生存形式都内含着本质的、基本的高焦虑(焦虑)。生存于这样的基本焦虑之中,人对于自身“在世”(beingintheworld)既害怕又焦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想象下述似乎矛盾的现象: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
——M·博斯(M Boss)
大学时代,我的一位老师是专门研究中世纪史的教授,在该领域备受赞誉。他承认,他对中世纪了解愈深,就愈没有什么可说,因为中世纪是如此复杂,如此多样化,以至根本无法作出划一的概括。同样的道理完全适用于精神病理论领域。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现象,谁敢来写这一领域的“总观”?如果一个人并非精神病学家,恐怕就更难有这样的勇气。就本书而言,我觉得应该有“总观精神病”这样一章,然而,写作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才能强迫自己动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史上已有这样一些的心理学家,他们的终身成就摆在面前,一目了然。这些人具有丰富的个人敏感性,他们的工作反映了非凡的理论禀赋,又有广泛和多样的临床资料作为基础。既然如此,何必还要重新翻耕这一领域,而所依据的方式,还有可能流于肤浅和头脑简单?
答案也许是:今天我们需要简单的头脑,让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事情。事实上,这是我的老师那番话的另一面意思。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在于:所有关乎人性的重要内容,需要知道的,似乎都已经知道了。然而要注意,我们的时代与别的时代全然不同。今天,确切掌握的知识是如此之可怜,共同的理解是如此之少。这完全是专业化所造成的后果。专业化使我们无法进行总观性的概括,导致了普遍的低能。然而,以本章不大的篇幅,我想冒一次头脑简单的危险,突破专门化及其浩繁的资料,摆脱并非故意的低能,趟出一条路子。哪怕后的成功十分可怜,似乎也值得一试。在如今令人窒息、破碎不堪的科学时代,必须有某个人来自愿充当愚者,以便改善普遍的精神近视。
当然,专家们马上会说,谈论精神病的总观性理论有狂妄之嫌,这件事情属于未来,是一个遥远的、甚至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就好像人类浩如烟海的书籍从未提出过总观性的理论。然而,事实上,关于神经症、精神紊乱或其他类型,现代心理学巨匠已然完成深刻的研究,达到了透彻的理解。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剩下的问题是找到恰当的手段,把某种总体秩序引入大师们的洞见和认识。方法之一就是对总体秩序作出为总观性的表述——事实上,迄今为止,本书一直在运用总观性表述关联不同领域的事实。我们看到,人这种动物害怕死亡、追求自我永生、希望完成对于自身命运英雄主义。那么,英雄主义的失败,就意味着人的失败。本书第2章曾引阿德勒的话作为章首题词,那段文字已然简洁表明:谈论精神病也就是谈论那些丧失了勇气的人们,也就是说,精神病反映了英雄主义的失败。这一结论与上一章对神经症的讨论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我们在那里看到,神经症患者格外无法承受自己的受造性,无法藉有力的幻象包围自己的肛门性。阿德勒看出:低自尊是精神病的中心问题。在生活中,人自身命运的努力可能会出问题,他会怀疑自己的不朽、怀疑自身生命的持久价值,他可能不相信已经过去的一切会有什么特殊意义。在这种时候,人就会备受自尊问题的折磨。人总是试图否认自己的受造性,精神病则代表了这种否认的诸种陷身状态(boggingdown)。
抑郁症
虽是精神病的“总观”,然而,如果无法概括每一种精神病综合征的细节,那么就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有幸的是,我们恰好能做到这一点。阿德勒已然指出,抑郁症完全是一个勇气的问题。阿德勒考察了那些害怕生活的人,他们没有勇气争取独立、完全被他人的行动所遮蔽、全然依赖于他人帮助,阿德勒研究了抑郁症在他们身上的发生与发展。这些人生活于“系统性的自我限制”之中,其结果是自我行动的能力愈来愈小,愈来愈无助,不得不依赖他人。在生活的困难和打击面前,人愈是退缩,就愈是产生身不由己的无能感,终,自我评价也会愈低。这是无法逃避的逻辑。如果生活成为一系列“默默的退避”,人必会终陷绝境。这是抑郁症的陷身状态,也是博斯在本章题词中的提醒。到了后来,人甚至不敢动弹——患者卧床不起,厌食,家务事堆积如山,床上又脏又臭。
这就是缺乏勇气的例子,它给我们这样的教益: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为生命付出代价,随时准备去死,投身于生活的危险,让自己被淹没,耗尽一切。否则,人就会在逃避生死的企图中虽生犹死。阿德勒在20世纪初的认识,为现存论精神病学所印证,两者对抑郁症的理解完全一样,博斯就此概括说:
在其整个生存中,患者无法坦然地、有责任感地接受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就将形成他真实的自我。其结果,患者无法获取独立的生存地位,只能一如既往屈从他人的要求、愿望和期望,成为牺牲品。患者竭尽全力迎合外界的期望,为的是不失去外界的保护和爱[然而失去的却更多]。因而,抑郁症患者可怕的罪感……源于其生存之罪(existential guilt)。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学术现象:阿德勒和生存论精神病学派先后揭明:抑郁症动力机制并不复杂,但各派意见仍然如此难以统一,其原因之一是,这些动力机制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它们深藏于人性处境的核心,而对于这一核心,有关人士一直无法达到简洁明了的认识。生活中某些人有效排除了生死恐惧的概念,从根本上说,不再被活生生的受造恐惧所左右,因而无法理解那些遭恐惧剧烈撕咬的人,不明白他们内心痛苦的折磨与扭曲。以阿德勒为例,他早已写出的总观性理论,然而,不知何故,他居然还在唠叨什么抑郁者的私心和善心、什么拒绝长大、什么拒不承担生活责任的“宠坏了的儿童”,等等,令人失望之极。固然,阿德勒所论现象的确存在,而且,他其实非常清楚问题的本质:是生活本身的分量让人变得如此脆弱不堪。然而,他强调的重点有些失之偏颇。按道理,他应该更多强调纯粹的恐惧——恐惧个体化、差异和孤独的存在,恐惧支撑性力量和代表性力量的丧失。阿德勒揭露了人们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生之谎言”;然而他也许未能注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样或那样的“生之谎言”是多么必要,人们多么缺乏可资依赖的力量。连弗洛伊德或荣格这样的巨人也会因罗马而退缩或昏厥,何况普通人,应该不难体会他们承受着多么可怕的生存分量。普通人始终把自己置于他人力量之内,试图以此确立某种平静的英雄主义。此类手段一旦失败,“生之谎言”就暴露出来,让普通人遭受威胁,他可能就此退缩,沦入抑郁症的陷身状态,甚至像弗洛伊德或荣格那样昏厥过去——这一切是多么合乎逻辑。
兰克告诉我们抑郁症动力机制中被忽视的另一种复杂性:患者之所以想要愉悦他人,服从他人的行为法则,是因为患者试图藉此自我永生,满足不朽的渴望。人渴望不朽,家庭的小天地,单一的对象……凡此等等都是人争取不朽的场所或手段。人在一切可能之处争取不朽。移情对象是我们良心的焦点,是我们整个善恶世界观的焦点。它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英雄主义系统,因而不是什么轻易就能摆脱的事物。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移情可以达到何等和复杂的程度。弗洛伊德说得好:由于害怕被孤立,我们终生服从心中的,一旦试图摆脱他们的要求而独立自主地行动,害怕失去的焦虑便会膨胀起来。失去的力量和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也看到,移情对象本身表明:生存是令人畏惧的神秘(mysterium tremendum)。事实上,移情对象本身就是根本的奇迹,在其具体生存中了单纯的符号指令。还有什么比服从这一神迹更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跟兰克一道补充说:人们履行移情对象所代表的伦理准则,藉此将争取不朽的奋斗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情?为了永恒的自我永生而主动利用移情对象,这就是移情。这也解释了移情对象死后仍然保持的移情,其控制力量得以继续存在,而当事人内心则是这样一种逻辑:“对象本身可以不在人世,但他的遗物会继续发挥影响,甚至从不可见的灵性世界行使其权能;而我保持了对他的忠诚,也因此不朽。”这部分是古人崇拜祖先的心理过程,也适用于继续遵守家庭荣誉和行为法则的现代人。
概而言之,抑郁症概括了生与死的恐惧以及自我永生的渴望。瞧瞧人可以成为怎样的英雄啊!在小家庭的安全空间做一位英雄,在相爱者面前做一位英雄,等等,并且,为保证这样的英雄诗成功上演,随时准备“默默退避”,这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向宇宙奉献独特禀赋以确保自身独特的不朽。唯有创造性人格可以为此惨淡经营。普通人没有这样的幸运,一旦其安全的英雄诗失信于观众,或无法掩盖其英雄诗的失败,他们就会陷于抑郁症及其可怕的罪感而无法自拔。我特别喜欢盖林(Gaylin)的洞见,他认为陷于抑郁症的全然无助与依赖性,本身就是哺乳动物后、自然的防御机制:
依赖性是人类机体基本的存活机制。……当成人对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明白了自己在逃避和斗争两方面的无能,他就被“还原”到一种抑郁状态。正是这种与婴儿的无助相应的还原,变成了……藉依赖而解决存活问题的吁求。换句话说,防御机制的丧失,刚好是防御机制的一种形式。
博斯说,抑郁症患者可怕的罪感是生存性的,它们代表了实现自身生命、完成自身潜力的失败;为成为他人心中的“好人”,当事人拼命扭曲自己,所以失败。既然自身是否不朽由他人来决定,那么,自己未展开的生命也就交给他人去了——这是一种被奴役的关系,由此留下罪感的后遗症。帕尔斯这样的现代精神疗法专家提醒他的患者说:“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本就不必去取悦于他们的搭档,正如搭档并不需要来取悦他们;因而,他们可以积极地反抗奴役的。”沿此路径,他们可以切入“个人不朽演出”的伦理学。帕尔斯所言固然不错,却难以概括患者的所有罪感,或者说,难以概括患者据以谴责自己的所有罪过。患者谴责自己无价值,据此可以断定患者有着巨大的罪感。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自我谴责不仅表达了生命未能展开的罪感,而且,也是从自身处境得出意义的一种语言。简言之,哪怕当事人是一位充满罪感的英雄,但毕竟还是自身英雄系统中的英雄。抑郁症患者利用罪感死死抓住移情对象,以免自身处境发生变动。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能力对移情对象进行分析,以便摆脱和这一对象。比起自由和责任的可怕重担,罪感要容易承受一点——尤其重建生活的可能性来得太迟的时候。如果你无法惩罚他人,如果他人代表了你所认同的不朽观念体系因而不能甚至不敢加以批评,那么,你好选择罪感和自我惩罚。如果你的神不可信赖,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你不能归恶于神,只能归恶于自身,这样你才能活下去。罪责使你失去了一部分生活,然而避免了死之大恶。抑郁症患者夸张他的罪责,因为正是罪责,以安全和轻易的方式,疏通了他的困境。阿德勒指出,抑郁症患者也无法调动旁人的反应,让旁人对他产生怜悯、重视和关照。这是因为,他的自怜和自恨恰好是控制旁人、抬高自身人格的手段。所有这一切,使得抑郁症表现出十分突出的强迫性罪感。
我们看到,抑郁症动力机制的确具有某些复杂性,这些复杂性让人们对该机制难以拥有一致和直接的理解,虽然抑郁症可以概括为非英雄主义人生的自然沉沦,而且,一旦如此概括,其机制相当简单。此外,弗洛伊德的有关用语和世界观也妨碍一致和直接的理解。例如,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更年期抑郁症的发病,是因为重新经验了早期的阉割焦虑。这种解释容易遭人嘲笑,它似乎表明,弗洛伊德主义者再次企图把成年生活的难题还原到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或者说,还原到他们自己的父权中心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看来,可怜的、被阉割的女性要为自己天生的短处还债。10年前,我自己由于缺乏经验和狂妄自大,对上述说法作出了鲁莽的反应。当时,我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更年期抑郁症,然而,我当时的理论仅仅考虑了社会角色的丧失,走向与弗洛伊德主义者相反的。我当时认为,更年期妇女之所以易患精神病,是因为她们的生命不再有用。在一些病例中,她们由于晚年离婚而丧失了作为妻子的角色;在另一些病例中,上述情况还伴随着她们母亲角色的终结,因为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剩下她们孑然一身,无所事事。她们从未在家务之外习得任何社会角色、手艺或技能,因而,一旦家庭不再需要她们,她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这些妇女的抑郁症刚好发生在更年期,这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更年期抑郁症诱发于社会角色的丧失。
我们几乎处处都要遭遇弗洛伊德的用语和世界观,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难题,因为弗洛伊德思想包含着有力的真理,其表达方式看上去却那么离谱,而我们自己则常常受到诱惑,试图对上述两方面加以区分,如此幼稚的举动,让我们把两方面一并抛弃了。我想,在专家猛增的时代,为保证自己还能做点什么,人应该莽撞一点;但此举又十分危险。一个偶露峥嵘的嘲讽者,不可能单凭一厢情愿,就抹掉半个世纪的临床观察和思想。学术领域一个始终存在的危险是:每一种收获都是冒险,都可能失去曾经牢牢占领的地盘。这一点更真实地体现于目前关于精神病的各种“角色理论”,这些理论威胁着以身体的事实为基础的弗洛伊德理论,使它有被遗弃的危险。
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妇女在更年期对阉割情结的再次体验,是实在的体验——只是,我们这样的表述,并非出于弗洛伊德狭隘的生物主义焦点,相反,这一表述的背景,是兰克、生存论以及布朗所提供的更为广阔的意义。博斯说得非常好:“阉割恐惧”仅仅是一种突破,或者说,一道裂缝,从这儿,整个生存中固有的焦虑得以闯入人自己的世界。在此不难看出,更年期显然是重新唤醒了对身体的恐惧、对自因企划崩溃的恐惧——早期俄狄浦斯式的阉割焦虑正是源于这一经验。患者被一种为有力的方式所提醒:她是一种动物。更年期,不过是“动物生日”,特别标明退化的生理履历,仿佛大自然把确定的生理里程碑强加于人,竖起一堵墙并且说:“你不能向生活再迈出一步,你正在走向结束,走向死亡的定局。”由于男子没有这样一种动物生日、特殊的生理标志,因而,对于作为一种自因企划的身体,他们通常体验不到那种完全的疑惑。一次就足够了,藉助文化世界观的符号力量,他们可以一劳永逸埋藏这个问题。然而,女性却没那么幸运,她们被安排在那样一种位置,被迫突然从心理上去把握生命的生理事实。套用歌德的格言,死并非单单敲响她们的门,因而可以置之不理(犹如男人可以忘却自己的衰老),不,死要破门而入,并充分展示自己的。
我们再次看到,精神分析必须得到拓展,以便引入死亡恐惧而不是来自父母的惩罚恐惧。“阉割者”不是父母而是自然本身。或许,父母自己的罪感也表达了一种新的、真正的自我评价,这种自我评价了仅仅作为大便动物的存在,了那种肮脏的、无价值的存在。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事情另外的一面:在相当的程度上,弗洛伊德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产生了自然的融合。通常,文化的自因企划掩盖了对阉割焦虑的再体验;然而,正是社会角色和文化企划的失败,会强化天然的、动物的无助。两种企划——身体性企划和文化性企划——合并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失败。那么无疑,更年期抑郁症现象特别产生于那样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老年妇女丧失了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位置,身体和死亡的英雄主义路径被阻断。同样肯定的是,另一些社会向个体提供自我永生的安全图式,藉其保护,个体有权把生命的永恒视为理所当然,但抑郁者反而感到这样的惩罚:他不得不面对永恒的毁灭。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只能承认:社会角色是影响抑郁综合征的关键因素,因而,强调社会角色,无疑是正确的取向,因为社会角色是问题的高级层次,其中已然吸收了身体的层次。英雄主义把死亡恐惧转变为自我永生的安全,其程度足以让人欢乐地面对死亡,甚至在某些观念体系的武装之下游戏死亡。
不仅如此,从一种实践的观点来看,强调辅助性的社会角色是更为现实主义的取向,因为总的说来,如果没有某种延续性的英雄主义手段,大多数人就不可能摆脱对于对象的终身依赖性,也无法获得自我依赖和自我支撑的力量。生存的负担的确过于沉重,人难以逃脱对于对象的依赖和身体的衰败,这是人的普遍命运。如果缺乏某种“辩护性的观念体系”,人就会自然趋于沉沦和失败。我们再次看到,对于精神病的历史层面,兰克的强调是多么正确:精神病绝不仅仅与自然有关,也与自然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有关。如果无法成为自身社会公共观念体系中的英雄,就必然成为小家庭中喋喋不休、怨天尤人的失败者。并非离题的一点议论是:今日时代,英雄主义和精神病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谁对谁喋喋不休”?对于上界诸神、他国军队、本国领导或自身配偶,人们不是乐于慷慨陈词、大声斥责吗?无论如何,生命的债务总要偿还,人不得不尽其所能,以自身好的、的方式成为英雄。在我们这个喋喋不休的时代,在贫困的文化中,正如哈林顿(Harrington)如此真切的指陈:个体甚至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仅仅为了提升弹球机技艺而呕心沥血”。
序言
用户评价
我拿到《死亡否认》这本书的时候,就被它低调而富有深意的封面设计所吸引,仿佛里面藏着一个等待被发掘的秘密。这本书并没有给我带来那种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而是像一次缓慢而温情的对话,在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作者对生命、对失去、对回忆的深刻体悟。它更像是一本散文集,又掺杂着小说叙事的片段,作者用一种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与伤痛。我特别喜欢书中那些关于“遗忘”与“铭记”的探讨,它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限,而是让我们在阅读中,去感受那种模糊而又真实的情感。书中的人物,他们或许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否认”那些让他们痛苦的现实,但这种否认,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地去面对生活,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意义。它不是那种会让你在短时间内看完的书,它更适合放在床头,每天睡前翻几页,在静谧的夜晚,让那些文字慢慢沉淀,引发你内心的思考。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放下”这件事,它或许不是遗忘,而是更深刻地理解与接纳。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死亡否认》,但我拿到手里的时候,感觉它传递的不仅仅是对死亡的否定,更像是一种对生命中那些无法言说的、深埋心底的遗憾和失去的温柔探寻。我拿到书的时候,就被封面那种略显疏离却又充满故事感的画风吸引了,仿佛一幅陈年的旧画,里面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翻开书页,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近乎哀伤的诗意,作者的文字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又像一个温暖的拥抱,将那些关于告别、关于释怀、关于即使面对终结也依旧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瞬间,一丝不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我尤其喜欢其中一些片段,它们描绘的场景并不宏大,但那种细微的情感变化,那种在沉默中传递的千言万语,却深深地触动了我。它不是那种会让你拍案叫绝的故事,也不是那种会让你义愤填膺的叙述,更像是一次漫长而宁静的冥想,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投射进去,在那些虚构的人物身上找到共鸣,或者说,找到一种面对现实的勇气。这本书仿佛在告诉我,死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如何去面对它,如何去铭记那些曾经拥有过的,才是生命真正意义的所在。它不是为了让你恐惧,而是为了让你更加珍惜,更加懂得爱与被爱。
评分拿到《死亡否认》这本书,我并没有立刻沉浸其中,而是把它放在床头,时不时翻看几页。我最欣赏的是作者构建的叙事空间,它有一种独特的宁静感,仿佛将读者置于一个与世隔绝的角落,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消化那些文字所带来的情感冲击。这本书不是那种让你一口气读完就丢下的作品,它更适合慢慢品味,就像品一杯陈年的普洱,越是细细品味,越能品出其中的醇厚和回甘。书中的一些人物,他们身上都带着某种程度的“否认”的痕迹,但这种否认并非是逃避,而更像是一种笨拙却坚定的守护。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试图留住那些即将逝去的,试图在无常的世界里找到一丝永恒的慰藉。我被作者对人性的洞察力所折服,他没有刻意去美化或者丑化任何一个角色,而是将他们最真实、最复杂的一面展现出来,这种真实感,反而让故事更加动人。这本书让我开始重新审视“失去”这个词,它不再仅仅是痛苦和悲伤的代名词,它也可以是成长和蜕变的契机,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评分初读《死亡否认》这本书,脑海里最先浮现的画面是那种阴雨连绵的午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看着雨滴落在玻璃上,汇聚成细流,模糊了窗外的世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它不像市面上那些节奏紧凑、情节跌宕的小说,而是更像一股缓慢而绵长的溪流,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你的内心。我喜欢作者对细节的捕捉,那些微小的动作,那些不经意间的表情,都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它让我想起很多我曾经以为已经被遗忘的片段,那些在时间的洪流中逐渐褪色的记忆,因为这本书的出现,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故事中的人物,他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波澜壮阔的爱情,他们只是平凡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那些无法回避的失去和遗憾。我反复阅读了书中的几个章节,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它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待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的方式,是否因为生活的忙碌而忽略了太多本应珍视的东西。这本书没有给我直接的答案,但它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部分。
评分《死亡否认》这本书,读完后留给我的印象,就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纯音乐,它没有直接诉说什么,却能引发你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共鸣。我尤其被作者的语言风格所吸引,那种冷静、克制的叙述方式,反而更加凸显了故事背后隐藏的巨大能量。它就像一位老友,在你失意的时候,静静地坐在你身边,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着你,让你感受到一种无声的支持。书中的一些情节,虽然看似平淡,但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仿佛平静水面下的暗流,随时可能涌起惊涛骇浪。它不是那种让你感到压抑的书,反而是让你在一种沉静中,找到一种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和力量。我喜欢书中那种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它没有给出任何教条式的结论,而是引导你去思考,去探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即使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依旧可以保有内心的尊严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否认”,与其说是对死亡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