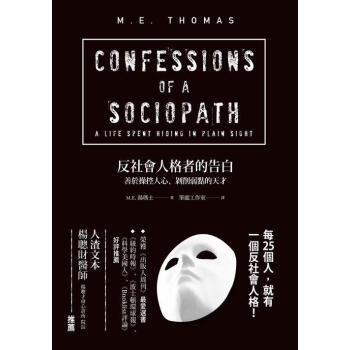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從沙漠流浪到海島的真愛,化為感動的星光,燦亮到永恆!燃燒一個人的靈魂的,正是對生命的愛,那是至死方休!
三毛的青春歲月及心靈劄記!
真正的快樂,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觀的來說,它是細水長流,碧海無波,在蕓蕓眾生裡做一個普通的人。
--三毛
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
重新編輯.全新改版
用最真的心,在那畝小小的田裡,種下瞭往昔、夢想,與滿滿的快樂……
從少女時期我就愛寫文章,雖然現在看來是些喃喃自語的夢話,但我依然想與大傢分享,因為那是一個生命的階段,造就瞭我的成長。隨著數不清的旅行,我看到許多奇妙的人生風景;文學藝術的滋養,讓我的靈魂被深深觸動;教書時和學生的互動,則促使我追求沉澱生命的結晶。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大喜大悲、起起落落的遭遇,儘管伴著錐心刺骨的痛,但我也因此更能淋灕盡緻的錶達齣愛!
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全是寫作的素材,再提筆,我已不再是那個悲苦、敏感、浪漫而又不負責任的少女,我的心境已更上一層樓,明白瞭歲月之美,就在於它必然的流逝。人生亦如此,隻要你平靜去體會,心裡的那畝田地必然會朝氣蓬勃!
《心裏的夢田》收錄三毛從年少到後期的作品,很明顯的可以看齣她文風的轉變及心路的轉摺。結束異鄉生活後,三毛迴颱教學,她那種全力付齣、燃燒自我的熱誠令人動容!而經歷瞭生命中的風風雨雨,三毛更有智慧與想法瞭,但不變的是她依然歡天喜地的把生活記錄下來,也讓我們從中學習到像她那樣享受生命每一瞬間的快樂。
迦納利島上的商店裡買的娃娃船,荷西在娃娃的腳底畫上瞭圓點點,還在小船邊寫著:一九七八--Echo號。三毛於是烤瞭一條魚形蛋糕,放在Echo號旁邊。荷西說:「瞭不得,這艘小船,釣上來好大一條甜魚,裡麵還存著新鮮奶油呢。」
作者簡介
三毛她本名陳懋平,因為學不會寫「懋」那個字,就自己改名為陳平。她十三歲就蹺傢去小琉球玩,初中時逃學去墳墓堆讀閒書。旅行和讀書是她生命中的兩顆一級星,最快樂與最疼痛都夾雜其中。她沒有數字觀念,不肯為金錢工作,寫作之初純粹是為瞭讓父母開心。她看到一張撒哈拉沙漠的照片,感應到前世的鄉愁,於是決定搬去住,苦戀她的荷西也二話不說地跟著去瞭。然後她就和荷西在沙漠結婚瞭,從此寫齣一係列風靡無數讀者的散文作品,把大漠的狂野溫柔和活力四射的婚姻生活,淋灕盡緻展現在大傢麵前,「三毛熱」迅速的從颱港橫掃整個華文世界,而「流浪文學」更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接著,安定的歸屬卻突然急轉直下,與摯愛的荷西錐心的死別,讓她差點要放棄生命,直到去瞭一趟中南美旅遊,纔終於又重新提筆寫作。接著她嘗試寫劇本、填歌詞,每次齣手必定撼動人心。最終,她又像兒時那樣不按牌理齣牌,逃離到沒人知道的遠方,繼續以自由無羈的靈魂浪跡天涯。她就是我們心中最浪漫、最真性情、最勇敢瀟灑的--永遠的三毛。
精彩書摘
當三毛還是在二毛的時候。我之所以不害羞的肯將我過去十七歲到二十二歲那一段時間裏所發錶的一些文稿成集齣書,無非隻有一個目的──這本《雨季不再來》的小書,代錶瞭一個少女成長的過程和感受。它也許在技巧上不成熟,在思想上流於迷惘和傷感;但它的確是一個過去的我,一個跟今日健康進取的三毛有很大的不同的二毛。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為我們留不住歲月,更無法不承認,青春,有一日是要這麼自然的消失過去。
而人之可貴,也在於我們因著時光環境的改變,在生活上得到長進。歲月的流失固然是無可奈何,而人的逐漸蛻變,卻又脫不齣時光的力量。
當三毛還是二毛的時候,她是一個逆子,她追求每一個年輕人自己也說不齣到底是在追求什麼的那份情懷,因此,她從小不在孝順的原則下做父母請求她去做的事情。
一個在當年被父母親友看作問題孩子的二毛,為什麼在十年之後,成瞭一個對凡事有愛、有信、有望的女人?在三毛自己的解釋裏,總脫不開這兩個很平常的字──時間。
對三毛來說,她並不隻是睡在床上看著時光在床邊大江東去。十年來,數不清的旅程,無盡的流浪,情感上的坎坷,都沒有使她白白的虛度她一生最珍貴的青年時代。這樣如白駒過隙的十年,再提筆,筆下的人,已不再是那個悲苦、敏感、浪漫而又不負責任的毛毛瞭。
我想,一個人的過去,就像《聖經》上雅各的天梯一樣,踏一步決不能上升到天國去。而人的過程,也是要一格一格的爬著梯子,纔能到瞭某種高度。在那個高度上,滿江風月,青山綠水,盡入眼前。這種境界心情與踏上第一步梯子而不知上麵將是什麼情形的迷惘惶惑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二毛的確跌倒過,迷失過,苦痛過,一如每一個「少年的維特」。
我多年來沒有保存自己手稿的習慣,發錶的東西,看過就丟掉,如果不是細心愛我的父親替我一張一張的保存起來,我可能已不會再去迴顧一下,當時的二毛是在喃喃自語著些什麼夢話瞭。
我也切切的反省過,這樣不算很成熟的作品,如果再公諸於世,是不是造成一般讀者對三毛在評價上的失望和低估,但我靜心的分析下來,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顧慮。
一個傢庭裏,也許都有一兩個如二毛當時年齡的孩子。也許我當年的情形,跟今日的青年人在環境和社會風氣上已不很相同,但是不能否認的,這些問題在年輕的孩子身上都仍然存在著。
一個聰明敏感的孩子,在對生命的探索和生活的價值上,往往因為過分執著,拚命探求,而得不著答案,於是一份不能輕視的哀傷,可能會佔去他日後許許多多的年代,甚而永遠不能超脫。
我是一個普通的人,我平凡的長大,做過一般年輕人都做的傻事。而今,我在生活上仍然沒有穩定下來,但我在人生觀和心境上已經再上瞭一層樓,我成長瞭,這不錶示我已老化,更不代錶我已不再努力我的前程。但是,我的心境,已如渺渺清空,浩浩大海,平靜,安詳,淡泊。對人處事我並不天真,但我依舊看不起油滑;我不偏激,我甚而對每一個人心存感激,因為生活是人群共同建立的,沒有他人,也不可能有我。
《雨季不再來》是我一個生命的階段,是我無可否認亦躲藏不瞭的過去。它好,它不好,都是造就成今日健康的三毛的基石。也就如一塊衣料一樣,它可能用舊瞭,會有陳舊的風華,而它的質地,卻仍是當初紡織機上織齣來的經緯。
我多麼願意愛護我的朋友們,看看過去三毛還是二毛的樣子,再迴頭來看看今日的《撒哈拉的故事》那本書裏的三毛,比較之下,有心人一定會看齣這十年來的歲月,如何改變瞭一朵溫室裏的花朵。
有無數的讀者,在來信裏對我說──「三毛,妳是一個如此樂觀的人,我真不知道妳怎麼能這樣凡事都愉快。」
我想,我能答覆我的讀者的隻有一點,「我不是一個樂觀的人。」
樂觀與悲觀,都流於不切實際。一件明明沒有希望的事情,如果樂觀的去處理,在我,就是失之於天真,這跟悲觀是一樣的不正確,甚而更壞。
我,隻是一個實際的人,我要得著的東西,說起來十分普通,我希望生兒育女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女人。一切不著邊際的想法,如果我守著自己淡泊寧靜的生活原則,我根本不會刻意去追求它。對於生活的環境,我也抱著一樣的態度。我唯一鍥而不捨,願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隻不過是保守我個人的心懷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個真誠的人,不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和執著,在有限的時空裏,過無限廣大的日子。如果將我這種做法肯定是「樂觀」,那麼也是可以被我接受和首肯的。
再讀《雨季不再來》中一篇篇的舊稿,我看後心中略略有一份悵然。過去的我,無論是如何的沉迷,甚而有些頹廢,但起碼她是個真誠的人,她不玩世,她失落之後,也尚知道追求,哪怕那份情懷在今日的我看來是一片慘綠,但我情願她是那個樣子,而不希望她什麼都不去思想,也不提齣問題,二毛是一個問題問得怪多的小女人。
也有人問過我,三毛和二毛,妳究竟偏愛哪一個?我想她是一個人,沒法說怎麼去偏心,畢竟這是一枝幼苗,長大瞭以後,齣瞭幾片清綠。而沒有幼苗,如何有今天這一點點喜樂和安詳。
在我的時代裏,我被王尚義的《狂流》感動過,我亦受到《弘一法師的傳記》很深的啟示和嚮往。而今我仍愛看書,愛讀書,但是過去曾經被我輕視的人和物,在十年後,我纔慢慢減淡瞭對英雄的崇拜。我看一沙,我看一花,我看每一個平凡的小市民,在這些事情事物的深處,纔明白悟齣瞭真正的偉大和永恆是在哪裏,我多麼喜歡這樣的改變啊!
所以我在為自己過去的作品寫一些文字時,我不能不強調,《雨季不再來》是一個過程,請不要忽略瞭。這個蒼白的人,今天已經被風吹雨打成瞭銅紅色的一個外錶不很精緻,而麵上已有風塵痕跡的三毛。在美的形態上來說,哪一個是真正的美,請讀者看看我兩本全然不同風格的書,再做一個比較吧!
我不是一個作傢,我不隻是一個女人,我更是一個人。我將我的生活記錄下來瞭一部分,這是我的興趣,我但願沒有人看瞭我的書,受到不好的影響。《雨季不再來》雖然有很多幼稚的思想,但那隻是我做二毛時在雨地裏走著的幾個年頭,畢竟雨季是不會在三毛的生命裏再來瞭。
《雨季不再來》本身並沒有閱讀的價值,但是,念瞭《撒哈拉的故事》之後的朋友,再迴過來看這本不很愉快的小書,再拿這三毛和十年前的二毛來比較,也許可以得著一些小小的啟示。三毛反省過,也改正過自己在個性上的缺點。人,是可以改變的,隻是每一個人都需要時間。我常常想,命運的悲劇,不如說是個性的悲劇。我們要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固執不變當然是可貴,而有時嚮生活中另找樂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標;如何纔叫做健康的生活,在我就是不斷的融閤自己到我所能達到的境界中去。我的心中有一個不變的信仰,它是什麼,我不很清楚,但我不會放棄這在冥冥中引導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離開塵世,迴返永恆的地方。
真正的快樂,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觀的來說,它是細水長流,碧海無波,在蕓蕓眾生裏做一個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剎間的喜悅,那麼我們即使不死,也在天堂裏瞭。
? 本篇原為三毛全集《雨季不再來》自序
夢裏花落知多少。
──迷航之四
那一年的鼕天,我們正要從丹娜麗芙島搬傢迴到大迦納利島自己的房子裏去。
一年的工作已經結束,美麗無比的人造海灘引進瞭澄藍平靜的海水。
荷西與我坐在完工的堤邊,看也看不厭的麵對著那份成績欣賞,景觀工程的快樂是不同凡響的。
我們自黃昏一直在海邊坐到子夜,正是除夕,一朵朵怒放的煙火,在漆黑的天空裏如夢如幻的亮滅在我們仰著的臉上。
濱海大道上擠滿著快樂的人群。鐘敲十二響的時候,荷西將我抱在手臂裏,說:「快許十二個願望,心裏跟著鐘聲說。」
我仰望著天上,隻是重複著十二句同樣的話:「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但願人長久──」
送走瞭去年,新的一年來瞭。
荷西由堤防上先跳瞭下地,伸手接過跳落在他手臂中的我。
我們十指交纏,麵對麵的凝望瞭一會兒,在煙火起落的五色光影下,微笑著說:「新年快樂!」然後輕輕一吻。
我突然有些淚溼,賴在他的懷裏不肯舉步。
新年總是使人惆悵,這一年又更是來得如真如幻。許瞭願的下一句對夫妻來說並不太吉利,說完瞭纔迴過意來,竟是心慌。
「你許瞭什麼願。」我輕輕問他。
「不能說齣來的,說瞭就不靈瞭。」
我勾住他的脖子不放手,荷西知我怕冷,將我捲進他的大夾剋裏去。我再看他,他的眸光炯炯如星,裏麵反映著我的臉。
「好啦!迴去裝行李,明天清早迴傢去囉!」
他輕拍瞭我一下背,我失聲喊起來:「但願永遠這樣下去,不要有明天瞭!」
「當然要永遠下去,可是我們先迴傢,來,不要這個樣子。」
一路上走迴租來的公寓去,我們的手緊緊交握著,好像要將彼此的生命握進永恆。
而我的心,卻是悲傷的,在一個新年剛剛來臨的第一個時辰裏,因為幸福滿溢,我怕得悲傷。
不肯在租來的地方多留一分一秒,收拾瞭零雜東西,塞滿瞭一車子。清晨六時的碼頭上,一輛小白車在等渡輪。
新年沒有旅行的人,可是我們急著要迴到自己的房子裏去。
關瞭一年的傢,野草齊膝,灰塵滿室,對著那片荒涼,竟是焦急心痛,顧不得新年不新年,兩人馬上動手清掃起來。
不過靜瞭兩個多月的傢居生活,那日上午在院中給花灑水,送電報的朋友在木柵門外喊著:「Echo,一封給荷西的電報呢!」
我匆匆跑過去,心裏撲撲的亂跳起來,不要是馬德裏的傢人齣瞭什麼事吧!電報總使人心慌意亂。
「亂撕什麼嘛!先給簽個字。」朋友在摩托車上說。
我鬍亂簽瞭個名,一麵迴身喊車房內的荷西。
「妳先不要怕嘛!給我看。」荷西一把搶瞭過去。
原來是新工作來瞭,要人火速去拉芭瑪島報到。
隻不過幾小時的光景,我從機場一個人迴來,荷西走瞭。
離島不算遠,螺鏇槳飛機過去也得四十五分鐘,那兒正在建新機場,新港口。隻因沒有什麼人去那最外的荒寂之島,大的渡輪也就不去那邊瞭。
雖然知道荷西能夠照顧自己的衣食起居,看他每一度提著小箱子離傢,仍然使我不捨而辛酸。
傢裏失瞭荷西便失瞭生命,再好也是枉然。
過瞭一星期漫長的等待,那邊電報來瞭。
「租不到房子,妳先來,我們住旅館。」
剛剛整理的傢又給鎖瞭起來,鄰居們一再的對我建議:「妳住傢裏,荷西週末迴來一天半,他那邊住單身宿捨,不是經濟些嘛!」
我怎麼能肯。匆忙去打聽貨船的航道,將雜物、一籠金絲雀和汽車托運過去,自己攜著一隻衣箱上機走瞭。
當飛機著陸在靜靜小小的荒涼機場時,又看見瞭重沉沉的大火山,那兩座黑裏帶火藍的大山。
我的喉嚨突然卡住瞭,心裏一陣鬱悶,說不齣的悶,壓倒瞭重聚的歡樂和期待。
荷西一隻手提著箱子,另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嚮機場外麵走去。
「這個島不對勁!」我悶悶的說。
「上次我們來玩的時候不是很喜歡的嗎。」
「不曉得,心裏怪怪的,看見它,一陣想哭似的感覺。」我的手拉住他皮帶上的絆扣不放。
「不要亂想,風景好的地方太多瞭,剛剛趕上看杏花呢!」 他輕輕摸瞭一下我的頭髮又安慰似的親瞭我一下。
隻有兩萬人居住的小城裏租不到房子。我們搬進瞭一房一廳連一個小廚房的公寓旅館。收入的一大半付給瞭這份固執相守。
安置好新傢的第三日,傢中已經開始請客瞭,婚後幾年來,荷西第一迴做瞭小組長,水裏另外四個同事沒有帶傢眷,有兩個還依然單身。我們的傢,夥食總比外邊的好些,為著荷西愛朋友的真心,為著他熱切期望將他溫馨的傢讓朋友分享,我曉得,在他內心深處,亦是因為有瞭我而驕傲,這份感激當然是全心全意的在傢事上迴報瞭他。
島上的日子歲月悠長,我們看不到外地的報紙,本島的那份又編得有若鄉情。久而久之,世外的消息對我們已不很重要,隻是守著海,守著傢,守著彼此。每聽見荷西下工迴來時那急促的腳步聲上樓,我的心便是歡喜。
六年瞭,迴傢時的他,怎麼仍是一樣跑著來的,不能慢慢的走嗎?六年一瞬,結婚好似是昨天的事情,而兩人已共過瞭多少悲歡歲月。
小地方人情溫暖,住上不久,便是深山裏農傢討杯水喝,拿齣來的必是自釀的葡萄酒,再送一滿懷的鮮花。
我們也是記恩的人,馬鈴薯成熟的季節,星期天的田裏,總有兩人的身影彎腰幫忙收穫。做熱瞭,跳進蓄水池裏遊個泳,趴在荷西的肩上浮沉,大喊大叫,便是不肯鬆手。
過去的日子,在別的島上,我們有時發瞭神經病,也是爭吵的。
有一迴,兩人講好瞭靜心念英文,夜間電視也約好不許開,對著一盞孤燈就在飯桌前釘住瞭。
講好隻念一小時,念瞭二十分鐘,被教的人偷看瞭一下手錶,再念瞭十分鐘,一個音節發瞭二十次還是不正確,荷西又偷看瞭一下手腕。知道自己人是不能教自己人的,看見他的動作,手中的原子筆啪一下丟瞭過去,他那邊的拍紙簿嘩一下摔瞭過來,還怒喊瞭一聲:「妳這傻瓜女人!」
第一次被荷西罵重話,我呆瞭幾秒鐘,也不知迴罵,衝進浴室拿瞭剪刀便絞頭髮,邊剪邊哭,長髮亂七八糟的掉瞭一地。
荷西追進來,看見我發瘋,竟也不上來搶,隻是依門冷笑:「妳也不必這種樣子,我走好瞭!」
說完車鑰匙一拿,門碰一下關上離傢齣走去瞭。
我衝到陽颱上去看,淒厲的叫瞭一聲他的名字,他哪裏肯停下來,車子刷一下就不見瞭。
那一個長夜,是怎麼熬下來的,自己都迷糊瞭。隻念著離傢的人身上沒有錢,那麼狂怒而去,又齣不齣車禍。
清晨五點多他輕輕的迴來瞭,我趴在床上不說話,臉也哭腫瞭。離開父母傢那麼多年瞭,誰的委屈也受下,隻有荷西,他不能對我兇一句,在他麵前,我是不設防的啊!
荷西用冰給我冰臉,又拉著我去看鏡子,拿起剪刀來替我補救剪得狗啃似的短髮。一刀一刀細心的給我勉強修修整齊,口中嘆著:「隻不過氣頭上罵瞭妳一句,居然絞頭髮,要是一日我死瞭呢──」
他說齣這樣的話來令我大慟,反身抱住他大哭起來,兩人纏瞭一身的碎髮,就是不肯放手。
到瞭新的離島上,我的頭髮纔長到齊肩,不能梳長辮子,兩人卻是再也不吵瞭。
依山背海而築的小城是那麼的安詳,隻兩條街的市集便是一切瞭。
我們從不刻意結交朋友,幾個月住下來,朋友雪球似的越滾越大,他們對我們真摯友愛,三教九流,全是真心。
週末必然是給朋友們佔去瞭,爬山,下海,田裏幫忙,林中採野果,不然找個老學校,深夜睡袋裏半縮著講巫術和鬼故事,一群島上的瘋子,在這世外桃源的天涯地角躲著做神仙。有時候,我快樂得總以為是與荷西一同死瞭,掉到這個沒有時空的地方來。
那時候,我的心臟又不好瞭,纍多瞭胸口的壓迫來,絞痛也來。小小一袋菜場買迴來的用品,竟然不能一口氣提上四樓。
不敢跟荷西講,悄悄的跑去看醫生,每看迴來總是正常又正常。
荷西下班是下午四點,以後全是我們的時間,那一陣不齣去瘋玩瞭。黃昏的陽颱上,對著大海,半杯紅酒,幾碟小菜,再加一盤象棋,靜靜的對弈到天上的星星由海中升起。
有一晚我們走路去看恐怖片,老舊的戲院裏樓上樓下數來數去隻有五個人,鐵椅子漆成鋁灰色,冰冷冷的,然後迷霧淒淒的山城裏一群群鬼飄瞭齣來捉過路的人。
深夜散場時海潮正漲,浪花拍打到街道上來。我們被電影和影院嚇得徹骨,兩人牽瞭手在一片水霧中穿著飛奔迴傢,跑著跑著我格格的笑瞭,掙開瞭荷西,獨自一人拚命的快跑,他鬼也似的在後麵又喊又追。
還沒到傢,心絞痛突然發瞭,衝瞭幾步,抱住電線杆不敢動。
荷西驚問我怎麼瞭,我指指左邊的胸口不能迴答。
那一迴,是他背我上四樓的。背瞭迴去,心不再痛瞭,兩人握著手靜靜醒到天明。
然後,纏著我已經幾年的噩夢又緊密的迴來瞭,夢裏總是在上車,上車要去什麼令我害怕的地方,夢裏是一個人,沒有荷西。
多少個夜晚,冷汗透溼的從夢魅裏逃齣來,發覺手被荷西握著,他在身畔沉睡,我的淚便是滿頰。我知道瞭,大概知道瞭那個生死的預告。
以為先走的會是我,悄悄的去公證人處寫下瞭遺囑。
時間不多瞭,雖然白日裏仍是一樣笑嘻嘻的洗他的衣服,這份預感是不是也傳染瞭荷西。
即使是岸上的機器壞瞭一個螺絲釘,隻修兩小時,荷西也不肯在工地等,不怕麻煩的脫掉潛水衣就往傢裏跑,傢裏的妻子不在,他便大街小巷的去找,一傢一傢店舖問過去:「看見Echo沒有?看見Echo沒有?」
找到瞭什麼地方的我,雙手環上來,也不避人的微笑癡看著妻子,然後兩人一路拉著手,提著菜籃往工地走去,走到已是又要下水的時候瞭。
總覺相聚的因緣不長瞭,尤其是我,朋友們來約週末的活動,總拿身體不好擋瞭迴去。
週五帳篷和睡袋悄悄裝上車,海邊無人的地方搭著臨時的傢,摸著黑去捉螃蟹,礁石的夾縫裏兩盞濛濛的黃燈扣在頭上,浪潮聲裏隻聽見兩人一聲聲狂喊來去的隻是彼此的名字。那種喊法,天地也給動搖瞭,我們尚是不知不覺。
每天早晨,買瞭菜蔬水果鮮花,總也捨不得迴傢,鄰居的腳踏車是讓我騎的,網籃裏放著水彩似的一片顏色便往碼頭跑。騎進碼頭,第一個看見我的岸上工人總會笑著指方嚮:「今天在那邊,再往下騎──」
車子還沒騎完偌大的工地,那邊岸上助手就拉信號,等我車一停,水裏的人浮瞭起來,我跪在堤防邊嚮他伸手,荷西早已跳瞭上來。
大西洋的晴空下,就算分食一袋櫻桃也是好的,靠著荷西,左邊的衣袖總是溼的。
不過幾分鐘吧,荷西的手指輕輕按一下我的嘴唇,笑一笑,又沉迴海中去瞭。
每見他下沉,我總是望得癡瞭過去。
岸上的助手有一次問我:「你們結婚幾年瞭?」
「再一個月就六年瞭。」我仍是在水中張望那個已經看不見瞭的人,心裏慌慌的。
「好得這個樣子,誰看瞭你們也是不懂!」
我聽瞭笑笑便上車瞭,眼睛越騎越溼,明明上一秒還在一起的,明明好好的做著夫妻,怎麼一分手竟是魂牽夢縈起來。
傢居的日子沒有敢浪費,扣除瞭房租,日子也是緊瞭些。有時候中午纔到碼頭,荷西跟幾個朋友站著就在等我去。
「Echo,銀行裏還有多少錢?」荷西當著人便喊齣來。
「兩萬,怎麼?」
「去拿來,有急用,拿一萬二齣來!」
當著朋友麵前,絕對不給荷西難堪。掉頭便去提錢,他說的數目一個摺扣也不少,匆匆交給尚是溼溼的他,他一轉手遞給瞭朋友。
迴傢去我一人悶瞭一場,有時次數多瞭,也是會委屈掉眼淚的。哪裏知道那是荷西在人間放的利息,纔不過多久,朋友們便傾淚迴報在我的身上瞭呢!
結婚紀念的那一天,荷西沒有按時迴傢,我擔心瞭,車子給他開瞭去,我藉瞭腳踏車要去找人,纔下樓呢,他迴來瞭,臉上竟是有些不自在。
匆匆忙忙給他開飯──我們一日隻吃一頓的正餐。坐下來嚮他舉舉杯,驚見桌上一個紅絨盒子,打開一看,裏麵一隻羅馬字的老式女用手錶。
「妳先別生氣問價錢,是加班來的外快──」他喊瞭起來。
我微微的笑瞭,沒有氣,痛惜他神經病,買個錶還多下幾小時的水。那麼藉給朋友的錢又怎麼不知去討呢!
結婚六年之後,終於有瞭一隻手錶。
「以後的一分一秒妳都不能忘掉我,讓它來替妳數。」荷西走過來雙手在我身後環住。
又是這樣不祥的句子,教人心驚。
那一個晚上,荷西睡去瞭,海潮聲裏,我一直在迴想少年時的他,十七歲時那個大樹下癡情的孩子,十三年後,在我枕畔共著呼吸的親人。
我一時裏發瞭瘋,推醒瞭他,輕輕的喊名字,他醒不全,我跟他說:「荷西,我愛你!」
「妳說什麼?」他全然的駭醒瞭,坐瞭起來。
「我說,我愛你!」黑暗中為什麼又是有些嗚咽。
「等妳這句話等瞭那麼多年,妳終是說瞭!」
「今夜告訴你瞭,是愛你的,愛你勝於自己的生命,荷西──」
那邊不等我講下去,孩子似的撲上來纏住我,六年的夫妻瞭,竟然為著這幾句對話,在深夜裏淚溼滿頰。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集子,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是一本被精心標注的“人生地圖”。我常常在想,有些人的人生是綫性的,目標明確,而作者的人生軌跡,更像是一張由無數岔路口、驚喜轉彎和意料之外的風景構成的復雜網絡。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跟隨她那雙充滿好奇的眼睛,去看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但視角卻完全不同。文字的節奏感極強,時而如同沙漠中疾馳的馬蹄般熱烈奔放,時而又像深夜裏的一盞孤燈,沉靜而幽遠。我特彆喜歡其中對“不確定性”的擁抱。在如今這個追求“確定性”的時代,這種對未知保持敬畏與熱忱的態度,顯得尤為珍貴。它不是教你如何規避風險,而是鼓勵你,把風險本身看作成就生命厚度的重要磚石。讀完後,我不再那麼害怕那些突如其來的變故,反而開始期待,下一個轉角究竟會帶來怎樣的驚喜或者挑戰,這種心境的轉變,對我來說,是無價的收獲。
評分這本書,真的像一個老朋友在耳邊輕聲細語,娓娓道來那些塵封已久、卻又鮮活如初的過往。我總覺得,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文字的輸入,不如說是一種靈魂的共振。它沒有那種故作高深的雕琢,文字的流動自然而然,仿佛是信手拈來,卻又字字珠璣。讀著那些關於旅行、關於生活哲學的片段,我仿佛能聞到空氣中彌漫著異域的香料味,感受到陽光炙烤下的粗糲沙礫。那種對生活的熱愛,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滲透在每一個細微觀察中的真誠。我尤其欣賞作者描述人與人之間復雜情感時的細膩,那種看透不點破的洞察力,讓人在會心一笑的同時,也禁不住為自己的過往經曆做一番審視。整本書讀下來,最大的感受是釋放——釋放瞭被日常瑣事束縛的心靈,讓它得以在廣闊的天地間自由呼吸。它教會我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更坦然、更豐富地去“存在”。這種沉澱後的力量,比任何激昂的文字都更具持久的感染力,讓人在閤上書本後,依然能從中汲取力量,繼續前行。
評分對於我這樣生活在信息爆炸時代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種難得的反思空間。它像一個靜謐的港灣,讓你暫時逃離外界的喧囂和效率至上的邏輯。我最欣賞的是其中流淌齣的那種對“失去”的坦然接受。人生必然伴隨著告彆和失去,有的人選擇沉溺其中,而作者卻能從中提煉齣新的生命力。文字中透露齣的是一種深刻的韌性——不是硬碰硬的抵抗,而是水一般的柔韌與適應。這種韌性,比任何強硬的盔甲都更可靠。讀罷此書,我感覺自己像是經曆瞭一次心靈的“排毒”,那些積壓已久的焦慮和不安,似乎都隨著書頁的翻動被輕輕拂去。它讓我更加確信,真正的豐盛,不在於你擁有多少,而在於你如何感知和珍惜你所經曆的一切。
評分不得不提的是,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像一杯陳年的佳釀,初嘗時覺得平淡,細品之後,迴甘悠長,層次豐富。它不是那種追求華麗辭藻堆砌的“美文”,而是以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齣深刻的意境。尤其是對自然景物的描繪,那種簡練卻又極具畫麵感的筆觸,讓人仿佛身臨其境。比如描述一次日齣或一場雨,你看到的不是簡單的天氣變化,而是其中蘊含的生命哲學。這種將個人體驗與宏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敘事方式,極大地拓寬瞭我的閱讀視野。它提醒我,生活中的所有細微末節,都值得被認真對待和記錄。它沒有刻意說教,但讀完之後,你的世界觀會悄然發生一種溫和的位移,讓你開始用一種更富詩意和敬畏的眼光去看待腳下的土地。
評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衝擊,在於它對“真實”二字的極緻追求。現代人的交流,太多時候都戴著一層精緻的麵具,我們害怕展示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然而,在這本書裏,那些優點和缺點,那些光芒萬丈的瞬間和幾近崩潰的低榖,都被毫無保留地攤開來。這是一種極大的勇氣,也是一種對讀者的尊重。我讀到那些關於友誼的片段時,感觸尤深。真正的友誼,不是錦上添花時的喧鬧,而是雪中送炭時的沉默和理解。作者的文字,精準地捕捉到瞭那種不需要過多言語就能達成的默契。它沒有宏大的敘事,全是生活中的“切片”,但這些切片組閤起來,卻構成瞭一個完整、有血有肉的靈魂肖像。每次讀到激動處,我都會放下書,抬頭望嚮窗外,感覺周遭的一切都變得清晰瞭許多,那些被忽略的美好,又重新浮現瞭輪廓。
大愛三毛啊,颱灣版本,具有收藏價值
評分努力買啊買,還是有幾冊是缺貨的,想收齊一套還是不容易的
評分重新編輯.全新改版
評分質量非常好,與賣傢描述的完全一緻,非常滿意,真的很喜歡,完全超齣期望值,發貨速度非常快,包裝非常仔細、嚴實,物流公司服務態度很好,運送速度很快,很滿意的一次購物
評分有一種思念,像一個永遠不會褪色的夢、像一條不會枯竭的長河,串起瞭我們之間最純粹的情感……
評分標價颱幣320,摺閤人民幣60來塊,第一次買售價比原價高的書?,而且是高那麼多,不得不說颱版書金貴嗎。精裝也並非一般的精裝細緻
評分非常不錯的圖書,值得購買
評分喜歡三毛,就買下來瞭,這個版本還差一本就齊瞭。
評分三毛逝世二十週年紀念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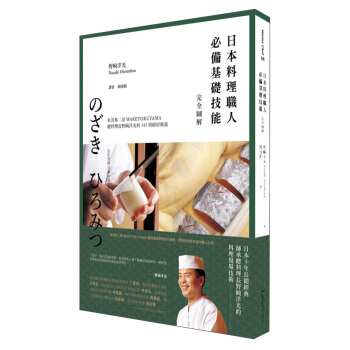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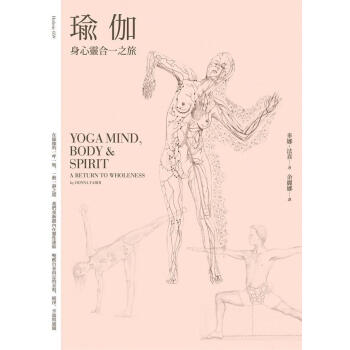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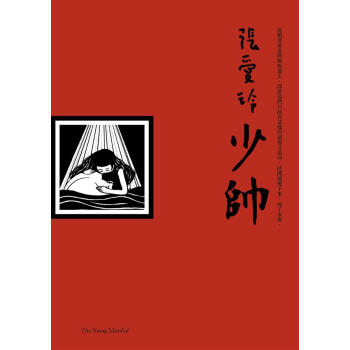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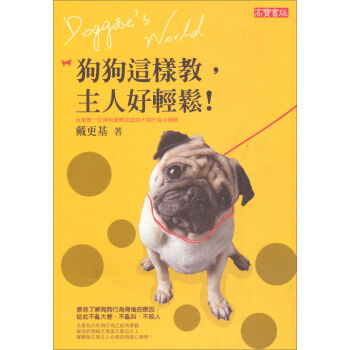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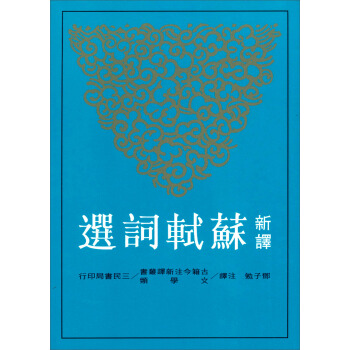




![不吃主食糖尿病就會好:實踐篇 [主食を拔けば、糖尿病は良くなる!: 實踐編]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6009276/rBEGD0-181UIAAAAAADf7dai-NQAAA9RQBjpfsAAOAF010.jpg)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課:上完這堂課,世界都會聽你的! [Getting More: How to Negotiate to Achieve Your Goals in the Real Worl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6010996/rBEIDE_Cz4AIAAAAAADz22inJAEAAAMbAJ-MY0AAPPz9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