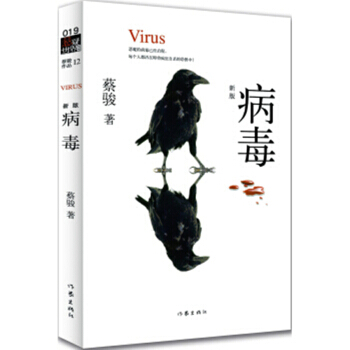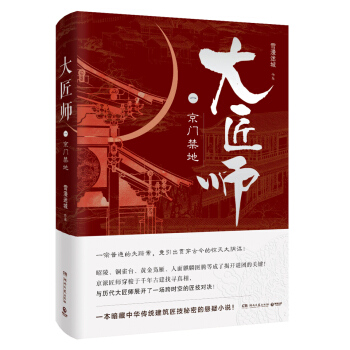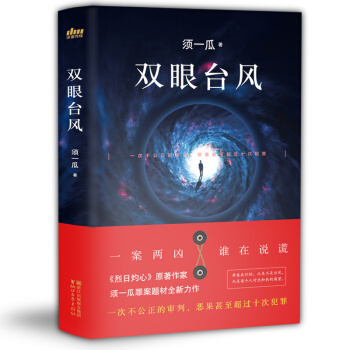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时下具有杀伤力的老年病:阿尔兹海默症
想要浪迹天涯的年轻人,如何被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改变?
某一段历史的既得利益者(父辈)如何对待那一段不同寻常的青春记忆?
城市移民家族的通病:每一代都有移民的因由
七零代作家的继续创作,以翻译为漫长的间隔年,暌违文坛十年。
内容简介
子清,自小缺失家族观念,是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一代都市移民后代,
浪迹天涯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无根的无奈。子清被迫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责,因此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作品深刻、细腻地描写了都市养老现况,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时代里,这样的记录极具现实意义。
子清不得不去东北替父寻亲,也在此过程中,惊讶地发现父母的命运和那段历史息息相关,诧异于远亲印象中的父母和自己所认识的父母是截然不同的。
父亲的病,犹如隐喻,意味着一代历史的消隐,一方面是当事人的主动忘却,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因病而忘,结果便是后代的无知,上一代的人生无法得到证据。
在表层的寻亲访故场景之后,作为隐线的内省增添了作品的精神内核,将失智、失忆作为动乱年代既得利益者的回忆的隐喻体,含蓄表达了这一代中老年对中国近代史的态度——
失去记忆的老人,也很快被遗忘、被告别,恰如他所经历的那整个动荡的时代。
寻找记忆的中年人,则陷入不可考的时代泥沼,一切只能归结于想象。传统、历史、家族……这些厚重的生命附加值在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隐没,但她们也将拥有这一代人所独有的生命印记,在非家族化的城市人际关系中继续领略生老病死的意义。
作者简介
于是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签约作家。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至今已出版九部个人著作(含再版),包括小说《一只黑猫的自闭症》、《事后》、《六翼天使》,书影评选集《慌城孤读》,以及数部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作品曾刊发于《收获》、《上海文学》、《鲤》等文学刊物。
同时,于是致力于文学翻译。至今已有二十六部译作面世,包括赫赫有名的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所著《黑暗塔》之第七卷、《杜马岛》,丹·布朗的《失落的秘符》,英国女作家温特森的《时间之间》、《橘子不是wei一的水果》、英国作家亨利·S·斯托克所著《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等。
专业写作之余,于是还是时尚报刊的书评、影评和情感专栏作家,也是人物报道的资深记者。十余年来,持续为时尚杂志撰写人物专访等特约稿件,作品见于《LOHAS乐活》、《瑞丽·伊人》、《时装》、《芭莎》等多家时尚刊物。
精彩书摘
样章选段(一)
大多数时候,这座内装修规格达到三星宾馆的福利院里都很安静,公共活动区的一大半空间都被一张大桌占据了,老人们大多围坐在桌边,什么也不做。只要有人弄脏了地板,就会有保洁员出现,在几分钟内收拾干净。每一条走廊都被拖洗得锃亮,反衬着某种肮脏的必然性。她还见过几次洗地机工作的场面,肥皂水和消毒水转出一圈圈的白色泡沫,像一幅缓缓铺张的抽象画,那是她在这个空间里见过最有生机的图案。
她常觉得这里的洁净维持得太好,让人放心,却也伪饰太平。都市化的养老机构里有宽敞好用的大洗浴室,走廊、窗边、床边和卫生间里都有扶手,瓷砖地,涂料墙,木制原色吊顶,吸顶灯,中央空调,统一的洁具……没有任何个性,也没有缺点。她在心里称之为:老年幼儿园、时空结界、生灵墓园……
今天,一出电梯,她就觉得四楼的气氛有点怪异。大厅里的人影寥寥无几,摆在电视机墙对面的蓝色沙发上竟然空无一人。通常,护工们会在这个钟点把老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各就各位,围坐大桌,准备开饭,她会在那一群老人的剪影中迅速找出父亲,因为他的座位几乎是固定的,整个白天,他都默默地坐在那里。今天桌边没有人。但她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她看到,父亲双手抱着一台微波炉,绕着长方形的大桌走成背影,插头线在桌脚绊了一下,又被拖着走,不情不愿的跟在一双白生生的赤脚后头,随着蹒跚的脚步一顿一顿。肩胛骨仿佛要刺穿汗衫耸出来,和怀里沉重的分量艰难对峙着。现在,他又拐弯了,微波炉有一扇镜面门,摇晃在他身前,映现出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左右颠动中,反倒是她更像被招进魔镜的魂,而他是巫。她强忍着,把视线从过分清晰的镜面中的自身拉出来,去看他的脸,他凸起的膝盖,他几乎瘦到隐形的胯部,他颤抖的小腿和大腿裸露在外,皮肉就像裹尸布垂挂下来。他继续绕行,又走成了背影。她不知道他这样捧着一台微波炉绕着桌子走了多少圈。她想象不出一个耄耋老人有多大的气力能完成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我们不敢去碰他。他刚刚踢走了小黄,还差点用微波炉来砸我。”穿着靛蓝色护工服的胖阿姨走到她身边,并没有压低嗓门。她是负责给老人清洗身体的女工,几乎每天给她父亲擦下身时都会被父亲扬手掴掌,甚至握紧拳头,砸向她的任何部位。
“他走累了应该就会自己停下来的。”胖阿姨的语气显示她并没有太大把握,“怕就怕微波炉掉下来砸到他自己。”
但谁也没有动,空气里有一种紧迫的张力,但被更稠密的哀伤冻结住了。她突然害怕地想到,也许这些护工都在等待,微波炉像块巨石一样坠下来,都在默默倒数,数着她父亲病卧在床、因而乖乖听话的时刻。那将意味着每个人都获得解放。她想象着腿骨骨折、趾骨断裂,脆生生的骨茬刺穿疲软的肌肉,而父亲终于肯与肉体妥协,所有护工都将不会再被父亲踢打,她们或许会更疼爱他。这残忍的想象一闪而过,让她不寒而栗。
这是她第一次在福利院里看到父亲衣冠不整,虽然听说过几次——他总是拒绝穿衣,或是拒绝脱衣——但从此往后,这样的场景只怕会越来越多。
第一个月里,护工给她打电话,“你爸爸是不是以前常常打人?他把好几个护工都打了,因为护工要帮他穿衣或是洗澡……他拳头好重呀!”
子清紧握手机回答:“他从不打人的!肯定是因为他不习惯(习惯真的是好事吗?)……他大概还有意识,觉得脱衣服是自己的事。以前,我不会硬脱他的衣服,我会哄他自己脱自己穿。”
“我们每个护工都要照顾七八个病人,没有时间哄的……”
子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很担心父亲会被最后一家可以收容他的机构拒绝。
老男人拖沓的步伐近乎匀速,有种催眠的格调。她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两步,但还没等她张口,胖阿姨就扯开嗓门叫起来,“老王!你看看谁来了!老王!老王!”
每一次,她都恨透了护工们的大嗓门、反复的问,“她是谁?你知道她是谁吗?”
王世全不知道自己是王世全。不知道自己有两个女儿。不知道这是哪里。不知道一切。否则他不会住在这里,24小时受到照料和监控。但也有可能,王世全什么都知道,却被言语抛弃了,因而被一切伦常、逻辑、情感的表达抛弃了,因而酝酿了更充沛的恨,因而有使不完的力气,像个武疯子,在一群失去行动和思维能力的老朽病人中孑然独立,为所欲为。
她恨那种低级的测试。如果病人能说出家里有几口人,微波炉该放在哪里,十减八等于几,那又何苦来这里?她恨他们每次心情好就要执行这番对答,乐此不疲,仿佛只为了向她一个人强调:她是他的女儿。
她也恨那种大嗓门,刻意的,对着理论上应该耳背、应已退智的老人们。她总觉得,既然言语已对这些人无用,那就该换成轻柔的语调、轻柔的抚触。但没有人赞同她。他们说,你必须大声点,引起他们的注意。她已不再申辩或反驳:那是不是也会引起他们的惊慌和恐惧?
父亲不理睬任何人。微波炉仿佛就该是他的一部分,现在,冰冷的金属应该已分享了他的体温,依附在金属箱子上的四肢用恒定频率制造了机械化的心跳。当他又一次在桌角拐弯,迎面向她走来时,她突然惊出一身冷汗,仿佛看到一个机器人捧着自己的遗像向自己走来。
她慢慢迎上前,距离拉近,脸孔被推出镜面,很快变成胸腹、腿脚,在她伸手抱住微波炉的时候,清晰的意识到,她用肚子挡住了画面,黑场,谢幕,再会。她让自己倒着走,好像隔着金属箱子成为父亲的镜像,她希望不要吓到、打断他。她轻轻的说,爸爸,我来了,爸爸。就这样,她轻轻唤着,仿佛念咒,倒退着走完了半圈,父亲终于抬了抬眼帘。之前,他一直沉沉的低头看着地面。
微波炉那么沉。真的,她感到父亲慢慢的把手里的力量转移给她,而那简直是她捧不动的沉重。
样章选段(二)
老家·1996
已经没有人叫她寡妇了。八个孩子都生了孩子,人人都叫她王家奶奶,都羡慕她能收到儿子们从各地寄来的生活费、食品、土特产和生活用品。钱都揣在她腰包里,从不给老幺和媳妇用,也不给孙子孙女买东西。
这时候,落户上海的老四世全才显出了优势。有一天,从上海寄来了一块的确凉布料,正是的确凉走红的时候,老太太赶上了时髦,乐滋滋的,当天下午把料子铺在炕上,立马裁出一件斜襟上装,配的是盘扣,内襟上有揣钱的暗兜,针脚细洁轻柔,料子纹丝不乱。
王家奶奶过了六十大寿,开始给自己缝寿衣。绣花鞋,从鞋底到鞋面绣花,全是自己一针一线完成。贴身的白绸褂子,年年阴雨时节过后都要拿出来晒。一整套寿衣寿裤,挂满了整条晾衣绳,老太太从这头走到那头,用赞许的眼光扫视自己未来阴间的风采,再从那头走回这头,不慌不忙等待阳寿终了。她确实找算命的来过,问自己能活多久,瞎子翻了翻白眼,说,“攒攒攒,散散散……死时都散光,啥也没留下。”
腰包里的零花钱攒够了,王家奶奶就要出门了。她擅长突袭,从不提前预告,出门当天挎个小包袱皮儿,逢人就说去“溜达一圈”。这家那家都要去,这一圈又一圈就是整七年,搞得七个孩子几乎家家人仰马翻。她摆足了媳妇熬成婆的姿态,目标明确,只知道心疼儿女,把媳妇和姑爷当外人对待,从不给好脸色。即便是在新中国七十年代,她这个强悍的顽固的老封建始终认为媳妇要对婆婆磕头行礼,媳妇不能和自己、和儿子同桌饮食,必须低她一等。七个孩子都看得出来,她这是在视察,在揣度哪个孩子能成为她最终的归宿。但出于某种谁也解释不了的原因,她就像掰玉米的笨熊,从不知道珍惜自己已得到的孝顺。
她最希望留在闺女家。当年,闺女跟着三哥去了油田,如今已是大庆油田某一科的科长,姑爷的薪水也十分滋润,为此,她甘愿帮带两个外孙,多少要为将来自己的归宿攒点功绩。但她太不心疼姑爷了,明知姑爷爱好汽车和摄影,就专挑他喜欢的物事骂,骂他玩物丧志,骂他攒不下钱,骂他没有全心全意对老婆。如此半年,姑爷造反了,卷着铺盖到单位去睡。面对由自己引起的夫妻不和,王家奶奶非但没有劝和,还嚷嚷着,“姑娘还找不到小子?”一句话就表明了立场,宁可闺女离婚,她也不愿向姑爷投降。
她知道老三在油田当书记,条件是最好的,她溜达过去,就想要掌管家里的财权。老三媳妇是城里人,当初跟着世祺来到大庆,看到几个油罐就傻了,还哭了几次,心想,我好歹也是城市户口,怎么到了这种荒凉的地方。干活时,啥也不会,刨地也要人教,后来找到在幼儿园带孩子的活儿,倒也适合她。好在身子骨够好,怀了三胎,冬天出门上厕所都不披大衣,仗着年轻气血盛。但她生了三个孩子都不敢让自己亲妈过来看,怕失望。亲妈没来,婆婆来了,婆婆要她交账本,她就漂漂亮亮地交上去,每天陪着老太太去采买,故意去那几个不老实的摊贩前问价,老太太就傻眼了,那么个农妇,怎么知道如何砍价?夫妻俩每个月才几十块钱工资,不砍价、不算计就没法活。三媳妇把各种各样的难题都扔给老太太,看她如何招架。果不其然,老太太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账本搁在了桌上。
比大庆的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就是老四家。老太太不知道上海是啥模样,总觉得远,怪,轻易是不去溜达的。而且,世全和庆芸只生了一个闺女,所有的儿女里面,只有世全没有儿子。1976年头上,老太太听说世全媳妇又怀上了,终于决定去上海溜达一圈。
世全的第二个娃出世,又是个女娃。老太太心不甘情不愿,还是踏上了火车月台。但她万万没想到,世全一家三口,再加刚下来的娃,只能住在14平方米的小屋里——工人新村的朝北房间,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太阳。新村里的邻居都讲上海话,苏北话,她一句也听不懂,听起来都像是在吵架。
第二个女娃生下来八斤半,胖得不像话。庆芸坐完月子就回去上班了,白天里,只有老太太和胖丫头在家。老太太没事儿的时候就看窗外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看他们的穿着打扮,看他们停下来寒暄聊天的姿态,就知道上海有上海的好处。她既羡慕又委屈,因为明白自己不会久留,上海再好,终究不是故乡,冬天冷,夏天热,公用厨房四家人分着用,还没老家的灶房大,公用厕所十分局促,黑漆漆的,还不如老家的露天粪坑来得爽快。老太太在上海,在邻居们面前,总觉得没法施展老婆婆的姿态,庆芸也曾听几个妯娌说过老太太的刁难,心里早有准备,下班回来看到老太沉着脸,就会嘘寒问暖,几句话就把老太太的郁结说开,就算不长久,也至少让她不得发作。
老太太这些年习惯了作天作地,要把百堂英年早逝后吃的苦都挣回来,她的资本就是寡母的霸道。也不止是霸道,她是真的敢干。离开上海时,她背上三个555挂钟,那时候这可是新鲜货,只有大上海有。一台挂在老家,一台送给满意的准亲家(结果那家的漂亮女儿还是没有嫁进来),一台送给对一直很照应寡妇的姑奶奶家。显然,在东北的小屯子里不讲究,没有“送钟”就是“送终”的忌讳。留在老家的那台钟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保持光泽,虽然发条松了,拧紧发条也没法走足半个月了,但依然挺拔体面的挂在砖墙上。
大庆没戏了。上海没戏了。奶奶检讨自己舍近求远。休息了一阵子,决定去沈阳。和老大打官司也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在85年卖掉了前院的房子,赚了四千元。搬去沈阳和女儿住了。老二换了工厂,也去了沈阳。
二媳妇风流迷人,是所有媳妇里最美艳的,老太太却从一开始就瞧不上,溜达过去,除了视察,也有挑战的况味。若不是这么美,年轻气盛的世魁也不会要定了她,最终吃了她的苦头。世魁心善,听说老娘跑遍大江南北,辗转几个孩子家,便有心接管养老的事。但老太太来了他家,和媳妇从第一天吵到最后一天,美艳的妻子当真以死相逼,喝下了敌敌畏,送进医院去洗胃。世魁气不打一处来,两个女人都是烈性子。媳妇从医院回来后,世魁便失去了话语权,只是忍气吞声。
老太太在老二家逼得媳妇要死要活,脸上有得意,心里却酸楚,知道老二碍着媳妇的面子,不能收容自己了。她要强到了极点,索性顺路去了老大家。
世元听说老太太要来,并没拒绝。但谁也没想到,他还记着多年前的恩仇,这次铁了心要刁蛮的老娘好看,便使出阳奉阴违的招数来。他和媳妇以“年纪大不能多吃”为由,不给老太太饭吃,饿了她一个月,吊着瓶子勉强支撑,为了省心,为了不听倔老太的呻吟,他每天给她吃一粒安眠药。人人都说老太太的脾气比石头都硬,硬是要去,又硬是不走。世元掐准日子,叫来老弟,说,轮一圈了,该还给你了,老娘活不了几天啦。老幺心想,这不是坑我吗,送回来就死,让七个兄弟怪罪我?但老幺从小在老太太身边,心一软,把她接回了家,一口一口喂米粥,粥里有煮烂的白菜,老太太喝了两天,没有拉屎;喝了一周,能坐起来了,就不肯撂筷子,老幺问,还要吗?她说,你能再给点吗?老幺鼻头一酸,说,别再溜达了。就这样过了二十一天,老太太才拉出两个带血的羊粪蛋,老幺的大儿子拽来铁锹砸了几下,扯着嗓子对他妈喊:屎球砸不烂!
老太太溜达了七年,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她本可以一声令下,要去哪家就哪家,但她就是不说。她说不出来。她想听到哪个孩子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把她领回家。溜达了七年后,老太太显出了老态,有时兴起,挎上了包袱皮,走到村口又回来了,嘴里骂骂咧咧,
故乡老家,就这样成了议事厅,要议论的只有一件事:老太太何去何从。
七兄弟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每一次聚齐都不容易。因为世全最远,每一次都要提前约定他的行程日期,别人才能附和。会议召集者,通常都是世祺,当了几十年领导,说话掷地有声,兄弟们一般都会服气。
世全接到世祺的电话时,偶有推脱,就会被批评。世全说,农村像个无底洞啊。世祺就会骂他学会了城里人那一套,太冷漠。真正开会时,世全见到大哥世元就假装没看到,兄弟俩的心结还是没有解开,一个邀功,一个记仇。老幺看到大哥世元也假装没看到,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小时候的皮肉辛苦,知道大哥这辈子没干过重活,没挑过水,也知道这位大哥怎样对待溜达过去的亲娘。只有老五老六不明就里,喜欢巴结有钱有势的兄弟。于是,每次开会都是无疾而终,一半人看热闹,个别人挺身而出,还有个别人挑拨离间。
最后一次开会,特邀老太太本人列席。老太太躺在炕头,一声不吭,听七个兄弟吵吵了一晚上。那天,兄弟们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由老幺在老家帮老娘养老送终,兄弟们同意每年送五百块钱。好不容易有了定论,世元却一撇嘴,说,爱捡臭鱼赚钱多,老幺冲上去揍他,老五老六忙拉架,老四摇着头、跺着脚急匆匆离开,说是着急赶火车回上海。
就这样,王家奶奶最后的岁月留在了老家,没有再折腾谁,给吃就吃,从不挑剔,吃完到门口溜达一圈,骂骂咧咧走回来,“一个不要,三个不要,三个不要,都不要。”老太太心里的酸楚、伤心、痛恨、梦想轮番涌上,从未平和下来,但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自己只能在最穷困的儿子家终老此生,再抱怨老幺的穷酸、笨拙也没用,再向往优渥生活的大庆、上海和沈阳也没用。
世全和别的兄弟第一次接到老娘病危的电报时,正要出差去重庆开一个大型会议,赶紧交接了工作,回了老家,但老太太撑下来了,一个星期后,非但没有咽气,又能起身坐稳,把这群儿女一个一个怨毒地瞅。
接到第二次病危电报的时候,世元家的三个孩子各给了两百块,说是给奶奶买好吃的。那一次,世全有点犹豫,但老太太真的咽气了,他又后悔没赶紧买票。到了老家,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但气氛很怪异,他只听到世元说:既然人死了,那就要退还六百块钱,然后,眼见有谁把几张钱撇出来,纸笔依直线散开,年过六旬的世元立刻奔上去,一张一张都捡起来了。
老幺在灶间压低了喉咙吼:伺候老太太这些年,统共只收到过一万三千块钱,只有老二、老三、老四和姐姐汇过钱,汇票都保存着,别人都是一毛不拔。
世全不知道他们刚刚在说哪件事,但又很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年复一年,兄弟们见面不为情义,不如不见。见了也没用。幸好,老娘死后,不用再见了。
他真的再也不想回到这样的老家了。
前言/序言
烟火债·很少的事·枯荣之心(序)
张怡微
许多年来,于是的主要职业更像是一个文学翻译。尽管她曾以畅销小说名世,主打都市言情。在文学与网络相遇伊始,许多人都读过她的作品。
于是从事过许多工作,写过很长时间的专栏、评论。与都会生活中许多独立女性一样,她拥抱自我、热爱旅行。但历经时光砥砺,终于又回到小说写作中,契机却源于父亲的一场病。
在父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于是的生活惯性被打破了。和父亲单独相处的时光,孕育了《查无此人》这部小说,而直至这本书真正完稿、出版,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疾病突然创造了负担与责任,但换一种方式来想,也许是父亲又将于是拉回到更纯粹的文学世界中。《查无此人》令她仔细爬梳了父亲的来历,其实也就是自己的来历;找寻到遥望祖辈的乡愁,其实正是检阅现世的哀愁。也令她从一个都会女性,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女儿。
“我不再是我。”
她借由小说人物“子清”在故事中自陈。
“她甚至怀疑,命运要她把前十年欠下的烟火债一次性还清。”
《查无此人》被分割成不同时空。一是父亲的身世,出身于东北,一个乱世商人家族;另一个则是女儿子清的内心生活。身世越来越完整,离别就越来越切近。从子清的独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女生举重若轻地介绍着自己的前半生:“我有一个安分的童年,姐姐远嫁加拿大,大学时母亲亡故,两年后父亲再娶,毕业后我独自生活,没有固定单位。父亲和母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再也没有离开,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到退休,无波无澜。续弦后他和女方一家住在一起,每年我大概会过去看几次。父亲三年前中风跌倒,同时被宣判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大约一年前就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就这样。”
显然,“就这样”不足以生成一部创作的根基。所谓“烟火债”,更像是子清对于复杂的身世、离散的阴影及捡回一个没有记忆的父亲时的无奈、惶恐、不习惯的浅浅应答。子清的善良、乐观包裹着敏感脆弱的内心,残酷的命运横陈眼前,在审美和批判之间,她选择了吞下难以细表的苦衷,一头栽入对新的日常生活巨细靡遗的描述和接受,以期缓解内心的种种丧气与哀凉。
女作家书写“父女关系”是一个经典的母题。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茱帕·拉希里的《不适之地》、又或者李翊云的《千年祈愿》……父亲象征着权威、尊严、品德,女儿对父亲的爱看似简单却又深厚,看似隔阂却又温柔。父女之间,既是男女,又是长幼。如戴锦华所说,在“父亲情结”之中,潜藏着的不仅是潜意识和欲望的诡计,而且是女性现实困境与生存困境。
在父亲丧失的记忆之后,子清反而夺下了父女生活的话语权。那个被继母还回来的父亲,在她的引导下一点一滴完成日常生活。这本身很反讽,全部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但温馨居然是真切的,悲伤也是。子清心里明明白白,她的付出不会有人真正懂得,也不会有人认真记得。父亲的疾病与离开,照耀她的孤独,这种孤独令他生前的出走、破坏都可以显得是打发时间的小事。对于子清而言,病魔险恶过任何一个陌生女人,与子清拉扯、搏斗。子清的孤独、骄傲,只能令她假装虚与委蛇,“她挽着他,像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小老婆,决不允许他离开自己半步,决不信赖外面的花花世界。她挽着他,也像一个耐心的早教老师循循善诱……只有她永远是父亲的女儿,这一点无可改变。”所有人都离开了父亲,但是子清不能。子清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走失了,却没有人去寻找他们”,但她做不到。那是一位女儿童年以后,一位父亲晚年以前,被生生挖去一大块的残破生命史。
小说开篇,子清说起父亲的一生,“和我们一样,做了很多事,但不一定很重要。”小说末尾,“她们每天都好像去很远的地方,但只做很少的事,很累地回家。”洋洋洒洒一辈子,可以说出来的事却显得那么苍白。父亲零碎的一生在原乡亲眷们口中,像碎片一样降落。只有子清知道,唯有内心的野兽是父亲交给她的血脉、遗产,谁也夺不走,因为他生养了她。
“查无此人”这个题目很严酷。闺阁之间,昭旷之原,都不再有父亲这个人。世界、世间都像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一样,将普通人的欢喜哀愁一并忘却。像于是自己说的,“一代人离去,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
有情的人,情何以堪。
后记
在这十多年里,我的父母相继去世。
在火葬场里为父亲捡骨时,我竟然为了火化时间那么短而感到悲愤,有点难以理喻。用一双很长的竹筷子夹起父亲的股骨时,过分的亲密感来得那么晚,那让我流下眼泪来。但真正的痛哭发生在我在精疲力尽的深夜给父亲的葬礼撰写悼词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些什么,不能面对自己和上一代人的巨大隔阂,也不愿承认自己疏忽了对父母的认知和关怀,因而像受了极大痛苦、或是犯了极大错误的孩子那样失声大哭。
在一个城市人的短暂、逼仄的生命里很难亲历一个物种的灭绝,但父母的消失就给了我这种感知:这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类、一个概念的消失。
在生和死之间,我们注定成为孤儿。这么简单的结论,竟花费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在这个年纪失去父母,看同龄朋友们激越地谈论工作、孩子和旅行,就像独自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虽然会和所有人在尽头相逢,但我相信,那时候别人的感受会和此刻未满中年的我有所不同。
未满中年的我,被父亲的病改变了很多。当我决定把这种改变本身诉诸文字时,也遭遇到了种种拷问。这本书最初的名字是《一岁一枯荣》,最初的设想是纪实地去写一种老年病威胁下的中年危机,非虚构。但在写作中途我放弃了,因为我不想无视疾病的隐喻,也不能回避平凡人家追溯家族故事时的无力感。
如果我信任记忆,这将是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小说。但很遗憾,我已经不相信记忆了。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家属都会理解这种心情,目睹记忆的实体被蚕食殆尽;甚至于,每个目睹过疾病和死亡的人类都能明白,肉身是多么脆弱。然而,当我们身处巨变的年代中,太多当下太迅速地被压缩成太不可信的个体记忆时,我们又会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呢?
因为遗忘是太容易了,除了肉身被动退化,还有精神上的主动遗忘。一代人离去,下一代人还没办法收拢那些记忆,又要汲汲营营地去创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加速运转,信息加速淘汰,记忆也被加速遗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可避免地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写作计划也因此搁置起来,直到父亲去世。正因为害怕自己会渐渐习惯遗忘,我又把尘封已久的十万字又拿了出来,重新写过。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写作者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唯一的救赎方式。不止是我,许多作者都曾在这样的时刻反省家庭和自我,用文字梳理哀伤。在写作的漫长空白里,保罗·奥斯特、井上靖、李炜、马丁·苏特、阎连科、萨曼莎·哈维、谢尔·埃斯普马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恰克·帕拉尼克……是各式各样的作品维持我的思绪,但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依然是艰难的,永远不可能完美。但,在看了那么多杰作之后,我也曾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写一本了。
就像很多野心勃勃的事,会在用力过度的过程中,忘记初衷。也有人劝我索性把《查无此人》的主题发挥到极致,让子清去探查父亲的过去,必须挖出一个惊天秘密出来,生造一出“文革”时代的生死大戏也未尝不可。我知道朋友们是为了让书大卖而好心创想,但我还是不想距离初衷太远了。不想夸饰一个平凡人在巨变的年代中的平凡生死。 事实上,这是一本难产的小说,距离我上一本书大约有九年之遥,它见证了我在家庭事件中的疲惫和笨拙,我白发的滋生,我对生活的接纳,以及我对大历史的好奇和不解。
每一个凡人,都是出生、入死。
每一个凡人在牢记历史之前,历史是否已将他遗忘?
在父亲去世后的某个时刻,我恍然大悟,这本来就不是朝向完美的写作。写作也不该是朝向完美的一种自以为是的声张。都不是。 于是,这本书慢慢地远离非虚构,慢慢地在虚构中获得了自由。我的父亲确实罹患阿兹海默症,最终因肺部感染去世,本书的主线毫无疑问是取材于真实事件,但在这本书成形之后,所有人物都已远离了现实中更狭隘、或更决绝的形象,他们只有源头,无所谓原型。
谢谢所有关心过我的朋友。谢谢《小说界》在2014年3月刊发了《六小时》,也就是本书中寻找第二次走失的父亲的片段。
谢谢所有从第一页看到这里的读者。
谢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给予的经济资助和精神鼓励。
于是
2014年12月7日上海
用户评价
从文学技法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展现了极高的成熟度。特别是其声音的运用,作者似乎能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景调配出完全不同的“语调”。有时候是清晰、精确、近乎新闻报道式的客观陈述,让人感到一种冰冷的疏离感;而另一些时刻,文字又变得极为口语化,充满了地方色彩和鲜活的生命力,仿佛就是邻桌老友的窃窃私语。这种在文体间游刃有余的切换,不仅避免了全书风格单一的枯燥,更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和真实感。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看似熟悉,实则处处暗藏玄机的世界,让人在放松警惕时,突然被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或一句精辟的洞察所震撼。这本书无疑属于那种需要被反复阅读和研究的作品,每一次重读,都会发现新的纹理和隐藏的结构,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故事,更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全新框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探险,而非单纯的故事消费。它的信息密度高得惊人,初读时可能会感到有些吃力,因为作者似乎在刻意设置一些门槛,要求读者不能带着敷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段落。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频繁地使用书签,标记那些充满隐喻或暗示的句子,以防在后续的阅读中遗漏关键线索。它探讨的哲学命题宏大而晦涩,关于“真实”的定义、身份的流动性,以及时间在记忆中扭曲的特性,都引发了我对自身处境的深层反思。这种需要“动脑子”的阅读体验,对于长期被过度简化的文本轰炸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一股清流。这本书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观察点和视角,让读者自己去拼凑出理解世界的碎片。它不是一本用来消磨时间的读物,而更像是一份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邀请函,邀请你进入一个深邃而复杂的心灵剧场。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留白”艺术。作者似乎深谙“不把话说满”的东方美学精髓,大量的叙事空间被留给了想象力——读者的想象力。他描绘的场景往往是勾勒出轮廓,而不是填充细节,这反而让读者得以将自己最深刻的恐惧或最美好的憧憬投射其中,使得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一次独一无二的、高度个性化的体验。我读到一些场景时,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或许与作者原本设想的有所出入,但这正是阅读的奇妙之处,它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一种双向的共创。角色的选择往往令人扼腕叹息,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愚蠢的决定,而是因为他们的每一步都似乎是命运逻辑下无可逃避的必然,这种宿命感带来的悲剧张力,比突如其来的灾难要深刻得多。整本书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忧郁气质,但这种忧郁并非令人沮丧,反而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深刻的、带着敬意的凝视。
评分这本小说的情节铺陈得极为细腻,仿佛作者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织工,用无数细密的线索编织出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画卷。人物的塑造尤为出色,每一个角色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有着鲜明的动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无可指摘的真实感。尤其是主角的每一次犹豫、每一次挣扎,都让人感同身受,仿佛那不是书中的虚构,而是自己正在经历的真实困境。书中对于环境的描绘也极为考究,无论是闹市的喧嚣还是僻静角落的幽深,都通过精准的感官细节跃然纸上,读者很容易就被带入到那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叙事节奏的把控更是炉火纯青,时而舒缓如散文,让读者有时间品味其中的哲思;时而陡然加快,如同山洪爆发,将悬念和冲突推向顶点,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这种高低起伏的阅读体验,使得整本书读起来酣畅淋漓,绝非那种一目了然的流水账式叙事所能比拟。它探讨的主题也相当深刻,涉及了人性的边界、选择的代价以及记忆的不可靠性,引人深思,读完之后很久都无法从那种沉浸感中抽离出来,会忍不住反复咀嚼其中的意味。
评分我必须承认,初翻开这本书时,我对它的期待值其实并不高,总觉得这种注重氛围和情绪渲染的文学作品,多半会牺牲掉扎实的叙事骨架。然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它的结构设计极其巧妙,并非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像一个精妙的迷宫,充满了回溯、闪现和多重视角切换。每一次看似不经意的侧写,最终都会在后续章节中以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方式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这种“等待揭晓”的阅读乐趣,是很多现代快餐式小说所无法给予的。更难得的是,作者的语言风格变化多端,时而冷峻克制,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析人心;时而又变得温暖而富有诗意,将那些微小的日常瞬间镀上了一层永恒的光芒。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冲突时所展现出的克制,它没有诉诸于廉价的戏剧化冲突,而是将最大的张力隐藏在人物眼神的交汇和沉默的对话之中,需要读者以极大的专注力去捕捉那些弦外之音,这无疑是对读者智识的一种尊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复仇者联盟 [The Avengers: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9164/5af458bdNe48998f9.jpg)
![成长必读外国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伤心咖啡馆之歌(套装共2册,插图珍藏版) [The Moon and Sixpence;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9612/5b111df9N833861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