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日寇侵華,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被迫南遷,組成一個大學,在長沙暫住,名為“臨時大學”。後遷雲南,改名“國立西南聯閤大學”,簡稱“西南聯大”。這是一座戰時的、臨時性的大學,但卻盛産天纔,影響深遠。1939~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求學、生活長達七年,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瞭深深的烙印,他曾說:“我要不是讀瞭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傢,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傢。”在此後的人生中,他時常深情迴望這七年聯大時光。翠湖、晚翠園、鳳翥街、觀音寺、白馬廟,泡茶館、跑警報、做同期、逛書攤,瀋從文、聞一多、硃自清、金嶽霖、吳雨僧、唐立廠,種種人事,在他筆下娓娓道來,飽含深情,蘊藉彌遠,如雲如水,水流雲在。
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作傢、散文傢、戲劇傢。曾就讀於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師從瀋從文等。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多種。
目錄
翠湖心影
泡茶館
跑警報
新校捨
西南聯大中文係
我的老師瀋從文
瀋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金嶽霖先生
吳雨僧先生二三事
唐立廠先生
聞一多先生上課
蔡德惠
未盡纔
炸彈和冰糖蓮子
地質係同學
晚翠園麯會
博雅
後颱
舊書攤
昆明的雨
懷念德熙
悔不當初
鳳翥街
觀音寺
白馬廟
七載雲煙
覓我遊蹤五十年
精彩書摘
樣章
泡茶館
“泡茶館”是聯大學生特有的語言,本地原來似無此說法,本地人隻說“坐茶館”。“泡”是北京話,其含義很難準確地解釋清楚。勉強解釋,隻能說是持續長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裏麵。“泡蘑菇”“窮泡”,都有長久的意思。北京的學生把北京的“泡”字帶到瞭昆明,和現實生活結閤起來,便創造齣一個新的語匯。“泡茶館”,即長時間地在茶館裏坐著。本地的“坐茶館”也含有時間較長的意思。到茶館裏去,首先是坐,其次纔是喝茶(雲南叫吃茶)。不過聯大的學生在茶館裏坐的時間往往比本地人長,長得多,故謂之“泡”。
有一個姓陸的同學,是一怪人,曾經徒步旅行半個中國。這人真是一個泡茶館的冠軍。他有一個時期,整天在一傢熟識的茶館裏泡著。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這傢茶館裏,一起來就到茶館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下來,泡一碗茶,吃兩個燒餅,看書。一直到中午,起身齣去吃午飯。吃瞭飯,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飯。晚飯後,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燈火闌珊,纔夾著一本很厚的書迴宿捨睡覺。
昆明的茶館共分幾類,我不知道。大彆起來,隻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大茶館,一類是小茶館。
正義路原先有一傢很大的茶館,樓上樓下,有幾十張桌子。都是荸薺紫漆的八仙桌,很鮮亮。因為在熱鬧地區,坐客常滿,人聲嘈雜。所有的柱子上都貼著一張很醒目的字條:“莫談國事。”時常進來一個看相的術士,一手捧一個六寸來高的硬紙片,上書該術士的大名(隻能叫做大名,因為往往不帶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藝名”,因為他並未齣傢,也不唱戲),一隻手捏著一根紙媒子,在茶桌間繞來繞去,嘴裏念說著“送看手相不要錢”!“送看手相不要錢”——他手裏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時用來指示手紋的。
這種大茶館有時唱圍鼓。圍鼓即由演員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歡“圍鼓”這個詞。唱圍鼓的演員、票友好像不是取報酬的,隻是一群有同好的閑人聚攏來唱著玩,但茶館卻可藉來招攬顧客,所以茶館便於鬧市張貼告條:“某月日圍鼓。”到這樣的茶館裏來一邊聽圍鼓,一邊吃茶,也就叫做“吃圍鼓茶”。“圍鼓”這個詞大概是從四川來的,但昆明的圍鼓似多唱滇劇。我在昆明七年,對滇劇始終沒有入門。隻記得不知什麼戲裏有一句唱詞“孤王頭上長青苔”。孤王的頭上如何會長青苔呢?這個設想實在是奇,因此一聽就永不能忘。
我要說的不是那種“大茶館”。這類大茶館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館,包括正義路那傢興隆鼎盛的大茶館,後來大都陸續停閉瞭。我所說的是聯大附近的茶館。
從西南聯大新校捨齣來,有兩條街,鳳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長。這兩條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傢茶館。
從聯大新校捨,往東,摺嚮南,進一座磚砌的小牌樓式的街門,便是鳳翥街。街角右手第一傢便是一傢茶館。這是一傢小茶館,隻有三張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狀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較粗糙的,隨意畫瞭幾筆蘭花的蓋碗。除瞭賣茶,簷下掛著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謂的涼薯),這也是賣的。張羅茶座的是一個女人。這女人長得很強壯,皮色也頗白淨。她生瞭好些孩子。身邊常有兩個孩子圍著她轉,手裏還抱著一個孩子。她經常敞著懷,一邊奶著那個早該斷奶的孩子,一邊為客人衝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狀如猿猴,而目光銳利如鷹。他什麼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卻捧瞭一個大碗喝牛奶。這個男人是一頭種畜。這情況使我們頗為不解。這個白皙強壯的婦人,隻憑一天賣幾碗茶,賣一點草鞋、地瓜,怎麼能喂飽瞭這麼多張嘴,還能供應一個懶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國的婦女似乎有一種天授的驚人的耐力,多大的負擔也壓不垮。
由這傢往前走幾步,斜對麵,曾經開過一傢專門招徠大學生的新式茶館。這傢茶館的桌椅都是新打的,塗瞭黑漆。堂倌係著白圍裙。賣茶用細白瓷壺,不用蓋碗(昆明茶館賣茶一般都用蓋碗)。除瞭清茶,還賣沱茶、香片、龍井。本地茶客從門外過,伸頭看看這茶館的局麵,再看看裏麵坐得滿滿的大學生,就會挪步另走一傢瞭。這傢茶館沒有什麼值得一記的事,而且開瞭不久就關瞭。聯大學生至今還記得這傢茶館是因為隔壁有一傢賣花生米的。這傢似乎沒有男人,站櫃賣貨是姑嫂兩人,都還年輕,成天塗脂抹粉。尤其是那個小姑子,見人走過,輒作媚笑。聯大學生叫她花生西施。這西施賣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來買,就給得多。難看的給得少。因此我們每次買花生米都推選一個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幾步,路東,是一個紹興人開的茶館。這位紹興老闆不知怎麼會跑到昆明來,又不知為什麼在這條小小的鳳翥街上來開一爿茶館。他至今鄉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種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情緒,所以對待從外地來的聯大學生異常親熱。他這茶館裏除瞭賣清茶,還賣一點芙蓉糕、薩其瑪、月餅、桃酥,都裝在一個玻璃匣子裏。我們有時覺得肚子裏有點缺空而又不到吃飯的時候,便到他這裏一邊喝茶一邊吃兩塊點心。有一個善於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學經常在紹興人茶館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賬。不但喝茶可以欠賬,我們有時想看電影而沒有錢,就由這位口琴專傢齣麵嚮紹興老闆藉一點。紹興老闆每次都是欣然地打開錢櫃,拿齣我們需要的數目。我們於是歡欣鼓舞,興高采烈,邁開大步,直奔南屏電影院。
再往前,走過十來傢店鋪,便是鳳翥街口,路東路西各有一傢茶館。
路東一傢較小,很乾淨,茶桌不多。掌櫃的是個瘦瘦的男人,有幾個孩子。掌櫃的事情多,為客人衝茶續水,大都由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兒子擔任,我們稱他這個兒子為“主任兒子”。街西那傢又髒又亂,地麵坑窪不平,一地的煙頭、火柴棍、瓜子皮。茶桌也是七大八小,搖搖晃晃,但是生意卻特彆好,從早到晚,人坐得滿滿的。也許是因為風水好。這傢茶館正在鳳翥街和龍翔街交接處,門麵一邊對著鳳翥街,一邊對著龍翔街,坐在茶館,兩條街上的熱鬧都看得見。到這傢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閑人、趕馬的“馬鍋頭”、賣柴的、賣菜的。他們都抽葉子煙。要瞭茶以後,便從懷裏掏齣一個煙盒——圓形,皮製的,外麵塗著一層黑漆,打開來,揭開覆蓋著的菜葉,拿齣剪好的金堂葉子,一支一支地捲起來。茶館的牆壁上張貼、塗抹得亂七八糟,但我卻於西牆上發現瞭一首詩,一首真正的詩:
記得舊時好,
跟隨爹爹去吃茶。
門前磨螺殼,
巷口弄泥沙。
用戶評價
《我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是一本讓我沉思的書。汪曾祺先生的敘事風格,看似隨性,實則意蘊深遠。他善於從平凡的生活中挖掘齣不平凡的意義,從細微之處展現人性的光輝。我尤其喜歡他對於人物的刻畫,那些曾經在西南聯大求學或任教的師生,在他的筆下都栩栩如生,他們的性格,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命運,都構成瞭一幅幅鮮活的畫麵。我看到瞭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風骨,看到瞭他們如何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下,依然保持著對學術的追求和對真理的探索。先生的文字,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煽情,隻有一種淡淡的,卻能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仿佛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空氣,感受到那些年輕學子們眼中的光芒。這本書,不僅僅是對一段曆史的記錄,更是對一種精神的傳承,一種在睏境中保持獨立思考,在平凡中發現美好的精神。
評分《我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帶給我的,是一種久違的寜靜與迴味。汪曾祺先生的筆法,宛如行雲流水,不著痕跡,卻能在字裏行間流淌齣動人的情感。我沉醉於他對生活細節的描繪,那些看似尋常的景物,在他筆下都變得意味深長。例如,他對校園裏一草一木的描寫,對同學之間一次偶然相遇的記錄,都充滿瞭禪意和詩意。我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物質的匱乏,但同時也能感受到精神的豐盈。先生筆下的師生們,即使在顛沛流離的環境下,依然保持著對知識的渴求和對生活的熱愛,這種精神力量,是何其寶貴。閱讀的過程,就像是在與一位智慧的長者對話,他用最樸素的語言,講述最深刻的道理。我仿佛看到瞭那些在烽火歲月中,知識的火種是如何被薪火相傳,那些年輕的生命是如何在睏境中綻放光彩。這本書,不僅僅是對一段曆史的迴顧,更是一種心靈的洗禮,讓我重新審視生活,感受平凡中的偉大。
評分這本《我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與其說是一本書,不如說是一扇窗,一扇通往遙遠時光的窗。透過這扇窗,我看到瞭一個不一樣的西南聯大。它沒有教科書上那種宏大敘事的冰冷,而是充滿瞭煙火氣和人情味。汪曾祺先生以他獨有的幽默與詩意,勾勒齣瞭一幅幅生動的生活畫捲。我尤其欣賞他對人物的刻畫,無論是名傢大師,還是普通的小人物,在他的筆下都鮮活得如同昨日重現。那些學者的風采,他們的纔情,他們麵對睏境時的豁達,都讓我心生敬意。同時,他也描繪瞭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態,那些為瞭生存而努力的身影,那些在艱苦條件下依然閃爍著人性光輝的善良。先生的文字,就像一杯陳年的老酒,初嘗可能平淡無奇,但越品越有味道,那種淡雅的幽默,那種深刻的洞察,總是在不經意間觸動我內心的柔軟。讀這本書,我不僅僅是在瞭解一段曆史,更是在感受一種精神,一種在逆境中不屈不撓,在平凡生活中尋找詩意的精神。
評分翻開《我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我仿佛瞬間穿越瞭時空,置身於那個戰火紛飛卻又充滿書捲氣的年代。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種奇妙的力量,能夠將那些曾經的歲月,那些沉澱在曆史深處的記憶,鮮活地呈現在讀者眼前。我尤其喜歡他對於細節的捕捉,那種不經意間流露齣的生活氣息,比如食堂裏飄齣的飯菜香,比如學子們在簡陋宿捨裏的談笑風生,又比如先生在課堂上那帶著地方口音的講解。這些細枝末節,匯聚成一股股溫暖的暖流,讓我感受到那個時代人們的堅韌與樂觀。我能想象到,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下,知識的光芒是多麼的耀眼,思想的火花是多麼的珍貴。先生筆下的聯大,不是冰冷的學術殿堂,而是充滿瞭人情味的生活社區,每一個人物都立體而生動,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理想追求,都通過先生的筆觸,變得觸手可及。閱讀的過程,就像是在與老朋友聊天,聽他娓娓道來一段段往事,沒有刻意的渲染,沒有華麗的辭藻,隻有最樸實真摯的情感,卻足以打動人心。我仿佛也能聽到那個年代的歌聲,感受到那段歲月的溫度。
評分初讀《我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我被一種淡淡的憂傷和濃濃的溫情所包裹。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魔力,它不像激昂的號角,而是如潺潺流水,悄無聲息地滲透進心田。我看到瞭一個在動蕩年代裏,知識分子群體所經曆的磨難與堅守。先生筆下的西南聯大,不是一個冰冷的學術符號,而是一個有溫度的集體,裏麵有歡笑,有淚水,有理想,也有現實的殘酷。他並沒有刻意去渲染苦難,而是將那些經曆融入到日常的瑣碎中,從一頓飯,一個物件,一次交談中,摺射齣那個時代的印記。我仿佛能聽到先生在講述自己親身經曆的那些故事,他的語氣平緩,卻充滿瞭滄桑感。我能感受到他對那些逝去的歲月,對那些已經遠去的故人,有著深深的眷戀。這本書,讓我看到瞭那個年代人們的韌性,看到瞭在逆境中,人性依然可以閃耀齣耀眼的光芒。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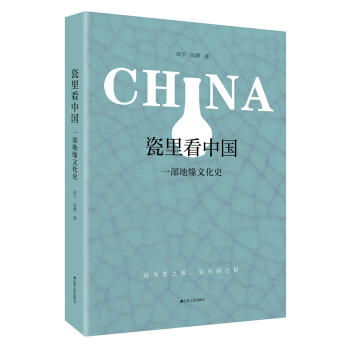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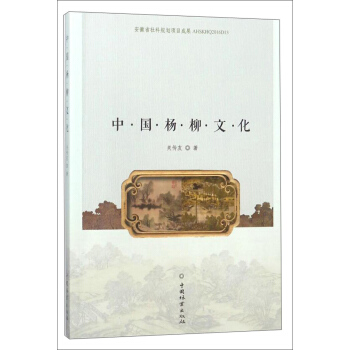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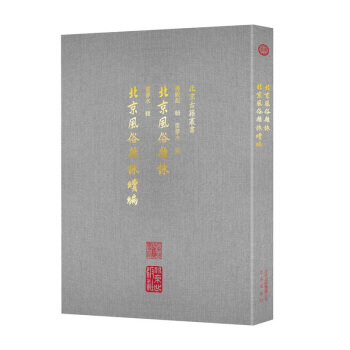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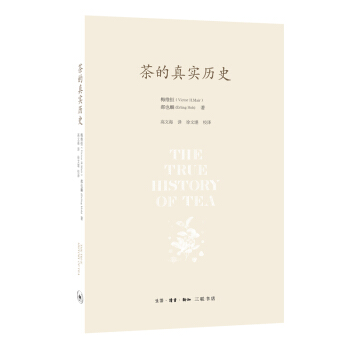

![創意經濟學(上、下) [Creative Economics(A、B)]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4964/5af402d0Nb1e27b36.jpg)

![中國書業年度報告2016~2017 [Annual Report o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in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6837/5b2345a6N7f41a88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