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五十年的共同记忆、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借勾勒若干精彩的生活断片,呈现特定环境中的个体记忆与历史想象。内容简介
《筒子楼的故事》汇集了北大中文系二十余位教师及家属回忆在北大筒子楼工作生活经历的文章。筒子楼是20世纪在中国高校中相当普遍的教工宿舍,营造出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其居住条件构成了书中诸多学者感悟人生的重要对象,成为他们塑造文化风格的影响因素。书中几代学人记述了艰苦的求学治学经历,感人的师友交往,苦中取乐生活场景,读来令人叹息,又富有趣味,留下了对特殊时期的生动叙述。此次修订,除请各位作者修改各自的文章外,主编还特地写了《筒子楼的故事再版后记》。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著作三十余种。目录
目?录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代序)......陈平原/003
形形色色“筒子楼”......陆颖华/001
怀念50年代住在未名湖畔的朋友......唐作藩/021
燕园忆旧(1950—1954)......王理嘉/027
孩子们在燕园成长......陈松岑/044
燕园长屋与迷糊协会......段宝林/064
世事沧桑话住房......周先慎/083
湖畔的雪泥鸿爪......谢冕/099
半间“小屋”旧事琐忆......孙玉石/106
我与筒子楼......马振方/120
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严绍璗/124
往事杂议......赵祖谟/147
筒子楼的回忆......张晓/159
家住未名湖......么书仪/164
19楼的回忆......商金林/179
我的那间小屋......钱理群/192
?
北大“三窟”......温儒敏/196
燕园筒子楼琐忆——从19楼到全斋......葛晓音/204
我们家的八年筒子楼生活......岑献青/213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陈平原/228
44楼杂记......陈保亚/236
我在燕园住过的那些地儿......杜晓勤/243
筒子楼杂忆......漆永祥/259
末代筒子楼......孔庆东/266
附:北京大学校园简图....../272
《筒子楼的故事》再版后记......陈平原/274
精彩书摘
我的那间小屋钱理群
那天,听说我可能(仅仅是可能!)要搬到别人住过的“新”居里去,一位学生突然对这间斗室留恋起来,对我说:“老师要是永远有这间小屋,该多好!……”
我对他笑了笑。我理解他的心情。这间屋对他来说,意味着,可以随时闯门而入,在书堆里乱翻,然后坐下来高谈阔论,即使“神聊”到半夜两三点钟,也不会有人干涉……
但,这间屋,对于我,又意味着什么呢?
学生没有问,他也想不到问这样的问题。
唉,该怎么对你说呢,该怎样让你理解这一切呢,我的年轻的朋友?
……也是这样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也是这般说话没有顾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挥舞着拳头,我傲然宣布:“我同意费孝通教授的意见,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无非是‘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一位大学教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个大学生的共鸣:这事情普通而又普通。但那是30年前……
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被批判会严厉的呵责声弄得昏头昏脑,我坐在临湖轩旁边的小山上,呆望着未名湖。……湖水荡开,隐约显出一间“小屋”——哦,我梦中的“小屋”,一个永远的“诱惑”!我突然站起来,狂奔着,把未名湖远远地抛在后面,仿佛“小屋”的梦也深埋在湖底里了……
然而,“白专道路”的“罪名”却如影一般永远跟随我了,并且以其无情的魔力把我从北京驱赶到贵州一个边远的山城。居然在那里安顿下来,一晃就是十多年,日子也还过得悠闲,不像眼下年轻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如果不是那一天……也许我就这样平平稳稳,心满意足地生活下去——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仿佛也是一个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在灯下读鲁迅的书,随手写一点笔记以自娱。写得有些累,停下笔来,习惯地打量四周。心怦然一动,突然想起了遥远的燕园里的“小屋”,那心中的“梦”!要是能回去,在北大讲坛上向青年学生讲讲“我的鲁迅”,那该多好呵。我被自己的“奇思异想”弄得兴奋起来,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
从此,“小屋”的梦日夜缠绕我的灵魂,我再也不得安宁——不知这对我是幸还是不幸?
1978年的夏天,我又回到了未名湖畔。距离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已经整整20年。两鬓斑白的我又拾起了那“小屋”的梦。渐渐地,我有了半间小屋,也还算窗明几净,我露出一丝苦笑,但不久就被通知:搬到一间谁也不要的,由浴室改装的阴冷的小屋,以与我们在北大的身份相适应。我愕然了。一群人去找一位领导申诉,不久就传出流言,说我们像当年红卫兵一样“冲击”领导。我们这些除了申诉就别无能耐的“老童生”,在一些人眼里,竟然是一伙暴徒。我没有愤怒,却只想哭——为人与人之间可怕的“隔膜”。而且我们还得继续申述。
这一次回答却简单而明确:北大条件就是如此,要留,就得“忍”,不想留,悉听尊便。我们面面相觑,倒抽一口冷气:这群人的致命“弱点”,就是热爱、留恋北大。呵,我的该死的“小屋”的梦……
又开始了漫漫无尽的“等待”。我的同屋“熬”不住,远走高飞了,我还“等”着。终于,那一天,爱人从远方调来,总该有自己的“家”了!不,你们没有小孩,不能参加分房。天哪!我不正是为了这“小屋”的梦,而放弃了做父亲的权利,难道今天我还要为这惨痛的牺牲继续付出代价吗?是的,谁叫你傻乎乎地做什么“牺牲”,那就继续“牺牲”吧。……面对这谁也不曾公开宣布,却在生活中实际起着作用的“铁”的“逻辑”,我唯有沉默。“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失去了的时间却不会再有。我已经人过中年,不容再“熬”与“等”。我必须再一次埋葬那“小屋”的梦,在递上调离北大申请书的那天晚上,我已无兴趣注意天上有没有星星,也没有力气再走到未名湖畔,只是麻木地在黑暗中躺着。“小屋”的影子也不曾闪现,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连梦也从未做过。
以后的“事”是简单的:由于某种“外援”(那又是一个长长的辛酸的故事,不说它了!),我没有走,“家”安顿下来,我在北大有了一间小屋。仿佛韶梦初醒:再也不用无休止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申诉,请求;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粗暴的、冷漠的、同情的“脸色”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竟然有一种精神解放感。并且立即沉浸在书堆里。于是,一篇篇文章写出来,一群群学生拥进来,小屋挤得满满。那一天,我走上讲台,面对着几百双闪光的眼睛,讲我心中的鲁迅,课后,我被一群学生簇拥着,回到这间小屋,突然觉得说不出的疲倦……
但我终于沉醉而且自得。于是,又有了一个夜晚,莫名的不安悄悄袭来。耳边固执地响着一个声音——电视里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名人的讲话:“我们知识分子只要求能够工作,并不计较物质待遇。”是的,人们早就说过,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誉满全球”……
但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耻辱?!还有什么比将耻辱当做光荣四处炫耀、兜售更令人难以容忍的呢?!——我差点叫了出来。
几十年笼罩在“小屋的梦”上的诗意与崇高,陡然消失,直露出“安贫乐道”的卑琐与平庸。
……
我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做“梦”。
但离开了“小屋的梦”,我将何以立足?我茫然、默然。
迁居的名单里出现了我的名字。
但我不再兴奋。也没有丝毫感激之情。
“是的,我可能搬家。这间小屋再也不会有了。”我对学生说。
我为自己语气的平静感到吃惊,同时又欣慰于这平静。
1988年1月21日
筒子楼杂忆
漆永祥
“筒子楼”这个词,大概将要慢慢变成历史名词。筒子楼带给我的感受,就是喜乐忧愁,各占其半。于今思之,则忧愁已然消散无踪,而喜乐却日兹而弥漫,历久而长新。
一?何谓筒子楼
何谓筒子楼?筒子楼者,双面单间、门户相对、过道如筒子的大小板楼之谓也。我甚至认为,单面楼都不算,一定要双面楼才算是标准的筒子楼,也才具有以下所言各种“筒子”的表征与功能。
窃以为筒子楼有五大特色:一是昏花灰暗。我的印象中,极少看到有堂皇明亮的筒子楼,总是脏污断阶的楼梯,昏暗甚至漆黑的楼道,即使偶尔亮几盏顶灯,也是淡如昏雾,几近于无光。
二是杂物叠置。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以及诸多家当,都是摆在楼道里,灯光昏暗,触物莫辨,行在中间,如机关暗藏,处处险情,然最可称奇的就是这里的饮食男女们,却可以自如灵活地穿梭其间,视如无物。
三是百味杂陈。楼道里充斥着油烟、煤气、香水、茅厕以及各种说不清楚的杂味儿。如果是在午间或晚饭时,则家家门口,炉火高蹿,刀跺锥砸,烹煮煎炒,锅铲翻飞,这时便千香万辣,竖飘横移,沁心呛鼻。
四是充满温情。这里的邻居们,因为有一半生活区域在楼道,所以大家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新老住户很快就会熟识,尤其是在做饭的时候,或者大嗓门,或者轻曼语,大家总是聊得热火。遇上谁家孩子感冒,谁家老人来了,或者出个事儿故儿的,大家还可以互相关照,互通有无。
五是毛贼公行。凡住过筒子楼的,几乎没有哪家没有丢过东西的,从家电、煤气罐、衣服、米袋、锅碗等,小到一块香皂甚至一块破抹布,都为可偷的奇货。毛毛贼似乎具有电子眼的功能,因为他能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你刚买了块新香皂,中午刚打开包装纸,尚未用过就不翼而飞了。有时候一家忍不住,骂几句粗口,周围便会起一片随喜声,同时通报各自丢的物什,比比损失大小,苦中作乐一番。
二?在西北师大:流浪借居筒子楼
我自己的筒子楼生活,比起长期蜗居数十年筒子楼的前辈来说,无甚可谈,但也还有些说叨的话题。
上高中的时候,我与房东舅爷垒了一间小土屋,大约不足五平米,就是当时个头才一米六又骨瘦如柴的我,也在里面很难打转身,但我仍在里面蜷缩了五年,虽然冬不遮风,夏不挡雨,但却养成了“独居”的习惯,最不喜与人“同居”。但上了大学,先是八个毛头小子住一间宿舍,后来是六个,再后来四个,留校任教时为两人一间。从发展的前景看,势头喜人,似乎马上就要一个人住一间屋了,但在那个时代,这却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因为只有结婚的同事,校方才能赐给一间屋子;我是钻石牌的,根本就没有资格。
当时筒子楼的住户朋友们,谁家的屋子空着,凡出国的、外地读书的、城里有房的屋主,都愿意找个熟人帮着看房子,以免遭胠箧之灾。那个年代的人,经济意识不强,房子空着的也不知道出租来赚钱,借房子的也不知道给人家房钱,我借住过的房子,甚至连一分钱的水电费也没有掏过,脸皮硬是比城墙还厚三分。
我在母校西北师大的时候,住过学校有名的南单楼、单三楼、旧校医院平房、学生区的旧家属区等筒子楼,但都是借居。后来学校修了一栋个别有小套间的单面楼,家家户户有个小厨房,分配给已婚的青年教师,当时被称为“鸳鸯楼”,热极一时,我在那栋楼里,也曾经栖身,当然还是借居。
当时古籍所的王锷师兄,因为在城里有房,所以他在南单楼的一间房,就成了朋友们的“眼中钉”。我借他房子住的时候,正是因踢球断了脚的“蒙难”时期,脚坏不能走路,就整天躺在床上发呆,刚好是“一缺三”,所以晚上常常有几个弟兄来打麻将。天冷脚疼,我就包着毯子打牌,好在赢多输少,还不至于把王兄的房子给输掉。王锷兄在那里生了儿子,后来凡是借他房子住过的夫妻,据说都生了儿子,因此他的房子就成了颇具神秘感的阳刚宝地。我在北京数年后,也生了儿子,还有朋友说这根基啦,就是在那间屋子栽的也。
世上最无聊的,莫过一个人住又一个人做饭吃了,我当时经常在路口堵和我一样的光棍们一起做饭吃。我手艺本就极差,有时做了请人家吃,还落得个太难吃的评价,极是扫兴。所以我也就不怎么做饭,硕士期间的同学离开兰州时,留下七八个不同类型的饭盒饭碗,于是我就一天用两个在学校食堂买饭吃,一周洗两次,最合我懒人的习性。
有次拎着饭盆到食堂门口,碰到本系的一位仁兄,他说家里正在炖排骨,请我去品尝,嫂夫人炖了一锅猪排,竟然被啃个精光,为了照顾好我这个饕餮,嫂子都没怎么吃。第二天上午,我仍打着饱嗝儿晃到系里,见我的人都大吃一惊,说昨晚那位仁兄和儿子食物中毒去了医院,一大早他夫人风火颠倒地来办公室说赶快找小漆,他吃得最多,是不是这人已经没了。那时没电话,大伙正着急找人的当口,我竟然天全浑然地出现了,大家像是遇到了鬼。从此我就落了个“铁肚”之名,说那小子是百毒不侵的。我在师大期间,在那些朋友家吃白食,不知多少次,此不过极端之一例而已,于今想来,仍感念不已。
我到北京上学后大概第二年,师大也在南单楼给了我一间屋子,但是因为我已经绝意要离开,所以好不容易到手的屋子,对我来说仍是借居的感觉。等我离开的时候,那座小楼也很快被推平,盖起了漂亮的家属楼。
三?舒心惬意的筒子楼生活:北大南门27楼
1996年秋,我经过一番艰苦而不卓绝的折腾,终于留在了北大。当时新教员一般都住在南门附近的那几幢旧筒子楼里。因为我是定向委培生改派留校的,所以要等教育部改派完毕,才能正式报到;当时没有工作证、身份证,粮户关系无处落脚,身份不明,被大家戏称为“三无”人员,校方总务处房管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万一给了房子人又进不来将来赖着不还,岂不麻烦,后来好说歹说交了押金,才暂时在27楼借我一间屋子,算是栖身有地了。我当时教香港来的短训班,有同学写作文说“进入南门,两边有一些快倒的破烂大屋”,我说我就是那些“破烂大屋”的住户,不知为何同学们不露惊异,反而是一片钦羡之色!
27楼的那间房子,伴随我在北大度过了一段最舒心惬意的光景。房间不足10平米,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电脑桌,便占据了所有空间,虽然简单却不失安宁。第二年,妻子也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到了北京工作,两个人都领薪了,便陡觉银子多得不行,就天天请人吃饭,楼道里总是我家在叮哩哐啷地做饭,假若哪天不请客,对门数学系的哥们儿就会奇怪地问:今天你家怎么没人来吃饭呢?
那时一起留校住前后几个楼的,有中文系的孔庆东、历史系的黄春高、哲学系的周学农、数学系的王福正等一彪人马。因为我们读博士期间住在四院,所以别人称我们为“和尚”,我们称自己为“院士”。“院士”们经常打扑克牌,“手扶拖拉机”开得热火朝天,这一伟大传统在工作后,也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先是在学农家中,他夫人每天笑盈盈地为我们端饭添茶,众人杀得天昏地暗。后来他们的宝贝女儿降生,据点就转到了我家,偶尔有外地进京的原四院“拖拉机手”,就开一个通宵以示隆重欢迎。那些可怜的家伙,输得糊里糊涂大清早红肿着眼睛就直接上车了,好在还没听说过往南边走的坐到哈尔滨去的。
因为我的屋子不能上户口,所以妻子的户口总是装在兜里,很是着急,从系里报告往上申请,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于是,我又开始一趟又一趟地跑房管处,希望换房。有次房管处领导问我有没有孩子,我说没有,领导黑着脸正色道:“没有孩子你急什么急?”孩子不是一天两天能有的,所以我很是垂头丧气。有次碰到中文系的杨荣祥老哥,也苦着脸在跑房子,他夫人孩子进京了,急需像样点儿的屋子。我赶快给他通风报信,说你要特别强调你的困难,你有孩子。他依计而行,结果没想到领导说:“这算什么困难,结了婚的,谁家没个孩子?”
四?热门非凡百鸣室:中关村25楼
过了两年多,我终于从校内搬到了中关村。说起来,这次得到两间屋子,纯属偶然。
有天晚上,我在楼道里做饭,看到有人敲楼道口春高兄的门,就随口问了一句:“您找春高有事吗?”找人的是位老太太,说她刚旅游回来,有两大包东西,想请春高帮忙给送到家里去,我说这点小忙我也可以帮,就帮老人将两件行李送到了承泽园家中。老人极其热情,请我喝茶聊天,其间聊到我的住房不能落户口。老人主动说她跟一位副校长很熟络,她出面请校长帮忙。
我依老人之计,又递了报告,没过几日,还真管事儿,主管校长批了,然后又七转八拐地经过几道衙门签注意见,最后到了房管那里,这样我终于搬到了中关村科学院25号楼。虽然仍是筒子楼,但由一间屋子,扩大到了两间,且有公用厨房,当时幸福感从心中往外溢流,有进了天堂般的美妙。因为一点小小的善举,因缘得到两间屋子,可见在人世间行点小善,还是有大大好处的!
我的房子朝南的一间,窗下正好是320路车站,那正是客运小公共车盛行的年代。每天早上从6点钟开始,到晚上12点前后,日复一日地重复“320—人大—白石桥—木樨地—西客站—走啦”的吼声,呼喝者有男有女,有高清嘹亮如小号者,有腔润浑厚似圆号者,有尖厉凄苦像板胡者,有嘶哑断续如沙锤者。没过多久,马路被剖,千军万马会战,开始修建四环路,大型挖掘机巨大的钻头震动,有摇滚乐中的重金属铿锵震颤心肝的效果,我的书架玻璃,也有节奏地配合发出吧吧嗒嗒的声音,犹如密集的鼓点。上下班时间,马路上车辆堵塞,各色喇叭,此起彼伏,刺耳竞鸣,像初学者在吹奏黑管。这些声音,响彻在我的房间里,再加上屋子里的电视声,孩子叫声,真如同是管弦乐团大合奏,所以我当时称自己的书屋为“百鸣室”者,即因此也。又因为线路老化,带不动空调,每到夏日,顶楼西晒,屋子里总是在40度以上,如同桑拿,我经常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读书写字。但那时气力之雄壮,精神之强健,堪比牦牛,我的好多拙劣文字,就是在“百鸣室”里拼凑出来的。
在中关村住了三年多,中间经历了2003年“非典”的考验,而且与邻居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架之后,在盛夏酷暑之日,我搬到了京郊西二旗的新家,终于有了像样的套房,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也正式结束了住筒子楼的历史。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从此有了好的住房条件,整齐的书架,宽大的书桌,舒适的坐椅,终于像过去电影里演的教授的书房了。可我似乎也失去了很多的乐趣,整日孤单寂寥地坐在生冰的案头,脑袋发木,两眼滞呆,笔墨干涩,思维枯竭,黄面对墙,形同楚囚。偶尔想到筒子楼昏暗的灯光,杂乱的过道,那些荡在鼻间口中的各色味道,以及渊睦弥漫的人情味儿,总有一种身在世外的感觉。住房改善,换得了宁静与安逸,但那些浓郁的生活味和温暖的人情味儿,却如浮云刍狗,消散无踪。有时想想,这得之与失,还真是难呐!
前言/序言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代序)
陈平原
这是一本饭桌上聊出来的“闲书”。
去年3月,北大出版社高秀芹博士来谈书稿,听我讲述当年借住女教师宿舍的尴尬,竟拍案叫绝,说类似的“筒子楼的故事”,许多北大教师讲过。那是一段即将被尘封的历史,高博士建议我略作清理,为自己、也为后人,编一本好玩的书。当时颇为犹豫,因为,此类“苦中作乐”,自己珍惜,旁人未见得能理解,更不要说欣赏了。
几天后,同事聚会时,我谈起此事,竟大获赞赏。于是,乘兴发了个短信,试探一下可能性。说清楚,这不是北大中文系的“集体项目”,纯属业余爱好,很不学术,但有趣。作为过来人,我们怀念那些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与校园记忆。再说,整天跑立项、查资料、写论文,挺累人的,放松放松,也不错。4月1日发信,说好若有二十位老师响应,我就开始操作;若应者寥寥,则作罢。一周时间,来信来电表示愿意加盟的,超过了二十位。这让我很是得意,开始底气十足
地推敲起出版合同来。
接下来的催稿活儿,可就不太好玩了。约稿信上称:“文体包括散文、随笔、日记、书信、诗歌、小说等,唯一不收的是学术论文;全书规模视参与人数多少而定;文章篇幅不限,可自由发挥。不求文字优美,但请不要恶意攻击昔日邻居,以免引起‘法律纠纷’。利用暑假写作,10月交稿,明年春天由北大出版社刊行。”说实话,大家都很忙,此计划可能推迟,从一开始我就有心理准备。平日里,不断转发同事文章,利用这一方式,温和地提醒:有此一事在等着你。到了暑假或寒假前,再稍为督促一下:“暑假将至,本该放松放松;苦热之中,竟然还邀人撰稿,真是罪过。好在此类‘豆棚闲话’,尽可随意挥洒。”“平日里,大家忙于传道授业解惑,放寒假了,想必可稍微放松,写点‘无关评鉴’的文字了。这些蕴含真性情的随意挥洒,十年二十年后,说不定比高头讲章更让你我怦然心动。”这都是真心话。此类闲文,老师们可写可不写;别想得太伟大,基本上是自娱自乐。
当初决意编此书,脑海里浮现的,一是郑洞天的电影《邻居》,一是金开诚先生的随笔《书斋的变迁》。1981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二年获第二届金鸡奖的《邻居》(郑洞天导演),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形态——筒子楼里,两两相对,排列着几十个狭小的房间;邻居们大都属于同一个单位,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过道里堆满杂物,只留下一人通过的空间;开饭时,满楼道飘散着东西南北各种风味……环境如此艰难,邻里间却温情脉脉。今日习以为常的“走后门”(房管科吴科长偷偷把一间小屋分给了省委董部长的侄子),当初竟义愤填膺。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氛围,大家对公平、正义等有很高的期待。也正因此,才有了电影里那“光明的尾巴”:市委决定停建高级住宅,着重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一半是自嘲,一半是期望,80年代的读书人,大都记得《列宁在十月》中的豪言壮语:“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起转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的金开诚(1932—2008)学长,在1988年2月1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书斋的变迁》。此短文流传甚广,后收入他的《燕园岁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有这么一段:“我虽然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但因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书斋。1978年爱人带了孩子调到北京,结束了18年的两地分居,这时才有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房中有两张书桌,一张给孩子用,以便她好好学习。半张给爱人备课写文章,另外半张亦归她,用来准备一日三餐。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文章。”据说,老友沈玉成来访,看到此情此景,戏称将来为金先生写传时,一定要带上这一笔。
如今,金、沈两位先生均已归道山,轮到我来编书,猛然间想起20年前读过的文章,翻检出来,摘抄一段,以展示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界。阅读此文,后人很可能感叹嘘唏。可金文的主旨不是抱怨,而是借十年间自己如何从没有书斋到有“床上书斋”到“桌面书斋”再到“小康书斋”,说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80年代的乐观主义情绪,还有那一代知识人的大局观,作为后来者,你不一定认同,但千万别轻易嘲笑。
出版社要求申报选题,我脱口而出:“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不用说,那是套用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如此“信口开河”,日后再三斟酌,觉得不妥。原因有三:一怕拾人牙慧,二担心限制老师们的思路,三不希望此书过于文学化。但有一点,我认定:就像台湾的“眷村”,大陆的“筒子楼”,既是一种建筑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时代倒影、文化品位、精神境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筒子楼,也都发生过无数动人心魄的故事。不夸耀,不隐瞒,不懊悔,只是如实道来,这样,琐琐碎碎的,反而动人。
关于此书的编辑工作,我有五点技术性说明:第一,学校不断调整布局,同一座19楼,一会儿住的是男教工,一会儿又变成了女教工宿舍,端看你何时入住。第二,文章有时29楼,有时29斋,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文革”前叫“斋”,“文革”中改为“楼”。第三,未名湖边的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斋”,乃原燕京大学建筑,不按数字排列。第四,为了叙事完整或文气贯通,集中文章,有的溢出了题目,兼及学生时代或搬进单元房后的,编者也不做裁撤。第五,文章排列顺序,不叙年齿,依据的是正式入住筒子楼的时间。
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趁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
对于昔日筒子楼的生活,说好说坏,都不得要领。你想很辩证地来个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也不是什么好主意。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我的想法是:先别褒贬,也不发太多的议论,“立此存照”,供后人评说。
本书的征稿工作,得到了北大中文系周燕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
2010年2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让我感到温暖和治愈的书。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那些微小的、却能带来幸福的瞬间。而《筒子楼的故事(修订本)》恰恰提醒了我这一点。它让我看到了,即使在有限的空间里,人们也可以构建出丰富的情感世界,维系着牢固的友谊和亲情。作者用一种诗意而又朴实的笔触,描绘了这些美好的画面,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满足。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故事,它更是关于爱,关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连接,是当下社会非常需要的一部作品。
评分这本书读起来,感觉像是坐在老朋友的旁边,听他娓娓道来那些陈年的往事。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舒缓,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浸润人心的力量。我喜欢他对于生活琐碎的捕捉,那些平凡的小事,在作者的笔下却有了别样的光彩。比如,一个邻居如何每天为生病的伴侣熬汤,另一个家庭如何省吃俭用也要给孩子攒钱读书,这些点点滴滴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坚韧和温情。我常常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联系起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那些相似的场景,那些共鸣的情感,都让我觉得这本书与我的内心产生了深刻的连接。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即使在物质条件不那么优越的年代,人们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意义,那种纯粹的情感,是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所稀缺的。
评分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它的名字就吸引了我:《筒子楼的故事(修订本)》。听起来就像是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又带着点儿时间的沉淀。我一直对那种老式居民楼里的故事很感兴趣,总觉得那里藏着最真实的人情味和生活百态。翻开书页,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仿佛能看到那些狭窄的过道里,邻居们互相搭把手,孩子们在楼道里追逐嬉闹的场景。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烦恼与希望,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尤其喜欢作者对细节的描绘,比如那斑驳的墙壁,老旧的家具,甚至是晾在窗外的衣服,都传递出一种浓浓的生活味道。读着读着,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个年代,感受着筒子楼里特有的温暖和人情。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个故事的堆砌,它更像是一幅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时代画卷,记录着一段即将远去的过去,也让我们反思当下。
评分坦白说,我一开始对这本书的期待并没有那么高,以为只是讲述一些怀旧的片段。但越读下去,越发现它有着超出预期的深度。作者在描绘筒子楼生活的同时,也触及了一些更宏大的社会变迁。那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书里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引导读者去思考。我特别欣赏作者的克制,他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去歌颂过去,而是用一种平和的态度,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读完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宽广的视角。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一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作者的文字有一种魔力,能够将读者瞬间带入那个特定的时空。我仿佛能闻到筒子楼里饭菜的香味,听到楼道里孩子们的嬉闹声,感受到夏日午后沉闷的空气。这种感官上的代入感,是很多书都难以达到的。而且,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也非常到位,每一个角色的动机,每一个眼神的含义,都被描绘得细致入微。我能够理解他们的选择,体会他们的无奈,甚至为他们感到欢喜。这本书不是那种读完就忘的书,它会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让你反复回味,甚至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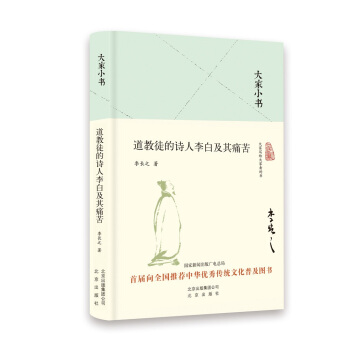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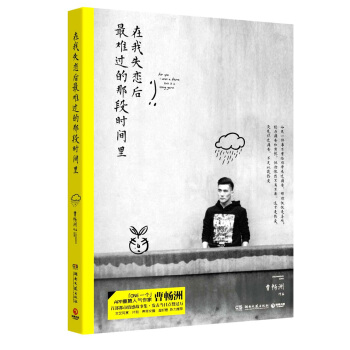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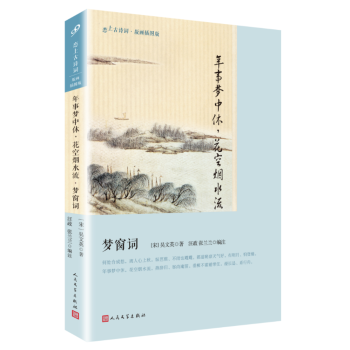
![远山的记忆:大凉山彝民生活纪实 [The Memory of the Distant Mountai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3671/5b0289bcN3446838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