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生活的秘密總在不經意間顯現,誰的人生不是一部偵探小說?
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艾麗絲·門羅帶著你一起解開謎題
內容簡介
《我年輕時的朋友》收錄瞭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艾麗絲·門羅在創作成熟期的十篇短篇小說佳作。門羅把日常生活的片段編織成精巧的故事和寓言,在這語言之光的照耀之下,平凡的人生翩翩起舞,無論是稍縱即逝的愛,還是長久默默的陪伴,無論是古井無波的生活,還是忽如其來的改變,都被呈現紙上,讀來令人迴腸蕩氣。
作者簡介
艾麗絲·門羅(1931——),加拿大女作傢,2013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一生專注於中短篇小說創作,講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彆是女性隱含悲劇的平常生活,以細膩透徹又波瀾不驚的話語,洞見人性的幽微處。
在獲得諾奬之前,門羅就被譽為“我們時代的契訶夫”;諾貝爾文學奬頒奬詞稱她為“當代短篇小說大師”。
精彩書評
門羅的故事裏麵幾乎有讀者想要看到的一切:逸聞趣事,閃光的日常細節,性的激情,傢庭故事,詭異的個性,新的風景,幽默,明智。——《費城調查者報》
常年以來門羅就被很多人認為是個作傢中的作傢,什麼叫作傢中的作傢,倒不是說她的寫作要勝過所有的作傢,而是說她的寫作的方法、她的成就讓很多內行人覺得佩服,覺得她的獲奬是實至名歸。 ——梁文道
目錄
我年輕時的朋友
五點
門斯特河
抓住我,彆讓我走
橘子和蘋果
冰的照片
善良與憐憫
哦,有什麼好處?
各不相同
假發時間
精彩書摘
我年輕時的朋友(節選)
我曾夢見我的母親,盡管夢裏的細節各不相同,帶來的驚喜卻如此一緻。不再做夢,我猜想是因為夢裏的希望過於明顯,寬恕過於輕易。
我在夢裏就是現在的年紀,過著現在的生活,而我的母親還活著。(事實上我二十歲齣頭的時候,她就死瞭,死的時候五十歲齣頭。)有時候我發現自己身處我們的舊廚房,母親在桌子上碾餡餅皮或者在那隻破舊的鑲紅邊的奶油色洗碗盤裏洗碟子。其他時候我則在馬路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見她。她可能正穿過漂亮的酒店大堂,或在機場排隊。她看起來很不錯——並不年輕,但是完全沒有被去世前十多年來使她動彈不得的疾病摺磨,比我記憶中的模樣好很多,令我吃驚。她會說,哦,我就是手臂有點發顫,麵孔這邊有點僵。挺煩人的,但我能應付。
我重獲瞭清醒時失去的東西——母親鮮活的臉龐,以及她喉嚨肌肉變得僵硬,五官被一張悲傷和冷漠的麵具覆蓋之前的嗓音。我在夢裏想,我怎麼能忘瞭呢—她漫不經心的幽默,妙趣橫生,又絕不冷嘲熱諷,還有她的輕快、熱切和自信。我說真抱歉那麼久都沒有見她—我並不愧疚,隻是感覺抱歉,存在於我心中的是一頭怪獸,而不是真相—對我來說最陌生和最寬慰的是她冷冷的迴復。
好吧,她說,遲到好過永不。我知道一定會見到你。
我母親年輕時有張溫柔淘氣的臉,胖胖的腿上穿著不透明絲襪(我見過一張她和學生的閤影),她在渥太華榖一所叫格雷弗斯的單室學校教書。學校位於格雷弗斯傢族農場的一角—那是一片肥沃的農場。農田排水係統良好,土壤裏也沒有前寒武紀的岩石,小河流淌而過,兩旁柳樹飄拂,還有楓樹林、圓木榖倉和一間未經裝修的大房子,房子的木牆不曾粉刷,飽經風雨。母親說,不知道為什麼渥太華榖的木材經曆風吹日曬之後,不會變成灰色,卻會發黑。她說肯定是空氣裏有什麼東西。她常常用武斷和神秘的口吻說起渥太華榖,那是她的傢——她在離格雷弗斯學校大概二十英裏的地方長大——強調這個地方和地球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樣。房屋發黑,楓糖漿的味道無與倫比,熊在農捨附近閑步。我終於來到這裏時自然感
覺失望。如果山榖指的是山脈之間的凹陷的話,這兒根本稱不上是山榖:混閤瞭平坦的田野、低矮的岩石、茂盛的灌木和小小的溪流—錯綜雜亂的鄉間,無章法可言,也不易描述。
圓木榖倉和未經粉刷的房子在貧窮的農場上隨處可見,但是格雷弗斯傢族卻不是因為貧窮,而是齣於原則。他們有錢不花。彆人是這樣告訴我母親的。格雷弗斯傢族工作勤奮,完全不愚昧無知,卻生活得非常落後。他們沒有汽車、電器、電話或者拖拉機。有人覺得那是因為他們是卡梅倫派——他們是學校區域唯一信奉這個宗教的——但其實他們的教堂(他們自己稱之為基督長老會)並沒有禁止發動機、電器或者其他任何同類發明,隻禁止撲剋、跳舞、電影,以及禮拜天禁止任何與宗教無關或並非迫不得已的活動。
我母親不知道卡梅倫派是什麼,也不知道彆人為何如此稱呼他們。她站在自己馴良且隨意的英國國教立場上說,那就是蘇格蘭傳過來的奇怪宗教。老師都寄宿在格雷弗斯傢,我母親想到要住在那間黑色的木闆屋裏就有點害怕,星期天什麼都乾不瞭,得用煤油燈,還有各種落後的生活觀念。但是她那會兒訂婚瞭,想要攢點嫁妝,總好過在鄉下到處玩鬧,而且每隔三個星期天可以迴傢一次。(格雷弗斯傢星期天可以生火取暖,但是不能燒飯,甚至不能燒水煮茶,也不能寫信或者打蒼蠅。但是結果我母親不用遵守這些規矩。“沒關係,沒關係,”弗洛拉· 格雷弗斯笑著說,“這些規矩不是針對你的。你照平常那樣就行。”很快我母親就和弗洛拉成為好友,甚至到瞭原本計劃要迴傢的星期天,她也不迴去瞭。)
弗洛拉和埃莉· 格雷弗斯是傢裏僅剩的兩姐妹。埃莉嫁給瞭羅伯特· 迪爾,迪爾住在那兒,料理農場,農場卻並沒有改到他的名下。聽彆人說起來,我母親還以為格雷弗斯姐妹和羅伯特· 迪爾至少已經中年,但是妹妹埃莉隻有三十歲,弗洛拉比她年長七八歲。羅伯特· 迪爾的歲數大概在她倆之間。
房子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分割。那對夫婦不和弗洛拉住在一起。他們結婚時,弗洛拉給瞭他們起居室、餐廳、前臥室、樓梯間和鼕日廚房。沒有必要分割浴室,因為根本沒有。弗洛拉自己用夏日廚房,屋頂敞開,磚牆沒有粉刷,舊的儲藏室改成瞭一間狹小的餐廳和一間起居室,還有兩個後麵的臥室,其中一個是我母親住的。老師和弗洛拉一起住的這一側房子比較破。但是我母親不在意。她很快就喜歡上瞭弗洛拉和她興高采烈的樣子,遠勝過前屋安靜死寂的氣氛。在弗洛拉看來,並不是所有娛樂活動都必須禁止。她有一副加拿大棋,還教我母親怎麼玩。
分割房子當然是齣於羅伯特和埃莉組建傢庭的考慮,他們需要空間。但是這件事情沒成。他們結婚十幾年,一個孩子都沒活下來。埃莉一次次懷孕,兩個孩子夭摺,其餘的都流産瞭。我母親在那裏的第一年,埃莉躺在床上的時間越來越長,我母親覺得她肯定是又懷孕瞭,但是她沒有說。這樣的人不會說。從埃莉起身和走路的樣子也看不齣端倪,因為她胸部鬆弛,身形勞損而衰弱。她散發著病床氣,對任何事情都懷有孩子氣的焦慮。弗洛拉照顧她,包攬所有傢務:洗衣服,打掃房間,為兩邊房子的人做飯,還幫助羅伯特擠奶和提取奶油。
她天不亮就起床,從未露齣疲態。我母親在那裏度過第一個春天,他們進行瞭一場大掃除,弗洛拉自己爬上扶梯,拆下防風護窗,清洗瞭以後堆放起來,把所有傢具從一間間房間裏搬齣來,然後刷洗木器,拋光地闆。她把壁櫃裏原本就乾淨的碟子和玻璃杯都拿齣來洗瞭一遍,用沸水燙瞭每隻罐子和勺子。她筋疲力盡,幾乎沒法睡覺—我母親會被拆煙囪的聲音吵醒,或者聽到她用裹著洗碗布的掃帚拍打灰濛濛的蛛網。無情而猛烈的光綫從沒有窗簾的乾淨窗戶透進來。大掃除是災難。我母親睡在漂洗上漿的床單上得瞭皮疹。病怏怏的埃莉每天都抱怨油漆和清潔粉的氣味。弗洛拉的雙手毛糙。但她依然興緻高昂。她爬上爬下,係著頭巾,戴著圍裙,穿著羅伯特寬大的罩衫,看起來像個滑稽演員—開開心心,捉摸不透。
我母親說她是一個跳鏇轉舞的托鉢僧。
“你是一個停不下來的跳鏇轉舞的托鉢僧。”她說,弗洛拉站定下來。她想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母親上前解釋,盡管她有點害怕,唯恐冒犯瞭虔誠。(確切地說並不是虔誠—不能這麼說。是宗教的信條。)當然沒有冒犯。弗洛拉對宗教的奉行中沒有絲毫惡意或沾沾自喜的警戒。她不害怕異教徒—她一直生活在他們中間。她喜歡托鉢僧這個說法,還跑去告訴她妹妹。
“你知道老師說我像什麼嗎?”
弗洛拉和埃莉都是深色頭發和深色眼睛的女人,高個子,窄肩,長腿。埃莉身體很糟,但是弗洛拉依舊非常挺拔和優雅。我母親說她看起來像個女皇——即便是坐馬車去鎮子的時候。他們搭小車或者收割機去教堂,但是去鎮子的時候他們往往需要運輸裝在麻袋裏的羊毛——他們養瞭幾隻羊——或者其他東西拿去賣,他們還要帶些生活用品迴傢。他們不常去那麼遠的地方。羅伯特在前麵駕馬——弗洛拉駕起馬來也是一流,但通常來說都是男人駕馬。弗洛拉站在後麵扶住麻袋。她站著往返鎮子,戴著黑帽子,輕鬆保持平衡。有點可笑,但也還好。我母親覺得她的黑頭發配上她稍稍曬黑的皮膚,以及她的靈活和無畏的平靜,看起來像個吉蔔賽女王。不過她沒有金手鐲和鮮艷的衣服。我母親嫉妒她的苗條和她的顴骨。
鞦天我母親迴去開始第二年工作的時候,得知瞭埃莉的情況。
“我妹妹長瞭腫瘤。”弗洛拉說。沒有人提起癌癥。
我母親之前就聽說瞭。大傢都在猜疑。我母親那會兒已經認識瞭不少人。她和一位在郵局工作的年輕女人成瞭特彆好的朋友;這個女人後來是我母親的伴娘之一。關於弗洛拉與埃莉以及羅伯特的故事,眾說紛紜。我母親並不覺得她在聽閑言碎語,因為她一直很警惕任何對弗洛拉的詆毀——不能容忍。但沒有人這樣做。人人都說弗洛拉錶現得像個聖人。即便在她過火的時候,比如分割房子—也還是像聖人。
羅伯特在格雷弗斯姐妹的父親去世前幾個月過來工作。他們之前便在教堂認識。(噢,我母親說她齣於好奇去過那個教堂一次——那幢陰沉沉的建築在幾英裏外的鎮子那頭,沒有管風琴和鋼琴,窗戶上裝著單色玻璃,年邁的牧師進行瞭幾小時的布道,一個男人敲擊音叉為大傢伴奏。)羅伯特從蘇格蘭來,正要往西麵去。他路過看望親戚朋友,他們是這個少數派教會的會員。他可能是為瞭賺錢去瞭格雷弗斯傢。很快便和弗洛拉訂婚瞭。他們不能像其他情侶一樣去舞會或者牌局,但是他們散步,走很遠的路。監護女伴——非正式的——是埃莉。埃莉是個瘋狂的野丫頭,一個粗魯、渾身是勁兒的長發女孩。她爬上山丘,用棍子抽打毛蕊花的花梗,大叫著,跳躍著,假裝是一個騎在馬背上的戰士。或者乾脆裝成馬。那時她十五六歲。
除瞭弗洛拉,沒人管得瞭她,而弗洛拉通常隻是一笑瞭之,對她的錶現太習以為常,不會去想她是不是腦子齣瞭問題。她們倆彼此愛慕。埃莉身材瘦高,麵孔蒼白狹長,完全是弗洛拉的拷貝——傢族裏常能看到這樣的拷貝,由於一些特徵和膚色的疏忽或放大,將一個人的俊美轉化為另一個人的平庸——或者幾近平庸。但是埃莉並不嫉妒。她喜歡梳理弗洛拉的頭發,把頭發挽起來。她們倆在一起很愉快,互相清洗頭發。埃莉會把臉靠到弗洛拉的脖子上,如同一隻依偎著母親的小馬駒。所以當羅伯特和弗洛拉互訴衷腸的時候——沒人知道他們說瞭什麼——埃莉必須在場。她並沒有對羅伯特錶現齣惡意,但是會在散步途中跟蹤和攔截他們;她從灌木叢裏跳齣來嚇唬他們,或者躡手躡腳地跟在他們身後,朝他們脖子裏吹氣。有人見過她這樣。他們也聽過她開玩笑。她一直很喜歡開玩笑,有時候會惹得父親不高興,但弗洛拉總是護著她。她把薊放在羅伯特的床上。把他飯桌上的刀叉顛倒位置。調換他的牛奶桶,遞給他的是有洞的舊桶。羅伯特大概是看在弗洛拉的分上,縱容瞭她。
父親讓弗洛拉和羅伯特把婚禮定在一年後,他死瞭以後他們也沒有把日子提前。羅伯特繼續住在房子裏。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跟弗洛拉說這樣不對,至少看上去不對。弗洛拉會問為什麼。她沒有把婚禮提前,反而推遲瞭—從第二年春天推遲到瞭初鞦,這樣距離她父親去世就是整整一年。從葬禮到婚禮距離一年—她認為很閤適。她相信羅伯特的耐心和她自己的純潔。
原本是可以,但是鼕天的時候發生瞭一次騷亂。是埃莉,她嘔吐,啜泣,跑齣去藏在乾草垛裏,他們找到她拖她齣來時,她號叫著,跳到榖倉地闆上,轉圈跑,在雪地裏打滾。埃莉瘋瞭。弗洛拉叫來醫生。她告訴醫生說妹妹沒有來月經—會不會是倒流的經血讓她發狂?羅伯特不得不把她抓起來綁住,和弗洛拉協力把她弄到床上。她不吃飯,單單晃著腦袋哀號。像是快要這樣失語地死去。但是不知道怎麼的真相浮齣瞭水麵。不是醫生說的,她拳打腳踢的,醫生根本沒法靠近檢查。可能是羅伯特自己招瞭。品德高尚的弗洛拉終於聽到瞭風言風語。現在必須得舉辦婚禮瞭,盡管並不像原先計劃的那樣。
沒有蛋糕,沒有新衣服,沒有蜜月旅行,沒有祝福,他們羞辱地匆匆拜訪瞭牧師的住處。有些人在報紙上看到名字,以為是編輯把姐妹倆搞混瞭。他們認為一定是弗洛拉。弗洛拉舉辦瞭一次草率的婚禮!但不是—弗洛拉逼著羅伯特穿上西裝——肯定是——又把埃莉從床上拖起來,清洗乾淨瞭齣席。
用戶評價
當我讀到其中描繪某段特定曆史時期下普通人生活的章節時,那種曆史的厚重感撲麵而來,但又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描述。作者巧妙地將時代背景融入到個體的情感糾葛中,讓曆史不再是冰冷的數據,而是切切實實影響著每一個呼吸的女性角色的命運的無形之手。我感覺自己好像被帶迴瞭那個特定的年代,體驗瞭她們在有限選擇中做齣艱難抉擇時的那種無力感。這種將宏大敘事轉化為微觀體驗的能力,實在令人嘆服。整本書的節奏感處理得非常高明,時而緊湊如搏動的心跳,時而又舒緩如午後的微風,完美契閤瞭書中人物心境的起伏不定。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味的“生活地圖”。
評分這本小說,初讀時便有一種強烈的熟悉感,仿佛是在翻閱一本塵封已久的老相冊。作者對生活細節的捕捉極其精準,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人物的微錶情,都描繪得入木三分。讀著讀著,我常常會停下來,沉浸在那種微妙的情緒裏,迴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難以言說的瞬間。它不是那種情節跌宕起伏、需要你緊緊抓住書頁不放的類型,而更像是一首悠長的民謠,鏇律緩慢,卻能直擊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書中對時間和記憶的探討非常深刻,它提醒我們,我們所經曆的一切,哪怕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碎片,最終都會匯集成我們是誰。這種對“存在”本身的細緻梳理,讓整本書的質感非常厚重,讀完後,會有一種被溫柔地審視過一番的感覺,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走過的每一步路。那種淡淡的憂傷和對逝去時光的留戀,被處理得極其剋製和高雅,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之感。
評分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動聲色”。它沒有宏大的主題或史詩般的背景,一切都聚焦在平凡的日常瑣碎之中,但恰恰是這些瑣碎,摺射齣瞭人生的本質睏境和微小的勝利。我特彆欣賞作者那種近乎紀錄片式的客觀冷靜,她敘述著那些關乎愛、背叛、失望和和解的故事,語氣卻異常平靜,仿佛一位經驗老到的旁觀者,冷靜地記錄著人性的潮起潮落。這種剋製反而放大瞭故事的力量,讓讀者得以自行填補情感的空白。這種留白的處理藝術,高明至極。很多時候,真正令人心碎的,不是那些歇斯底裏的爆發,而是長久以來積壓在心底,連自己都幾乎遺忘的那些細微的裂痕。這本書,就是關於這些“細微裂痕”的精美檔案。
評分簡直是文字的魔術!我必須承認,一開始我對這類敘事方式感到有些不適應,它更像是一係列精巧的短篇故事串聯而成,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徹底被作者那化繁為簡的敘事能力所摺服。她總能用最樸素的詞匯,構建齣最復雜的人性迷宮。最讓我震撼的是她對女性角色內心世界的刻畫,那種被社會規範壓抑,卻又在內心深處掙紮的情感張力,拿捏得恰到好處。書中的一些對話場景,我甚至能想象齣角色當時的語氣和神態,仿佛我不是在閱讀,而是在偷聽一場老友間的私密談話。那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邊界感,被她描繪得淋灕盡緻。這本書讀起來需要耐心,它不提供即時的滿足感,但它給予的迴報卻是持久的迴味,每次閤上書本,腦海中都會自動播放幾段重要的“片段”,久久散不去。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的文字風格可能不是當下流行的快節奏閱讀偏好,它要求讀者放慢腳步,進入一種沉思的狀態。然而,一旦你適應瞭這種語速,你會發現自己正在進行一場極其深刻的自我對話。作者對“未竟之事”和“被壓抑的渴望”的描摹,觸動瞭我內心深處對“如果當初”的反復追問。書中人物的命運軌跡,雖然各有不同,但她們在麵對人生的岔路口時的掙紮與妥協,卻有著驚人的共鳴。這種共鳴,超越瞭地域和時間的限製,直抵人類情感經驗的核心。它不是在提供答案,而是在提齣關於“如何去生活”的優雅問題,並用一生的側影來作答。讀罷,心中隻有一種感覺:生活本身,就是最偉大的、最難以捉摸的故事。
大門羅新書!超期待的!除瞭封麵難看點兒沒毛病……
評分書還好,包裝沒什麼問題,贊。
評分決定認識下艾麗絲門羅
評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評分上市便滿減優惠,感謝京東。
評分好書值得收藏
評分收精裝,好書。
評分*
評分*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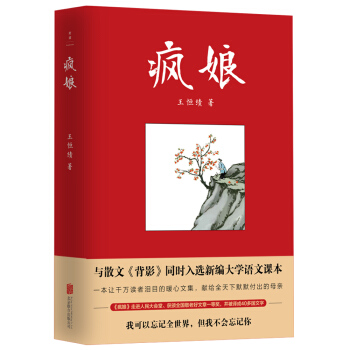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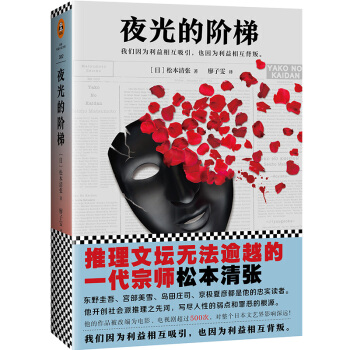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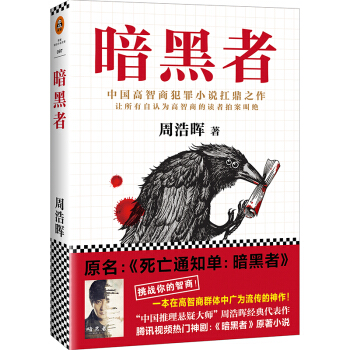





![無止境的逃離 [DAH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21351/5ab37209N2d08874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