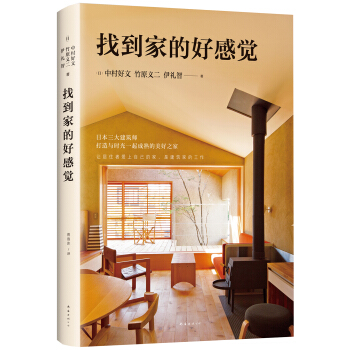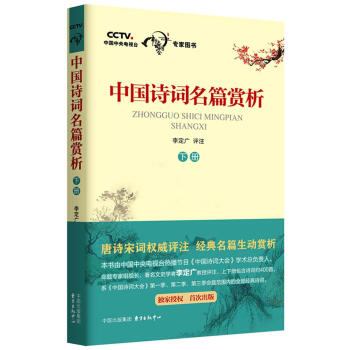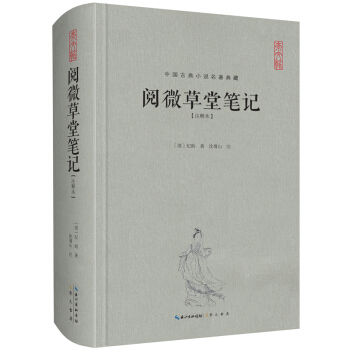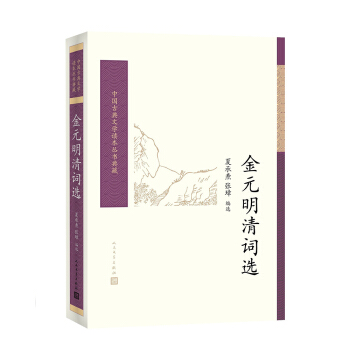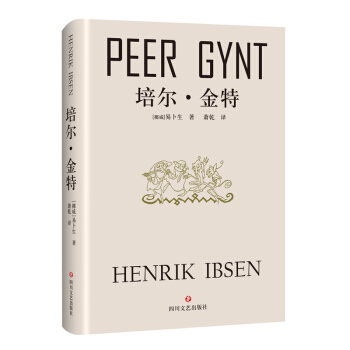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近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代表作,开创文学新时期。以诗的语言写作剧本,剧中讽刺与夸张传神,发人深思。
翻译文本语言优美,完美体现翻译大师大师对于“信达雅”的掌控。
内容简介
《培尔·金特》是挪威著名的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具有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译者是著名翻译家萧乾。《培尔·金特》通过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探索了人生是为了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重大哲学命题。作者简介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曾长期担任剧院编导,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战争爆发后长期侨居罗马等地。内页插图
前言/序言
译者前言一
第一次在伦敦中心区一家剧院看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外面还响着警报。纳粹的轰炸机正在头上盘旋——说不准那是一九四几年的事了。剧院经理按照市政当局的规定,先把幕落下来,然后向观众宣布:凡愿暂避一下的,可以退场。当时剧场里动静不大,一方面是出于观众对纳粹的蔑视,同时也由于戏的确有吸引力。旅英七年,戏我没短看:歌剧、莎剧、话剧,甚至圣诞节为孩子们演的“哑剧”。然而没有一出戏曾那么整个地攫住我的心灵。那以后,我还在剑桥收听过两次此剧的广播。每次接连近几个钟头哪!然而我总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一气听到底。
从那以后,我有时就在思想里把这个剧本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比如1948年至1949年,像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我也在考虑思想改造问题。那时我就把《培尔·金特》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并且在我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1949年8月15日)上以整版篇幅写了篇《培尔·金特——.一部清算个人主义的诗剧》,其中有一段涉及我对此剧主题的理解:
在所有的戏里,易卜生都要我们忠于自我,殉道者般地坚持自我。在这部诗剧里,他却告诉我们说:“我是军队,里面排列着愿望、食欲和贪婪。我是海,里面浮着幻想、索取和期待。”他告诉我们:“要保持自我,就先得把自我毁灭了。”没有比这更不像易卜生的了!然而《培尔·金特》这个寓言讽刺剧所抨击的,自始至终是自我。
当时我对思想改造的理解,就是个人主义的克服,因而也就把《培尔·金特》这个诗剧理解为对个人主义的清算。这当然是很肤浅,很不全面的。
1978年为《世界文学》(内部发行)译完此剧第一及第五两幕后,在写前言时,我又把它同十年浩劫时期的风派人物联系起来了。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这部诗剧笔势纵放,内容着实庞杂;然而全剧还是有一个前后呼应、贯串始终的主题,即人妖之分。易卜生认为做个“人”,就应保持自己的真正面目,有信念,有原则,不投机取巧,不见风使舵;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原则,什么苦头都准备吃,什么侮辱都准备受。那个剁掉自己指头的人也可以说就是《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的雏形。“妖”则无信念,无原则,蝇营狗苟,随遇而安;碰到困难就“绕道而行”,面临考验就屈服妥协。他掂斤拨两,看事物只凭利害,不讲是非。他八面玲珑,处处“适可而止”。为了娶上妖女,他可以安个尾巴;在群猴围攻下,他不惜巴结老猴王。但他越是自我扩张,侵人自用,他就越失掉自己的本来面目。这种人进了铸勺,铸成纽扣也还是废品——没有窟窿眼儿!
在理解一部古典作品时,会受到当时心境的影响,这是难免的。然而这毕竟不是诠释一部作品的正途,因为它不完全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有些借题发挥。
1880年5月,当此剧德文本译者卢德维希·帕萨尔格写信问起《培尔·金特》的主旨和作者构思经过时,易卜生在同年6月16日从慕尼黑写的回信中没做正面的阐述。他说:“要把那个说清楚,我得另外写一本书,而时机尚未到来。”接着他又说,“我笔下的一切,虽然不一定都是我个人经历的,却都与我心灵所感觉到的有着密切关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类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净化,因为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因此,我曾经在一本书里写下这样的题词:‘活着就是要同心灵里的山妖战斗,写作就是坐下来对自己作最后的评判。’”
易卜生始终也没写出“另外”那本书。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这个五幕三十八场幻想、象征、寓言、哲理诗剧的中心思想,众说纷纭,有些易卜生研究者中间甚至存在着“不可知论”。例如蒂龙·格斯理在为英国1944年演出本写序言时就说:“这个戏只能凭各人主观去解释,这个人同那个人的解释可能完全不同,而二者又可能都正确。”R·法夸尔森·夏普在为《万人丛书》版英译本所写序言中说:“剧中有哲理,但它主要不是哲理诗;剧中有讽刺,但它主要不是讽刺诗,而是个幻想曲。”
易卜生本人认为,这个戏出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不大可能为人们所理解了。但是他的英国私塾弟子萧伯纳显然不以为然。1896年他在伦敦《星期六评论》(11月22日)剧评栏中写道:“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这个剧本的普遍意义,在所有国家中都必昭然若揭。”
我很同情那位德文译者,因为这个戏倘若不大致掌握住它的中心思想,首先翻译上就有困难。这两年,特别是1979年出国时,我曾留意国外有关《培尔·金特》的著作。同时,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年轻汉学家依利莎伯·艾笛女士也曾热情地帮我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有些评论家(如比昂逊)认为易卜生写这个诗剧,用意主要在于讽刺、抨击挪威国民性中的消极因素,如自私自利,回避责任,自以为是,用幻想代替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培尔·金特就是挪威的阿Q。
关于人妖的问题,有的学者(如《现代文学中的灵的声音》的作者特雷弗·戴维斯)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认为越是忠于自己的,越要否定自己。反之,越是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越不会得到满足。到头来只会毁灭自己。还有的学者是把人妖这么分的:人要忠于自己的原则理想,这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而妖所遵循的,则是利己主义(egoism)。
总之,易卜生这部诗剧的主人公一生都在两种哲学、两种做人的方法、两条道路中间徘徊、斗争。在这一点上,它比易卜生后来写的社会问题剧探索得也许更为深刻、大胆,更具有超过时间空间的普遍意义。这可以说是一出以人生观、世界观的抉择为主题的戏,然而写得生龙活虎,一点也不沉闷。
二
1862年,易卜生在一次徒步旅行中,偶然听到培尔·金特这个名字。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叶,确实有个叫这个名字的农民住在古德布兰斯达伦地方。这个人物形象在易卜生的头脑里足足酝酿了九年。1867年1月他才动笔写此剧。同月5日,他在给知友黑格尔的信中说:“我正在开始写一个新剧本,如果一切顺利,今夏即可完成。它将是一个长篇诗剧,主人公一半出自传说,一半出自虚构。它将和《布兰德》很不同。剧中不会有什么议论。这个主题在我心中酝酿已久了。我现在正写第一幕。写成之后,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请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同年3月,他又写信给黑格尔说,已写完第二幕。5月2日又去信说:“全剧轮廓已经异常清楚了。”说明写此剧之前他虽已酝酿了很久,动笔时还是让剧情凭着奔放的想象来发展。最后一幕写了25天,在同年10月14日完成的。当时,易卜生正侨居在罗马附近一个小镇上。
易卜生在信中提到的《布兰德》,是他的另一部剧作。两个作品是紧接着写的,而且都是五幕诗剧。1865年11月易卜生写完了《布兰德》,仅仅过了五个星期,他就动手写《培尔·金特》了。
然而这两部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大不相同。《布兰德》在结构上相当谨严,行文也较平稳。除了那个看不见的唱诗班和最后一幕中的幻象,全剧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空间,它始终也没离开挪威西部一道狭窄阴暗的峡弯和附近的山峦,时间则不出五年。
同一支笔,写《培尔·金特》时则如野马奔腾,走笔若飞。作者像是把亚理士多德以来欧洲戏剧结构那些条条框框全抛在九霄云外了。全剧确实如一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背景忽而遍地石楠花的挪威山谷,忽而西非摩洛哥海滩,一下子又来到撒哈拉大沙漠,来到埃及,最后又回到惊涛骇浪、暗礁四伏的挪威峡湾。全剧迷离扑朔,时而是现实生活(山村婚礼),时而又飘进童话世界(山妖宫殿)。这些变化使全剧充满了动与静、光与暗的强烈对照,也为舞台设计家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
更强烈的对照还是布兰德和培尔·金特这两个人物。前者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想主义者,后者则是个没有原则,不讲道德,只求个人飞黄腾达,毫无理想的投机者,一个市侩。
然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却同为一个问题所困扰着:人怎样才能忠于自己。
19世纪中叶,像培尔·金特这种经历,在欧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挪威农业经济濒于解体,像培尔那样离乡背井,到海外(新大陆或非洲)去撞大运的人,是很常见的。
这个人物绝不仅仅是个坏蛋。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不务正业,胡作非为,可是在他妈妈弥留之际,他佯作驾着马车送她去天堂赴宴那一景,确是感人!他放荡极了,几乎见了女人就没命,不管是山村的新娘,是妖女,还是沙漠酋长的姑娘,他都要捞上一把;然而他真正爱的,却是那位圣洁的索尔薇格。对她的追求和崇敬,代表着培尔灵魂中善的一面。他拒绝英格丽德的爱,就是因为她不具备索尔薇格的圣洁。当索尔薇格背弃家庭到山里去找他时,培尔自惭形秽,不敢接受她。分手时,他要求索尔薇格永远等着他,无论多久。索尔薇格没辜负他这个请求。易卜生写到最后,可能也为这对恋人的离合所感动了。他仿佛让培尔在索尔薇格忠贞不渝的爱情中,得到了拯救。
《培尔·金特》出版后,评论家比昂逊立即写信给易卜生说:“我爱你在剧中发的脾气,我爱那股愤怒给你的勇气。我爱你的精力,你的怔忡不安。啊,你的剧本使我由衷地发出笑声,就像久居一间憋闷的病室里闻到了海的气息。”信末,他还说,“这只是一封表示爱慕的信。易卜生,你的《培尔·金特》真是辉煌伟大,只有挪威人能了解它有多么好。”
其实不然。1981年,法国青年导演帕特利斯·谢罗认为这个剧本是“一个遗失了的大陆,一个星球,一个纪念碑式的巨作,写得深刻而富有启发力”,以至使他产生了一种“非把它原原本本地搬上舞台不可的迫切感。一种压倒一切的强烈愿望“a。他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望。
然而这样一部抨击了挪威生活种种方面的作品,也不
能不激怒一些人。有些人甚至怀疑易卜生写的不是诗。这下易卜生发火了。他愤然反击说:“我这个戏就是诗。如果它不是,那么它将成为诗。挪威将根据我这个戏来树立诗的概念。对我做的那些不公正的抨击,使我感到高兴。愤怒将给予我更大的力量。如果非交战不可,那么就开火吧。如果说我不是诗人,那无损于我一根毫毛!”
从易卜生对此诗剧的捍卫,可以看出他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并且对它是信心十足的。
除了主题思想,《培尔·金特》的技巧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方面。挪威的B.J.提斯达尔写了一本书,题名《乔伊斯与易卜生》(挪威大学联合出版社1968年版),其中引用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1907年的一段日记,证明乔伊斯在写他的巨著《尤利西斯》时,曾说要把那部心理小说的主人公写成都伯林的培尔·金特。事实上,《培尔·金特》中那大段大段的独白确实赤裸裸地刻画出培尔在各个阶段、不同场合的心理活动。剧中有些场景,特别是妖宫、开罗疯人院和第五幕中那个陌生人的出现,可以说把一些潜伏在人物下意识中的憧憬和噩梦搬上了舞台。难怪有的学者(如《易卜生:分裂的意识》一书的作者查尔斯·R.里昂)把此剧看作是意识流派文学的先驱。
据说易卜生在写《培尔·金特》时,由于感情奔放,不想受舞台技术的限制,根本没考虑上演问题。事实上,此剧出版九年后,也即是1876年,作者应挪威国家剧院之请,对剧本做了删节后才搬上舞台的。著名挪威作曲家艾德华·格里格(1843—1907)为该剧的首次公演谱写了《培尔·金特组曲》。有些评论家认为格里格的组曲同诗剧配合得不好,但那组组曲至今仍是西方乐坛上脍炙人口之作。
挪威之外最早的演出为1886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英语世界于1909年10月29日,在美国芝加哥的歌剧院首次公演。
这个诗剧的生命力真是强得惊人。笔者在写此文时,看到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80年10月24日)上登着对此剧1980年10月初在大学城牛津演出的评论,舞台脚本是由艾德里安·米奇尔根据卡林·班包罗的英译本改编的,作曲者得尼克·比凯特。妖宫一幕配的是摇滚乐!1981年5月萧曼同志在法国又看到了全本《培尔·金特》的演出,那的确是一番壮举。
三
自从在伦敦看了那次演出后,我就留意搜集《培尔·金特》的英译本。20世纪50年代初,一次叶圣陶先生召宴,席间有潘家洵先生。我曾问他有没有翻译这个戏的计划,并竭力怂恿他把它译出来。潘先生居然被我说得兴致勃勃起来。事后,我就亲自把我所藏的四种英译本送到他在未名湖东大地的寓所。这大约是1956年初的事,转年我就跌入深渊,再也没见到他或任何文艺界友人了。
1973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回京后,冯宗璞同志告诉她的同窗文洁若,说潘先生正在到处打听我,并托她把一包书转交我。打开一看,正是《培尔·金特》的那四个译本。随后不几天,当我正在东直门那间阴暗、潮湿的门洞里挥汗赶译着《拿破仑论》时,忽然听到有人叩门。哎呀,八旬的潘老先生拄着拐杖走进我那间寒舍了。他微喘着气说:“来向你道歉的!”意思是17年前他答应把《培尔·金特》译出来,他爽了约,交了白卷。
1978年,大地逐渐转暖了,暖到使我从鬼又重新变成了人。多年不往来的朋友又敢见面了。这时,《世界文学》的邹荻帆同志来找我译点什么。我真是受宠若惊,因为我早已被编入翻译大队,与文学翻译绝了缘。好在那时的《世界文学》还是内部发行。当时全家只有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桌角上正堆放着潘先生退回的《培尔·金特》英译本。经刊物编辑部首肯后,我就着手翻译起来。
我显然不是这部名作的理想译者。当时为什么冒昧地自告奋勇呢?我想,一是一场浩劫之后,那时除了《培尔·金特》,我手边没有旁的文学书可译。那个时期,我接触的都是些国际政治方面的书。其次,我确实多年来希望这部作品能和我国读者见面。潘先生退回来,我再也没旁处可送了。于是,就干脆自己来试它一下。
当然,我只能用散文来译。我对于诗歌向来一窍不通,与其把它糟蹋成洋快板,不如先让它朴朴素素地与我国读者见面。除了剧中个别短歌外,译用的一律是大白话。译短歌时曾得到孙用及屠岸两位同志的帮助。希望将来有诗人——特别是懂挪威文的诗人,用韵文来译它。
目前这个译本主要根据的是诺曼·金斯伯里1944年的演出本(1946年伦敦出版),同时参阅了《万人丛书》《蓝带丛书》以及最早的威廉·阿切尔的英译本。
用户评价
读完《培尔·金特》这部史诗般的巨作,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横跨人生、地理、文化乃至哲学的大冒险。亨利克·易卜生这位剧坛巨匠,用他那如椽巨笔,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中主人公培尔·金特的人生轨迹,既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想象,又蕴含着对人性深邃的洞察。我被深深吸引,沉浸在他那不断追逐虚幻的梦想、逃避现实的纠缠,以及最终在人生暮年回首时的迷惘与顿悟之中。每一次翻页,都像是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挪威的雪山到摩洛哥的沙漠,从奴隶市场到疯人院,培尔·金特的足迹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象征着他不断膨胀的野心和永不满足的欲望。他是一个多面体,既有世俗的狡黠,又有浪漫的幻想,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每一次的“出逃”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境遇,而每一次的“回归”又似乎带不走一丝真正的慰藉。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也极具特色,既有诗意的抒情,又有辛辣的讽刺,易卜生巧妙地将现实主义的描绘与象征主义的手法融为一体,使得这部剧作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培尔·金特那永不停止的自我欺骗和自我辩解,仿佛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部分不安的投射,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评分《培尔·金特》读罢,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息。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戏剧,不如说是一面照妖镜,折射出人性的各种 G;,甚至是扭曲。培尔·金特这个角色,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寻找”,寻找财富,寻找地位,寻找所谓的“真我”,但他所做的,却一直是“拆毁”和“逃离”。他是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用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和一颗狡猾的心,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却始终无法找到那个最真实、最安稳的落脚点。我被书中对社会百态的描绘所震撼,从挪威的乡野到埃及的金字塔,再到美国的大陆,易卜生用辛辣的笔触,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培尔·金特,就像一个穿梭于这些人群中的幽灵,留下的是一片狼藉。然而,最让我动容的,是索尔维格的爱,她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苦难,她依然在那里,等待着那个永远无法真正“归来”的培尔·金特。这部作品的结构之巧妙,语言之凝练,都让我叹为观止。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仿佛这本书记载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
评分初读《培尔·金特》,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其宏大的叙事结构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易卜生似乎拥有某种魔力,能够将一个人的传奇一生,如同史诗般地铺陈开来。培尔·金特这个角色,可谓是复杂至极,他的人生轨迹如同狂风卷起的落叶,四处漂泊,却又似乎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引。书中描绘的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年轻时的狂妄不羁,中年时的精明算计,晚年的疲惫不堪。他渴望成为“帝王”,渴望活出“真我”,但这种渴望,却常常被他的虚荣和短视所扭曲。我尤其被他与生命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之间的互动所吸引,奥赛、英格丽德、索尔维格……每一个女性都如同他人生中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不同侧面的特质,也揭示了他情感上的缺失和逃离。索尔维格这个角色,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她的坚守和爱,成为了培尔·金特一生中唯一不曾被他玷污的纯净之地。这部作品的魅力,还在于它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讽刺,从腐败的官场到虚伪的宗教,易卜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人性的阴暗面。每一次读到他与其他角色的对话,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智慧和力量。
评分《培尔·金特》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品尝一杯陈年的烈酒,初入口时可能有些辛辣,但回味却悠长而深刻。易卜生并没有刻意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英雄,相反,他笔下的培尔·金特是一个充满缺点、充满挣扎的普通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些令人讨厌的家伙。他自私、贪婪、善变,为了自己的欲望,可以毫不犹豫地伤害他人,抛弃亲情和爱情。然而,正是这种赤裸裸的人性展现,反而让我看到了最真实的生命力。他的一生,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是逃避。逃避责任,逃避平庸,逃避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他不断地用华丽的谎言和虚幻的成就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身份切换到另一个身份,但始终找不到内心的宁静。这种“不着边际”的人生,却在某个层面上呼应了现代社会许多人的困境:在物质充裕的时代,精神却日益贫瘠,我们渴望“不同”,却又被“不同”所裹挟,迷失了方向。剧作的结尾,那个“钮扣”的比喻,简直是神来之笔,将培尔·金特一生的追寻与意义做了一个既戏谑又充满哲思的总结。我反复琢磨,这本书带来的思考,远不止于对一个虚构人物的评判,更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审视。
评分《培尔·金特》这部作品,带给我的震撼,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绵延不绝的感受。我常常在想,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够承载多少的漂泊和追寻?培尔·金特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在路上”的故事,他试图从一个境遇逃向另一个境遇,从一个身份跳向另一个身份,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空虚和无根感。易卜生通过极富想象力的情节设置,将培尔·金特的人生经历描绘得如同神话般传奇,却又充满了现实的苦涩。我对他每一次的“冒险”都感到既好奇又心悸,他时而像一个成功的商人,时而又像一个被欺骗的傻瓜,这种落差感,让人不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书中关于“自我”的探讨,尤其发人深省,培尔·金特一生都在寻找那个“真正的自我”,但似乎他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那些象征性的情节,比如他在地中海遇到的人们,以及他最终遇到“形迹不明者”的场景,都充满了哲学意味,引人深思。我读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读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对话,一场与内心最深处自我的对话。
评分物流速度快 快递员服务好 商品包装完好 价格优惠 图书内容很有思想值得一读 好评
评分感谢京东,物流很快质量好。本书是塞尔努达1924~1938流亡早期前诗,内容丰富翔实,主旨丰沛,各种风格长短句的锻炼,充盈的欲望矛盾,对各种经典的引伸指摘,非常好读,推荐大家购买
评分乔治,巴塔耶的诗歌全集。。。精装。非常不错
评分特朗斯特罗姆第一次授权简体中文全集,收录了诗人从1954年至今创作的《17首诗》《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等13部诗集近200首诗歌,囊括了特朗斯特朗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
评分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多诗选,还是外国的诗?
评分京东的服务比当当好多了,尤其是退换货,就是优惠活动99块10本,京东买书很划算!都是自己喜欢的!而且物流超快啊!!!
评分哈代的诗冷峻、深刻、细腻、优美,言简意赅,自成一格,较他的小说更具现代意识。
评分書品很好,物流也快。謝謝京東!
评分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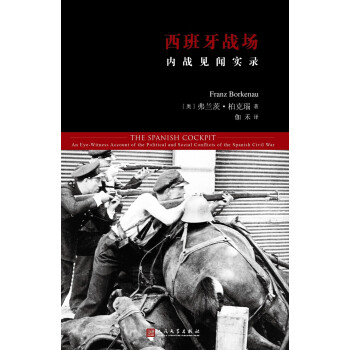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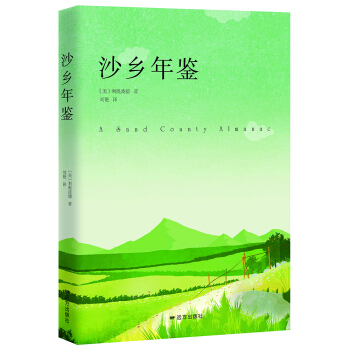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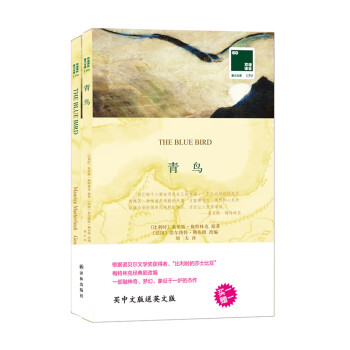
![染匠之手(奥登文集) [The Dyer's Han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98453/5abe2d53N1bb1854c.jpg)